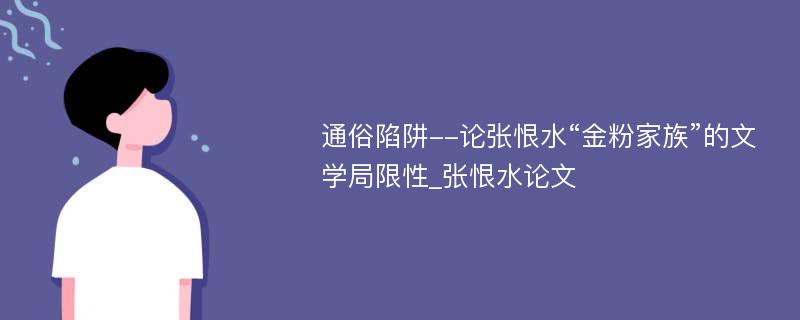
通俗的陷阱——论张恨水《金粉世家》的文类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粉论文,通俗论文,世家论文,陷阱论文,张恨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文学史上,《金粉世家》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在它写作、刊出之初,社会反响十分热烈,而其后半个世纪里,研究者又似乎忘记了它的存在,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集体对它保持了沉默。改革开放以来,在“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下,学界对此书的评价又有戏剧性变化。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评价变化之大有如霄壤。而其中有些意见涉及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如有评论者撰文称:“《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①这种看法至今仍有一定影响,因此有必要分说、厘清一番。
《金粉世家》是一部颇具典型意义的通俗文学作品。这样讲,并非要贬低其价值,而是要更准确地认识它的属性与特征。《金粉世家》是张恨水为《世界日报》的副刊《明珠》写的连载,自1927年2月14日开始,一直到1932年5月22日,“约可六年”,“凡八十万言”。而在此前后,他还同时为《北京新晨报》、《新闻报》、《新民晚报》等多家报纸撰写连载小说。毋庸讳言,这既有其创作精力旺盛的原因,也不排除利益驱动的因素。
作为报载小说,《金粉世家》无疑是成功的。几年间始终处于洛阳纸贵的地位,报纸与作者都是名利双收。推究其成功的原因,迎合普通民众的心理,当是重要原因。
首先是故事层面,《金粉世家》具备了一般通俗言情文学的基本要素:美女的命运起伏,俊男靓女之间的三角恋爱,富贵人家的生活状况与家庭矛盾,爱情中的“公子”负心,等等。从故事的主线说,《金粉世家》演绎的是一个“灰姑娘”——冷清秋的故事,不过她是一个开端幸运而最终失败的“灰姑娘”。这种“才女薄命”之悲加上一度的“灰姑娘”之幸,跌宕起伏,足以引起多情而无聊的市民读者唏嘘不已的关注,也适于在大众传媒上作长篇连载的故事题材。
其次,作者多年的记者生涯,养成了善于观察、长于描摹的本领。小说在家庭内容之外,或多或少掺杂了一些类似“黑幕”的笔墨,从而满足了普通读者不满现实的心理。如官场的因循苟且,社会的世态炎凉等。
张恨水的记者生涯也养成了对于社会风气、潮流的敏感。《金粉世家》之走红,有一种社会现象值得关注。在那个时代,一般市民的艳羡富贵心理可从当时所谓“京城四公子”之说的流行窥见端倪。“京城四公子”称谓产生于北洋军阀时期,是当时四位声名显赫的政界军界显贵之后,后来版本多有演化,几乎成为显贵风流子弟的泛称。各层次的人们或啧啧称羡,或品论其高下,作为社会热点话题,几历十余年而不衰。《金粉世家》是以北洋军阀时期某国务总理的两位风流“公子”(金燕西与金凤举)为男主角的作品,可以说其创作动因与“四公子”之说的被追捧不无关联。《金粉世家》用大量笔墨铺陈渲染富贵生活,如阔少们逛妓院、捧戏子、吃喝玩乐的场面,并非都是“主题”(假如有这样一个思想性的“主题”的话)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大众艳羡富贵心理的迎合。
此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张恨水“新旧杂糅”的思想观念。《金粉世家》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社会观念、家庭观念游走于“新”“旧”之间,既反映出清末民初以来“西学东渐”、社会变革以至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新观念,却又在很多问题上持守传统立场,如对于婚姻制度,一方面大讲西方世界一夫一妻的好处,讲多妻制带来的麻烦与痛苦,可另一方面又以欣赏的态度讲述贤惠大度的妻子金道之如何包容小妾,甚至助成丈夫把小妾带入家庭。又如一方面大讲男女平等,一方面又站到男性的立场上揭示女性“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之类的“毛病”等。如果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这种摇摆甚至混乱肯定会引起读者的质疑。但作为报纸副刊连载的通俗之作,这种“新旧杂糅”反而有利于扩大读者的范围。
对封建大家庭的批判,是清末民初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以贯之的话题。对大家庭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论者、作者的思想倾向。
《金粉世家》描写了金铨大家庭的盛衰。金铨的家庭包括他的三个太太、四个儿子与四个女儿;故事开始时,子女中有四个已经结婚,仍然住在一起;随着故事进展,又有一个儿子结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包括了五个核心家庭的大家庭。大家庭中,有三个小家庭是多妻的;八个子女中,七个嫡出,一个庶出。可以说,中国封建大家庭的要素几乎齐备。这种情况前可以比《红楼梦》,后可以比《家》、《京华烟云》与《四世同堂》。但作品所表现的家庭观念,彼此却有大相径庭之处。
《金粉世家》对待大家庭有明确批判的一面。这既可以从作者设计的金家“树倒猢狲散”结局、从作品描写的大家庭里那些无谓的鸡吵鹅斗之中透露,也可从书中人物的一些直接有关的议论中看出②。但是,张恨水对于大家庭制度的批判基本是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亦即“兄弟阋墙,孔方作祟”的水准。如金鹏振议论到分家所讲:“本来西洋人,都是小家庭制度,让各人去奋斗,省得谁依靠谁,谁受谁的累,这种办法很好。作事是作事,兄弟的感情是兄弟的感情,这决不会因这一点,受什么影响。反过来说,大家在一起,权利义务总不能那样相等,反怕弄出不合适来哩。”(八十一回)引据西方制度看似很深刻,但其实类似这样的认识,中国古已有之(在古代社会,多数的“大家庭”到第二代各有家室后也是要分炊另过的)。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对于传统大家庭的批判早已超越了这一层次,不少先觉之士更进一步从“父权”与“专制”的角度,深入到大家庭权力结构之中,就其对家庭成员人格的压制扭曲进行剖析。如陈独秀1915年12月发表于《青年杂志》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所论:“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
而《金粉世家》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激进”的观念,它对待大家庭总体的态度还是“温情脉脉”的。这种基本态度集中表现在对大家长金铨形象的塑造上。金铨出场不多,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正面的,如对冷清秋的婚事,毫无门第俗见;评骘冷清秋的诗作,不乏真知灼见,显示出其确有真才实学;对子女的态度——三个女孩子全部送出国留学,对男孩子也是恨铁不成钢,但并不滥用威权。即使在小事情上,这个形象也是颇为通达,甚至可亲可爱的。如三十回,金燕西做寿,金铨走来凑趣,身为国务总理,不摆架子,不使威风,对丫环仆妇竟说出“平等”、“解放”的话来。且不论对于今天的读者,这一形象的真实感如何,只就文本传达出来的信息而言,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的形象,这个“父亲”的形象却是威严中透着慈祥,严肃中兼有通达,是相当正面的。小家碧玉冷清秋嫁入“宰相府第”的婚礼上,金铨作为家长有一番长篇讲话,涉及子女教育与婚姻门第。在一定程度上,这番言论甚至还可看作作者理想的婚姻观念的流露。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虽然他的四个儿子皆不成器,但作者笔下,金铨也还是个相当不错的父亲。首先,他对大家庭制度的弊端,特别是权贵门第对子弟们的腐蚀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给下属写信论及此事道:“中国大家庭制度,实足障碍青年向上机会。小儿辈袭祖父之余荫,少年得志,辄少奋斗,纨绔气习,日见其重。若不就此纠正,则彼等与家庭,两无是处。”(五十九回)其次,发现金凤举的劣迹后,当即致信其上司,要求免去他因祖荫的职位,以此刺激其个人奋斗。同时,他的严格、严厉都不显其粗暴,态度始终保持着理性。如果说教育效果并不好,那作品的描写也是归咎于金铨“抓而不紧”,而不是父权的失败或缺位。与《红楼梦》的贾政相比——金铨形象大体脱胎于贾政,两个形象同属“严父”,同样面对着不肖子弟,但金铨显然要亲切一些,“父权”的负面色彩也要淡薄不少。
我们不妨把巴金《家》中大家长的形象拿来比较一下,发现其中“完全不亲切”、“像敌人”的描写比比皆是,显然,二者在对待大家庭的父权方面,态度大相径庭。在这里,笔者并不想评判二者的优劣,只是要指出《金粉世家》与《家》是分别站在社会思潮的不同位置上。换言之,尽管《金粉世家》声称反对大家庭制度,但就其塑造的大家庭之家长形象来看,他的“反对”是很浅层、很温和的。特别是对大家庭必然伴生的专制权力,情节中完全付诸阙如。这就明显与时代思潮脱节,而把自己的身段放低到一般大众、市民的水平。《金粉世家》叹息着大家庭的衰落——不可避免的衰落,而叹息中我们更多感受到了作者脉脉的温情。
在现代文学中,《金粉世家》是描写多妻制家庭落墨最多的作品之一。书中的大家长金铨“率先垂范”,娶了两房姨太太;长子金凤举娶了个妓女晚香做妾,还在外边另起炉灶弄了小公馆,结果闹得家宅反乱——这是全书仅次于金燕西与冷清秋之恩怨的另一重要情节;长女金道之由日本归国,带入金宅的却还有个日本姨太太。三个多妻制的“核心家庭”,各有鲜明特色,既增加了矛盾冲突的复杂性,也表现出作者对于婚姻制度的复杂态度。
从表面上看,作者无疑是对多妻制持否定态度的。三个多妻制的“核心家庭”,以金凤举这边描写最细。他的娶妾过程时间不过两三个月,而对于金凤举来说,却是经历了由天堂到地狱的跌落。其间反差最大的是小妾晚香的形象。金凤举初见晚香时,眼中的晚香是“约计十五六岁”的“娇憨”小姑娘;随行的朋友评价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用得着这一朵解语之花”③。而小公馆的陈设,富丽之外还带上几分清雅,处处以菊花比喻晚香,似乎格调相当高雅。而在金燕西的眼中,这个晚香“活现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并没有什么青楼习气”。可是“蜜月”未出,两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晚香的形象也随之大变,经常醋海生波大吵大闹,完全变成了泼妇的形象。
金铨的妻妾关系呢?他的一妻二妾相处似乎还算融洽。而等到他突然去世,一切就全都变了。首先是金太太和子女们沆瀣一气,算计着剥夺小妾翠姨的继承权。接下来翠姨突然席卷财产潜逃。前一个情节使我们想到《金瓶梅》中,西门庆身后,正妻吴月娘对待小妾潘金莲的手段。后一个情节使我们想到《红楼梦》中“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的《好了歌》。总体上看,金铨的多妻家庭描写也是指向对这种婚姻制度的否定。不过,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作者的否定是带有“附加”成分的。
我们把《金粉世家》与《水浒传》做一比较,具体说就是拿晚香的形象与阎婆惜的形象做一比较。先要明确一下可比性,也就是比较、分析的基础。这一基础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晚香与阎婆惜都是“外室”的身份——即别居在外的小妾(阎婆惜也可算是宋江的“外室”)。其次,二者委身做妾都是因为钱财。再次,晚香与金凤举反目,阎婆惜与宋江决裂,都是女方生了外心。阎婆惜与宋江决裂,最后被宋江杀死。按说宋江杀死一个弱女子,读者的同情应在阎婆惜一面,但实际的阅读效果却不是这样。文本对读者的引导是,阎婆惜咎由自取。在面对阎婆惜的冷落侮辱与敲诈勒索时,作品描写宋江一再迁就,而阎婆惜却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甚至有置宋江于死地的可能,终于迫使宋江出手杀人。这一点与《金粉世家》在描写晚香与金凤举反目的过程颇为相似。晚香全不顾及金凤举的脸面,做出种种让他丢脸的举动。而金凤举步步退让,竭力维持。直到最后,晚香席卷全部财物逃走。其中有些描写与《水浒传》颇为相似:男主角枯坐一旁,无奈“叹气”;小妾无情“冷笑”,决绝驱赶;男主角失意离开自己的“外宅”。我们之所以做这一比较,当然不是简单地说张恨水模仿了施耐庵,而是要彰显二者一种类似的情况——作者带有偏向的叙事态度影响到价值判断。《水浒传》无疑是肯定、赞扬宋江的,它通过阎婆惜一连串不近人情,甚至刻薄狠毒的“表演”,就把读者的同情引导到宋江身上。《金粉世家》同样使读者对晚香产生厌恶感,对金凤举的处境产生些许怜悯乃至同情,对金凤举在此处境下发出的关于“女人”、“家庭”的感叹、议论产生共鸣与理解。
这种同情与理解的重心,就是在否定多妻制的时候,并非站到人类文明的高度,俯察其不人道,批判其对女性的歧视与不公,而是站在男性的立场,把多妻制带来的痛苦归结到小妾的素质,甚至是女人的秉性。这样,坏制度的一部分责任就转移到了女性的身上。而身为婢妾的女性本来是最大的受害者。
作者在性别立场、性别视角上的偏失,还可以透过另一对形象的比较看出。这就是同在《金粉世家》中的两个小妾:晚香与樱子。樱子是一个谦恭守礼的小妾,金道之是一个大度宽厚的正妻,于是丈夫就乐享齐人之福。如果把这一图景和金凤举狼狈的遭遇对比来读,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是:多妻制既能带来痛苦,也能带来幸福,而关键全在于当事的两个女人的素质——金凤举碰上了妒忌的妻子和不明事理、贪鄙成性的小妾,便使当事三个人全都陷入痛苦;刘守华碰到了宽厚的妻子和贤淑明理的小妾,生活就一片欢声笑语。如此推论下去,男人不妨多妻,只要遇合淑女;女人不妨共侍一夫,不妒忌便有幸福。这样的结论,明显是男性本位的,明显是倒退回封建时代的道德标准了。
作者对待多妻制,既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否定、批判性描写,也有上述温情脉脉留恋性的描写。这种矛盾的态度在冷清秋与翠姨的一段对话中有集中的表现。冷清秋对多妻制给予有限肯定,而翠姨则持反面看法,批评多妻制对女性的不公。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让对话的双方展开争论,而是让翠姨用一句“你所说固然不错”把二者调和到了一起。这种写法,对于报纸连载的通俗作品来说,实在是取巧的做法:各类读者——守旧的、趋新的、男性中心的、女性解放的——都可以找到自己认可的观点,自己喜欢的立场,于是就把读者群实现了“最大化”。
《金粉世家》的“男性本位”,还表现在对女性从家庭中“出走”的描写。“出走”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知识界对于女性决定自己命运而开出的颇有影响的药方,也是历时久长的一个社会热门话题。1914年,春柳社演出《玩偶之家》,拉开了“出走”话题的序幕。此后,“出走”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批评的热门“母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恨水以“出走”为冷清秋的命运选择,以“出走”作为全书的结穴,以及结构的大框架。同情、肯定冷清秋的出走行为,这无疑是作品的一大亮色。不过,如果我们以之与同时代、同题材的作品相比较,就会发现张恨水笔下的“出走”仍然带有“通俗”的痕迹。
张恨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最熟悉《红楼梦》,其次便是《儒林外史》。他多次提到自己在创作中有意借鉴《儒林外史》。不仅在《春明外史》中可以看到这种借鉴的结果,而且如果细心阅读的话,在《金粉世家》中也不难发现借鉴《儒林外史》的痕迹。如金燕西结诗社的情形,如金氏兄弟身边的几位帮闲形象等。就是女主角冷清秋,也有借鉴的“嫌疑”,特别是在作品开端部分塑造的形象上——“出走”之后的表现。《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写一“出走”的才女沈琼枝,出走后无以为生,只好在市井“写扇作诗”。杜少卿邂逅颇赏识,便到其家中探访。这一段情节与《金粉世家》开篇写冷清秋的出场十分相似,也是文人闲走,看到“广告词”,心生疑惑,对女子身份的猜想,等等,境况颇有相类之处。而《儒林外史》对沈琼枝诗才的加意描写,则与《金粉世家》中对冷清秋诗才的描写也相类似。我们的比较并非要揭出张恨水有所借鉴的“老底”,而是要说明:张恨水笔下的“出走”既有时代潮流的影响,也有继承传统的成分。张恨水刻画冷清秋这个形象,一定程度上与杜少卿怜惜落魄才女沈琼枝的心理近似,而与鲁迅之于子君则大相径庭。
《金粉世家》中写了两个“出走”,人们往往只关注其中的一个:冷清秋的“出走”,而很少注意另一个。另一个“出走者”是丫环小怜。同样是“出走”,可以拿来比较的是“出走”之后的命运。小怜在书中虽非主角,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配角。如果拿《红楼梦》来类比,她近似于鸳鸯;如果拿晚出的《家》来类比,她近似于鸣凤。而她的“出走”,在作品中也是一个重要情节。
“出走”之后的命运,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之深浅,可以天地悬隔。鲁迅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出走之后怎么样”,他的答案也很具体:“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④。他使用了“战斗”这个词,而且使用了两次,还使用了“剧烈的”做修饰语。至于战斗的结果,他悲观地以“不知道”来回答。这是一个思想家的答案,惟其“不知道”而更见其深刻。
张恨水在小说里通过人物的命运写出了自己的答案。冷清秋“出走”之后,隐姓埋名,依靠自己的一点语文修养,通过教私塾、写春联一类的事情糊口,晚间还要做手工活,可以说是挣扎过活。而小怜在金家败落之后却衣锦荣归了。原来她“出走”之后,嫁给了柳春江。而柳春江是个“有出息”的男人,带着她出国到日本,终于“混出了人样”。本来她是丫环的身份,而且是背主潜逃。可现在又有地位又有钱,回到金府,不但原来的小姐妹们艳羡不已,就是原来的主子们也换了面孔,换了称呼,甚至成了小少爷的“姑母”。
两个“出走”者,结果迥然不同。所差者只在有没有自己栖身的高枝。这个高枝不是别的,就是一个有出息的男人。《金粉世家》正是用自己讲述的故事给出了张恨水关于“出走之后怎样”的答案。“出走之后的”小怜扬眉吐气,“出走之后的”冷清秋经济窘迫,心有余戚,可怜可悲。强烈的反差自然而然地告诫了读者。如此叙事的效果,便有力地抹杀了“女性自立”的主张。客观地讲,《金粉世家》为两位“出走”者安排的不同命运,可能是合乎“现实”的。只不过,这样的“现实”是属于世俗的——小说也因此被世俗所理解、所接受;这样的“现实”也是属于男性中心的社会的,由此衍生出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旧有的男性中心主张。
《金粉世家》在作品涉及的主要观念上,都表现出摇摆不定的姿态,而骨子里更多地迁就一般民众的水准,是与其预设的阅读对象相关,更与其传播媒介的性质相关。作为副刊的连载,对大多数读者的迎合与迁就可以说是办报的不二法门。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其实也可看作报社老板的“雇员”。“通俗”——不仅是语言层面,还包括观念层面,是销量的保证,当然也是老板的要求。接受了这份工作,也就落入了这个“通俗”的陷阱。对于作家来说,无论其口头如何表白,这都是他的宿命。
注释:
①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②《金粉世家》的一个特点是书中人物好发议论,其中有些显然是作者自己意见的传声筒。
③“浊世佳公子”云云,恰是当时人物议论所谓“四公子”时的常用语。
④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