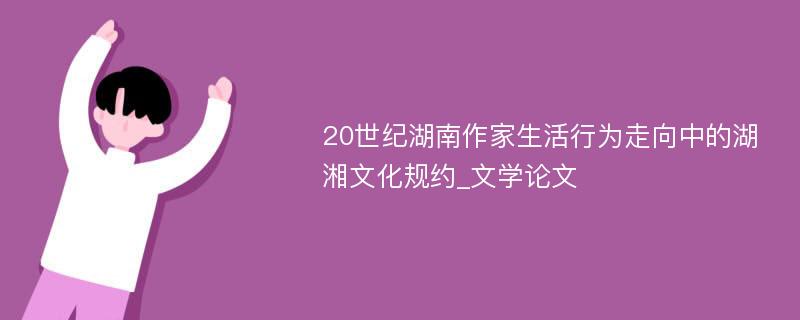
湖湘文化对20世纪湖南作家人生行为走向的规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约论文,湖南论文,走向论文,作家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4—0084—06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对20世纪湖南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他们的人生行为走向以强韧的规约和制导。它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即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经过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辈的阐释、传播和实践应用,湖湘文化已在湖南社会尤其是在湖南士人中产生了一种“心理定势”,蓄积成了一种足以俯凌后世的巨大的心理势能。本文主要探讨湖湘文化精神所产生的心理势能对20世纪湖南作家人生行为走向的影响。
一
20世纪的湖南作家们几乎都把政治置于他们人生价值的首要位置,政治是他们文学事业的主宰,也是他们人生命运的牵引之神。当他们在人生道路上面临着政治、文学孰先孰后、孰去孰从的选择时,他们一定首选政治而先之从之。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作家表现最为自觉,最为直率。陈天华有《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传世,但他的文学事业只是其革命实务的一部分。他曾参与组织同盟会,最后为反抗日本政府颁布的《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蹈海自杀,这一壮烈的人生结局,最集中体现了陈天华的生命价值取向。宁调元有“监狱诗人”之称,就义时仅30岁。他也是以革命实务为重,他加入同盟会,参加萍浏醴起义,后又参加反袁斗争而被捕牺牲。他短暂的一生中有三年在狱中度过。杨度称之为“旷代逸才”,但他一生辗转反侧于官场政界,希冀在政治上一展抱负,而不能专心于文学事业。观辛亥革命前后世纪之初湖南的这些可载文学史册的人物,皆相当一致地把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他们的人生行为全是自觉的,可视为文化秉性使之。
五四至左联时期的湖南作家其人生轨迹也有着大体一致的趋向。成仿吾、欧阳予倩、田汉、丁玲等最初都是在“文学革命”的潮流中登上文学舞台的,但后来一致性地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仿吾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欧阳予倩因参予十九路军反蒋而遭通辑,田汉被列入当局“缉拿归案”的黑名单,丁玲被囚禁三年,他们纷纷跻身于政治革命的行列。左联成立后,一大批湖南作家成为了它的成员,如周扬、田汉、丁玲、周立波、萧三、欧阳予倩、叶紫、蒋牧良、白薇、彭家煌、彭柏山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湖南作家在左联的领导层中占了重要位置。在尔后的解放区文学中,湖南作家更占据着统领的地位,领一代风骚。如果把毛泽东、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李木庵等湘籍革命家的文学活动都包括在内,那么,解放区文学主导的力量无疑是湖南人。即使不计毛泽东等革命家的文学活动,其他云集解放区的湖南作家也够得上支撑解放区文学的栋梁之辈了。他们在解放区这块天地里生活和斗争,政治更是人生价值的首选。他们宁可做革命的实务,也暂时将文学搁置一旁,即是文学创作,也首先选择那些能立竿见影的形式。成仿吾到解放区后从事教育事业,对文艺工作主要起领导作用。丁玲担任过“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等职,她有许多高质量的文学创作,但她在陕北十年,只写了十个短篇小说,却写了七八十篇着力表现边区各条战线英雄模范人物的战斗风貌的报告文学。周立波从上海开始文学生涯,至1948年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脱稿,整整20年,他的人生选择首先都是在“政治”一方,这期间他的作品有影响的主要是报告文学,直到《暴风骤雨》问世,才使他作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家的人生角色得到定位。周扬一直担任文艺界、教育界的领导职务,在这期间,已奠定了他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阐释人的地位。此外,萧三、康濯、彭柏山、张庚、欧阳山尊、陈辉、柯蓝等在解放区都有着大体一致的人生选择。这么多湖南出来的作家云集解放区,且他们都有着大体一致的人生运行轨迹,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犹如指南针一样直指“政治”方向,他们都如此沉潜于政治,如此热心于行政领导工作,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深潜的湖湘文化基因在规约着他们。萧三说得很明白,他说,“我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诗人”,他“不以诗篇为生命,而以生命作诗篇”。[1]
建国后的头17年,周扬、田汉、丁玲、萧三、周立波等人曾一度成为执新中国文艺牛耳之人,尤其周扬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个要求文艺绝对服从于政治的时期,湖南作家之间的政治恩怨之深,政治瓜葛之多,也是其他省域的作家群所少见的。最典型的有周扬与丁玲的矛盾,丁玲与沈从文的矛盾。这和一元化的人生价值观似有某种联系,大家都投身、执著较劲于政治,犹如挤上一个独木桥,总有落水者、不幸者。这时期湖南作家们政治情结的一种特殊体现,还表现在一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抵制、反思、批判极左政治给社会、给文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湖南的作家们认为现行政治不合理时,他们总免不了“指划天下,物议朝野”,这恰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精神的真诚执著的体现,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精神的当代版本。康濯的《水滴石穿》发表于1957年7月, 在“反右”的非常时期发表这样一个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确不寻常,这是那时候最尖锐深刻地揭露党内官僚主义、腐败习气的作品。周立波则是通过风俗的描写来消解极左政治对文学的制约力的。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建国后写的短篇小说,沉潜在风俗层次,在当代描写农业合作化的所有作品中,没有一部作品对现实关系的描写达到了《山乡巨变》的真实度和深刻度。尤其是曲笔的运用,对极左政治作了反思和批判。如刻划李月辉这个在极左政治席卷吞噬一切的时代里能够保持实事求是作风的干部形象,可以说是描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中仅有的一个,这不但是生活中确有这样的干部,更重要的是应视为周立波“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一种投射。田汉的《关汉卿》创作于1958年,关汉卿那种“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的可贵性格及其与权势作斗争而导致的坎坷命运,有作者自况的影子在内。到了60年代初他改编的《谢瑶环》,对现实生活的影射就十分清晰了。作者抓住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相通或相似之处立意构思,突出谢瑶环“为民请命”的高贵品质和“载舟之水也覆舟”的深刻思想。他成了当代的“谢瑶环”,为了《谢瑶环》,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文革”十年中,湖南作家开顶风船也堪称中国第一。湘剧《园丁之歌》,小说《第二次握手》,都是勇敢挑战之作。从以上分析可见,与极左政治抗争是建国后前30年湖南文学的主导趋向。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学行为,还不如说这是一种对现实政治不满不平而鸣叫呐喊的政治行为,是一种用文学形式的“上书”,甚至是一种“死谏”。这同样是政治价值取向和经世致用精神的呈现,而且是更富人格光辉的呈现。这种人格光辉在王夫之、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身上薪尽火传,源远流长。湖湘文化精神薰陶濡染下的湖南士人和现行政治相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归属它服务它,一是悖逆它反叛它,其主观愿望都是为了社稷苍生的利益。
新时期湖南文学掀开了新的一页。周扬出山当了文联主席,丁玲复出又一次红火,沈从文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周立波和康濯等也老树新春,后起之秀层出不迭。在“伤痕”、“反思”、“改革”文学阶段,湖南作家里应外合,不断引起文坛的“轰动效应”。“文坛湘军”崛起,确不为虚言妄谈。这时期湖南作家的创作心理定势与当时文学拨乱反正的主潮高度合拍,因而成就了湖南文学一个阶段的辉煌。从80年代中期始,这支建立在传统文化根基上的、具有基本一致的创作心理定势的“文坛湘军”则走向先瓦解后重聚的时期。80年代中后期是湖南作家最心神不宁、最难以作人生角色定位的时期。这从文化深层来分析,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价值取向一元的时代,而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多元的时代。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中以政治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价值观被极大地摇撼了,在更为前瞻的时代面前,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前,湖湘文化心理基因不适生存而必须更新。在沿海沿边省区不断开放的情况下,湖南在全国的地理总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发展不畅,湖南作家那种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在消失,不但是写什么和如何写成了问题,而且写不写都成了问题。湖湘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成了一个艰难而又非行不可的任务,它靠“经世致用”的精神舍弃不适时的陈旧内容而求涅槃新生。而湖南作家在这一转折性历史时期,在其人生选择和角色定位的寻找中,又一次映现了这一过程,表现了大体一致的人生行为走向。莫应丰比较典型,他病逝于1989年,韩少功曾作《然后》一文追悼,记叙了他在新时期不断易位和错位的过程。他在“伤痕”文学阶段,曾因《将军吟》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而“好评如潮从者如簇”,“固一世之雄”,后走上“由文学而仕宦”的道路,但“一晃几年,他领导的机关似没有多少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后放弃官位,“来到海南筹办农场”,终因积劳成疾去世。莫应丰的人生境界、人生历程和人生角色转换具有典型的意义,标本的价值,反映了80年代中期以后在急剧变化的历史转型期,湖南作家一种重新辨识自己,确认自己,重铸文化新观念,调整人生方向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显得浮躁,而且归宿不一定合理,但这个过程是肯定会发生的,而且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古华定居加拿大,韩少功迁居海南,水运宪当了经理,他们无疑都有过莫应丰那样的改变自我、战胜自我的人生搏击。
经历了80年代中后期的分化瓦解,湖南作家又重新集结,但斗转星移,这支队伍也非清纯一致了。他们与传统的脐带连着,依然是“湖南人”,但他们更应与时代的脉搏相通,更应是“世界人”;他们依然注目“政治”,然再不全去求官求爵,作品的表达也不全是直来直去,而讲究多视角表达;他们与“市场”相联系,发行量、版税额再非不屑一顾。不能说这种转变已经非常成熟,但这种转变是人的意志不能阻遏的。也还是有作家操旧法的,关注现实政治,讲求经世致用,王跃文就是突出的一例。他身居官场,近水楼台写起“官场小说”,他的“官场现实主义小说”在全国形成影响,说明操传统之法仍有用武之地。况且王跃文不是简单地重复传统,他对政治的关注,是真正用文学的手段表现出来的,他的文学是人学而不是政治说教。
二
以上,我们描叙了20世纪湖南作家群在几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大体一致的人生走向。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群体性的人生行为,不但是同时代的,而且还是纵贯百年湖南文学史的,和近世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的人生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人的外行为方式和规范模式无疑是由人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制约着的。湖南作家群这一区域性的人生行为无疑是由湖湘文化精神对他们心理世界的影响规约着的。湖南作家中没有鸳鸯蝴蝶派,没有高居于象牙之塔的贵族文学家,这也从悖面说明湖湘文化精神对湖南作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20世纪的湖南作家们,一生充当着“政治人”的角色,但他们在追求着政治价值体现的同时,却忽略了现代人格的建构,他们在波翻云涌的政治斗争中沉浮起伏,却消弭了自己的独立个性,他们基本上保持着传统人格的面貌。这种政治价值的追求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的延误,恰好反映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在20世纪湖南作家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也显示了湖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嗣传在近世的发展衍生所具有的先天不足。
所谓现代人格,是指个性获得充分或比较充分地发展的、适应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独立人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的价值只能是外在的,只有作为对外实现集体利益的工具时才有价值,这样就决定了中国人人生价值的理想体现就是实现某种社会政治伦理目标。直到近代,中国社会还无人如康德那样提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口号。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格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通过满足各种需要而形成的。他说:“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2]即人只有在高级需要得到良好满足的情况下,完满的个性才会形成,个人的特质才会获得充分的发展,也才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由于中国传统人格的需要层次长期处于较低层次的安全需要、归属需要,甚至最低的生理需要上,而没能向更高的尊重、自我实现需要的层次发展,所以他们普遍表现为一种依附型人格,自我意识十分淡薄。五四运动是中国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实现历史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关口,涌现出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一批高张个性并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但中国传统文化积淀过于深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制度也没建立起来,特别是救亡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主题,救亡和启蒙构成一对矛盾,五四精神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甚至被消弭。这种历史的先天不足造成的后遗症在建国以后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如此步履艰难,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人的现代化即现代人格的培养和构建重视不够。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不怎么现代化的人在干着现代化的事业,是我们社会的一大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更深刻地展现出来。
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精神的旗帜,应该具有比一般人更健全的人格,更高尚的个性,这样才不仅仅是“写字儿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知识精英。20世纪湖南作家总的说是时代的精英,但主要还是政治意义上的。由于湖湘文化价值取向对他们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限定,他们具有明显的人格缺陷,最主要的就是缺乏独立性。
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南作家我们不必苛求。陈天华、宁调元等具有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们也作了许多反封建的宣传,但他们都还无暇顾及到现代人格建构的历史工程,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都还没到这一步。他们本人从小饱读中国传统经书典籍,虽然接受了许多现代的思想观念,但他们的人格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是他们的人格范本。至于王闿运和杨度就更老旧了,倘若一旦他们政治上的抱负得到实现,其心态也会和唐代孟郊中进士后所表达的那般:“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五四以后的湖南作家不同了,他们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初,一般都强调个性解放和独立人格,但湖湘文化的基因是早就植下的,现代思想是后来接受的,现代思想要占据主导地位,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濡染薰陶的过程,而且外部条件也必须相应创设。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民族救亡和政治革命是主题,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又是农民,所以现代人格的建立绝非易事。丁玲、田汉、周扬、周立波等都走过了一条从倡扬个性到个性逐渐消弭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伴随着心理的、精神的搏斗,他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常常犬牙交错地交锋。丁玲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三个口号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这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只要是活着的人,就脱离不了政治。”她还说:“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3]这个讲话是1980年发表的, 当时中共中央十分明确地废止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以“两为”方针替之,这一举措大大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但丁玲这时却还偏执地坚持“政治化”。其实,在丁玲的后半生,独立人格的保持与政治归属需要的追求之间构成一条基本的人生轨迹。到新时期,湖南作家的人格结构在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但真正能进化到韩少功这种境界的人却不多。蒋子丹在《韩少功印象》里这样写道:
若以中国人世代相袭的道德观念作准绳,韩少功无疑是极符规范的一个。诸如治学则博闻强识学贯中西,为文则金相玉质不落窠臼,出言则持之有故崇论宏议,处世则思深忧远宠辱不惊,居家则不丰不杀,待客则不卑不亢,以及和谐于伉俪全家之间、睦处于四邻之内、尊其长恤其幼之类的优点,简直罄竹难书。然而好比一个社会生产过剩就要发生经济危机一样,一个人优点过剩的后果是重如泰山的信誉负担,这对韩少功来说,似乎已成为无可逃遁的定局。此生此世,他非要背着这副辉煌的十字架艰苦跋涉不可了。
她还说韩少功“到家的精明乃是西方人的礼貌与东方人的狡猾之混和。韩少功骨子里处处充盈着东方人含蓄柔软的狡猾”,但“韩少功本质上仍是一个清醒的现代人”。[4]蒋子丹的描叙绘形绘色, 既有性格的表征,又有文化的底里,由此可见到韩少功人格建构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他为《马桥词典》引发的官司中的所作所为所再次证实。其他的新时期湖南作家的人格大约都表现这样一种两重结构,但他们大多本质上还是传统人,还是“湖南人”。古华的《芙蓉镇》从政治层面来讲具有揭露批判功能,但并没有一种现代文化观念作底蕴,相反对历史作道德化处理,恰恰表现出思维方式、心理定势和价值观的老旧之色。古华远走加拿大,实际上已放弃了他的文学事业,这是人生的升华还是沉沦,是新的人格的体现还是旧的人格的复位,我们姑且不论,但这一行为绝对不是人的、特别是一位作家的“高级需要”的追求的实现,它的层面和芸芸众生相当。而在1995年出版的湖南作家的三部长篇——何立伟的《你在哪里》,蔡测海的《三世界》和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精神品位是较低的,缺乏现代意识,作家的人格精神投射是灰色的。
三
在对20世纪湖南作家的“人格缺陷”作了一个扫描之后,我想重点剖析周扬和丁玲,他们经历过中国20世纪许多重大历史变革的人生历程,当最能反映他们的人格本色,即是他们之间至死都没有化解的政治恩怨也最能反映他们的人格缺陷。
当我对周扬作历史地审视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自然浮出另一个20世纪的湖南人,他就是杨度。周扬和杨度的人生经历、价值追求及人生结局似有相当的相似性。他们一生都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度过,都力求归属于某种政治,但政治的变幻使他们很难有一个固定的立足点,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改换自己的人生位置,变换自己的人生角色,但政治一直与他们的命运和人格厮守难分,最后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周扬是很有才华之人,20出头就成了“左联”的掌门人。在极左的政治运动中,他整了不少人,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尤其是与冯雪峰、胡风、丁玲的矛盾。但具有极端的讽刺意义的是,“文革”一开始,周扬也成了阶下囚,演出“请君入瓮”的人生大悲剧。当年反胡风运动的第一篇檄文《我们必须战斗》是他写的,冯雪峰与丁玲在1957年反右中的冤案是他敲定的,而现在自己在重复他们的命运。历史就是这样开了一个大玩笑。周扬在逆境中,终于发现历史的荒唐。他忏悔, 他赔礼道歉。 他居然还成为1983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的理论代表人物。但周扬的人格毕竟还是传统的。他太在乎政治,太在乎上级对他的看法,他缺乏特立独行的人格支撑。马立诚、凌志军在《周扬的人道主义悲歌》中如此描叙:
周扬在“文革”当中的处境是悲惨的,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八年的冤狱。1975年7月, 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达观,自认为“身体还可以”。……“文革”的遭遇并没有彻底地摧毁他的身体和意志,他很快恢复了往日的豪迈和潇洒。他把这种气概一直保持到1983年,然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的豪迈一落千丈,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该不该如此长寿。
根据他的女儿周密的陈述,在那次众所周知的“事件”之后,他的精神备受刺激,身体急剧衰老,面容憔悴,动作迟缓,他不止一次地对周密说:“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疲倦,实在太累了。是不是我活得太长了?”然后他就开始念叨那些他所熟悉的已经去世的人:“主席、少奇、总理、陈老总,他们都走了,还有梅兰芳、郭老、茅盾、老舍、田汉、立波、赵树理……”
周密所说令周扬“备受刺激”、“急剧衰老”的“事件”,乃是指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
周扬就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中度过他的最后岁月的,他一直想讨个说法,以表自己的清白,“天天念叨胡耀邦同志是否能够看到他的陈述”[5]。他的晚境很像一位落魄失意的委身政治的传统儒家士子的晚境。杨度晚年有《自题小像》诗:“我是苍生托命人,空空了了入红尘。救他世界无边苦,总是随缘自在身。”其可爱可敬可叹可悲之处,似亦是周扬心迹的一种表白。周扬是20世纪湖南作家中最不幸者,这主要是从现代人格的建构与政治归属需要的执著追求相冲突所产生的人生悲剧作如此观的。在这里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我所说的政治归属需要,不是指的政治信仰层次的,而是指的政治功利性的、权力层次的。
丁玲是20世纪湖南作家中个性与政治相互挤压终成“政治化了的”的颇值惋叹的人物。她17岁走出湖南,秉着“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6]的信念, 开始她的人生探索。她的创作和人生,都曾颇具现代个性色彩。1955年她被作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受到严厉的政治处分,直到新时期才平反。按照一般的逻辑,丁玲受极左政治之害如此之大之深,复出后毫无疑义地会站在反“左”的立场上,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阵营里的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新时期,周扬反而成为思想解放的代表,而丁玲却成为保守的和“左”的思想的代表。
一些研究者往往从周扬与丁玲的矛盾纠葛的角度去理解丁玲的“左”,认为“晚年的丁玲仍然没有摆脱周扬的阴影,不论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某种策略性需要,还是由于对对方无理压迫的一种带有某种情绪性的反驳,丁玲一些给人留下“左”的印象的言论和做法,都与周扬直接有关。正是周扬的继续围剿,把她逼进了一个走不出的怪圈”[7]。应该说,论者们提出的这些现象是存在着的,但解释是肤浅的。事实上,在新时期宽松得多的政治环境里,周扬再去整丁玲已经不大可能。而1983年以后周扬自己都在惴惴不安中打发光阴。我认为丁玲新时期的“左”的政治化以及她和周扬的矛盾,正深刻地反映出她现代人格已基本缺失,她没有从“人”的本位去思考人,没有悟透一个作家的生命价值,而把政治归属需要当成最高的价值追求,急功近利。何清涟说:“学者本是寂寞的,一旦成为政治人物,就已不成其为学者。”[8]作家也是如此。丁玲晚年的所作所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站在历史高处的现代人格力量。她所批判的对象并不限于周扬,相反的是很多与她毫无恩怨纠葛的人,甚至与她同样遭受极左政治迫害20余年的“右派”。如她批评张贤亮的《绿化树》是“使人感到共产党把人变成了兽”[9], 这样的批评简直使人不寒而栗,尤其出自丁玲之手,更显现病态的灰黑。《绿化树》发表于《十月》1984年第2期,这时,周扬的影响已经不大, 如果只是为了周扬,丁玲完全不必这样做。这种“左”的事例晚年丁玲还有许多。王蒙说她“画虎不成反为犬,本来是非政治家,太政治了反而没了政治,只剩下了勾心斗角”[10]。我认为丁玲最充分地体现了湖南20世纪作家的人生轨迹。从她身上,看得出湖湘文化精神对他们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强韧的规约,给他们造成的了现代人格的缺失。在20世纪湖南,没有出现像鲁迅、钱钟书那样具有健全的现代人格的代表作家。在他们纷乱复杂的人生行为表象之下,我们看到湖湘文化基因起着多么大的制导作用。他们的人生大多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从表层来看,是政治的、人生的,但从深层来看,则是人格的、精神的,说到底是他们由传统文化所规约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与现代的文化新建构发生冲撞而最终未能得到涅槃新生的文化悲剧、性格悲剧。性格决定命运,文化决定性格,我觉得这是深层次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带有世纪意义的悲剧。他们既充当了勇敢的普罗米修斯,同时又充当着尴尬无奈的西西弗斯。
收稿日期:2000—04—05
标签:文学论文; 湖湘文化论文; 周扬论文; 韩少功论文; 丁玲论文; 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艺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