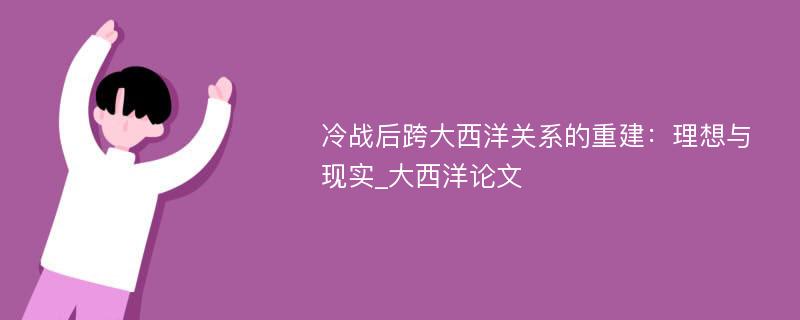
重构后冷战时期的跨大西洋关系:理想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重构论文,时期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跨大西洋关系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欧国家为共同遏制苏联结成了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这一“特殊关系”主要受国际形势和美欧双方实力这两大因素制约;这意味着,一旦特定的历史条件削弱或消失,“特殊关系”也就难以正常维持下去。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动摇了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欧盟的建立和发展亦对传统的大西洋关系格局形成了冲击。面对双重压力,调整与重构后冷战时期的跨大西洋关系势在必行。
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不仅直接关乎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将对21世纪国际格局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与这一重要性不相称的是,国内学术界对于美欧之间跨大西洋关系的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欧美学界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①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冷战时期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大国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美苏关系和所谓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对西方内部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虽有所关注,但研究明显不够。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以往不太受重视的美欧关系研究日渐升温,尤其在伊拉克战争造成西方联盟分裂后,研究者更加关注美欧关系的走向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美欧关系研究一时几成显学。但也必须指出,美欧关系的现实复杂性为学术研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美欧关系的复杂性除了源于其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特点,更多的是因为“多面孔欧洲”② 和美欧关系中的多元行为体使得美欧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而增加了研究难度。具体来说就是,不同“欧洲”观念和范畴内的国家行为体以不同方式和途径参与不同形态或组织形式的美欧关系,并随之带来了欧洲国家组织属性的重叠和交叉问题,突出的表现是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另有少数欧洲国家不同时属于欧盟和北约。美欧关系的概念大体上可有三层含义,与此相应的是美欧关系呈现三种形态,或者说运行于三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双边层面上美国与欧洲各国的关系,这种双边关系的总和曾长期作为美欧关系的主要形态。③ 二战后美国仍然重视与欧洲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的双边关系,尤其在防务安全领域美英“特殊关系”时常发挥着比美国与欧盟关系更重要的作用。其次是二战后新形成的北约框架内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即大西洋联盟。北约是战后美苏争霸和东西方冷战的产物,作为大西洋联盟的组织形态和主要支柱在冷战时期保持了总体稳定,冷战后虽仍得以维系但基础却已大为动摇。再有就是超国家层面的欧盟—美国关系,美国与欧盟的关系萌芽于上世纪70年代初,④ 美国同当时的欧共体打交道并与之保持非正式联系;这一关系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发展较快且潜力巨大。如今,作为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一个重要机构和国际行为体,欧盟的组织形式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虽然与国家行为体相比仍存在明显的缺点,但毕竟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政治和行政能力。欧盟所获得的这一新角色和新作用对欧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欧盟不仅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其政策触角的不断延伸影响到美国的对外政策,而被美国视为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对话者。随着双方互动日益密切和重要,美国与欧盟关系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上升。美国在谋求继续保持其在大西洋联盟内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与欧盟打交道。
美欧关系的观念、形态与组织体制的复杂性对于研究者而言意味着挑战,对这种复杂性认识不足易导致将不同形态和组织体制下的美欧关系及其多元行为体混淆,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简单化或片面性的缺点。从现实的研究情况来看,国内的一些相关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传统的北约框架内的大西洋联盟关系与欧盟一体化背景下的美国与欧盟关系区别开来,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的倾向和情况。这不利于从总体上认识和理解当代美欧关系的性质及内涵,也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调整与重构的趋势和特点。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大西洋联盟关系和美国与欧盟关系纳入一个整体性的跨大西洋关系框架,通过考察两者的互动以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战略与政策博弈,揭示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重构问题的实质、重构进程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尝试性地提供一种新的跨大西洋关系研究的方法体系。
一、重构跨大西洋关系:作为一项外交议程
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安全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美欧关系模式已不能满足双方外交政策的主要需求,重新定义新时期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并为大西洋合作确定新的基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⑤ 应当说,欧美双方对于重构彼此间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共同的认知,但是其角度和出发点并不相同。欧盟早就不满于旧的大西洋从属关系,希望同美国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5年宣称,已有56年历史的北约已经过时,需要重新整合,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应当有新的起点。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更明确地说,欧盟要成为“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⑥ 欧洲人认为冷战的终结和欧盟的诞生开启了大西洋关系的新纪元,为改变旧的从属关系和建立新的平等关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冷战后,美国也意识到了大西洋联盟的局限性。冷战期间北约联盟为美欧关系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框架,并使双方在军事安全之外其他领域的关系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是冷战后北约已经不能满足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了。基辛格指出,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更加趋于广泛,军事冲突的次数已经下降了”。⑦ 而经济竞争对于国际关系愈加重要,地缘政治有可能被地缘经济取代,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日益从经济而非军事的视角来看待当今世界及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冷战后北约虽然存活下来,但是对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却起不到多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过去曾长期被安全关注抑制的贸易争端变得更趋激烈和频繁,而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亦受到挑战,对此北约既无力应对也难以提供寻求解决方案的论坛。形势的发展要求美国同欧盟建立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关系仍将包括安全方面,但同时必须在其他方面找到力量。⑧ 换言之,必须重构一个以经济合作和大西洋一体化为基础的新联盟:虽然安全关系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新联盟的关键却在于重组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即便实现不了经济一体化,至少也应将这种关系从冲突转向合作。贸易将对美国—欧盟关系起到促进作用,正如英国《经济学人》的社论所指出,“贸易的发展将有助于巩固北大西洋联盟……经济和安全应齐头并进;欧盟虽有其弱点和不足,但是经济合作可以使双方拥有一个更加精细的共同事业。”⑨ 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认为,构建一个拥有一定经济一体化基础的永久性美欧(盟)联盟,将会使大西洋两岸之间越来越难以分离,这同时也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防止欧洲重新回到上世纪的战争和冲突的需要。基辛格称,大西洋关系的重建将“在帮助美国应对21世纪国际秩序演变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⑩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美欧关系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调整与重构跨大西洋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次危机在严重程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危机,使美欧关系降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一些欧美人士甚至预言:“旧的跨大西洋联盟的终结已显露端倪。”(11) 美国与“老欧洲”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冷战后大西洋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失去共同敌人的美欧难以形成新的共同战略目标,而欧盟的崛起使得美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美国学者库普乾在其所著《美国时代的终结》中断言,欧盟与美国的分歧早已超出贸易领域,两者正由传统的盟友变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欧盟最终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挑战美国霸权力量中心的前景不可避免。(12) 库普乾的这一论断或许有些偏激,但其所揭示的美欧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在上升却是事实。德国马歇尔基金会2004年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过去两年里,欧洲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的支持率显著下降,欧洲人越来越希望欧盟发展成为一个脱离美国控制而自行自立的超级大国。从2005年起美欧出于各自的内政外交需要都试图修补双边关系,布什于2005年2月出访欧洲时有意放低身段,使双方关系有所改善。而欧洲政治也发生了变化,默克尔和萨科齐先后出任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他们上台后亦寻求修补同美国的关系。有分析认为,默克尔政府采取了“新大西洋主义”路线,试图将德国带回德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轨道,寻求与美国建立一种不同于施罗德时期的双边关系。(13) 萨科齐则发表了一些亲美言论,做出了一些亲美姿态,颇有些要同希拉克的对美政策划清界限的味道。此外,德法英三国以及欧盟还在伊朗、科索沃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协调,所有这些都对促进美欧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产生了影响。然而,双方修补关系的努力及效果终究是有限的,欧洲的政治变化和美欧之间短期利益需求的汇合确实有助于双方关系获得暂时和局部性的改善,但并不足以消除彼此间的战略分歧,更难以扭转由国际环境改变和大西洋地缘政治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美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进程。正如有分析指出的,欧洲新的“亲美”领导人的上台不会导致更密切和更好的大西洋合作;仅有共同的价值观并不够,基于地缘差异而形成的利益分歧限制了未来大西洋关系的强度。(14) 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委员瓦尔德纳2007年9月在纽约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称美欧关系依然位于国际体系的核心,但是她承认这种状况不会永久持续下去,毕竟当前美欧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已根本不同于冷战时期。(15) 很显然,美欧关系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的打击后已元气大伤,近些年来虽然有所改善,但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时代了。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二战后迄今美欧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变化。
总而言之,冷战后的美欧关系已今非昔比,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以及美欧外交政策需求的变化,旧的大西洋关系模式暴露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因而重构新的跨大西洋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提上了日程。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而成为大西洋两岸共同的外交议程。从学术意义上讲,对该问题的探讨将提供一个观察冷战后美欧互动和大西洋关系动向的新视角。
二、美欧在跨大西洋关系重构问题上的互动与博弈
跨大西洋关系重构的议程既已确立,美欧之间的互动与博弈便随之展开,双方从各自战略利益出发提出相关倡议和计划,谋求掌握博弈的主动权。
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既是一个现实课题,同时也是二战后美欧之间围绕应建立怎样一种大西洋关系进行互动与博弈的历史的延续。历史上美国先于欧洲就建立某种紧密的大西洋关系进行过思考;二战后初期曾提出建立一个大西洋联邦的想法,即把美国的建国经验放大至大西洋层面,在美国和西欧的民主国家之间建立一个联邦。(16) 持这一看法的人认为,1949年缔结的北大西洋公约虽然超越了传统的联盟,但仍不是联邦主义的文本。(17) 1962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赫特领导的一个小组提出了“北约国大西洋公约”(Atlantic Convention of NATO Nations)构想,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大西洋共同体”描绘了蓝图。(18) 该构想主张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即高级理事会,以及一个高等法院;还提出要拟订一个大西洋经济共同体的计划,该共同体虽然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主,但不会对外封闭,而是“向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开放”。如此宏大的共同体一旦建立,将会是高度集权的;北约组织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将得到加强和发展,并能够在某些领域以多数决定程序采取行动。但是该构想因过于激进而未被美国政府采纳。不久后,一个较为现实的“伙伴关系”模式开始浮出水面。1962年7月,肯尼迪提出了“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宏大构想”,称如果欧洲能够不断完善其联盟并保持同美国的合作,美国愿意与这样一个欧洲实体平等、相互依存地交往。但这一构想也并未真正转化为现实,在此后至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西洋“伙伴关系”外交依旧是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而非在美国和一个新的欧陆集团之间展开。事实表明,由于受冷战格局和欧共体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因素的制约,这一时期并不存在建立真正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到了80年代末,随着欧共体内外形势的发展,构建某种新型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前景出现了一些曙光。美国国务卿贝克提出了“新大西洋主义”,强调美欧之间应建立制度性的磋商网络。(19) 德国总理科尔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我们必须加强欧美之间的协作,并在必要时建立新的机构。”(20) 在贝克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进一步提出为美国与欧共体的关系建立一个法律基础,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于1993年呼吁提升美国—欧共体关系并使之正式化。(21) 显然,美欧双方都意识到了冷战后大西洋关系调整与重构的必要性,并有意为此累积共识。
关于建立一种新型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讨论真正开始于1995年2月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外长和英德两国的国防部长共同提出签署一项大西洋协定的想法。法国外长朱佩主张订立一个“新大西洋宪章”;德国国防部长吕厄强调,“美欧伙伴关系必须成为一个全面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共同体。必须把旧的大西洋联盟中那种以安全保护换取影响力的讨价还价(美国通过提供安全保护来换取领导权)转变成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大西洋契约,以处理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一战略问题。”北约是一桩“摩门婚姻”,美国作为一个善意的族长统治着一群感激涕零的欧洲伴侣;现在需要的是建立两个平等伙伴之间的现代婚姻。(22) 科尔、根舍等德国政治领袖赞成订立一个新的大西洋条约,以便将1990年的跨大西洋声明变成“欧洲和北美之间的一个全面的条约”,并组织一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3) 英国首相梅杰1995年4月访问美国时也提出了签署一项大西洋自由贸易协议的想法。概言之,欧洲人认为欧盟与美国之间的新联盟应当建立在大西洋两岸经济一体化和双方文化共通性的基础之上,为此需要先建立一个正式的经济联盟,以便为双方的新关系奠定牢固的基础,然后再建立一个政治和安全联盟。
美国对欧洲方面的倡议做出了表面上的积极回应。1995年6月,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马德里发表演说,承认大西洋关系难以靠怀旧来维持,称每代人都必须适应时代的挑战以更新这一伙伴关系;(24) 克里斯托弗肯定了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想法,称它为一个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勾画了远景;这样一个跨大西洋关系不应只包括安全问题和只建立在北约基础之上,还应建立在不断加强的政治与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他指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伙伴关系一定能建立起来,我们有责任通过共同的努力以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从而确保我们的关系在今后50年会像过去50年那样伟大。”(25) 基辛格1995年在伦敦发表演说称,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应让位于美国同欧洲的特殊关系,他建议成立一个北大西洋自由贸易集团,以便为这样一种关系打下经济基础。(26) 在基辛格看来,北约本身并不能创造一种新的大西洋共同体意识,因为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安全已不再是将大西洋两岸团结在一起的主要因素和纽带,现在“到了建立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了”。(27)
虽然都宣称新的大西洋关系应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但实际上美欧对于双方关系“新基础”的认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美国和欧盟曾于1990年11月发表跨大西洋声明,1995年12月又签署了新大西洋议程(NTA),这两份文件包含了一些共同的原则,并就双方会晤磋商以及在诸多领域开展合作和采取联合行动等达成了谅解。但是欧盟对此并不感到满足,认为仅有这些原则和谅解不足以使欧美关系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主张为欧美新型关系建立一个约束性的框架,亦即双方应在签署一项新的大西洋协议或条约的基础上形成平等的伙伴关系。法国要求重新书写北大西洋公约,由欧盟和美国作为平等伙伴签署新的大西洋宪章。德国虽不主张对北约条约做彻底的修改,但是认为必须进行调整,以使之转变成为“一个新的大西洋公约”。总之,欧盟主张“另起炉灶”,在订立一项新条约或协议的基础上重构跨大西洋关系。
美国声称愿意看到一个新的更加平衡的大西洋关系,但认为没有必要同欧盟订立一项正式条约;虽然双方尚未在外交政策领域形成全面的伙伴关系,但是“在该领域确实存在着伙伴关系的成分,其形式是合作性的行动和声明”。这种伙伴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将主要取决于欧盟成员国能否成功地实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28)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旧的大西洋关系原本就不平衡,加上美欧(盟)双方在组织结构及大西洋两岸社会等方面尚未完全准备好,此时缔结一项全面的伙伴关系协议或条约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而且这样做也是无益的。假如订立一个全面的伙伴关系条约而结果却未能获得批准,那么它造成的政治破坏将是无法挽回的。(29)
美国反对缔结一项新条约的表面理由是欧盟自身存在缺陷(即欧盟还不是一个能够作为美国的平等伙伴、与美国达成一项全面条约的统一行为体),实际原因和考虑却要复杂、深刻得多。首先是受到国内僵化体制的制约。在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力量通常会增强,任何制度或体制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僵化。(30) 美国的宪政体制根本上是为了防止错误的行动,而不是促进可能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变革,无形之中强化了美国对变革的抵制。体制和机制的僵化也使得美国难以打破自闭的民族落后意识,这点透过美国拒绝向其欧洲盟友和竞争者开放市场的行为可见一斑,即便这种开放给美国带来的过渡性阵痛很小。(31)
其次是受到了主权问题的制约。欧洲国家大都有在二战中战败的经历,因此在战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能相对容易地接受主权的让渡;而美国的经历则完全不同,它不仅没有战败的记忆,还习惯了统治全球。事实上,美国从未真正面临过不得不放弃部分国家主权的挑战,孤立主义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是试图通过完善国内民主和避免纠缠于外部事务来树立“高尚的”榜样,后来威尔逊尝试用美国的民主模式塑造世界体系,从而打破了这一最低纲领派的观点,但美国仍坚守着国家主权的底线。冷战后美国拥有的支配性权力以及对自身价值观的坚定信念,构成了其坚守国家主权的最大动力,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同欧盟订立正式条约的意愿。
再有就是大西洋两岸社会疏离所构成的制约。冷战后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和公众对美欧联盟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总体上趋于弱化。老一代美国人大都有过在欧洲从军的经历或是在欧洲有亲戚,因此他们对欧洲怀有某种亲切感,至少存有某种深刻的记忆。而当今一代美国人对欧洲的关注明显少得多,尤其是随着拉丁裔人口日益增多,美国社会中的欧洲“印记”正在削弱。据有关学者分析,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对欧洲的兴趣自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急剧下降了。“虽然莫内和欧洲其他重要官员可以轻易接触到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肯尼迪,但是在老一代美国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后,如今的欧洲官员们很难再同新一代的美国政治家建立起非正式的联系……(美国的)这些领导人对构建他们前辈们设想的那种世界没有多大的兴趣。”(32)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斯坦利·霍夫曼说,“欧洲一体化初期有莫内、舒曼、加斯贝里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起推动作用,建设‘1992年欧洲’的事业也聚拢了德洛尔、撒切尔、科尔和密特朗等一批领导人,但今天的欧洲却明显缺乏有智慧的精英和有胆识的远见。”(33) 而与美国拉丁裔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相似,欧洲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口数量也在日益增多,这两股不同的移民潮正悄悄地把美国和欧洲越拉越远。
最后是更为关键的权力政治因素的制约。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际来看,若想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确实需要欧盟发展成为一个统一、有效的欧洲行为体,但美国在该问题上陷入了困惑:一个更加统一的欧盟固然能在处理欧美关系上变得更加有效,但这样一个欧盟又有可能产生某种霸权倾向,并给欧洲的市场开放带来更多限制。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欧盟因顾忌美国的这种担心而在深化内部一体化方面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结果不仅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反过来又为美国指责自己的“缺陷”提供了口实。
综上所述,美国和欧盟在跨大西洋关系重构问题上的互动和博弈虽然有妥协与协调的一面,但更多暴露出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在是否应为构建一种新的大西洋伙伴关系订立一项条约或协议的认知差异背后,反映出美欧之间深层次的利益与战略分歧。从本质上讲,跨大西洋关系重构问题上的美欧博弈是双方长期以来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某种延续。
三、“平等伙伴关系”的迷思
换个角度说,美欧在跨大西洋关系重构问题上的分歧也与双方对“伙伴关系”性质及内涵的认知错位有关;而双方在“伙伴关系”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博弈,也是美欧关系历史延续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二战后美欧合作与纷争的历史表明,双方对于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概念及其内涵的认知存在严重错位。简言之,欧洲人认为“平等”乃是“伙伴关系”应有之意且是其核心内涵;战后欧洲国家搞一体化既是要维护和促进欧洲自身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谋求与美国的平等地位。戴高乐曾经对西德总理艾哈德说,他并不“排斥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建议,但希望这种伙伴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34) 而对于美国来说,“伙伴关系”意味着西欧应当配合美国的战略,分担美国的负担(即所谓“财政上的伙伴关系”)。美国希望通过提供安全保障以换取西欧在其他领域支持美国,并拥护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肯尼迪曾说,美国真正拥有的“唯一杠杆”就是“核技术和核能力”,“在50年代,欧洲人把时间花在了挣钱上,而我们则花时间造原子弹。伙伴关系实际就是用他们的钱来交换我们的原子弹。”(35) “伙伴关系”还意味着必须阻止戴高乐及其他西欧国家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欧洲的企图,因为这样一个欧洲是与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相冲突的。当然,政治上难以做到“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西欧在美国看来也没有资格与自己平起平坐。冷战时期美国虽然抛出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计划和倡议以对盟国进行安抚,但是由于并不想真正给予西欧平等的伙伴地位,这些计划和倡议皆是雷声大、雨点小,难怪基辛格60年代以“麻烦的伙伴关系”来定义美欧关系。(36)
冷战后虽然美欧(盟)对于重构跨大西洋关系的必要性拥有共识,但不足以克服双方在“伙伴关系”问题上的认知差距。欧盟希望同美国建立一种“新大西洋伙伴关系”,而“新”的核心在于“平等”。换言之,欧盟构想的“新大西洋伙伴关系”要求认可欧洲性质上的变化,尤其要承认欧盟国家日益一体化的事实。而这样的认可对于美国而言则意味着其欧洲霸权将成为过去,美国同样也将失去其在大西洋联盟内扮演的(主要是针对德国)“平衡者”角色,不能再把德国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战略影响因素(即把德国作为其在欧洲大陆的一个“附庸”)。(37)
美国时常拿欧盟自身的“缺陷”说事,强调欧盟发展并拥有可信的安全和防务能力是双方形成某种更加均衡的新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前提条件。虽说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但是从总体趋势看,欧盟仍可能继续朝着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政治实体的方向发展,从而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提供重要基础。如此,问题的关键仍在于美国是否会支持欧盟继续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抑或接受或者准备接受欧盟要求的那种“新大西洋伙伴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或许仍需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肯尼迪、尼克松和老布什政府都曾尝试对大西洋关系进行调整,以使之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及美欧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每次“调整”时美国都要求西欧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以此作为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条件;西欧虽有些不情愿却终究还得按美国的要求办。但令欧洲人感到失望的是,每一次“调整”都没能带来他们所希望的大西洋从属关系结构的改变。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后仍在延续,小布什政府甚至比肯尼迪和尼克松政府更明确地坚持捍卫美国的领导作用。(38) 历史表明,美国同欧洲从未有过真正平衡的关系,如今也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点。孤立主义时期美国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担心“新世界”被“旧世界”腐蚀;冷战期间美国作为西方霸主根本不担心会受到欧洲的过分影响,实际上是美国控制了欧洲;冷战后美欧双方实力虽然趋向于某种均衡,但美国仍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只要欧洲在军事上继续依赖美国,它就不可能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简言之,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其控制欧洲的既定战略不变,抑或是欧洲仍持续不断地追求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则重构一个更加平衡和平等的跨大西洋关系的前景将不会乐观。
美欧在是否应订立一项新的条约或协议上的争执是双方围绕“伙伴关系”命题的博弈再现。美国对重构跨大西洋关系施以口惠,但是并不想就建立一个新的全面和机制化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同欧盟签署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条约或协议。针对欧盟提出的新大西洋关系应借鉴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经验的主张,(39) 美国称1990年的跨大西洋声明已经把欧洲政治合作机制的有关成分纳入了大西洋对话;1995年欧美联合工作小组成立后,美国认为大西洋磋商机制中已经有了某种类似于欧洲政治合作中的政治委员会机制,可用以处理北约未能涉及的一些事务,至于其作用能否得到发挥则要看双方的政治意愿。换句话说,美国认为美欧之间已经拥有了一个可以对北约进行补充的机制性的对话磋商框架,尽管双方并未签署一项全面的条约。可见美国的主张是仍以北约作为新大西洋关系的基础框架,并通过大西洋对话磋商机制对北约进行补充。与此相关的另一种方案是以北约为基础,通过对其进行重组以建立新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把北大西洋公约转变为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协定,该协定将维系美欧之间的军事联盟;但是与以往不同,这一新的安排不要求美国继续在欧洲驻军或者只要求美国保留一些海军和空军分队,以及在特定一段时间里弥补欧洲在后勤、通讯和情报等方面的不足。如果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无疑将会显著改变北约及美国在北约中的作用;然而这样的改变似乎又与冷战后北约的演进趋势大体相符,毕竟从长远看,无论是美国公众还是欧洲国家都不会支持美国永久保持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因此不如化被动为主动,通过赋予欧洲在联盟内的“平等”地位来构建新的大西洋关系。但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也是有条件的,即欧洲必须在大西洋联盟转型前向美国做出两点承诺:一是欧洲必须对自身防务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一是认同新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将是一个全球范围的联盟,参与国应同意采取共同行动,不仅要防卫自己的领土,还要在本国领土之外追求共同利益。
不难看出,与欧盟要求在新的基础上(而不是继续维持北约的基础结构)发展新大西洋关系的主张相比,美国仍试图维护北约在新大西洋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即便是美国准备放弃一些利益和同意重构北约(以给予欧盟更多的发言权),其让步也是有限的。美国尤其不会放弃其作为欧洲的“平衡者和保证人”以及作为“地缘政治的平衡者和仁慈的仲裁者”的作用。(40) 因此,不应指望美国对大西洋联盟做出结构性调整。相较于双方战略利益上的分歧,近年来美欧之间的经济关系有所加强,尤其是2007年大西洋经济一体化协议的签署被视为双方在深化经济领域合作和发展新关系方面取得的一个进展。不过该协议也仅是一份政治性宣言,并不真正具备法律约束效力,况且其签署很大程度上与双方的短期需求有关。美国不顾欧洲盟友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大西洋联盟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小布什政府急需调整对欧政策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而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无疑是最好的润滑剂。另一方面,欧盟也有意通过签署该协议来缓和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总之,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仅仅是试探性的,该构想变成现实仍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中包括双方在运行机制、一体化程度和组织形式上存在的较大差异所构成的制约。
总之,美欧长期以来在“伙伴关系”问题上的认知错位,继续影响并主导了冷战后双方在重构跨大西洋关系问题上的博弈。欧盟要求的那种“新大西洋伙伴关系”无疑将会比美国主导的旧的大西洋联盟关系显得更加平等,但问题是美国无意对大西洋联盟做出结构性的调整,因而“平等伙伴关系”对于欧洲人而言依旧是一个迷思。
四、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目前,构建一个新的全面和机制化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仍缺乏现实基础,但是在重构跨大西洋关系上的美欧博弈将会继续下去。当前美欧关系处在这种重构的理想与现实之间,预判其动向和演进趋势应当把握如下几点:
首先要指出,冷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霸权性目标(防止欧洲出现挑战美国的霸权以及将欧洲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与欧盟追求的自主性目标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而且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难以克服。有观点认为,如果美欧共同做出妥协,即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继续保持开放体系,而美国亦放弃其霸权政策,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彼此都能够接受的“相互依存的平衡”,如此或能消除双方目标之间的对立和紧张,至少有可能使二者的矛盾达至某种调和。但说易行难,鉴于冷战后双方利益与战略目标上愈益扩大的分歧,达至并维持这样一种平衡谈何容易!美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仍是妨碍冷战后跨大西洋关系重构的最大制约因素。
其次应认识到,尽管短期内难以建立一种全面和机制化的新大西洋关系,但是美欧关系有可能在渐进的过程中发生演变,从而形成某种局部性的伙伴关系。事实表明,现实的妥协而非宏大的设计是摆脱当前困境的可取方式,这一模式遵循了功能性差异的原则,有助于促成“局部性的大西洋伙伴关系”。(41) 例如在军事安全领域北约和欧洲军团之间的妥协(1992—1993),以及北约和西欧联盟在“诸兵种联合特遣部队”问题上的妥协(1994—1996),这些妥协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敏感的安全问题没有同其他问题领域牵扯在一起,而其他一些主要安全问题,包括欧美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磋商安排,也不大可能在北约之外的机构框架内获得解决。有鉴于此,美欧安全关系今后可能会呈现某种既收缩又扩张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欧盟安全防务政策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其决策过程日益独立于北约;另一方面,欧盟应对和处理国际犯罪、难民和移民等软安全问题的能力提升又可能会促进美欧安全关系的扩展。又比如在经济和贸易领域,欧盟早已是一个统一的经济行为体,且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进一步改善了欧美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双方形成某种大致均衡的经济伙伴关系。此外,功能性差异模式和问题领域的区隔,也有利于商业共同体通过合作方式来管理美欧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并防止某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外溢”到其他领域。
最后要强调的是,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看,对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走向持过于消极的判断并不足取。今后一个时期,美国仍可能继续保持其世界“一超”的地位,仍将处于全球政治的中心。而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也会继续扩展其权限(包括获得外交和防务领域的权限),从而为建立与美国之间更加均衡的伙伴关系创造条件。从趋势来看,结构性力量无疑在推动美国和欧盟走向一种更加平衡的新型关系,但是最终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欧双方适应新的形势变化的能力。假以积极的思维,如果美国真能不滥用其支配性权力而欧盟也不介入同美国的霸权竞争,或许双方有可能通过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的一体化来拓展双边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反之,如果美国仍一味地固守其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并阻挠欧盟发展独立的外交政策,那势必会对美欧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不排除出现一个针对美国的欧洲平衡力量,以及双方之间发生经济“霸权之争”的可能。(42)
五、结语
合作与冲突是贯穿当代美欧关系发展变化的一条主线,而研究者对于美欧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孰多孰少、孰强孰弱的判断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量的标准。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些非正式或临时性的联盟相比较,二战后建立的大西洋联盟堪称世界史上迄今最为持久、最为成功的联盟;虽然联盟内始终都存在着冲突因素,但是在冷战格局之下,双方战略利益的根本一致决定了合作是美欧关系的主导面。斗转星移,世事变迁。面对冷战后新的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新的挑战,美国和欧盟认识到旧的美欧关系模式已不能适应彼此外交政策的需要,因而都希望对之实行变革。美欧关系随之进入了一个历史性和结构性的调整时期,所谓“结构性”调整,主要就是指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亦即构建一种超越传统的大西洋联盟框架,包括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在内的新型美欧双边关系。美欧关系的内涵的扩展,意味着这一关系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冷战期间美国主导了大西洋联盟的话,那么,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进程中欧盟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虽然美欧双方对于重构跨大西洋关系的必要性有着共同的认知,但是重构这一关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却存在着差距。美欧在利益和战略目标上的差异和分歧,决定了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从表象上看,大西洋联盟和美国与欧盟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较冷战时期明显增多,竞争的一面更加凸显。欧盟要求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诉求反映了其对旧的大西洋从属关系的不满,这实际意味着对美国欧洲霸权的挑战。当然,美国也决不会放弃其在美欧关系中的既有利益,甚至还谋求获得更多的利益。由此观之,美欧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在美欧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复杂关系中,合作依然是主导面,或者说合作仍大于竞争。欧盟虽然不满于旧的大西洋从属关系,但是目前它在安全方面仍离不开美国,也仍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大西洋联盟虽然趋于衰落但在短期内仍不至于瓦解。
总体来看,现阶段跨大西洋关系调整的特点,犹如2005年2月2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欧美间存在的是一种“菜单式伙伴关系”,即在某些问题上,双方观点一致,并尝试合作;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双方意见不合,存在冲突;或双方虽然观点各异,却愿意寻找共同点。这一关系复杂调整的特点提示我们,判断今后跨大西洋关系重构的趋向与走势应避免极端倾向,既不能无视冷战后美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不能夸大美欧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既要看到高度相互依存的美欧关系仍难以摆脱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根本性制约,即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政治体系内,名为盟友的欧洲(欧盟)和美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竞争者甚至是对手,同时也要清楚,美欧之间的竞争不大可能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冲突,而将更多地体现为“合作性竞争”,其结果是彼此之间有可能形成某种“合作性均势”。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或可作为对今后一个时期跨大西洋关系演进特点的一种相对稳妥的判断,其正确与否将由实践来检验。
注释:
① 关于欧美学界对美欧关系研究的概述,请参见赵怀普:《欧美学界美欧关系研究述评》,《美国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根据政治、经济、文化或实际考虑,欧洲的边界线并不总是一致的,故而产生了若干不同的“欧洲”观念。若从世界政治的视野观之,则“欧洲”有三个主要涵义:一是指近代以来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作为民族主权国家的欧洲各国;二是指二战后作为美国主导下的跨大西洋联盟(北约组织)成员的欧洲盟国;三是指作为战后欧洲一体化产物之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也就是说,当代“欧洲”具有三幅不同面孔,即“民族国家欧洲”、“北约欧洲”和“欧盟欧洲”。
③ 虽然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同英、法等一些欧洲国家结盟,但这些联盟属于临时性的战时同盟,不构成美欧关系的常态。
④ 关于早期美国与欧共体的关系,请参阅 R.Ginsberg,Foreign Policy Ac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The Politics of Scale,Boulder:Lynne Rienner,1989; R.Ginsberg and K.Featherstone,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1990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
⑤ Geir Lundestad,“Toward Transatlantic Drift?”in David M.Andrews,ed.,The Atlantic Alliance Under Stress:US-European Relations After Iraq,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28.
⑥ 赵怀普:《从“特殊关系”走向“正常关系”——战后美欧关系纵论》,《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第48页。
⑦ Henry A.Kissinger,Die Vernunft der Nationen,Berlin:Siedler Verlag,1994,p.895.
⑧ Financial Times Editorial,“Atlantic Dialogue”,Financial Times,July 13,1994,p.17.
⑨ “In Need of Fastening”,Economist,May 27,1995,p.6.
⑩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p.826.
(11) 转引自方详生:《处于十字路口的美欧关系》,《光明日报》,2003年5月9日。
(12) Charles A.Kupchan,The End of American Era: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Vintage Books,2002.
(13) A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iefing,Daimler-Chrysler U.S.-European Forum on Global Issues:Political Change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Its Impact on the Alliance,November 2,2006,http://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events/2006/1102europe/20061102.pdf.
(14) “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ttp://atlanticreview.org/archives/942-The-Future-of-Transatlantic-Relations.html.
(15) See Benita Ferrero-Waldner,“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U-US Relationship”,Breakfast Meeting at the French-American Foundation,New York,September 28,2007,http://europa-eu-un.org/articles/en/article_7343_en.htm.
(16) C.K.Streit,Union Now,A Proposal for an Atlantic Federal Union of the Free,New York:Harper,1949.
(17) A.K.Henrikson,“The Creation of the North Atlantic Alliance”,in J.F.Reichart and S.R.Sturm,eds.,American Defense Policy,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pp.296—320; L.S.Kaplan,The United States and NATO:The Formative Years,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4.
(18) C.A.Herter,“Atlantic Convention of NATO Nations:Declaration of Paris”,in C.A.Herter,Toward an Atlantic Community,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3,pp.79—90.
(19) Secretary of State Baker,Talk Given at the“Berliner Pressclub”,December 12,1989,in Euro-Archiv,4/1990,pp.D77ff.
(20) Werner Link,“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Dimension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in Geir Lundestad,ed.,No End to Alliance: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Past,Present and Futur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176.
(21) Mark M.Nelson and G.John Ikenberry,Atlantic Frontiers:A New Agenda for US-EC Relations,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93.
(22) Rick Atkinson,“U.S.and Europe Seek Stability but Wrangle over Bosnia”,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5,1995,p.A29.
(23) Werner Link,“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Dimension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p.177.
(24) Steven Greenhouse,“Christopher Backs Free Trade with Europe”,The New York Times,June 3,1995,p.3.
(25) Ibid.
(26) “There'll Always Be an...” The New York Times,April 2,1995,sec.1,p.9.
(27) Henry Kissinger,“For U.S.Leadership,a Moment Missed”,The Washington Post,May 12,1995,p.A25.
(28) Werner Link,“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Dimension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p.178.
(29) Christoph Bail,Wolfgang Reinicke,and Reinhardt Rummel,Medium-term Perspectives o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Baden-Baden:Nomos Verlag,1997,p.43.
(30) See Mancur Olson,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31) Thomas J.Duesterberg,“Prospects for an EU-NAFTA Free Trade Agreement”,Washington Quarterly,Vol.18,No,2,Spring 1995,pp.74—75.
(32) Pascaline Winand,Eisenhower,Kennedy,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p.366.
(33) Stanley Hoffman,“Europe's Identity Crisis Revisited”,Daedalus,Vol.123,No.2,Spring 1994,pp.21—22.
(34) FRUS 1961—1963,Vol.XIII,Washington,DE: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4,p.237.
(35) Walt Rostow,Recorded Interview by the John F.Kennedy Library,pp.131—132.
(36) See Henry Kissinger,The Troubled Partnership:A Re-appraisal qf the Atlantic Alliance,New York:McGraw Hill,1965.
(37)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以后,德国作为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附庸”之功能一直是美国对欧政策延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38) Geir Lundestad,“Toward Transatlantic Drift?”p.27.
(39) 欧盟的主张得到了美国一些学术机构和思想库的呼应,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外交政策研究所主张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政治合作机制(EPC)的“大西洋政治合作”机制;该大学的跨大西洋关系研究小组建议把1990年11月的《跨大西洋声明》所确立的磋商机制升级为类似于欧洲政治合作模式的“大西洋政治合作”,并将其置于一个总体的大西洋条约和一个“重新机制化的新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下。参见 Werner Link,“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Dimension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p.177.
(40) Werner Link,“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Dimension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p.175.
(41) Werner Link,“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Dimension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p.180.
(42) See Jeffrey E.Garten,A Cold Peace:America,Japan,Germany,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New York:Times Books,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