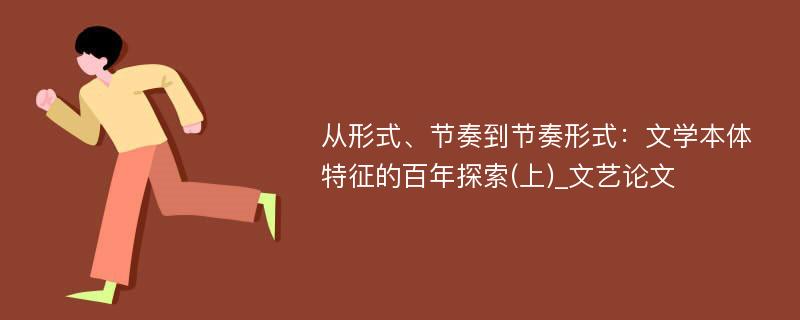
从形式、节奏到节律形式——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轨迹扫描(上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节律论文,本体论文,轨迹论文,上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01)02-29-05
探寻文艺本体特性,质言之,就是要弄清文艺活动的终极特性,从而最真切地把握它的自身性质与规律。笔者在《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中专门讨论了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问题,即对文艺活动的审美原生特性从人类生命存在的生态关联进行考察,从而对原来的“节律形式”和“节律感应”说作出生态学的阐释。这是从生命活动本源上进行的考察,是在起源中认识本体并进而认识本质,因为本体特性恰是最深层的本质所在。
认识文艺活动的本体特性,无论是对于正确而且充分地发挥文艺的功能还是文艺自身的发展都至为重要。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年,贯穿一百多年文艺论争和对抗中的一个核心,就是文艺的本体特性问题。为了充分利用和发挥文艺在社会改造和发展中的作用,人们总要对文艺的本体问题有所触及。即使像毛泽东那样,为了引导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当时的革命斗争而把“文艺的定义”问题搁置起来,也没有忘记要求人们重视文艺的特殊规律,在着重解决政治问题的同时,也指出“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就同一个问题而言,确实应该这样,以使定义符合实际。但是,在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就不能说只有政治现实才是实际,其实对什么是文艺的论识包括文艺的定义也是一种重要实际。如果连文艺究竟是怎么回事都没有恰当的认识,又怎么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它对革命政治的作用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忽视了隐含在文艺定义中的文艺本体特性问题,才使文艺走上了极端政治化的歧途。)经历了一百年来的探寻和争论,在新世纪的起点上,理应对文艺本体特性有更清楚而深入的认识。这是因为,在人类的生态现实中,不仅文艺活动对人类的生态功能问题比过去更加复杂而敏感,而且文艺自身的生态问题也日益突出。对文艺活动的本体特性有正确认识,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文艺能够做什么,并在此基础上认识文艺应该做什么;同时,也才能更充分地了解文艺自身生态优化的条件与趋向。笔者凭借生态思维的优势已从感应论审美观阐释了文艺审美活动以节律形式引发节律感应的生态本性,这一认识(或者说是一种阐释模式)应当说只是过去一百来年文艺本体探寻的一个延伸与综合,其中凝聚着许多思想家和文艺家的思维成果。本文仅就目及所见,展示若干重要的坐标点,以大致见出文艺本体百年探寻中一条值得注意的思想线索。
坐标点之一:王国维的“形式”说
文艺本体百年探寻中第一个自觉的探寻者是王国维,他秉承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明确地提出了具有鲜明的现代西方色彩的“形式”说。1907年,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从“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这一观念出发,认为“戏曲小说之主人翁及其境遇,对文章之方面言之,则为材质;然对吾人之感情言之,则此等材质又为唤起美情辽最适之形式。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注:《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247页。)这一观点显然是他的“意境”说的基础。他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注:《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5页。)这就是说,相对于情来说,一切景物都是形式。把此理生衍开去,文学作品中抒发情感的“情语”也是形式。因此,王国维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注:《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1页。)写真景物的情语有境界,也就成了表“意”之“境”,即引发情思的形式。在王国维看来,文学就是要创造这样的形式,其上者则有意境;所谓意境即一具独特情致内涵的浑然透明之形式。
这种形式本体说,旨在申说文艺超越功利的独立性和游戏性,使其成为于烦嚣的尘世之外得以超度人生、抚慰心灵的世界。它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形式与情感的对应关系,亦即“景”与“情”、“境”与“意”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又有意划地为牢,割断这种对应关系必然深入现实而与功利相通的生态联系。这种观点,尽管在学理形式上十分西化,但却无疑与中国传统的文艺本体观念相通,可以从中找到文道、形神、意象、情景等观念的灵魂。
以王国维的“形式”说为起点,中国古代文艺本体论的主流观念通过与西方近代美学交汇而开始走进了文艺本体探寻的现代进程。在往后的探寻中,西方美学成了越来越受重视的学理资源,同时中国传统文艺本体观念也逐步在会通中得到发现和阐释,并在二十世纪末实现了综合性的融会超越。对此,王国维“形式”说这个坐标点是功不可没的。
坐标点之二:鲁迅的“兴感—移情”说
第二个重要坐标点应是鲁迅早年阐述文艺鉴赏的“兴感—移情”说。
也是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阐释“诗力”之源时直接论及了文艺的本体问题。他在针对“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论述诗歌的功能时说:“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书,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谈,心弦立应,其声彻于灵府,令有情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这段论述巳包孕着他后来明言过的“感应”说。他不仅以“人应虫鸟,情感林泉”来描述这种感应之状,而且明确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同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所谓“兴感”,也就是“感兴”,亦即感应。这在他对修黎(即雪莱)的诗心的描述中表达得更为具体。鲁迅把雪莱对现实的诗意态度与功利和科学态度于崇高伟大美妙之现象“绝无所感应于心”的状态相比,特地指出他“心弦立动,自与天籁合调”的诗心。就是说,诗情诗意乃是生发于诗人对“现象”的感应,这种感应又因主客同调而发生;正是通过感应,才有诗歌使人神质悉移的功能。对此,他以游泳为譬写道:“吾人乐于观涌,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注:以上见鲁迅《坟》第47-67页。)而“游”,正是对感应活动中的生命状态和审美性质最生动而真切的描述。
到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引言”中,鲁迅说:“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可见他是赞赏厨川白村的观点的。厨川白村还阐释了鉴赏中“生命的共感”引起的体验。鲁迅明确地用生命律动来说明这种体验的感应特性,他说:“生命的最显著特征之一的律动(Rhythm),无论怎样,有从一人传到别人的性质。一面弹钢琴,只要不是聋子,听的人也就在不知不识之间,听了那音而手舞足蹈起来。即使不现于动作,也在心里舞蹈。即因为叩击钢琴的键盘的音,有着刺激的暗示性,能打动听者的生命的中心,在那里唤起新的振动的缘故。”显然,鉴赏的过程就是感应,文艺的象征也基于感应。“这样子,读者和作家的心境贴然无间的地方,有着生命的共鸣共感的时候,于是艺术的鉴赏即成立。所以读者、看客、听众从作家所得的东西,和对于别的科学以及历史家、哲学家等的所说之处不同,乃是并非得到知识。是由了象征,即现于作品上的事象的刺激力,发现他自己的生活内容。”(注:以上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页,第70-71页。)
在鲁迅的文艺观念中,文艺的移情功能源于感应,文艺对生活内容的象征也源于感应中的刺激,而引起感应的最重要的能动因素就是作为“生命的中心”的生命律动。在这里,生命的律动成了最重要的感应中介,并且因此也是最关键的象征中介。即然如此,文艺就是要表现这律动,创造这律动,文艺作品中表现的生命律动就是文艺审美活动的本体所在。一个文艺作品,如果没有这律动,就不能激发感应,也不能由感应引进审美的象征,也就不可能具有使人形质悉移的功能。鲁迅赞成从生命律动来说明文艺本体的特性,这无疑比王国维的“形式”说跨进了一大步,并且以这律动为中介把中国传统美学的感应和移情观念同西方的象征说相联结,显示了中国古代美学通过东西融会而获得现代阐释并具备现代形态的可能性,也显示了中国古代文艺本体观的现代意义。显然,在对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的回顾和反思中,鲁迅的观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坐标点。无论是对于全面认识鲁迅的文艺观还是重建文艺本体观来说,深入研究这个坐标点都非常必要。
坐标点之三:郭沫若的“节奏—感应”说
从感应体认和揭示文艺鉴赏的特性并且感悟到律动与感应密切关系的,在上世纪初,并不只是鲁迅一人,而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性的感悟。比鲁迅稍后,郭沫若以更加自觉而明确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节奏—感应”说。
1920年2月,郭沫若发表《生命的文学》,张扬与泛神论互为表里的生命哲学的文学观。在同年的《读诗三札》中还在继续阐发这种生命论文学观。到1925年他在大夏大学担任文学概论课讲师期间,先后发表了《文学的本质》和《论节奏》,集中地阐述了文学的本质在于生命节奏的观点,并依此构建他的“文艺的科学”的体系。对于这个体系,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的回忆中作了一个轮廓清晰的概述。(注:对此,笔者在《郭沫若关于“文艺的科学”的构想及其对美学理论建设的当代意义》一文中有具体介绍和评析,见《郭沫若学刊》198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1999年第3期)。)在这个体系中,郭沫若明确地视生命节奏为文学的本体,以此回答了“文学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郭沫若对文学本质的探寻,直指文学的本体特性,这在他自觉的方法意识中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他说:“我的方法是利用我的关于近代医学、尤其生理学的知识,先从文艺的胎元形态,原始人或未开化人及儿童之文艺上的表现,追求出文艺的细胞成分,就如生理学总论是细胞生理学一样,文艺论的总论也当以‘文艺细胞’之探讨为对象”。(注:郭沫若:《文艺论集》第207页。)这个意向,在《论诗三札》中就已十分明确了,他那时就认为,“要研究诗的人恐怕当得从心理学方面,或者从人类学、考古学——不是我国的考据学方面着手,去研究它的发生史,然后才有光辉,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注:《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第247页。)。这种发生学和细胞形态的研究方法的确认,充分体现了本体追寻的思维意向。郭沫若当时的方法意识,不仅以其方法论的自觉性而且也以其方法选择的科学性,在今天仍然对美学和文艺中的本体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正确的方法决定了目标的实现。郭沫若在对原始诗歌和儿歌进行提纯考察后指出:“诗到同一句或者同一字的反复,这是简到无以复简地地步的,我称呼这种诗为‘文学的原始细胞’,我们在这儿可以明了地看出文学的本质。”“这种文学的原始细胞所包含的是纯粹的情绪的世界,而它的特征是在有一定的节奏。”“节奏之于诗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的,决不是第二次的、使情绪如何可以美化的工具。”他得出结论说:“诗是文学的本质,小说和戏剧是诗的分化。”“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注:郭沫若:《文艺论集》第223-227页。)正是通过发生学的细胞形态研究,郭沫若认定节奏是文学的基元,亦即文学的本体。在他看来,文学的创作和欣赏都离不开节奏:文学创作是把激起情绪及其节奏的条件加以再现,文学欣赏则是由节奏引起相应情绪反射的“感应”过程。因此,文学的生命就是这节奏,文艺科学的核心范畴也是节奏。郭沫若还从中国古代美学中找到了这个结论的先声,那就是谢赫的“气韵生动”说。他解释说:“动就是动的精神,生就是有生命,气韵就是节奏,……艺术要有‘节奏’,可以说是艺术的生命。”(注:郭沫若:《文艺论集》第93-94页。)
郭沫若认为:“宇宙内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死的,就因为都有一种节奏(可以说就是生命)在里面流贯着。做艺术家的人就要在一切死的东西里面看出生命来,一切平板的东西里面看出节奏来,这是艺术家的顶要紧的职分。”这就从节奏的生命意义肯定了它在艺术中的本体地位。他由此揭示了节奏的普遍性,正是这种普遍性使节奏在物物之间、心物之间、身心之间建立对应、映照、交流和象征的关系。这种节奏论实际上把郭沫若过去信奉的泛神诗学科学化了。在这里,普遍存在并作为普遍中介的节奏取代了泛在于万物的“神”,同时它不仅像“神”一样赋予万物以生气,还以其类生命特征而显示、表征生命。进一步,由于节奏相互转变的规律,它还是引起感应的基因所在。(注:参见笔者《论郭沫若对泛神论的诗性接受和科学转化》,《郭沫若学刊》199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1999年第1期)。)
郭沫若非常重视节奏的美学地位,他认为“这节奏在诗的研究上是顶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学上的顶大的问题”。正是在节奏本体观的基础上,郭沫若建构了“文艺的科学”的初步体系。郭沫若深化了鲁迅的思路,并在更深入更全面的格局中加以考察,对中国古代的“感应”论和“气韵”说进行了现代化的科学诠释。可惜,他的这个构想没有最终成形,也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今天,我们把这一观点置于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的历史轨迹中来审视,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坐标点,它那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大综合视野和气度,还有那从方法到结论的科学性内涵,都使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闪射出格外引人注目的光辉。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宗白华实际上也持有与郭沫若相通的观点,并以他特有的艺术体验和中外美学的修养作了更加精辟细腻而剔透的论述,理应同时确立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坐标点。比起郭沫若的观点那昙花一现似的发表来,宗白华难得地终身坚持并阐述这一观点,以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更加耀眼地吸引着学界的眼光,并直接推动了文艺本体探寻的进程。因此,我们把这个坐标点置于二十世纪的后期,以期更加鲜明地显示其与鲁迅、郭沫若的观点相呼应并贯穿整个世纪的态势。
坐标点之四:现代诗人群的“象征—感应—节奏”说
郭沫若是一个诗人,他对文艺本体的认识凝结着自己诗歌创作中的体验和感悟。诗心总是相通的,在众多的现代诗人中,也广泛存在着与郭沫若同样的体认。仅就《中国现代诗论》的上编所载就可看出,从感应和节奏来认识和揭示诗歌的本体特性,已是许多现代诗人的共识。康白情、穆木天、王独清、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梁宗岱等,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过相近相通的见解。
在《新诗底我见》中,康白情从“感兴”谈诗,他说:“刻绘底作用,在把我底感兴,完全度与诗的人。”(注: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97-99页、第121页、第133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70-184页。)这就是说,诗人对形象的描绘,无非是要把引起自己感兴的事物生动地表现出来,以引起读者相应的感兴。
穆木天的《谭诗》着重论述诗的持续性,特别突出“波”和“律”的地位。他主张,诗人“要表现我们心的反映月光的针波的流动,水面的烟网的浮飘,万有的声、万有的动,一切动的持续的波的交响乐。”他说:“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波,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夕暮里若飘动若不飘动的淡淡光线,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他用“律”来指称诗的形式,“诗的律动的变化得与要表的思想内容的变化一致”。在他看来,“用有限的律动的字句启示出无限的世界是诗的本质”。(注: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97-99页、第121页、第133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70-184页。)
在《诗的格律》中,闻一多把诗的形式归结为格律,而“格律就是节奏”(注: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97-99页、第121页、第133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70-184页。)。徐志摩则认为“诗的生命是在他内在的章节(Internal rhythm),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凭你体会到得音节的波动性”。(注: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97-99页、第121页、第133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70-184页。)这些偏于唯美主义的见解,尽管过于执着于形式,然而诗之为诗不正在这形式上表现出它的本体特征吗?后期的戴望舒在《望舒诗论》中声称“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就意在克服形式主义诗学的偏颇,而强调诗的情感内容的诗性。他说“诗的自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他的意思很明白,“真的诗的好处不就是文字的长处”(注: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97-99页、第121页、第133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70-184页。),不只在于用“文字的魔术”在形式上音乐化,更重要的是思理和情绪本身那抑扬顿挫的“音乐性”。戴望舒的这个主张,正是后来的现代派诗人群的艺术追求。在他们的诗作中,情感和意象及其运动自身的节奏更受重视。
王独清同当时很多诗人一样,深受波特莱尔的影响,他明确宣告:“Baudelaire的精神,我以为便是真正诗人的精神。”(注: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97-99页、第121页、第133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70-184页。)而波特莱尔诗学的核心就是立足于“感应”(又译“感兴”、“契合”)。对此梁宗岱说得非常明白。在专门介绍评述象征主义的文章中,梁宗岱指出:“象征之道也可以一以贯之,曰‘契合’而已。”他生动地描写这种契合的境界:“当我们放弃了理性与意志底权威,把我们完全委托给事物底本性,让我们底想象灌入物体,让宇宙大气透过我们心灵,因而构成一个深切的同情交流,物我同一之间同跳着一个脉搏,同击着一个节奏的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粒细沙,一朵野花或一片碎瓦,而是一颗自由活泼的灵魂与我们底灵魂偶然的相遇:两个相同的命运,在那一刹那间,互相点头,默契和微笑。”(注: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97-99页、第121页、第133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70-184页。)以节奏为中介的契合(感应),同时也实现了象征。在《谈诗》中,他又说:“诗的真谛只是借联想作用以唤起我们心境或意界,或二者相并底感应罢了!牵涉的联想愈丰富,唤起的感应愈繁复,涵义也愈深湛而意味愈隽永。”(注: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97-99页、第121页、第133页、第106页、第161页、第170-184页。)在这之前论梵乐希(Paul Valery,又译瓦莱里)的文章中就曾说“节术底生命是节奏,正如脉搏是宇宙的生命一样”。(注: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上述见解虽然仅限于诗歌,但由诗歌在文学系统中的生态位所决定,这些见解实际触及了文学乃至艺术的共性。这所有的见解归纳起来,就是认为文艺的生命就是节奏,无论感应还是象征都是以节奏为基础和中介的。节奏乃是诗和文艺的本体特性所在。对于这些凝结着诗人们最本真的诗性体验的见解,应当予以特别的重视。
坐标点之五:朱光潜和林语堂的“节奏”说
在朱光潜著于抗战期间的《诗论》中,对节奏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不仅立专章在诗与乐的关系中论述节奏,还用三章来对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中的声、顿和韵分别加以详论。朱光潜是从佩特的“一切艺术都以逼近音乐为指归”的观点来考察诗的音乐性的,但他仅仅从诗歌的语言形式上看待这种音乐性,并没有明确肯定节奏对于诗和文学的本体意义。尽管如此,他的这些深入细致的剖析和对节奏的审美性质的揭示,仍然有助于文艺本体特性探寻向节奏的看重和趋近,以至到八十年代仍受到人们的重视。
朱光潜说:“节奏是宇宙中自然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自然现象不能彼此全同,亦不能全异。全同全异不能有节奏,节奏生于同异相承续,相错综,相呼应。寒暑昼夜的来往,新陈的代谢,雌雄的匹配,风波的起伏,山川的交错,数量的乘除消长,以至于玄理方面反正的对称,历史方面兴亡隆替的循环,都有一个节奏的道理在里面。艺术反照自然,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在造型艺术则为浓淡,疏密,阴阳向背相配称,在诗、乐、舞诸时间艺术,则高低、长短、疾徐相呼应。”这是从自然发生和艺术本性上说明诗与节奏的必然联系。他还指出“在生灵方面,节奏是一种自然需要”,人的生理节奏又引起心理节奏,并且“常不知不觉地希求自然界的节奏和内心的节奏相应和”,甚至“有时自然界本无节奏的现象也可以借内心的节奏而生节奏”。他说:“主观的节奏的存在证明外物的节奏可以因内在的节奏改变。但是内在的节奏因外物的节奏改变也是常事。 诗与音乐的感动性就是从这种改变的可能起来的。”这里所说的显然就是由节奏互动而生的感应现象。他还从节奏的“模型”引起的“预期”来说明节奏的功能,并且在论述节奏与情绪的关系时还谈到声音的节奏怎样“浸润漫延于身心全部”而唤起相应的情绪。(注:以上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第110-114页。)这些从生理和心理上对感应活动的阐释,已经触及音乐和诗的本体特性;既然一切艺术都逼近音乐,这也理当是一切艺术的本体特性所在。而且,从主观方面说节奏乃是包括生理、心理和意识在内的整个生命活动的特性,它不仅是主客双方相互感应的中介,也是人的身心之间相互感应的中介。十分遗憾的是,朱光潜未能从他所描述和阐释的由节奏应和引起情绪变化的事实中作出应有的理论提升。
值得注意的倒是林语堂,他于不经意间说出的话却更切近真理。在并非文论和美学著作的《苏东坡传》中,他以简练集中的方式明确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文艺本体特性的见解,指出:“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德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疾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艺术家爱慕书法时,他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走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他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抽象画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的抽象画。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美感便是律动感’),发展成为中国绘画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注:参见林语堂:《苏东坡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2年,第200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否由书法确立,这个问题固然可以讨论,但林语堂这段议论的美学内涵无疑丰富而又精辟,可以说远比许多专门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来得深刻剔透。在肯定美与运动的本体联系的基础上,他明确肯定“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仅把全部艺术囊括其中,还指出人品也有节奏存在,鲜明地揭示了节奏的普遍性。他说“美感就是律动感”,正说明美感是由主客体双方的节奏互动即感应引起的,节奏正是美感得以生成、艺术之成为艺术的本体所在,也正是艺术本体的特性所在。
对于林语堂的上述观点,可能谁也未曾认真对待过。但当我们将其置于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的历程中加以审视时,它无疑以明快和警策的方式让人不能不予以注意。林语堂以其对艺术精髓的特殊敏感而避免了不少专门的理论家难免遭遇的理性屏蔽。他的这段话,无意间对几十年间的探寻作了一个尚不全面却已直击核心的概括。
至此,中国的历史走到一道门槛边,往后五十年的探寻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中断和岐路之后,才主要依凭宗白华难能可贵的一以贯之的坚持得以承续和深化。对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后半段的扫描,将在下篇继续。
收稿日期:2000-02-19
标签:文艺论文; 郭沫若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鲁迅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