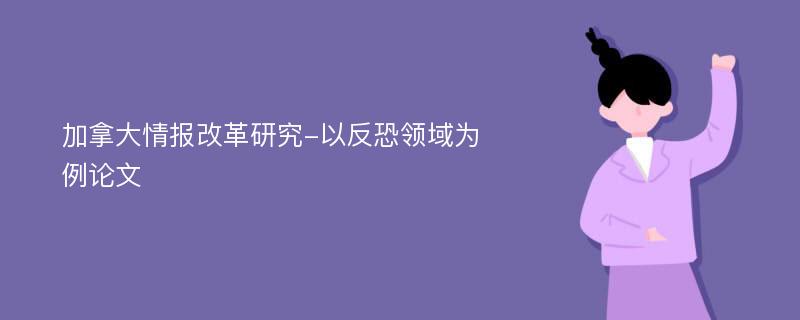
加拿大情报改革研究 *
——以反恐领域为例
李 子1马振超1范万栋2
(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2.山东警察学院 济南 250014)
摘 要: [目的/意义] “9·11”事件后,加拿大政府为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与国内极端组织的双重威胁,在情报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配合实施反恐战略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其经验教训对我国情报工作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方法/过程] 通过分析解读加拿大恐怖主义风险评估报告及反恐战略文件等资料,梳理加拿大情报改革的过程与主要措施,将改革内容划分为三个方面:组建新的情报融合机构、增加国家安全威胁类别、通过立法扩大反恐侦查权。[结果/结论] 我国在颁行《国家情报法》之后,可结合域外经验教训,在构建国家情报支援与共享机制、及时识别新型安全威胁、妥善处理反恐侦查权的扩张与规制等方面寻求突破。
关键词: 加拿大;情报;反恐情报;情报融合;极端组织;反恐侦查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兴起的恐怖主义日益成为威胁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9·11”事件更是掀起了全球反恐怖主义斗争浪潮。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主要是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与国内激进社会组织的双重安全威胁。为应对国际与国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加拿大在反恐情报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反恐情报系统的新架构,但在改革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
1加拿大反恐情报改革的措施
1.1机构整合:组建综合安全部 在“9·11”之前,加拿大的安全情报工作一直由联邦政府、警察、安全机构等角色分别承担,尚未设立综合的情报收集与研判中心。因为从历史上看,加拿大并不是国际恐怖组织攻击的焦点国,其国内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魁北克自由阵线的暴力行动,该组织的势力在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得到控制。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加拿大国内部门民众受圣战思想蛊惑,与境外恐怖组织取得联系,甚至接受中东地区极端组织的训练。加拿大政府2014年9月提出的一份报告指出“约有130名加拿大籍圣战者离境加入中东等地区的圣战活动,并且这一人数在不断增长。”[1]这不仅对所在国的安全造成危害,也直接威胁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因为这些接受了极端思想的人一旦回国,势必造成极端思想的传播扩散,甚至在加拿大本土策动恐怖活动。此外,近年来,在叙利亚参战的数千名美欧籍独立“圣战”分子回流母国[2],使北美地区独狼式袭击案件大幅上升,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现实威胁。迫于涉恐事件情报搜集与应急处突的需要,在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的主导下,从多个涉及安全领域的机构中抽调人员,组建了加拿大综合安全部(Integrated Security Unit,简称ISU),集中承担国家安全情报工作。
综合安全部的人员构成范围涵盖了加拿大的省属警察、市属警察、皇家骑警、国家安全情报局(CSIS)以及军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机构混合体。加拿大主要的联邦机构,如皇家骑警、国家安全情报局和国防部,都是综合安全部中的核心角色。综合安全部在加拿大设有两个分支机构,分别是为冬奥会组建的温哥华综合安全部(VISU)和为G8与G20峰会组建的多伦多综合安全部(G8/G20ISU)。2003年,在G8峰会和G20峰会即将举行的背景下,ISU成为实质上协调加拿大警力、保障美国和北欧参会国安全的警务中心。2007年,ISU内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ntegrated Threat Assessment Centre,简称ITAC),负责对来自境内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与预测预警。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TAC)集中处理所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情报收集与传递工作,是继加拿大联合情报组(Joint Intelligence Group,简称JIG)之后新的反恐情报整合中心。正是得益于ITAC在情报认知与分类方面的不断探索,加拿大反恐情报的实质性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一些新的威胁类型开始成为关注与监控的焦点。
1.2增加安全威胁类别:关注 MIE新型极端主义威胁 全球反恐时代到来后,除却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造成的威胁,一类新的安全威胁悄然浮出水面:许多西方国家的国内激进组织开始响应全球范围内的“正义运动”,在诸如生态环境、土著居民权利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等方面,策划实施一系列“新社会运动”,持续触动国内政治敏感点,形成了一股对抗政府政策的民间力量,成为各国安全机构的关注对象。
1.2.1 MIE的内涵 受国际环境影响与自身利益驱动,温哥华冬奥会筹办前夕,加拿大本土的环保人士和公益组织发起了广泛的反对抵制活动,使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TAC)的关注目光,从遥远的国际恐怖组织转向这些切实的、迫在眉睫的国内抗议运动和反对人士。这些由激进团体、土著群体、环保主义者和其他公开抵制政府政策的人所构成的威胁,被加拿大安全部门概括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国内极端主义”(Multi Issue Extremism,以下简称MIE)。此类左翼激进组织策划的社会运动,多数是为了反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或借由某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催动发酵,使用传媒造势、集会游行以及破坏财物等手段进行抵抗,对地区乃至全国的稳定局势构成威胁。例如,加拿大部分土著居民认为奥运区的土地权属有争议,策划了包括封锁道路、桥梁和铁路、占领办公场所和纵火在内的多项反奥行动,还号召民众围堵机场、火车站和码头。
MIE概念的前身是国家安全情报局(CSIS)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斗争”(Multi Issue Militancy),该报告列举出了一系列国内抗议活动的目录,例如在渥太华举行的反战会议(NOWAR/PAIX)、海洋守护者协会(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的行动、艾伯塔省的“YES MEN”讽刺表演等。但在之后的一系列报告中,加拿大安全部门普遍认可这种威胁的性质为“极端主义”,因此“以问题为中心的斗争”的说法变更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国内极端主义”。
随后的2007年7月20日,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TAC)为即将在魁北克蒙特贝罗举行的安全和繁荣伙伴关系会议(Security and Prosperity Partnership Meeting)发布了一份威胁评估报告,论证MIE正在逐渐成为威胁加拿大利益的中心要素,该报告指出:“(会议)的主要安全问题将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国内极端分子’可能进行暴力抗议。许多组织正在魁北克蒙特贝洛和安大略省积极组织和策划抗议活动。”同时,在CSIS于2008年8月30日发布的“国内恐怖主义局势”报告中可以看到,基地组织、独狼式袭击者和邪教徒等传统恐怖主义威胁仅占据少量篇幅,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左翼激进主义的。ITAC甚至在同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作出警告:“虽然‘以问题为中心的国内极端分子’的攻击往往不是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但美国2008年2月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MIE攻击发生的可能性是恐怖袭击的7倍。因此,基于高频率的袭击,MIE实际上比恐怖分子造成了更多的经济损失。”可见,MIE策划的社会运动已经逐步取代传统的恐怖主义,成为加拿大情报机构集中关注的新目标。
差异化教学是根据学生的特点、兴趣和天赋的不同,有针对性的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每个学生都有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学安排。通过这些安排,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积极自觉地学习,使得学生在自己最适合的方向快速成长,才能迅速提高,成为能够很好适应社会的人才。
人们总是要用什么东西填满移动时花费的时间,阅读与吃都是消磨时间的手段,也算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帮助人们度过飞驰的时光。现在人们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各种APP,看蛇精脸女生跳舞或者看宠物视频之类各种视频或者骇人听闻的各种网帖,让人没有空再来拿瓜子磨砺自己的牙齿。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关于MIE出现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界定。2008年11月的一份报告称,MIE包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对运动、全球反恐战争以及关于动物权利、反全球化的一系列运动”。在某些情况下,MIE的内容与全球正义运动直接相关,ITAC在2009年9月22日的一份报告中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例子:“许多抗议和暴力的共同原因是抵抗对资源的剥削、对原住民权利的侵犯和虐待动物,早在2001年,这些活动人士便聚集在魁北克,进行大规模抗议,对当地的社会稳定造成影响。”[3]
1.2.2 应对MIE威胁:构建“恐怖身份” 在加拿大综合安全部(ISU)中,针对反对派组织和激进分子的调查工作称为“任务摸排”(Mission creep),主要通过秘密监视的方式收集高风险群体的信息。但是这类监控行为在合宪性方面屡受公众的质疑,为了减少工作阻力,国家安全情报局(CSIS)开始利用警方、安全机构、情报机构与大众传媒的综合力量,构建一种“恐怖身份”(terror identities),使公众相信某类组织或个人具有真实的威胁性。通过建立MIE的“恐怖身份”,扩大情报机构的调查权限,从而使针对基层社会运动的国内间谍活动合理化。
不过,事实上,随着温哥华冬奥会的临近,“关键基础设施”的概念被扩展到各种各样的物体,如奥运场馆中的私营企业标志;与此同时,诸如核电站这样的大型国有设施的受关注度却呈下降趋势,甚至一度从威胁评估报告中消失。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TAC)越来越明确地将冬奥会的一系列象征物,都视为加拿大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例如奥运钟、奥运会会旗,等等,几乎任何形式的反对都等同于对平民的暴力威胁[14]。这无疑激化了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情报部门负担加重,模糊了真正应当关注的恐怖组织目标,尤其是对“独狼”式袭击和网络恐怖主义袭击等新型恐袭方式的关注。
式中K代表弹簧的弹性系数,F代表对其施加的外力,Δx代表施加外力后弹簧发生的形变。对同一根弹簧来讲,K与F、Δx没有关系,只与自身材质有关,但K要通过F和的比值才能测出。在胡克定律中,可以把F看作是外部对弹簧施加的扰动(或胁迫),Δx则是弹簧对这个扰动做出的响应。到这里,不难看出胡克定律中弹性系数K的含义和两个变量与国家脆弱性的含义和成因中的因素很相似,所以在此尝试通过胡克定律的表达式构建脆弱性指数的表达式。
构建“恐怖身份”的主要作用,是扩展情报机构的侦查权限。根据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TAC)所做的威胁评估是为了应对“名单上的恐怖组织以及在加拿大活跃的任何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极端组织”,将“恐怖组织”与“任何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组织”混合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宽泛的监控网络,使得原先处于安全部门视线盲区的组织和个人重新成为关注目标。
模糊威胁类别的做法已经成为加拿大情报机构的一项策略,在这项策略的指导下,许多新兴的社会运动和知名反对人士开始以“威胁国家安全利益”的形象出现在CSIS和ITAC的报告中,并被情报机构归入MIE总体威胁类别中进行监控。多年来,ITAC一直利用MIE这项威胁类别来监视一些公众知名度很高的组织,如“善待动物组织(PETA)”以及在所有威胁评估中最常被提到的“绿色和平组织”。
1.3法律修订:扩大反恐侦查权 加拿大自2001年通过《加拿大反恐法案》(Anti-Terrorism Act)以来,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反恐怖法律与政策文件,包括2012年《建设反恐应变能力——加拿大的反恐战略》《恐怖主义受害者公正法案》(The Justice for Victims of Terrorism Act ) 、2013年《打击恐怖主义法》(Combating Terrorism Act )以及2013年和2014年连续发布的《加拿大恐怖威胁的公开报告》等,这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扩大情报机构的反恐侦查权限方面不断新增条款。
五女山巅遍植枫树。每年的深秋时节,枫叶或红或黄,红得似火,黄的如金,还有的黄色枫叶又镶了粉边,层层叠叠,千姿百态,染遍层林。漫步于山巅彩色甬道,宛如画中一般。置身于南北二峰,可谓一步一景,如一幅隽秀的画面,让人百看不厌。感叹江山如此多娇!
a.在扩大监听权限方面,2001年颁布《加拿大反恐法案》第6条授权情报机构对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监听无需再遵循最后手段原则,第7条将实时监听的合法期限从60日延长至1年,第8条将对被监听对象的告知期限从监听开始之后的90日内延长到3年。该法案还授权情报机构拦截、监听位于加拿大境外的外国实体的通信信息,而不受加拿大刑法中关于禁止拦截私人通信规定的约束。
她把他变成一个在电视机前喝着啤酒入睡的男子。她成为养育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琐碎劳顿的主妇生涯中,每日辛劳操持家务朴素忍耐,每周一次独自出门,焕然变化成另一个女子衣锦夜行,如同少女时百无禁忌。否则她就会觉得被庸俗现实彻底湮没,身心无法勃发出生机。这分裂的生活又如何自治。当下只觉无限疲倦,再无力气踏出前行或后退的一步。坐下来,靠着门闭上眼睛,试图获得安睡。
b.在扩大羁押权方面,《加拿大反恐法案》创新性地赋予了执法人员实施预防性拘留的权力,即在认为危害即将发生或有必要时,可以实施无证拘留。并在2015年修订的新反恐法案中,将此项权力进一步扩大,放宽拘留条件,将预防性拘留条件中的 “有合理依据相信恐怖主义犯罪即将 (will) 发生”改为“有合理依据相信恐怖主义犯罪可能 (may) 发生”,将 “拘留是防止恐怖主义犯罪发生的必要(necessary) 手段”改为 “拘留是防止恐怖主义犯罪发生的可能 (likely) 手段”[8]。
c.在突破嫌疑人口供方面,加拿大的法律给涉恐案件的刑讯保留了余地,默认一些非常手段的可行性。2015年修订的反恐法案规定,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情报机构可以在加拿大本土或以外采取任何措施获取证据,而不必为所造成的伤害承担法律责任。情报机构的这项豁免权的例外条款十分有限,几乎只在发生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时才会被追责,而诸如饥饿、水刑、幽闭等会对人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却不致命的刑讯手段,均在被容忍的范围内。
除此之外,为配合应对来自社会面的新型恐怖主义威胁,加拿大一直在通过立法扩大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增加罪名,2012年的《加拿大打击恐怖主义法》增加了4个恐怖主义罪名,2015年的《加拿大反恐法》又增加了一个罪名。
2.4 水提工艺验证试验 按处方比例称取药材3份,按优选的最优水提工艺为条件,平行试验3次,测定浸膏得率和葛根素含量。见表7。
为什么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因为我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贫富差距过大,环境破坏严重,想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国的必由之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必然的。政府应通过进一步提升工厂排污标准来有效缓解污水排放的问题;同时加强生态建设,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此外,还应坚持走区域协调化发展之路,推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致富。更具我国区域的实际情况和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做好发展性政府投资。
2加拿大反恐情报改革评析
加拿大反恐情报改革在许多方面成效显著,有利于整合国内反恐情报资源、应对本土高发的新型极端主义威胁,也在机构设置、法律修订方面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反恐战略接轨,是全球反恐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改革措施从实施效果看存在一些问题。
当学习者期冀在生活工作的间隙实现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学习,借助移动泛在技术所实现的碎片化学习也就成为颇具潜力的一种学习方式。但是随之产生的碎片化、多任务和读图等特征所带来的学习深度问题也浮出水面。学习就是对碎片化的知识、信息等“构件”进行加工的过程[1]。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所构成的学习,往往具有浅阅读的特征导致由阅读所引发的思考变得支离破碎,进而让知识与思想也呈现出碎片化的危机[2]。
2.1组建综合安全部之利弊 加拿大政府整合国内反恐情报资源、组建综合安全部,是回应“9·11”事件中美国情报失败所采取的直接举措,有一定的必要性,也是加拿大政府在情报工作中转变冷战思维的表现。“9·11”事件暴露出美国情报工作最突出的问题,是在丰富的情报资源面前缺乏整合共享机制。美国曾拥有13个情报单位,分属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能源部、司法部、财政部等部门,它们之间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中央情报局长兼任美国情报系统的首脑,但他因缺乏作为情报首脑所必备的经费控制权和人事任免权而形同虚设[9]。各个情报机构间彼此独立的体制设置,导致职能重叠、壁垒高筑,情报资源非但无法在不同机构间形成交流共享,反而成为各部门进行信息封锁、资源垄断的牺牲品。
在冷战时期,虽然情报网络问题重重,但因资本主义阵营的“敌人”较为明确,情报工作的关注对象处于显性状态,各情报部门之间能够“一致对外”,达成某种合作平衡。冷战结束后,这种单一的显性敌人的状态被打破,来自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以及由发展带来的许多矛盾问题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性威胁。此时,基于威胁源的不确定性,情报的共享与整合显得尤为重要。而美国的情报部门未能及时转变思维,始终以冷战时期的思路来安排情报工作,对来自世界其他国家以及不同民族、宗教团体的信息敏感度不高,更遑论在整合情报资源的基础上做出一份较全面的威胁评估报告。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约翰·洛克菲勒曾说:“我们的政府没有把点连成线,从而导致‘9·11’事件的发生。”[10]
情报孤岛状态以及冷战后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不足,导致在面对重大恐袭事件时的情报失误。“9·11”事件后,美国果断对情报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重组,建立国土安全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负责搜集整合反恐情报,协调本土警力,防止恐怖袭击,在国内各大城市及西方主要国家均设有分部。加拿大政府紧随其后,借鉴美国模式,成立综合安全部的总部与分布,整合共享全国的情报资源;同时转变冷战思维,增强情报的敏感性,注重对重大国内外事件进行综合风险评估与预警。
表2从精确度和时延两方面进一步评估了算法的性能。作为比较,我们测试了其他深度学习模型的性能,比较模型包括一个两层的卷积神经网络(CNN),一个两层的循环神经网络(RNN)以及一个CNN-LSTM混合网络。其中RNN和CNN-LSTM中的LSTM部分的参数设置与表1所列相同;CNN和CNN-LSTM中的CNN部分采用了维度为[1,50]的一维卷积核,其余参数与表1一致。
加拿大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在满足反恐需要的同时,也是出于某些现实利益考虑。一方面,加拿大的人口稀少、国内市场狭小,出口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恐怖袭击频发的中东和非洲是加拿大重要的外贸伙伴。积极参与到国际反恐体系中,在国内营造对恐怖主义与激进主义零容忍的政策氛围,能够保护加拿大的海外利益与国民安全,也有利于树立国家安全形象,为扩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对加拿大的国内市场而言,作为世界第三大原油资源国和第五大原油生产国,油气投资一直是加拿大国内经济的支柱项目。而石油的开采、运输会与当地居民之间产生环境破坏与土地使用权纠纷等争议,因而遭到环保组织、人权组织与原住民的抵制。例如,耗时数年论证的北方门户输油管道计划(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由于沿线原住民的持续反对,于2016被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撤销。于是,为了减少政策阻力,加拿大政府将本土的环保组织、人权组织等冠以恐怖主义之名,对它们实施监控和打击,这是政府搭着反恐的“顺风车”谋求自身利益、排除反对者的策略。
推荐理由:最好的早教在家庭,最好的老师是父母。百万公号“大J小d”创始人大J从父母们普遍关注的“潜能开发”问题入手,介绍了潜能开发观念、潜能开发实战、情商力培养、游戏力培养、挫折教育、幼儿园教育、情绪引导等12个版块,书中不仅融合了美国早期教育专家、幼儿园老师和认知老师的理念,并将管理学思维应用到育儿当中,得到了广大父母的认可和推崇。
2.2创建新型安全威胁类别之利弊 将“以问题为中心的国内极端主义(MIE)”作为国家安全威胁的新类别,纳入情报监控网络,是保障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G8与G20峰会等国际重大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措施。
MIE组织借由温哥华冬奥会的时机发展壮大,在加拿大国内造成了许多现实威胁。首先,它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加拿大本土的活动支点。随着国内反对运动的持续暴涨,安全部门认识到,国外的恐怖势力可能利用国内的金融组织、公共卫生组织、环保组织等发挥作用,这些国内组织在表面上不具有恐怖主义表征,因此之前一直未受到安全部门的重视。经过分析认为,部分将矛头指向西方世界的国际恐怖组织,会以资本主义制度、基督教信仰、政教分离等因素作为策动恐怖活动的动因,此时,加拿大国内激进组织及抗议者的不满情绪和抵制运动,极易成为恐怖势力渗透、利用的对象。例如,由皇家骑警(RCMP)提供的报告中曾作出警告:“由于奥运会期间将有大量媒体报道(16天内有200亿观众),许多抗议者可能会将奥运会视为对抗全球企业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场所。”这些打着反对奥运会的旗号所策划的行动,并不会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而终结,因为抗议的根源是来自于加拿大本土的土地所有权争议和反贫困斗争。这些根源问题是持续存在的,也是境外恐怖主义可以长期利用的。
其次,MIE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关键基础设施(critical infrastructure),尤其是其中的大宗私人财产。早期的威胁评估关注的是核设施和其他敏感的公共基础设施,如电力线路等,情报机构一度认为恐怖主义威胁仅是外国组织(如基地组织)针对加拿大政府的行动。但之后,由综合威胁评估中心(ITAC)发布的报告显示,以MIE为代表的新兴恐怖威胁完全专注于对私人财产的破坏(如作为奥运会赞助商的企业)。ITAC曾在2008年11月的报告中指出:“基地组织、MIE组织、土著极端主义者都表示了攻击‘关键性设施’的意图和能力。”除了以常见的抗议形式进行阻挠,这些组织还会以封锁铁路、砸坏建筑物等方式对目标进行直接破坏。根据ITAC的这些报告,加拿大的安全情报机构将保护各地区的私人“关键性设施”作为重新分配警力资源的依据。
构建MIE“恐怖身份”在操作上的关键,是在威胁评估报告中尽力模糊“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威胁的区别,给那些有争议的基层组织贴上一个笼统的“恐怖标签”。国际社会上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界定本就莫衷一是,这为模糊处理二者的性质创造了条件。根据主流观点,恐怖主义大致可以被界定为:针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通过将特定对象置于恐惧和焦虑之中,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暴力斗争的策略和思想[4]。而极端主义,由于行为动因复杂、表现方式多样,其政治诉求不如恐怖主义强烈和明确,因此在认知上的分歧更多。一般而言,极端主义可以指行为人因推崇某一种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社会秩序、法律体系、政治秩序是至上的、决定性的、唯一的,而排斥、贬低其他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思想[5]。从对二者的界定可以看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在动机和表现形式方面都有交集,后者容易成为前者的诱因。社会心理学认为,恐怖主义与狂热的宗教情绪、狭隘的民族意识、心理失衡、复仇本能、盲目的集体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有关[6],而这些非理性因素都可以表现为极端主义,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作为恐怖主义的重要背景、思想根源和首要诱因,在政界和学界已成共识[7]。鼓动歧视与仇恨的极端主义,往往是暴力恐怖活动的思想基础,在恐怖主义日益泛滥的形势下,加拿大政府认为模糊威胁的类别是反恐警务工作的现实需要。
但是,在进行情报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庞大的组织机构建设与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也有过度占用公共资源、夸大恐怖主义风险之嫌。北美是全球恐怖威胁最小的地区,2007-2012年,恐怖威胁指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说明北美的总体安全状况稳步提升。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状况在2011年得到很大改善,并在2012年继续保持稳定的安全局面[11]。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加拿大政府不断追加反恐经费预算、扩大反恐机构规模。目前,加拿大综合安全部(ISU)及其分支机构已超过一万名警察,并且仍在继续融合更多警力。2001年的联邦预算,计划在未来5年内向反恐、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以及包括与美国的双边伙伴关系在内的国际安全行动提供了77亿加元。随后,在现有预算的基础上又注入3 700万加元的额外资金,直接用于研究开发反恐技术。2006年当选的新保守党政府重申了国家安全的财政优先事项,拨款13亿美元用于与安全相关的支出。2007-2008年,单加拿大通讯安全局(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简称CSE)这一个情报机构的预算已达到2.2亿加元[12]。资源的投入成本与面临的风险严重不协调,机构趋于臃肿,并影响到加拿大政府其他职能的发挥,削弱其公共服务能力[13]。
同时,情报机构模糊处理“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威胁类别的做法,也使得许多执法行为的对象边界不清,许多参与请愿活动、表达反对意见的民众被与极端分子、原教旨主义者混为一谈,被采取强制措施甚至入狱,这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对加拿大多年建立起来的自由、法治的社会秩序是一种损害。
2.3反恐侦查权扩张之利弊 加拿大通过立法扩大反恐情报的侦查权,一方面,是扩展情报来源的需要,例如,情报部门模糊恐怖威胁类别的做法,实质上是在扩大自身的侦查权限;另一方面,也是传统情报活动在反恐需求下的限制过多,需要进行调整的结果。
虽然加拿大的反恐情报改革存在许多问题,但仍然对我国的情报工作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2017年6月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以下简称《国家情报法》),并于2018年4月进行修正,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工作推向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应当以此为契机,吸收域外经验,将我国的反恐情报工作进行更加系统的规划与整合。
目前,大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但也有少数人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马列信“迷信”,不信组织信“大师”。习近平总书记尖锐地指出,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他们出了问题首先是因为理想信念垮掉了。“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⑧党员干部一旦理想信念产生动摇,精神支柱迟早会坍塌。因此,在思想建党的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抓住这一问题,就等于拧住了“总开关”,牵住了“牛鼻子”。
在全球反恐的严峻形势下,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通过立法对反恐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在秘密侦查权、讯问权、羁押权等方面显著放宽了限制条件,扩展反恐情报来源。而加拿大,作为美国对外反恐战略的坚定盟友,此前一直支持战争反恐模式,参与海外反恐行动,追加反恐财政开支,但这种做法并未给加拿大本土带来安全。2014年,加拿大接连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包括震惊世界的“10.24议会大厦枪击事件”,这使加拿大政府意识到,跟随美国脚步进行的反恐战争以及战争的扩大化,已经招致国际恐怖主义对加拿大的仇恨。因此,加拿大的反恐战略有必要向司法反恐模式进行适当转型,修改完善反恐法律,放宽对反恐侦查权的限制,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手段。
不过,各西方国家在扩张反恐侦查权的同时,也在侵犯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方面饱受争议和诟病。这些反恐法案普遍赋予了情报机构和警察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能够自行判断一个人是否需要被监视和搜查,而不是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立法中界定的“恐怖行为”概念十分宽泛,表征模糊,使得情报机构的侦查行动变得毫无规律,甚至在法律面前有失公平。减少了法律约束之后,执法和情报机构就可能以反恐为名滥用侦查权,例如,2017年4月,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名记者的通话记录,事后承认是判断失误[15]。
加拿大的情况也是如此,通过反恐法案扩张情报机构的权限,使得搜集情报与保护隐私权、公民权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也令部分反恐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屡受质疑。为扩展情报的来源,尤其在网络恐怖主义兴起的现实环境中,加拿大的情报机构不断加大对公民电话、邮件、社交平台等的监控、扒取,用以分析公民的活动规律、职业家庭状况、心理特征等个人情况,加拿大通讯安全局(NSA-North)甚至可以直接截获与加拿大通讯的境外实体的原数据。这些秘搜秘取的手段在新的反恐法案的授权下,几乎不受程序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和隐私权。
3加拿大反恐情报改革对我国情报工作的启示
现代恐怖主义具有显著的隐蔽性特征,其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攻击对象、破坏手段等均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因此其威胁往往是潜在的、多方面的;同时,由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嫌疑人心理更为顽固、思想更为极端,在抓捕后,运用常规讯问策略难以获取有效供述,这些都给反恐侦查及情报搜集带来一定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情报活动还要受到一系列法律规则的严格限制。在侦查阶段,出于保障公民自由权和隐私权的需要,秘密侦查措施受到最后手段原则、令状规则等程序规定的严格制约,必须经过严谨的审批程序才能实施;而在讯问阶段,任意自白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证据规定也在严格约束着审讯手段,对恐怖分子的审讯也只能依靠文饰、分化等常规策略。对情报机构活动权限的重重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为恐怖活动的预谋与实施提供了便利,有资料表明,在“9·11”之前美国情报部门已经觉察到一些苗头,但由于对监听、跟踪、监视等手段的严格制约,未能及时进行深入调查,因此错过了最佳预警时机。
3.1构建国家情报支援与共享机制 我国目前在国家安全层面上的情报工作,仍然分散在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军队等不同组织机构中,尚未建立统一的情报融合机构,也尚未实现社会中涉恐情报的汇集共享。习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我国国家安全体系扩展到11个重要领域,这些领域互相影响、相互交织,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局”,这种特点客观上要求情报机构实现情报支援与共享,方能满足国家安全的决策需求[16]。我国的《国家情报法》秉承情报资源融合共享的理念,在第三条中规定了国家安全机构和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并在第七条、第十四条中明确要求公民和组织有支持、协助、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的义务。
构建情报支援与共享机制,首先,在硬件方面,应当探索建立全国性的情报融合中心,作为国家情报常设机构。加拿大为整合情报资源而组建的综合安全部,虽然在人事、财政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确实为保卫其国土安全以及国家反恐战略的整体推行,提供了技术保障与风险管理。基于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情报中心,整合来自不同机构的情报力量,集中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的搜集、传递与研判工作,实现从宏观上对国内安全情报的总体把控,从而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重大事件风险评估等方面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我国2010年,7省在京签订的《环首都七省区市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框架协议》,强调在反恐、刑侦等方面的合作[17]。应当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建立覆盖全国的情报中心,可以借鉴加拿大模式,在各省及主要的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打通壁垒,实现情报融合。
其次,在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应当建立情报搜集、传递、共享的工作机制,培养合作共享的情报意识。我国《国家情报法》第三条中,虽然规定了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对国家情报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组织军队情报工作,但具体到各机构、各部门的情报职能与配合方式,在情报传递过程中出现信息抵牾应如何落实责任等问题,未做出细化规定,在实际的情报工作中仍然不免出现部门间的壁垒与内耗。同时,该法规定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应当配合情报机构的工作、保守秘密,情报机构也可与上述主体建立合作关系,这表明我国在统筹协调情报资源、促进社会各领域间的信息通联方面所进行的规划。下一步,应当在此基础上细化规定,健全情报工作协调机制,明确国家情报机构和公民的合作关系,以及情报机构内部的协同关系。除却情报部门,也在社会各主体间树立起及时发现、及时传递、实时共享的情报意识。
3.2及时识别新型安全威胁 加拿大的情报机构在此次改革中,通过增加国家安全的威胁类别,将MIE极端组织纳入管控范围,虽然此举遭受争议,但这也是其及时适应国内外新形势、重视情报知识建设的体现。受国际环境影响,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形势也日趋复杂多变,这其中不仅有境外恐怖主义势力、反华势力的派遣渗透,也有境内的民族分裂组织、宗教极端组织与暴力恐怖组织的勾连响应。尤其在网络时代,他们利用社交平台与自媒体、线上广播等途径,树立舆论代理人,煽动大众对热点事件、敏感事件的不良情绪,歪曲事实、掩盖真相,挑动激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一个具有迷惑性的舆论氛围。这比之直接的暴恐行动,影响更为深远,可能会误导青少年一代形成错误的民族观,使一些境内顽固的极端组织“后继有人”。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华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数目不断增长,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境外反华势力利用在华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公益慈善、学术交流等活动,收集情报、策反重点人员、渗透意识形态,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要求情报部门及时识别新出现的不安定因素,并做出有效的评估和反馈。具体来说,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a.情报机构转变单一向度的思维模式,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隐性问题)保持极高的敏感度,扩展情报来源。b.注重情报专业人才的培养选拔,结合我国《国家情报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建立情报人员的录用、选调、考核、培训等管理制度,可以借鉴加拿大模式,在各级安全机构、警察、军队或科研机构中抽调适应情报工作需要的人员,尤其注重因地制宜在本地区选拔人员,作为情报融合机构在各地分部的人才力量。c.情报实务部门还应当与各高校情报专业,以及各地的科技情报(信息)研究机构加强合作,结合我国国情,在建构情报知识、探索研究方法上实现突破。
近年来,在“健康中国”战略下,受益技术驱动,响应分级诊疗政策,各大型公立医院纷纷加大智慧医疗与全民健康事业的深度融合力度,旨在进一步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促进服务效率提升的智慧化项目相继落地。
除此之外,为促进情报研究及时把握国内外的安全形势,还应当加强对情报学科建设的关注与呵护。在我国,作为与国家安全关联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情报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与图书馆学、档案学混合在一起,基础理论薄弱,各分支学科关系混乱,甚至对“什么是情报学?”等元概念和元问题尚不清晰,这就给情报研究适应变化中的安全形势,识别、论证新的安全威胁因素带来困难。在实践中发现的涉恐人员、案事件的苗头趋势,难以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归纳,不利于情报部门研究制定较为全面的风险评估报告。因此,应当尽快实现情报学从图书馆情报学中分离,使之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以推进情报实战的有效开展。
3.3平衡反恐侦查权的扩张与规制 出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在反恐领域实施的侦查活动势必触及公民的自由权、隐私权等权利范畴,如情报搜集会涉及公民的个人信息,因此,需要在满足反恐需求的基础上对侦查权进行有效规制,以实现国家安全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兼顾平衡。我国《国家情报法》中对于情报机构履行职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如“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应当依法搜集和处理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利益行为的相关情报,为防范、制止和惩治上述行为提供情报依据或者参考。”(第十一条)并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第十四条)与此同时,《国家情报法》也制定了保护公民权益的条款:“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第十九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18]可以看出,《国家情报法》在平衡情报侦查权和公民权的关系上经过了审慎考虑。
西方国家以反恐需求为由,任意窃听、截取甚至泄露公民信息的做法屡见不鲜,加拿大此次通过立法扩张情报部门监听、监视等权力时,也激起了国内民众普遍的忧虑与反对。我国应当吸取教训,注重在反恐情报搜集中对公民、组织信息安全的保护,明确、细化情报机构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法律责任。
首先,设置反恐侦查权的合理边界。a.在立法中较为科学、明确地界定恐怖主义,避免将其概念扩大化。b.设置事前审查制度,将适用于反恐目的的特殊侦查措施严格限制在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内,与普通刑事犯罪的侦查相区分。c.禁止酷刑,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以非法手段刑讯逼取口供,以反恐为名行破坏道德与法律底线之实。
其次,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取得其对情报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在加拿大反恐情报改革中,多采取的是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比较强硬的措施,对公民和组织的活动进行限制、管控或者施加压力,缺少与公众间关于情报活动的意义、要素以及法律责任等事项的告知与沟通,引发了许多冲突。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情报透明度原则”,以公开的方式提供情报信息促进决策,从而增强公众对情报活动的理解,使公众明确泄露情报信息对国家及公众的巨大危害,促进公众自觉配合情报部门的工作。我国情报部门也可以借鉴相应举措,建立情报透明度委员会并制定透明度政策,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保护[19]。
最后,在条件成熟时制定情报监听法。监听是反恐情报搜集中最为常用的手段,其隐蔽性与专业性极强,离开法律的约束规范,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造成侵害。美国、英国等情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家情报监听法制体系,以规范政府部门的情报收集工作,防止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我国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当在《国家安全法》与《国家情报法》的统领下,考虑制定情报监听法,从情报监听的客体、规程、监督制约、资料的使用、救济程序等多方面进行法律规范[16],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保障公民权利。
参考文献
[1] 胡裕岭.加拿大:反恐立法在恐袭中推进[J].检察风云,2015(1):61.
[2] 严 帅.“独狼”恐怖主义现象及其治理探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4(5):47.
[3] Jeffrey Monaghan,Kevin Walby.Making up'terror identities':Security intelligence, Canada's integrated threat assessment centre and social movement suppression[J].Policing & Society,2012(6):133-151.
[4] 谈东晨.恐怖主义国际传播的身份建构转向[J].文化与传播,2018(4):48-49.
[5] 肖建飞, 孙志敏. “极端主义”与“极端化”含义分析——基于《反恐怖主义法》与新疆《去极端化条例》的文本考察[J].实事求是,2018(4):32-33.
[6] 吴 宁, 周艳华.恐怖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对策[J].襄樊学院学报,2005(11):16.
[7] 张金平.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策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王 林, 章立早.反恐背景下侦查权的扩张与规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8(4):47-50.
[9] 董鑫华.美国“9·11”事件情报预警失误与相应对策探析[J].四川兵工学报,2009(12):138.
[10] John T Rourke.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M].McGraw Hill De Mexico,2008:125.
[11] 樊守政.当前全球恐怖威胁新态势[J].现代国际关系,2013(3):24.
[12] Martin Rudner.Canada's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 signals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terrorism[J/OL].[2008-06-05].http://dx.doi.org/10.1080/02684520701640449.
[13] 唐小松.加拿大反恐战略评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5(4):27.
[14] Innes M,Fielding N,Cope N.Appliance of scienc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ime intelligence analysis[J].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05(1):39-57.
[15] Royes L.AFP officer accessed journalist's call records in metadata breach.[J/OL].[2017-04-28].http://www.abc.net.au/news/2017-04-28/afp-officer-accessed-journalists-call-records-in-metadata-breach/8480804.
[16] 邓灵斌.《国家情报法》解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的思考[J].图书馆,2018(8):54.
[17] 蔡士林.美国国土安全事务中的情报融合[J/OL].[2019-01-0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1.1167.G3.20190109.1055.002.html.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EB/OL].[2018-04-27].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7-06-28/content_4783851.htm.
[19] 张 鹏, 周西平.基于演进视角的美国情报共享研究——从“犯罪情报共享”到“情报融合”再到“情报透明”[J].情报杂志,2018(3):13-14.
Analysis of Canadian Intelligence Reform —— In the Case of Counter-terrorism Intelligence
Li Zi1 Ma Zhenchao1 Fan Wandong2
(1.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2.Shandong Police College, Jinan 250014)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ember 11,2001,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ffective reforms in intelligence in response to the double threats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forces and domestic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These reform measures have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coordinati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terrorism strategy, but they have also caused some problem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work in China.[Method /Proc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Canadian terrorism risk assessment report and anti-terrorism strategy document, we could untangle the process and main measures of Canadian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divide the content into three aspects: integrating new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agencies, increasing the categ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expanding the power of anti-terrorism investigation through legislation.[Result /Conclusion ]After the enactm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Law in China, breakthroughs can be made in building a national intelligence support and sharing mechanism, identifying new security threats in time, and appropriately dealing with the expansion and regulation of counter-terrorism investigation power.
Key words :Canada;intelligence;counter-terrorism 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fusion;extremist organization;counter-terrorism investigation
收稿日期: 2019-02-16
修回日期: 2019-03-19
基金项目: 公安部公安理论与软科学计划项目“叙利亚极端组织的嬗变对我国反恐怖工作的影响”(编号: 2017LLYJSDST024)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 子 (ORCID:0000-0002-8649-5870) ,女,1987年生,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国家安全与反恐怖;马振超 (ORCID:0000-0003-1489-3877),男,1964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范万栋 (ORCID:0000-0003-1836-0066),男,1983年生,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反恐怖。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12-0040-08
引用格式: 李 子,马振超,范万栋.加拿大情报改革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12):40-47.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12.007
(责编:贺小利;校对:刘武英)
标签:加拿大论文; 情报论文; 反恐情报论文; 情报融合论文; 极端组织论文; 反恐侦查论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论文; 山东警察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