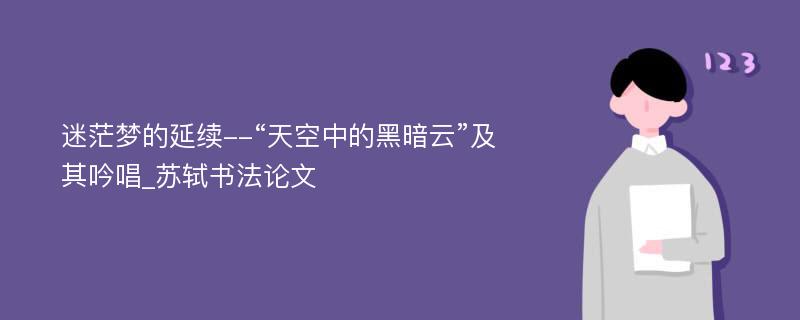
迷离梦事的续接——《天际乌云帖》及其题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云论文,天际论文,迷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9)07-0208-04
诗与书法的结合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形式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审美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书法通过羊毫、狼毫或其它书写工具将诗的精神生命铺展于纸上,赋予其亲切而实在的质感。而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们则可以“题诗”、“题跋”等形式,借助“帖”这纸质载体遥相唱和,实现精神感情的续接和传承。
著名的传世法帖《天际乌云帖》书写的是北宋大书法家、诗人蔡襄(字君谟)《梦游洛中十首》绝句之第一首: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
嵩阳居士今安否,青眼看人万里情。
传说《天际乌云帖》是苏轼笔迹,以灵动洒脱的行书写成。后来的题咏者也都相信该帖为苏轼听书。蔡襄和苏轼同为北宋杰出的书法家和诗人。蔡襄首先是书法家,苏轼对这位前辈极为推崇,曾说“仆论书以君谟为当世第一”[1],而苏轼诗歌成就为当世公认。《天际乌云帖》非蔡书苏诗却为苏书蔡诗,对于收藏者和观赏者来说会另有意味。无论其书是否苏轼真迹,此后该帖在世间流传。
《梦游洛中》诗前有序云,“九月朔,予病在告,昼梦游洛中,见嵩阳居士留诗屋壁。及寤,犹记两句,因成一篇,思念中来,续为十首”[2]。诗的前两句,即为蔡襄自注“梦中两句”。此两句诗意境清晰,对此鲜明,却从历代典籍中都找不到出处,恍如天外飞来,无据可查,使墨帖笼罩着一层神秘感。
诗后又加注:“司门员外郎王益恭年四十余,致政居洛中,自号嵩阳居士。”[2]宋时朝廷规定的致政(退休)年龄是70岁,而王益恭“四十余”就请退,此后“与浮图、隐者出游,洛阳名园山水,无不至也”。[3]蔡襄在病中梦见嵩阳居士王益恭题壁诗,因而《天际乌云帖》又称“嵩阳帖”。诗人与隐士青眼相看,在“天际乌云”的压抑气氛中,一句“嵩阳居士今安否”的问候,似乎在探询隐林中可有立椎之地能躲过“乌云”,退隐之意与豁达之情相照映。
《天际乌云帖》中,蔡襄诗句“嵩阳居士今安否”被苏轼改为“嵩阳居士今何在”,诗后附两段短文,也依苏轼的语气。蔡诗最后一句“青眼看人万里情”,结在一个“情”字,是表达名士间知已的友情,苏轼却笔锋一转,写到蔡襄的爱情:
此蔡君谟梦中诗也。仆在钱塘,一日谒陈述古,邀余饮堂前。小閤中壁上小书一绝,君谟真迹也:“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长垂玉筋残妆底,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闲愁何日尽,一分真态更难添。”二诗皆可观,后诗不知谁作也。[4]
“君谟真迹”的诗作从男性角度抒发对美人的思念,“绰约新娇”,人影恍惚,若有若无,正是怀想到了极致出现的幻象。而蔡襄的《端明集》并未收录这首诗。“不知谁作”的和诗描写美人此时在异地的情态,一说为苏轼所作,被收入明代万历年间焦竑、康丕扬、毛九苞汇辑的《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但此书的版本并不可靠。《外集》卷首有康丕扬的《刻苏长公外集序》,叙述发见底本的情况:“往余于京郊见一学士家尚有外集一书,系抄册,非完本,字多鲁鱼不可读,而其文亦多全集所未载。”[5]这说明《东坡外集》是辗转抄录而来,编校者也说不清楚来历。所谓“君谟真迹”诗及和诗其实都“不知谁作”,但二诗确“皆可观”。
无名氏的和诗想象美人此时在异地的情态。“肯为金钗露指尖”出自张祜与杜牧的联句。据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记载:“张祜客准南,幕中赵宴,时杜紫微为支使,座中有属意处,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因露指尖。’”[6]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评论道:“苏轼《天际乌云帖》里写美人:‘肯为金钗露指尖’,真是贵气。”[7]
“君谟真迹”及和诗仍不离“梦”的主题。“侵寻旧事”已成迷离梦事,真真幻幻混成一片。
《天际乌云帖》又叙述了一段与蔡襄、陈述古有关的妓女周韶的故事:
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常与君谟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座嗟叹,遂落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澹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苑旧桃李,强匀颜色待东风。”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蹔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惠也。
蔡襄又是茶学专家,在福建期间,发展了建安北苑的贡茶,改大龙团为小龙团。他茶艺精湛,著有《茶录》,可是斗茶(比试茶艺)却屡屡败给杭州营妓周韶。茶品高下不仅取决于知识和经验,也与烹茶者的气质、审美层次相关联。苏轼被流放海南时所作《汲江煎茶》诗把斗茶写成超然物外、陶养心志的过程:“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椀,坐听荒城长短更。”[8]
陈述古知杭时,蔡襄已去世。周韶诗中句“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引人生发关于蔡周情谊的联想。“君谟真迹”中的“绰约新娇”指代的就是周韶吗?在蔡襄的迷离梦事中,会出现周韶的婷婷身影吧。
营籍即营妓,指集中于乐营习歌舞的妓女,有陪侍官员宴集的义务,人身权属地方政府或军队。周韶与胡楚、龙靓皆有诗才,曾合著《三妓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子容是北宋名臣、科学家苏颂的字,其与蔡襄为姻亲。他作为中央朝臣经过杭州,知府陈述古有召营妓饮宴接待的义务。不料才艺出众的周韶身着白衣,“泣求落籍”,以诗言志,其高洁气质和纯真性格令“一座嗟叹”,也令后世读者赞叹感动。
周韶不穿艳服却着“雪衣”,显得与身份格格不入,因而胡楚说“澹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龙靓说“桃花流水本无尘”。周韶如此装束本为“有服”并“泣求落籍”,一身雪白却倍显惊艳。
《天际乌云帖》在书写了蔡襄的《梦游洛中》绝句一首之后,漫说开去。从陈述古处的“君谟真迹”及和诗,说到周韶的“落籍”;从蔡襄梦中诗转写杭州风月。蔡襄“昼梦游洛中,见嵩阳居士留诗屋壁”,苏轼于陈述古“小閤中壁上”见诗,一在梦中,一在醒时。而嵩阳居士诗写“天际乌云”、“楼前红日”的实景,苏轼所见壁上诗写“绰约新娇”的幻象,两诗对看,虚实相间,不免启人蕉鹿之惑。尽管梦境恍惚,第二段短文以周韶与蔡襄斗茶起笔,暗示蔡襄的男女朋友是同一类人物,居士辞官隐居与美人“泣求落籍”,其气节和品格相仿佛、相映照。
当《天际乌云帖》在世间流传,清绝脱俗的雪衣女形象吸引着后世的诗人们,该帖的题跋诗大多围绕雪衣女展开,续接着北宋文人的迷离梦事。
从《天际乌云帖》的题跋看,该帖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元代书画家、曾任元文宗(图帖睦儿)时期奎章阁鉴书博士的柯九思。柯作跋语说明此帖来历:“此卷天历间得之都下,予爱坡翁所书之事,俊拔而清丽,令人持玩不忍释手”。从蔡襄、苏轼生活的年代到元朝天历间,200多年过去了,改朝换代,风雨沧桑,《天际乌云帖》曾经辗转于哪些人之手,曾经被什么人“持玩”,则不得而知了。
著名书画家虞集在柯九思处得见此帖,题跋云:“及取观,则吾坡翁书蔡君谟《梦中诗》及守居閤中旧题也。第三诗以为不知何人作,其轩辕弥明之流与?陈太守放营妓三诗,亦辱翁翰墨,流传至今,亦有缘耶?”[4]虞集认为周韶、胡楚、龙靓三诗“辱翁翰墨,”看来他不能理解苏轼写这段故事的用意,居士和妓女在他眼里还有贵贱之别。但同时虞集却又题诗步蔡襄梦中诗原韵,向往杭州太守与妓女斗茶的乐趣:“只今谁是钱塘守,颇解湖中宿画船。晓起斗茶龙井上,花开陌上载婵娟。”虞集还由周韶联想到人生的轮回:“三生石上旧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论。纵有绣囊留别恨,已无明镜着啼痕。”此诗前两句出自苏轼《僧圆泽传》中的竹枝词,该文叙述了圆泽转世变成放牛娃的故事。未必有多少中国人真相信转世说,苏轼未必信,虞集也未必信,但传说中的故事适宜引发遐想和感叹,雪衣女正像圆泽转世的牧童,不知从哪里来,不知到哪里去,一代代人物来了又去,只是江山如梦。元末文人透过《天际乌云帖》的墨迹,回望200多年前的古人,怀想当年杭州城里的风流雅事,唤起充满羡慕的想象。
柯九思将《天际乌云帖》送给了好友王子明:“予携归江南,会荆溪王子明,同予所好,携之而去。”12年后,当柯九思被逐出朝廷,流落江南,再见到王子明家中环庆堂的《天际乌云帖》,恍若隔世,不由兴发今昔之慨:“他日再阅环庆堂,俯仰今昔,为之慨然,因走笔尽和卷中之诗,以舒其悒郁之气。”[4]柯九思于至正三年(1343)夏天题写和诗九首,其中有和周韶原韵:“云中初下势如惊,白凤蹁跹雪色翎。多少旧游歌舞地,不堪回首又重轻。”
雪衣女如“云中初下”,似“白凤蹁跹”。《天际乌云帖》说明“韶时有服,衣白”。中国人以白衣为丧服,《红楼梦》第110回描写贾母丧事时宝玉见宝钗“浑身挂孝,那一种雅致,比寻常穿颜色时更自不同。心里想到:‘古人说: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看来不止为梅花开的早,竟是那“洁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更不知怎样的丰韵呢!’”古代女性只在“有服”时才能依理法着白衣,也才有机会显示那别一样的雅致、别一样的风姿。
柯九思又和“君谟真迹”诗,想象蔡襄对红颜知已的思念:“绿窗度曲初含笑,银甲弹筝不露尖。人生莫待春如雪,华屋春宵酒屡添。”蔡襄的“绰约新娇生眼底”,似真似幻,也不知思念中的美人是否真的存在过,那情愫是否真的发生过。而柯九思笔下的“绿窗初度”、“银甲弹筝”美人的高贵矜持也撩人绮思。是真是梦,无从分辨也不必分辨,于是柯九思在另一首和“君谟真迹”诗中传达人生如梦的感悟:“不道人生从梦寐,诗新犹话梦中情。”
就在柯九思题诗的这年冬天,著名画家、道士张雨又为《天际乌云帖》题诗,身为道士的张雨偏对蔡襄与周韶的交往兴趣盈然。苏轼以平实语句叙述“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常与君谟斗胜之”,被张雨从杭州名贵的小龙团茶点染开来,虚拟出蔡、周二人较量茶艺的具体情境:“听碾龙团怯醉魂,分茶故事待谁论?纤纤玉椀亲曾见,只有春衫旧泪痕。”诗中的斗茶者仿佛触发了爱情,又仿佛掩饰了心愫,张雨随后的跋语也承认自己“言无伦次,且有广平媚语之罪,信识法者惧也”。[4]
张雨之后,为《天际乌云帖》题诗的是元末明初的书画大师倪瓒。倪瓒性格孤高,藐视权贵,他题诗时已改朝换代,故交四散零落,家境转贫,而气节与志趣未改。苏书蔡诗使他联想起北宋昙花一现的繁荣,江山易代的无常。他的题诗贯穿着伤感思绪,与其画风一样萧瑟荒疏。其绝句之一为:“湖边窗户倚青红,此日应非旧日同。太守与宾行乐地,断碑荒藓卧秋风。”在倪瓒眼里,北宋诗人妓女的文采风流已一去不返,他只能借此题诗,传达自己的心绪。
最后一位为《天际乌云帖》题诗的元末明初文人是吴中名士马治。他也被周韶的故事打动,周韶身着雪衣使马治联想起白衣大士莲花女(观音),他取柯九思题诗中的“银筝”意象,诗云;“多情应是莲花女,留得银筝金字经。”“多情”与皈依佛门之间的跨距看似遥远,却由周韶从容实现。这个女子的飘然离去仿佛人生的隐喻——她的生命不可能长存,却留下了雪衣女的形象,类似的人物和人生还会不断重复。于是马治又和胡楚、龙靓韵,想象周韶的前生后世:“透海丹砂一粟红,前身宜与后身同。”“须知剩水残山外,冰雪肌肤别有人。”人世流转,生生死死,没有谁能让美好的人和事物永留人间。但追绎曾经发生过的雪衣女的故事,那出尘脱俗、灵慧美丽的形象吸引着、震撼着后代不同时世中的人们。明末的柳如是曾被雪衣女的高洁打动,陈寅恪考证柳如是于崇祯末年致汪然明信中句“某翁愿作交甫,正恐弟仍是濯缨人耳”,[9]即引用《天际乌云帖》中龙靓诗意:“河东君尺牍以‘交甫’‘濯缨’二事连用,当出于龙靓之诗,用事遣辞,可谓巧妙。至其所以能用此古典以拟今事者,当非得见东坡手迹,恐是从此帖摹刻之本,或记载西湖名胜诸书中,间接得知耳。”[10]
马治又在题诗中以诗人的敏悟慨叹大自然的凄清:“归来世人空尘土,云白江清月满沙。”[4]但这凄清的背景下毕竟发生过故事。云、月、江、沙由于承载着历史,便不再是单调的无情物质,而成为可供凭吊的风景。
马治题诗于“洪武十四年,岁在辛酉秋九月朔”(公元1381年),各种书画谱录所载《天际乌云帖》文本均截止于马治题诗。明末汪砢玉著《珊瑚网》,在“苏文忠公天际乌云卷”一条后注道:“此卷向在项又新处,余尝获观,今为越石售去。”[4](项又新为明代大收藏家项元忭之子,元忭去世后《天际乌云帖》曾由其收藏。越石,姓王,《珊瑚网》中曾误写作黄越石,经常向汪砢玉展示书画逸品。)在有据可考的古代文献中,这是该帖的最后去向,此后便下落不明。
明末清初,河北涿州的冯铨编选《快雪堂法帖》,收录晋至元代名家法帖,冯氏摹写,由刘光旸刻石,其中收入《天际乌云帖》。“快雪”拓本流传颇广。乾隆年间,太臣杨景泰进献此石刻,乾隆皇帝在北京北海建快雪堂贮之。另有翁方纲藏《天际乌云帖》,“墨迹今入上海博物馆,定为赝本参考品”,[11]但翁本《天际乌云帖》2002年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作为《中国墨迹经典》之一种出版。
可以大致肯定:世上已无苏轼《天际乌云帖》真迹。
古人流传下来的作品多有出处不可考者,如古文《尚书》、王羲之的《兰亭序》等,历代都有研究者指其为伪作。然而,对于已经深深溶入民族血脉的文化遗产,即使能够辨其本源而证伪,也无法消除这些“伪物”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从苏书蔡诗到200多年之后元末文人虞集、柯九思、张雨、倪瓒、马治的题咏,组成了一个精神感情的链条。蔡襄的迷离梦事和雪衣女的故事不断召唤着后世诗人幽远的怀想和钦羡,也使《天际乌云帖》叠印了越来越多的情怀和缘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