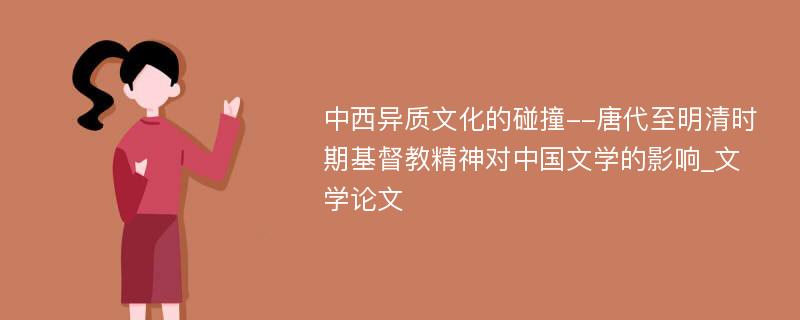
交织在历史中的中西异质文化碰撞——自唐至明清之际基督教精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明清论文,中西论文,中国文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359(2008)04-0098-05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1]外来文化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应当说发轫于汉代,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盛行于唐代。据此,有两大外来文化与我国文化发生了碰撞:一是以印度佛教文化为中心的中亚文化的传入,从晋宋开始直到晚清。二就是起于唐代、继于明清、盛于“五四”前后的西方基督教及其文化的输入。中国文学汲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健美了形式,丰富了内容,冲破了雅正、单纯的大文学传统格局,扩展了雅俗共赏的纯文学领地。
文化昌明的唐朝留下的史料相当丰富,但有关景教的记载却如凤毛麟角,只留下一鳞半爪,以致这段历史险些被岁月的长河湮灭。在《大秦景教碑》出土以前,唐代长时间里有过基督教流传之事早已鲜为人知,唐朝典籍中偶尔记载到的“波斯僧”、“大秦穆护祆”,一般都认作是佛教一类的称谓,直到明末天启三年(1623年),陕西周至县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经过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考释,才揭开了这段久已湮没的史实的面纱。碑文中清楚地记载了景教自唐贞观九年(635)始传华的经过、盛况、教义。后来敦煌石窟又发现了少量的唐代景教文献,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据此,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我们才得以一睹这本来就不甚显眼但又有重要意义的史实:基督教曾连续得到唐朝六代皇帝的优待,在唐代中、前期间,先后活跃了210年,其影响不言而喻。《大秦景教碑》提供了基督教在唐代即传入中国的确凿证据。此碑诞生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湮没于地下达近千年之久。这方碑碣犹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耆老,向人们宣示珍贵的史实。此碑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镌有十字架图案和碑名,碑身上刻有1780个汉字的碑文,碑底和两侧是古叙利亚文的70多位景教士的名录。据碑文及《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唐太宗于贞观九年(635年)接待了罗马帝国景教传教士阿罗本(Olopen),因其“深知正真,特令传授”;唐太宗派房玄龄亲自迎接,并拨款修建数座“波斯寺”准许传教。又于贞观十二年诏令景教“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唐高宗“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唐玄宗于开元七年(719年)又接纳了罗马17个传教士,将5位先皇圣像放于教堂内,亲为教堂题字。唐肃宗于灵武五郡重立景寺。唐代宗“翻经建寺”。唐德宗允建丰碑,记载九朝间景教的业绩。“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景教直到会昌五年(845年)才因唐武宗独尊道教、消灭佛教,景教受到了牵连而逐渐式微。佛教本为这次打击的主要对象,一时遭受大劫,但不久便又开始复兴。景教则一灭殆尽,景寺荡然无存,中国的景教徒统统被勒还俗;外国教士则多被遣返回国,个别留居者也不得不改换门庭,或讲习中国儒术,或潜入中国佛门,或委身于道教。不过,景教虽在唐末被禁绝,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依稀可见。以吕洞宾为代表的吕祖道派就融进了景教的成分,像《吕祖全书》以及专记吕祖故事的《海山仙迹》等书中,就杂糅了与景教有关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吕祖全书》中的《救劫证道经咒》篇中,包含着景教赞美诗歌中的许多语句。对此,有的学者做过专门考证。[2]但无论如何,景教作为一个教派,自唐末在中国内地就不复存在了。一直到元朝建立,这数百年间,在中原大地上连其几星残火也已罕见,惟在边塞某些地方,尚有一息相延。
但到后期,即明清之际就颇具规模了。据统计,迄至1851年,来华的新教差会就达35个。[3]继英美之后,其他国家新教组织如德国和荷兰等也派出一些传教士前往中国,但人数和影响力都远远不如英美的传教士。自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欧洲平均每年有近30名传教士在华传教,如康熙九年其教徒人数竟多达27万并遍布12个省区。[4]之所以如此,这同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的“学术传教”做法有关。利玛窦说:“为了使一种新宗教的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神父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谈论宗教的事。……把时间用在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上。”[5]一方面,他们采取“格义”法,将“天主”与中国古代经籍中的“上帝”相配,把中国画在世界地图中央并照中国古书已有的地名来命名国名等,以迎合中国文人的趣味以及传统学识;另一方面则努力结交中国官员与文人学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王应麟、李贽等,通过传授科技再进而宣传教义并吸收入教,由此使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官员入教。这些人深受“西学”之影响,仅明末学者在各种著述中明说自己受到影响的就不在少数。如徐光启说,传教士带来的“西学”,“较我中国往籍,多所未闻”。[6]并说:“格物穷理之学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7]王徵承认“余得朝夕晤请教益,甚灌也。”[8]李之藻更进而表示“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9]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使其精神在不同程度上启迪了中国文学的想象与创作。首先,译入了《圣经》及其神话故事。这方面,唐代译有30多部。[10]现存可认的有7种,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尊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等,共计15000多字。这些译作中,一方面介绍了《圣经》的各卷篇目,另一方面也大致译介了基督教的基本观念、教义、教规与教仪等。如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即“三位一体”的上帝,当时译为“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我三人分身景尊弥施诃”等。[11]摩西十戒,则被译成“事天尊”、“事父母”、“莫奸他人妻”、“莫作贱,自莫煞生亦莫谏他煞”等“十愿”。[12]原罪说,也被译为“浑元之性,虚而不盈。素荡之心,本无希嗜。洎乎娑殚施妄,钿饰纯精”。[13]翻译时比附、依托道教的一些经典比较明显,这可能与唐朝尊奉李老为祖先,崇奉道教有关;或者说,是道教兴盛时的产物。《圣经·旧约》中的创世纪,则很简约地译成了上帝“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别赐良知,令镇化海。”[14]敦煌文献中有一卷汉文手稿,标题为《序听迷诗所经》,意思是“听弥赛亚经札记”,有头无尾,存2800多字。文章先叙述上帝无人得见又无所不在,如经说:“天尊容颜似风,何人能见得风?”然后讲到上帝的十条诫约(只拜上帝、不拜偶像、不妄称上帝之名、守安息日为圣日、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作伪证、不贪财色),它把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思想加了进去:“合怕天尊及圣上,并怕父母作好”。再下面便记叙了童贞女末艳(圣母玛利亚)无男受孕、移鼠(耶稣)降生传教的故事。今据影印,录其最后一段:
……大王毗罗都思索水洗手,对恶缘(人)等(说):“前!我实不能杀其人”。恶缘人等更重咨请,非“不杀不得”。弥师诃将身施于恶,为一切众生,遣世间人等知其人命如转烛,为今世众生布施,代命受死。弥师诃将自身与遂即受死。恶业人乃将弥师诃别处,向[木](原为沐)上[绑](原为枋,古音通绑),绑处名为“讫勾”,更将两个劫道人,(将)其人比在右边。其日,将弥师诃木上缚着,及到日西,四方暗黑,地战山崩,世间所有墓门并开,所有死人并悉得活。其人见如此,亦为不信;经叫死(者)活,并(成)为弥师诃,其人大有信心。人即云:……[15]
作者行文中的言辞颇具文采;但其译作也显然比较粗糙,不仅有字词的脱落,与后来的标准译法尚有不短的距离,读起来也略有滞涩。不过,这正看出景教初传时的真实情形,以及时人不无比附、想象的解读。
其次,基督教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唐代的文学,如好奇、冒险、叛逆、自信、勇决、平等、自由、博爱等。在中国,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伦理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基督教则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如唐传奇《关司法》就可视为基督教平等思想渗透到唐传奇的证据之一。这是个颇属离奇的故事,佣人钮婆见自己的孙子和主人的儿子不平等,便说:“皆是小儿,何贵何贱!而彼衣皆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并用法术将两个孩子变得一模一样。钮婆明确地喊出了人人平等、“何贵何贱”的口号,遂使中国古代文学开始看到了一个“文学即人学”的视角曙光。
性爱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是个羞答答的角色,所以在先唐文学中出台的不多;但在唐传奇中,却如雨后春笋般,比比皆是,而且描写细致,无甚顾忌。《任氏传》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可以想见,当时居住在唐朝的都会及港口的众多“洋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肯定会影响中国文人乃至文学;尤其是他们的蕴涵着人文精神的性爱观。西方人把性爱观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人性,因此而违法都会受到宽容。《圣经全书·约翰福音》就记载了神的这段著名的教诲。唐代基督徒在传教中肯定也会宣讲这个情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代传奇性爱故事特别多的因由了。
再次,因景教传教士是“非我族类”的人,其所传教理又是不同于佛教的“居止既别,行法全乖”[16]的异言异举,从而也激发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唐代杜环《经行记》说:“拂林国有大食法、有大秦法……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17]段成式《酉阳杂俎》中也颇为生动地写了古波斯王鸟瑟多习筑城的故事:开始时城随建随坍,后来,小女那息得知父王的焦虑后,就“自截右手小指,遗血成纵,匠随血筑之,逐日转纵匝,女遂化为海神”。[18]至于在作品中写到的“蕃胡”的人或事的,在《玄怪录》和《续玄怪录》以及后来的《太平广记》中均有所见。
中国文学殿堂居首位与主位的诗歌中,也浸染景教徒的宗教气息。唐诗中既有杜甫的“时有西域胡僧识”,还有韩愈的“越商胡贾脱身罪,珪壁满船宁计资”[19]等诗句。至于吟咏异域的诗篇则更多,张说、张祜、王绩、李白都写过。例李白所作乐府诗《上云乐》,可窥见景教思想:
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仪容,戌削风骨。碧玉灵灵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康之老亲,抚顶弄磐石、推车转天轮、云见日月初生时、铸冶火精与水银。阳鸟未出谷、顾兔半藏身。女娲戏黄土,工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若沙尘。生死了不尽、谁明此胡是仙真。[20]
诗中写的“胡人”,就是指的“洋人”;据罗香林《景教入华及其演变遗物特征》所考,“大道”与“元气”,当指“天父”与“上帝”。[21]往下的字句则是景教创世说与我国神话的杂糅。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诗歌以他的《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最为杰出。“无题诗”超俗的情爱和灵性,则展现出基督教基本精神,突显了李商隐独特的艺术风貌。我国古代不少爱情诗的作者,往往以一种玩赏的态度来对待女子及其爱情生活,李商隐则从一种纯情的而不是色欲的角度来写爱情、写女性。他曾在《别令狐絢拾遗书》中对女子被深居幽闺而缺乏婚姻自主权,寄以极大的同情。他的爱情诗,情意真挚,深厚缠绵。如: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屏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大中三年己巳(849年)]
诗中,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几成千古绝唱。颔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比喻中寓有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颈联则在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尾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明净而又缠绵悱恻。又如: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应转蓬。[开成四年己未(839年)]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那种显然难得结合,却已经目成心许的爱情;那种终生难忘却又无法排遣、不易言说的恋情,那种既有美丽喜乐也有忧愁乃至伤痛,都凝缩成这一句话。而这些描写都或多或少有悖封建礼教对于女性和爱情的态度。写这些诗时李商隐已值思想成熟的年龄,对《圣经》所昭示的灵性生活理念当有一种体证。这样说并不突然,从他的《上崔华州书》[22]中即可窥视他的文学批评及创作思想受到基督教精神影响的必然。
唐代的玄言诗也浸染着基督教神学思想;现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中,有一篇名曰“三威蒙度赞”的诗道:
“三威蒙度赞”
无上诸天深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
人元真性蒙依止,三才慈父阿罗诃。
一切善众至诚礼,一切慧性称赞歌。
一切含真尽归仰,蒙圣慈光救离魔。
难寻无极正真常,慈父明子净风王。
…………
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广度苦界救无亿。
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耽苦不辞劳。
愿舍群生积重罪,善护真性得无繇。
…………
大师是我等慈父,大师是我等圣主。
大师是我等法王,大师能为普救度。
大师惠力助诸赢,诸目瞻仰不踅移。
复与枯燋降甘露,所有蒙润善根滋。
大圣普尊弥施诃,我叹慈父海藏慈。
大圣兼及净风性,请凝法耳不思议。[23]
这首诗糅合了儒家的孝道、三才,佛教的普度、善根等观念,浸透着浓浓的景教思想,该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徒所写的基督赞歌。诗用字准确明白,毫无洋味;但囿于七言和韵律,难免略欠通俗。现今释疑为:“三威”即三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4]“三才”即三在,指下句的三个一切;秦音称“在”为“才”。“慈父明子净风王”,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净风当时是“圣灵”的中文译名。“弥施诃”即“弥塞亚”,希伯来语“受膏者”、希腊文之“基督”,意为救世主,指圣子耶稣。“大师”指东罗马教皇或主教阿罗本。“大圣”指圣子耶稣。诗歌无不渗透着景教神学思想,又在其流传中撞击着整个社会文化。
外来的科学、技术、商品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它们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册府元龟》第五四六卷记载:
柳泽,开元二年(714)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泽上书谏曰:“臣闻: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欲而心乱必矣。窃见庆立等,雕镌诡物,制造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譎怪为异宝;乃理国之巨蠹,圣王之所严惩……今庆立皆欲求媚圣意,摇荡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于天下。必若庆立矫而为之,是禁典之无赦也”……
这段记载表明,外国的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曾引起了唐朝政界的争议,也为文学创造提供了素材。景教徒及烈的这次进贡,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做过结论。景教传教之方,以此窥见一斑。这与明代利玛窦进奉报时自鸣钟于宫廷,以固天主教传道之基础,是一个道理。景教这些依托上层政治的传教方法,不但是需要的,也是很成功的,毫不逊色于后来的利玛窦等人。
涓涓溪流终于汇成波澜壮阔的江海。宋元,尤其是明清时期,直接为基督教天主教正名张言的诗文,则上自首辅、下至庶民,写者更多,著述也更丰富;既有成百上千的序、跋、章、疏,也有各式各样的律诗绝句:
如写基督教遗物遗迹的诗,宋代诗人苏轼及其弟苏辙,就写过几首关于大秦寺故迹的律诗。嘉祐七年苏轼游南山写了题为“大秦寺”的五律,其弟苏辙的五律写得更为直白:
大秦遥可说,高处见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回。山平堪种麦,僧鲁不求禅。北望长安寺,高城远似烟。[25]
金朝的杨云翼也写过五律的“大秦寺”,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还奉敕撰写了有关“十字寺”的碑文。[26]明初官至北平按察使的刘嵩,则写了一首“铁十字歌”:
庐陵江边铁十字,不知何代何年岁。何人作之孰置此,何名何用何宛然。……此物千载为英精。[27]
身居显位的叶向高在赠利玛窦诗中说:“圣化破九埏,殊方表同轨。于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大哲学家与文学家李贽在赠利玛窦诗中说:“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学者与书画家李日华也在赠利玛窦诗中说:“蠲洁尊天主,精微别岁差。昭昭奇器数,元本浩无涯。”这中间,似乎以戏曲家汪延讷写的最为传神:“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27]
随着交往的深入,时人接受、濡染的范围在日渐扩大,基督教的知识也日渐丰富、宽广起来,不再是一种单一层次上的叙述和描写——这当然是基督教渗透的一个必然结果。
译介,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的标志。到了19世纪50年代,一些具有文学性质的宣教书籍陆续译出:1852年《金屋型仪》(可直译为《扎特,或十字架的魅力》);1853-1866年《天路里程》(英国作家班扬著);1870年传教士胡迈得(Thomas Hall Hudson)还将原著第二部分译为《胜旅景程》,在宁波出版。1854年香港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第九号上刊登英国诗人米里顿(John Milton)的《目盲自咏》(On His Blindness,是一首十四行诗),这可能是迄今所知最早的英语诗歌。1864年前后《长友诗》(即《人生颂》,A Psalm of Life)出版。《目盲自咏》与《人生颂》在形式上都采用了中国读者熟悉的诗体。译介新词语对晚清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革新,意义非同一般。其吟咏的事物、意象与修辞新颖而独特,对习惯于中国诗歌典故、用语和选字修辞的读者无疑受到极大的震动。
中国古代的文学语言是典型的书面语言,与口语有很大距离,而这种书面语历两千多年,直到晚清也变化不大,其最高典范依然是上古经典与先秦文章。作为书面语的雅驯的文言文讲求“练字”、“用典”等“义法”,虽然表面上无烦琐语法,实际上在遣词造句上束缚极多。结果,文言文的训练形成中国文人的集体意识,使之很难发现文学自身需要的新语言,只有在外来语言系的参照下,才发现了中国言文脱离的弊病。通过传教士译介作品而来的大量外域新鲜经验与观念,是传统文学语言无法描述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与最终的磨合再生使传统文学语言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在梁启超等的倡导“新小说”之前,中国文学的正宗历来是诗歌和言志载道的散文。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为古老,最发达,形式最完备,也是取得成就最高的一个领域。然而,传统的诗歌语言越来越无力表达基督教精神浸润过的新情绪、新经验,变革的呼声与实践由弱而强,至19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其代表人物是黄遵宪。他的新派诗引人注目,如《今离别》(四首)分别以近代科技: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为题材,抒写男女离别之情,别开生面:
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镜匳来,入妾怀袖中。临行剪中衣,是妾亲手缝。肥瘦妾自思,今昔得母同?自别思见君,情如春酒浓;今日见君面,仍觉心忡忡。揽镜妾自照,颜色桃花红;开筪持赠君,如与君相逢。妾有钗插鬓,君有襟当胸;双悬可怜影,汝我长相从。虽则长相从,别恨终无穷;对面不解语,若隔山万重;自非梦来往,密意何由通?[28]
这首咏照相诗,被近代著名“同光体”诗人陈三立赞为“千古绝作”。黄遵宪既是“新学诗”的理论倡导者,也是用力最勤的实践者。他认为他的灵感首先来自对中西方语言文学的比较。[29]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精神深刻波及了我国的文学;对我国文学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形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包括生产文学的制度、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与文学空间。
自古以来,文学作品所关注的焦点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纳含于其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而生与死、爱与恨、灵与肉、情感与理智、欲望与意志力等文学性的二元张力,其实恰好折射着人类对有限与无限、时间与永恒,“是”与“在”的宗教性关怀。从而宗教往往最集中地蕴集着文学作品用之不竭的永恒主题。宗教和文学在神性的终极关怀和世俗的社会关怀两大信念的支撑下,也许自身就体现着某处深层的同构。基督教文化精神,拓宽了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传统世界观和知识观,认识到了“彼西洋邻近三十余国”、“欧罗巴数十国暨其他国土以千计”[30]的一个实在的西方世界,最终突破了“天圆地方”的传统空间观而代之以“东西两半球”的“天地圆体”世界目光。本着“补儒易佛”的动机,做出了糅合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博爱思想合一的“道”。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广泛开放的社会,至明清以后,连绵不断的文化碰撞,终于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扇窗口。“基督教与艺术的统一更为深刻地显露于我们自己的意识之中。这是人类体验本身的统一性。……基督教对思想的补充之一就是感情。基督教总是超出心智的限度之外;它是心灵的一种态度或意想;它是对实在的直接体验,是对上帝的冥想,是与上帝的交流。……它需要运用一切进行至高精神探索能力。”[31]人对永恒和超越的追求,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尚难以见到。21世纪虽然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但人们仍离不开宗教,也离不开文学——文学的受众是人,其主要作用于精神。宗教的受众也是人,也同样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二者的合力又如何呢?这已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文学是真理的敞开与澄明。
标签:文学论文; 基督教论文;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明清论文; 传教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