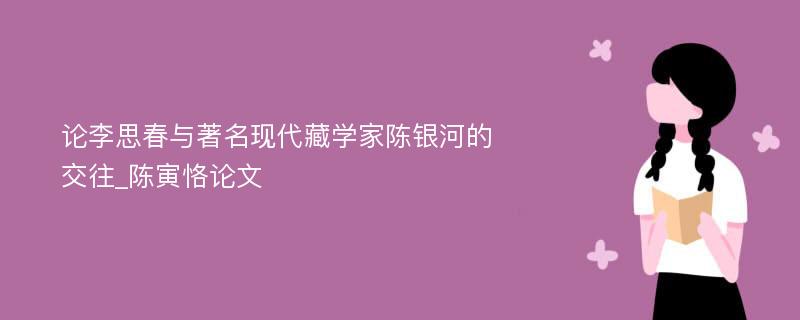
现代著名藏学家李思纯与陈寅恪交往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家论文,著名论文,陈寅恪论文,李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0)01-067-07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近现代著名学者,青年游学欧、美、日各大学,历任清华、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于藏学、突厥学、蒙古学、中外关系史、蒙元史、古音韵学等学科无不精通,被誉为一代史学宗师。
李思纯先生(1893-1960),字哲生,四川省成都市人。晚清光绪一十九年(1893)在父亲就仕的云南昆明出生,幼年全家迁回成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于1919年6月参与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同年秋赴上海,年底与李劼人(1891-1962)、王光祈(四川温江人,1892-1936)等同乡学友同舟抵达法国勤工俭学,出国时,得到了张君劢(1887-1969)的资助,并兼任《时事新报》驻欧通讯记者。李思纯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前后近四年(其中三年在巴黎大学),通法文、拉丁文,曾从巴黎大学历史学者瑟诺博司治史学、文学。瑟诺博司又译“色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独著有《西洋文明史》、合著有《史学原论》(合作者为法兰西国家图书馆馆长朗格诺瓦【Charles V.Lanfflois,1863-1929】)等书。学成回国后,李思纯历任东南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四川外语专门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大代表。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不久退休,1953年进入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为馆员。[1]1960年3月14日,李思纯在成都去世。李思纯一生,未参加任何党派,主要活动在于教学与研究、翻译。就研究而言,主要在于史学与翻译,如他著有《元史学》、《江村十论》等书;翻译有瑟诺博司与朗格诺瓦合著的《史学原论》[2]、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rancois Core,1880-1954)的《川滇之藏边》以及法国诗人的诗歌《仙河集》(原名《法兰西诗歌集》)。1945年吴宓《赋答李哲生思纯诗》有“仙河传译美”、“史业名山富”之句[3],就总结了李氏治学的两大领域:史学、翻译。此外,李哲生与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能作旧体诗,所遗《岫云庐诗词》稿收录了李氏生平所作诗近千首、词近百阕。
陈寅恪先生在中国藏学(Tibetology)研究上的先驱作用,藏学界王尧《陈寅恪先生对我国藏学研究的贡献》、《吐蕃简牍综录》,苏发祥(才旺南加)《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等论文均有详论,[4]他年龄长李思纯3岁,且有共同的留德求学、执教于同一高校的经历,而且二位先哲在藏学、史学、旧体诗唱和上有着共同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二人的文化观念相近。因此,叙述二位先哲之交往及二人在藏学、中外关系史、蒙元史、古音韵学等多个研究领域中的交流与切磋,以显示两位学人的卓识远见及发覆之功,对于后来者治学无异于提示和导向了治学的津梁和途径,无疑值得尝试。
一、陈寅恪与李思纯之初识
在新版《陈寅恪书信集》中,陈寅恪、李思纯二者来往的信函仅存陈寅恪致李思纯之一封函。[5]这一封函只是陈、李二人40年的交往与相知的一叶而己。
陈寅恪与李思纯系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留学德国时相识。1921年春李思纯游柏林,初识在柏林大学读书的陈寅恪;之后二人从讨论学术开始逐渐相知,由此开始了二人长达40年的友谊。
1923年李思纯学成再至柏林,同年仲夏,李思纯挥赋《柏林留别陈寅恪诗》(见刊于《学衡》第二十二期)后从欧洲返国,到南京就任东南大学(吴宓从1921年已在此校执教)外文系法文及法国文学教授,与吴宓、梅方迪等人共事,并捐助《学衡》。
李思纯与陈寅恪之所以在柏林缔交并相知,与二人在欧洲的求学经历、不涉及政治与不参加政治派别以及文化观念的相近有关。
首先,二人均系专心致志求学,能吃苦忍劳。如李思纯哲嗣祖桢(1916-?,四川大学毕业,曾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讲师)回忆说:“父亲是流着眼泪出国的,因为没得钱!”“父亲在巴黎生活很艰苦,他住寓所无钱生火炉,冷极了竟捡报纸烧火取暖”,“到柏林去吃廉价面包了”。[6]陈寅恪之女公子美延(1937-)则追记:“父亲在德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日子一长,营养太差,加以学习繁重,终于大病”,[7]等。
其次,二人家世相类。陈寅恪氏不必言,李思纯氏之祖父、父亲为晚清滇省知州、候补知县,虽然在官场地位上有所差别,但是本质上却比较接近。而且,更重要的是二人与当时吴宓、梅光迪等人所谓的“学衡派”见解相类,如李思纯不仅与吴宓校系相同,文化观念一致,而且相知甚深。[8]
1926年李思纯到达京城,在北大预科任教,谒见了王国维、梁启超,与陈垣、马衡等人过从甚密,抗战期间先后任浙江大学史地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与李思纯的友谊止于1960年3月李思纯逝于成都,双方的诗歌唱和则到五十年代李思纯歇笔为止。
二、陈寅恪与李思纯之诗作唱还
1926年1月12日李思纯来访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接待;2月6日吴宓宴客,来者有汤用彤、叶企孙、冯友兰、汪懋祖及李思纯等人;[9]之后李思纯谒见梁启超,有诗(《学衡》第五十五期);2月14日吴宓“导李君谒王国维先生,以所着《新元史学》请正”,[10]事后李思纯有诗述之(《学衡》第五十六期);5月1日吴宓“偕柳公及李思纯、叶企孙,同游白纸坊崇效孝,观牡丹,又观青松红杏图,柳公与李君,各有诗纪游”,之后吴宓与李思纯还有多次游宴,相互有过诗作唱和,吴宓甚至将李思纯诗题于他人物品上。6月14日上午十时吴宓“访李思纯于太平湖饭店。十一时许,黯然而别(今夕出京)”(《吴宓日记》第3册,第178页)。[11]7月7日陈寅恪就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系1925年夏从柏林大学学成归国),与李思纯的“黯然而别(今夕出京)”相距不到一个月。
根据李思纯之女孙李德琬(思纯哲嗣祖桢之女公子)于1998年夏季的公布,[12]陈寅恪与李思纯有过数次的诗歌唱和。1998年公布的这批历经数次劫难而残存的陈李遗墨,以陈寅恪抄录1938年《蒙自南湖》为最早,抄录年代约为1944年,同时抄录的又有《昆明翠湖书所见》、《暮春重庆夜宴归有作》。李思纯在执教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后,回到故乡执教于成都诸高校,1930年11月曾与来成都文殊院讲法的太虚法师论学。[13]教学之余,在自己的书房为“岫云庐”读书、治学等。[14]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东部的众多大学被迫内迁至大西南。昆明、贵阳、桂林、成都、重庆成为大批学者、文化人的汇集之地,西南成为战时中国的学术中心。当时,陈寅恪、吴宓、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闻宥(字在宥,1901-1985,江苏松江〔现属上海〕人)、缪钺(1904-1995,江苏溧阳人)、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人)、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等众多外地学人被迫徙走于西南天地之间。国难当头,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精神力量,入蜀后众学人弦歌未绝,在各自的治学领域中奋发潜研,努力地拓展了以往研究的畛域,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吴宓、陈寅恪随校先后内迁于蜀地,与李思纯共同执教于蓉城高校,因此三人之间相互来往更为方便;吴宓对李思纯评价非常高,认为“蜀士多资性聪明,而处境丰裕”,但恋官爱财者不少,“独李哲生思纯尚能勉为真名士、真学者,笃于故旧之情,而气味渊雅,高出一切人上。为难能可贵矣”[15]。因相互来往更频繁,在他的日记李思纯夫妇及子女祖桓、祖桢、祖桂是经常出现的字眼。[16]
之后,在陈寅恪滞蜀的1944、1945两年中,由于二氏共同执教于成都,因而来往甚密,如1945年1月14日下午李思纯与吴宓前往存仁医院,“探寅恪病,久坐”;3月9日下午李思纯与吴宓前往广益学舍陈寅恪寓所,“访寅恪病榻”;9月9日吴宓“至寅恪宅”,“适李思纯来”,吴李在陈宅不期而遇。[17]
此一时期,李思纯、陈寅恪二人诗歌唱和亦颇多。如1944年李思纯曾和诗2首,有《陈寅恪写示近诗,赋赠一首》:
沧海逢君玉貌英,华颠重聚锦官城。宝书百国韦编绝,柱史三唐炬眼明。
应劫洪波沉此土,慰情悲顾托来生。南枝雪下春机在,珍重梅花镧骨清。
此诗回顾了二氏在海外的初识及在成都的再度重逢。之后,李思纯有《峨眉一首和陈寅恪》:
峨眉谣诼动深宫,万里飞琼碧海东。罗袜金钱娇未足,玉纤团扇怨何穷。
三姝薄媚排香阵,一夕微霜冷蕙丛。如水君恩任花落,殿头西角有凉风。
同年,李思纯另赋诗1首,即《九日访陈寅恪寓庐共话》:
黄花红叶斗霜秋,无分登高倦欲休。匝地玄阴催暮景,出门沧海讶横流。
图穷早卜输秦璧,天堕终疑验杞忧。历劫共君成一叹,多生才白此生头。
1945年李思纯曾和诗3首。
当年春,陈寅恪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养目,赋有《乙酉春病目不能出户,室中案头有瓶,供海棠折枝,忽忆旧居燕郊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感赋》(《诗集》第38页);接诵后李思纯有唱和诗《陈寅恪海棠诗次原韵》:
不遇花开那觉春,逢春垂老更伤神。绿章丽色能倾国,红粉高枝解笑人。
金缕曲终天若醉,胭脂山关恨犹新。杜陵溅泪乾坤眼,付与香泥十里尘。
7月7日,逢七七事变八周年纪念日,陈寅恪赋《乙酉新历七夕》(《诗集》第44页),之后李思纯有《和陈寅恪新历七夕并次原韵》:
灵鹊星桥竟有期,漫积短别与长离。蘼芜诗怨缣空织,絮阁梅藏镜已亏。
海外仙丹疗妒减,怀中纨扇到秋知。钗分铀合寻常事,莫遣猧儿覆乱棋。
当(7日)夜;陈寅恪又赋诗《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诗集》第44-45页),接诵后李思纯有应答之作《和陈寅恪读宋史》:
坐见宣和到靖康,三朝扰扰事全荒。北盟借助倾天水,南面因人帝阜昌。
童蔡百污随腊尽,桧飞双厄共金亡。长安年少胡心满,掩袂西台泪数行。
对于陈诗及前后数诗,吴宓已有附注:“时宋予文与苏俄订约,从罗斯福总统雅尔达秘议,以中国东北实际割让与苏俄,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此诗及前后相关数诗,皆咏其事而深伤之”[18],李思纯亦应有此意。
抗战胜利后,李思纯执教于成都的四川大学。他对于陈寅恪在京华、岭南的执教还是知悉的;同时,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亦有李思纯的旧友,如中文系教授李沧萍、吴三立(1897-1989)等人。
1946年春,李思纯以国民大会制宪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出席大会,得知陈寅恪“已自英国归”,乃于6月12日前往陈寅恪下榻处——俞大维宅,“晤寅恪,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君亦至,共谈约三小时”。16日,李思纯再往“晤陈寅恪,谈数小时。既而俞大维君亦至,俞君新任命为交通部长,较二十余年前在欧时为丰腴”,“寅恪告余,新得一联语云‘托命非驴非马国,处身不惠不夷间’,余为大笑。寅恪并嘱余常往谈,以解寂寥”。以后,李思纯还多次往晤陈寅恪,并在6月25日受托飞渝后“访陈寅恪家属”。[19]这以后,陈李二位生前再未有见面的机缘。
1950年,李思纯在成都致函陈寅恪,并附近作,同时有托陈寅恪代问移席中山大学事;陈寅恪收读后,于9月14日复函称“惠书及大作诵悉,弟近来依旧作诗文自遣”,告以“足下中大友人已斥去矣”,四日后陈寅恪致吴宓函称李思纯“欲在广东谋事,盖未知广州情形之故”[20]。陈寅恪随函并录赠近赋诗《庚寅广州七夕作》及新著《元白诗笺证稿》,并言“成都友人请代致意”。陈寅恪的“成都友人”无外林思进(1873-1953,四川成都华阳县人)、徐中舒、闻宥、缪钺、孙次舟(?—?)、华忱之等数人而己。
收到陈寅恪寄来的诗、书新作后,李思纯赋诗答谢,此诗应曾寄给陈寅恪。诗即《陈寅恪自广州诒所着(元白诗笺证稿),赋谢》:
元和长庆斗浓纤,白傅微之此并参。俳体新开成气格,警言相次出青蓝。
稗官律讽风骚继,史笔诗才议论兼。却羡横流沧海日,一编裁定在天南。
李思纯此诗,赞扬了陈寅恪诗之“史笔诗才”。而这也是1945年吴宓《赋答李哲生思纯诗》称赞李思纯除了能诗外还“仙河传译美”“史业名山富”相类似[21],总结了李氏治学的两大领域:史学、翻译。这也说明了陈、李二人在较多方面有共同之处。
陈寅恪与李思纯之诗作唱还,是二氏生活习性、情趣喜好等方面气类相投的表现,也是当时中国学人在更本真的生存样态方面仍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士”的生活习性与情趣喜好的见证,李思纯留下的一部从未示人的日记也充分证实了此点。[22]
三、陈寅恪与李思纯治学方法与研究领域之同异
陈寅恪、李思纯二人在治学方法上一致,均深受德国史学中的语文考据学派(Kritisch Philologie/Historisehe QueUenkritik)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负笈德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如陈寅恪、傅斯年(1896-1950)、毛子水(1893-1988)、姚从吾(1894-1970)、韩儒林(1903-1983)甚至连同俞大维(1898-1993)等人均受此学派影响,皆以研究史学、国学而著名于世。[23]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上,二人亦有较多的一致之处,如藏学、蒙元史、音韵学、(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
陈寅恪、李思纯二人探讨西藏史地,陈寅恪的相关研究自不必言。李哲生早年留欧时“见外人所著关于康藏之书甚多,慨叹国内康藏研究之不力”,所以积极进行了相关学术研究。如考察西康省后留下了《康行日记》手稿,“积极参与康藏研究社之发起,义务为社刊供稿”[24],他撰写了《西康建省的消极改善条件》等时政评论文章[25],以及翻译了多篇民国早期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rancois Gore)的著作《川滇之藏边》(Trente Ans aux pores bu Tibet Interdit 1908-1938),从1946年起发表于任乃强主编、自费出版专业刊物的《康藏研究》月刊(该刊物从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共出版29期),主要有《川边(四川之藏边)》(第15期,1947年12月,第5-18页)、《川边之打箭炉地区》(第16期,1948年1月,第2-11页)、《川边之打箭炉地区(续)》(第17期,1948年2月,第18-26页)、《川边之霍尔区与瞻对区》(第18期,1948年3月,第21-28页)、《理塘与巴塘》(第19期,1948年4月,第26-31页)、《理塘与巴塘(续)》(第20期,1948年5月,第20-29页)、《维西》(第21期,1948年6月,第18-24页)、《旅行金沙江盆地(1922年)》(第22期,1948年7月,第10-16页)、《察哇龙之行》(第23期,1948年9月,第22-28页)、《康藏民族杂写》(第26期,1949年4月,第22-32页)、《康藏民族杂写(续)》(第27期,1949年7月,第29-32页)、《康藏民族杂写(续)》(第28、29期合刊,1949年8-9月,第43-53页)等文。古纯仁一译古德诺,系天主教神士,在西康地区传教三十年,游历所及,有康定、泸定、巴塘、理塘等西康各地,综其闻见而撰成此书。
1946年任乃强转任四川大学教授后,发起并组织了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社会团体——康藏研究社,自费出版专业刊物《康藏研究》月刊。民国后期,李思纯成为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西康省第二选区候补代表;此外,抗战结束后,李思纯成为了国民大会的正式代表(因正式代表马泽昭因故丧失代表资格而递补),所代表的正是康藏民族人口占有大多数的西康省(1939年1月1日成立,1955年10月撤销)。1946年11月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
1939年李思纯在成都治学、读书时,写有札记《学海片鳞录》,后来存下了166条,其中部文内容收入了李思纯所著的《江村十论》。1965年,中华书局《文史》编辑部从该札记中“选择了可供研究者参考的三十二条,由傅振伦先生重加编次,整理文字”而仍以《学海片鳞录》为名发表[26],从这32条札记有“中国语之一音二字一字二音”、“畏吾儿语中之汉语”、“满语官名多本元代旧名”、“中国植棉古名译自外语”、“支那译自起源有二”、“清道光间俄国赠书之异译”、“明清以来西方诸国之旧译名”、“中国历代求法名僧行记之欧译”、“国际条约所用文字之例”、“清道光时初译之英语名词”等内容,可见李思纯治学兴趣较广,涉及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而且研究。其中,“畏吾儿语中之汉语”一条,引用《元朝秘史》及其相关研究著作多处,可见李思纯对于蒙元史、中外关系史、音韵学有相当研究。
李思纯早年在欧洲学习,掌握了法文、拉丁文语,接受了较为严格的法国汉学训练,购置有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霍渥尔特《蒙古史》及有关中亚、印度等史书多部,故归国后在南京的一年中,他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元史学》一书的著述,其间曾向王国维请教,并得到了陈垣、柳诒征、朱希祖等名流的寓目,厘正伪误(《元史学·自序》),此书1926年由中华书局初次出版。晚年所撰论文《说歹》、《说站》、《唱诺考》、《说外族王号异译》等篇网,均与蒙元史有关,而且还曾就蒙元史等问题与王国维、李氏的研究成果曾受到过罗常培等人的瞩目网。抗战期间,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陈乐素(1902-1990,陈垣之子)已多次对研究生程光裕(1917- )等人介绍本系教授“姚从吾、牟润孙、李哲生、方壮猷等先生有关宋辽金元史方面之研究成果。在当时,这几位先生,也就成为心目中所敬佩的前贤”[29],也说明李氏对蒙元史确有较深入的研究。
陈寅恪对蒙元史有很深的研究。早在1926年回国执教之初,就指导清华学子进行“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此后发表过多篇蒙元史研究的论文[30],并曾依据蒙满藏文诸本,考订《蒙古源流》的“得失”,撰成《蒙古源流注》书稿[31],他不仅从《大藏经》中检出元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造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对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32]。而且,对于李思纯反复征引的重要史料《元朝秘史》,陈寅恪有更精深的研究,如不仅在巴黎与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共同讨论该书的版本“优势如何也”[33],但陈寅恪李思纯在蒙元史研究领域的具体交流内容,目前则难以遽而言之。
李思纯与陈寅恪早在留学柏林期间,就中国古音韵学进行了讨论,李思纯就中国古语有无纯粹a音请教陈寅恪,“陈君慨然谓世界古语多a音,中国不能自外”,李思纯“颇承认其言”[34]。
李思纯与陈寅恪之所以在柏林缔交并相知,之所以在性格、识见等方面甚契合的原因是,与二人文化观念和史学思想的相近有关。表现之—即前面所言二人与当时吴宓、梅光迪等人所谓的“学衡派”见解相类,往来密切,二人视《学衡》为精神家园,常在上面发表论文,如第十九期的《与友论新诗书》等近十篇文章,给以吴宓以很大的鼓舞与支持。如1923年8月吴宓记道:“平日办理《学衡》杂务,异常辛苦繁忙。至各期稿件不足,中心焦急。处此尤无人能知而肯为设法帮助。仅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为帮顾”[35]。至1946年2月吴宓还“翻阅各期《学衡》,叹诸友之卓识宏论,中国近世莫可及”[36]。此中所谓“二三私情相厚之友,可为帮顾”当应包括陈寅恪、李思纯。因为1923年在柏林读书的陈寅恪,所写的致胞妹陈新午之函《与妹书》,8月发表于当年《学衡》后被视为陈寅恪一生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37];而李思纯不仅与吴宓校、系相同,文化观念一致,而且相知甚深。李思纯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学衡》杂志,如第19期的《与友论新诗书》等。陈、李二人不能说是学衡派,但与该派颇为接近。
可以说,学衡派在肯定文化具有的历史与世界的统一性的基础上所展开的文化观,虽有自己的弱点,但它既强调继承传统建立民族新文化,又主张中西文化互相融合,不仅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反映了世界文化潮流的新变动,而且也反映了学衡派既摆脱了东方文化派“隆中抑西”的虚骄心理,而且也超越了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学衡派具备了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38]。可以说,学衡派对人文关怀的强调,具有极可贵的前瞻性。在当今人类社会诉求人性和呼吁人文精神的大背景下,学衡派文化观的价值将进一步得到世人的客观评价与正面认识。
正是由于有了“学衡”这一层原因(表面的和深层的),学衡派主将吴宓常常诵读陈寅恪、李思纯的诗句就容易被人理解。一如1946年8月30日,吴宓“抵武昌机场降落,下机。晴,热,念柳公及哲生诗”[39];“柳公”即柳诒徵(1880-1956),乃吴宓父执辈,《学衡》创办人之一,曾与吴宓共同执教于东南大学。二如1961年夏吴宓到中山大学探访陈寅恪,8月31日在日记中记道:“终夜大雨,风猛雨急,宓感孤寂,又忧水灾,有‘板天檐瀑沸肠肝’(李思纯一九二三年诗句)之情景”[40]。当晚为什么吴宓引用了吴、陈二人共同朋友李思纯的诗句,可能与当日二人曾谈论过李思纯等昔日友人有关,更主要在于三人文化观念极其相同。
此外,陈寅恪、李思纯二人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亦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而且在关于史学的观念更新上尤其是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上,亦有一致或者相近之处之处,这可从二人进行的史学史、藏学、蒙元史、音韵学、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的具体研究中反映出来,或在二人的著作如李思纯的《江村十论》也可以清晰看出,但他与陈寅恪之间如何交流以至互相影响则阙于材料,今尚不能言也。
当然,陈、李二人亦有一些相异之处,如李思纯勤于译述法文学术著作,古纯仁(Francois Gore)的《川滇之藏边》一书外,李思纯还曾译有其师瑟诺博司与朗格诺瓦合著的《史学原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1931年再版)等书,陈寅恪则终生无一译作。
收稿日期:2009-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