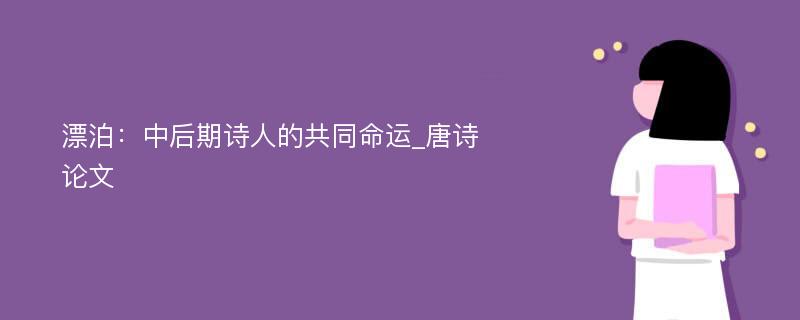
流浪:中晚唐诗人的共同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诗人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那是一场劫数,那是一场恶梦,“那是一个从恶梦中醒来却又陷落在空虚的现实里因而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①。社会抛弃了我们的诗人,他们,象突然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零,被世界所放逐,象那文化根被突然切断的诗人,现实的一切只是在竭力使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面对搅痛的忧伤,无望的绝境,有着无限的疑惧与游离彷徨,他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地踏上其漫漫长路的流浪历程。疲于奔命为了自我肯定,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归宿停泊在社会颠簸的港湾。这种精神的探索与追求,在中晚唐诗人中留有清晰的投影,跟随我们的诗人进行一次心灵的流浪,我希望找到他们在社会政治背景与个人情态上的细致感应及其轨迹行程,大略地勾勒出晚唐诗人流浪、挣扎命运的几种主要精神样态。
一、美的抗衡
如此辉煌壮大的全盛王朝,曾经活生生在他的眼前,他也无愧于这个时代,为它奏响了最强音。可是慢慢地他发现在这富丽堂皇中、笑语欢歌中蕴藏的却是一种败絮其中的糜烂、卑劣和腐朽。“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杜甫,他作为时代的先行者,已经敏感到了。这样两种似乎令他一时难以同时接受的现实,却那么生动地并置在眼前,作着强烈的对照比较,他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种对比越强烈,其悲愤的意味也就越浓,而这种对比往往更加侧重于从“现在”向“过去”的追忆,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寻梦意识。故时的繁华,这个玫瑰色的梦仿佛还正在诗人眼前浮现,但也正因为故时的繁华,这种思维在诗人脑中形成的定势由于惯性不可能一时完全改变,所以诗人尽管感到忧伤、悲愤,却只是“怨而不怒”,即便是这种衰败的出现,毕竟还在一层金玉装璜之中。诗人满腔焦虑游疑之情并不是直接倾出,而却将之隐藏在一个个美学世界的建构中去(如紧凑的结构、准确的意象、粘合的律动等),这大概也就是杜甫之所以主要运用着律诗这一创作形式的原委。企图创造一个美学的世界来抗衡正在解体的现实的世界,去弥补那个破裂。用诗人洛夫的话说:“写诗即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杜诗所创造的一大部分艺术世界也正如其所处的现实世界一样,表面富丽堂皇,内里却浮泛着一种危机,一种骚动不安。这是诗人面对这个正在破裂、危机日益加剧的时代,下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灵的悸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一种艺术上的补偿,让诗人那颗因时代风雨的侵蚀而愁苦的心灵达到一种平衡,在这片艺术世界中掩饰其一切幽怨,寄托其对此社会的热切冀望。而具体到各个时期的杜甫诗歌,我们又会发现,杜甫认识现实的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灵律动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现在,大概不会有人怀疑《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作都是或抨击时弊,或同情人民的现实主义杰作。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值得思考分析的。我们真正需要注意的不是它实际反映了什么,而是它反映这些时的情绪。无论在那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中,还是在长安丽人热闹非凡的游春场景中,或是《三吏》、《三别》一幅幅惨绝人寰的画面中……我们看不到诗人任何明言的诘责,贯穿始终的是诗人那浓郁深沉的忧国忧民情绪,这种深沉的忧患感也就构成了大部分杜诗的基调。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②后人以为这两句诗“状尽子美平生矣”。的确,当我们读到“登兹翻百忧”、“忧端齐终南”、“独立万端忧”之类的诗句时,浮现在眼前的不正是一位“醉里眉攒万国愁”的老人吗?不仅如此,在其忧国忧民的情思之中自有一股凛然正气在回荡。现实现象的不合理,杜甫并没有象一般文人那样简单地、一股脑地把它和对君王的抨击直接挂起钩来,因为,这种简单的推卸说到底只是一种臣民心理的思维定势。而作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杜甫,他是以主人的姿态出现,他好象一位长者,面对孩子的错误,他要规戒,使之改正,但也容易谅解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恼怒之,责骂之。正是这种心理上的长者风范、凛然正气使其艺术世界具有足够的力量与破毁的现实世界相抗衡,从而发挥其消解功能。
晚年的诗人主要是过着漂泊依人的生活,特别在成都时期,营建草堂,得以闲居江村,诗酒自娱,但为时并不长,就总的情况看,还是困苦多于安适,更何况背井离乡、政治失意,又怎能真正忘怀于诗酒?特别是国家多难,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周边民族的入侵、地方军阀的叛乱、百姓遭殃……这一切都时时牵动着、撞击着诗人那根敏感的心弦,写下了大量感时伤世、缅怀往事、追怀故交的诗篇。这些诗篇中展示的将是诗人心灵流浪的又一阶段的特征。我们来看看他那首最有情韵、最富含蓄的《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是一首描述故交相逢的诗。诗人首先记起的是昔日在歧王李范提供的聚会场所里的“寻常见”、“几度闻”,现在,失去了可以随意相聚的机会,“寻常”便成了异乎寻常,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失落。然而,作者却似乎轻松地把它视为过去“寻常见”的一次普通的重复,其实,他们何尝不知这是历经世变之后的万幸,说不定也许是最终的一次,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从中感受出来的有作者独特的欢愉,不也有作者难言的苦痛吗?而作者却极力掩饰其失落的痛苦。“正是江南好风景”,他只谈到此时此刻眼前美景,遗憾的是,“好风景”至“落花时节”,落花又一次使我们想到,繁华已经终结。诗人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姿态,可它却犹如一层透明的薄纱,实际上,反而更增添了面纱所覆盖的东西的诱惑力。通过无言喊出想说但又没有说的东西:四十年来世事的沧桑,人生的巨变。诗中没有一个字正面及此,只谈相会,但透过那深沉的追忆感喟,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正是那场大动乱的阴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吗?这里艺术上的故作轻松,正是诗人对唐王朝盛衰嬗递的现实及其创伤的反应姿态。这种实为沉痛之至的“轻松”不正是诗人心灵痛苦挣扎的无奈自哂吗?
时至中唐后期,盛世的繁荣只是在老人们的记忆中残留着,现实却是暗淡而阴沉的。生活于其间的韩派诗人,承继于杜,在艺术上刻意求新,求奇,以美为丑,以丑为美,构造一个个光怪陆离的美学世界来托寄那份清苦的心境,抒写命运的悲剧。
李贺,他也许天生就是一个内向而敏感的人。骑着驴,背着破锦囊,象一个梦游病人似的游荡着,寻觅他的诗句,一方面以抒其心中浓雾般的忧郁,一方面编织着色彩斑斓的憧憬,他好象一个失魂落魄的孩子,总在凄凄惶惶中寻觅着,又总什么也找不到,这是安史之乱后诞生的一代人的普遍感觉。李贺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东西,于是神往那飘缈的仙境,构想着一个个他自己心目中的神仙世界。如《天上谣》,你可以看出诗人在穷愁苦恨之际,是多么厌倦这个尘网,多么热忱地憧憬着那另一个世界的幸福生活。而同时,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灵,另一端又牵着冥界,他宁愿与鬼交友谈心,应知李贺心中人世间冷酷的程度。我们不能不一掬同情之泪,诗人的挣扎竟是如何的悲苦!诗人呀!你那颗流浪的心灵,在人世间,竟然连一个偏僻的角落也找寻不到?
二、寻找心灵的避难所
如果说,安史之乱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的严重危机的一次总爆发,那么它带来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却是盛唐精神的丧失、文人心灵的裂变。昨天还是霓裳羽衣舞,而今却是渔阳鼙鼓来,他们的灵魂在这两极中被撕扯,心灵作为战场,必须时时经受住他们互相的残杀与蹂躏。于是,主体的重心移位了,倾斜了。时代放弃了他们,他们也抛弃了时代,面临重新选择的命运,一颗颗孤寂荒凉的心,一双双空茫失落的眼睛,在搜求……
孤独的哀吟,无可奈何的感喟以及心理变态的孤芳自赏或自暴自弃的沉沦,是他们的共同选择。力图采取逃避、超脱现实的态度,在山水田园这片宁静的天地安顿流浪的身心,寄托那段纤弱的情意,那段冷漠的幽趣。这里,人是孤独的,是自我选择的孤独,就是要获得离开尘世的孤独。也许并不孤独,他们以自然为侣,看飘泊的船随风吹转:“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江村即事》);在峰回路转的回旋中与明月做迷藏:“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韩翃《宿石邑山中》);甚至见新月而下拜:“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李端《拜新月》);人归去而独寻:“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在松荫泉畔弹起那不合相宜的古调:“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刘长卿《听弹琴》),孤芳自赏;在秋风冷雨之夜送去一瓢冷酒:“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带去友情的安慰……可是这种种萧疏散懒的心态,无可无不可的人生观的内层却又是潜在着一颗多么无奈深悲的忧心!透过这一颗颗灵魂,不也可以感到时代传来的讯息吗?“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韦应物《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波浪中的船,在风里打旋,那也是不由自主的。
中唐山水诗人的那种心灵的深刻矛盾,历史地延续到元白身上,却又有所不同。他们清醒地接受了现实的残酷,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文人,当然就要极力地匡国济民,“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③然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是皇权专制下的文官政治。唯其如此,兼济天下的志向能否畅通,便首先得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圣明的天子,就是说,他们兼济天下的志向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天下好治而龙颜难犯啊!而事实上,现实也总不是那么理想,皇帝并不那么英明,因而士大夫们的仕途也就不那么顺利,天下也并不永久太平,于是文人们就要兼济,兼济之举乃是天下之大公,但普天下又属于天下之大私,于是兼济之公便每每触犯天子之私,而天子又是独尊的,结果便是奉兼济之公者将危及自身之私。他们便只好“独善其身”,退出或躲避这种争夺倾轧,这是一个无可逃逸的怪圈,一代代知识分子就在这怪圈中挣扎、讨生活。
白居易始终是个儒者。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思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今,奉身而退。”④“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期间,自以为皇帝初即位,朝廷有正人,陈力以出,“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写了大量的讽谕诗,结果数遭打击、贬谪,于是有了很多感伤诗。如此现实,感伤又有什么用呢?独善其身,心平气和吧,于是有许多闲适诗。白居易对自己诗歌的分类──讽谕、感伤、闲适──恰好同步于他追求理想、失败而起悲感,努力消解悲感的心路历程。它是诗人对自己一生流浪探索的总结,而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所有中国士大夫文人理想追求之路的一种典范,它的准确性也足以使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显得多余偏颇。
迫于现实的压力,白居易的兼济之心内缩为独善之道,带着一颗要求平静自己的心走向了自然,自然也象慈母一样以温存柔爱安慰了他痛苦的心灵。“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白居易《浔阳春》)风和日丽,花香鸟语,春天带着她欢快的节奏,来寻找心怀伤感、沦落不遇的诗人,温暖他痛苦的心灵,然而春虽好,愁意浓,自然能把诗人从悲苦心境中解脱出来吗?“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春题湖上》)“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钱塘湖春行》)明朗、热闹、流利、有生气,这里充满了一个凡人雅士对自然的爱,从他对自然景色认真细腻的观察欣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深的爱恋就知道,自然完全可以解愁。《遗爱诗》《暮江吟》《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充满了欢愉和闲适,显得美丽悦人。感伤之情已完全转化为闲适之心了。西方的勇士在外面战得遍体鳞伤,就逃到爱人身边,得到一丝温存,中国士大夫在仕途中受到重创之后,往往逃到自然这块避难所,得到安慰,在这种安慰中,白居易已经真正闲适起来了,面对温存美丽的自然,他忘情地吟出“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达哉白乐天》)的诗句。
三、追赶梦中的“蝴蝶”
太和、大中年间的诗人由于时代的苦闷压抑,心理消沉,灵魂裂变,自我信念失落,与之同步的便是主体内在感受的加强。诗人们或是缅怀过去或是钻进私人生活的狭窄圈子吟诵只属于自己的歌。“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思古之心昭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溺情之深易见。怀古、咏史、爱情之作大兴,怀念既往,堕入私情,是晚唐五代文人不满现实心态的曲折反映。自己不满当道,就逃避,或另造一虚境,或于温柔乡里寄托自己的精神。杜牧把作赋论兵和听歌纵酒集于一身,怀着跌荡坦率的豪情,唱出十载扬州的绮梦;温庭筠则拖着仆仆风尘的身影,吟唱穿行在亭台楼榭和荒村茅店之中;而李商隐却又那么执着而惆怅地留恋着乐游原上的夕阳,绵邈而深沉地弹奏着那象征华年如水的锦瑟。不同个性的诗人,有着不同的追索探求,然而却共同地走进了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彩色的捕捉追求之中。
李商隐从一个孤儿考取进士,从此踏入仕途开始其宦海浮沉,早依令狐楚而楚卒,继依王茂元而元亡,并由此卷入党争。“党局嫌猜,一生坎坷,自此基矣。”⑤不仅如此,作为李商隐这样一个激切主张“安危须共主君忧”的诗人,原来是具有“欲回天地”的中兴壮志的,可是因为“凤巢西隔”,得不到朝廷的使用,无从施展他的抱负才略,“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方命两相妨”(李商隐《有感》)便是诗人的自我感叹。一路颠簸,一路挣扎,已是遍体鳞伤,于是诗人希望借用爱情这块柔软的轻纱来擦干那伤痕累累的灵魂的血迹。然而,在爱情生活中,诗人同样经历了深深的痛苦折磨,先是柳枝,后是王氏,接连夭折,又在受伤的灵魂上猛戮一刀。美好的愿望终无法逃脱厄运的蹂躏,因而,在李商隐为爱情所唱出的“祝酒歌”中,我们也没有听到太多欢乐明亮的调子,诗人在政治、爱情两方面的理想都遭到严重的郁结,却仍然坚持执拗的努力,他是一个顽强的人,他有一颗流浪的心,始终不会因理想的受挫而停止继续的追求。爱情的轻纱已被现实的魔爪撕得粉碎,他于是另辟蹊径,转为精神上的爱情追求,这也许是对现实压抑的一种特殊反抗形式吧!现实彻底驱逐了诗人,诗人的心只能到梦中寻找一个非现实的安顿处,这意味着诗人对现实追求的放弃,但并不表示诗人对理想追求的放弃,相反,梦以表现为对现实悲剧意识的提醒而执行着执着追求的功能。梦中需要实现的东西,就是他们在现实中要实现的东西。
无题诗中对于纯洁爱情的歌颂,隐约透露出一个“我”不甘理想破灭、勇于探求真理的呐喊。无题诗中的爱情,犹如水晶碧玉,纯洁无瑕几达透明的程度。纯真的爱情,在人生无尽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是以爱情形式体现出来的一支“生命进行曲”,同时担负着把那久被压抑的美好理想与精神追求解放出来的使命,一句话,那是以爱情的视角而透视整个社会人生的深沉吟思。有着丰富两性情感生活的诗人,在寻找失落的爱情时,感悟到了整个生命的意义,融入到整个社会人生中去,化为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探究的复杂情感,由爱情升华深化到更广阔的情感天地。因此,许多无题诗既可理解为爱情诗,又不仅仅如此。因为坚贞的纯洁爱情与高尚的精神寄托在同一首诗歌境界中得到了完善和谐的统一。《锦瑟》诗一开始就展示出一种非常的执着性。“无端”使人对人生的意义产生怀疑,那是探究生命价值的困扰。“思华年”,是对人生道路的反省、追寻,“一弦一柱”都化作诗人对“华年”的一声声感喟,对人生目的刻骨铭心的质疑。接着又以蝴蝶、杜鹃的意象引起梦境与现实的对比,这般对比,正体现了诗人的艰苦探索。而颈联中,鲛人与诗人、泪珠与珍珠、现实与想象,在沧海月明之中融为一境,是那样渺茫恍惚,那样朦胧迷离,却通过“沧海月明”、“暖玉生烟”的优美意象表现出来,恰恰传达出美好理想逝去后,诗人只觉一片混沌、如梦如幻的主观感受。“此情”与“追忆”和“当时”的联系确立了作为对华年往事的回忆所具有的非现实感,这样就把诗从幻觉的朦胧自由带到对不可回避的确定现实的自觉,这正是诗人自觉探究人生价值而不得其解的一种痛苦折磨。诗人不只是为了追求梦境而向往梦境,寄意杜鹃而盼切杜鹃,不要忽略了诗人矢志不渝的高洁信念,忘记了诗人密切结合着“善”的一种卓越的美和理想的追求。尽管在坚持理想的同时还不时透出彷徨、脆弱的情绪,但他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毕竟是始终处于在寂寞中燃烧的状态。火焰从未熄灭,标志着“华年”的“锦瑟”永远弹奏着婉转却又执拗的弦声。对于“晓梦”中“蝴蝶”的迷恋追赶,是诗人精神追求的自我写照。这种由“锦瑟”而触发的情爱,以及由于爱而难得,青春不能长驻引起的悲感,而引发到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思索,不正是诗人对于流浪自身本质的一次探求顿悟吗?
只要我们的诗人们还在浅吟低唱,他们就只能永远带着一颗流浪的心灵,无法摆脱流浪的命运。为了他们的“原罪”,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去开始其漫漫人生、茫茫追求……
注释:
①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序
②《老杜浣花溪图引》,见《豫章黄先生外集》卷四
③白居易《新乐府序》
④白居易《与元九书》
⑤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开成三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