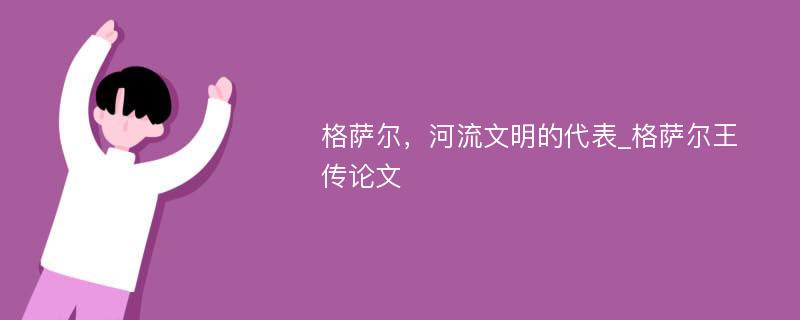
江河源文明的代表——《格萨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表论文,格萨尔论文,江河源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决定,在2002-2003年参与中国史诗《格萨尔王传》千年纪念。
这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包括藏、蒙、土、裕固、纳西族史诗创造智慧的国际认可和崇高的肯定;也是对建国50多年以来,尤其是近20多年来我国《格萨(斯)尔》史诗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国际认可和崇高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海等地的民间文学研究组织,在抢救、翻译和出版《格萨尔》方面,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做了不少难能可贵的工作。80年代初至今,我国政府对抢救《格萨尔王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史诗的抢救与出版多次被列为国家级重点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四部委专门设立了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在西藏、青海、内蒙古、甘肃、新疆、四川、云南等七省区设立办公室。四部委联合召开了全国范围的表彰会两次,《格萨尔》说唱家命名大会一次,成果展览一次,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四次,出版研究集刊、集成、论文集等15部。迄今共出版藏文《格萨尔王传》75部,蒙文《格萨尔传》22部,藏译汉近30部,蒙译汉5部,《格萨尔》文库(科学版)4本。另有学术研究专著近20部,录制艺人说唱磁带5000小时。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的40部的《格萨尔》精选本,已出版4部,45部的桑珠艺人说唱本已出5部。也就是说,经过近20年的努力,这项史诗建设工程已初具规模,规划领导已形成体制,文本整理出版已上了路子,研究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千年纪念乃是对一项国宝级的文化遗产进行世纪性的展示。我们有责任把这项纪念活动做好,做得精彩深入,扩大影响,从中展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光彩。这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盛举,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盛举,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盛举。
《格萨尔》是中国西部藏、蒙等几个少数民族在这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共同创造的盖世瑰宝。对它的纪念,就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创造力的纪念。你要了解高原上、草原上的少数民族具有何等辉煌的第一流的创造力吗?请读一读《格萨尔》。它的想像空间是雄伟壮阔的,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这千年最具有高山旷野气息的超级史诗。其想像出入于天地寰宇,驰骋于高山神湖。写英雄则自天而降,赛马夺魁,降妖伏魔;写魔王则“吃一百个人做早点,吃一百个男孩做午餐,吃一百个少女做晚餐”,胃口极大,贪欲无限,凶恶至极;写美人则如彩虹,如雪山月光,灿若太阳,美若莲花。这些想像方式都具有高原民族的崇高感和力度。就拿写美人来说,中原民族喻之杨柳腰、樱桃口,与此对比,就显得过于文弱秀巧了。霍尔王派出选美的乌雅说珠牡“她前进一步,价值百匹好骏马;她后退一步,价值百头好肥羊”,这也是游牧民族才有的比喻,汉族地区说是“价值连城”,说绝世佳人是“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都是平原地区以城池作为攻守的基本依靠所产生的比喻。
只有具备这种高山旷野的气魄和气概,《格萨尔》才可能在千年间的艺人说唱过程中,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成为世界上篇幅最长,达50万行以上的超大型史诗,茫茫九流,滚滚滔滔如长江大河。
《格萨尔》是人类文化多样性魅力的伟大见证。对它的纪念,也就是在全球化的当代潮流中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文化多保留一份精采。它产生于西藏九世纪达玛灭佛、赞普王朝崩溃之后,那几百年间藏传佛教教派纷起,政治上分崩离析,民心、民气、民风都转向一个“寻找英雄”的时代。这个英雄在北方可以征服吃人魔王鲁赞,征服抢劫美人和牛羊财富的霍尔王,也就是说北方是他们的家庭、国家的主要威胁。这个英雄在南方可以保护盐海不被姜国萨丹王吞占,可以保护自己的盟友不被门国的魔王骚扰,即是说,南方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和后院。这个英雄赛马夺魁,不需什么高贵血统,就能当岭国国王,娶最美的美女珠牡为妻,这也是游牧文化的价值观,而不是宗法文化的价值观。
它的战争观也与中原礼乐文化不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康德说:“战争乃是带动文明继续前进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西方文化在战争观上带有进攻性。中原文化,比如《诗经》少有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多写征人思归。《老子》则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这种文化主张“耀德不观兵”,即使战争失败了,也能以柔克刚,以文化把对方同化过来。而《格萨尔》则是战争的颂歌,降妖伏魔,大小百十战役,连它的赞词长至十数行、数百行,也多是英雄赞、马赞、鞍赞、刀剑赞、弓箭赞、盔甲赞等战争礼赞。主张以柔克刚的中原文明,由于有了这种少数民族边疆文明而变得质文互补、刚柔相济,呈现出内在的丰富性。我常说,文化上有一种“边缘的活力”。就是说当中原文明模式化甚至僵化之后,边疆地区的文明给它输入带原始野性的新鲜血液。中华文明五千年不中断而保持坚韧的生命力,正是这种中原文明的凝聚力和边疆文明的新鲜活力互动互补的结果。
就史诗本身而言,《格萨尔》提供了高原史诗的形态,与《江格尔》、《玛纳斯》和南北少数民族的百余部史诗一起,又提供了草原史诗和山地史诗的形态。这是与巴比伦的河流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海洋城邦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森林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形态不同的文化创造。《格萨尔》既丰富了人类史诗的形态,也将改变人类史诗分布的地图。
《格萨尔》蕴含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历史文化哲学。对它的纪念,包含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包含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也包含着对中国文化哲学的重新反思。在数千年的民族行程中,汉族先在黄河地区实行多部族的融合,然后及于长江、岭南和北方部分胡人,都在滚雪球过程中形成汉民族。藏族和蒙古族内部也有滚雪球、融合多部族的过程,最明显的是松赞干布在公元7世纪统一吐蕃,蒙古各部落1206年在鄂嫩河源头结盟,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即成吉思汗。《格萨尔》写岭南有上岭色氏八部落,中岭文布六部落,下岭穆姜三部落,还噶珠秋部落,丹玛12万户,达绒18部落,也表明它们在竞争中融合的民族史哲学。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明形态,是包含着各民族的文化原创性和兼融性的双重的文化哲学,以原创牵动兼融,以兼融托起原创。我们过去讲中华文明,着重讲黄河文明,近30年发现了大量楚文物,四川三星堆,浙江河姆渡文明。长江文明的加入,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开拓了新的境界。《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在长江黄河源头的周围发生。江河源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它在丝绸之路的侧翼,既保持了高山文明的原始性特征,又渗透着中原文明、西域文明、蒙藏文明、印度文明的多重因素,是东亚、中亚、南亚文明的结合部,各种文明交汇之地。1219年,全真道道士丘处机以70余岁高龄,率18高徒跋涉数万里,远赴西域雪山行营见成吉思汗。40年后,即1260年,忽必烈入主中原,尊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就发生在这块土地的附近。江河源文明的加入,也势必如当年长江文明的加入一样,将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加强对藏族文化史,蒙古族文化史,蒙、藏、汉、西域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格萨尔》代表的江河源文明的混杂性,高原文化的崇高感、神秘感和它的自由想像空间的开阔性。因此,《格萨尔》不仅代表人类史诗的一种形态,而且代表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子文明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