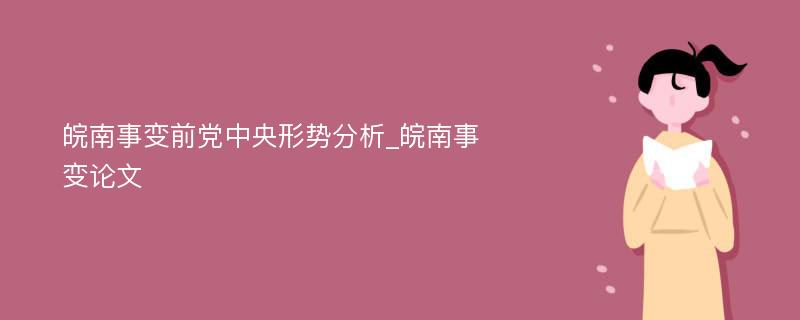
论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事变论文,中共中央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辅一同志所著《项英传》出版后,引起了党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肯定、赞扬的同时,对书中的某些史实和观点,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和质疑。我对有的学者提出的批评是同意的。但对另一些学者提出的批评,如关于皖南事变前党中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估计是否有失误?1941年1月15 日《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否应该肯定等,我认为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一
1940年9月27日,德、意、 日三国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并立即对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苏关系、中德关系以及国内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
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仗着三国军事同盟的强大实力,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在中德关系方面,德国再次扮演劝降角色;在中英、中美关系方面,英美因担心日本南进,迅速改变对华政策,英国放弃对日妥协,重新开放被关闭三个月之久的滇缅路,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中立主义”,表示不承认刚成立的汪伪南京政权,并宣布给中国贷款。当时的苏联,深知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只是时间问题,最担心的是德国从西进攻,日本从东进攻,从而使自己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认为进一步增加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可以捆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手脚。1940年11月斯大林决定派崔可夫将军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并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面前,蒋介石怀有自己的图谋和计划。他对日本的诱降和德国的劝降,其态度是明确的,即他不能搞什么蒋、汪合作,作新的卖国贼,但认为保持与日本的接触,对争取英、美、苏更多的援助,是非常有用的。他稍稍往日本方面靠一点,英、美、苏都会立即感到不安;他若再往英、美、苏这边靠近,日本也会很着急。这时,蒋俨然成了一个左右时局的大筹码。当然,蒋介石最为高兴的是,他可以利用新的国际形势,为他在国内搞反共摩擦服务。日本要拉他,他可在反共方面同日寇达到某种默契;英、美、苏要靠他拖住日本,对他加剧国内国共摩擦或者会无可奈何,或者亦不至横加干涉。他欣喜地说:“抗战以来国际情势之好转,未有如今日”。(转引自陈枫:《皖南事变始末》,1版,4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蒋介石决心在此种形势下加剧国共摩擦,并很快将其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中。
1940年10月上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韩德勤统率三万余兵力,在苏北抢占黄桥。10月19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给我军发出《皓电》,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11月初,国民党军队李品仙、张义纯部在皖中、鄂东“围剿”新四军。11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38师拟定作战计划, 要对皖东新四军进行“扫荡”。接着,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种新的国际国内局势,是如何分析和估计的呢?毛泽东认为,目前国民党掀起的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投降日本与加入德意日同盟的准备”,“蒋介石不论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给我党以大的打击,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指出“时局将急转直下”,国共有“永久决裂之可能”,“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1版,7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为了取得苏联的大力援助,毛泽东致电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依意斯基,告知国内危局:蒋介石准备投降,近日发动大规模反共运动,企图为直接投降肃清道路,并请求苏联对蒋施加压力,以延缓两三个月。
在这种形势之下,毛泽东对全党的应变方针、策略、部署作了周密的考虑,并拟定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其具体内容是:政治上坚决地、大张旗鼓地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投降面目;军事上则是当顽军发动军事进攻时,我仅在根据地附近进行自卫反击,不攻入顽军后方。为此,八路军需调5万人南下支援新四军。 毛泽东认为,采取此方案,政治上有利,可剥夺蒋的借口,但军事上不利,“不能以实力制止投降”,我军可能遭日蒋之夹击。
第二方案为“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进攻”。采取此种方案,“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出至少十万至十五万(以后改为20万人——引者注)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在原地抗日”。毛泽东认为,采取此方案,政治上有利之处是“可能制止投降”,不利之处是“给蒋以政治资本”,而军事上的好处是“可制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同上书,第77页。)
毛泽东认为:不论目前采取何种方案,如投降实现,最后也是严重内战,故整个军事部署,目前即需考虑。拟将华北的兵力组成三个纵队,以老黄河以南各军为左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鄂豫陕边;以汾离路、正太路、仓石路以北各军为右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陕甘川边;以两地之间各军为中央纵队,其精锐约五万,或出左纵队方向,或出右纵队方向,依将来情况决定。以后毛泽东又提出组织一支二万人左右的挺进军,打到敌人后方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计划。为此,他指示在华中的黄克诚、罗炳辉部,必须在半月或一月筹集50万元以上贮积备用。在此期间,党中央决定对皖南新四军驻防采取让步,多次催促叶挺、项英尽快北移。
事实证明,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央认定蒋介石将立即投降日寇、全面反共,国共将“永久决裂”的分析和估计,确有过头之处。因蒋介石究竟不同于汪精卫,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是决定一切的,只要这个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蒋介石就不可能真正投降,因而他也不可能真正与中共全面决裂,发动全面内战。但我们又应该说,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上述分析和估计、以及有关我党应变的准备和部署,是无可非议的。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谁也不可能料事如神,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总能作出精确无误的预测;此外,对于党的领导者,把时局的黑暗面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困难设想的多一点,对武装全党思想,提高警觉性,也总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应对此有过多的计较,作事后诸葛亮。
问题是在国际国内局势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对蒋介石动向的分析,突然转到另一极端,由强调蒋将立即投降、全面反共,转为强调他对日投降远未讲好条件,强调他搞反共摩擦的困难性和欺骗性,而对我之政治优势、军事实力又作出过高估计,在党的行动方针上则淡化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紧张气氛。
在毛泽东看来,目前蒋介石仍处于矛盾与犹豫之中:一方面,积极调兵遣将进攻新四军;另一方面,又担心乱子闹大不好收拾。因此,低估了蒋介石。1940年11月5日,他致电周恩来及八路军、 新四军高级将领,认为蒋介石对我发动军事进攻,存在五大困难:1.我取缓和态度,何应钦缺少挑拨的借口;2.蒋很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北突出;3.蒋怕我在皖南不动,扰乱其后方;4.蒋与顾祝同怕我消灭韩德勤;5.蒋还未同日寇讲好投降的条件,其剿共战场多有不便,难以形成。因此,“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同上书,第101页。)
21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项英等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指何应钦——引者注)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引者注)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毛泽东说,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同上书,第101~102页。)
29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等人,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目前蒋介石向我大举进攻都是不可能的。30日,毛泽东又电示周恩来等,再次阐述蒋的吓人战术:蒋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外部不稳固。毛泽东断定,蒋现在奉行的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故“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同上书,第104页。)
11月30日,日本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华基本条约》,正式承认汪精卫伪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毛泽东认为,日、汪合作,日本大举向鄂西进攻,对蒋介石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关系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即“反共高潮快要完结,我们要准备新的攻势了”。所谓新的攻势,就是我军在苏北举行的曹甸战役。曹甸战役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曹甸位于江苏淮安东南,兴化以北,其所在一带为韩德勤部盘踞,隔断了我军苏北与皖东间的联系,实为一大障碍。11月1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着手作战准备,29日开始发动攻击,目的是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打通苏皖通道。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共出动了1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进攻韩部。战斗开始后进展很顺利,很快占领了许多县城和村镇。12月1日,韩德勤向蒋介石发出特急电文, 请求增援,以挽危局。最后,由于韩德勤拼死守卫,曹甸经多次强攻未下,战役不得不于12月7日结束。此次战役,韩德勤部被歼灭8 000人,我亦伤亡2 000人。
曹甸战役是在轻敌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它暴露出我华中实力不足。对蒋介石来说,这既使他感觉在苏北仍有余勇可贾,同时更刺激他要尽速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决心,而无须顾虑投鼠忌器。12月10日,蒋致“特急”电予顾祝同:“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进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指示顾祝同“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主编:《新四军参考资料》,1版,2册,377页,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1。)蒋介石在曹甸战役进行中,就对消灭我皖南新四军下了这样的死命令,这是当时我党中央未曾料到的。中央对形势仍是一片乐观情绪。毛泽东在12月6日、19日和23 日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仍重复说:“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蒋“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版,中卷,241、242、 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蒋介石到底是一个既精于算计,又善于逢场作戏的政治家。韩德勤在抢占黄桥战役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蒋极为恼怒,问题在于,他虽决心“复仇”,但“捏住鼻子没有说话”。(《周恩来选集》,1 版,上卷,2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这次曹甸战役, 韩又遭沉重打击,蒋下令对皖南新四军要“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可是他不仅未大肆嚷嚷,而且选择四年前西安事变中他回南京的12月25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重庆召见周恩来,作了一番“极感情的神情”的长篇谈话。主要内容是:1.新四军立即开往黄河以北,按照划定区域发展;2.如果坚持留在江北,国共冲突在所难免;3.经过皖北,我绝不出兵,保证安全通过。
对皖南事变前夕蒋介石这一席重要谈话作出准确判断,是极为重要的,只可惜当时党中央未能作到这一点。周恩来认为,蒋是“大灌米汤”,(同上书,第201页。)是“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 认为时局的发展不过是“半拖半打,半打半拖”。(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2页。)毛泽东在12月30日、31日致周恩来、 致几个中央局等的电报中,则说现在是蒋介石“着急”,我们并不着急,“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同上书,第124页。 )此电对蒋介石进攻山东的决心有了新的认识,但对顾祝同火速从浙赣闽三省调兵遣将,在皖南新四军周围共集结7个多师、8万余兵力,设置袋形包围网,对第32集团军具体拟定了《围歼皖南新四军计划》,则十分隔膜,毫无察觉,甚至还说:“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同上书,第127页。)
从以上这些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1月12日以前,中央对当时形势的黑暗面、危急面、不利面估计过重;11月12日以后,对形势中的光明面、缓和面、有利面估计过头,轻率得出蒋搞的不过是“流氓”、“吓人”战术,实际他很怕内战、很怕国共破裂,因而这次反共摩擦“只会比上次小,不会比上次大”,北移可“拖一两个月”等错误结论,并在这种乐观、轻敌思想指导下,进行了很不合时宜的曹甸战役。我们知道,项英对离开皖南一直思想不通,迟迟下不了北移的决心,他对中央的许多好意见、批评,可说一句也听不进去,但是他对中央指示“偏要拖一两个月”,可谓全部接受,彻底的听进去了,以致当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出征北移时,为时已晚。因此,皖南新四军的悲惨结局,项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
有人认为,皖南事变前,中央在对形势的分析及决策上并无失误,如果承认中央有失误,那就会“涉及到抗日战争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性”,并会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看法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这样一种以点代面、以个别代替一般的观点,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因为我们说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在对待蒋介石抗日和反共的问题上,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上,在指导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问题上有“失误”,而不是说党中央关于抗战中期的方针政策是错误的,也不是说中央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方针政策是错误的,我们怎么能把这两个不同概念等同起来呢?难道这两个概括不同时间、不同问题的提法是一致的吗?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由反蒋到逼蒋,再到联蒋,政策上的转变较为迟缓,曲折较多。西安事变之后,中央曾一度提出要“审蒋”、“诛蒋”,难道人们指出这一点,就是否定党中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否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延安整风时,中央的审干工作曾一度出现很大的偏差,后来发展为“抢救失足者运动”,极大地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不良后果,难道指出这一点,就是全盘否定整风运动。
至于胡乔木对这段历史的分析和评价,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胡乔木对皖南事变前后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予以肯定和高度赞扬的。他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抗战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一段。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次运用得淋漓尽致。这是很难得的一段历史经验”,“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1版,27~28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但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胡乔木的这些论断,即可看出他讲这些话,是纵观第二次反共高潮全局和结局来说的,是讲毛泽东根据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则,制定了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对顽固派的斗争有理、有利、有节,从而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极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绝不是说,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夕关于蒋介石搞“流氓”、“吓人”政策,此次反共高潮“只会比上次小,不会比上次大”,因而我们北移“偏要再拖一两个月”等,也会是正确的,更不是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一时万分激动,制定“政治上军事上全面进攻”的政策,要派我军主力打到国统区去,这也是正确的。
有人在引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论断时,故意不引用书中有关评价毛泽东在皖南事变中表现的下面这段话,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段话是:“从毛主席的文电以及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同他的电文来往,还可以看到,他(指毛泽东——引者注)的有些认识最初也并非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是立即北移的主张。……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新四军的无比愤慨,一度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又只强调坏转的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之合作已经完结,目前不是打退反共高潮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的问题,提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全面大反攻的方针”。由于刘少奇的建议,中央最后“放弃了一度产生的偏激的认识”。(同上书,第119~120页。)这段话,不正是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在皖南事变前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对蒋的方针政策上,曾有过失误吗?
有人认为,毛泽东指示项英“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说其中的“拖”是以“走”为前提;又说“拖”只是对国民党的“斗争策略手段”,并非“行动方针”;还说如果说“拖”,这也是项英“逼出来的”。似乎毛泽东本来是不想“拖”的。这种辩解实在也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当时的确没有指示项英停止北移,只说了“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项英也只是接受了“拖”的指示,从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说“拖一两个月”,到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出发北移,一共“拖”了44天,最后走进了顾祝同严密设置的袋形包围圈,招致惨败的结局。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去总结“拖一两个月”和不拖一两个月的教训得失,却去争辩“拖”是不是以“走”为前提,这会有何教益?难道“拖”并未错,只是项英理解错了,未能理解“拖”是以“走”为前提吗?
说“拖”是“斗争策略手段”,“走”才是“行动方针”,这也不对。任何“策略”,都是为了指导斗争“行动”的,根本不准备付诸实践的斗争策略,恐怕是没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斗争策略”与“行动方针”二者是相一致的。从1940年11月12日到12月31日的五十多天中,中央的几十个电报反复的指示:蒋介石搞的不过是“流氓”、“吓人”战术,他搞反共摩擦困难重重,此次反共摩擦规模“只会比上次小,不会比上次大”,“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这怎么能说中央仅是“斗争策略手段”,而不是“行动方针”呢?项英当然是把中央的指示当成“行动方针”来理解的,我们不能拿这点来责怪项英。
说“拖”是项英“逼”出来的,这就更离奇了。毛泽东有如此的不讲原则、如此的软弱吗?难道他会在五十多天中天天被逼着说项英爱听的话,而自己全无主张?其次,项英果有如此大的能耐,能逼得中央天天附和他。
三
在此,我还想就1941年1月15日《决定》的结论是否正确, 简单谈一点看法。
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确有“中央在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的观点。有人以此为据继续坚持过去的看法。这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学术问题,一切都必须以实践来检验,必须言之有理,以理服人。如果一定要以本本来协助论战,我倒觉得应仔细研究一下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于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及由胡绳主编于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两部权威著作,只字未提1941年1月15日《决定》。 这一点绝非偶然,也不是一种巧合。这两部著作在写皖南事变时,对项英的评述、批评都是很有分寸的,如说项英有很大的弱点: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固派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损失。其中没有一句话重复了中央1941年1月15 日《决定》中的批评。
历史证明,中央1941年1月15日《决定》,是在形势紧急, 情况不明,情绪悲愤、激动的特殊条件下仓促作出的,因此对项英的批评,明显的有很多过头和不实之处,如说项英“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决定》不仅把项英与张国焘视同一类,而且还怀疑“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显然,《决定》中的这些话说过了头,与历史事实是相悖的。项英从参加革命到牺牲,前后有31年之久。他曾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军内曾担任过非常重要的职务。他经历过严酷的白区工作斗争的考验,也经历过出生入死的三年红军游击战争的考验。1937年12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受到中央的肯定,称项英是“全党的模范”,号召全党向他学习。抗战开始后,他对新四军的创建、发展,对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都是有功劳、有贡献的,怎么他一夜之间就成了“一贯的机会主义”,“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呢?皖南事变之后,把一切责任都推在项英头上,对项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作法,这既不公平,也与中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一贯方针相背离。因此,对中央1941 年1月15日的《决定》,不应笼而统之地唱颂歌,而应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分清其正确与错误之处,还项英、袁国平等人的本来面目。
标签:皖南事变论文; 新四军论文; 项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毛泽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