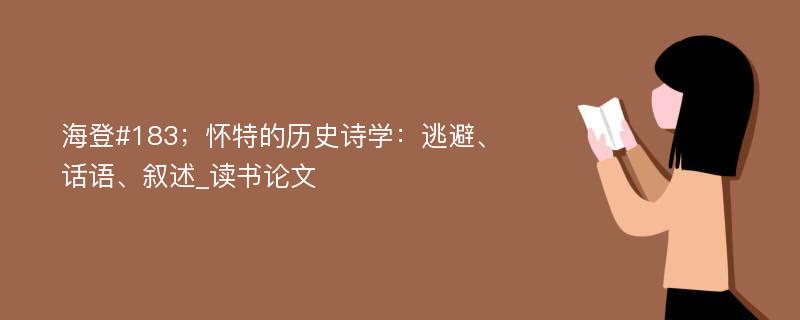
海登#183;怀特的历史诗学:转义、话语、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特论文,诗学论文,话语论文,海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1)06-0051-05
海登·怀特与其说是一位文学批评家,毋宁说是一位历史批评家。他不撰写历史,在严格意义上也不研究“真正的”历史,而是把历史修撰甚或历史研究的方法作为他的研究对象,因此,他所从事的是历史研究的研究。他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修撰就所涉及的史实性材料而言,与其他方式的写作没有什么区别。历史修撰中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文本形式。而形式说到底就是语言,因此,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注:海登·怀特:《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前言:历史的诗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第2页。)如此看来,怀特的研究方法是形式主义的。他的目的是要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找到共同的结构因素,包括不同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思维中体现的相同特征,以及他们撰写的历史著作可能包含的理想的叙事结构,以便“追溯变化,勾勒出所论时代的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注:海登·怀特:《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前言:历史的诗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第2页。)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怀特首先从历史著作的概念化层面入手,详尽厘清了历史修撰中的5个重要方面:(1)编年史;(2)故事;(3)情节编排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含义的模式。这5个方面是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可或缺的要素,构成了怀特所说的“历史场”,其中包括未经加工的历史记录,各种历史叙事,以及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协作关系。严格说来,这5个要素是历史的书写及其接受的5个阶段。
“编年史”和“故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类”或“体裁”,而是历史修撰的最初步骤,都是历史叙事中的原始成分,都是有待选择和编排的“数据”。一个编年史是一个纯粹罗列的事件的名单,它是开放的,因而无始无终,没有高潮和低谷。但它并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按事件发生的年代顺序排列的,是经过编年史家的精心选择的。这样,经过这个选择和编序的过程,事件就变成了“景观”或“发生过程”,就有了可辨认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然后通过具有“初始动机”、“终极动机”或“过渡性动机”的描写,编年史中的事件就具有了意义,这就是“把编年史变成故事”的过程。而“编年史”与“故事”的区别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故事”是指历史学家所讲的那种故事,具有可辨认的形式,追溯从社会和文化过程的开端到终止的序列事件的发展过程。但是,故事中的“事件”与编年史中的“事件”是有区别的:编年史中的事件是“在时间中”的事件,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被“发现”的,因而不具有“叙事性”。换言之,编年史中的事件存在于作者即历史学家的意识之外,是可证实的已经构成了的事件,历史学家要对这些事件进行选择、排除、强调和归类,从而将其变成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也就是通过“发现”、“识别”、“揭示”或“解释”而为编年史中掩藏的故事“编排情节”,这就是历史学家把编年史变成故事或建构成历史叙事的过程。如是理解,故事中的“事件”也就是历史中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是历史学家的“发现”,但也具有一定的“发明”性质,因而是“叙事性”的,而正是这种“叙事性”揭示和解释了历史中事件的意义、连贯性和历史性本身。
那么,历史学家所讲的那种故事是怎样被“编排”或“组织”起来而成为完整的叙事性故事的呢?这要经过以下3个运作过程。
首先是“通过情节编排进行解释”的过程,怀特将其定义为“通过识别所讲故事的种类为故事提供意义”,而“情节编排则是把一系列事件编成一个故事,通过逐渐展开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种类的故事”。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识别故事的种类。怀特根据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识别出4种“故事”形式,也就是他所说的“情节编排模式”:即罗曼司、悲剧、喜剧和讽刺,不同的历史学家必然会以某种原型或综合的模式编造他的故事。如米什莱用浪漫模式,兰克用喜剧模式,托克维尔用悲剧模式,而布克哈特则用讽刺模式。“重要的是,每一部历史,甚至最‘共时的’或‘结构的’历史,都必将是以某种方式编排的。”这些情节编排模式也就是历史的原型情节结构,历史学家依据这些结构解释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事件,并在这些“事件的涡流之后或之内看到一种正在进行的关系结构,或在差异中看到同一性的永久回归”。(注:《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7—11页。)
第二个过程是“通过形式论证进行解释”。这里的“解释”是就历史上“发生的事”提出下列问题:“它的主旨是什么?”“它的总体意义是什么?”而“论证”则指的是“话语论证”。在这方面,怀特虽然没有完全抛弃自然科学中使用的自然规律推理的论证方法(或三段论),但根据“历史有别于科学”的观点,他通过借鉴史蒂芬·C·佩珀在《世界的假设》中分析的假设的世界类型,把历史分析中话语论证的形式分为4种:形式论的,有机论的,机械论的和语境论的,即历史分析的4种“范式”。形式论的解释在于识别、标识、确定特定研究客体的特性,包括它的种属和类别,其所属领域所展示的现象的多样性和客体的独特性等。有机论的解释以“集成”和“还原”为特点,把在历史中识别出来的特殊因素看作综合过程的因素,“把个别实体看作各个过程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在聚集成整体时便大于或在性质上不同于各个部分的总和。”(注:《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7—11页。)这种方法注重描写整合过程,往往针对确定的目的或目标,并把充斥于个别过程和整个进程中的思想和原则作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目标的形象和预设,以此赋予历史进程以意义。采用这种模式的历史学家有兰克、封·聚贝尔、莫姆森、特赖奇克、斯塔布斯、梅特兰等。机械论的解释注重因果关系的研究,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结果。按照这种解释,历史中的客体以部分对部分的关系形态存在,因此受控于相互作用的规律。理解这些规律,确定这些规律的特殊性,并用这些规律解释“数据”,就是机械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采用这种模式的历史学家有巴克尔、泰恩、马克思和托克维尔。语境论模式则通过把事件置于它们所发生的“环境”当中来解释事件。这涉及到事件与周围历史空间的关系,与这个空间内其他事件的关系,以及在这个时间和空间的特定环境里,历史作者与动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学家W.H.沃尔什和艾赛亚·柏林所说的“类连结”。所谓“类连结”,是要找出所要解释的客体与同一语境中的不同领域相连结的线索,追溯事件发生的外部自然或社会空间,确定事件发生的根源或判断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把历史中的全部事件和线索编织成一个意义链。有待说明的是,这4种解释模式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也不是可以随意结合运用的;喜欢一种模式而不喜欢另一种,这是由历史学家就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采取的特定立场所决定的。
所谓“意识形态”,怀特指的是在社会实践中采取的立场,而按照这个立场行事就必须遵守一套规则:你要么改造世界,要么维持现状。根据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怀特提出了4种基本的意识形态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怀特那里,这4种立场指的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倾向,而不是特定政党的标识。按怀特自己的解释,“一般的意识形态倾向”包括:
对把社会研究还原为科学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做法之可行性所持的不同态度;对人文科学所能教的课程所持的不同看法;对维护或改变社会现状之可行性所持的不同概念;对改变社会现状所采取的方向和促成这种变化所用的手段的不同构想;最后,还代表着不同的时间取向(把过去、现在或将来看作理想社会范式的时间取向)。(注:海登·怀特:《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22—29页。)
换言之,历史学家在选择特定的叙述形式时就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取向,因此,他给予历史的特定阐释也必定携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比如,就社会变化的问题,保守派不赞成有计划地改变社会现状的做法,而自由派、激进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则肯定持相反的态度。即使在后3者中,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自由派提倡对社会进行机械的调节;激进派提倡依据新的基础重建社会;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旨在废除社会,以普遍信奉“人性”的“群体”取代之。然而,无论哪种意识形态倾向,就其所要实现的乌托邦的时间定位来看,最终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超越社会,另一种是顺应社会。即便政治倾向不甚明显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如布克哈特和尼采)也都难以避免这两种基本倾向,至少可以在情节编排(实际上是审美观照)和话语论证(实际上是认知运作)上反映出来。
至此,怀特已经论证了历史叙事中的“情节编排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含义模式”,并据其各自的“四元组合”找到了它们相互间结构的亲和力。现用图表示如下:
情节编排模式
论证模式
意识形态含义模式
浪漫的 形式论的 无政府主义的
悲剧的 机械论的
激进派的
喜剧的 有机论的
保守派的
讽刺的 语境论的
自由派的
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并不是与其他模式的任何因素任意相容的。这些因素中有些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甚至是相互排斥的。怀特进而从传统诗学和现代语言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这些历史学家在解释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概念策略,这就是他认为能为特定历史时期内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提供语言和诗学基础的转义理论。
在《话语的转义》中,他首先追溯了“转义”这个概念的词源:
转义(tropic)一词派生于tropikos,tropos,在古希腊文中意思是“转动”,在古希腊通用语(Koiné)中意思是“方法”或“方式”。它通过tropus进入现代印欧语系。在古拉丁语中,tropus意思是“隐喻”或“比喻”,在晚期拉丁语中,尤其是在用于音乐理论时,意思是“调子”或“拍子”。所有这些意思后来都沉积在早期英语的trope(转义)一词中。
与“转义”直接相关的是“转义行为”:
是从关于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运动,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从而使事物得以用一种语言表达,同时又考虑到用其他语言表达的可能性。(注: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第2—3页。)
按照传统诗学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怀特识别出4种主要转义: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它们的主要功能是间接或比喻地描写作为客体的经验内容:在字面意义的层面上产生不同的意义还原或综合;在比喻的层面上为抵制清晰再现的内容提供深层的启示。而从性质上说,这4种转义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隐喻是再现的,强调事物的同一性;换喻是还原的,强调事物的外在性;提喻是综合的,强调事物的内在性;而反讽是否定的,在肯定的层面上证实被否定的东西,或相反。就描写功能而言,隐喻表明两个客体之间具有许多明显差异,但却具有一个重要的共性;换喻以隐含的方式比较两个不同客体,通过二者间相互还原的关系形态解释现象之间的差异;提喻从事物的微观与宏观角度解释一个整体内的两个部分,把两个现象的外在关系解作具有共性的内在关系;反讽则是辩证的,元分类的,自觉的。它的基本策略是词语误用,即用明显荒唐的比喻激发对事物性质或描写本身的不充足性的思考。前3种是语言自身提供的运作范式,后一种则是语言为思维方式提供的一种范式。前3种通过语言作用于意识,意识可以根据这些范式预设认知上有问题的经验领域,以便对它们加以分析和解释,这就是说,它们为思想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解释范式。而反讽由于是自觉的,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世界观,因此也是跨意识形态的。这4种转义不但是诗歌和语言理论的基础,也是任何一种历史思维方式的基础,因此是洞察某一特定时期历史想象之深层结构的有效工具。如果在一个特定话语传统中(如19世纪欧洲的历史)运作的话,那就可以通过探讨这四种转义,“从对世界的隐喻理解,经过换喻的和提喻的理解,最终对一切知识的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达到反讽的理解”。(注:参见《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第31—38页。)
与转义直接相关的另一个范畴是“话语”:按怀特的定义,“话语”是一个文类,在形式上有别于逻辑论证,又不同于纯粹的虚构。与转义一样,话语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赢得说话的权利,同时相信事物是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的。就话语与转义的关系而言,怀特认为转义是话语的灵魂,没有转义的行为和机制,话语就不能发挥作用,就不能达到目的。话语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具有一种辩证的双重性。从词源上说,其拉丁语词根(discurrere)就是“前后运动”或“往返运动”的意思。从这种辩证的运动概念,怀特首先看到话语的前逻辑性,即用话语标识出一个经验领域,以供后来进行逻辑分析;和话语的反逻辑性,即解构这个经验领域里已经僵化的概念,从而促进新的认识。其次,这种辩证的运动也说明话语本质上起到了一种协调作用:话语既关注阐释活动本身,同时又关注构成话语主题的客体;既超越对现实的各种对抗性阐释,又在这些阐释之间进行仲裁;因此,话语既批评自我又批评别人,既是阐释的,又是前阐释的。这决定了话语分析的3个步骤:为了分析而对辨认出来的“数据”加以描写;对所描写的题材进行论证或叙述;对前面的描写和论证加以辩证地排列。这就是说,话语在赢得自身说话权利的过程中经历了人类认知意识的整个发展过程:话语中作者叙述的“我”从对经验领域的隐喻描写,通过对话语诸因素进行换喻的建构,转而对这些因素的表面属性和假定的内在关系进行提喻的再现,最后对所发现的任何对比或对抗因素进行反讽的阐释。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就是转义,它们都反映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全过程。
怀特由此在历史修撰中发现了4种“解释”观念:研究特殊规律的解释,语境论的解释,有机论的解释和机械论的解释。特定历史学家之所以喜欢特定的解释方式,是由他所选择或讲述的特种故事、叙事模式、情节编排结构决定的。如果说历史学家借以阐释其材料的方式都具有意识形态或道德含义的话,那么,他们在形式上就只有两个选择:选择情节结构和选择解释范式。而如果情节结构指历史话语的表面现象、解释范式指意义生产系统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历史与文学(和神话)之间、甚或在历史话语与文学批评之间看到了共性。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作为叙事,历史与文学和神话一样都具有“虚构性”,因此必须接受“真实性”标准的检验,即是否具有赋予“真实事件”以意义的能力。作为叙事,历史并不排除关于过去、人生和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虚假意识和信仰,这是文学通过“想象”向意识展示的内容,因此,历史和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想象的”解决。作为叙事,历史使用了“想象”话语中常见的结构和过程,只不过它讲述的是“真实事件”,而不是想象的、发明的事件或建构的事件,这意味着历史与神话、史诗、罗曼司、悲剧、喜剧等虚构形式采取了完全相同的形式结构。(注:见海登·怀特《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载《历史与理论:历史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第1—33页;又见《历史中的阐释》,载《新文学史》,1972—1973年,第4期,第281—314页。)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也是寓言,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以笑剧形式“重演”了1789年的那场悲剧一样。
正是由于历史使用了虚构形式(纯文学形式)的意义生产结构,历史以及关于历史书写的理论才与以语言、言语、文本性为指向的现代文学理论密切联系起来。这也是怀特的历史诗学之所以引起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广泛注意的原因,并使他的《元历史》等主要著述成为英美大学英文系和历史系的必读书。首先,怀特对历史修撰和历史研究的研究是以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特定模式和概念为基础的。他看到了历史著作中不可避免的诗歌性质,这不仅把文学看作一种发明,一种制造,属于一个虚构想象的世界,而且还把历史看作一种具有相同叙事性的话语模式,因为个别的历史话语必然要对它处理的材料进行叙事性阐释。在这个意义上,怀特的历史批评代表了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向历史研究领域的移植。其次,怀特看到了情节编排的意识形态维度,其对世界的描述,无论是分析、叙述、解释还是阐释,都必定带有伦理的、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含义,而且,这一洞见在怀特这里已经与对叙事和修辞技巧的分析融合在了一起,并达到了一定的形式化和技术化,这对近年来的读者接受理论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发生了很大影响。最后,怀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涉及如何捕捉过去的问题,这也是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热切关怀。当然,怀特探讨的主要是历史话语,提倡诉诸历史意识,重建历史与伟大的诗歌、科学和哲学关怀的联系,同时也注重借鉴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洞见。这不仅由于现代文学理论对于理解有关历史思想、研究和撰写的问题至关重要,还因为“现代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是出于理解文学现代主义,确定其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历史特殊性和意义,开展一种适于研究客体的批评实践的需要而被建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