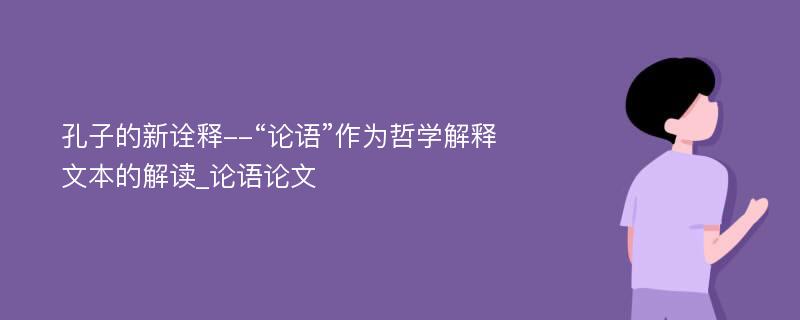
孔学新诠——对《论语》作为一个哲学解释学文本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论语论文,作为一个论文,文本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828(2006)01-0069-06
历代儒者对四书五经的读法,大体都遵循着一种深度模式的阅读理念,即热衷于探索、发掘圣人赋予经典字面内部的深层意蕴(古圣先王之道、圣人理法或微言大义),正所谓“儒生擿经,穷竟圣意”(《论衡·程材》)。对儒者来讲,其中的《论语》一书尤为“圣人言行之要”(《汉书·匡衡传》),更是一部“垂宪万世”的伟大经典著作。这无疑是基于一种神圣化的孔子观:孔子以“千古一人”的先知形象垂教万世,而后人则能够一劳永逸地只是就自己时代的问题到孔子那里寻求现成的答案。在与古人对话之前,这是我们首先必须破除的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幻想。
为了破除上述幻想的执迷,对《论语》采取一种伽达默尔式的读法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想尝试与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思想的孔子,而不是作为圣人的孔子,进行全面充分的精神遭遇和灵魂的对话,以期达到某种“视界的融合”,那么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解释学便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论语》的极富启示意义的读法。作为一个哲学解释学的文本,《论语》只是被视为一个能指的言语符号系统,而孔子作为一个努力使思想与存在打成一片的行动者,即作为一个对人的信念与其存在在一种动态的人的能动生成过程中融为一体的典范,他的整个人生实践本身作为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回应,应该而且能够给我们提供某种典范的启示性意义。
然而,与古人灵魂的对话,无疑是一种思想的探险。这一探险并非是随意的,因为对话必须是开放性的,而且它理应“是对那种将我们引向某一既定主题的探索”[1]。对笔者而言,对话绝不意味着旨在寻找某种古人能为我们已指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而重要的是在一个思想自由、价值多元的世界里,尽可能地尝试开启解决我们自己时代问题的各种可能的有益路向。孔子遭遇到的是一个对神的信仰已趋于衰微而圣人又不得而见的世俗化的生存状况,同样,我们面临的大体也是这样一种颇为类似的生存境遇。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基于这样同一种生存主题来与孔夫子展开对话,即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神启的力量已然失效而又遭文化英雄(圣王)遗弃的时代,我们的问题是由我们自身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唯有立足于我们自身的人为努力才能解决我们时代面对的人类生存困境,不管成败如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一、解释学情境
神圣传统的解体,造成了生存意义的失落与文化认同危机的时代性生存焦虑感,这使现实世界处在一种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传统符号世界的崩颓使人们受着虚无主义的诱惑。伴随科技文明的凯歌行进而生的是个人的无能感。这就是20世纪的敏感思想家们所指出的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
正是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可以与身处社会大动荡时代的孔子产生某种内在的共鸣。孔子同样面临着旧有的价值符号世界的崩颓。是建立一个新的价值符号世界,还是复兴一个旧的价值符号世界,面对这一时代的挑战,每个人都应给出各自的回应。这不仅需要理论的反思,而且更直接关涉着人们无可逃避的现实生存抉择,每个人在这样一种抉择中都应担负起个体生存的责任。孔子为此刻意高扬个体主义的道德人文理想的呼声,一生穷途奔波,满怀将世界时世的命运忧患放于双手之间的激情,却屡遭困厄及当权者的冷落和世人讥刺,而受着无奈的自我精神流放。
人只能活一次,孔子及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业的严肃性足以要求我们直观地想象这个情景,仿佛你是他的同时代的人,而把他看成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人。
因此,如果我们试图与孔子达成哲学解释学的“视界的融合”,重要的不应是看作为圣人的孔子说了些什么,并对人所共知的内容作一种简单的解释,而必须把孔子作为一个身处具体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处境中的人,即生活于有哭有笑、行动、希望、恐惧的人群和先秦“对话”的时代情景之中的思想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使文本即《论语》“作者的说法重新回到生活中去”[2],而且我们必须尝试“理解我们从中看到的我们自己的问题的那些叙述”[3]。
毫无疑问,面对现代化的课题,对传统儒学内在意义的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转化的热切探寻,即如何切近孔子、儒学,这不仅仅是纯学理的事务,而更应是内在于我们的直接生存问题的挑战。这就是我们解读《论语》的解释学情境。
二、天命与行动的介入
孔子本人除了被神化外,自始至终便被作为人文教之父为中国人所敬仰和推崇。然而,在世俗生活中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超越和寻求现实人生的崇高感,却正是自孔子始。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避而不谈天道性命,更不语怪力乱神,这无疑是对神学信仰问题采取了一种存而不论的悬置态度。不过,面对天命,孔子却又心存敬畏,正是在这里隐含着常被人忽略的孔子的世界观。
为了真切地理解、把握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简略地考察反省一下先秦时代的上帝神学观。如所周知,帝或上帝乃殷商人的至上神,为商人生活上或生产上的主宰,上帝赐风雨、降祸福以示恩威,但似乎缺乏对人的行为道德的规范性,正如《尚书·西伯戡黎》所示,当祖伊谏阻商纣王的荒淫时,纣王却有恃无恐地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而周人对“天”的信仰虽然秉承自商人的上帝信仰,却作了重要的修正,较之殷商的帝,周人的“天”奖善惩恶,赐人以祸福乃是出于道德义理化的正义观,故天命惟德是授。
在孔子那里,“天”的含义则颇多歧义,孔子表现出了明显的踌躇不决。孔子所谓的“天”有时指自然之天,有时指世界的精神原则,天无所命令而又能生成万物。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天的生成义似乎又不具有纯粹的道德的意味,即在道德规范的意义上,天又似乎显示了一种“为所欲为”的主宰品格,子曰: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①)
“天生德于予!”(《述而》)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由上所见,孔子的“天”显然深藏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天是不可欺诬的,而天之于人类生存意义的关切,既含有道德的意义,而又与人德缺乏必然的正相关性。正如《荀子·宥坐》所载,子路问:“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的回答是:“遇不遇时也……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显然,子路的问题非常尖锐地质疑了天的道德正义性,而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子路的问题,似乎在有意回避而不愿深究天的意志是否具有道德的正义性。但综观孔子的整体言行,这一问题却始终在困扰着他,而且正是这一问题构造了孔子整个人生的生存性悖论,其以德拯世的神圣使命感既来自对天与天命的意志力量的深刻洞见。反之,这一洞见却又终究无法使他摆脱“道之不行”的困忧而达成以德拯世意愿,而在这一生存性悖论境遇之下,孔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不怨天不尤人、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生存勇气和刻意行动来介入改造现实世界的人生道路。
因此,天命之于孔子,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消极的否定力量或单纯的积极的肯定力量,毋宁说是一种成就君子之德之行的极具张力的构造性力量:一方面,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显然,对孔子而言,君子之所深存敬畏者,乃在于天命与大人和圣人之言共同赋予君子的德行以一种统摄性的驱动力,同时三者亦构成了作为自我实现者的君子的德行的限界。另一方面,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知命”作为成为君子的前提,旨在唤醒君子作为一个现世的行动者的天职观:行动即对世界的道德介入乃是生命内在的绝对命令。故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又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虽然“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然而对天、命的洞达导致的并非是对救世行动的放弃,恰恰相反,它却激起了孔子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的仁道自觉。
可以说,孔子正是以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整个人生实践证实了其“天生德于予”的自信,这种自信张扬了一个人个体生命价值的极至正在于他以完全不顾个人得失成败的存在勇气而向世人所作的刻意入世的道德宣示。尽管孔子并没有真正实现他救世的道德理想,然而,他作为一个以其道德理想刻意介入改造世界的行动者,无疑已永久地成为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无法回避而又令人不安的难题,搅动人的灵魂不得不面对道德的力量进行个人的决断。总之,天命既可以使人绝望而放弃自为的意志,也可能激起人们作一种注定“无望”的行动努力的悲壮性热忱。孔子的天命观正属于后者,这使他在以刻意的行动介入到当下的实现生活之中的同时,试图建构的正是一种由伦理的“应然”所主宰的人文世界,并将传统对神的信仰抛在了身后。
三、自治的伦理
孔子搁置了信仰问题,其天命观也并不具有神学的意味。因此,他便试图从理论上建构一个人文的世界,并不得不以“温良恭俭让”的人文教育与世人周旋到底。
在自治伦理的人文世界,人性不再是神的衍生物,而是为自身理由而存在的自足存在物,人成为自身的真正主人,从此建立一个真正的人道的世界便成为世人追求实现的社会理想,正是孔子开始将人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人的美德——道德的个人性自治、自律之上。故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无疑,人文的世界作为一个生命成为自觉的世界,其中人不再崇信神的意志的引导与诱惑,因为人不仅能而且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这一自觉来自人的道德理性,在道德的激励下,人应该自觉践行人道,从而实现为真正的人,并通过人际积极能动的互动使世界变成个人的或充分人性化的世界,这正是孔子的人文理想。
孔子罕言“性”,直接讲到人性问题的只是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从“性相近”这一人性命题,可以说已提示了孔子对人性肯定的基本信任态度,而正是基于这一对人性的积极的基本信任态度,孔子明确提出了一种人本主义的理论假设:人类社会生活理应朝着人类道德自我完善的目标这一确定的方向(“仁”)前进,如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洲》)“习相远”命题的意义则在于说明了,现实人生迥然相异乃是由后天的社会生存环境造成的。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所以,道德人格的成长需要人择善而处,入人之国亦应访贤问仁。如子贡问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
孔子蔑视蝇营狗苟的人生追求及对外在功名利禄的占有欲,然并不蔑弃人生的价值,而是更关注于奠基在对人的内心世界或内在精神需求或道德理性的开发之上的人类的福祉,以此来重整人类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秩序。因此,我们不能用宋儒所谓“减”的工夫去理解孔子所讲的克己、修己与内自省等,实际上孔子坚持的是这样一种的人类观:每个个体只会面临一股强烈的道德(抉择)的力量;人的真实存在于人的关系之中;人生的价值被视之为人之道德品格在各种可能的社会伦理政治关系中的充分展示和实现。
从孔子的上述人类观来看,“政”在承担人道之播化上的核心地位,以及一种积极建设性的人际互动关系(忠恕之道)之于人的成长,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终极的意义上,个人最终只能是自我实现者,即自我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最终只能是个人的事务,社会的完善也最终取决于每个个体都能自觉地践行人道而自我实现。因此,社会伦理政治关系中的互动是有限度的,它的原则便是“不可则止”。正是在这里,对于社会权威、政治权力,孔子只是希望其能够受到自我实现的规范(“正名”的意义也不过在此),这也正是孔子的局限性所在。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评:“他(孔子)的局限性在于:面对邪恶和失败,他只是庄严地悲叹和忍受,而没有从痛苦的深渊中得到任何促动力。这一局限性说明了他为什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3]
总之,在孔子建构的人文世界中,个体的人必须受到道德自我完善或(人之为人)实现愿望的引导,任何人都不应例外,无论你身居高位、手握重权,还是身居陋巷、位处卑贱。而所谓只有仁人才能真正地爱或恨,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好恶情感的单纯表达,因为对孔子来讲,爱与恨的情感表达是基于对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的期望和人格成长的理性要求之上的,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一个真正的仁者,必须在立人与达人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自我实现与成就他人又是融为一体的。基于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孔门之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之义,孝悌之义虽不排斥但绝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特殊的私人情感的表达。对孔子而言,家庭伦理毋宁说更主要的是指这样一种道德理性,即基于亲情关系之上的家人相互之间的对彼此道德人格的尊重与完善的深切关怀,唯其如此,而且人们能够将此情感此理性扩展及于他人与社会,家庭伦理才能真正构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状况与良好秩序的根基。
四、对话:道德实践的具体化
孔子所提出的自我实现的人性化的命题并不是一句空话,它的根本实践特征便在于“仁”的具体化,从这一意义上讲,孔子的整个人生实践并非是完全失败的,他获得了私学的巨大成功,这在根本上又取决于他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贯穿了“仁”的实践的具体化原则。据《中庸》,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毫无疑问,“道问学”对孔子来讲具有特殊的意义,“问学”对一个人的成长是不可缺少的,孔子本人便是一个“每事问”,且自以为“好学”的典范。从孔子的教学活动中,我们正可以具体形象地体会“问学”及贯彻其中的道德实践的具体化之于人的成长的意义是怎样受到最深切的关注的。
众所周知,孔子兴办私学的目的与宗旨正是为了培养“人”,不仅是为了培养能够治理国家的智能之士,而且在最终的意义上是为了培养一种自我主导性的、能够自觉参与创造社会和谐与秩序生活的新人——社会的新生的主体,孔子的这一教育理念乃是基于一种整体人的观念:即人作为一种道德的存在在介入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时,个人“道德自我”或“人之为人”的自我实现具有“统合”的主体功能,即以道德自我统摄各种社会政治——伦理文化活动。因此,孔子私学最突出、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其教学活动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是融贯而打成一片的。教与学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具有一定时限的过程或现象,而是贯穿一个人终生的志业,是与一个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处境中不间断地人生经验、行动、自我实现密不可分的一种全身心地投入。
因此,在孔子的教学活动中,孔子自身人格的启示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对话体的《论语》,我们可以深刻体认到的是,由问答即具体对话而展开的对生存问题的深入探索,正基于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无可逃避的生存抉择问题。人生的问题是不可能一次性解决的,也不可能靠整齐划一的教导使弟子获得一致的介入社会生存的方式。在孔门师徒的对话交流中,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而进行随机、个别的面对面交谈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对话——一种积极建设性的互动关系,对于普遍原则的具体化及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从《论语》所见,弟子所问者有道、仁、礼、知、孝、政、干禄、学稼、君子、士、成人等不一而足。尤其是问仁,孔子对弟子的回答因人而异,且因不同的具体语境而有别。学者多因孔子对礼、仁的强调,而断言其思想核心为仁或礼,然而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贯穿于仁、礼思想之中的是具体化原则。如果我们可以对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作如是理解的话,即如为伽达默尔所引用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的“规则的合理运用是无规则可循的”[4],那么,可以说,对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既不是仁,也不是礼,而是抽象道德的具体化实践原则,即个体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践行抽象的普遍道德原则。也就是说,道德之于个体生存的呈现是一个能动的具体的生成或实现过程。
孔子本人强烈、鲜明的个性特征便是因人因事而异。他将这一个性贯彻于教学活动中便是“因材施教”。因此,在孔门教学活动中,人格评价与情感的介入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得到了充分的鼓励与实现,这塑造了一个松散而亲密的教学群体。如《先进》曰:“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所乐者乃“乐各尽其性”。孔子这种“乐”的态度无疑隐含着这样一个关于人格成长的教学原则的假设:积极建设性的个性特征的尽情发挥,是人们在“当仁不让”的对话关系中携手走向普遍人性的基石。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子路》)曾子亦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当我们理解了孔子尽心于道德原则的实践具体化的不懈努力,才能认识到,孔子对后世的真正启示性力量应该在于:为了人的成长,必须营造一种能动的共同参与共同体生活塑造的活的精神性气氛,即建立一种真诚的对话关系,从而才能使道德理想——正确的善的生活方式得以具体化地实现!这才是孔子实践哲学(道德理性)的本质特征所在。
五、述而不作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这一作为传统的叙述者的角色自觉,表达了孔子本人的一种深刻的文化使命感。叙述是针对时人面临的生存问题之挑战的一项伟大事业,这曾被人称之为“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即将孔子视为他那个时代的一位承上启下的文化英雄。无疑,这是将孔子置于了世纪的转折点上,这一角色期待也就成为后世“托孔改制”的活的内在资源。
孔子本人曾给历史叙事或传统注入一种道德的意义,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孟子亦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历史叙事或传统所具有的道德意义,显然在理想的正名意义上对世人构成了一种“人之为人”的教化作用。正是基于“人之为人”的规范意义或教化作用,孔子亦特别关注于对传统之“礼”的“损益”。而孔子所以特别推崇周礼,乃是因为他认为经由对夏、殷二代之礼的损益,周礼更完备而趋于“文”化即人道化。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所谓“文”,其动词义即使人“成人”(成为一个社会化的人)的“文之以礼乐”(《宪问》)之“文”。“礼”赋予人们的生活实践以某种秩序化的形式,从礼的社会化的规范意义而言,礼之为礼的理想意义即在于它能够为人之为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生活的有序化提供一种善的正确的生活形式。
但是,“事情不可能通过直接恢复得到解决”[5],这对于孔子也是适用的。从孔子的损益观我们知道,尽管孔子没有“视界融合”的观念,他却明确揭示了传统之于“人之为人”的实现所具有的规范教化意义,及其能够提供某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形式的中介意蕴。正如哲学解释学对我们所启示的:与传统建立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规范性观念是确定无疑和不可改变的,并将超越出任何批评;相反,“社会生活就是由某种对以前一直坚持为有效的东西加以不断改变的过程构成的”[6]。可以说,既“述而不作”,而又坚持礼的损益观,并积极投身于对社会共同体富有人道意义的秩序与和谐的生活形式的塑造,这正是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之道的核心理念之一。
传统的中介意蕴是在与古人的灵魂进行精神对话中(所谓“梦周公”)加以体认的,这在自我实现的意义上,毋宁说是一种与内在自我的对话。传统并不是神圣的强制性的权力之源,它的中介意义以人的自觉的自我实现为限界。因此,孔子本人在从神本向人本的文化转型中,自觉地承担了以传统为中介而重整世界秩序的文化使命,正是这一自觉使他从一个旧时代的拥护者而翻身成为了开启新时代的伟大哲人,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反思过去会改变对过去的看法。把传统的思想、习惯变成自觉原则将导致与古文化相一致的新哲学的产生。”[7] 孔子对传统的自觉反思与辩护,既维持或拓展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生命力,同时亦激发了战国诸子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刻批判。就人自身价值的实现而言,文化传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教养的根基,无论是对它的自觉辩护,还是对它的批判反思,只要有利于人自身价值的实现,都是有益的。相反,那种对文化传统的简单肯定与简单否定的态度,才是真正亵渎文化传统的行为。对自我实现者来说,传统不必是异己、陌生的力量,但将传统教条化却无疑会阻碍人自身潜能与价值的拓展与实现。
六、小结
孔子可以说建构了一个为自我实现愿望所引导的人文化的理念世界,它是与受利欲支配的世态对峙而立的,如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孔子尽管没有明确的“恶无限”的观念——“恶无限意味着终点不断地推迟到来”[8],然而,对君子、小人的辨析显然暗示着:无所忌惮的小人与自我实现的君子的永恒对抗,致使人人充分人性化的世界被无限期地推迟到来。
不过,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孔子所倡导的人人应充分实现其自身道德价值的人性化理想,对我们现时代的人仍然有其启示性的意义。当面对现代技术文明所导致的物的异化的世界,人本主义思想家们呼唤听从人性自身内在的要求的时候。笔者相信,孔子人性化的道德理想及其道德实践的具体化原则,也将在新的现代化课题的生存境遇下仍然规定着我们生存实践的问题,也只有在一种对话——实践的具体化情境中我们才能触摸到自己的真实的存在。正是在这样一种有限的意义上,笔者才尝试将《论语》作为一个哲学解释学的文本予以解读。本文的命意既然在此,亦同样蕴涵着另外一层意思,即笔者决意要拒斥的是那种漫无节制的陈词滥调及立意煽情而蛊惑人心的本质主义的孔圣观,以为只靠盲目地尊孔读经、只靠盲目地迷信圣人的教条,一劳永逸地占有它,我们便可以固守住我们那僵化(不可改变)的所谓“文化自性”。对于时中的孔子来讲,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庸人自扰,更是一种真正的渎圣行为,吾宁信雅斯贝尔斯之言:“我们必须自我决定,进行推论,否则,一切都将存在于假象中。”[9]
更进一步地讲,依笔者之见,从文化建设的意义上而言,我们实有必要厘清孔学两个层面的意涵或区分两个不同的孔子:一个是遵循着传统的教诲(礼教传统下的生活形式)的保守的孔子,一个是立足于观念更新(仁学)而通过主体的改造(君子之道)以实现社会变革的激进的孔子。这两个孔子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而不同的影响,更对我们当代的文化建设事业有着各不相同的意义。孔子之为孔子,不仅通过对自身文明的演进史的批评的系统反思与自觉诠释,而培育了我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意识,而且,其关注于现实人生、伦理与政治问题的实践智慧,与其说彰显了“实用理性”这一“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毋宁说开显了一种以文明教养为核心的人文理念。正是在这一人文理念的自觉意识的根基之上,孔子主要从两个方面积极地思考和应对他所面对的时代性的人类生存困境与社会政治难题。
面对周天子权威的失落、周代礼乐制度的僵化与失效和天下秩序的崩坏与解体,孔子一方面致力于周代文化传统与礼乐制度的因革传承,这主要体现了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另一方面,孔子则努力探索重整、建构世界秩序的主体改造的行动方案,而致力于人文价值与生活理念的重新抉择与定位,以便为现实社会的变革注入新的主体性的活力因素,从而开创了一种以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与自治的伦理理念为根基的新的道德理想与人文精神,这主要体现了孔子思想的开新性。只有基于这样一种分疏与诠释,我们才能真正揭示清楚孔学在当代有可能推陈出新的意义境域。而这一分疏绝不意味着我们便可以据此而做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取舍,因为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自身时代的问题性,无论是从事制度的建设,还是进行观念的更新,如何回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是褊狭而抱残守缺地固守我们的所谓“文化自性”,还是在文化多元对话的语境中自觉地建构我们的文化未来,我们必须自我决定,进行推论。
注释:
①以下出自《论语》的引文只注篇名。
标签:论语论文; 孔子论文; 人生价值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解释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国学论文; 道德论文; 自我实现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