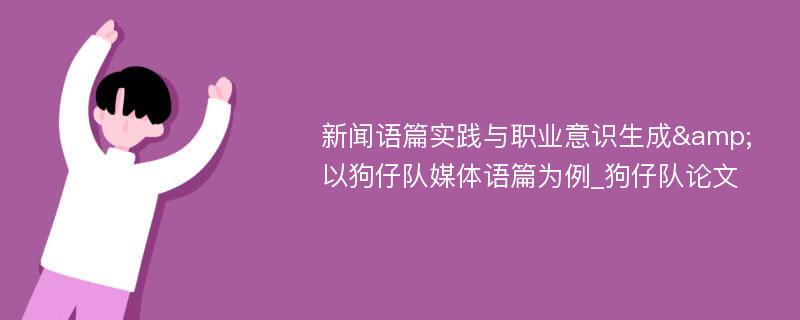
新闻业的话语实践与专业意识生产——以媒介有关狗仔队的话语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新闻业论文,为例论文,媒介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新闻生产者塑造成专业人士,是新闻业长久以来的努力。从成立专业协会到制订专业规范,从开展专业教育到从事专业研究,无不反映了拉森(Larson,1977)所谓的“专业工程”的建设任务。但是,专业形成不仅仅以这些物质工程为标志,从业者是否具有共同信仰或意识才是新闻专业真正成为共同体的表征,上述物质工程建设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发展专业共同意识。共同的专业意识,不仅是微观层面新闻生产得以按照常规进行的保障,从宏观层面来看,更是专业群体自我认同的标记,是公众认识、理解和支持新闻业的角色与功能的基础。
在吉登斯(1998)看来,行动者的意识,包括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是在社会生活的连续过程中,通过对其行为的反思性监控而获得的。简单地说,实践意识是无需多说、按照“惯例”“习俗”操作即可,而话语意识则是可以言说或需要言说的。当实践“常规化”,成为习俗、惯例之后,行动者很少反思,也无需讨论;只有习俗、惯例被打破,或者行动者力图合理化、合法化一种新的实践的时候,相关话语才会滋生。因此,在言说过程中,行动者也重新建构了有关自我的意识和认同。
不过,个体的意识如果没有互动与交流,也无法形成专业群体的共同意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翟利则(Zelizer,1993)把新闻专业视为“阐释性社区”——通过共享对现实的某种解释而组织起来的一群人。新闻从业者通过对共同历史的话语建构和协商而形成行为标准,而这个共同历史又随着对特定的关键事件的反复叙述而改变。引发叙述的关键事件,往往就是打破惯例的新的实践。因此,新闻专业意识又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随着新闻实践的一幕幕行动而开展,并在反复言说和交流中得以赋形。
对于新闻业来说,大量惯例与常规无需明言,或者未能明言,这对于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各国新闻业如此(Tuchman,1973; Eliasoph,1988),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业来说尤其如此,诸多日常工作依靠“临场发挥”(潘忠党,1997),而非成文法规;新闻专业主义呈现出碎片的、局域的特征(陆晔、潘忠党,2002)。不过,也正是因为缺乏严格规范,一些核心概念不断需要重申与强调,比如真实性、客观性等等,成为新闻从业者的“恒久话题”,尤其是在一些反思意识比较强烈的从业者当中,得以反复言说。这些言说不仅仅是完成、规范工作的需要,而且反映了新闻专业群体的自我意识,对内具有团结、凝聚的作用,对外则有建构形象、确立认同的功能(Schudson,2001)。
新闻专业意识的这些特点,要求我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在具体情境中,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反复言说的专业话语有哪些?反映了何种实践要求?获得专业群体的何种回应?对于既有专业意识有何作用?是维持还是更新了专业意识?国内新闻媒介有关狗仔队现象的讨论和批评,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下中国新闻业专业意识生产的具体过程和方式,分析、研究这些话语实践,对于理解和发展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自我意识呈现
2006年,一个“狗仔”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2006年的春天,是“狗仔之春”①。有诸多因素促使中国“狗仔”获得春天般的感觉,他们自己所属的群体——新闻圈——的部分认同应当是一个重要内容。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媒体,如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等都不约而同地刊发了有关国内“狗仔”的报道和评论。虽然仍有媒介对狗仔队持批评立场,或者有保留的接受,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正面或中立的意见、形象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有翻案的意图。
其实,狗仔队并非新事物。2003年7月诞生的娱乐刊物《BIGSTAR》被视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批“狗仔”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作为“狗仔”前身的八卦新闻记者则更早出现,有人将中国内地的“八卦元年”追溯至1997年②。这一年,“小燕子”赵薇成为八卦记者追逐的明星;同一年,英国戴安娜王妃遭遇车祸身亡,紧随其后的就是西方的“狗仔”——帕帕拉齐。如果说2006年是狗仔队的春天,毫无疑问,1997年则是狗仔队的寒冬。当时主流媒介对追逐戴安娜王妃的西方狗仔队进行了猛烈抨击,被斥为“西方媒体极度自由的怪胎”③。与此相对照的是,9年以后的2006年春天,当香港影星黎明被狗仔队偷拍、香港艺人群起而攻之之际,大陆却有媒体评论“狗仔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④,“狗仔无需被审判”⑤,同时,内地一些“狗仔”也纷纷在传媒亮明身份、抛出内幕。
中国新闻业有关狗仔队话语的变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狗仔队是否真有春天?或者说:“狗仔”春天般的感觉是否反映了他们在中国新闻业版图上地位的变迁?如果说过去的狗仔队是新闻业边缘的异类,那么,他们现在是否占据了更为有利的地位?这样的问题也许很难做出客观的、实证的回答,因为与其说“春天”的表白是一种描述,不如说是话语策略,它表达了部分新闻从业者(不仅仅包括自称的“狗仔”)重新确立自己专业身份的要求。而且,这种局部的言说必定具有整体的效果,它将或多或少地对整个新闻业的专业意识(专业版图)产生影响。
对于批评者来说,狗仔队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不真实,经常被批评为捕风捉影、随意炒作。但是,在近期一些有关“狗仔”的新闻话语中,真实性、客观性却反过来成为“狗仔”去“妖魔化”的重要依据。化名张楚寒的“狗仔”认为:“……这是种比较客观的报道形式,强调现场感,强调调查。现在社会上是把‘狗仔队’妖魔化了,它其实就是一种正常的报道形式。”⑥
狗仔队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于明星日常生活的干扰和隐私权的侵犯。而在有关“狗仔”的新闻话语中,这种侵犯行为却与新闻专业另一个核心理念——责任——联系在一起:监督不良行为、满足受众知情权。在一些报纸评论当中被表述为“知情权大于隐私权”、隐私权不能成为“公众人物藏污纳垢的保护伞”⑦。“监督”成为体现专业逻辑的第二个关键词。
专业逻辑的第三个被征用的核心概念是新闻价值。在《实话实说》节目现场,卓伟面对王小鱼偷拍的照片即毫不犹豫地表示:“这个照片它本身的新闻性大过了它的艺术性。这个照片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但是它有新闻的价值,它的新闻价值就在于它是第一次拍到王菲跟李亚鹏在一起的照片。证实了王菲跟李亚鹏两个人确实在谈恋爱。”⑧
真实、监督、新闻价值,这些都是新闻专业的核心理念,也是新闻从业者认同的标签。当“狗仔”们将这些标签贴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其意图有目共睹:他们力图使用这些符号资源进行重新归类,表明“娱记”也是记者,“狗仔”也是新闻人。很难说“真正”的新闻人没有识破“狗仔”的形象建构策略。确切地说,应当是各种主流、非主流媒介帮助他们从事建构事业,这不仅仅体现在为其提供话语空间和渠道上,而且,在新闻媒介上以各种身份发言的其他社会角色也共同参与了这一事业。在有关狗仔队的话语中,真实、监督、新闻价值、职业道德这些重要观念得以重申,这对于言说者来说,不能不说也具有自我认同的作用。
二、媒介话语实践与新闻专业身份建构
有关狗仔队的话语实践,消解了一些传统二元对立,而代之以新的二分法,从而重新确立新闻业的版图与边界。1997年在对西方新闻媒介的批评之中,言说者树立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从而从反面表达了“我们”的新闻观。有意思的是,在2006年“狗仔”内己的言说中,也会经常与香港狗仔队进行对比,强调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不过此时香港“狗仔”已不是西方记者的同义词,恰恰相反,香港“狗仔”背离了新闻记者的基本要求:他们“只拍照不写稿,虚假失实问题严重”⑨。
在商业逻辑中,上述对立却被取消了。根据1997年《人民日报》的批评,杀害戴安娜的罪魁祸首就是“西方新闻媒介残酷无情的竞争和新闻记者对于金钱的疯狂追逐”⑩。但在2006年关于狗仔队的媒介话语中,却出现了不少以商业逻辑为狗仔队的存在进行辩护的观点。《南方人物周刊》在一篇文章当中深入描述了“狗仔”的“供求链”:媒介需要提供受众市场规模——明星需要借助媒介提高知名度和市场价值——阅读明星隐私是人类基本欲望⑾。
西方小报唯利是图的工作逻辑和品位低下的新闻内容,一直是大报记者口诛笔伐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业者自我崇高化的意图(Bird,1990)。也就是说,西方新闻从业者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二元对立来进行专业意识的建构。然而,在2006年的春天,这种传统的建构被有关狗仔队的媒介话语部分地消解了。“狗仔”的工作方式(偷拍)不仅为主流从业者常规使用,他们的工作理念也符合专业规范;“狗仔”的商业逻辑不仅深受看客、明星的欢迎,而且也并非小报的专利,为各类媒介所普遍采用。
当“狗仔精神”成为一个褒义词时,言说者“正名”的努力就达到了。正如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揭丑记者扣之以“扒粪者”的污名。却被“改革者视为一枚光荣的勋章而欣然接受”(埃默里等,2001)。批评者把狗仔队与“扒粪者”相提并论⑿,岂不正中“狗仔”下怀?重新洗牌、重新归类,这是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对于更多的媒介言说者来说,亦是如此,不过他们的话语表达没有如此清晰,只是正面阐述“狗仔精神”,而不贸然树起对立面。模糊既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也是建构过程中的必然——这种身份和意识对于言说者自己来说也正在通过话语实践而努力使得这些意识清晰并获得更大的认同。
三、新闻专业意识建构的意义与缺憾
“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成为什么,取决于我们所能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流心,2005)。
在2006年的春天,新闻媒介让“狗仔”们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讲述了各种关于“狗仔”的故事。在故事讲述过程中,讲述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与“狗仔”的认同。虽然没有一家媒介胆敢宣称“狗仔是属于我们的”,但是,种种话语策略表明:这是我们的狗仔队!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关系结构,甚至可以说:我们都需要有“狗仔”精神!
从新闻专业意识建构的角度来看,有关“狗仔”的话语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打破了原有的一些二元对立,也重申了一些价值规范,对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自身发展和谋求媒介贡献于社会进步,都不无裨益。然而,这种话语建构同时又是脆弱的。新闻媒介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多种话语在竞争人们的注意力、篡夺话语意义。而且,还有来自大众传媒以外的话语,以及来自话语以外的力量,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专业意识的建构。
另外,这种话语建构也可能是危险的,一些符号资源的挪用、关系的重组,一些话语逻辑的征用,都有可能将这些符号和逻辑中原有的负面要素带入专业意识与专业形象之中。而且,由于这种话语实践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也就极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反弹。
在考察当代中国个体的自我呈现与自我建构时,人类学者流心(2005)发现,个人难于以连贯的方式表述个人自己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他将这一现象称为“自我的他性”。专业意识的建构既是个体从业者自我意识的建构,也是作为共同体的“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在讲述狗仔队故事的时候,讲述者能将自我与“我们自己”连贯地加以表述吗?也许,正如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主持人阿丘所说: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对自身的这种需求自己有时也是糊涂的,整个状态就是,媒体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媒体,受众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受众,这样模糊的状态。”⒀
要走出模糊,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更开放的讨论和更丰富的媒介话语。
注释:
①⑾《供求链上的“狗仔”》,《人物周刊》2006年6月1日。
② 《“帕帕垃圾”来了》,《南方周末》2006年3月2日。
③ 《“西方媒体极度自由”的怪胎 “帕帕拉齐”行为恶劣》,《文汇报》1997年9月2日。
④ 《黎明—你的觉悟太低了》,《东南快报》2006年4月3日。
⑤ 《狗仔的伦理学问题》,《新京报》2006年3月30日。
⑥⑨ 《怎么证明公众反感狗仔队?》,《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6月1日。
⑦ 《隐私权不是保护伞》,《新京报》2006年3月29日。
⑧ 《你到我身边(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2006年3月27日。
⑩ 《残酷的“自由”》,《人民日报》1997年9月4日。
⑿ 比如,《人民日报》2004年4月2日刊发的新华社文章《中国记协自律维权委员会呼吁新闻媒体:抵制低俗之风提高娱乐报道品格格调》。
⒀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2006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