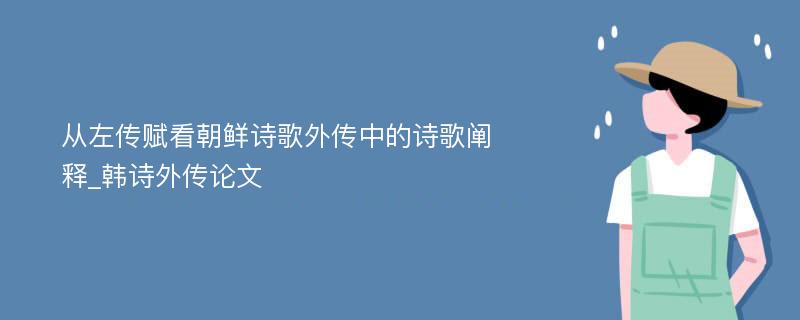
从《左传》赋诗看《韩诗外传》解诗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外传论文,解诗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0)04-0192-05
《韩诗外传》是汉代重要的今文经学著作,它以故事为主要内容,辅以议论、杂说,大部分篇章以“故事+诗经诗句”的结构模式出现。对于《韩诗外传》中出现的《诗经》诗句,学界意见不一,有用诗说、解诗说、用诗解诗两可的调和论。
综观用诗说和解诗说,研究者一般多从《韩诗外传》的内部文本入手,考察诗句与文章主体的关系。独立地考察《韩诗外传》一书中的篇章,虽可知其大致面貌,甚至有利于对叙事与诗句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因缺乏对《诗》学传统的历时性考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治丝益棼。
用诗之风源起于周,兴盛于春秋,至今可见的先秦文本中,《左传》以其所记载的赋诗数量多、真实可信,成为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更重要的是,《左传》中赋诗的用诗性质,学界并无异议,因而可以把它当作用诗的标准。对《左传》与《韩诗外传》中相同诗句出现的篇章加以统计,作两书之间诗句与篇章关系性质的比较,可以廓清《韩诗外传》解诗、用诗之惑。
一
据统计,《左传》记载赋诗共58首69次[1]。关于《左传》赋诗之法,《左传》中就有很明确的说明,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2]1145定公九年有君子之言:“《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2]1572可见《左传》赋诗之法是赋诗者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意义,赋《诗经》中某篇或诗篇中的某些章,诗句中所含字句或意义与赋诗者在当时情境中所要表达的情志相合。《左传》赋诗只出现诗题,具体诗句并不出现,至多只提到章数,如《左传》文公七年:“荀林父……为赋《板》之三章。”其余未提及具体章数的,则多取首章之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赋六月”一句杜预注:“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其全称诗篇者,多取首章之义,他皆仿此。”[3]321
《左传》赋诗模式大致相同,即赋诗者在具体、真实的事件中因情境与诗义的某一点相遇合,受到激发而即席赋诗,以诗言志。如襄公十四年: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2]1008
诸侯之师不渡泾水,叔向请示叔孙豹如何应对,叔孙豹赋《匏有苦叶》。《诗经·邶风·匏有苦叶》首章如下: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诗原义指葫芦成熟之际,可作腰舟,渡河时水深则脱下衣裳,水浅则提起衣裳。而《左传》赋诗之义却非如此,《国语·鲁语》下:“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参考《左传》原文,可知叔孙豹赋诗意在表达一定渡河的决定。
以上是诗句在具体情境中,脱离原义,产生特定引申意义的例子。叔孙豹面对着军队渡河的抉择问题,而所赋之诗首章之义中含蕴着渡河时无论深浅,皆有对应之策。诗在具体事件中,被当时的情境激发出诗句潜在的意义或引申之义。诗句是事件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容,是典型的情境用诗之例。
《韩诗外传》卷一第二十一章中出现了相同的诗句:
楚白公之难,有仕之善者,辞其母将死君。其母曰:“弃母而死君,可乎?”曰:“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请往死之。”比至朝,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何不反也?”曰:“惧,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闻之,曰:“好义哉!必济矣夫。”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此之谓也。[4]73
《韩诗外传》中如果对“深则厉,浅则揭”加以经学阐释,则必然会出现以事释诗,从故事中推衍、引申出诗义中的儒家道义。从这则仕之善辞亲死君的故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经师对这句诗的理解与《左传》颇为相似,其引申义都是“必济”。不同的是,《韩诗外传》通过设置叙事情节对诗句意义作经学解释:其一,故事中仕之善既有母亲和仆人的劝阻,又有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但是仍决意就死,可见其舍生取义的坚定意志。其二,仕之善之死,是为成就君子之德,因而舍私济公,践行儒家忠君理念。结尾处诗句前有君子“必济矣夫”的评价,这实质上是经师假托君子之口,对叙事与诗句间的关联所作的意义过渡和解释。“必济”当然不是指涉水,而是引申为以死济义,即叙事中仕之善的高行义举。
另外,与《左传》相比,《韩诗外传》中诗句虽然与故事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篇章,但却并不包含在故事当中。诗句通过经学引申义与故事发生联系,二者各自独立而又意义紧密相关。整个事件情节是针对诗句经学意义而设置,着重强调经师理解的诗句意义。
比较《左传》与《韩诗外传》中相同诗句出现的形式及内涵,可以发现《左传》情境赋诗与《韩诗外传》设置故事情节解诗是两书中十分普遍的现象。再如两书都出现过的《卫风·淇奥》一诗。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使韩宣子至卫国聘问:
自齐聘于卫,卫侯享之。北宫文子赋《淇澳》,宣子赋《木瓜》。[2]1228
《淇奥》一诗首章如下: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这一章诗句以茂盛的绿竹起兴,描写一个有德君子的文采、进取、修行。《左传》中韩宣子作为当时诸侯霸主晋国的使者,到卫国聘问。卫国北宫文子在宴会上赋此诗,其意在于以诗中的有德君子譬喻韩宣子。诗句作为替代性话语向韩宣子传达了赞誉之意。诗句是这一事件情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事件情节的组成部分。《左传》此文当中,诗句是当时情境的一种言语表达工具,仍属于明显的用诗。
《淇奥》首章中的两句在《韩诗外传》中也有出现,即卷二第五章,其全文如下:
闵子骞始见于夫子,有菜色,后有刍豢之色。子贡问曰:“子始有菜色,令有刍豢之色,何也?”闵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门。夫子内切瑳以孝,外为之陈王法。心窃乐之。出见羽盖龙旂旃裘相随,心又乐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浸深,又赖二三子切磋而进之,内明于去就之义,出见羽盖龙旂旃裘相随,视之如坛土矣。是以有刍豢之色。”《诗》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4]127
这一章中,诗句与叙事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在原诗中,喻指君子的神采德行如同磨治过的骨器、玉器一般美好。《韩诗外传》中则两次出现“切磋”,六次出现“色”,着重强调闵子的不断进修以及进修前后在面色神采上的差异。叙事中“切瑳”一词两见且与诗句中字词相同,绝不是两者之间单纯的偶然巧合,而是经师借叙事对于诗句中字词的着意强化。因为诗句是固定不变的,而叙事却可以灵活多变,完全可以不用“切磋”二字,而是用含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变换句式等方法来表达相同的意思。比如在早于《韩诗外传》的战国子书《尸子》中,也记载了相同的故事,其全文如下:
闵子骞肥。子贡曰:“何肥也?”子骞曰:“吾出见其关车马则欲之,入闻先王之言则又思欲之。两心相与战,今先王之言胜,故肥。”[5]
这则故事应是闵子骞故事的原有形态,叙事中并无引诗,且《韩诗外传》中与诗句相应的“切磋”及“色”两词都没有出现,而是以“战”来表示内心的交攻过程,以“肥”来描写君子进修后的状态。
由此可知,《韩诗外传》中的这则故事,是经师为解说“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诗句而精心设置,有意在叙事中加入与诗句相对应的字、词,不仅使叙事与诗句有潜在的联系,更将之外化于语言。叙事中反复出现的重要词汇与诗句相呼应,突出了事件与诗句经学讲读之间的联系。可见这一故事正是儒家经师从经学角度理解诗句后,针对诗句所特意设置的叙事性解说。
《左传》与《韩诗外传》中两则相同诗句故事的篇章分析,反映出《左传》与《韩诗外传》中叙事与诗句关系的异同。相同之处在于,对诗句的理解以及诗句与叙事的联系都遵循与诗本义相关的原则。这种相关性比较宽泛,可以联系紧密,用其本义,也可以对个别字句加以引申,用其引申义或比喻义与叙事发生联系。不同之处在于,《韩诗外传》中的诗句意义与儒家学说紧密相关,经师精心设置叙事,在叙事中设置与诗句相应的儒家义理、字句,诗句与叙事相互独立,但意义关联紧密。《左传》对诗句的使用往往着眼于在事件情境中表情达意的实用功能,诗句承担着完成事件进展中传递信息的任务,并不注重诗句的儒学义理;诗句是故事情境的组成部分,包含在叙事当中。
二
《左传》情境赋诗往往只要求诗句与情境之间有松散的联系,这决定了赋诗必然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情境本身是事件自然发展的过程,现实情境激发赋诗者的内心情感,与以往积累的《诗经》诗句意义相遇合,从而出现赋诗言志这一行为。赋诗者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他对此情境的感触是独特的,不同赋诗者的诗歌素养也各不相同,因而,《左传》中经常有在同一情境中不同的赋诗者所赋之诗迥然不同的情况,这也是春秋时有“赋诗观志”之风的根本原因之一。如《左传·昭公十六年》: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齤善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2]1380
宣子请郑国六卿各自赋诗,认为在当时情境中各人所赋之诗,能够传达赋诗者的情志。子大叔赋《褰裳》,杜预注:“‘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尔不我思,岂无他人?’言宣子思已将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岂无他人?”其余五人,皆赋诗表达对宣子的赞美或追从之意。子齤所赋《野有蔓草》,取“邂逅相逢,适我愿兮”之义,表达自己与宣子相处的美好感受。子产赋《羔裘》,以赞美宣子。子游赋《风雨》,取“既见君子,云胡不夷”之义,表达子游见韩宣子的喜悦心情;《有女同车》取“洵美且都”之义,用以表达爱乐宣子之心;《萚兮》取“倡予和女”之义,言宣子倡,已将和从之。
以上所赋诗篇在这一事件中皆非诗本义,但是都与情境相遇合,激发出新的引申义,用以表达赋诗者的情志。同一情境中子齤等五人赋诗各不相同,但都表达了赞美及追从之义,可见《左传》用诗时可以只取诗中大致的情感基调,不必拘泥于字句。这体现出《左传》事件情境与诗歌之间连接纽带的松散和宽泛,可以在同一情境中用多首不同的诗歌来表达相似的情感,诗与情境是多对一的关系。诗歌既属于叙事中的一部分,又是对当时情境的阐发,是用诗的典范。
子产所赋《羔裘》一诗在《韩诗外传》中多次出现,共有六处之多,分别是卷二第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卷九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可以此为例,分析《左传》与《韩诗外传》中用诗与解诗的性质差异。
《羔裘》全诗如下: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这首诗共三章,每章四句。每章最后两句十分相似,都是对于君子的赞颂之词。上述《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赋《羔裘》一诗,《春秋左传注疏》杜预注:“取其‘彼己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彦兮’以美韩子。”[6]杨伯峻注:“诗有《羔裘》者三,《郑风》有《羔裘》,《唐风》、《桧风》亦各有《羔裘》。言《郑》之《羔裘》,所以别于《唐》、《桧》之《羔裘》。《羔裘》有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子产用以赞美韩起。”[3]1381全诗三章末句极为相似,则不必拘泥于赋诗取首章之说,因而杜注与杨注中以为三章皆用。子产在当时的情境中赋此诗,以诗中所赞美的忠贞、正直、美好的贵族来比喻韩起,传达自己对他的敬意和赞美,是典型的情境用诗。
再看《韩诗外传》中的《羔裘》一诗。卷二第十三章引《羔裘》整个首章:
崔杼弑庄公,合士大夫盟。……崔杼谓晏子曰:“子与我,吾将与子分国;子不与我,杀子。‘直兵将推之,曲兵将钧之’。吾愿子之图之也。”晏子曰:“吾闻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婴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钩之,婴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绥而乘。其仆驰。晏子抚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悬,安在疾驱。”安行成节,然后去之。《诗》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4]153
故事开头描述了一个紧张而血腥的场面,把主人公放置在生死抉择之中。晏子的言行表现出在生死存亡面前对德行的坚持,有儒家君子的风范,与诗句“舍命不渝”的本义相对应。叙事着眼于诗句本义基础上生发出的儒家经义,对诗本义与儒家经义均有兼顾,与诗句联系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有一段引诗,即《诗经·大雅·旱麓》:“莫莫葛藟,延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晏子以此诗表达自己坚持正道、不改其志的决心。这与《左传》用诗何其相似!它作为篇章中间出现的诗句,是故事的情节之一,不独立存在,并在叙事中起传情达意的作用。而这种引诗只是偶尔出现,并不是《韩诗外传》中诗句的主要形式。结尾处仍以诗句作结,也表明了两处诗句的不同性质,无法相互替代。用诗与解诗的同时出现,正反映出《韩诗外传》以解诗为主的性质。
《韩诗外传》卷二第十四章,卷九第十章、第十一章都以“邦之司直”结尾,篇章内容则以生动有趣的故事为主体,各章大致情节分别如下:石奢为人“公而好直”,任楚国司法官吏,其父杀人,石奢放父亲逃跑之后,以死殉法;景公因为看鸟的颜邓聚不小心让鸟逃走,暴怒之下要杀了他,晏子以陈述看鸟人陷景公于不义之罪巧谏,使景公恢复了理智;魏文侯向解狐询问西河守这一官职的合适人选,解狐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荆伯柳,不以私害公。三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德行高尚之人,身体力行孝、忠之道,不计私人利益,为国为君尽忠。这三个故事的情节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主人公却都是符合儒家标准的正直君子,其事迹与结尾所引《郑风·羔裘》诗句的儒家经学理解相吻合。
另有卷二第十五章和卷九第十二章以《郑风·羔裘》末章“彼其之子,邦之彦兮”结尾。前者描述蘧伯玉为人“外宽内直”,为父子君臣所喜爱,在宗亲与政治关系中深得人心。后者叙写看相人劝谏楚庄王,以自己看相的经验谈如何观友识贤,庄王因此称霸天下,其功在于此人。蘧伯玉和看相人的事迹说明,两人都是结尾诗句称颂的“邦之彦”,是儒家所推崇的睿智君子形象,叙事正与诗句的经学意义相对应。
判断两种事物的阐释与被阐释关系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观察两者之间单位数量的对比。即:被阐释者作为单一的对象出现,而阐释者则以群体的形式相对应,形成阐释意象群。如同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用的演绎法,一个定理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证明,而这多种方式,正是这一定理的具体展开形态。以此来分析两书,《左传》同一情境中用六首诗,正是以情境为中心的体现,这也与《左传》本身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文本性质相合。《韩诗外传》中则以六个故事对应同一诗篇,这是将诗句作为叙事解说对象,以叙事对诗句的经学意义进行演绎、阐发的结果。从逻辑思维方式来分析叙事与诗句的对应关系,可以确证,《韩诗外传》正是以解诗为目的的讲经叙事文本。
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韩诗外传》中叙事解诗中也存在另一种形式,即所叙之事相似而结尾所用诗句却不相同者,如卷九第十章及与之极为相似的卷八第二十七章晏子故事:
齐景公出弋昭花之池,颜邓聚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夫邓聚有死罪四,请数而诛之。”景公曰:“诺。”晏子曰:“邓聚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而杀人,是罪二也。使四国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罪三也。天子闻之,必将贬绌吾君,危其社稷,绝其宗庙,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当杀无赦。臣请加诛焉。”景公曰:“止。此亦吾过矣,愿夫子为寡人敬谢焉。”《诗》曰:“邦之司直。”[4]722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召左右枝解之。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其枝解人,不审从何枝始也?”景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诗》曰:“好是正直。”[4]736—737
同一主人公晏子,同样是巧谏君王,除了言语内容不一致外,情节基本一致,但是结尾所引诗句却不相同。同类叙事结尾所引诗句不同,这与《左传》中同一情境中以不同诗句来阐发情境的现象类似。这是否表明《韩诗外传》中诗句只是叙事随意加以援引,而不是经师精心设置叙事来解诗呢?
对比两章中结尾诗句可以发现,两者虽属于不同诗篇,但是“邦之司直”与“好是正直”的意义、内涵包括字词,都很相近。《诗经》当中有很多诗句意义相近或相同,对这些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诗句的经学理解自然也是相近的。经师在设置故事情节解释这些相近的诗句时,故事内涵要与诗句相对应,则故事之间必然意义相近甚而情节相同。这恰恰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经师以叙事解诗时思维、方式的一贯性。
对比《左传》与《韩诗外传》中叙事与诗句的关系,可以看出,《左传》中赋诗是叙事情节中的组成部分,起着传情达意的重要功能;在同一情境之下,可以出现多首表达意义相近的诗篇,形成对这一情境的多重阐发,证实了《左传》情境用诗的性质。《韩诗外传》中诗句独立于叙事而存在,经师精心设置叙事语言,与诗句字词相呼应。对同一诗句或相近诗句,设置多个相近故事进行多重叙事解说。通过对比,可以确证:《韩诗外传》正是以叙事解诗的讲经文本。
收稿日期:2010-0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