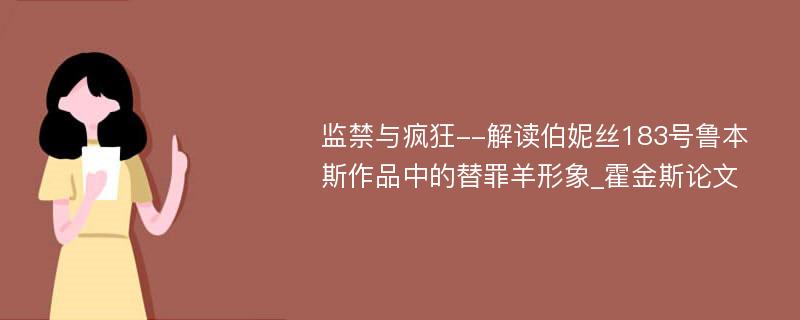
监禁与疯癫——解读伯尼斯#183;鲁本思作品中的替罪羊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替罪羊论文,形象论文,伯尼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英国犹太女作家伯尼斯·鲁本思(Bernice Rubens)(1928-)以其对英国犹太生活的真实描述以及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怀而声名鹊起。作为犹太作家,她作品中体现的不是狭隘的犹太性而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层关注。“对与我同时代的犹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存意识……我以犹太作家而闻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书写的都是生存”(Silver 48)。鲁本思侧重以“日常精神的普遍性”来体现“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Cheyette 37),因而她的作品充满着丰富的直觉感受,表达出本真的生存关怀。
鲁本思的两部代表性小说《入选者》与《五年刑期》中的主人公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替罪羊的位置,也正是其替罪羊身份决定了他们悲剧性的人生。从犹太教祭祀仪式意义上讲,替罪羊是“祭祀羔羊的名称,团体将自己的罪孽转嫁到替罪羊身上,由此去除罪孽”(Bronowski 7)。从社会意义上讲,替罪羊是被冤枉而为他人的过错承担责任的人,也就是吉拉尔所说的“一个受难者代替其他人受罪”(吉拉尔146)。一般来说,挑选牺牲品不是根据人们给他们的罪名,而是根据他们具有的受害者的标记。“替罪羊机制”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无意识地发挥着作用。鲁本思作品中的主人公即是不同背景下的替罪羊,替家人、替社会而受难,然而他们的生存境况却又是相同的,他们在受难中崩溃,在监禁下疯癫。
一、祭祀性替罪:献祭与救赎
1970年的布克奖得主《入选者》(The Elected Member)中的主人公诺曼·切克是祭祀仪式意义上的替罪羊。替罪羊主题源于《圣经·旧约》中亚伯拉罕献子以撒以示对上帝的忠诚,最后以公羊作为祭品的故事。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指出,替罪羊仪式早在人类远古时代就已流行,替罪羊的功能是带走邪恶与不幸,带来丰收与好运。在现代社会,替罪羊仪式在犹太教中盛行。埃里克·纽曼指出犹太人通过宗教仪式,“以庄重的方式把所有的不洁与邪恶堆积到替罪羊身上,将它放逐到荒野上,以实现集体的净化”(Neumann43),从而“替罪羊心理”帮助族人从“无意识的心理阴影”中摆脱出来(Neumann 47)。在“替罪羊”主题中,“羊”本身并没有过错,只是为了他人的愿望而被迫承担厄运。根据纽曼的观点,“杰出人物因其具有代表性的才能而获得资格,代表集体成为摆放到‘强权者’面前的祭品”(Neumann47)。既是犹太后代又是神童的诺曼无可非议地被选为替罪羊摆到了受难的祭台上,替犹太人、替自己家庭在夹缝中的痛苦存在而受难。小说一开始,鲁本思借用卡夫卡《变形记》里的幻觉模式,描述诺曼被幽禁在卧室里,感觉银鱼成群结队向他爬来,他惊恐万分。银鱼是一种无形力量的象征,正是这种力量在冥冥之中包围着诺曼并将他“挑选”为受难的替罪羊。诺曼的父母属于英国社会的第一代移民,他们生存状况堪忧,而且又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与异质社会的吸引之间找不到平衡点,因此他们身上存在着一种“既有归属又没有归属”的感觉,一种“监禁性精神分裂症”(Head 158)。这种焦虑被扭曲变形,通过犹太家庭权威的力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泄到下一代身上。他们既希望子女出人头地,改变家庭的处境,又不甘让他们脱离自己的控制,于是父辈的失败与痛苦转化成对其后代肆虐的期许和强行的管制。诺曼因其杰出而被挑选为家庭的替罪羊,为家庭的失败而受难,用他的痛苦来维持家人内心的平衡。诺曼从小颇具语言天赋,12岁时就精通数十种语言,母亲出于一种盲目的期许,向外界隐瞒了诺曼的真实年龄,谎称他只有10岁,以渲染“诺曼神话”,父亲的沉默纵容了母亲的气焰,迟来的成人礼却阻碍了诺曼正常的成长。诺曼长大以后,母亲为了长期控制儿子以维系自己一手打造的神话,千方百计阻止他出去独住,在她眼里,“诺曼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她的附属品”。①家庭的禁锢使诺曼原本健全的自我开始破碎,他不明白“当他身上所有的热情被耗尽,所剩的只是对那敲击在他头骨上的折磨的清醒认识,这种所谓的正常生活还有什么意义?”(175)绝望的诺曼走向了迷途:他对好友大卫萌生了爱恋之情;当大卫爱上了他的妹妹埃丝特之后,他鼓励妹妹与异教徒私奔,却不曾想促成了大卫的自杀。大卫的死带给诺曼更深的迷茫,与姐姐贝拉的乱伦只不过是他迷惘途中的又一次无效尝试。吸毒成了他最后的盾牌,毒品所代表的白色是投降与幻觉的色彩,诺曼终于彻底崩溃,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在家庭的禁锢中疯狂,又在疯狂中被送到了另一个监禁地。
愤怒的诺曼也曾质问过上帝,“难道你挑选我们来承担你的愤怒,你的嫉妒,你的期望,你的万能,你的仁慈与怜悯,你纯粹的残忍吗?”(273)但最终他只能无奈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当他无法承担身上的负担时,他不得不承认是他的家人把他推到了那里,“除了成为装载他们苦难的容器,我还能是什么?我只不过是他们身旁的过客,除此之外我还能是谁?除了包容悲哀与苦难,我还能过别的生活吗?”(273-4)小说的最后,银鱼的幻影再次出现在诺曼面前,这一次,他被征服了,“他惊恐万分地看着它们……生命中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了……他看着它们像朝圣者一样聚集到他脚下。如同他的父母和姐妹,它们也选择了他,他像个不情愿的门徒一般站在那里,充满了恐惧。突然,它们朝他袭来,他被淹没了”(239-40)。然而,作者在小说的结尾似乎又点燃了一丝希望。从宗教意义上来讲,“替罪羊”除了承载苦难,还暗含着“救赎”的希望,献祭替罪羊的目的就是获得宽恕与拯救。因此,“鲁本思构思替罪羊主题是为了用它全部的仪式含义来指涉对罪恶的救赎以及对未来的希望”(Head 159),小说以诺曼的祈祷而结束,但他的祈祷不是纯粹犹太宗教仪式上的祈祷,而是包含了多种手势,象征着文化融合的祈祷,“他得为自己祈祷。出于困惑,他必须祈祷,由于他继承了应许的言词,他必须祈祷”(274),不仅为自己,他还为那些与自己有着共同遭遇的人祈祷,“上帝,眷顾我们这些苍凉的入选者”(275)。诺曼最后的祈祷中隐藏着作家美好的希望,这希望“始自希伯来,却以一种包含多种信仰的手势而收尾,暗示了犹太身份的同化,这种同化不是指犹太性的消亡而是要将其稀释淡化”(Head159)。
二、机制性替罪:受过与毁灭
获1978年布克奖提名的《五年刑期》(A Five Year Sentence)没有继续犹太主题,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处于社会无形压力之下的女性个体,让女主人公成为机构性权力体制的牺牲品。小说中的霍金斯小姐是社会意义上的替罪羊,为他人和社会的过错承担责任,同时也是吉拉尔所说的“替罪羊机制”的牺牲品。“替罪羊机制”从根本意义和简单意义上来说指的是“在文化和社会中无意识发挥作用的替罪羊生成原则”(Williams 294),也就是“迫害行为与表征的无意识机制”(吉拉尔152)。替罪羊机制的无意识性使迫害者在一种混沌状态中实施迫害,他们虔诚地相信受害者有罪,“迫害者封闭在迫害表述的‘逻辑’中,他们再也无法越狱……社会集体限止受害者的自由,使他们无法替自己辩护”(吉拉尔50)。霍金斯受权力体制压迫,而替罪羊机制又让她无从申述,无法改变自己悲剧性的人生。
霍金斯具有替罪羊的某些标志,她是女性,是弱者,同时又是一个弃儿,“弃儿命中注定是要被逐出他的团体,弃儿永远无法改变命运,只有暂时被救,他的命运至多只能延续”(吉拉尔31)。作者赋予霍金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身份点明了她无根的存在状态,一个没有根源的个体更容易被权力掌控和管制,因而删除个体的根源就成为权力体系的一种控制策略。从孤儿院这个社会机器里学到的只是她“什么也不是的性质”②。她从未探询过自己的父母究竟是谁,一句简单的“我们从空无中得到你”让她陷入沉默,也将她推上替罪羊的祭坛。霍金斯的生活自出生起就处于社会机构体系的严密控制中,从孤儿院到工厂,她在一系列规训与惩戒中习惯了囚禁似的生活模式,也学会了服从。被压制的霍金斯在极度孤独中精神崩溃,错位的追寻显示了她内心的疯狂,也导致了她的毁灭。权力机制压制个体,规训个体,却不为自身的缺陷给个体带来的悲剧承担任何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霍金斯成为社会权力体制的替罪羊,她替权力体制给个体带来的灾难承担过错。霍金斯的存在揭露了权力体制的真实面目,它带给人的不是自由和幸福,而是孤独与毁灭。但权力体制不会承认自身的缺陷,受其摆布的大众群体也相信霍金斯的悲剧是她自身的过错,作为个体的霍金斯无法替自己辩护,只能替权力体制顶罪,用她的牺牲维系团体的平衡。
根据福柯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监狱领域’愈益远离严格意义的惩罚,愈益扩大,监狱的形式慢慢削弱乃至最终彻底消失”(福柯,《规训与惩罚》342),收容所,孤儿院,工厂,医院等都带有监狱制度的痕迹,最终“这张大‘监狱网’包容了遍及整个社会的所有规训机制”(福柯,《规训与惩罚》343)。于是,在社会这个大监狱里,服从成为霍金斯的天性,服刑则成为她基本的生存方式。小说中的孤儿院是一个功能性社会机构,它是社会这一庞大的机构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传输的是“强制服从”而非人道关怀。“在霍金斯小姐的一生中,都是别人对她发号施令,她则服从”,惯性使然,到后来她竟然觉得“执行命令给予她一种强烈的身体快感”(4)。从孤儿院出来以后,霍金斯一直在一家糖果厂(社会权力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工作。霍金斯奉献了大半生的辛勤劳作,却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与关怀,甚至没有人知道她的闺名,“霍金斯小姐”这一称呼作为一种语言权力把她与人类的亲近隔开。吉拉尔认为,“在替罪羊机制启动的沸点上,人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吉拉尔134)。在霍金斯的周围,人们无意识地疏远她,自发地将她“监禁”起来。孤儿院的舍监更是“替罪羊机制”里迫害者的代表,她受“迫害逻辑”影响,坚定地相信霍金斯不应该享有美好自由的生活。霍金斯本来极有希望被人收养,那是她奔向自由的唯一出路,然而舍监破坏了这一切,将她牢牢地囚禁起来。
退休之后的极度孤独逐渐唤醒了霍金斯尘封的自我,她开始小心翼翼地追寻那些失却在她生命里的体验。然而服刑已经成为她的生存状态,服从则是她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她的追寻也必须合乎这种习惯形式。于是工厂送给她的日记本成为她行动的合法性外壳,她把自己新的服刑期定为五年,每天在日记本上为第二天的行动设置命令,“被迫”完成相应的任务后再将其从日记上划掉,从中得到满足与快乐。在霍金斯尝试要走出社会牢笼的时候,布莱恩成为机构体系的帮凶,他用性服务骗走了霍金斯全部的积蓄,打破了她的梦想,毁掉了她残余的生命。然而,归根结底,毁灭霍金斯的还是“囚禁似的生存模式”——一种从社会机构的规训与惩罚中习得,并在个体身上固定下来的存在模式。“服刑”是霍金斯唯一知晓的生活方式,“服从”已成为她的天性,就算外在的桎梏已不存在,她也会设立一座心灵的监狱将自己囚禁其中,日记本便是“心灵监牢”的外化形式。日记本是“她的生命线,让一切成为可能”(44),对日记的过分依赖使那“绿色皮革的奴役”在她身上实施暴政,“她并不特别想嫁给布赖恩。她是嫁给她的日记,一个暴虐又愉悦的综合体”(159)。霍金斯明白自己的悲剧是由社会权力体制造成的,但她无法将机构体制的罪过公之于众,也无法获得补偿。她将怒火与仇恨集中到孤儿院的舍监身上,“‘希望舍监死掉……我希望她下地狱。我希望她身体的每一部分被慢慢烧毁。慢慢地燃烧,一直烧下去。杀死她,杀死她’”(142)。当她在养老院里不期然遇到了当年的舍监时,积蓄的怒火让她自然而然地勒死了舍监。然而霍金斯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由与毁灭同在,自由只是霍金斯永远无法获得的奢侈品。
三、替罪之生存:监禁与疯癫
《入选者》中的诺曼·切克同《五年刑期》中的霍金斯虽然个体境况不一样,但他们身上具有许多相似点,从他们身上也能折射出人类生存中的某些共性。二者都成为替罪羊,一个为家庭的失败而受难,另一个则成为权力体制下的牺牲品。诺曼的家人为让他们自己能获得内心的平衡而将诺曼推上替罪羊的席位,并将他从家庭的桎梏中转移到疯人院的囚禁下,诺曼的疯癫是他无力摆脱自己替罪羊身份的结果。霍金斯在社会大牢笼里孤独而悲惨地度过了一生,替罪羊机制让她无法与权力机构相抗衡,心灵的疯癫正是她抗争无果的下场。正是其替罪羊身份决定了他们悲剧性的人生,让他们在监禁之下受难而后疯癫。监禁是两位主人公身上共同的烙印:家庭的桎梏和社会人群的漠视是囚禁他们的无形外壳,社会机构则是监禁他们的具体形式。霍金斯自出生就被送进孤儿院,诺曼则在吸毒后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孤儿院和精神病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那里规训主导一切,服从必不可少,惩罚的阴影随时存在。隐藏在监禁中的规训与惩罚接替了自19世纪以来被废除的对肉体惩罚的公开展示,心灵折磨——“一种深深地刻在心上,思想上,意志与倾向中的惩罚”(福柯,《规训与惩罚》17)——以更大的威力成为权力体系管制被统治者的有效手段。根据福柯的理论,孤儿院和精神病院都戴着伪善的面具,把自己装扮成弱者的拯救者,实质上它们与监狱一样,都是实施监禁的社会机构。个体一旦被投入这些机构,在经受了暂时的肉体折磨之后,精神上的折磨会永久伴随他们,恐惧与畸形将笼罩他们的生活,通过这种方式,权力使其影响长期存在,将它的威力无限扩大。
诺曼与霍金斯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终,于是男性替罪羊选择了屈服,而女性替罪羊走向了毁灭,他们背后折射出的都是各种压制下扭曲的生存态势。理性的光芒挡不住现代文明背后滋生的混乱与癫狂,如果说被关在精神病院的诺曼披着一件有形的疯癫外衣,霍金斯的举动只能用裹藏在貌似健全的躯体下无形的疯癫来解释。“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所以它现在对于那些正在承受它的人来说,就将成为一个受尊敬和同期的对象”(福柯,《疯癫与文明》73)。他们代表的是被统治权威放逐的疯癫者,在人类的荒原中,这些疯癫者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然而这种被驯化的疯癫依然参与对理性的评估和对真理的探索,“它在事物的表面,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一切表象的运作,通过现实与幻觉的混淆……发生作用”(福柯,《疯癫与文明》31)。那些被关进疯人院的疯子深谙世间的癫狂,那些浑浑噩噩的所谓正常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在一个本身就已颠倒的社会中,谁能说得清到底谁是真正的疯子谁是正常人?福柯一语道破了疯癫的本质,“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与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福柯,《疯癫与文明》32)。
《入选者》具有犹太独特性,《五年刑期》则从女性角度反映了人类的畸形生活。然而从深层次上讲,鲁本斯笔下解析的是人类生活的某种普遍性,正如鲁本思所言,人类的生存才是她关注的主体。诺曼与霍金斯的遭遇是独特的,但又是普遍的。在现实社会中,旧有的价值体系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逐渐解体,人们处于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压力之下,在现实与内心的矛盾中痛苦挣扎,精神无法获得解脱,对许多人来说,清醒与疯癫只有一步之遥。人类充满痛苦咆哮与扭曲反抗的生存困境可以从这两部小说中窥见一斑。鲁本斯平实的叙述中包裹着血淋淋的事实,她让读者体会到了耸人听闻却又真实无误的现实。作为一个关注人类本真,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鲁本斯不仅是要唤起读者对人类生存本质的重视,更希望读者同她一起去思索探询人类的出路。
注释:
①Bernice Rubens,The Elected Member (New York:Atheneum,1969)199.本节中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只标页码,不再另注。
②Bernice Rubens.A Five Year Sentence (London:A Howard & Wyndham Company,1978)4.本节中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只标页码,不再另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