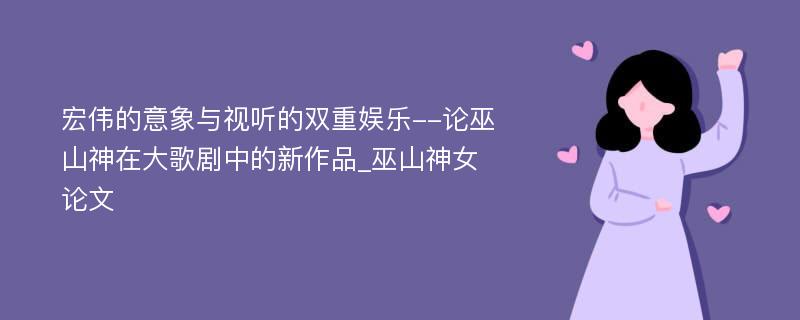
意象瑰丽 视听双娱——评大歌剧新作《巫山神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巫山论文,神女论文,意象论文,瑰丽论文,歌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古往今来,巫山神女曾引发过多少人的奇思遐想,而今,该是神女睁大美丽的眼睛,关注华夏子孙在她脚下开创的举世伟业:长江即将截流,高峡出平湖将变为现实,长江将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福祉,神女也将因万顷碧波的映照而更加容光焕发。为了这项造福子孙万代、功盖千秋的伟业,重庆辖区沿江百万人将作旷古未有的大移民。这项工程更深层的精神价值,在于显示了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强我中华的伟大气慨,全国人民、四川人民,特别是新辟为直辖市的重庆人民显示了非凡的创造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牺牲精神。是这次举世瞩目的工程催生了年轻的直辖市的诞生,而直辖市重庆也在建制之始,由重庆歌剧院贡献了气势磅礴、创意新颖、优美动人的大歌剧《巫山神女》,其用意、其影响都十分深远,而且对歌剧艺术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巫山神女》是作者昌达、柯愈劢、曹宪成编织的新神话。古老神话反映了人类幼年的形态。神话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着特殊的精神美和形式美,今人创造神话,要把现代意识融在古朴的神话载体中,把当代的审美理想交织在古拙、单纯美之中,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巫山神女》的成功是建在这个新编神话的基础上的。《巫》剧写了爱情的力量,但是并没有落入这个称为“永恒主题”的老套子中。剧中巫峡航道上的险滩“朝我来”,原是女娲补天时遗落人间的狰狞巨石,千百年挺立在急流之中,每每使行船撞滩而舟毁人亡。九妹是这个险滩的神化人物。这样定位使这个神话具有新的文化内涵。它不进入善与恶的道德涵盖之中,它是自然的造化,因而阻挡航道,危害人类,作为滩主的九妹不负道义上的责任。作者从人文角度探视九妹,只写了她的冷漠与无情,因为她还没有获得人的良智和美好的人性。是久惯行船闯滩的川江汉子水旺引发了她的爱慕之情;爱温暖了她冰冷的心,升腾起良智和同情,明白了是非,所以再一次发生舟船撞滩而毁的悲剧之后,她唱出了“我不愿意这样遭人恨,我不愿血染衣裙。”为什么过去面对人类的悲剧、苦难无动于衷而现在有了这种感情呢,她大姐一语点破:“只因为爱上水旺,你才觉于心不忍。”大姐要她依然心安理得地面对这样的悲剧,九妹却不,她以此为起点,步步向前,终于向决心疏通航道的水旺说出了毁滩的办法,并且帮助水旺深入阴曹地府,取得了毁滩的“还阳血”。最后水旺怀揣“还阳血”,以身撞滩,舍身取义,他到最后才知道他舍命撞毁的险滩也就是他所倾心相爱的九妹。滩毁河静,九妹无存,她飞升而上,成为屹立山巅、俯身于天地之间的神女峰,而水旺则化为七彩云雾,朝朝暮暮萦绕在他所爱之人的身旁。
这不是一个拘囿于“心相知,长相守”狭獈情感天地的爱情神话,它反映着当代人的胸怀与气慨。九妹为爱而献出了生命与爱情;水旺为排险救难、造福后人慷慨赴死;地府中三万六千受难的阴魂,为了活着的人不再重蹈复辙,都献出了他们赖以轮回转世的还阳血,为了后来人能享受安宁,他们不惜在阴曹地府万韧不复。只有这样崇高的牺牲、奉献精神所形成的整合力,才能消灾灭祸,改变造化,造福人类。这个歌剧所讴歌的不是小爱,而是大爱,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恒、永垂千古,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宽阔胸襟和美好情怀。
剧中虽有一系列牺牲,但并不是一出悲剧。《巫山神女》中那首清丽优美的主题曲反复叩击着我们的心灵:“阿哥阿妹心莫慌呀,太阳落了有月亮,月光落了星星亮,星星落了又会出太阳。”它不仅激励着九妹、水旺获得精神的永生,也让我们领悟到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生生不息的哲理。这首歌优美动听,意境高远,雅俗共赏,是这出歌剧神髓的写照。
从歌剧剧本的创作上说,《巫山神女》也有很好的经验。歌剧剧本担负着叙事、抒情、刻画人物的功能,但是其品格必须是诗。《巫》剧剧本创作先后十数易其稿,历时三年,也可以说是从叙事戏剧走向真正诗剧的历程。这不仅仅是叙事和抒情分量及比例调整的问题,而是关乎歌剧品格和审美特征的把握问题。正是这种对诗剧体裁、结构和表述特征的把握,使《巫山神女》赋予音乐创作以生发灵感的契机和充裕的时空。大家看完这部歌剧,都说音乐好,这与《巫山神女》编剧对诗剧品格的把握分不开。
(二)
大歌剧(俗称西洋歌剧)这种外来艺术形式引入我国的历史不长,这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精深博大、辉煌瑰丽的艺术样式,被称为戏剧门类中的“重工业”。它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但它并未在我国深深扎根,中国民众观赏大歌剧存在某种文化隔阂,对于以宣叙、咏叹调来叙事抒情的表达方式以及大歌剧音乐旋律的“旋”法,我国观众是有审美阻隔的。多少年来歌剧工作者一直苦苦探求大歌剧的民族化问题。近几年,戏剧界、歌剧界对大歌剧的民族化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张骞》《苍原》以及最近的《巫山神女》等(就我视野所及)都是我国大歌剧发展史上的最新成就。若以剧目数量以及演出场次而论,大歌剧不如其它戏剧门类,但就歌剧的进步与发展来说,这些歌剧的出现,意味着大歌剧创作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其意义不可低估。以我浅见,这些歌剧的创意着重于以下几方面:解决戏剧性与音乐性、故事性与抒情性的和谐统一;解决大歌剧音乐创作中如何体现民族特色、地域特色问题;解决歌剧演出中歌唱与表演的生动结合问题;解决在视听之娱中加强形象塑造以及全面加强歌剧综合表现力等问题。上述歌剧在这些方面多有建树,《巫山神女》是最新的成果。我的直观感受和我所听到的反映,都对《巫山神女》的音乐创作和舞台呈现交口称赞。它既有大歌剧音乐的气势和丰富,又有鲜明而亲切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把交响性与歌曲性结合得相当成功,合唱的配置和演唱酣畅淋漓,很富感染力;对贯串全剧的哑女的心声用无字花腔女高音来表现,令人称绝。《巫山神女》作曲兼指挥刘振球先生是我国富有创新精神的著名歌剧作曲家,他成功地为好几部歌剧作过曲,他在《巫山神女》中又一次实现了自我超越。说超越过去,不等于抛弃以前探索所积累的经验与成果。这次刘振球先生说要有新的突破,在大歌剧的创作上实现与“世界接轨”,我体会这是指在探求大歌剧的民族特色同时要发扬大歌剧音乐的独特审美效应,也就是不要丢失“大歌剧性”。我们从《巫山神女》的音乐创作和舞台呈现中感觉到了这种成功创造。《巫山神女》的魅力正来源于此。它的确是一部大歌剧,虽然也许还不完美。
(三)
《巫山神女》集中了一批戏剧和音乐名家,导演陈薪伊,声乐指导王秉锐,合唱指导吴灵芬、左天龙,舞美设计刘杏林,灯光设计伊天夫都是我国当代戏剧、歌剧、音乐界的翘楚,他们的通力合作,使这台歌剧壮哉美哉,视听双娱,意境深远,情思感人。《巫》剧是陈薪伊继《张骞》之后执导歌剧的又一部力作,她使这部歌剧气势不凡,情感浓列、构思新颖,充分发挥了舞台手段的综合效应,使演唱声情并茂、唱做并重。她在这个戏中对大歌剧体裁的把握和写意手法的运用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第三场,阴曹地府里的神秘、恐怖、幽怨都在空灵之美的笼罩下,着力于幽灵内心冲突和情感形态的揭示。用玫瑰花象征三万六千怨魂所奉献的还阳血,想像奇丽,血的恐怖升华为美的具像与联想,真是出奇制胜,诚可谓陈薪伊的又一“导演名句”。此剧男女主角分别由米东风和张礼慧扮演。米东风早在《张骞》中显示了功力和才华,张礼慧是重庆歌剧院自己的著名女高音,他们音色亮丽,演唱饱满,声情并茂并且表演自如,有塑造形象的自觉意识,这既是他们功力和艺术素养的显示,也与导演对歌剧表演的全面要求分不开。
(四)
《巫山神女》取得了众所瞩目、令人欣喜的成就,但是几次改动,几次赶排,以及为主客观条件所限,至今还存在一些欠缺。从剧本看,叙述性与抒情性的结合还有可改进之处,人物刻画特别是对九妹的塑造还比较粗线条,如“朝我来”险滩即是九妹的物化,九妹是这个险滩的神化人物,从意念到具像的联系点染得不够明晰和着力;九妹几个情感递升的关节处,如得知所爱的水旺矢志要毁滩排险;她告诉水旺毁滩要以自我毁灭为代价;她受众多冤魂甘愿献出还阳血的感召;她帮助水旺毁滩,最后导致她与水旺同归于尽时的内心冲突等,这些都是九妹情感转折、提升之处,是刻画人物的支点,还可以适当加强笔墨。我不是要求很着实地去描写人物的转变,而是在这几处再着力点染,加强心理和情感抒发的力度与深度,这样会使这个人物更丰满起来。就音乐而言,合唱很有感染力,但是铺排得有些过满,在进一步加强变化的同时也还可以挤出一些时间和空间来,用以加强对人物的刻画,比如第一场水手们合唱、重唱、独唱“想婆娘”,说到底是一种铺垫和“装饰”,完全可以再压缩一些。从导演来说,整个演出动势不足,其中包括合唱队的调度与动作设计以及进一步加强舞蹈性。场面处理中如一开头的行船因撞滩而船毁人亡和最后的水旺怀揣“还阳血”撞滩自毁,场面和动作设计还不似想像中那样精彩和富于震撼力。最后撞毁险滩导至的山崩岩裂及神女飞升构想很好,但操作还没有到位。关于服装设计,对神女的头饰、服装的想像和提炼似还可改进,众船工的服饰巴蜀特色还可再加强些。
《巫山神女》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希望进一步加工,成为久演不衰的精品,使它如巫峡神女峰是重庆的自然标帜一样,成为重庆的文化标记,让所有流连于巴山蜀水之间的人士在向神女峰高山仰止的同时,永远记住《巫山神女》这个美丽的新神话和这部歌剧美好的风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