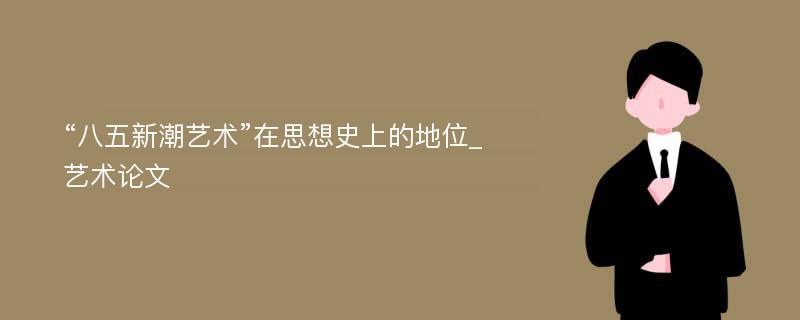
作为思想史运动的“85新潮美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论文,思想史论文,美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5新潮美术”运动随着中国社会由启蒙文化向消费文化的迅速转型而成为一段被封存的历史。显然,要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史逻辑,我们就无法忽略这一重要时段。我们已经在很多层面上谈论过这场艺术运动:艺术史、政治史、社会运动史,但到底是哪些思想和观念促成了这场艺术运动?这些思想和观念是通过怎样的“文本”、“话语”和传播方式影响着艺术实践?这些方式与其他领域的问题有着怎样的关联?这样一些思想史的话题似乎并没有引起过严肃的讨论。而本文想讨论的是:什么是思想史意义上的“85新潮美术”?
就最宽泛的意义而言,“85新潮美术”既是中国“新启蒙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一时代的具体内容,而要了解这一运动产生的历史依据应该从以下的问题背景着手:虽然有着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启蒙时期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思想内容和文化任务,但“85新潮美术”的主题词依然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产生的批判性的价值主题,它的不同语义和形态只有在具体的历史上下文中才能判断。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有历史和现实两个批判维度:其一是对长期封建文化专制的批判,其二是对50年代以来社会实践中的极左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两组性质不同的批判主题,但在80年代却时常混淆)。前者涉及的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转型问题,后者则是中国思想文化在“现代化”实践中如何超越极左意识形态的问题。前一主题更为宏观和深刻,而后一主题则更为现实和严峻;前者的实现有赖于后者的完成,而它们的前提都是需要新型的思想史资源。在80年代,“人文主义”和“现代化”这两个并非完全同一的文化主题却决定了“85新潮美术”的基本特质:首先,它是19世纪开始的“西学东渐”和20世纪初“五四”运动等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延续;其次,它是对长期以来艺术领域工具论创作模式的思想革命;最后,它也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西方化的视觉社会实践。而正是这种面向西方、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确认目标又使这场艺术运动染有浓厚的目的论和决定论色彩。
作为“新启蒙主义”的一个有机部分,“85新潮美术”的思想背景主要是哲学和文化学,它们分别从艺术本体意义和艺术文化学价值两方面为这场艺术运动提供了理论场景和语境。其具体的思想资源,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次西学翻译热潮,一是“走向未来”(金观涛)、“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甘阳)这类文化丛书。在“文革”前,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关系,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与介绍就是哲学引进的重点,“文革”后这一译介倾向依然延续,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自然哲学》、《美学》在艺术界都有广泛读者。80年代中期以后,译介重点开始转向西方现代哲学。除商务印书馆的传统品牌“汉译名著”系列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属“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上海三联书店的“20世纪人类思想家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西方著名学人丛书”等,几乎囊括了20世纪西方从人文哲学、分析哲学、精神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到文化学等代表性人物的著作。而中国学者撰写的评介著作更成为艺术家进入哲学殿堂的捷径:如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84)、张世英《论黑格尔精神哲学》(1986)、薛华《青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批判》(1980)、《黑格尔与艺术难题》(1986)、金岳霖《罗素哲学》(1988)、舒炜光《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1982)、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研究》(1988)、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1988)、夏基松《波普哲学述评》、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1984)等。而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986)、刘小枫的《诗化哲学》(1985)更是艺术界“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的直接源头。以介绍各种边缘学科的新兴成果为宗旨的“走向未来”丛书,以介绍传统文化为宗旨的“中国文化书院”丛书和以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史为宗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分别从不同角度为“85新潮美术”这场视觉革命提供着思想方案。
在“85新潮美术”中,哲学成为最直接的思想批判和精神重建的武器。20世纪80年代艺术界的所有思想陈述、论辩内容和语言形式都有浓厚的哲学色彩,甚至可以这样说,“哲学腔”在那时构成了某种话语权力:一个缺乏基本哲学素养和不谙熟哲学词汇的人很难成为艺术运动的中心人物。对大多数人而言,钻研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兴趣,不如说是一种实践本领的操练。
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中国思想界处于由保守向开放转型的阶段,从马克思早期学说中(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理论获取合法性思想资源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宣传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价值是这一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基本策略,对“革命现实主义”这种工具论性质的创作原则的批判,往往借助“人道主义”这把利剑。同期发生的艺术创作理论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自我表现”之争,艺术史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争,艺术创作上的“伤痕美术”、“生活流”,都可以看到这种阶段性特征。80年代中期,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启蒙主义“理性”思想,到欧美现代哲学的各种理性和非理性学说(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戈尔的“生命哲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都开始成为“85新潮美术”的思想资源。
启蒙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同时也是自我主体的重塑和重构运动,而“85新潮美术”选择“理性”作为这种重建过程的中心词,它由艺术家提出,经理论家的逻辑推演和倡导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流性思潮,主要弥漫于内陆北方地区。和“人文主义”一样,“理性”和“理性主义”也是西方哲学中语义宽泛得足以相互牴牾的概念。从并不具备逻辑严密性的表述看,“85新潮美术”中的理性主义从理论品质上更接近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理念”这一概念。在黑格尔历史辩证逻辑的正反合推演中,“理念”占有中心的位置,是绝对、无限、自由和独立自在的精神或心灵存在。而在他的美学体系中,艺术不仅被视为“理念”这种绝对精神的一种“感性显现”,而且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这种带有目的论、决定论和独断论品质的历史观给希望创造新历史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提供了理想的基石;而在艺术表现的“冲突说”和“悲剧说”中,黑格尔关于人物性格与普遍力量的矛盾描述(如古代希腊雕塑“静穆中泰然自足的神情”),又无疑给在这场艺术运动中寻找精神位置的艺术家提供了足够的“英雄”想象。在“理性绘画”的提出者、“北方艺术群体”的代表艺术家舒群那里,“理性”这一概念不仅等同于中世纪先知性、精神性的“神性”(只不过是以肯定人性为基础的新理性),而且是代表人类未来方向的新文化的代名词(它被具体命名为“北方文化”或“寒带—后文化”)①。而在王广义(“北方艺术群体”的另一位代表艺术家)看来,“85新潮美术”与其说是一场艺术运动,不如说是“一种哲学观念的表述和行为过程”。他说:“生命的内趋力——这一文化背后的力量在今天真正到了高扬的时刻了。我们渴望并‘高兴地看待生命的各种形态’建树起一个新的更为人本的精神形式,使之生命的进化过程更为有序。我们仅反对那些病态的、末梢的、罗可可式的艺术,以及一切不健康的对生命进化不利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将助长人类弱的方面,它使人远离健康、远离生命。”②显然,批评家也看出,“在这种变调的黑格尔语气中,还夹杂一些尼采和生命哲学的噪音”③。
与这种抽象的、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方式不同,在广大西南、华中和东南地区的艺术家则更趋向直接从各种非理性、反理性的“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哲学”、“存在哲学”中寻找重塑自我的精神依据。作为“西南艺术研究群体”领袖人物之一的毛旭辉在他那篇宣言式的文章中阐述了他对“艺术”与“生命”关系的理解:
生命是创造力的精神本原……艺术作为生命和创造的代名词首先是在摆脱了除自身外其他任何目的和功用,从个体的生命出发并维护这个实体时,它才展开了自己的羽翼……新具象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行动意识……它构成对死亡的征服,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的价值……当艺术从我们生命中外化出来时,生命得到了最高层次的延续,同时忘记了生命本身。于是:行动,呈现,超越。④
在东南地区,一种宗教性的悲剧意识使这种关于生命的假设具有某种救世主的神秘性质。艺术家丁方写道:
我们在献身的严肃性中找到共同的支点。我们渴望在内心深处再创一个生命体。我们在涉向彼岸的旅程中获得了崇高。我们在与永恒碰撞时感应到召唤的神秘……这种悲剧感同时显现为“画面中的悲剧意识”:它不仅是我们对于普遍“人”的命运的关心,而且是对他们的命运在永恒存在中无终始运行的深刻体验。⑤
而“新野性画派”则崇尚“本能”:“由本能这种深层心理支配了的艺术态度和情感意向是具有多意义、多层次的丰富内涵——诸如神秘、恐慌、焦虑、怅落……基于这种认识,新野性主义画派就必然地历史地把本能作为自己创造的内在动力和源泉。”⑥以上两种思潮支配下的现代主义绘画运动被后来的理论家归纳为“理性之潮”和“生命之流”⑦。而在这些庞杂生硬的语境中,叔本华的“意志本能”、尼采的“超人”、克尔凯戈尔、萨特的“存在”和“自由选择”、柏格森的“生命绵延”、弗洛伊德的“力比多”都以一种实用性、本土性的话语方式被统合在这场艺术启蒙运动中。而从思想史逻辑看,无论是“理性”的文化建构方案还是“非理性”的“人本重塑”理想,作为中国艺术现代化的一种理论实践都体现为一种决定论、目的论性质的历史观和思维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为对“85新潮美术”中各种哲学运动的反思和观念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分析哲学(尤其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如波普尔的理性批判主义和库恩的“范式”理论),甚至各种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后学”开始成为影响东南地区“85新潮美术”运动的主要思想资源。同时,作为对激进的西化运动的逆动,对本土哲学(主要是庄禅哲学)的兴趣也开始成为中国现代艺术问题的思想史资源。在“85新潮美术”后期出现的这种思想倾向首先表现为对前期运动中过度哲学化、宗教化和人本化的不满。浙江的“池社”就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我们既鄙视那些‘实验’的‘游戏’的艺术,又反对将艺术置于哲学的从属地位,我们致力于倡导一种介于哲学和非哲学、宗教和非宗教、艺术和非艺术以及世俗与理想之间的‘艺术’,而这种‘艺术’是属于理性的,还是感性的,还是中性的,则无关紧要。”⑧而上述这种不满引发了来自三个方向上的反思性清理。
其一,将艺术视为一种“纯粹的”语言或文字的逻辑分析活动,从而将艺术中的泛人文热情作为应予清除的外在意义假设。这种倾向明显流露出分析哲学对世界意义解释的语言学化和反形而上学的影响。与同期在艺术界发生的“纯化语言”讨论不同,这种语言分析倾向与罗素的那个著名的信条有关:“任何哲学问题经过必要的分析和净化,或将不再成其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或将成为我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逻辑问题。”⑨吴山专就曾明确宣称“艺术语言在艺术史上起着决定性命运的作用,艺术的价值就在于他对艺术语言的创造与发现(所以康定斯基和杜桑对我们的启示是有意义的)”⑩。“中文的每一个美的形式,大多数都表达一个观念,而且这些美的形式经过一定的排列、组合,可以表达一个复合观念。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以上的方式告诉人们,这是我们的世界”(11)。他确认中国文字的印刷体结构和单音节读法作为艺术符号的合法性,也毫不隐讳这种分析性的“文字”艺术所受到的西方语言学(如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现象的“直接指证定义”)、概念艺术(杜桑的“艺术即思想”)和本土禅学(禅机偈语的运用)的启示。张培力的“方案艺术”(《艺术计划第2号》、《褐皮书1号》、《1988甲肝情况的报告》)都有将规则、语言、社会现象“语言化”和“分析化”的倾向,类似维特根斯坦对“家族相似”概念和“遵守规则”悖论的描述(《褐皮书1号》甚至就是维氏《蓝皮书和褐皮书》的直接袭用)。而谷文达对中国书法的破坏性重组和徐冰对汉字复数性的戏谑性营造,则不仅是“意义就是用法”这种语言学教条的视觉实践,而且具有对传统文化反讽与批判的时代性内容。
其二,对“85新潮美术”中“表现”理论和本质主义的质疑使各种具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后学”成为这场艺术启蒙运动的直接反题,而这个反题又与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主义、波普主义相呼应,构成了中国由80年代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向90年代“当代主义”观念运动转型的先声。黄永砯和他的“厦门达达”是这场“后学”思潮的先锋和代表。早在1985年3至4月间黄永砯就完成了他的“非表达绘画”,他以一种自设程序表明自我选择与自我表达间的悖论关系:
(它是)按程序进行(自我规定)而又与我无关的(非表达)绘画,这是精心地选择某种媒介,而这种媒介的使用又使“精心”和“选择”归之无效,这就是偶然与随机之结果。当我把自我决定之权利归于随机之结果时,我既不是按我个人的需要,也不是按照所谓的超越个人的法则的需要;当我把决定的东西只限于随机之结果时,也就很大程度地否定了有“被决定的东西”的存在。把一切归于偶然的决定比决定了的偶然更接近于自然。(12)
在一年以后的“厦门达达”展中,这种反表现论、目的论的个人艺术实验被放大为一场反文化、反艺术甚至反人本价值的后现代艺术运动,《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作为一篇檄文,它宣称从1983年至1985年以来现代艺术运动只具有“前现代主义”的性质,预言了以“达达”精神为依据的“后现代”艺术时代的到来,它还直言不讳地谈论“达达”与“道、禅”在艺术态度上的同一性:
作为“道家”和“禅宗”本身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如同世界万物一样处于盛衰和变动不居之中,所以“达达”是深刻的,“达达”宣称不是所有运动上再加上一个运动,而是反对所有运动,这是一个悖论:“达达”反对自身,如此一来“师之所处,荆棘丛生,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而凶年之后呢?(13)
在这以后的一份手稿中,黄永砯再次提到“绘画死亡”的问题:“86年底的焚烧作品并不完全意味绘画的死亡,它更多是一种最极端的处置办法,存在着多种处置办法,但一个人愿意把焚烧作品作为处置他的作品的恰当方式,明显地意味着作品——偶像的消亡(作品是艺术家自己造出来成为自己崇拜的偶像),这是一种价值的明显贬低。”他还谈到了“艺术史”和“权力”:“如果追求艺术史中的艺术就是追求权力,或接受权力的引导,换句话说,使一种东西成为艺术必须使用权力或利用权力这一渠道。不存在统一的艺术史,只存在各种不同世界的艺术史。这些观点可以改写艺术史。”(14)
解构人性表现的启蒙神话,解构知识统一性的理性神话,使“85新潮美术”这个具有浓厚目的论色彩的中国现代主义艺术运动进入到某种“后学”语境。
如果说黄永砯的“达达主义”是从后现代主义方向对前期“85新潮美术”的某种棒喝,那么,1989年王广义提出的“清理人文热情”的口号则是来自对这个运动自身的反省。他用“形而上学的意义”与“情境中的逻辑问题”区别了“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他说:“‘现代艺术’和‘古典艺术’是由古典知识的整体结构赋予其意义的,它们是由人文热情的投射而产生的准自然的艺术。这一切都与人的信仰和形而上学的恐惧相关联,如人的微观同神的宏观的相似性假设等等。艺术家们以在共同的幻象中所经验的一般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共同建构神话史,在这种神话史中一切都经过夸张和放大的人文处理。”在他看来,要摆脱“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这种相似性的“语言惯性”,只有“抛弃艺术对人文热情的依赖关系、走出对艺术的意义追问,进入到对艺术问题的解决关系之中,建立起以已往文化事实为经验材料的具有逻辑实证性质的语言背景”(15)。作为艺术家,他以他后来的艺术实践兑现了这种理论承诺。在《后古典系列》中,他以一种分析性的图像方式解构了他早期作品中的文化乌托邦情结;而在90年代后的《大批判》中,这种解构方式又逻辑性地发展成为波普主义这种更具文化实证功能的语言,从而也完成了他由一个现代艺术家向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转换。
对“85新潮美术”的第三种思想清理来自于这个运动的外部,批判的武器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贡布里希艺术史中的“情境逻辑”理论。1984年开始,范景中和他的学术伙伴们开始了一场延续至今的西方艺术史、学术史和思想观念史的引进工程,它以对温克尔曼、沃尔夫林、贡布里希的西方艺术史研究成就以及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的翻译和评介,提倡一种尊重历史价值和开放思维的文化观念。虽然这项工程与“85新潮美术”没有直接的理论联系,它对这场运动的历史决定论性质,对其“进步”观念和非理性倾向的深刻批判甚至使它一直作为这场运动的反题而存在,但从更宽阔的历史维度观察,它却为这场改变中国人价值生活和思想观念的运动提供着更为深刻持久的理论资源。从“理性绘画”(16)到“大灵魂”(17),从“时代精神”到“民族精神”,在“85新潮美术”的思想方向上始终弥漫着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气息,这就使这场艺术启蒙运动在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同时又包含了扼制这种自由和解放的价值。思想史的问题最后必然会归结为文化问题,因为思想的反思只有真正落实到对文化的反思才能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1988年,在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一书的译者序中范景中借贡布里希在艺术史中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之口,分析中国现代艺术中“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表现理论,揭示了艺术“创新”、“进步”这类历史决定论套话背后隐含的文化危险性,同时他也介绍了黑格尔主义在艺术史中的替代理论:艺术情境理论或“名利场逻辑”(18)。1989年,笔者发表《中国现代美术的两难》一文,直接向“85新潮美术”中的“艺术本质主义”和“艺术整体主义”两个主流性思想倾向发难:
……(中国)现代美术的形而上学倾向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它认定艺术的本体意义在于它传达的是某种属于人类的永恒超验的文化精神,——至于这种精神是绝对的理性力量还是某种来自我们自身的“生命力”的冲动,抑或是与我们民族“本土精神”紧密相连的“灵性”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总是由每一个时代中少数走在历史前列的贤哲所代表和显现的。美术的病态和衰落正反映了我们民族时代精神力量的衰落,因此,美术的现实使命和崇高目标就是高扬人类的理性精神,这种使命从根本上讲是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而不是艺术的……我想借用波普尔在批判历史决定论时所使用过的两个名词,把上面的表述概括为“艺术的整体主义”和“艺术的本质主义”。整体主义认定历史发展总是通过某种集团精神(作为集团传统载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用‘民族性’或‘时代精神’来理解历史的发展”(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本质主义则进一步肯定支配历史发展的这种精神力量是可以进行某种形而上学的本质描述和把握的,由此出发必然产生出另一种自信:由于支配历史发展的集团精神是可以人为把握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一套历史发展、进化的有序规律也不应是困难的,剩下来的是:我们如何在这套规律的导引下各行其是。不难理解,历史决定论的必然归宿只能是文化宿命论。(19)
我当时希望从中国现代艺术产生的悖论性、决定论对这场艺术运动的危害性以及艺术精神与艺术情境关系的分析中寻找到中国现代艺术走出两难困境的方案。
以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对“85新潮美术”的思想清理可以说是在“新启蒙主义”和“后学”之间的第三种方案:一方面它希望在情境逻辑的理论构架下完成对艺术中历史决定论的政治批判;另一方面它力图在维护人类理性价值的前提下完成对相对主义、解构主义艺术观念的思想和立场清理,而就这种思想的文化学旨归而言,我们又可将它视为中国艺术领域的一种现代化的反思理论。
就思想史而言,只有那些具有思想强度的时代才能进入思想史的时间。所谓“思想强度”,一是指历史和社会提出了只有独立的思想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指适应这种需求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对答和方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在中国发生的“85新潮美术”正是在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时段中产生的。“85新潮美术”既是一场本土性的视觉革命,又是一场庞杂的思想史运动,它的非主流性、民间性和批判性使它在整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启蒙运动中扮演着某种无法替代的角色。无论从思想性质、思想内容还是从思想形式、思想方向上,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为上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的延续,也正因如此,它也承载着这一过程的所有矛盾、悖论和冲突。在以抽象的普世文化目标替代传统的意识形态时它往往表现出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陌生,而在以西方式启蒙价值进行文化、艺术的改造时又往往陷入目的论和决定论的陷阱。“85新潮美术”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一场具有浓厚形而上学和思辨色彩的思想、文化运动,它的思想史意义在于:首先,它不仅中止了传统意识形态对艺术的单一的、工具论性质的思维习惯,使艺术创造有了“批判性”这一全新的思想维度,而且训练了中国艺术家在政治、哲学和文化的宏观视野中思考艺术问题的能力;其次,“85新潮美术”对主体性的建构和重塑过程是以西方各种抽象的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具有过分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色彩,缺乏与本土历史和实践的深刻联系,无法真正面对和应答诸如艺术与资本、中国本土艺术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艺术霸权这类更为复杂情境中的问题,这一弱点在90年代中国文化全球化转型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一历史仍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在文化上的精英主义立场在抵制消费主义时代各种低俗的犬儒主义时仍具有很强的价值功用;最后,在这段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中展开的各种思想讨论和反思也为90年代艺术界各种具体学术课题的展开做出了厚实的理论铺垫,如80年代艺术界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兴趣对90年代中期关于语言与意义问题讨论的潜在影响,艺术情境理论对艺术市场、艺术公共性等问题展开的实践作用,各种后学思潮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课题展开的学术意义等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甘阳认为80年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是完成中国文化由“前现代化的文化系统”向“现代化的文化系统”的历史转折,而两种系统间深刻和复杂的“文化冲突”使这一过程更多地体现为“黑格尔所说那种悲剧性的不可解决的历史二律悖反冲突”。他又认定在一个没有完成“现代化”文化转型的时代如果急功近利、登高望远地走入“后现代文化”,“客观上却多半仍只是滑落于‘前现代文化’的井底之中”(20)。文化学者这种历史的逻辑判定也许有其深刻性,但这种二分或三分法却往往会使我们丧失对现代化过程中一些更为复杂的实践过程的判断,而这种实践在大多数情形中并不表现为由此及彼的阶段,相反,往往表现出交叉或“跨现代”(trans-modern)的特征,从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思想发展方向和路径,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实显然要比逻辑更加丰富、诡异和令人不可捉摸。
注释:
①舒群:《为北方艺术群体阐释》,载《美术思潮》1987年第1期。
②王广义:《我们——85美术运动的参与者》,载《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36期。
③严善錞:《当代艺术潮流中的王广义》,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④毛旭辉:《新具象——生命具象图式的呈现与超越》,载《美术思潮》1987年第1期。
⑤丁方:《红色·旅箴言》,载《美术思潮》1987年第1期。
⑥樊波:《新野性画派的观念变革》,载《美术思潮》1987年第1期。
⑦高名潞等:《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⑧石久:《关于“新空间”与“池社”》,载《美术思潮》1987年第1期。
⑨Bertrana Russell,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George Allen & Unwin,1926,p.42.
⑩吴山专:《我们的绘画》,载《美术思潮》1987年第1期。
(11)吴山专:《关于中文》,载《美术》1986年第8期。
(12)黄永砯:《非表达的绘画——一种按程序进行(自我规定)而又与我无关的(非表现)绘画》,载《美术思潮》1986年第3期。
(13)黄永砯:《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载“厦门达达”展刊。
(14)黄永砯:《87年的思考、制作和活动》(手稿),《黄永砯》,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15)王广义:《清理人文热情》,载《江苏画刊》1990年第10期。
(16)高名潞:《关于理性绘画》,载《美术》1986年第8期。这是对“理性绘画”进行史学归纳和理论阐释的最早文献,作者认为“理性”包括作为恒定的精神原则(真理)及通过分析、推理察觉和判断这一原则的过程、途径。而他认为各地各种形态的“理性绘画”正是对这种“超验的、带有构筑意志的、具有永恒原则或崇高精神的对世界秩序的表达”,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主流性的追求”。在其后来编著的《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中,更将“理性之潮”作为主要章节,并对它进行了“人文理性”、“本体理性”(又细分为“宗教理性”、“哲理理性”、“客观理性”)和“思维理性”的归类,称它是“建树中国新艺术体系的关键所在……而一旦告成,那就将是世界意义的成功了”(《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17)胡村(栗宪庭):《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载《中国美术报》1988年第37期。文章针对同期发生的“纯化语言”的理论讨论指出:“我们时代的灵魂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冲撞和先进与落后的巨大反差中形成的。在这个大灵魂的深处,剧烈滚动着无穷的困惑:希望与绝望的交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传统与未来的冲突,以及翻来覆去的文化反思中的痛苦、焦灼、彷徨和种种忧患……一旦语言、技巧、风格成了艺术家的目标时……艺术便在‘自律’的幌子下,失去了它生命冲动的自足状态。”
(18)范景中:《贡布里希对黑格尔主义批判的意义》,《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译者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情境逻辑”可参见该书第94页注释。
(19)黄专:《中国现代美术的两难》,载《美术》1989年第5期。
(20)甘阳:《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五题》,《古今中西之争》,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5页。
标签:艺术论文; 思想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美术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艺术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黄永砯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