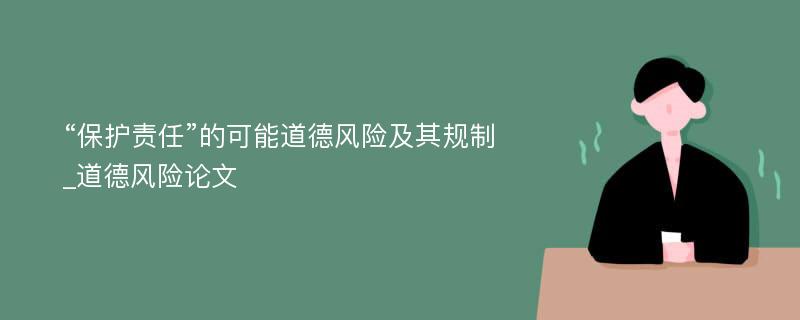
“保护的责任”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及其规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制论文,道德风险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3) 6期0122-12
一、“保护的责任”理念进展态势
20世纪90年代起,作为国际人权保护领域的新兴概念,“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迅速成为西方世界进行国际干预的“指导原则”,显示出建构新国际共识与全球规范的强大潜力。作为一项规范性概念,R2P的兴起与成型过程却带有强烈的现实意蕴。冷战结束初期,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使国际社会在维持和平、保护平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等方面陷入某种僵局。1993年索马里维和失败、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1995年塞尔维亚斯雷布雷尼察惨案等事件,表明联合国相关行动的不确定性与不完善,无法充分实现预期目的。1999年,俄罗斯在科索沃问题上威胁使用否决权,使安理会行动再次陷入僵局,而北约在科索沃的单独行动则引发了关于国际规范的激烈争议。国际社会对上述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基于联合国合法性护持方面的考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尽快达成共识,以改善相应形势。①
R2P概念的前置基础是所谓“主权的责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1993年,为应对全球范围内国家内部冲突剧增的问题,联合国委派弗朗西斯·登作为特别代表对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进行研究。调研结果首次提出强调主权的责任内涵(相对于绝对排他性而言),但仍将保护国内平民的主要责任寄予当事国。②2001年是R2P概念成型的关键节点,由加拿大政府组成的“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CISS)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题为《保护的责任》报告。2005年,R2P被写入第60届联大《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15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签署了该文件。2009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联大提交《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提出了三个支柱概念:国家的保护责任(运用必要手段,保护人民免于种族屠杀、战争罪、族裔清洗、反人类罪,并因此改善主权);国际援助与能力建设(国际社会的责任形式);国际社会及时而果断的反应(在国家明显不能或不愿保护人民免于四种罪行的情况下)。③
早前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主要围绕军事干涉行动合法性、主权与人权等话题,这些话题相对狭窄,带有浓重的高政治、抽象式特点,经常将讨论引入死角。④相比之下,R2P讨论视角更宽阔、发散、具体,重点关注弱者与受害者情感,将注意力引向行动方案、代价、结果而不是干涉本身。据学界归纳,R2P推广者主要使用“诊断式框定”和“预期式框定”,构筑相对精致的“道德实践框架”。⑤
“诊断式框定”集中关注受害者一方而不是干预实施者的强权问题,重点强调“什么是错的,什么现象应受谴责”,将此前“不愉快但仍可忍受”的社会政治生活事实加以重构,成为必须纠正的问题。ICISS报告避免直接质疑“不干涉内政”这一保证秩序与行为可预期性的原则,反复强调主权作为一种“有条件的权力”,依赖于当事国对人权最低标准的尊重以及保障,并试图强调国际社会在国家不能或不愿妥善应对人道主义灾难时应承担的责任。
“预期式框定”的应用体现在ICISS报告对具体问题解决方案、行动动员、目标实现手段等方面的大量关注。ICISS考虑到国际社会围绕“人道主义干涉”存在的激烈辩论与理念分歧,以及原有关于干涉权力的措辞只能引发疲劳争辩、无助于解决问题的现实,选择以干涉方式、条件而不是干涉行动本身作为突破点展开论述。它强调“责任”包括预防、做出反应、重建,并以预防作为最重要方面,尽量少用侵入或强制方式。为此,ICISS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军事干涉原则”:正当理由(已经或即将发生大规模丧生、种族清洗)、合理授权(安理会)、正确意图(阻止或减缓平民苦难)、最后手段(先穷尽和平手段)、均衡性(规模、期限上的最低强度)以及合理成功机会(行动有可能达到预期结果)。⑥
在经历迅速发展期之后,R2P陷入某种瓶颈状态。联合国在此原则的具体内容方面仍处于“继续审议”状态,其法律化过程被暂时搁置。综合来看,R2P在诸多层面面临挑战。
1.背景层面。R2P体现的世界主义关怀、后现代式的良善构想,与目前的现代性国际环境之间仍有诸多不适。无政府体系下的初级社会体制缺乏充足的组织化、制度化要素,不能为国家行为与国际道义提供充分担保。“人的安全”经常被作为国家意志合法化的包装,国家安全、不同群体利益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纠缠难解。这就是说,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固有矛盾并未得到妥善处理,而只是被掩藏或绕开。R2P对此作出了各种妥协,例如,弗朗西斯·登在其后论述中,同意将“主权的责任”加以限制,承认当地权威或当事国在保护国内难民时,如果不“武断地屏蔽”国际援助,仍享有主体地位;联合国成果文件强调对具体个案区别对待,不采纳设立军事干预普适标准的建议等。⑦
2.内容层面。R2P自身逻辑架构的建设仍面临一个核心困难,即目的与手段的冲突问题。由于模糊定义更容易保证R2P共识的广泛性,许多困难并未得到足够认真的解释。例如,国家应如何保护人权才算符合R2P标准,如何判定国家“已经不能或不愿”履行保护责任,如何保证干预手段的合理性(如出现干涉的任意、武力作为优先手段、干预时烈度超出适当或对称要求等),如何改变对干预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预防和重建问题,等等。⑧如果一味强调“高尚目的”,而不讨论过程、手段、结果的非正当性,无疑会使R2P概念的进展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与阻力。
3.前景层面。对被干预方和干预方而言,R2P的实践过程都存在若干问题。在被干预一方看来,由于R2P在主体资格、行动监督、后果问责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滥用这一原则为有选择地打击他国提供了极大便利。由于标准模糊、后果的不可预知性、行动评估的重叠验证(难以确切认定具体行动效果)等问题,干预行动可能不到位(卢旺达)、无限制(科索沃)、褒贬不一(达尔富尔),或是突破既定规制(利比亚),甚至明显基于其他目的(格鲁吉亚、伊拉克等)。对行动方而言,即使干预的资格较易获得,在无明显利益关涉地区或干预代价较高时,干预缺失现象仍较为显著。相反,在利益攸关地区则经常出现干预过剩现象。R2P倡导者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即该概念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所获得的政治支持并不理想。大国的疑虑主要在于滥用(中、俄)和妨碍行动自由(美、英)。利比亚战争后,R2P共识的保持再次面临挑战,保护的目的与手段两难再次凸显。
二、“保护的责任”与道德风险问题
2000年,安南秘书长在《联合国千年报告》中提请“注意人道主义干涉可能导致的非预期后果问题”,即“有可能鼓励分裂分子、叛乱者、反对派等故意触动该国政府压制和侵犯人权,并以此引致更多外部干涉,获得对抗现政权的资本和进一步援助”。⑨艾伦·库珀曼称这一现象为“道德风险”。库珀曼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R2P导致道德风险的内在机制主要在于外援预期导致的威慑失败,即由于外部干涉的可能性,反叛组织不相信现政权压制行动的可信性;相反,他们越来越具有冒险性,将主动挑起事端,拒绝协商安排,期待成为政府压制行为的受害者,以某种可承受的代价配合外部干涉取得反叛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人道主义灾难可能源于政府军、反叛者或第三方势力,外部干涉实际上导致并延续了国内暴力过程。⑩
道德风险论提供的主要启发在于效用导向与结果关怀,其主要不足则是沉陷于结果论,而无法给出建设性、积极进取且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方案。换言之,道德风险论在解构一种既有价值之后,并未创建一种新价值。它对于R2P的理论态度是一种所谓“至善论”思维,未能考虑R2P作为理念和实践的含义区隔,缺乏对进步概念的宽容度。回溯“保护的责任”原意可以看到,它最初是为了解决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应对全球范围内对“人道主义干涉”先入为主的反对情绪,尝试在人权与主权之间建立可能的一致性,使两者相互支持。(11)R2P在实践扩展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如对国家动乱“外溢效应”的应对思考,寻求形式平等(例如主权)与实质正义(例如R2P所宣称的诸种道义目的)在实践中的关联与统合,寻求国际社会“监督”一国政府施行法治、对国民负责,阻止其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可能性,等等。这是一种改革性的、基于问题解决逻辑的思维路向。至于被滥用或出现某些意外结果的可能性,任何规范或制度都不能排除。这就需要R2P在具体扩延层面进一步完善,例如考虑如何理顺预防、反应、重建之间关系,尊重当事国主体性;考虑平衡非军事手段、信度及威慑力因素等。
广义上的道德风险论凸显了手段的不可靠性。干预方式不当可能导致恶劣结果,压缩冲突政治解决的空间。例如,粮食援助对许多冲突当事国而言已成为战争的助燃剂,大量援助导致当事国民众产生依赖心理,相应投机现象盛行;不同人道主义组织之间出现不良竞争与诋毁。当前,我们需要尝试一种以结果调解人道主义干预涉及的道德风险问题的新思路,重视结果的独立意义,将结果置于手段之前。为分散和规制道德风险,真正实现所谓“责任”,有必要在结果意义上考虑近期与长远两种思路,前者强调规范武力,后者关注根源治理。
就武力规范而言,正义战争论能够带来较多启发。它基本肯定了战争作为追求正义目标的手段所具有的合理性,同时注重总结和发展一套标准来规范武力过程,而非抛弃后者。(12)“保护的责任”核心应是规范武力乃至寻求和解:虽然干预方在很多情形下缺乏耐心,然而真正的保护所亟需的并非武力本身,而是解决问题。动用各种资源、花费更多的时间寻找真正的矛盾点,以非武力的方式施加必要的制度化压力,寻求更多当事方的满意与和解。强调“负责任的保护”,意味着R2P的不断完善,在过程及手段之外更强调预防,注重生存权、发展权以及更多涉及结构性预防、根源治理的议题,促进人权领域内的议题联系,保证在横向、纵向意义上都能够体现结果对于道德风险的纵深规制效应。
三、行动取向与负责任的保护
确认结果导向对解决人道主义干预涉及的道德风险问题的关键意义之后,宜应继续讨论解决冲突的行动原则与取向。这一问题的前提是:确认“主权的责任”与“国际社会保护”的联接正当性,以便在行动层面缓解“保护的责任”涉及的目的与手段冲突问题。对此,相关的学理回应主要有两种思路,即诉诸自然(目的)与诉诸常规(常识)。
诉诸自然或目的,是一种基于罗马法的思路。其主要特征是对人性与普遍法律原则的强调,以自然法为主要依据,关注抽象的“权利”(rights of humanity)、“目的”(end)、“终极因”(a final cause)等概念。所谓自然,是指一种有自明性质的事实。它指向一个终极目的,并提供某个起点(a starting point)。然而,它的内恰性建立在“不断上诉”行动中,并将权利置于诸善之前,在理念与行动的联接论证方面缺乏应有关注。基于“天赋人权”观的行动方案,在理论正当性方面亦存在若干致命缺陷。首先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自然正当性向自然权利的偷换式颠覆,导致价值虚无、缺乏可供上诉的最终依据;权利无条件至上,不能节制其所涵括内容的泛化趋向;承诺过高(永不剥夺),成本惊人(为恶风险小、收益大),内在冲突不断(破坏其他权利者享有权利),往往无法保证过程的持续性与结果公正。即使诉诸自然的思路具有良好动机,也极易导致R2P行动价值混乱、行为失序、缺乏可持续动力和正当结果的难以保证。由此看来,它至少在理论上考虑不周,缺乏应有的谨慎。
诉诸常规或常识,是一种更有现实意蕴与实践弹性的思路。它支持“人赋人权”,相信利益(interest)和意志(will)等趋于现实的要素。它不是强调目的或律法本身,而是更多强调施行的结果(results that come with exercising them)。这反映了由责任(抽象概念)到负责(具体实践)的转向,也是一种将常识置于目的之前的做法。在一般意义上来看,所谓“存在”本身必须在“做”中实现并得到证明。如果忽略现实境况与利益关系的联结,偏重于理想主义的规范理念(R2P),有可能面临“剥洋葱”的效应,即各层表面的抽象措辞剥离后,并未剩下任何实质内容(行动痕迹)。显然,这种思路更符合当前R2P实践的境况与困难(道德风险),能够为相应行动提供某些有益的原则指引,尤其是在如何协调效率与公平、干预和限制的关系,在诉诸常识基础上尽量保证行动结果,实现由责任(responsibility)到负责(obligation)的转变。
首先是干预过程的利益与动机问题。不可否认,干预行动总是存在道德价值与自利价值的显性重叠或隐性暗合,即使是最“真诚”的国家,也会隐藏这种自我取向的“巧合”结果。人道主义的工具性质涉及行为者动机的不可测度性、区分机制的缺乏等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相应行动的对象国与具体模式选择。(13)例如,相比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干预,尽管单边干预在效率方面往往更胜一筹,但其更容易倒向自我利益。对这一问题,应充分考虑而非回避各方利益问题,可通过寻求利益的激励、竞争、规制以及制衡机制,将现实与实践摆置于最终目的之前,尽量实现利益与道德的“积极均衡”。
其次是干预行动的节制问题与有限性。鉴于干预国实际动机的复杂性、国际社会价值观的差异性以及道德风险的不确定性等因素,R2P实践的目标、方式难以精确预期或得到控制,在干预后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干预者一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及利益标尺,对目标国政治与社会权威重设施以深度影响,实则将维持和平(peace keeping)变为制造和平(peace making),原本宣称的道德正当性流失。为规制这一风险,简单逃避任何行动、寄托于朴素的“道德元律”、将R2P建立在道德伦理范式中的思路都过于简单。应对这一难题,首先是回归现实,调整各方心态,较少强调干预行动的政治性,对行动必要性做出审慎分析;抱持务实态度,避免设置过高期望。最关键的行动原则在于将R2P目标和过程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快进快出,无损主权,将“道德风险”降至最低限度。如能在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积极促成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则更为明智。
为此,与负责任的保护相适应的行动方案,实际上更侧重实践与常识,而优先于目的本身。(14)“负责”至少应包括如下几点内涵:认真考虑主权与人权的矛盾点,愿意尝试并努力规范武力,调和目的与手段的冲突;明确授权主体与标准,在维护联合国权威前提下,首先寄希望于当事国政府而不是从最初即诉诸最后手段;(15)有所为有所不为,确保不得已的军事行动仍不失其有限性,行动应倡导多边机制,尽量避免单边主义,考虑将目标框定为“对目标国人民与行动结果负责”,使结果有益于地区稳定,并在此前提下尽可能推进军事行动的监督、制约、限定以及过当问责机制的建立;(16)考虑以负责为主线,优先应用政治、外交、经济等非军事手段,限制道德风险生成的可能性,稳固R2P实践成果。
四、道德风险规制的若干思路
基于上述论述,关于人道主义干预涉及的道德风险问题,解决思路是诉诸结果和常识,而不是单独诉诸手段或目的。基本目标是从“保护的责任”转向“负责任的保护”。在结果维度上,较为适切的议题包括代价与效用、近期与长远等。在策略层面,R2P道德风险的规制有赖于一种回归常识、尊重常规的思路。具体可以从微观(能力与意愿)与宏观(动机与平衡)两个维度展开讨论。
代价与效用议题主要就R2P对象国而言,首要目的是尽可能降低行动的代价,获得最大效用。实际上,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整合历史一直充斥着暴力与人权侵害,这些代价对现今的非西方国家而言似乎并不容易绕开。(17)为此,关于R2P的评测在某种意义上应关乎实际的代价与效果对比,阶段性目标包括:可观察的人道主义罪行实施代价上升;R2P行动出现效果高于代价的显著趋势;在实施方式、过程、结果等方面呈现更多关乎人权保护的认同与价值共享;行动合法性能够承担较长时间的检验等,而不是以道德至上的方式,经过貌似善意的行动,却未见实质性的改善。代价和效用考量可能使当事国各方停止冲突、实现和解更有效率,具体方式可包括武力暗示、显示决心、集体制裁、制造稀缺与竞争压力、经济援助与政治支持、道德压力与反复劝说等。调解过程宜采取“逐步升级、不失弹性”的时间方案设定,坚持明确条件不可变更,及时遏制事态的不良发展,为主动配合的意愿、争端态势的改善提供奖励。(18)
近期与长远议题主要涉及R2P如何平衡“治标治本”的关系,从切近的审慎发展逐步过渡到积极的根源治理。由于R2P的道德风险问题尚未解决,不能保证相关行动取得良善结果,国际机制也不能直接给予个体民众以有效、公平、妥当、普遍的保护。R2P法律化过程仍需得到审慎控制,其具体范围应限于“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标准表述,配合现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框架内的多种人权保护模式,而不宜宽泛地将所有人权保护项目悉数纳入。在R2P的施行过程中,具体国家的预防责任最为关键。国内各层面保障措施、社会冲突的缓解、社会秩序的保障、包容文化的培育等问题,都首先需要当事国政府的积极行动及其后续效果,其后再考虑国际社会与大国提供支持鼓励的补充责任(residual responsibility),以确保R2P真正有利于(而不是包办)负责任主权的实现。
R2P的前景在于其所提出的“预防”及“重建”责任,即当事国问题的根源治理。具体国家的人权发展,更大意义上是国内社会进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贫困、被剥夺、法治缺位、社会不公正、国内整合度低下、政府缺乏足够资源提高其治理能力等社会结构问题的原因,实际上已成为国内叛乱、种族冲突、民族分离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首要动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R2P实践效果的不可持续性。为此,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发达国家,都有必要在这一方向投入更多资源,给予目标国家更具实质意义的发展援助,改善其生存境遇。相反,直接制裁、匆忙诉诸军事行动、简单推动政权更替,或是仅停留于操作化、应急性的预防努力,都不能称为“负责”的保护方式。
能力与意愿问题主要涉及R2P主导国家。为提高行动效率与绩效,改变集体行动困境对干预效果的影响,能力问题应得到更多重视,相对客观公正的行为主体(国家或国际组织)宜发挥主导作用。相关行动往往伴生政治、经济等道德外目的,严格限制这一目的也可能破坏相关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而放纵这一目的则可能导致“保护过当”的道德风险。为此,相关行动的制度化水平有待提高,应适度允许主导国享有某些“机制化利益”、“威望利益”、“优先合作利益”以及在参与重建过程中的“合理权益”。同时,应明确“结果原则”与责任原则,对增强制度与法律对“故意保护过当”问题的具体约束办法进行探索。这一办法同样应突破单纯道德目的,延伸至制度化、规范化利益操作层面。在安理会统一协调下,应适当考虑扩充执行主体资格,重视区域组织的关键影响力,形成灵活有度、竞争与牵制并存态势,引导合作共赢、共同收益,逐步弱化大国影响的中长期发展形势。(19)
动机与平衡问题属于宏观或中观层面,更注重自利动机的制度化限制与规范。例如,基于多边主义框架的国际介入,一般被认为具有更明确与可接受的合法性;履行R2P责任时用以限制军事行动的区分原则、预防原则、比例原则,已经成为比较明确的国际规范。(20)此外,尽管在国际组织的责任主体资格、联合国与成员国责任分担问题上仍存在某些争议,联合国组织体系在相关行动监督、调查、责任认定以及缓冲意见分歧、协调各国立场、做出最终决策、组织维和行动等方面,无疑具有公认的权威性与正当性。当前,在综合应用国际关系规范理论提供的行动选项方面,国际社会并未取得理想进展,仍停留于原始的、低层次的政治话语争议。只有适当搁置这些抽象争论,恰当平衡强制水平与可预期结果、干预效率与审慎克制、规范与利益、革新与常识等关系,关注切实可行的解决议案,R2P才有望转向“负责任的保护”,获得可预期的进展前景。
*作者特别感谢导师王逸舟教授的悉心指导与细致中肯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完稿日期]2013年9月27日
注释:
①Kofi Annan,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the General Assembly,September 20,1999.
②Francis Deng,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Conflict Management in Africa,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1996; Francis Deng,Masses in Flight:The Global Crisis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1998.
③Ban Ki-moon,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A/63/677,January 12,2009.
④Gareth Evans,"From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o R2P,"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24,No.3,2006,pp.703-722.
⑤David 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No.1,2000,pp.611-39.转引自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64页。
⑥Gareth Evans,R2P: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2008,pp.3-15.
⑦Alex Bellamy,Global Politics and R2P:From Words to Deeds,New York:Routledge,2010,pp.121-135.
⑧ICISS报告的主要贡献者,著名人权活动家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指出:目前R2P概念发展面临概念、制度、政治动员三方面挑战:概念上过宽或过窄理解都可能造成误解;制度上如何确保必要的预警能力、行动能力,强化制度网络:政治动员上如何提高国际意愿和共识,促进及时有效回应。可以看到:这些概括仍然是描述性的,不能对核心难题的解决给予更多帮助。参见Thomas Weis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deas in Action,London:Polity,2007,pp.116-17; Alex Bellamy,"R2P or Trojan Horse,"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19(2),2005,pp.31-54。
⑨Kofi Annan,We the Peoples: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54/2000,March 27,2000.
⑩Alan Kuperman,"Suicidal Rebellions and Moral Hazard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nopolitics,4(2),2005,pp.149-173; Alan Kuperman,"Moral Hazard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52(1),2008,pp.49-80.
(11)具体做法之一,即确认人权亦具有非绝对性质,与主权类同。比如:基于人权的分层性,R2P限定种族清洗、种族灭绝、战争罪、反人类罪作为基本理由,强调这些行为在道义逻辑上不可容忍,而且在绝大多数国际法和国际司法管辖机构中均被视为犯罪,应得到国际介入。这无疑是在人权与主权争执中划定红线,并作出必要妥协的做法。参见Louise Arbour,"R2P as a Duty of Car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4(3),2008,pp.445-458。
(12)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论者提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尽可能避免“附带伤亡”的“双重原则”,大量强调结果与效用。具体标准包括:干预行动本身合法;直接结果在道德上被允许:干预者意图良善,行为节制,不寻求邪恶结果或因之而寻求特定手段:过程参照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善恶对等弥补原则。参见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d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Basic Books,1992; Michael Walzer,Arguing about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Timothy Crawford,"Moral hazard,Intervention and Internal War:A Conceptual Analysis," Ethnopolitics,4(2),2005,pp.175-193; Thomas Smith,"Moral Hazard and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Politics,39(2),2002,pp.175-192。
(13)对于所谓“一致性”问题(人道主义危机国的干预状况并不一致),学者辩称,不能因为无法在所有地方做同样事情,就什么也不做。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仍需要明确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参见赵汀阳:“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25页。
(14)关于R2P概念中的“责任”与“负责”的深入辨析,参见William Bain,"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i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6(1),2010,pp.25-46; Gary Watson,Two Face of Responsibility:Agency and Answerabilit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60-288; Louise Arbour,"R2P as a Duty of Car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4(3),2008,pp.445-458。
(15)在ICISS报告中,相关问题表述是:“国家蓄意行动,或是疏于行动或无力行动,或是一国出现了瘫痪形势”,即提供了军事干预行动的“正当理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未影响本国利益时不得行使否决权”;“通过授权进行军事干预的决议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时不得阻挠”;安理会未作出决议时的替代方案包括联大紧急特别会议审议、由区域组织采取行动等。这未能体现国际社会应有的耐心,而是有可能导致问题进一步复杂化。ICISS,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IDRC),2001。
(16)例如在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当事国政府在干涉行动之前并未屠杀平民,大部分伤亡来自干涉战争本身;西方国家在得到安理会设立禁飞区授权后,公开支持反对派,擅自将打击范围扩大至该国全部军事系统,强推政权更替。为此,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南非常驻联合国大使巴索·桑库(Baso Sangqu)呼吁对“北约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
(17)Robert Jackson,Quasi-States:Sovereign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World,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Nicholas Wheeler,"Legitimat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2),2001,p.566.
(18)关于规范的推进策略问题,相关研究十分丰富,可参见Miles Kahler,"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2(4),1998,pp.919-941。
(19)区域组织的优势在于:在安理会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时,可以规避或绕开投票僵局,解决急迫问题;可以节省联合国行动的物质与人力成本;最重要的是,地区国家间相似的历史经历和安全文化,更有利于问题在因地制宜、尊重特殊性、避免外部势力过分干涉的情况下妥善解决。Alex Bellamy and Paul Williams,"Who's Keeping the Peace:Regio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Peac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29(4),2005,pp.157-195.
(20)Anne Orford,Intern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