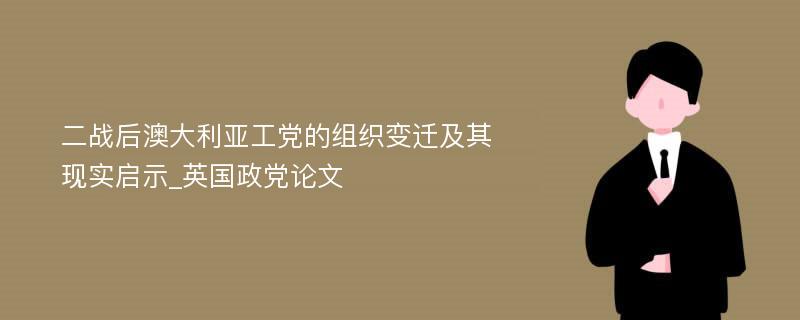
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的组织变革及其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澳大利亚论文,战后论文,启示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大利亚工党成立于1891年,并在1901年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联邦工党。在1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工党以赢得大选为首要目标,始终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尤其是二战以来,基于新科技革命而引发的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新式传媒工具的普及等,使得“陈旧的”工党组织无法同新的社会环境相融合。工党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持续在野①迫使其开始重视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于20世纪60年代正式开启了组织变革进程。本文试对澳大利亚工党在二战后的组织变革进行考察分析,并就其对现代政党组织建设的启示略述己见。 一、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二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不仅使工党组织在二战前原本就存在的问题更加显露出来,而且还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工党在二战后进行组织变革的直接原因。 1.党员结构失衡。二战前,工党主要从工人阶级和社会下层中发展党员,但工党所吸收的个人党员数量极其有限,工党的党员主要是来自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②。以工会集体党员为主体的党员结构存在其固有的弊端。第一,工会对内是工党的集体党员,对外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政策主张和组织机构的独立组织。工会与工党的功能和目标是不同的,工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工会作为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社团,在大多情况下往往只考虑工人的利益。当工会的目标与工党的目标相冲突时,工会优先考虑的往往是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工党的目标,甚至不惜采用激烈对抗的态度和行为来反对工党的政策,这使得工党内部派别斗争十分激烈,难以制定出统一有效的政策。第二,在以集体党员为主体的党员结构下,个人党员的权利容易被忽视,个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这就严重打击了个人党员的积极性。第三,女性、土著人等社会群体因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劳动大军之外,更没有资格加入工会。因此,工党党员在集体党员和个人党员方面的结构失衡,会进一步导致工党党员在性别、人种方面的不平衡,具体体现为白人男性党员在工党党员中占有绝对多数,而女性党员、土著党员的吸收和发展受到了忽视。工党在党员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狭隘性,不利于工党现代形象的塑造。 2.中央权威不足。在地域组织上,工党有六个州党部和两个领地党部,分别对应着澳大利亚的州和大陆领地,各州级党部下辖地方支部③。澳大利亚联邦工党成立于澳大利亚联邦之后,工党的党组织结构因此也是高度联邦制的,相对独立的各州工党支部本身就反对联邦工党将权力集中化的企图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工党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州一级的党组织中⑤。与此相对应的是党中央权威的严重不足。在组织结构上,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⑥,但直到1967年,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只有6个州的党组织各派出的6名代表,一共是36名成员⑦。1967年,时任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在参加西澳大利亚州的州代表大会时指出,澳大利亚工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党组织,澳大利亚工党的联邦机构只有一个全国秘书处加两个排字工人的小组⑧。 工党中央权威的不足对工党凝聚力的发挥是极为不利的,而且极易造成党组织的分裂。从历史上看,工党自建立以来曾经历了三次大的党内分裂。第一次是1916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强制征兵问题上党内产生严重分歧而导致的分裂⑨;第二次是1931年因在制定应对经济大萧条的政策问题上观点无法调和而发生的分裂⑩;第三次是1955年在东西方“冷战”条件下工党内部因对共产主义态度的不一致而再度发生的分裂(11)。尽管工党的每一次分裂都有着特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一致的——工党因中央权威的不足而无法对整个党进行集中协调和统一领导。 3.党内民主不够充分。随着二战后民主诉求的日趋高涨,工党存在的党内民主不充分的问题也便随之浮出水面。第一,基层党员参与直接选举的范围小。以工党领袖的选举为例,由党主席、副主席、书记组成的组织领袖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2),党的各级政治领袖由各级议会的议会党团表决产生(13),即基层党员只能以间接的形式参与到工党领袖的选举中。第二,基层党员无法参与到党内决策中。工党传统的决策体制是,只有州支部、澳大利亚青年工党、联邦议会工党以及其州分会与过半数州的澳大利亚工党有关系的工会,才有权向联邦执行委员会提交议题;在某些特别议题由过半数支部提出且这些议题确实具有全国意义时,召开特别全国代表会议(表决)(14)。工党的这种决策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基层党员基本没有机会参与到党内决策中来。而且,由于全国代表会议中工会代表占有绝对多数,这使得工党决策的结果往往是工会利益的体现,议会党团乃至党的领袖的意志在决策中很难得到贯彻,个体党员的意志更是被排除在外。第三,党内信息沟通渠道狭窄。在二战前信息传播媒介尚不发达的条件局限下,工党的基层党员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报刊、广播等途径来获取党内信息。这种上情下达的单向沟通方式使基层党员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无法将自身的意愿传达给党的高层来影响党的决定。因此,在党内沟通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党将信息强行灌输给基层党员,另一方面是基层党员的集体失语和积极性的减退。 二战后民众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使民众要求参与政治的民主诉求开始高涨。尤其是对于二战后崛起的新中间阶层而言,他们本身加入政党的意愿就不强烈,即使加入了政党也是倾向于通过更加民主的方式参与到党内事务中。在此情况下,工党组织民主性的缺乏便成为了阻碍工党吸收党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党内民主的不充分因此也会成为阻碍工党扩大社会基础的关键因素。 工党在组织方面存在的以上问题是工党同二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相脱节的表现,是导致工党在20世纪50、60年代长期在野的主要原因。当工党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组织变革也就随即开启了。 二、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组织变革的举措及评价 始于1967年惠特拉姆时期的工党组织变革(15),以增强工党的吸引力为目的,始终围绕着壮大党员队伍、削弱工会在党内的力量、深化党内民主、强化中央权力这样一条主线来展开。 1改善党员结构,壮大党员队伍。为了壮大党员队伍,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工党一改向来不注重吸收个人党员的传统做法,不仅鼓励工人以独立党员身份加入工党(16),而且开始从社会上大量吸收个人党员。对此,工党逐渐放宽了入党条件。党纲规定澳大利亚工党向所有接受工党目标并与其他政党或被取缔的组织没有联系的公民开放(17)。为了吸引个人入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工党还采取了多种新的措施。比如将党的入党登记表挂在网上,方便那些认同党的政策主张的民众随时办理入党手续或申请为志愿者(18);通过将“属地支部”改建为“环境支部”、“教育支部”、“维护小企业主利益支部”等“主题支部”的方式增加工党的吸引力(19)。2013年10月新上任的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比尔·萧藤(Bill Shorten),在2014年4月22日发表的题为“重建工党——朝向一个现代化的工党迈进”的演讲中,宣布工党将于2014年7月开始实施“一键式”网上入党申请、设立全国统一的低价党费,另外他还建议某些州应删除民众想要加入工党必须要先加入某个工会的条款(20)。这些措施因降低了个人加入工党的“门槛”高度而增强了个人加入工党的便捷性。 在吸收个人党员的过程中,工党尤为重视对女性党员、土著党员、年轻党员的吸收力度。因为工党发现,随着二战后妇女解放运动和土著人民权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步入了工作岗位并在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土著人也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提升了社会地位。另外,随着澳大利亚知识经济的崛起,很多年轻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优势,在短时间内展示出了自身的智慧和才能,而一跃成为了具有较高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的新锐力量,也成为了构成二战后新崛起的、占劳动人口最多数的新中间阶层的主体人群。在此情况下,澳大利亚工党逐渐增加了对女性党员、土著党员、年轻党员的吸收力度,并重视提高他们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体措施包括:在吸引女性入党方面,一是建立全国劳动妇女组织用于鼓励妇女加入工党、制定并推广一些劳动妇女的技术培训计划、组织会议、促进工党与社区妇女组织的交流、确保妇女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向妇女论坛提名代表等党务工作(21);二是重视提高党内女性党员、议员和高级干部的比例(22),强调妇女党员在党内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23)。在吸引土著党员入党方面,工党建立了由各州的劳工网络联合而成的全国土著劳工网络体系,该网络体系旨在吸引、帮助工党中的土著成员,增加土著居民在工党各层的参与度,增加认同感,培训、支持土著候选人,提高全工党对土著问题的意识,承诺全党党员在更大程度上代表土著居民利益,鼓励土著居民在党的职位上就业(24)。在吸引年轻人入党方面,工党也采取了多种办法。比如,设立网络党支部,在工作场所、大学校园中建立党的组织,允许不到法定选民年龄的青年人参加党内投票活动(25);考虑为青年党员提供党费折扣(26),等等。 澳大利亚工党为吸引个人党员入党而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尽管个人党员的人数会根据工党在选举中的表现而出现浮动,但总体来说,工党的个人党员数量同二战前相比还是表现出了大幅增长。2002年工党的个人党员人数为48334人,2007年达到了二战后的制高点49725人(27);与此同时,工党党员的性别结构、种族结构、年龄结构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均衡化发展,工党党员以往存在的一元化、老龄化特征得到了很大改变,工党组织传统的狭隘形象得到了颠覆。但是,由于工党设置的准入“门槛”本身比较低,加之工党既不注重对党员的教育,也不注重党员作用的发挥,党员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2.调整党内权力分配结构,强化中央权威。针对党中央权威不足的问题,澳大利亚工党采取的主要解决办法是调整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结构和人员规模,以提高党的全国组织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期,惠特拉姆将工党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从之前的12人扩大到17人,其中增加4个联邦议会党团的领袖和1个北领地的工党代表;将联邦工党代表大会的人数从之前的36人增加到了47人,其中增加了4个联邦议会党团的领袖、1个北领地的工党代表,还有其他州的工党代表,另外还特别要求参加联邦工党代表大会的每个州的州代表中必须包括各个州的工党议会领袖(28)。随着后来工党对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代表构成的进一步调整,构成执行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逐渐增多。2011年,工党执行委员会的人数有20位(29),2014已扩大到了26位(30)。工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人数在1981年时有99位成员(31),在1990年时有101位成员(32),到了2011年已达到了400位(33)。通过这样的调整,工党在参众两院的领袖、副领袖成为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各州工党在州众议院的领袖也成为了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当然成员,工党的全国组织的地位逐渐得到了提高(34)。 由于工党采取了调整党内权力分配结构的措施,工党的中央权威也因此而逐渐得到了强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尽管工党党内仍然分为政治立场分明的左派和右派,两大派之下又各有多个分派系,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也从未停止,但工党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再也没有发生过党内分裂,工党党内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工党允许党内派别和派别斗争合法存在的行为,说明工党对中央权威的维护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从长远来看,这无疑会为工党的内部团结埋下安全隐患。因为党内派别的存在在任何时候对于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来说都会构成威胁,尤其是对于澳大利亚工党的联邦制组织结构而言,由于各个州党部具有极大的自主权,党组织本身就相对容易分裂,外加存在于某些州党部的多个分派系同属于一个大派系(35),这样更是加大了工党分裂的危险。 3.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扩大基层党员直接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在扩大基层党员选举权的改革中,工党除了鼓励和支持各州、领地对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行直接选举外(36),还在工党的领导层选举中引入了直接选举办法。工党在党主席、副主席的选举中引入直接选举的时间是2003年(37),而在党魁选举中引入“部分”直接选举则是在2013年7月才进行的改革(38)。尽管工党政治领袖的直选改革时间最晚,但其对工党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因为自工党建立以来,党的各级政治领袖按照往常惯例都是由各级议会的议会党团表决产生和罢免,如果被罢免的领袖时任总理(州长),该领袖应立即辞去政府首脑职位(39)。因此,澳大利亚工党一直存在党领袖选举频繁、不民主的问题,议会党团成员垄断党领袖选举权、普通党员在党领袖人选上缺乏话语权、工党在执政期间以党内程序更换“民选”总理等问题,饱受诟病(40)。2013年7月,重新出任联邦总理的陆克文提出了改革工党联邦党魁的任免方案。根据该方案,联邦党魁由普通党员与国会议员各占50%的选票共同选举产生;如果党魁带领工党赢得了大选,则可在其任期结束之前一直担任党魁;如果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则会自动转入更换党魁的投票程序;工党执政时,如果出现现任党魁辞职或提出重选要求,以及有超过75%的议会党团议员联名上书要求改选党魁的情况,也可重新进行党魁选举;工党在野时,如果有60%的议会党团议员联名上书要求改选党魁,即进行党魁选举(41)。比尔·萧藤在2014年4月的演讲中鼓励各州及领地分部在选举党领袖的时候应该像联邦工党一样采取工党决策委员会和基层党员的意见各占一半的办法(42)。工党对党魁选举制度的这一民主化改革,在扩大了基层党员选举权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联邦工党领导层的稳定性,可有效地避免因工党高层的频繁更换而带来的党内动荡。 在扩大基层党员决策参与权的改革中,工党首先提高了代表大会中个体党员代表的比例。2002年8月,时任工党领袖的西蒙·克林(Simon Crean)将代表大会中的联系工会代表与个体党员代表的配额比例由之前的60∶40改为了50∶50(43)。在2011年召开的第46届全国代表大会所修订的党纲中,工党强调50∶50的代表比例一定要保持(44)。比尔·萧藤在2014年4月发表的演讲中仍然在强调这个比例(45)。工党通过提高党员代表中个体党员代表的构成比例,增加了个人党员在党内决策中的话语权。其次,为了给党员参与党内决策中搭建平台,工党还建立起了工党全国政策论坛以及各州、领地支部政策论坛。全国政策论坛以促进联邦议会工党、党员及分支机构之间关于政策的讨论、发展为主要目标,由来自党的各个部分的提名代表组成,每三年改选一次,负责审核政党纲领、组织政策委员会领导党内的辩论、就政策问题向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执行处提供建议,全国政策论坛每年至少开会三次,且至少在首都之外的城市开会一次(46)。为了使全体党员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在全国执委会的指导下,各州、领地支部都效仿全国政策论坛的形式在省会城市及主要区域中心设立了中心政策支部或论坛,用以向全国政策委员会提供建议,所有党员都有资格参加各个州、领地政策委员会的会议,探讨相关政策议题(47)。各州支部、澳大利亚青年劳工组织、联邦选举理事会、劳工运动策略委员会,以及附属于党的工会组织等机构都有权向全国政策论坛提交议案,作为反馈,全国政策论坛会以书面形式把对议案的审阅意见告知这些机构(48)。这样一来,二战前工党的决策体制得到了根本改变。新体制保留了工党代表大会对党的政策的最终决定权,而全国政策论坛和各州、领地政策论坛的建立和运行,既为工党的中央权力机构与地区党组织之间的直接对话提供了可能,也为广大基层党员直接参与党的决策提供了平台。同时,新的决策机制使得工党中央在决策中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得到进一步增强,州一级的权力得到了弱化,而广大党员与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系得到了加强。但是,从政党选举的角度看,基层党员的参与只能对党内决策起到参考和补充作用,并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大选利益面前,工党会雇佣各类政策专家用于具体政策的分析和制定。 4.利用互联网推进党内各层级的交流沟通和良性互动。二战后,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式传媒工具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为工党拓宽党内信息沟通渠道、增加党内信息沟通方式提供了可能,工党顺势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转移到了网络空间来开展,除了在大选中通过网络平台来解读和阐释党的纲领政策、介绍党的组织原则和机构、宣传党的领袖和公职候选人、收集民意、动员选民等以外,工党还将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了党内事务管理和党内信息沟通中。比如,工党通过创建门户网站(http://www.alp.org.au)在网上吸收党员、吸收捐款、发布党内信息、公布党的新闻动态、组织问卷调查等;通过创设全国范围的基层网络党支部,并在网上公布各级党支部的机构设置及联系方式,来方便基层党员与党组织的日常沟通(49);通过电子邮件(labor@australianlaborparty.emailnb.com)向海内外党员发布党的信息和指示。除此之外,工党领导人还通过私人邮箱、Face book、Twitter等新兴网络沟通平台,就党的内部建设、政策主张和未来发展等问题同普通党员进行交流(50)。 工党通过使用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信息沟通方式,有效地实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及领袖和党员的双向互动,为党员及时掌握党内信息、直接参与党内活动拓宽了渠道,进一步实现了党员的民主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工党在组织建设中对互联网的高度依赖也给工党自身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工党重视“网络党”建设的同时却疏于传统的党组织建设,大量中间层级和基层的组织机构或形同虚设或直接被取消。据统计,工党地方分支机构的数目,2002年为1140个,2006年为1100个,2010年为1027个,地方分支机构数目减少趋势明显(51)。如果中间层级组织机构的减少可被视作工党组织“扁平化”发展之表现的话,那么大量基层党组织的消失则不利于工党组织的长远发展。因为基层党组织所具有的组织、团结、密切联系公众的功能是网络党组织所无法企及的,所以,基层党组织的逐渐减少会使工党面临脱离公众的危险。 总之,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工党从党员结构、党内权力配置、党内决策模式、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变革。尽管工党在二战后的组织变革中存在种种问题,但从整体上看,历经变革的工党组织不仅具有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而且在组织结构、运行方式等方面也具有了更多的科学性和合法性,这有效地保证了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选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52)。 三、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组织变革对现代政党组织建设的启示 “组织的建立与维护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行为,任何政党都必须重视党的组织建设”(53)。澳大利亚工党的组织变革中蕴含着世界政党组织建设的一般经验和规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当今政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1.维护中央权威是政党组织建设的根本前提。澳大利亚工党因中央权威的不足而导致了党内的不稳定,对此,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工党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以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就组织而言,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必要的,因为中央权威是党组织统一政令、指挥有力、行动一致的前提,看一个政党有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关键是看中央是否有权威”(54)。从世界政党现状看,在政党内部实行中央集权、保持中央权威,这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是一个政党组织特点所决定的“铁律”(55)。二战后的西方政党在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将权力向中央层面进行转移的步伐,或者说,西方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过程同加强中央权威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例。欧洲社会民主党党内运作的民主化趋势,与其组织专业化(表现在专职党务领薪官的增多和竞选运动中专门机构的活跃)及权力集中化(表现在中央尤其是领袖的集权)趋势,是并行发展的。社会民主党在决策过程中扩展直接民主的做法,实际上便于以领袖为首的中央层绕过地方组织,通过控制议事日程、选择表决议题、引导讨论等来控制决策,结果自然削弱了中层精英的权限,抑减了它们可能对中央发起的挑战,加强了中央对全党的控制(56)。因此可以说,“集权化是西方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另一明显趋势。即政党权力向中央尤其是领袖手中集中,主要表现为人事权及决策权的集中”(57)。而对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58)。对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在保证中央绝对权威的前提下向下级党组织适度分权;要以严肃的党纪党规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在党的各层级组织中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 2.发展党内民主是政党组织建设的基本要求。党内民主是现代民主社会向政党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政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任何政党的发展都离不开党内民主建设的推动。澳大利亚工党在组织变革过程中虽然没有就党内民主问题提出系统完整的理论,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目的是通过党内权力的合理分配和党员权利的充分行使,把党员个体、党的各级组织等构成工党组织的诸要素有机地联结起来,使党组织能够灵活、高效地运转。从世界范围看,在二战后民主诉求日趋高涨的时代条件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规范党内权力运作、落实党员的民主权利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必由之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西方国家政党,就已经逐渐实现了“党员公决”这一直接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党内民主建设的推动。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在基层党员的选举权和决策参与权的实现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党内民主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从目前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情况来看,离时代的要求和党员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对此,我们应该学习澳大利亚工党在推进党内选举民主化和决策民主化中的有益做法,积极探索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形式,努力实现党内民主的体制化和具体化。 3.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是政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工党为了壮大党员队伍而加大了对个人党员的吸收力度,不仅采取措施吸引女性、土著人这些曾经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入党,更是不遗余力地吸引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新中间阶层人士入党,党员的阶级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种族结构等均得到了完善。党员是政党的细胞和行为主体,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鉴于党员人数的多寡在象征意义和物质意义上均为政党执政提供帮助,因此,西方政党较为重视发展党员”(59)。尤其是面对二战后党员人数下降的客观现实,增强党组织的开放性、在社会各类人群中广泛吸收党员成为了西方政党的普遍选择,西方政党的党员结构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多元化、均衡化发展。但是,西方政党党员的基本功能是在竞选中发挥作用,因此西方政党更为重视的是党员的数量而不是党员的质量。这一点,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来说,是应该避免和引起注意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员质量,党章中规定了明确的入党标准和严格的入党程序。但不容忽视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发展总体上属于粗放式的外延发展,党发展的规模‘硬实力’彰显了,质量素质‘软实力’却没有质的提高”(60)。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的数量,更取决于党员的质量”(61),所以,“在党员队伍规模较大的情况下,要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使党员队伍结构不断得到优化”(62),为此,要“科学确定党员比例和发展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党员数量控制机制,使发展党员工作建立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基础之上”(63)。 4.推行网络党建是政党组织建设的创新举措。从澳大利亚工党的运作方式上来看,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工党审时度势地将党组织的日常工作基本都转移到了网络平台上来开展,塑造起了澳大利亚工党在新时期的网络化、信息化特征。二战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强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各国朝向信息网络社会转变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带来了新的手段和广阔空间。建设“网络党”因此而成为了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大政党的普遍选择。早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社民党就提出了“网络党”的概念,并率先建立起了网站并实现了通过网络办理入党手续(64)。西方国家的“网络党”建设,无论在政治宣传、党务管理,还是在同基层党员的交流互动上都已经较为完善。而在互联网发展较晚的社会主义国家,网络党建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利用网络信息管理系统来进行党员信息管理、收缴党费、转接组织关系等党务管理工作,以及如何利用新兴的社交网络媒介来开展同基层党员的交流与互动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网络党建,不应局限于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信息沟通和组织管理,更需注重利用互联网平台来开拓党员教育、培训以及自主学习的新途径。另外,澳大利亚工党在组织变革中的教训告诉我们,尽管网络党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不可因此而忽视传统党建工作,应该将网络党建同传统党建有机结合起来,应该使两者在相互推进和相互补充中共同服务于党的组织建设。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澳大利亚工党曾于1941年10月至1949年12月之间执政。但齐夫利政府在1949年因国有化、镇压煤矿工人罢工等问题而下台后,工党接连输掉了20世纪50、60年代所有联邦和大部分州的大选。 ②韩隽:《澳大利亚工党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 ③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澳大利亚工党,访问时间:2014年7月7日。 ④韩隽:《澳大利亚工党研究》,第128页。 ⑤沈永兴、张秋生、高国荣:《列国志——澳大利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⑥沈永兴、张秋生、高国荣:《列国志——澳大利亚》.第173-174页。 ⑦刘丽君、邓子钦、张立中:《澳大利亚文化史稿》,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⑧Ross McMullin.The light on the hill: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1891-199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16. ⑨韩隽:《澳大利亚工党研究》,第153页。 ⑩韩隽:《澳大利亚工党研究》,第155页。 (11)韩隽:《澳大利亚工党研究》,第158页。 (12)澳大利亚工党的党组织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领导,各州级党部有州级执行委员会。全国执委会的首脑是工党主席,下设两个副主席,一个书记。此外,各州级党部有州级主席和州级总书记。党主席、副主席的实际职责主要在党组织方面,并负责调停内部纠纷。全国书记和各州级总书记是各级党部的实际负责人,负责党内纪律,竞选时担任竞选主任。变革前工党的组织领袖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澳大利亚工党,访问时间:2014年7月12日。 (13)政治领袖,也称“党魁”或“党首”,是工党在相应层级的实际领导者,因此一般所称的“工党领袖”指的是政治领袖,不是主席或书记。工党执政时,政治领袖出任总理或州长,在野时则担任反对党领袖。变革前工党的各级政治领袖由各级议会的议会党团表决产生和罢免。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澳大利亚工党,访问时间:2014年7月12日。 (14)金太军:《当代各国政治体制——澳大利亚》,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 (15)Ross McMullin.The light on the hill: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1891-199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16. (16)秦德占:《塑造与变革:澳大利亚工党社会政策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17)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51.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18)柴尚金:《变革中政党:国内外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19)姜跃:《国外政党执政面临的几个共同问题及其应对》,《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20)Bill Shorten.Towards a Modern Labor Party,http://www.alp.org.au/rebuild_labor,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21)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41.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22)2011年修订后的工党党纲中规定的公职职位的性别比例为40∶40∶20,即相关公职职位中至少有40%的女性和40%的男性,其余20%可以由任一性别的候选人当选。 (23)秦德占:《塑造与变革:澳大利亚工党社会政策研究》,第61页。 (24)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35.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25)韩隽:《澳大利亚工党现代化进程评析》,《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6)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63.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27)Steve Bracks,John Faulknr,Bob Carr.2010 National Review—report to the ALP National Executive.p.10.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3年5月26日。 (28)惠特拉姆改革联邦工党代表大会代表构成的具体行为,可参考Ross McMullin.The light on the hill: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1891-199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18. (29)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37.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30)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详见http://www.alp.org.au/national_executive.访问时间:2014年7月28日。 (31)Ross McMullin.The light on the hill: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1891-199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399. (32)刘丽君、邓子钦、张立中:《澳大利亚文化史稿》,第149页。 (33)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35.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34)沈永兴、张秋生、高国荣:《列国志——澳大利亚》,第173页。 (35)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澳大利亚工党,访问时间:2014年8月9日。 (36)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64.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37)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39.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38)Caucus votes to support new rules.http://www.sbs.com.au/news/article/2013/07/22/caucus-votes-support-new-rules,访问时间:2014年8月9日。 (39)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澳大利亚工党,访问时间:2014年8月9日。 (40)陈健:《陆克文隐退,澳大利亚工党何去何从?》,《当代世界》2013年第12期。 (41)Caucus votes to support new rules.http://www.sbs.com.au/news/article/2013/07/22/caucus-votes-support-new-rules,访问时间:2014年8月9日。 (42)Bill Shorten.Towards a Modern Labor Party.http://www.alp.org.au/rebuild_labor,访问时间:2014年8月10日。 (43)韩隽:《澳大利亚工党研究》,第313-314页。 (44)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65.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45)Bill Shorten.Towards a Modern Labor Party,http://www.alp.org.au/rebuild_labor.访问时间:2014年8月10日。 (46)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43.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47)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54.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48)参见澳大利亚工党党纲National Platform,P.236.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4年7月16日。 (49)张光平:《西方发达国家政党运用互联网推进电子党务》,《当代世界》2007年第5期。 (50)工党领导人的私人联系方式在工党官网http://www.alp.org.au上均有相关链接。 (51)Steve Bracks,John Faulker,Bob Carr.2010 National Review—report to the ALP National Executive.p.10.http:/www.alp.org.au/,访问时间:2013年5月26日。 (52)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工党曾在1972年12月到1975年11月,1983年3月到1996年3月,2007年11月到2013年9月期间执政。 (53)王韶兴:《政党政治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54)王邦佐、谢岳:《党的作风问题是事关全局的政治性问题——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的体会》,丁锡满:《风正帆悬——党的作风问题研讨论文集》,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55)刘红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耦合与互动》,《理论探讨》2009年第6期。 (56)林怀艺:《政党民主:社会民主党的探索及其启示》,《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57)谢峰:《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功能及发展限度——执政能力的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58)习近平:《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前提》,《人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 (59)谢峰:《西方政党党内民主的功能及发展限度——执政能力的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60)崔桂田:《党员结构优化与质量建设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2012年第26期。 (61)习近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党建研究》2012年第1期。 (62)习近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党建研究》2012年第1期。 (63)陈海飞:《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求实》2006年第10期。 (64)黄明哲、赖路成:《国外政党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实践及启示》,《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