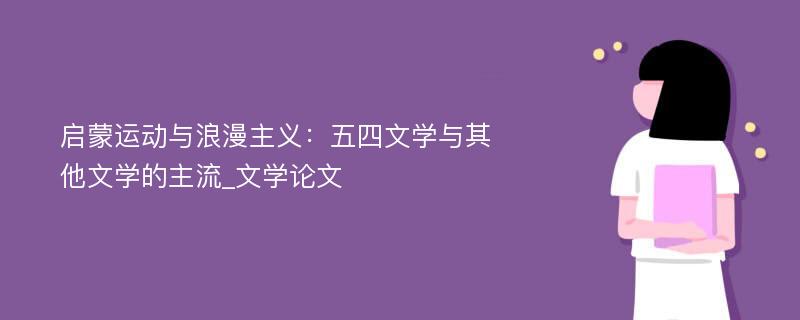
启蒙的与浪漫的——五四文学主潮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潮论文,及其他论文,浪漫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研究五四文学思潮时,我们习惯于把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而这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与之对立的仍有一个庞大且不无生命力的旧文学阵营。分析五四文坛,这无疑是一种意念中的假设。很明显,旧文学在当时不但创作毫无起色,而且理论辩驳也毫无生气。作为强大的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实在是强其所难。
而倒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却不断传出迥异的声音,乃至发展为不同思潮的严重对峙。如果再笼统地以新文学大的标准统称其为主潮,无疑会消弥这事实上的分野状况。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顺应它的感召而诞生的五四“启蒙文学”,因其初步显示的社会革命动机和政治功利追求而成为中国现代独尊现实主义主潮的源头,从而与“为艺术”的浪漫文学分道扬镳。这就形成了五四新文学阵营内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启蒙的与浪漫的。
一、思想启蒙运动与五四文学主潮
在开始进入论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纠正一个错觉。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发轫于“五四”时期的、因引进西方文化思潮而爆发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学革命正是其现实的表现形式。甚至有的论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混为一谈,这当然是一个错误。
事实上,“启蒙”在中国近代的戊戍变法时期已经开始,只是当时的范围还很狭窄,方向还欠明确。只是到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革新乃至革命运动的失败之后,国人面临被“从‘世界人’中挤出”之时〔1 〕,志士仁人们才感觉到其紧迫性和重要性。所以,严格地说,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首先是民族本身长期郁积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历史走入现代后必然的选择。而五四文学革命,如果排除形式方面稍带偶然性的变革,其观念的衍生也不是突兀而成的。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首先是戊戍变法时期,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戏剧改良”等运动。他们视文学为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有力武器,具有浓重的“文学救国”色彩。这种满蓄民族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不但构成了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构成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一个基础。其后,王国维引入叔本华、康德的哲学、美学思想,强调“超然于利害之外”的“文学自己之价值”,反对梁启超等“视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体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文学自觉意识的苏醒。到了《新青年》同仁时期,新的文学观念已基本形成。它兼容并包了先前梁启超和王国维观点的精髓,不但强调文学在开启民智进而在改良社会中的功利作用,而且呼唤一种现代的新文学的诞生。
不难看出,文学在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衍革是顺应“启蒙”需要,在思想启蒙的不断推动之下发生、发展的。只是到了“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为文学的表达工具之后,才显示了其“革命”性意义。
现在我们切入正题。
“五四”,作为近代思想启蒙郁积的一个爆发口,无疑是源于急迫的救亡图存的需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运动的价值取向首先是历史的与政治的,而非文化的、审美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作为近代文学观念衍革的一个飞跃,无疑是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直接呼求和推动的结果。但是,一旦这种新文学得以诞生,它同时就具有了自我的本体意识和独立品格,这就意味着作为新文学操作主体的作家拥有了不同价值选择的权利。而从近代衍革下来的急切的功利追求——审美追求的二律背反模式恰好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应启蒙运动的呼唤和要求,启蒙文学特别重视文学的“器械”作用。傅斯年曾直接地表白说:“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须唤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说晓喻是无甚效力的,必须用文学的感动力。”〔2〕这说明, 启蒙思想运动看重文学的是它的“感动力”,其目的是利用它开展思想革新。鲁迅也曾自我表白:
我也并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3〕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4〕
所以,尽管当时在理论上打倒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呼声很高,但在事实上,启蒙文学不仅变相继承而且又强调了这一传统。周作人期望于新文学的是用它宣传人道主义、辟人荒;李大钊想用它宣传“劳工神圣”、平民主义;沈雁冰提倡用它宣传德谟克拉西。正如郑振铎后来所说,我们反对文艺载那个道,而提倡载这个道。
从理论上讲,界定一个文学思潮是否当时的文学主潮无非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这种文学思潮对时代主潮的切合程度;二是这种文学思潮在当时创作的成果及影响程度;三是这种文学思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学潮流中所处的位置。
很明显,启蒙文学寄望最高的并非是什么现代的新文学的建构,而是国家、民族的新生与强盛。在这一点上,它刚好迎合了启蒙思想运动的时代主潮对文学的基本要求。其创作在当时不但成果丰硕,而且影响相当广泛。先是鲁迅的启蒙小说,它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把唤起民众的觉醒同改造社会人生、改造国民性同探讨辛亥革命的教训,个人解放同整个国民的解放联系起来予以考察;以深广的历史内容、崇高的功利目标和高超的审美追求的实现代表了启蒙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同一时期新潮社作家的创作尽管不乏幼稚粗糙,但也“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5〕。
应该说,真正能体现启蒙文学影响程度的还是一些跨流派、跨团体的创作题材热。譬如“问题文学”热中的“人力车夫”热,就是思想启蒙所呼吁的“平民文学”的直接结果。当时围绕这一题材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著名的有胡适的《人力车夫》、鲁迅的《一件小事》、沈尹默的《人力车夫》、郁达夫的《薄奠》等。尽管作品的体裁、思想意旨和艺术风格不尽相同,但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正是启蒙文学深入人心的现实表现。其它如“乡土小说”热、“民间文学”热、“民俗文学”热等,更把其笔触指向占下层民众上体的中国农村,对农村问题的重视更首先出自于一种社会,历史乃至政治的动机。
宏观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文学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由梁启超开启、中经鲁迅到《新青年》同仁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然后是发生于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革命文学”的倡导,最后到毛泽东《在延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为工农兵服务”为基础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号召。其间,文学的民族功利主义不断地得以明确和加强。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现实主义”由一种先天的偏嗜演变而成唯一的“独尊”,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
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文学观念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前一阶段有必然的联系。而“独尊现实主义”也不仅仅意味着对一种创作方法的强调,更重要的是它所含的对作家思想、政治观念的要求,对作品倾向性和作家现实态度的要求。这样,如果撇开庸俗政治学的负面影响,这种战斗的、有着深刻思想性和鲜明社会时代色彩的“现实”精神,实源于五四时代启蒙文学对社会思潮的自觉映合。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文学更是五四时代当之无愧的文学主潮。
二、游离:五四浪漫主义与启蒙文学主潮
考察一个文学思潮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必须有赖于其“外围”性研究,即回答它与时代主潮乃至文学主潮的关系问题。一个文学思潮与主潮的关系无非是两方面的——对立或游离。前者表示二者水火不容的直接冲突状态;后者指一个思潮既站在主潮之外,有自己的特质,不免与之发生或多或少的冲突,同时它又部分依附于主潮,但也不属于逆流,它是主潮的一个支流。
研究五四新文坛,除启蒙文学主潮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甚至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主潮的文学思潮存在,它就是五四浪漫主义, 1920年,郭沫若充满狂飚突进精神的自由新诗集《女神》和郁达夫满蓄孤冷情绪的小说集《沉沦》相继出版。此后不久,创造社、浅草社、湖畔社等成立,五四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思潮盛极一时,认为它构成了五四文学主潮的观点也有相当理由。一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在当时有它的普遍性;二是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为主题,而最能表达这一主题的就是当时“浪漫的一代”;三是五四浪漫主义创作曾兴盛一时。
但这仍不失为一个表面的、浅层次的认识。看一个思潮是否居主潮地位,不但要看它的影响、它的实际的创作水平,更主要的还要看它与时代主潮的切合程度。表面上看,五四时代的主题是“个性解放”,但事实上它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不但“个性解放”本身服务于启蒙运动,充当它的一个手段,而且在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手段和价值构成。正如论者最近指出的,“个性解放”本身也含有明显的悖论〔6〕, 其出发点、着眼点,仍然在于救亡图存。所以,构成五四时代主潮的不是简单的“个性解放”,而是有着更广更深意义,着眼于社会、历史乃至政治目标的大的思想启蒙运动。
问题仿佛依然存在。既然五四浪漫主义所依附的社会思潮“个性主义”是思想启蒙的一个手段,那么,为什么它不是五四文学主潮的一个有机构成呢?我们认为,其所以只是一个支流,重要的在于它与主潮的“游离”关系。
这种“游离”首先表现在对待文学功利观看法的不同。启蒙文学尽管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尽管它本身也含有建设新文学的文学本体意识,但说到底,它仍是出于反封建的启蒙需要诞生而又服务于这场运动的。所以,它在反对旧文学功利观的同时,又给文学树立了新的功利目标——“改革社会的器械”。而五四浪漫主义则更多地继承了从近代衍革而来的新文学观念中的唯美成份,反对文学的功利目标。创造社认为,文学创作要“本着内心的要求”、“表现自我”,所以“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我们的人生是充满缺陷的不健全的人生,正是艺术精神的美的召唤,我们才“因为想满足我们的艺术的要求而生活”,因此,“我们如把它应用在一个特别目的,或是说它应有一个特别目的,简直是在砂堆上营筑宫殿了”〔7〕。田汉、郭沫若等走得更远。田汉1920年曾借剧作《录光》主人公之口说:“寄托我所爱的只有艺术。”直到1928年他的《古潭的声音》还在表现“艺术不朽”的主题。郭沫若则干脆把文艺比作奇花异木,只为“娱目畅怀”,不为“充饥果腹”。他还称,艺术只要美,有毒也可以,毒草的色彩也有美的价值,有人误服毒草而死,那只能怪他自己〔8〕。
同属于五四浪漫派之列的弥洒社,1923年有宣言曰:“我们乃是文艺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何为而生……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道顺着我们的Inspationl”后来又干脆显明地标出《弥洒》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录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浅草社成立于1924年,主要作家有林如稷、陈翔鹤、陈讳谟、冯至等。其创作除很带点创造社气息之外,也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9 〕。
总之,以前期创造社为代表的五四浪漫主义由于对以鲁迅、文研会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作家对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精神的变相继承感到厌倦(从成仿吾的《〈呐喊〉评论》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对“表现自我”理论的特别热衷;对文学美的特质的夸大及与“人生派”论战时的宗派情绪使他们有意地与“垄断文坛”的新文学主潮脱节,企图以在文学功利观上的不同声音树立自己“异军”的形象,从而为自己在文坛争得一席之地。
其次,这种“游离”还表现在创作取材的不同。五四浪漫派关于创作取材可以两个人的说法为代表。一是郭沫若的“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10〕;二是郁达夫“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真的”〔11〕。“自我表现”和“自叙传”是郭、郁二人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世界所确立的基本命题。尽管内涵不尽相同,但都决定了五四浪漫主义作品的取材多注重从自我出发。小说方面,因多写自身经历、身边琐事、而有“私小说”、“身边小说”之称;诗歌也多抒发一己的情绪体验。他们较少关注启蒙文学特别重视的社会一般人的“悲欢成败”,尤其是农民题材,几乎未曾涉猎。这就从根本上划开了与启蒙文学主潮的距离。
启蒙文学主潮因面向大多数下层民众,必然要求作品题材的广泛。茅盾曾以“郎损”的笔名对民国十年《小说月报》四五六月份的创作作过客观的评估,并对其中98%都是恋爱题材表现出深深的焦虑和不安,并特别暗示,作家在克服公式化脸谱化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农村生活和城市劳动者生活的重视。尽管此后再无人做过类似的统计与评估,但从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看,暗示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在58篇小说中,婚恋题材只占一篇。但翻开同时由郑伯奇编选的“小说三集”,情况却大为不同。在37篇中,只婚恋题材就占20多篇,且又大都是抒发求爱不得的哀伤之情的。这些集子都编选于1935年左右,无论茅盾还是郑伯奇,审美观乃至整个文学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后者,已经放弃了早先的“自我表现”论,已较重视作品的社会、历史乃至政治的意义。这说明五四浪漫派作品中确实很难找到描写下层民众生活的作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取材范围的狭窄。
不妨再以作家或社团为例说明。郁达夫创作小说约40篇,除去三篇作者认为很带点“社会主义气息”的和一篇回敬攻击者的讽刺小说,一篇“普罗小说”,三、四篇充满“夫子气”的寄托小说之外,几乎全部以“我”的经历、感受、情绪为题材。而除去的那些又大都是二七年以后的作品,那时他已很具“写实”味了。可见,郁达夫的创作确可称为“自叙传”了。郭沫若创作小说约20篇,除去《函谷关》等历史小说之外,其它都可以看作是作家起居的“注脚”。就是那些历史小说也大都为“夫子自道”。其它如成仿吾的名篇《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冯沅君的《旅行》、黄庐隐的“游戏人生”小说、王以仁的《流浪》等,也都不出“自我”的圈子。社团如浅草社,以“玄发朱颜、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而著名,代表人物陈翔鹤等公开效仿郁达夫;湖畔社则寄寓湖畔一隅,宣称“我们歌笑在湖畔, 我们歌哭在湖畔” 〔12〕。
客观上讲,启蒙文学对题材的要求确实代表了一日千里的转折时代对文学的历史呼吁。应该说,五四浪漫派的创作是站在主潮之外的。
再次,这种“游离”还表现于作家对待作品中人物态度的不同上。从理论上讲,“启蒙”就是以一种新的、进步的文化价值体系否定乃至取代另一种垂死的、保守的文化价值体系。具体到五四时期,就是以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文化价值观取代愚昧保守的封建主义文化价值观。这中间必然是一种对立、批判的关系。反映到文学上,它要求以现代健全的人格向充满缺陷的人生挑战。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作品,作家必须在对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表示同情之余,对这种悲剧产生的根源和以旧文化在人物身上的表现为代表的主体缺陷,持不妥协的批判态度。鲁迅的《阿Q正传》为此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作家无疑对一无所有而又屡遭失败的的阿Q的悲剧命运持同情态度,但更重要的是, 作家对阿Q 身上沉重劣根性——精神胜利法及其根源的不妥协的嘲讽和批判,才使作品有了新的、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内涵。“哀其不幸”更重要的是“怒其不争”,只有如此才能促其奋争。如果说,在启蒙文学主潮内部,这种批判所需要的“俯视”关系也没有得到普遍实现,那么在五四浪漫主义笔下更无从谈起。在他们的作品中,作者只会把笔下的病态人物置于同等位置,表示同情甚至欣赏,和他们一同落泪、哀叹、绝望。他们俨然在与读者倾心交谈,不厌其烦地诉说自己的穷苦和病态的相思,从而求得同情和暂时的解脱。读者从“同志”般的主人公那里得到的不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而是共鸣乃至摹仿作品中人物行为放纵自我。从这一点上说,作品的消极方面确实毒害了一批人。更重要的是,国家、民族面临新生命抉择的历史机遇,本应成为这种选择的现实主体的一代青年都变成了感伤忧郁的“零余者”,不仅有悖于启蒙文学主潮,也有悖于历史时代主潮。
最后,这种“游离”还表现在二者对待传统文化截然相反的心态上。启蒙运动出于反封建、输入西方文化的需要,一开始就向传统发起了全面挑战。由对礼教、专制制度本身的批判发展为对整个传统基本持全面的否定态度(鲁讯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钱玄同称古文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但是,从他们那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对待中国社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中不难感觉到中国懦家文化的深层积淀。尤其在文学观上,在反对旧的“文以载道”的同时又自觉的继承了其内在精神。所以,传统文化在他们那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矛盾心态:表面的决绝而内在的继承。五四浪漫派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一开始就企图从传统那里寻找契合点,他们不顾一片“讨儒”的怒潮,以个性主义尺度重新肯定了孔子、王阳明等。另一方面,从他们对这些人物学说的重新解释乃至不惜曲解中,我们又分明感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精神的一种本能的厌倦。这样,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们又处于与启蒙主潮截然相反但同样是非常矛盾的二重心态:表面的继承、内在的背叛。
确证了五四浪漫主义与启蒙文学主潮的“游离”关系,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它部分揭示了五四浪漫主义“彗星”现象的历史之谜。处在一个急速变革的历史进代,“一味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13〕,与时代主潮脱节,是不会有长久生命的。历史注定,五四浪漫主义要么“抛弃自我”走入时代主潮、与日益剧烈的社会变革实践相结合(如太阳社、后期创造社),要么“反朴归真”、从远古纯朴的人性和自然的温馨爱抚中寻求依托和安慰(如郁达夫、沈从文等)。
其次,这种与主潮的“游离”关系也开启了中国现代自由文艺运动的源头。
事实上,在现代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自由文艺运动”的问题。它一方面与文学主潮乃至时代主潮脱节,一方面也绝对没有滑入逆流中去,相反,它还从一些方面弥补了主潮的缺憾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五四时期有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此后更有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闻一多、沈从文、戴望舒等。他们无疑存在一个分化和消亡的过程。但这种文艺运动不但为繁荣现代文学创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总的倾向上也与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总任务步调一致。如果再进一步,观照整个现代文学独尊现实主义的实际状况:“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一开始就不仅高度自觉地、而且十分绝对地要求文学起到改造人生、改造社会的作用;二十年代中期提倡‘革命文学’之后,更直接要求文学为实践的政治服务……而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从此得到独尊”,这样,“现实主义,从一种难免跟政治有一定联系的艺术倾向,变成了政治倾向的直接体现”〔14〕。
那么,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乃至整个“自由文艺运动”更表现为一种文学自我觉醒要求的现实载体,就更加难能可贵。
注释:
〔1〕《鲁迅全集》第1卷,3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2〕《白话与文学心理的改革》,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3〕〔4〕《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5〕〔9〕〔13〕《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6〕钱理群、刘纳、夏中文等的文章中都有此类观点。
〔7〕尽管都是一些个人见解,但颇能代表一个团体的看法。
〔8〕郭沫若《曼衍言(一)》《曼衍言(二)》、 《创造季刊》第1卷,第4期。
〔10〕《文学的本质》,《沫若文集》第10卷。
〔11〕《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文集》第7卷。
〔12〕《湖畔》扉页寄语。
〔14〕支克坚《胡凤与中国现代文艺主潮》,《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标签:文学论文; 启蒙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郁达夫论文; 作家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