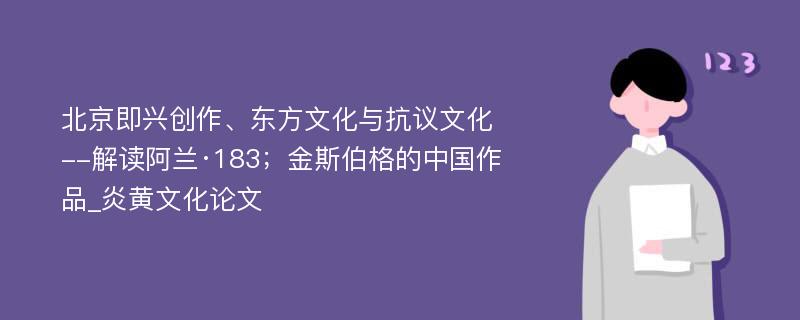
《北京即兴》、东方与抗议文化:解读艾伦#183;金斯堡的“中国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中国论文,艾伦论文,抗议论文,金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3-0122-08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他的名字常常与离经叛道、狂浪不羁、酗酒、吸毒、同性恋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个无所不为的“坏孩子”、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案的“危险分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曾因在窗玻璃上涂写下流文字而被停学;因在宿舍藏匿盗窃赃物而被逮捕,最后被判精神失常而关进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医院。1955年他以《嚎叫》("Howl")一诗闻名美国,逐渐成为那一代诗人的代表人物。1984年他与加里·斯奈德、托尼·莫里森、威廉·加斯、汤婷婷等组成美国作家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除了与中国作家广泛接触,在苏州和西安参观访问外,金斯堡还在中国多所高等院校举办诗歌朗诵会,拉着簧风琴朗诵《嚎叫》。(张子清:11—12;贺祥麟:27—28)在中国期间,他写下了包括《北京即兴》(“Improvisation in Beijing”)、《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One Morning I Took a Walk in China”)、《读白居易》(“Reading Bai Juyi”)等诗歌作品。① 在西方,美国作家代表团访华的经历零星地见诸金斯堡的传记和其他类似文献,但是他在这段时间创作的诗歌鲜有人问津。在中国,金斯堡的中国经历和中国作品被多位学者提及,赵毅衡、张子清、文楚安、贺祥麟、刘岩、朱徽等都曾经对这几首诗做过评介,文楚安还曾经翻译过这些中国作品,认为金斯堡的“中国组诗独具魅力,向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户”。(1994:32)然而,这些诗歌所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讨论。这些学者都给我们以重大启示,但是也留下了一些没有回答的问题。比如金斯堡到底在这些诗歌中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它们对这个异质文化表达了怎样的态度?东方和佛教对金斯堡的诗歌创作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与他的抗议文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本文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文本与真实 1984年10月,金斯堡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参加了一个题为“灵感的来源”的座谈会。根据座谈会的发言纪要,他后来创作了《北京即兴》。在诗歌中,他回答了“我为什么写诗?”这个问题。他说,“我写诗,因为庄子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人,因为老子说过水向山下流,因为孔子说过要尊重老人。”(2007:594)金斯堡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经典表示了浓厚兴趣,对其中观点表达了熟悉和认可。这些观点主要来自他阅读过的西方学者出版的书籍,包括庞德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他说,“我写诗,因为埃兹拉·庞德告诉西方青年诗人/要注意中文的象形字”。庞德的榜样使金斯堡意识到中国诗歌在语言运用方面的特别之处,与自己的诗歌理念不谋而合。 虽然金斯堡到1984年才看到真正的中国,但是他对中国和东方的兴趣始于他事业的早期,1953年他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了日本古代绘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后来他又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艺术书籍中看到中国南宋画家梁楷的《释迦出山图》,从而获得灵感创作了《释迦牟尼从山上下来》(“Sakyamuni Coming out from the Mountain”)。(Ball:386;文楚安,2000:29)1962年他游历了印度和亚洲,在那里他研读了藏传佛教的经典,认为西藏文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文化,如此独特,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开花结果”。(Schumacher:376)这次经历对金斯堡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他在笔记中写道,“我突然感到不愿意受制于那种非人的力量,那种拓展认知范围的道德责任,只想随心所欲,做自己,生活在现在……我突然感到能够自由地爱我自己,也爱身边的人,爱他们本身,爱我自己本身。”(Schumacher:394) 佛教对于金斯堡来说是一个奇特的“灵感”。他说,“我写诗,因为我遵守菩提萨埵的四大誓言”:1,需要解放知觉的造物不计其数;2,自己的贪婪愤怒愚昧没有极限;3,个人的心境多得无数;4,灵魂苏醒的路径遥远无际。也许我们不能理解金斯堡的性政治与“佛陀达摩冥想”有什么关系,但是至少它暗示了金斯堡的思想结构中浓厚的东方色彩。1967年他在意大利拜访了埃兹拉·庞德。在庞德对自己的错误发出了悔恨的自白时,他引用了《易经》来宽慰他,献上了一份“祝福”,表现了一个“犹太佛教徒”的宽宏大量。(Schumacher:492)在1970年代,他结识了一位定居美国的西藏喇嘛,定期参加后者举办的禅修班,奉他为精神导师,取法号“达摩狮”(Dharma Lion),向他学习坐禅和冥思,尝试他所提议的即兴创作。正如诗人北岛在《失败之书》中写道:“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5)② 到1984年为止,中国对于金斯堡来说仅仅是文本化的中国,仅仅存在于书籍之中。他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中国正是当年10月的中国之行。11月,在美国作家代表团返美之后,金斯堡开始在河北大学讲学。正是这次讲学经历,使他对中国有了真正的切身体验。为了授课,他重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并创作了《我如此热爱老惠特曼》(“I Love Old Whitman So”)一诗。他再次被惠特曼的诗意瞬间所感动:“酒吧童的眼神,采石犯人胡须上的汗水,太阳光中的妓女”等等。正如《加利福利亚的超市》(“A Supermarket in California”)一样,金斯堡表达了对惠特曼的敬意,他们之间既是心灵的神交,又是身体的接触:“触摸这本书就是触摸一个人”。(2007:572)惠特曼式的自由诗体裁、绵长的诗行、平行的结构、囊括一切的清单、预言家式的口吻,用金斯堡的话说,这样的诗歌可以让他“无阻碍地呼吸”。惠特曼的诗歌风格的恢宏、思想的包容性,似乎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现象纳入:“我很大,我包含了大众。” 在河北大学期间,金斯堡还创作了《一天清晨,我在中国漫步》一诗。诗歌记录了一名城市漫步者在保定进行的惠特曼式的游逛:他从校园出发,走进街道,甚至深入到这个当时仍未完全开放的城市的深处。我们跟随着他的眼睛,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的一个角落。(2007:573—74)像惠特曼在曼哈顿漫步、在布鲁克林的渡轮上瞭望一样,金斯堡的诗歌运用了惠特曼式的“列举”,捕捉到各种奇怪的细节:在河北大学门口学生们正在“舞剑”;早餐摊上正在出售像“多纳圈”一样的油饼;一辆辆驴车拉着砖头和石头;小贩在摊上出售“香烟”、“中国桔子”,以及“一盘一盘的花生,亮晶晶、指头般大小的冰糖葫芦”;理发匠在路边摆出凳子,在墙上挂起镜子,给一个学生理发,“黑色头发剪至耳朵,齐刷刷横过后颈部”;“煤球”晾晒在人行道上,大白菜堆放在楼前,“等着被取回去下锅”。吸引金斯堡眼球的显然是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生活方式,一种具有他异性的异国情调。 文楚安先生说,“我们丝毫看不到[金斯堡]对中国‘阴暗面’的嘲弄……如果对照他那用强烈的蔑视描写美国城市生活的诗,便不难看出诗人对中国的真挚的感情。”(1994:35)然而,看似用中立态度列罗的各种细节背后却暗藏着不安,暗藏着对中国社会缺乏人文关怀、缺乏尊严以及环境污染的关切:鱼贩“盆里大大小小的鱼头,被砍下、仍活着”;肉摊上,“半拉猪身子放在案板上,两只蹄子往外伸着”;绞肉机绞着牛肉,“白色脂肪红色肌肉和肌腱合在一起被绞成了肉的面条”。这些形象使人想起了痛苦、流血和不人道的屠宰。从工厂的巨型烟囱冒出的“黑色的烟雾直冲云霄”,天空中弥漫着灰白色的雾霾,“隔一个街区,我就无法看见那烟囱”。骑自行车进城的妇女们都用“口罩捂住鼻子和嘴巴”。金斯堡所描写的最令人恶心的场景是一个大型停车场的茅厕:“进入厕所,蹲在一块砖上,排泄你的脏东西/或者站着撒尿,对着一个大洞,里边满是淡黄色的、一小时前拉的粪便,发出咯吱的响声。” 也许金斯堡并不是在刻意丑化中国,也许这些确实是他在中国的所见。他的写实主义描写可能有点令人作呕,但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在《嚎叫》中描写的那些细节也许并不比这好多少。我想他一定是在诗歌中追求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感觉,用戏谑的方式将他的所见所闻呈现出来,以飨美国读者。他有点像传统的西方游记作者,像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所提到的那些法国游记作者,用敏锐的观察捕捉着异国情调:“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行为是怪异性的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东方成了怪异性的活生生的戏剧舞台。”(103) 二、古代与当今 金斯堡看到的“真正”中国,与他在文本里所读到的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对文本中国与现实中国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积极、后者消极。1984年11月在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期间,他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在宾馆里卧床休息时,他阅读了路易·艾黎翻译的《白居易诗歌200首》,写下了《读白居易》(七首)。组诗总体上是金斯堡的中国见闻的回放,看似一时的遐想、细节的杂乱堆砌,没有什么结构,但是在细节背后,在惠特曼式的自由诗行里,包含着金斯堡对白居易的敬意、对中国给予他的特殊照顾的感谢、对成千上万民众的贫穷境况的同情、对故去亲人(父母)和故乡的怀念、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思考、对佛教信仰的重申等等,(2007:574—77)基本上与路易·艾黎的《白居易诗歌200首》的七个部分相对应:1,在人民中间;2,社会与政治诗歌;3,朋友与亲人;4,偶感;5,自然描写;6,妇女命运;7,自我描写。 在诗歌中,白居易的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遥相呼应,金斯堡在古代中国中窥见了当代中国的影子。在第一首中,金斯堡躺在宾馆里,享受着暖气片带来的温暖(“在这个国家这是稀罕的东西”),暖气这个特意为外国人安装的奢侈品对他来说是一种尴尬,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寒冷中发抖”:工人在黑暗中唱歌,用以保暖;戴白色头巾的大婶在保定街边卖柿子;船夫在长江三峡的岩石岸边拉纤;农夫在无锡用竹扁担挑水到菜地里浇水。贫富差异是金斯堡挥之不去的思绪,与那些苦难的人们相比,他是著名诗人,不用做苦力,这更增添了他的负罪感。后来他再次提到他是“来自地球那边的富裕国家”,在中国“享受着有暖气的房间”、优质医疗和特殊餐饮。这些情感似乎都有白居易的《卖炭翁》、《秦中吟》等诗歌的影子,金斯堡的感慨大概是对白居易的著名诗句的回应:“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 金斯堡在白居易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像:“我也是看上去面色苍白,头发稀疏”。白居易与朋友的友谊使他感动得“捂住我的双眼而哭泣”。③在第三首中,金斯堡因为自己的朋友在美国受到迫害而心情沉重,犹如“一只鸡,砍掉头仍在跑,/从脖子喷出的鲜血洒满农家小院”。金斯堡感到自己与白居易有如此多的契合,以至于在第四首中他的思绪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漂到了三峡以西”,漂到了白居易曾经做过县令的四川忠州。白居易曾经以两江汇合为题,表达了一种合二为一、珠联璧合的思想:两只鸟在九月的寒冷中比翼双飞;两棵树在同一片泥土中暗中牵手;两只苹果结在同一枝头。受此启发,金斯堡有“两个思绪在梦中一起升起”的感慨,希望中美两国的友谊能够“合二为一”。 金斯堡不但与古代中国认同,而且对当代中国表达了负面的感受。第五首题为“中国支气管炎”,是金斯堡对当代中国现实的思考。他列举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长江三峡、大跃进、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饥饿、迫害、牛棚、上山下乡等。他深感传统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金莲花秘藏》已经被伤痕文学所代替”,“坐禅冥思受到非议”。在当代,上海女孩梦想着洛杉矶的电影明星;武术气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赞赏;穿蓝布衣服的人很有可能给单位打了小报告。同前几首一样,金斯堡以猎奇的视角,回忆了在广州的市场里,“多汁鲜美的烤全狗”正在出售,“眼睛从面部突起”。在竹制脚手架上,劳动的工人彻夜地喊着“嘿哟、嘿哟”的号子。针对“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金斯堡评论道,从中国历史看,从秦始皇开始,人民群众就是任人鱼肉的对象,而不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足轻重,我们算什么”。在工人“嘿哟、嘿哟”的劳动号子中,金斯堡听出了英文的“绞死你,绞死你”(Hang yu hang yu)。 诗歌最后一首题为“白居易《宿荥阳》的变奏”,是金斯堡对白居易诗歌的模仿。(Alley:303)白居易在诗歌中描述了回乡的经历,对照过去与现在,面对沧海桑田的变化,他感慨万千。金斯堡在他的诗歌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仅仅将内容更换为他自己的童年:他说,“我在新泽西的帕特森市长大”,离家时十六岁,现已五十八。他回忆了故乡的家、街道、商店、他初吻的那个女孩、他的父母等等。这些都已经消失了,“只有大瀑布和帕赛克河像过去那样”静静流淌。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些感慨理解为人生短暂、世事变幻,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正是来自白居易的类似感慨在金斯堡心中引起了共鸣。 三、背景与前景 在金斯堡的其他中国作品中,中国仅仅是背景,而不是内容。在保定创作的《W.C.威廉斯作于我的梦中》(“Written in My Dream by W.C.Williams”)一诗中,他梦见威廉斯正在为他指点诗学上的迷津:“没有必要/装饰/把它打扮成/美/没有必要/扭曲/……使之/被人理解。”(2007:572)诗歌很好地戏仿了《红色手推车》(“The Red Wheelbarrow”)的形式(两行一诗节,一诗节四至六音节,没有标点符号),成功地将金斯堡自己的诗歌理念植入了威廉斯的口中,从而获得了一种诗学上的权威性。同样,金斯堡在昆明期间创作的《黑色裹尸布》(“Black Shroud”)一诗,虽然以昆明饭店的12层为背景,但却讲述了一个与中国无关的故事。1984年12月25日,金斯堡在云南民族学院与师生“愉快地度过了圣诞节”。(张子清:11)回到饭店,他感到一阵恶心,他冲进卫生间,将“油腻的鸡肉”和“发霉的面包”呕吐出来。在他的梦里,他看见母亲冲进帕特森老家的卫生间呕吐。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母亲正经受病痛的折磨,“尖叫并且用头撞墙”。在医生的暗示下,金斯堡拿起斧子,砍下了母亲的头颅。 文楚安先生认为,这个噩梦与事实不符,因为金斯堡素来有“恋母情结”,对母亲感情深厚,在母亲去世后写下了感天动地的长诗《卡第绪》(“Kaddish”)。(1994:37)其实,我们应该看到,金斯堡对母亲存有巨大的愧疚。他不能在身边照顾她,致使她在孤独中死去:“终于——不再孑然一身活在世上——两年的孤独——没一个亲人伴随。”他甚至没有能参加母亲的葬礼。这种愧疚之情在《黑色裹尸布》中异常强烈,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个杀母情节是一个隐喻:强烈的愧疚感使金斯堡将母亲的死归咎于自己的遗弃,自责被转化为一个“杀母情节”。金斯堡的恐怖故事没有结尾,但暗示了他向警方投案自首,他称这个噩梦为“羯磨噩梦”(Karma nightmare)。羯磨在佛教中指“决定来世命运的所作所为”,即此生中的“业”。佛教认为这些“业”将决定该人在转世轮回中上层次或下层次。如果说该诗与中国有关,那么我们可以说,金斯堡的自责心理由于佛教因素得到了放大,以至于成为噩梦。 金斯堡在昆明还创作了《世界的业》(“World Karma”)一诗,该诗虽然表面上描写中国,而它的实际用意不在于此。中国仅仅是一个开头:秦始皇用兵马俑代替活人陪葬;明朝皇帝为了避免其坟墓被盗掘把修墓工匠一起活埋;在现当代中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因为质疑当今的政治或主义而遭到迫害。他还对人口爆炸表示了忧虑,说两百年以后,美国将像中国一样拥有10亿人口,学生将由号码来代替,“六人挤在一张床上”,早晨醒来朝地上吐痰,然后争前恐后地冲向盥洗间,只有一块肥皂。早餐是半块培根,加上麦饼和鸡蛋。虽然他看到的是中国,但是他思考的却是美国。 该诗虽然以中国开头,实际上大部分是在控诉全世界的恶。它谴责前苏联1952年8月12日屠杀意第绪语诗人;美国的地方官枪杀印第安人、中国人、犹太人和黑人;西班牙斗牛士杀戮公牛;法西斯屠杀无政府主义者;法国视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一部分,“不惜杀戮任何不认同的人”,他们向印度支那输入鸦片,使其永远对法国着迷;德国先有皇帝,后有希特勒,还有以科学和诗歌为荣的“一群畜生”,居住在神秘的黑森林,还建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意大利有黑手党,火车从来不正点;穆斯林扩张主义者和一神论者相信他们的神是唯一的神,不信者将被处死,他们不惜发动圣战。在这首诗中,金斯堡把“业”的概念突出了出来,说明世界并不太平,邪恶仍然存在。他以佛教的理念来看待世界的恶,更加深了对恶的理解。在诗中,金斯堡的关注焦点都不是东方,东方仅仅是一个背景。 四、“亚洲使欧洲复兴” 虽然金斯堡见到了真正的中国,但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接触很有限,认知也很肤浅。真实的中国与他所熟悉的“文本化的中国”又如此不同,因此他对中国的描写带有一种猎奇的心态。④中国对于金斯堡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多么好、多么真实,而在于给他提供了一个抗议的渠道。正如钟玲所说,他们“对西方的文化及宗教传统感到不满,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感到不满,而东方的某些文化恰好能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或弥补其缺憾”。(14) 在这个意义上说,东方是金斯堡从50年代开始就在经营的一种“叛逆工程”的一个部分。我们还记得他曾经在《嚎叫》(1955)中以愤青的方式猛烈地批判美国社会和西方文化,发出了垮掉的一代的怒吼。他用现实和超现实的手法表现了那一代人的“挫败感”和“垮掉感”,揭露了美国社会对所谓的青年精英的迫害:他们“被疯狂毁灭,饥肠辘辘赤身露体,歇斯底里”。(文楚安,2000:40)他将美国社会比喻为可怕的巨兽摩洛神(Moloch):正张开大嘴,吞噬着人才、生命和想象力。在《向日葵箴言》(“The Sunflower Sutra”)一诗中,他又将美国比喻为一座巨大的废弃的工场,认为现代工业毁灭了那一代人的灵魂。 有人说,1984年已经五十八岁的金斯堡不再是从前的叛逆青年,不再以正统文化为敌,已经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成员(1973)、美国全国图书奖的获得者(1974)——甚至他还被允许查阅了他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危险分子”档案——但是在七八十年代,他仍然参加朋克运动(punk movement)和反越战的抗议集会,仍然被新一代叛逆青年视为精神领袖,被辍学青年奉为崇拜对象。应该说,他叛逆的精神实质没有改变。放弃西方的正统宗教、转信佛教本身就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叛逆。他曾经多次、在多个场合以弹奏簧风琴为伴奏,口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摩珂迦罗颂》,表演他的佛教信仰,这种姿态本身就充满了叛逆精神。 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入一个更大的背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用东方文化来改造西方文化是金斯堡等一系列西方文人的浪漫幻想,被萨义德称为“后启蒙神话”(post-Enlightenment myth)。(115)这种行为的缘起是对西方文明的不满。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理性、技术和科学促进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致使西方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然而这个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理性和科学导致了物质主义、机械主义和异化,导致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也导致了种族清洗、贫富差异和环境污染等现象。向东方寻求智慧以解决西方的问题,“欧洲通过亚洲获得新生”,(Said:115)在英美文学中有深厚的传统。庞德曾经翻译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和中国古典诗歌,在《诗章》(The Cantos)中他不仅书写和传播中国文化,而且将中国模式视为世界文明的典范。艾略特在《荒原》(The Waste Land)中不仅描写了欧洲文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精神凋敝、宗教衰落和道德沦丧,而且提出了向印度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赵毅衡在《诗神远游》中列举了40多位美国诗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认为中国改变了现代美国诗歌的发展轨迹。 佛教和东方都为金斯堡的叛逆提供了契机和支点,使他得以从外部对美国文化的弊端进行抨击。他的“犹太佛教徒”姿态、他对中国和东方文化的痴迷都向世人表明,美国文化需要改造和更新,从而达到一种抗议和叛逆的目的。因此拥抱东方其实是满足了他自身的一种需求。他完全可能并不在乎这个给他提供契机和支点的地方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地方,只要能够帮助他实现抗议和叛逆的目的,就可以。他吸收东方文化和思想,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为本位,取其所需,而对其他细节视而不见。他书写的是东方内容,探讨的是西方议题。因此金斯堡的中国仍然是想象的中国,是为特定目的建构的中国。我们今天读他的作品有意义,是因为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国人如何认识中国,以及在对异邦的认知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东方化和东方主义化的偏差。 ①这些中国作品共七首,其中六首收录于《白色裹尸布:1980-1985》,一首收录于《都市问候:1986-1992》。(Ginsberg,2007:573-81,594-96) ②金斯堡诗歌的最后一个“灵感”是苦难,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金斯堡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俄国人,加入了共产党,最后死在疯人院。他自己是同性恋、瘾君子,有时还有狂想症。另一方面,他也关心社会苦难:“我写诗,因为东西方百万富翁驾驶着罗尔斯罗依斯小卧车,而穷人没有足够的钱来补牙。”他关心贫富差异,关心蒙古和美国西部的过度放牧所造成的荒漠化、原子弹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希特勒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金斯堡不仅仅是一个自白诗人,还是一个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 ③在第二首中,一名“无知而好争辩”的中国学生不能接受金斯堡的同性恋思想,对他的信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他认为自己纵然有改变世界的雄心,可能什么也做不到:“我为什么要装出一副英雄的模样,/费那么大的劲去完成非人力之所为”?金斯堡的挫折感与白居易在其诗歌中表达的挫败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后者曾经从长安贬谪到江州,然后再贬到忠州,政治抱负一再受挫。像许多中国古代文人一样,他事业不得志,有一种解甲归田、回归山林的冲动。不过,“种豆南山下”多是一种抱怨、一种策略,目的是等待机会出现。同样,金斯堡的挫败感也是一时的情绪,并非彻底放弃。 ④金斯堡1984年对中国的访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认识。他多了一些现实主义,少了一些理想主义。他的“中国作品”向人们展示:中国是落后的,污染是严重的;中国人无视屠宰动物的血腥、残忍和痛苦;传统中国(包括它的思想、文学和宗教)是辉煌的,而在当今这种辉煌已经不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导致了内斗、迫害和贫穷。金斯堡对中国的“性禁忌”表现出了强烈的不解,他说你不能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去告诉一个没吃没喝的人应该做什么。(Schumacher: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