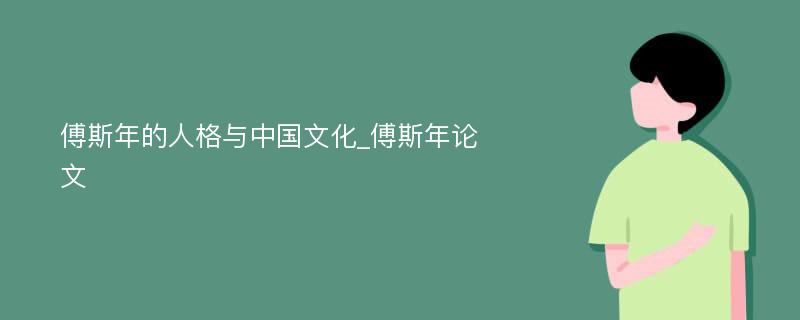
傅斯年人格与中国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人格论文,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傅斯年无疑是其中一个杰出人物。在人们心目中,这位徘徊于学界与政界之间、被胡适誉为人间“稀有的天才”的文人,他的名字,不仅与他那学贯中西、渊博精深的学识和才华紧密相关,更与他的人格密切相联。因此,科学地论述傅斯年的人格精神,不仅对于了解傅斯年其人,而且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塑造和熏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傅斯年的人格精神及其文化特征,略陈管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人格是既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的产物,它“作为人的文化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集合,凝聚着个人自身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多重因素”(注:郭洪纪《儒家德性人格学说对权利人格的僭越》,《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德性人格学说无疑建构了最初的人格观念,并且,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塑造,从古到今始终起着不庸置疑的影响作用。傅斯年人格之构筑,即是一个印证。他出身于儒学世家,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道德意识的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青年时代,他就读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受到新思潮的熏陶。此后,他留学英德七年,研读西方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傅斯年所生活的时代,既是中国新旧交替的时代,又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傅斯年自身的生活经历,使傅斯年在其人格构筑中,呈现出中西文化的许多精神内涵,是中西方知识分子人格的集合。因而,在傅斯年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格内涵中,既不乏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基本情怀,又不乏在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个人主义思想成份。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傅斯年是一个有现代思想又有浓厚传统名节意识的知识分子”(注: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页。),可谓切实、精到。
这是我们界定傅斯年人格精神的基本标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傅斯年是道地的中国人,他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他自幼所接受的文化根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意识在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和熏陶着他。因而,在傅斯年的人格构筑中,虽然聚焦着中西文化的多重因素,但从支配傅斯年一生的价值取向来看,他身上突显的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人格观念。可以说,这是傅斯年人格结构的主导方面。
这亦是我们在分析傅斯年人格精神时所应把握的基本尺度。本文所做的工作,其意义亦在于此。
其实,关于傅斯年人格结构的精神内涵,许多曾与傅斯年一起学习、共事的台湾知名人士在追忆故友时,亦多从傅斯年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儒家德性人格方面进行阐发、议论。如傅斯年的好友毛子水在议及傅斯年做人的大节时曾说:傅斯年有“居心的正直,对国家的忠贞,民胞、物与的胸怀,‘无我、无私’的风度,‘仁义为己任’的抱负”(注:毛子水《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等等。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傅斯年的人格精神及其文化特征,是颇具启发性的。
笔者认为,傅斯年的人格精神及其显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主要层面进行概括:
一、“大一统”观念与维护国家独立的民族情结。
追求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早在上古时期,我们的先哲就产生了朦胧的一统意识。我国最古老的经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其中心内容之一,就是阐释宇宙万物是统一与和谐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但他们在强调一统方面,却几乎如出一辙。儒家的鼻祖孔子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注:《论语·季氏》。)亚圣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一统天下的思想,在回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的提问时,主张“定于一”(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认为天下只有归于统一后,才会安定下来。法家的代表韩非则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注:《韩非子·扬权》。)介于儒法之间的荀子则提出了“笞捶暴国,齐一天下”(注:《荀子·儒效》。)和“臣使诸侯,一天下”(注:《荀子·王霸》。)的主张,并指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注:《荀子·非十二子》。)杂糅百家的吕不韦也认为:“一则治,两则乱。”(注:《吕氏春秋·执一》。)秦汉之际,伴随着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及《春秋·公羊传》传文作者围绕“一统”政治提出的许多政治原则和观点,使“大一统”观念向着不同侧面不断深入和张扬。特别是到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注:《汉书·董仲舒传》。)的政治理论为汉武帝所采纳后,“大一统”观念从此成为中国政治鲜明的价值取向。此后,经过历代帝王和思想家的不断强化、论证,大一统观念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理念,其影响之巨大之深远,至今仍是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和行动准则。
在世人眼里,傅斯年一向被目为自由主义者,如果说,这是傅斯年在西方文化熏陶下追求的一种“小我”或“自我”人格的话,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下,傅斯年则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甚至近乎狂热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这种人格精神(“大我”人格),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观念价值导向的产物。
从傅斯年的言论、著述和行为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傅斯年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因而被时人称为“狂热的爱国者”。他崇尚气节,推崇民族大义,视国家分裂为民族的耻辱,统一为民族的大义,并把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作为“书生报国”的神圣职责。“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北地区,并大造“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的谬论,以使其占领的地区合法化。为了驳斥侵略者的谬论,傅斯年联合几位学者,以书生报国的激情,奋笔疾书,写成《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从民族学、语言学角度,用大量历史资料,证明东北本来是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与这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1932年,傅斯年又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周刊,以其作为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旗帜鲜明的文章,揭露、声讨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制造抗日的舆论。1935年,当日军侵略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时候,在北平主政的萧振瀛召集教育界人士谈话,要求他们对日寇的入侵保持沉默,不要发表对日不利的言论,并以各人的安全为要挟。在座的傅斯年不顾个人安危,当即起立陈辞,痛斥萧振瀛,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抗日,使萧狼狈不堪。傅斯年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对日妥协投降的言行,遭到了日本人和亲日派分子的忌恨,但他不畏强暴,依旧我行我素,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怀。
大一统观念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是社会成员思想的趋同性。傅斯年,这个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知识分子,始终坚持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原则。他认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经常与外族同化,合成一体,中国境内现虽有若干种族,但也正在同化混合的过程中,不足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统一、完整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旋律,任何分裂行为,都必将遭到人们的坚决反对。他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时有不幸,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于外族,或裂于自身。在这时候,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统一,既一统时,庆幸一统,一统受到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复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会上之捣乱分子,视之为败类,名之曰寇贼。(注:《傅斯年全集》第5册。)
傅斯年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以及他爱国的真诚和狂热,在他的日常言论和行为中随时可见。他平生最敬重的是那些具有民族气节、抵御外侮的历史人物。他为其爱子取名仁轨,乃为仰慕唐代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所致。为了培养儿子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他还为不满十岁的孩子书写了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及其他几首诗,其跋中云:
为仁轨儿书文文山先生正气歌、衣带赞,并以先生他诗补余幅。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心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注:《傅斯年全集》第7册。)
傅斯年之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他对自己内心思想意识的真切坦露。
1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当傅斯年在重庆听到抗日胜利的消息后,他高兴地疯了:
从他聚兴村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仗,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注:《傅斯年全集》第7册。)
这既是他生性激切天真的裸露,更是他狂热的爱国激情的宣泄。
总之,在傅斯年的人格内涵中,蕴含着一种强烈的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的爱国情结。这种人格精神,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折射。从小的方面讲,则直接来源于大一统观念的价值导向。
二、群体观念和“以天下为心”的情怀。
做人的道理,不止一条,然最要紧的一条是:不可把自己看重。凡事要考虑别人的利害,千万不可自己贪便宜;做事要为人,不要为自己。自己为众人而生存,不是众人为自己而生存。小时养成节俭的习惯,大了为众人服务。(注:《傅斯年全集》第7册。)
这是1947年傅斯年在为其孩子的纪念册上做的一段题辞,它是傅斯年人格精神及其文化特征的又一鲜明表现,这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群体观念”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以天下为心”的情怀,呈现的是一种“为他”的人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抑或墨家文化,都强调人是合成群体的。如庄子在《齐物论》中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了作为个体的我和整个世界是一体的。既然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那么,维护群体利益便是公,追求违背群体利益便是私,人要超越自我,追求一种“为他”之人格。从《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墨子》提出的“举公义”,到《孟子·滕文公》中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以及张载《神化》中所讲的“无我而后大”等,都强调的是一种为整体献身的精神。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梁启超还把那些对社会群体漠不关心、自居局外、充当冷眼旁观者,视为“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认为“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无血性。”(注:梁启超《呵旁观者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观念虽然有束缚主体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消极作用,但它渗透着那种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确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
傅斯年一生的价值取向是坚持不从政,但这不等于说他因此而成为社会的冷眼旁观者,失去了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恰恰相反,傅斯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一位社会价值的积极建构者。他是以在野的身份,参与政治。他曾经这样放言:“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70页。);“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门里门外跑来跑去”(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544页。);“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者也”(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479页。)。这与孟柯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意毫无二致,正表达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和品格,闪烁着炽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正是因为傅斯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所以他一生敢于仗义执言,“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识何为明哲保身”(注:俞大彩《忆盂真》,《傅斯年全集》第7册。),因而获得了一个“傅大炮”的雅号。他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了许多刊物,如《新潮》、《独立评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并不断地在这些刊物及其它进步刊物上发表政论文章,针对时局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探索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方案。他认为“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我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官污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所以“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这样“才能真正帮助政府”(注: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他在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更是致力于社会的改造活动,“每次会议发言,均以促请政府整刷政风为主”(注: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第56页。)。他不畏权势,连章抨击、弹劾腐败无能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更是他这种以天下为心品格的凸显。
不能否认,由于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傅斯年的人格构成中,有一种追求个人自我意识的个体人格,但是,通观其一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傅斯年对人格理想的追求,却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小我”,放大自我价值的精神。换言之,傅斯年对自我意识的追求,并没有脱离开“为他”的人格,特别是现实生活中他那种在群体观念影响下以天下为心的信念和情怀,更是体现了他以积极的“经纶天下”来实现自我超越的文化品格。
三、向心观念与依附变异的文化品格。
傅斯年是中国“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受“五四”文化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熏陶,傅斯年早年对中国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有较多批判和抨击,极力提倡个性解放,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表现出同传统伦理观念决裂的信念和决心。这一时期的文论,就是他这一心态、品格的印证。但是,傅斯年西洋留学回国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生涯中,他的信仰则更多的返归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方面,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在向心文化观念映射下所体现出来的忠孝思想。
“孝”作为一种“始于事亲”(注:《孝经·开宗明义章》。)的家庭道德规范,可谓每个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情感,并深深地溶入中国人的血液。傅斯年,这位受过民主、平等文化思想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其骨子深处,也无时不蛰伏着“孝亲”的思想意识。他一生对母亲的恭敬孝顺,尽心奉养,正是中国人民大众敬老养亲传统美德在他身上的展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心观念特别强调的是“移孝为忠”,所以孔子讲“弟子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注:《论语·学而》。);“孝慈,则忠。”(注:《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孝”并未局限于家庭的范围之内,而是扩大、延伸到国家社会之上,成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忠”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观念,实际上也就成了这种家庭道德规范“孝”的一种延伸。诚如黑格尔在阐述中国的“孝敬”问题时所讲的那样:“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伦理观念的“忠”,与家庭道德规范“孝”一样,也同样深深地积淀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所谓“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便成为人们行为的内在指针和不可改变的信条。
“忠”之观念,是一个涵盖丰富、意义广泛的概念。其原始内涵,是一种“人们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彻底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出的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注: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先秦时期》,《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这种道德行为的外在表现,就是一种“利他”、“利公”、“利国”之行为。这种原始的忠节观念,也深深地烙印在傅斯年身上,并为他一生践履。诸如他对同志、朋友的忠信、关心、爱护,对工作以及国家、社会的尽职尽责、克己奉公,尤其是上文所述及的他那种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以天下为心的品格与行为,都突显了他这种人格观念。
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又是同构为一体的,国君就是家庭关系中的“父”,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常常把国家、祖国、王朝、君主混在一起,因此忠之观念又是和忠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忠君就是爱国。家国同构,忠君即是爱国,一方面”易激起全民一致对外的激情,确立明确的爱国目标”,但是另一方面,“把封建君主等同于国家、等同于王朝,即使是昏君主持朝政,或者君主为了保住皇权而置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而不顾,虐杀忠臣,为臣者也一味听命、依附顺从,或者至多到犯颜进谏,而决不‘犯上作乱’之意,难以突破王朝框架的限制”(注:罗大文《论古典爱国主义思想》,《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之观念,又造就了传统知识分子折节依附的变异人格。
在傅斯年的人格构筑中,十分明显地呈现出二重人格结构。一方面他非常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受以忠君为核心的向心文化观念的影响,又表现出异常突出的依附人格。后者其鲜明表现就是他虽然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但却始终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视为正统而加以拥护之。在他看来,国民党政府虽有弊病,但它却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政权,因此任何无政府之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即使法国式的‘内阁危机’,也是要不得的”(注:《傅斯年全集》第5册。)。他对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的连章声讨,他在处理1945年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对进步学生代表人物的压抑,都是他这种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
无庸置疑,傅斯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由于受浓厚的传统名节意识的影响,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带上了极大的历史局限性。无须讳言,傅斯年当时是把蒋介石这个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视为国家的代表,所以,他即使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有许多不满,但他的基本立场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这可从1947年2月他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得到说明,信中说:“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70页。)。正是因为他始终把国民党政权视为“正统”,所以现实生活中他只有反对贪官污吏之勇气,而绝无“犯上作乱”之决心。这就决定了他一生难以割舍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而甘愿为之殉节。因而当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因对国民党的不可救药而悲观失望自杀时,傅斯年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也遂生自杀殉国之念,只因俞夫人的爱护防范而未果。但由于受“正统”观念影响,傅斯年最终还是随他目为合法政权的国民党一起迁住了台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傅斯年的人格精神,呈现出对传统伦理观念的高度认同。当然,“道德继承性不会是具体内容的继承,内容随时代、社会、阶级具有极大的差异甚至对抗。但也不只是语言外形式的继承,不只是借用或沿袭道德的名词和概念。实际上继承的应是这种人类心理结构(理性凝聚)的内形式”(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2页。)。傅斯年人格精神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也正是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内形式”的继承,是一种理性的凝聚。虽然傅斯年人格的道德理想烙印着特定的时代特征,并在某些方面(如向心文化观念影响下的依附人格)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如果我们抛开特定的历史内容,而从其人格精神所呈现出的道德价值看,那么,傅斯年人格精神中那种对道义、善美的追求,那种“大公至正”的存心,那种在“以天下为心”精神激发下对邪恶势力的抗争,确实显示出永恒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