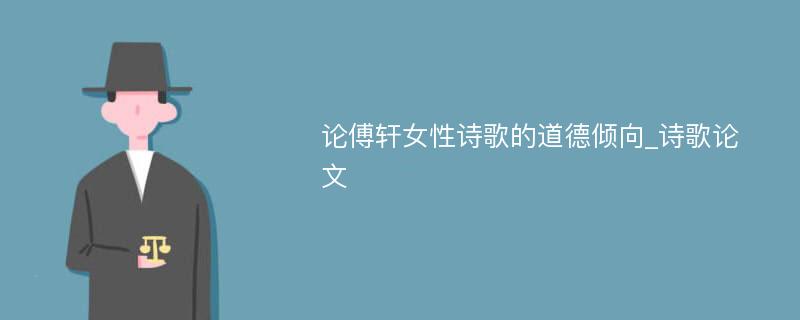
论傅玄女性题材诗歌的崇德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德论文,题材论文,诗歌论文,倾向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3)07-0059-07
“善言儿女”①是傅玄创作的特点。近年来关于其女性题材诗歌研究较多,但是主要集中在其内容、女性形象和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及其“善言儿女”即女性诗多的缘由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女性的品德,即使偶有涉及也主要是关注其儒家的思想,而且多只做事实的概述,有欠系统。其实傅玄的女性题材诗歌有明显的崇德的倾向,本文即就此试做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傅玄生活的时代,儒学不振,玄学正盛,“无为”之风弥漫。作为魏晋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傅玄拥护司马氏,攻击玄学是“虚无放诞之论”,力图挽救儒学济世救时的地位,致力于以名教治天下的理论阐述,强调“慎有为”,在《傅子·内篇》中批评“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并大声疾呼“汉魏之失未改”而推崇道德的力量。他尊儒而不拘,循道而不放,主张援法入儒、儒法兼济,并首先强调礼治,认为礼教是立政使民的根本,从人性的角度提出贵教。这种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推崇封建伦理道德。
一、崇德的表现
傅玄的女性题材诗歌有二十二首,有的同情女性的不幸,如《苦相篇》《历九秋篇》之后六首;有的抒写女性的相思情感如《青青河边草》《车遥遥》《昔思君》等;有的描绘女性的容仪如《美女篇》《艳歌行有女篇》《明月篇》(“丹唇列素齿,翠彩发蛾眉”)等;有的歌咏女性才华如《前有一樽酒行》写宴会上舞女起舞作乐的场面:“丝理东西廂,舞袖一何妙。变化穷万方”[1]559,《却东西门行》写舞女的舞态和舞姿:“丝竹声大悲。和乐唯有舞,运体不失机。退似前龙婉,进如翔鸾飞。四目流神光,倾亚有余姿。”[1]560傅玄女性题材诗歌中赞颂女性美好品德的倾向尤其明显。
(一)描写传统的妇德闺范
此处所谓传统的妇德闺范,主要是指“三从四德”,尤其是其中的“在家从父”和“妇德”“妇言”。“三从”是在家庭伦理上对女性的要求,“在家从父”主要指爱情婚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郑玄所说的“贞顺”是妇德的核心。“贞”是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诚不贰;“顺”就是《礼记》中说的“婉娩听从”,身为妻妇,事夫、事舅姑要恭顺柔和,身为正妻,还要“去妒”,帮丈夫纳妾;郑玄对“妇言”的解释是“辞令”,也就是善于应对,说话得体的意思。班昭认为“妇言”不必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只要说话时考虑言辞是否恰当,不恶言伤人,不抢话、不多言,不使人讨厌就行了。具体到古代女子的生活应当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藏六亲”,就像《诗经》“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这句话中所描述的那样:蛇居洞穴,以安全为吉祥。女子日常生活要深藏简出,决不与人面面相觑……傅玄的《苦相篇》虽然是同情女性的不幸,却在客观上反映了传统的妇德:“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的严守传统闺范、“婢妾如严宾”的不妒之德、“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的对丈夫和公婆的柔顺婉娩和“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的以夫为天……傅玄同时还表现了对男性喜新厌旧恶德的谴责:“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1]555,认为男性的好色、喜新厌旧、不讲信义的败德无行及其影响下的社会风气,是造成有德行的女性不幸的根源。如此符合传统闺范的女性却有着不幸的命运,这样正反两面叙述,在肯定妇德闺范的时候就加深了悲剧的控诉。因此《苦相篇》对女性的同情和对男性败德无品的斥责是交织在一起的。
傅玄同情的是有德行的女性,而对于不合封建淑范的行为,傅玄就在诗中予以委婉的批评或者删改,如《秋胡行》在肯定秋胡妻坚贞品德的同时,也有“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1]556的含蓄批评,认为秋胡妻刚烈的投水自杀行为,不符合女性应柔婉的要求;汉乐府《有所思》写少女婚前的自由恋爱,拟作《西长安行》对这种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遵从“在家从父”的行为不满,就改少女为思妇,婚前的自由恋爱变为婚后的相思;模拟《陌上桑》的《艳歌行》,也删掉罗敷“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和长篇大论的夸夫拒使君“共载”的嬉笑怒骂,因为这不符合“四德”中“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要求,改为“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阙位,愿君改其图”[1]555的言简意赅而应对得体的正面规劝。
(二)歌颂从一而终的坚贞品德
坚贞既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夫妻的情深、恩爱和谐,也表现在特定情景中坚贞不移甚至誓死卫护贞节。前者主要表现为情感生活,如《秋兰篇》和《饮马长城窟行》写女子对远游丈夫“感物怀思心”[1]556的深情挚谊;《车遥遥篇》以女主人公“愿为影兮随君身”[1]565的奇特想象表现其思夫的绵绵情思。后者主要表现在婚姻义务和夫妇的伦理大义。维护贞洁最典型的是《秋胡行》和《艳歌行》,其中有夫之妇秋胡妻和罗敷的拒绝调戏,都表现了对夫妻伦理大义的维护。《秋胡行》中秋胡妻得知桑园赠金者是自己的丈夫时,竟然不惜投水而死;《艳歌行》沿袭《陌上桑》歌颂罗敷谏拒使君“共载”的无理要求以维护婚姻伦理。
即使是弃妇亦“要君黄泉下”[1]557、坚守“生死同穴”的从一而终。如《昔思君》《怨歌行》等诗极写思妇被负心男子抛弃后的无奈、哀怨和孤独,但是她们依然深深地思念,心系薄情人,坚贞不变,很难看到愤怒和决绝,而是抱着破镜重圆、从一而终的幻想和希望、信念:“千秋要君一言,愿爱不移若山”[1]561“甘心要同穴”[1]559“要君黄泉下”。又如模拟汉乐府《有所思》的《西长安行》一改原来主人公“闻君有他心”后将精心准备的礼物“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的决绝之情,而为“香亦不可烧,环亦不可沉”[1]564的软弱留恋。即使不得不面对“妾心结意丹青”而“君心中倾”的现实,也是依然坚守自身的高洁“荞与麦兮夏零,兰桂践霜逾馨”[1]562。
(三)对其他伦理道德的推崇
傅玄不仅张扬传统的妇德和夫妻伦理大义,而且包括封建的道德规范,如孝道礼法、等级制度甚至文人志士的侠义、道义。《秦女休行》记叙了庞烈妇矢志为父母报仇的孝道、勇于报仇的烈义②、侠义和杀死仇人后果敢到官府自首的“不苟活隳旧章”遵循礼法之道义,高赞“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强”。所以清末以蓝鼎元《女学》为代表的女教书中,“妇德”标准更加具体繁细,不仅对妇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详细的规范,而且增加了本是男性应该遵守的诸如“敬身”“重义”“复仇”等对女性自身品德的要求。
儒法两家都以为,贵贱有等、上下有序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等级分配制度,对有效行使封建统治的权力,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既在制度上保障了尊卑之分,也有崇德教化的作用。傅玄在《傅子》中提出了定爵禄之制,强调隆礼尊贤要重德行,即《重爵禄》篇中的“德贵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禄尊官;德贱功寡者,受轻爵小位、薄禄卑官”。刘淑丽认为《艳歌行》中的罗敷不仅拒绝了使君,还申了礼法。作者想藉此劝诫当时社会日益增多的喜新厌旧、藐视礼法的行为,罗敷由此成为当时社会许多家庭女子学习的典型[2]。不仅如此,《艳歌行》的罗敷还是傅玄等级尊卑观念的传声筒。作为太守,在采桑女罗敷眼里,可谓官尊位大,则应该德贵功多。所以傅玄首先让罗敷懂得尊卑有序。虽然同是立场坚定的拒绝使君,汉乐府的罗敷有着太多的不恭和嘲讽,语言和态度都不合乎其身份和礼仪。傅玄笔下的罗敷言行中规中矩:她不仅没有责骂使君愚蠢、嘲笑他不思进取而专好女色,反而自称“贱妾”“鄙夫”,并“长跪”着规劝使君;其次罗敷的讽谏不用酣畅淋漓的侃侃而谈,也不用“侍中郎”很快就“专城居”的更“重爵厚禄”的夫婿来对比和威吓,《艳歌行》消除了《陌上桑》中作弄使君的自由睿智、嬉笑怒骂和夸夫的自信洒脱,这既使罗敷不违“妇言”和等级的规范,又宣传了作者“德贵就位大官尊爵重禄厚”的观点:罗敷只用自己这个位卑而低眉顺眼的民女对比、提醒太守,您是“天地正阙位”——重爵厚禄尊官之大位,“愿君改其图”——理应追求德昭功高!一语足以警醒使君。而且用这种严正庄重的言辞来拒绝才算是以理服人,这种正面宣教的方式和汉乐府的嬉笑怒骂、嘲讽不恭的态度甚至以捏造模糊的尊官显位③来“以暴制暴”相比,才是符合礼义道德的。
二、崇德的方法
傅玄女性题材诗歌崇尚而弘扬伦理道德的方法如下所述。
(一)改造人物
直接将人物再塑造,把人物的自由精神转化为符合统治意志的言行表达,如《西长安行》仿照《有所思》,不仅将恋爱中的少女变为婚后思夫的怨妇,而且将爱深恨深的决绝少女变为温和而道学的贤妇:《有所思》中少女“闻君有他心”后,就将精心准备的贵重礼物“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以毫不妥协的态度表现强烈的感情。但在《西长安行》中,她自语“香亦不可烧,环亦不可沉。香烧日有歇,环沉日自深”,这就失掉了原有的贞节道德与真情的冲突中展示的人格魅力,消解了原作真挚深沉的感情带来的回肠荡气的文气,在“香烧日有歇,环沉日自深”的情感的坚执中加深了对夫妻伦理的坚守,显得平和淡然、温柔敦厚;《朝时篇》“昭昭朝时日”和《明月篇》“皎皎明月光”所写的弃妇怨而不怒,与《诗经·氓》和《古诗·上山采蘼芜》中主人公事同而人物态度不同,完全进入一种道德规范当中。《艳歌行》中的罗敷由机智勇敢的少女变成遵礼守规的封建淑女。《青青河边草》模拟古诗十九首,但抹去了女主人公“昔为倡家女”的身份,而极力塑造一个深情思夫的思妇形象。
(二)直接下定义(定性)或者改动某个关键字词
《艳歌行》直接给罗敷定义为“贤女”;《秦女休行》几次赞扬女休的“烈”并称其为“烈女”:“庞氏有烈妇”“烈女念此痛”“一市称烈义”“烈女直造县门”[1]563“烈著希代之绩”[1]564等,“烈”此处应该指刚直、严正,“烈女”一般指刚正有节操的女子,特指抗拒强暴或殉夫而死的女子。此处应该指重义轻生的女子;在《秋胡行》中,傅玄称道秋胡妻为“节妇”“好妇”:“美此节妇,高行巍峨”“睹一好妇”[1]554。
改动关键字词如《美女篇》曰:“美女一何丽,颜若芙蓉花。一顾乱人国,再顾乱人家,未乱犹可奈何!”[1]565此诗模仿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而将关键词“倾”字改为“乱”字,这就完全改变了原诗的意味,将倾国倾城的美貌女子定性为“红颜祸水”,从而起到劝诫警示的作用;《陌上桑》则改“罗敷前致辞”为“贤女长跪对”,罗敷的从容上前,娓娓夸夫、光彩照人的机智形象,马上就变成了长跪在地、低头乞求的柔顺卑颜而更合妇道。
(三)增加议论或评论,赞扬符合封建道德的义行、反之则批评
傅玄的乐府诗喜欢评价人物或者发议论。有时候在中间穿插议论,如《秦女休行》在叙述完秦女休报仇的事情后,就议论曰:“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更多的是在叙事结束后加上一些议论,从而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叙事+议论”的模式,这些议论多为宣教规劝词句,大多都是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宣扬一些贞节孝悌之道。如《艳歌行》(日出东南隅)增入“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的说教,塑造的节妇罗敷形象,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指出:“傅玄《艳歌行》,全袭《陌上桑》,但曰:‘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盖欲辞严义正,以裨风教。”[3]《秦女休行》结尾与左延年的同名诗比多了议论,以之赞美“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赞颂的倾向固然更为鲜明,但是却给这一壮烈正义的复仇行为抹上了封建“节义”的伦理道德色彩[4];《秋胡行》(四言)叙述事情经过后就对事情进行议论和评价:“玉磨逾洁,兰动弥馨。源流洁清,水无浊波。奈何秋胡,中道怀邪。美此节妇,高行巍峨。哀哉可愁,自投长河。”[1]564,指责秋胡“中道怀邪”和赞扬秋胡妻“高行巍峨”;《秋胡行》(五言)结尾也议论曰“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表现了对秋胡妻维护贞节的“高行巍峨”赞赏的同时,对她耻与丈夫同生愤然投水的刚强性格不符合女性卑顺的妇德进行委婉的批评,这种观念体现了魏晋时期的封建思想。可见傅玄总喜欢在故事叙述后宣教一番,故刘勰说“傅玄篇章,义多规镜”[5]。
(四)材料的选择增删
左延年和傅玄都有《秦女休行》,不管是不是同一本事④,但是主旨相同,同是歌颂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的烈女,可算是同题创作,当时流行的资料也差不多,只是傅诗取材于汉庞淯母赵娥亲的故事,皇甫谧传文详细写了庞娥亲立志复仇的准备和行动过程,交代了杀死仇人李寿后“归罪有司”,使观者慷慨、县长解印、刑尉同情等细节。左诗详细叙写了关吏“呵问”、女休“生为燕王妇,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凄凄曳梏前”和“两徒夹我持刀”的苦楚,而傅诗没写女休报仇后为狱囚的痛苦,而强调观者慷慨、县长解印、刑尉同情的情节。虽然两诗和皇甫谧的传文一样都写了报仇的过程,但是,肉土成泥、血溅飞梁这一场面,却是傅玄诗中独有的[6]343,集中描写了庞氏妇杀人过程“猛气上干云霓”,突出了这场生死搏斗的惊心动魄,显示了娥亲的“猛气”。傅诗不仅仅是客观地复述,而重在“歌咏高风”,主观上是要为这种义烈壮举扬名的。
以上是选择材料及增加内容以表彰节烈,更多的是删改情节以使之符合伦理教化。《拟四愁诗》去掉了张衡《四愁诗》中对美人的思慕与爱恋的倾诉,着力突出美人“刚柔合德配二仪”的典型的儒家道德标准。《西长安行》既去掉《有所思》中幽会的情节描写,傅玄认为恋爱中男女幽会是违背礼教的,于是抒情主人公从乡野走进了深闺,少女变成了怨妇,婚前的自由恋爱变成了婚后的相思;还把“闻君有他心”以下六句表现女子毁烧信物的行为——始而折断(拉杂)再而砸碎(摧)三而烧毁,最后还要将灰烬迎风扬弃,不留痕迹——删去,因为如此果断决绝的愤激行为不符合温柔敦厚之道,因此原来的热烈果决的形象一变为婉娩贞顺。《艳歌行》将《陌上桑》中生动活泼、讽刺意味极强的罗敷夸夫一大段删去,改成了“节妇长跪对,天地正阙位,愿君改其图”,嬉笑怒骂、睥睨凡俗和“使君一何愚”的刚决地维护贞节的方式也一变成温柔敦厚地规劝使君改邪归正,张扬了道德的教化意义。
(五)乐府的回归和改造
傅玄还通过对乐府古辞的恢复与改造来表现其对伦理的注重。如《秋胡行》为乐府旧题,本事见于《西京杂记》和刘向《列女传》,汉武梁石室后壁第一层也刻有秋胡故事。但《秋胡行》古辞不存。曹氏父子的《秋胡行》抒写时事情志:曹操将其用于游仙,曹丕曹植但歌魏德和表现怀人之思。嵇康七首前四首叹人世,后三首谈玄游仙,都不取秋胡事。直到傅玄才将故事原型重新写入乐府,并分别以四言和五言两首来表现对秋胡妻贞烈的歌颂。傅玄使题目与古事相合的回归突出了秋胡妻的坚贞。
傅玄的《艳歌行》对汉乐府《陌上桑》的改写就非常典型。《陌上桑》写采桑女罗敷奚落、智胜太守调戏的过程。曹操的《陌上桑》是游仙诗,曹丕的是从军诗,这些都是汉末建安社会思潮和时事现状的真实反映。傅玄的《艳歌行》则重归汉乐府,除了沿袭题目,在诗歌内容上也是亦步亦趋,甚至直接引用或者化用前作的诗句:如开篇四句仅把“名”改为“字”;夸耀罗敷装饰之语“首戴金翠饰,耳缀明月珠。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也是直接套用汉乐府“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关于居所的描写沿袭曹植的《美女篇》,只是把原诗中罗敷夸饰夫婿省去,改为“贤女”跪地陈说,语气也改从容不迫的规劝为祈求甚至乞求,从而把罗敷纳入封建礼教的规范,使机智勇敢的少女变成遵礼守规的封建淑女。又如傅玄《董逃行·历九秋篇》的“复托夫妇”(见本文脚注①),可见傅玄拟乐府的创作目的在于裨补风教!
三、崇德的原因
傅玄喜欢在诗中推崇封建伦理道德,这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投影。
(一)魏晋世风、士风的影响
魏晋统治者推崇儒学,执行的更是崇儒的政策。魏明帝诏令禁锢玄学、痛斥“浮华不务道本者”之令;司马氏更加以崇儒为务,实行以儒业择士的用人政策,如举寒素制度规定寒族士子要以“学业优博”并“德行著称”者方可入仕,傅玄和张华就是凭道德和文章而仕进的,可见儒业和德行是关系到寒素士子前途的大事。道德学问才是他们的进身之阶。所以崇尚清谈玄风的多是士族而少寒族,而西晋诗人是以寒素士子为主体的。
但曹魏二祖的“好法术”“慕通达”政策和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强烈地冲击着名教的堤防,给仁义道德的礼防以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呈衰颓之势,至西晋朝廷就多是以礼法名教为标榜、而实际德行却污秽难称的士子臣下,如何曾有“孝”行却亏于“忠”德,名儒重臣荀勖等也是道德败坏之徒。总之当时笃尊儒术者少,像傅玄这样致力于弘扬儒术的正统儒者就更少,这对于儒学的素质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都有很坏的影响。司马炎执行宽纵政策,玄学在思想上毫无发明,却在任达纵诞上有很大发展,生活的放纵和道德的放纵相为表里,这引起了社会道德规范的消解和缺失,社会道德、责任的淡漠。所以“纯儒”傅玄有感于时风衰敝,士人的道德沦丧,大声疾呼,希望以尊儒崇德、行“礼义之教”来裨补时弊、匡正世风。并不忘在诗歌创作中不遗余力地借诗以正风化。傅玄描写思妇志节不变、弃妇温柔敦厚,贞妇烈女品质高尚,并且在诗中赞美她们,也许就为在现实中给世人树立道德价值标准。
(二)身世经历和婚姻状况的影响
傅玄创作女性题材诗歌多而且喜欢于其中倡导伦理道德,与其成长、生活环境有关。对傅玄有影响的女性有三个:母亲、继妻杜氏和岳母严宪。傅玄幼年丧父,与慈母相依为命,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处境与命运的感受与关注、思考,远远超越一般文人与官员。加之,壮年丧偶,续娶贤惠的杜氏,杜氏对其前妻之子咸很好。后傅咸出为冀州刺史,因为继母杜氏不肯随之官,就上表辞职。傅玄的岳母严氏,乃是一位见识不凡的女性。她明知傅玄与玄学家何晏等权贵不和,并且在“晏等每欲害之,时人莫肯共婚”的情况下,毅然答应了傅玄求婚。允婚这一举动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此令人格外钦佩。可见,傅玄的家庭婚姻状况对其妇女诗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傅玄所作的大量婚恋诗,其实与作者自身的人生遭际是分不开的。魏明安、赵以武先生在《傅玄评传》中考证推论:傅玄创作妇女诗大致都在年青时期,即正始及以前。这个时期,傅玄刚从不幸的童年、少年时期走过来。傅玄在这类诗歌,生动地描写了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卑微地位与悲惨遭遇。而含辛茹苦的抚育自己成长的坚强的慈母、贤惠的妻子杜氏和不畏强权的岳母,使他除了关注与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外,更崇敬她们的淑德,并在诗中不遗余力地赞颂和提倡。
同时,傅玄作为庶族士人的代表依靠修明经学而跻身仕途,这种入仕模式对于那些长期处于时局动荡之中的微臣下僚而言,无疑是充满了巨大诱惑力的。所以他“尊儒家之道,贵儒学之业”。
(三)性格和思想的影响
傅玄为人刚劲峻急,在玄风盛行、贵刑名、贱守节的大背景下,依然能刚正嫉恶,不尚空谈。在《傅子》中表现了傅玄与玄学人物的对立,如斥责何晏好服妇人之服是“服妖”,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不留情面;正始末,当面挫伤玄学少年王黎、刘陶,指责他俩得意忘形的言行。这是他为权贵所嫉恨、排挤甚至受到何晏、邓飏等迫害的直接原因。傅玄从兄傅嘏于正始中,亦因不与玄学家权贵合作,受到打击迫害,为司马懿保护才免遭不测。傅玄政治上也倾向于司马氏、与玄学权贵对立。司马炎登上宝座后,时为散骑侍郎的傅玄有感于当时礼教不畅,奢靡成风、虚诞肆虐的社会现实,上《举清远疏》请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睦风教节义,屏退虚诞鄙俗之臣,严惩不守礼教之人,被司马炎所采纳。泰始四年(268),傅玄再次上疏,请崇名教,尊儒学。司马炎接受了傅玄的建议,颁诏尊崇儒学,敦喻五教。以孝治天下。[7]傅玄以儒学为主兼宗各家,反对玄学[6]196。傅玄在文学创作中也传承了儒家的文艺观(如《云门篇》“乐以移风,于德礼相辅,安有失其所”),谨守风教,以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创作上的“宗经”使其作品思想向雅正靠拢,因而自然会产生崇德的倾向。刚直的性格和尚儒斥玄的思想、敦风化俗的激切之心,使其不惜一切手段推行自己的思想观念。除了上书皇帝,还通过诗歌创作来宣传教化。傅玄的女性题材诗多为代言体的乐府诗,乐府最初为了“观风俗,知得失”的政治目的而设立的。傅玄通过创作大量贴近社会生活向乐府民歌回归的乐府诗,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
综之,傅玄政治上想恢复汉代的“德治”、强调教化的作用,哲学思想的水性说(人性如水,善恶可以改变,教化可以扬善,刑法可以抑恶)和文学思想的诗教观及对汉乐府精神的继承,加之刚直劲切的性格使傅玄创作上的“以文载道”、用诗歌来扬善行教化以为德治思想服务的实践成为可能。
(四)对《诗经》以来泛德论的继承
当然,除了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也有文学传承的影响。《诗经》就有明显的崇德倾向,开首第一篇《关雎》所歌咏的“窈窕淑女”就是以德统美的标志。杨雄解释“窈窕”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淑”也是指善,“窈窕淑女”是指外秀内美的“淑女”,可见周人赞美女性更侧重于内在的品德,这对中国审美文化的泛德论有深远的影响。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以“道德论”改变了殷商“君命神授”的“血统论”,他们“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庄子·天下篇》)强调“以德配天命”,其伦理观念的核心之一就是“德”。因之周人评价女性是否美丽的最核心标准就是“以德为美”,强调女性的内在精神气质:贤淑娴雅,温柔和顺,庄重矜持。《周南·关雎》追求的是凝重矜持的淑女;《召南·桃夭》亦是要迎娶“宜室宜家”的淑女,《小雅·车舝》强调婚姻关系中要注重女子的德行“德音来括”“令德来教”,《邶风·燕燕》赞赏的是性情温柔和顺的“静女”:“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大雅·思齐》中的三位圣母都是端庄、凝重、有德操的:“思齐(端庄)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好)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美誉)”,因而也是最美的。这些都说明《诗经》的女性美是内德与外貌的统一。汉代班固的《咏史》歌咏缇萦舍身赎父的孝心,《古诗十九首》和古诗中不乏“楼头凝望,陌上相思”的坚贞思妇形象,《白头吟》《上邪》《公无渡河》等表现了女性对爱情婚姻的坚守、热烈、执著,而《陌上桑》将《神女赋》中的神女置换到桑园,并通过改造桑园意象,重申道德礼防[8]。傅玄继承这种对女性品德的张扬,并发展到更广阔的程度,如《秦女休行》对烈义、侠义、道义的强调、《艳歌行》对尊卑上下等级秩序和道德礼仪的遵守。
四、影响和意义
在张华等太康诗人的言情倾向和以陆机为代表的西晋“非政教”的主流诗风中,傅玄在诗中关注和弘扬道德也有其特定的价值,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魏晋以前的女性诗普遍专注于女性的情感,也偶有诗人关注女性道德,但是没有傅玄这么集中而多量,因此就无法形成一种新的倾向。尤其没有傅玄这种有意而为的明显的匡扶时风、为政教服务目的和追求,《诗经·关雎》的所谓“后妃之德”只是后人的解读,而我们不知道当时作者有没有如傅玄这么明确的目的;而且《诗经》、汉乐府和中唐的新乐府等是“美刺”并举甚至偏于“讽喻劝诫”之刺的,傅玄之作却偏于“美”,树立了儒家道德标准的楷模,如罗敷就是贞节的、懂得尊卑有序、言辞得当、言行举止态度都合乎礼仪道德的理想形象,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就指出了诗歌的一种描写的方向,也丰富了女性形象的类型和内涵。
傅玄在叙事结束后议论的表现方式,对以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中唐白居易和近代的革命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力求通俗晓畅而使老妪能解,“其辞质而径”是为了使“见之者易谕也”而更好地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白居易的讽喻诗末尾点题与傅玄的议论一致:如《轻肥》和《歌舞》在叙写了权贵们的豪奢和达官贵人的糜烂生活后,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和“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冷峻的议论作结;《红线毯》诗末以大声斥责宣州太守为议论;《新丰折臂翁》结尾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买花》最后也以田舍翁的叹息与贵族们的千金一掷买花对比等等,都达到了突出主题的作用。近现代诗人丘逢甲、黄遵宪、陈天华和梁启超等都有这种纯粹为宣传某种观念的作品,梁启超还提出了“政治小说”的观念。这种“卒章显志”表现手法有利于宣传自己观点,更好地揭露丑恶或者歌颂理想,达到教化民众、宣传革命的目的。
就像一个硬币有两面,如果这种手法使用不当,可能会使诗歌过于尽露而不含蓄蕴藉,没有余韵;有的作品,因为不是来自于作者自己亲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组织而成,明显地令人觉得真情实感不足,说教意味偏浓。为了达到“卒章显其志”的目的而在结尾以议论点明主旨,也时有画蛇添足之嫌,甚至不免令人有语言太过激切和直白,结果有语尽思穷之叹,有失诗歌的蕴藉含蓄之美。如唐代白居易的某些讽喻诗,宋代的某些理趣诗,近现代的某些政治抒情诗等。如果作者政治教化的功利色彩太浓,就会相应地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使女性形象成为某种道德观的图解,而有概念化、单一化的倾向,如《陌上桑》中机智美丽的罗敷形象在《艳歌行》中变得苍白道学[9],使“思想大于形象”。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就有很多这种理念化的扁平的女性形象,最典型的如元代高明《琵琶记》的牛小姐、(清)随缘下士的《林兰香》中的燕梦卿等。如果过分功利地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宣扬封建忠孝节义,为名教张目的目的,也会使文学作品变成了道德教科书,只有当今的历史价值而缺乏永恒的审美价值。当然傅玄的某些思妇诗能细腻地摹写女性的心理并赞扬其坚贞的品德,如《车遥遥篇》《苦相篇》《短歌行》等,有些诗音节激扬、古质健劲,虽然宣扬封建道德而令人荡气回肠,如《苦相篇》《秦女休行》等极具艺术感染力,这恐怕还与作者缘于身世而真诚地同情女性的不幸、赞扬女性的才德有关。她们与《红楼梦》中的李纨、薛宝钗和袭人以及《醒世姻缘传》中的晁夫人、《野叟曝言》的水夫人等“理想”的贤女、贤妻形象一样,成为兼具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圆形人物形象。这也从反面印证作者应该出之以情而不是出之以理念而创作,应灌注真情、融入经历实感来创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裨补时缺”施行教化而将诗歌作为理念的解说词。
总之,傅玄的女性题材诗有明显的推崇封建伦理道德的倾向。这既与其身世经历、婚姻状况和个人性格思想有关,也是受当时世风士风影响和对《诗经》以来泛德论的继承的必然结果。他主要是通过改造人物、直接下定义或改动关键词、增加议论或者评论、选择增删材料和恢复、改造乐府古辞来实现的,目的是使读者明白晓谕而直接接受其伦理教化。傅玄的这种倾向及其手法对后世有一定意义,并产生了积极消极的双重影响。
注释:
①张溥、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题辞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的《傅鹑瓤集·题辞》中说:“(傅玄)独为诗篇,辛温婉丽,善言儿女……”。明代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6页《诗教·内编》说:“《董逃行》实缘董卓作,然本曲已全无此意。至魏武乃言长生,陆机则感时运,傅玄复托夫妇,咸自足传”。两人都注意到傅玄诗歌较多反映女性生活的特点。
②孔演《汉魏春秋》“州郡莫不嗟叹,嘉其烈义,刊石,以表其闾”,转引自葛晓音《左延年〈秦女休行〉本事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65页。
③汉代的大夫间职位、俸禄悬殊,罗敷因为是随口编造镇吓对方的,所以没有说出具体的职务,如“侍中郎”在汉代也分侍中和侍郎。职位也有差别,但都是皇帝的亲信。罗敷也有意采用模棱两可的说法,给对方造成更大的心理威胁。罗敷的这番夸夫足以震慑到太守,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万一罗敷所言属实那可是后果严重,太守即使有怀疑至少现在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罗敷乘胜追击,夸耀丈夫的英姿风采,进一步在精神上打垮五马太守,让他感到自己不仅位卑职小、官运不佳、趣味低下,而且人物猥琐、自惭形秽,堂堂男子汉读书人,不去济苍生安社稷、树立崇高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或者谋求政治前途,却留恋美色为一女子而自轻自贱“谢罗敷,宁可共载不”,何况这可能会给自己招来严重后果……
④左延年和傅玄的《秦女休行》的本事是否均为庞氏烈妇传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认为是同一本事的主要有: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69页认为左诗是庞烈妇故事的前期状态,傅诗是该故事的后期状态;吴世昌先生《〈秦女休行〉本事探源》(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和《答俞绍初君的质疑》(1980年《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都认为左诗和傅诗都本于《后汉书》《三国志》、皇甫谧《列女传》中庞清母赵娥亲的故事。而葛晓音《左延年〈秦女休行〉本事新探》(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4期)则认为左延年《〈秦女休行〉本事》是陈留郡外黄县女子缑玉为父报仇事,朱立《〈秦女休行〉本事小考》《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6年09期与葛晓音先生一样;俞绍初《〈秦女休行〉本事探源质疑》认为左、傅“二诗主要人物与基本情节绝不相同”,“是用同一题名写不同题材的作品”。赵开泉《“秦女休”释辩》(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和吴浩军《隐括本传不加藻饰——〈秦女休行〉本事及结构》河西学院学报2006年2期与俞绍初先生一致。
标签:诗歌论文; 傅玄论文; 文学论文; 陌上桑论文; 诗经论文; 罗敷论文; 有所思论文; 秦女休行论文; 美女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