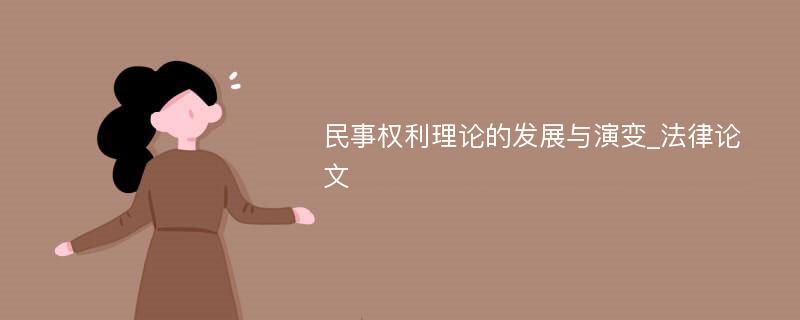
民事诉权学说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民事论文,诉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诉权包括民事诉权、行政诉权和刑事诉权及宪法诉权,即请求国家给予审判保护,属于“司法救济权”的范畴。司法救济权除了包括诉权之外,还包括执行请求权,即请求国家给予执行方面的保护。本文主要考察民事诉权学说的发展简史,旨在探析民事诉权理论的历史发展趋势,为我国建构完善的诉权保障制度,提供历史方面的经验。
民事诉权学说或理论产生于19世纪前半叶德国普通法末期,最早的诉权学说是“私法诉权说”。19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了“公法诉权说”,并发展为有力说。在“公法诉权说”的框架下,“宪法诉权说”已为人们普遍接受。
私法诉权说
私法诉权说(或称实体诉权说)认为,民事诉权具有私权性,是私权或民事实体权利被侵害后转换而生的权利,或者是实体请求权的强制力的表现。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实体请求权是本体而诉权则是本体的影子,即人们按照实体法构成要件享有向他人要求某物的权利(请求权),而这个要求无法满足时就可以向国家提起诉讼。
私法诉权说盛行于公法和公法学尚未发达的“私法至上”时代,存在于民事诉讼法的“私法的解释时代”。这一历史时期的通行观念是“私法诉讼观”,即仅从私法或民事实体法的立场来认识和处理诉讼问题。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民事诉讼仅是借助法院的力量实现私权或民事实体权利的单纯技术性的程序,民事诉讼法仅被作为民事实体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被作为民事实体法的助法或实现法。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诉权看做是私权,是实体请求权的变形或派生物。
私法诉权说的最大局限是忽视了诉权的公权性。根据此说,既然诉权是私权,那么诉权很自然地指向私权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即对方当事人(被告),因而只能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请求而不得向国家法院提出诉求。从本质上看,诉权是向国家法院请求诉讼保护或司法救济的权利,具有公权的性质。
公法诉权说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和政治发展,人们注意到应当加强公共利益的保护;同时,国家权力逐渐强大并开始向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扩张,与之相伴的是公法及其观念和理论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诞生了“公法诉讼观”,即从公法或诉讼法的立场来阐释和讨论民事诉讼问题,认为民事诉讼属于国家公力救济的范畴,民事诉讼法是公法而与民事实体法相区别。
公法诉权说也是从公法的立场来阐论诉权的内涵、性质和保护等问题,主张诉权是一种公权,是当事人对国家法院的司法请求权或司法救济权。公法诉权说经历了从“抽象诉权说”向“具体诉权说”的发展历程。归属于公法诉权说范畴的,还有“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和“司法行为请求权说”等。
抽象诉权说(或称形式诉权说)是作为私法诉权说的直接对立面而产生的。此说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认为诉权是个人对国家的一种自由权,是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利,与讼争的私权或民事实体权利没有关系。此说没有赋予诉权以“请求法院做出具体内容的判决”的内涵,只将诉权界定为当事人请求国家法院进行审判的权利,所以被称作“抽象”诉权说,而被看作从私法诉权说发展到具体诉权说的过渡理论。
具体诉权说(或称实质诉权说)认为,国家将强制性解决纠纷的职能全部收为已有,从而产生了国家对国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保护的义务,国民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则享有请求国家给予司法保护的权利,即诉权。此说主张,诉权是在个案诉讼中原告向法院请求特定内容的胜诉判决(利己判决)的权利,诉权的实体内容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主张,当事人通过行使诉权来请求国家法院保护遭受侵害的实体权利。
就诉讼观而言,抽象诉权说所持的是“诉讼法一元论”,即仅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考察诉权问题。抽象诉权说对私法诉权说矫枉过正了,完全割裂了诉讼法与实体法、诉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否定了诉权的实体内涵和诉讼的实体目的(保护实体权益和解决实体纠纷)。而具体诉权说所持的诉讼观是“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二元论”,即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综合立场来理解诉讼问题。具体诉权说赋予诉权以实体内容,能够合理处理诉讼法与实体法、诉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
但是,具体诉权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合理解释当事人享有请求法院做出利己判决的权利,以及这一权利与诉讼现实、诉讼原理之间的矛盾。德国诉讼法学者标罗批评道,诉讼程序终结前不可能知道原告的请求是否正当,因而在法院判决之前也就谈不到请求法院做出利己判决的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是以原告拥有合法正当的实体权利为基础的。由于无法解答上述难题,具体诉权说在支配诉权领域数十年后而逐渐被扬弃。
日本有学者认为,抽象诉权说所谓的诉权没有具体的内容,故不是权利,而具体诉权说将请求有利判决作为诉权的内容或目的,又过于贪婪,事实上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应当是“本案判决请求权”,由此该学者提出了“本案判决请求权说”。此说主张,诉权是要求法院做出本案判决的权利,即当事人请求法院就自己的实体请求是否合法或正当做出判决的权利,此种权利就是“纠纷解决请求权”,即请求法院在厘清当事人实体请求是否合法或正当的基础上来解决纠纷的权利。
我国有学者认为,诉权不是抽象的权利,包含着具体的程序内涵和实体内涵。诉权的程序内涵是指在程序上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以启动诉讼程序,当事人利用诉权的程序功能将民事纠纷引入诉讼程序中接受法院审判。诉权的实体内涵是指原告行使诉权或提起诉讼所欲获得的实体法上的具体法律地位或具体法律效果,体现原告的诉讼目的。比如,张某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丁某向张某支付某所房屋的价款”,“丁某向张某支付某所房屋的价款”则构成了本案诉权和诉讼请求的实体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诞生了司法行为请求权说(或称司法请求权说),并成为德国目前的通说。此说认为,根据国家法和诉讼法,法院有行使司法权的义务;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实施司法行为,这种权利可称为要求司法服务的请求权或者要求提供司法的请求权(简称司法请求权),因此,法院应当受理诉讼,合法推动诉讼进程,从事实和法律方面审理案件并在裁判成熟时做出判决。若法院拒绝或迟延提供司法保护,则可以通过违宪之诉由联邦宪法法院强制其依法司法。
宪法诉权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维护和尊重人权,签订了一些重要的人权公约。与此同时,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宪法的权威性地位,开始肯定人权(包括诉权或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与此同时,学术界开始从宪法的高度来认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
诸多人权公约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确定为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当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遭受侵犯时,人们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有效的救济。”第10条规定:“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充分平等地获得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的公正、公开的审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中规定:“法院面前人人平等,在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或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时,人们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公开的审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中规定:“在确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与义务或审理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时,人们有权获得依法设立的独立、公正的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公平、公开的审理。”
诸多国家的宪法直接或间接地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为宪法基本权。比如,《日本国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为保护其权利和合法利益,皆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了可由联邦法院审判的案件或争议的3个条件,只要某个案件或争议同时具备这3个条件的,就可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从而间接规定了国民的司法救济权。
宪法学界多肯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基本权地位。我国宪法理论一般认为,诉权是国民在权利和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或妨碍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有宪法学者将诉权作为“司法上的受益权”,其基本内涵是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如遇侵害则可行使诉权请求司法保护。还有学者认为,诉权是消极的司法受益权,即诉权是国民请求法院保护而非增加其权益的权利,仅为消极的避免侵害的权利。在日本,人们将本国宪法第32条所规定的权利称为“接受裁判的权利”,并将此项权利列入国民所享有的“国务请求权与参政权”,强调此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法院不得非法“拒绝审判”。
诉讼法学界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待诉权或司法救济权问题,始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灾难进行反省的德国的司法行为请求说。此说主张,诉权是国民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依照实体法和诉讼法进行审判的权利,现代法治国家原理要求宪法保障任何人均可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受德国司法行为请求说的影响,日本学界根据本国宪法第32条,提出了“宪法诉权说”,将宪法上“接受裁判的权利”与诉权相结合以促使诉权再生,从而在宪法与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成功地建构起宪法诉权理论。
我国诉讼法学界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当事人享有诉权的法律根据首先是宪法,诉权是宪法赋予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以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的同时,也赋予国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所以诉权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的救济权。
在诉权的“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有些人士将“诉权”等同于“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接受裁判的权利”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是内涵更广的权利,除了包含诉权的内容之外,还包含诉讼当事人享有的获得公正和及时审判的权利,即当事人有权获得依法设立、有管辖权、独立、公正的法院的公正、及时审判。《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等所规定的权利实际上就是“接受裁判的权利权”或“获得正当程序审判权”。
小结
诉权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ation)”是现代宪政发展趋势之一,而且日益呈现出普遍性来。诉权学说和制度发展到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诉权是公民享有的宪法基本权,是指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生法律纠纷时,当事人请求国家法院行使司法权或审判权来保护权益或解决纠纷的权利。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具有保护国民之责,承担着在国民的权利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及时保护的义务或职责。在现代权利主导的公法关系里,国民享有请求国家或国家机关履行其职责的权利,比如要求给予公平的对待、请求司法救济、要求公平审判、要求维持治安秩序等。国家或国家机关承担的是必须履行职责的义务或职责,而不是可选择的、以体恤为特征的责任。
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向国民充分开放诉讼制度作为权利救济或纠纷解决的方式,是国家向国民承担的保护义务或保护职责。诉权作为请求国家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请求权,体现了国民(或当事人)与国家(或法院)之间的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承认国民(或当事人)对国家享有公法上的审判请求权(诉权),即承认国民(或当事人)拥有要求国家给予利用诉讼制度的公权(诉权)。因此,在诉权与审判关系中,诉权主体是国民或当事人,义务主体是国家或法院,即国家或法院承担着保护诉权的义务或职责。
尽管我国宪法没有规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但是从我国宪法有关法院及诉讼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已加入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这些事实,均可看出我国宪法事实上是肯定并积极维护国民(或当事人)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不过,笔者一直主张,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诉权或司法救济权,从而突显诉权或司法救济权的宪法性地位和价值。将诉权或司法救济权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实际上也是让法院承担“不得非法拒绝审判”的宪法上的职责,从而通过法院履行其审判职责来有效实现国家“保民”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