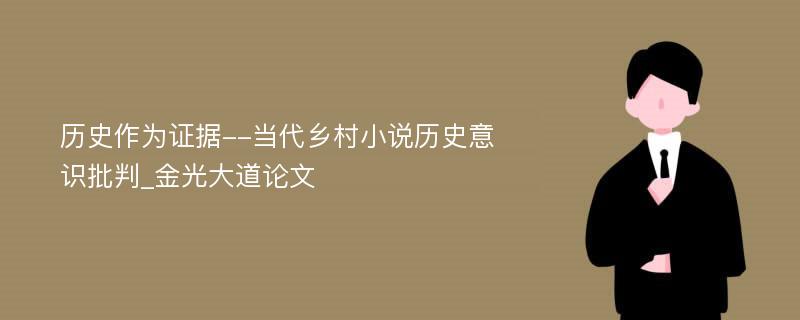
历史为证——当代农村小说历史意识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为证论文,当代论文,意识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迄今为至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史,以当代中国农村生活为审美对象的当代农村小说,无疑是其间影响最大之一者。“文革”前的十七年间,这类小说和革命战争小说最令人注目而同享盛誉。《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不能走那条路》和《李双双小传》等的盛名显赫即可为证。“文革”中,小说创作暗淡萧条而几近荒芜,但却有一部当代农村小说即《金光大道》闪闪发亮。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虽很快复苏而至百花齐放,但题材优势不再明显,而当代农村小说仍一如以往影响非常。在姑且谓之的“伤痕”、“反思”、“改革”诸阶段,在名目众多的小说流派和品种中,当代农村小说创作不仅数量丰硕且佳作频出。《满月儿》、《李顺大造屋》、《乡场上》、《陈奂生上城》、《月食》、《心香》、《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镢柄韩宝山》、《内当家》、《卖驴》、《黑娃照相》、《爬满青藤的木屋》、《种包谷的老人》、《赔你一只金凤凰》、《麦客》、《哦,小公马》、《一潭清水》、《五月》、《满票》、《支书下台唱大戏》等等可谓一批作品先后荣获全国奖(确实有点举不胜举),无疑极能说明问题了。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作为农民占全国人口比例最高而高得在现代社会已成为落后标志的国家,作为农业文化占据民族文化主潮的国度,生活于中的小说家们关注农民命运顺理成章。也正如此,当代农村小说创作的得失问题也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毋庸置疑,人们对当代农村小说的创作已关注不薄。但同样无疑的是有不少问题还需继续探讨。比如《金光大道》的再版及其引发的问题,就非常需要我们联系历史来一起审视。关键还在于,当代农村小说历史意识上所隐含的一些规律性的失误和缺憾,实在还需要勾沉和解析。而这正是我想在此尝试的。
一、为什么要这样轻率?
如果说文学的历史意识是作家经由作品而显示的对某个特定历史的把握与评价,那么当代农村小说历史意识,便可以说是当代小说家们经由作品表现的他们对中国当代农村历史进程与社会变迁的审视、感觉与评判。
说起这个问题,人们谈得最多的便是所谓“历史局限”。是的,历史局限是一个显然的事实。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历史唯物论者。比如《创业史》人物的某些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比如《李双双小传》中的极左意识,比如《艳阳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这确实都是因当时的历史所致而人们已说得不少。对这些历史局限,我们的确不能过于苛求作家。然而我们却又能不对这样一个问题发出决不是苛求疑问:为什么要那么轻率地评估历史?是的,说“轻率”决非危言耸听。当时不少小说家们的确是轻率地在进行历史评判。
众所周知,建国后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陆整个农村和全部农民的选择的事件,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全新的陌生事物。唯一的借鉴大约就是原苏联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可是有多少中国人去认真研究过它呢?因此,对于农业合作化这一既重大又陌生的历史变革,人们都应该抱以客观而慎重的态度。哪怕它当时很快显示了某些优越,也不能盲目乐观,而应该冷静地分析其长远发展。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人民公社是金桥,毛主席指出路一条。贫下中农跟党走,千军万马上金桥。”“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跃进新村风光好,人间天堂连呀连起来。”诸如此类的“爱社歌”。
普通的大众百姓未加思考地就这么齐声大合唱起来,那么我们的作家们——“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是不是要慎重些呢?结果并非如此。作家们的思考或许不像“爱社歌”那么轻松欢快,但历史意识上的认同则并无二致。换言之,他们同样笃信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历史的一种具有永恒性过程。也正如此,柳青谈到《创业史》时才充满自信地宣告:“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①赵树理也才肯定地认为农业合作社“还是应该扩大”,而抵触者则应该批评。②
浩然更干脆,直接就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样的灿烂词汇作为其小说题名。这其间,也有一些能够正视现实本来面目而不那么轻易欢歌历史的文艺作品出现,如海默《洞箫横吹》与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这样的剧本。但即使这样的作品,也并不否认农业合作化运动具有历史的永恒性,也断定它该是“金光大道”。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任凭想象和臆测的历史评判?这是今天的我们需要严肃思索的关键问题。显而易见,领袖意志论,权力意志论,思想的盲目性和驯服性,文学屈从政治主宰的工具论,这等等都极大地左右了作家的创作意识。“文革”后有两个著名的“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其思想实质早在十七年时期就存在了。当时农村小说历史意识的简单绝对化,当时国人和作家们无条件地绝对地相信“毛主席指出路一条”便必然是“金光大道”的事实,不能不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不少问题简直无法解释。只有是绝对迷信领袖指示和红头文件的政策号令,才会出现像“柳青却近乎天真地以为梁生宝经过了‘1952年冬天的整党学习会’,经受了县、区领导同志的开导和教育,就获得了‘社会主义觉悟’,就具备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的性格特征’”③这种问题。而对于浩然来说,领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号令,直接就作用到其小说《艳阳天》的情节主线结构。一旦作家的创作思想只是受制于政治号令而不是以独立的主体眼光来审视历史的客观运行,历史意识的盲目便无法避免,历史判断的轻率便极易产生。可悲的是作家本人却还完全不觉。这不能不是文学创作的悲剧和荒唐。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构成,无疑也应是艺术的审视对象。而这种审视,理应具有独立性和尊重艺术规律。倘艺术只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如何有艺术呢?
二、如何看待“生活真实”
据载,浩然多卷本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一九九四年秋在北京书市出售后引起人们关注。对此次以整体风貌再版《金光大道》,浩然本人表示:“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不应该受到责怪,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况且“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对它留有美好的记忆。”④早在十多年前,浩然就曾对一家当代文学史的编撰者们表示过类似看法。他声辩说,《金光大道》“早在五十年AI写作过大纲,文化革命前写出了草稿”,而“‘高大泉’等人名和书名都是当时拟定的”;其间“所描写的生活情景和人物,都是我亲自从五十年代现实生活中汲取的,都是当时农村中发生过的真实情况”。⑤作者的意思很明显:一是反对人们后来将“高大全”这种“三突出”的人物塑造法归始于高大泉形象;二是强调《金光大道》为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无可非议。
如果说浩然承认他在“文革”中修改这部作品难免受到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影响而留有种种遗憾,我们还可以不惊怪作品中明显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数。如果说作者还并不忌讳高大泉形象的拔高化,人们就会觉得作者还能够正视自己过去创作的缺憾而不失客观。然而作者不但没有什么自我批评的意识,反而以“反映了生活真实”来强调作品无过。这也好,因为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认可作者声称的他写的内容“都是当时农村发生过的真实情况”,我们也不能也无法肯定《金光大道》所显示的那些历史缺憾。我们要追问的是:作家是如何看待这种“生活真实”?
众所周知,尊重生活真实是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如实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是作家责无旁贷理应如此的追求。然而文艺创作作为一种主体性很强的审美活动,它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描述并不是被动消极的,必然存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与感受,必然存在作家对生活的把握和评价。“真实地写出生活真实”,这自然也是一种主体意识。但这种忠诚生活也同样带有主体个性的审美感受和思想认识。审美不可能是一种“镜子式”的反射,而总是对客观世界有所选择有所分解。对于浩然这位形势意识很强,创作上明显地具有“紧跟”特色(如《百花川》与《西沙儿女》的创作)的作家,可以肯定,他的创作不仅不会“纯客观”,而且会表现很强烈的“主体意识”——“紧跟”就是一种主体选择。
这一说问题就明显了。写“生活真实”,首先存在一个主体意识的评判问题。总不能肯定以丑为美的荒唐而反对以丑为丑的客观吧?是的,这就牵涉到价值尺度的问题,即什么是丑什么是美的判断问题。然而,再怎么尺度不一,总不能说吹牛、说谎、欺骗、专横、愚昧这些东西是美的吧?总不能将“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⑥这样现实情形意吹成“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⑦吧?
浩然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都是以欢呼的态度来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错误地估价形势而阻碍了生产发展的极左路线的,而且都以同一模式即以阶级异己分子、党内走资派(所谓“党内代理人”)、落后群众与“当代社会主义英雄”(如萧长春和高大泉)的矛盾和斗争为情节主体结构。至于当时带有明显冒进性质和脱离实际的空想色彩的公社化运动,浩然的作品更是十分欣赏。一九五八年中央的北戴河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作出并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中竟有这样的乐观:“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对当时连温饱问题还远未解决的中国农村社会作出这样的预言,实在是不可思议。而这种不可思议的估价与政策,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前也并非鲜见。对于所有这些极左思潮,浩然的作品却总是热烈欢呼从未批评过。这难道以写了“生活真实”而理直气壮得起来?
在中国当代农村五十年代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众人有走集体主义道路脱贫致富的追求,出现了一些梁生宝式的先进农民人物,产生了李双双这样的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无私者,这应该说都是生活真实。但是,正像《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所描绘的,当时农村也严重存在脱离现实的狂热、愚昧的幻想、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等另一些很糟糕的真实。而“大呼隆”作法和搞极左运动等亦为事实。所有这些生活真实都摆在作家面前,写什么样的真实及欣赏什么样的真实,就很能表现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水平了。作为历史进程中的形形色色的真实,作家的审美选择及褒贬扬抑,实质上与作家的历史意识紧密相关。即这上面正能体现作家对历史的估价。
三、关于“英雄”塑造
塑造“当代英雄”或“社会主义新人”,曾是当代农村小说众多作品共同追求的目标。十七年时期是这样,新时期一批以农村改革为题材的小说也是这样。前者如梁生宝、李双双、萧长春、高大泉等,众所周知不说了。后者像《内当家》、《玛丽娜一世》、《赔你一只金凤凰》、《哦,小公马》、《支书下台唱大戏》等作品,都极力歌颂了改革年代的农村新人如何杰出。浓墨重彩中,女子英姿不凡的巾帼英豪,男子则文武双全胸怀大志,都远远超过一般寻常农民的素质。虽平凡但英雄,抑或说一定要在普通中见出不凡,已成为当代农村小说写英雄树新人的流行模式。有意思的是,新时期的作家其实都知道十七年时期塑造英雄的这种缺憾,可在改革热潮的激扬中却又往往不自觉地重蹈了“拔高”旧辙。最典型的恐怕是蒋子龙《燕赵悲歌》中对农民改革家、“当代怪杰”武耕新形象的塑造。武耕新文蹈武略运筹帷幄的勃发雄姿,实在可以说是“改革文学”中的一位“高大全”。如果说蒋子龙呼唤改革的急切之情令人可敬,这种武耕新式的人物塑造显然理想化了。
我们不妨先从现实实例来作点反思。
1982年秋,一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曾专门访问了柳青生活过十多年的皇甫村,见到了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当年的农村英雄,如今不但穷困潦倒,而且斗志全无:“我今生再无所求,只希望生产队里在柳青墓旁给我二分地,让我住在那里守着他过完这辈子。”⑧英雄末路,并不仅仅因为“文革”中的迫害折磨,还在于英雄本身缺乏适应现代社会变革的种种素质。传统的文化心理与脱离现实的时代狂热,使“梁生宝”不可能那么高大伟岸。只能凄凉的怀旧则显示了艺术世界中的“当代英雄”,实在只能活在艺术符号中而与现实人物差距甚大。这不是否认艺术的理想性,而是我们不能不发现理想脱离现实的缺憾太触目惊心。
梁生宝形象的拔高化似乎还不及武耕新这位“当代怪杰”。我不能肯定大赵庄与武耕新在蒋子龙的描绘中,有多少因素是源于天津大邱庄的现实。但似乎是有所联系的。现实中的“中国第一村”大邱庄如何呢?是很富,可这种富却令人寒心地与封建家族统治、封建庄园模式联系一体。“庄主”禹作敏,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优秀农民企业家之一者,当他在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舞台上大显身手、大受青睐的同时,却做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颇有点阿Q革命成功后的模样。女人,金钱,权力,这都是想着“革命”成功后随便打小D咀巴的阿Q所热衷的。禹作敏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永贵这位曾红遍全中国、走向了国际舞台的“当代农村英雄”又如何呢?陈永贵可以让昔阳人和大寨人只“迷信两个人”(毛泽东和陈永贵),让人们“誓死和陈永贵团结在一起”,让农民喊出“谁要是胆敢动他的半根毫毛,我们就打他个落花流水。”⑩到后来,昔阳县完全成了以陈永贵为首的“家族统治”下的地盘了。陈永贵以后,山西还有个李计银。这位“全国劳模”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例子远不鲜见。这些曾在建国后农村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风云人物的角色,所以最终都走向了可悲的结局,除其他种种原因,关键就在于自身的素质还远不完满。他们虽然无疑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虽然能够在某些特殊历史情境中脱颖而出,但他们长期生长于中的农村环境与农业文化的整体落后性,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挣脱旧文化的束缚而以新的姿态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变化。加之使他们成为“当代英雄”的驱动力中,实质上夹杂了不少非科学因素。如唯心的狂热,如极左的愚昧,如狭隘的实用意识,如盲目的教条。传统的负重与现实的束缚,使这些农村的“当代英雄”、“社会主义新人”很难避免悲剧的发生。他们既是旧文化的中毒者,亦是旧意识的害人者。他们可能一时成功,但很难作出不断的超越。而不断地超越旧我,却正是现代科学社会的必须。
艺术不等同现实。也不能拿现实来“丝丝入扣”艺术。但无论如何,现实生活是检验艺术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统。况且,中国当代农村小说的作家们又老是声称他们的创作“尊重了生活真实”。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当代农村小说关于“当代英雄”的塑造,往往是脱离了现实实情的。这种脱离,一是艺术的主观拔高,二是对现实的理解太表浅。而这两者尤其后者,便都与作者历史意识的浅显和偏颇相关。想想中国历史上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永未成功,想想当年鲁迅笔下的阿Q们是那样麻木不仁,想想当代中国农村的现实,我们的确有些奇怪浩然们为什么将农业合作化运动及领头人描绘得那么金光灿烂。一场远远未触及到封建文化根本的革命,怎能一下子全无了阿Q?怎能一下子蹦出了似乎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农民英雄”?匪夷所思!
四、历史就是历史。
其实也并非匪夷所思。既然是以唯心的、盲目的、浅薄的甚至是愚昧的历史意识来估价历史的进程,既然是“单纯时代传声筒”地“写中心”,既然常常是根据“指示”、“语录”、“文件”来创作,既然连彭德怀如实地反映农村现实也被视为大逆不道,既然“两个凡是”还能在“文革”后一段时间成为国人的金科玉律,又有什么荒唐不会发生呢?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无论它是丑陋荒唐还是堂皇正大,它总归要赤裸在人们面前,它终究会在不断的延展中让人们比较,它不可能让科学退出舞台而让愚昧把守。对当代农村小说历史意识的反思,也使我们能够确信这一点。是的,历史总是“当代史”,当代人的视野与评价也存在种种局限,但除非当代人有意歪曲历史,通常情况下他们对历史的反思总有个有利前提:对象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倘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中国当代农村的历史事实则已经证明中国当代农村小说所显示的历史意识存在不少遗憾的迷茫。
历史很难重演,文学却要反省自身。历史还要前行,作家则必须认真看待前车之鉴。
注释:
①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8月号。
②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6月号。
③、⑧陈美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第127页,128页。
④见《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再版》,《作家报》1994年10月8日。
⑤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第2卷第155页。
⑥彭德怀诗《故乡行》。
⑦“大跃进”民歌,引自王新民《一九五八年民歌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倾向》、《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4期。
⑨《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造神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