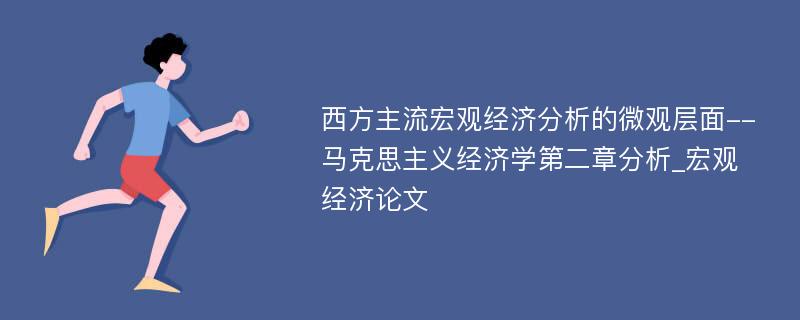
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析#II,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种马论文,微观论文,经济学论文,经济分析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宏观经济分析一般是以总量研究方法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所谓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是指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博弈论为主要分析工具,研究微观经济中的个体行为方式及其约束条件,并用个体行为直接去解释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过这种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的方式所创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完全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①。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这一巨大变化,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是“一场革命”,有的学者则认为是一场“反革命的复兴”。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在这方面作点探讨。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
就主流思潮而言,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分析大致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宏微观经济分析合一,到新古典学派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否定;再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创立的第一个宏观经济学体系,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这里侧重探讨西方宏观经济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虽然在个别问题上涉及宏观经济问题,但是,其三个基本假设(即货币中性假设、供给创造需求假设和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性的假设)堵塞了对宏观经济的全面分析。面对宏观经济层面严重失衡的1929-1933年大萧条,新古典学派毫无作为,其理论也就自然被人们所抛弃。凯恩斯对新古典学派理论的危机作了这样的分析:“古典学派把从鲁滨逊经济体系中得出的这个结论”,即“不存在交换;个人用于消费和保存起来的收入,实际是而且也只能是他自己生产活动的产物”,“用错误类比的方法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从而“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构成了“全部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②这显然“不符合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现实”。③为“避免现存的经济形式完全被摧毁”,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学派的二分法,“把货币理论推展成为一种总产量理论”,并突破其单一的个量分析,“专注于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变动的一种基本研究”,④以寻找“经济力量或经济因素的自由运行所需要的环境,以便实现生产的全部潜力”,⑤从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创立了第一个宏观经济学体系。具体来说,在凯恩斯看来,一国的总产量或总就业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或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市场力量不可能使后三种变量恰好同时处于实现生产的全部潜力或达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水平。实际上,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导致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即预期利润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他说,“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特别是能使我们称它为周期的时间过程和时间长短的规律性,主要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我相信,经济周期最好应被当作系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的变动所造成”,因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⑥1929年至1933年,“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于治理”。“资本边际效率已经崩溃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致利息率下降到现实上可能做到的水平都无济于事”。⑦由于“就业量(因而产量和实际收入)是由企业主决定的,其动机在于谋求他现在和将来的利润的最大化”,⑧而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必然导致非自愿失业量增加。这样,“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⑨由此,凯恩斯认为,有鉴于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为甚的下降,“安排现行的投资的责任决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而应“由社会控制投资量”,即实施一项“旨在取得最优国内就业水平的国家投资计划”。⑩显然,这样的国家投资计划会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但凯恩斯并不认为货币量的增加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他认为,在未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货币量的增加,主要会导致就业量或产量的增加,其次才会引起供给无弹性的产品的价格上升,但不会引起一般物价水平上升,而只会形成“半通货膨胀”(semi-inflation)。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增加的货币量已无增加就业量或产量的作用,只会导致一般物价水平同比例的上升,从而形成“真正通货膨胀”。因此,充分就业是真正通货膨胀的临界点。在达到这个临界点之前,“货币数量的扩大的作用完全是程度问题,从而在过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在哪一点画出一条分界线并且宣称,该线表明通货膨胀的到来。”(11)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实现过充分就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未出现过真正的通货膨胀。现实情况往往是通货膨胀与未充分就业并存。凯恩斯的“半通货膨胀”不过是一种乐观的幻想。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凯恩斯对西方宏观经济学进行彻底革命的时候,他的同事和追随者也发动了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即将微观经济学建立在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如果凯恩斯把他的宏观经济学建立在这种不完全竞争的微观经济学之上,那么,也就不会在他死后出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争。为什么凯恩斯没有这样做呢?老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认为“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其实,这个谜并非难以解开。谜底在于凯恩斯产生了一种理论错觉。客观地说,凯恩斯理论的科学贡献在于探讨了在现实的生产能力小于潜在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微观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宏观环境,从而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但是,这种成功却使凯恩斯产生了一种理论错觉,以为他的理论是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新古典学派理论的“假设前提”只要被凯恩斯理论所替代,它就可以从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转变为适用于一般情况。他说:“我们对已被接受的古典学派理论的批评,重点不在于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设条件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得到满足”。(12)如果说,总产量是取决于市场以外力量的话,那么,除此之外,古典学派关于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性的分析,以及生产与分配的分析都是正确的。实际上,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除了在反对公有制、维护私有制的问题上能找到共同点外,两者在核心观点上是完全不相容的。比如,如果你赞同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这一新古典学派的核心观点,那么你就必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而主张自由放任。如果你赞同投资必须社会化,从而政府必须干预经济这一凯恩斯理论的核心观点,那么,你就必然会认为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凯恩斯却将他的国家干预主张与新古典学派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观点相安无事地糅合在一起,竟对两者间的矛盾毫无察觉,反而认为“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13)凯恩斯在理论上的这种错觉,既阻碍了他去创立一个与其宏观经济理论相适应的完整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尽管他在《通论》中作了一些与其宏观经济理论相适应但又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又导致他对其同事和追随者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革命视而不见。
二战后,萨缪尔森等人沿着凯恩斯的思路,将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并借助菲利普斯曲线将“凯恩斯的乐观幻想”变成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主张,形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中的新古典综合派。而琼·罗宾逊等人则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中的新剑桥学派。在二战后的20多年里,主导西方经济学并对政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凯恩斯主义,只是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代名词。而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琼·罗宾逊及其新剑桥学派则被边缘化了。另外,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大体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代表人物为伦敦学派的哈耶克。哈耶克早在1931年出版的《物价与生产》一书中就认为,经济理论的主要命题“是以知悉个人决定的假设为基础的。正是借助于这种‘个人分析’法,我们才能对我们所获致的经济现象有所了解”。(14)如果试图“在货币总量,一般物价水平,乃至生产总量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则会导致“为害匪浅的结果”。(15)因为“各种总量本身对个人的决定从不发生影响”,而“事实上,无论各种总量之间或各种平均数之间都不能相互起作用,亦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像我们在个别现象、个别价格等等之间所能够做到的那样。”(16)当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哈耶克就认为他与凯恩斯的“真正的分歧在于”“宏观分析”上。(17)他说,“《通论》的主要意义是,它决定性地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崛起和微观经济理论暂时的衰落”,但“这一发展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凯恩斯“要对宏观理论的趋势负责”。(18)哈耶克1988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仍然坚持他在1931年提出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可以利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有关不同物品之可用总量的‘宏观经济’知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它甚至没有什么用处。对由大量不同的、有着形形色色组合方式的商品所组成的总产量进行测算的任何想法都是错误的”。(19)二是基本肯定凯恩斯的分析方法,其代表人物为新货币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虽然弗里德曼利用自然失业率假说对凯恩斯的未充分就业与半通货膨胀的关系(或菲利普斯曲线表述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从而与凯恩斯“思想的核心背道而驰”,但是,他基本上接受了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方法,并认为“脱离凯恩斯式思维方式是有害的”。(20)正是基于这些,弗里德曼在1966年2月4日致《时代》杂志的信中说:“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在另一意义上,现在没有人再是凯恩斯主义者。”(21)三是以探索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为切入点,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其代表人物为理性预期学派的R.E.卢卡斯、T.J.萨金特和R.J.巴罗。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哈耶克的“总量经济学毫无用途的信念被逐步瓦解”。(22)而弗里德曼的新货币学派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则在里根政府时期受挫。这意味着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都未能在理论上给予凯恩斯主义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对凯恩斯主义具有实质性打击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形势。理性预期学派正是借助了这种经济形势,才有机会给予凯恩斯主义最后一击,从而在理论上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中,本文更注重分析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
卢卡斯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前,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曾“试图献身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此,想借助“对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工资—价格部分建立‘宏观经济基础’对凯恩斯主义正统观念作贡献。”(23)1973-1975年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滞胀”问题,把“凯恩斯的乐观幻想变成恐怖的恶梦”,(24)西方政府各种经济干预政策的失效,使人们更加坚定了对“市场解决办法”最优性的信任。于是,卢卡斯便从“献身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转向投靠新货币学派,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进行严厉的批评”。(25)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学需要微观经济基础的看法已经成为常识。尽管人们对这一需要的本质及满足这一需要意味着什么还认识不清楚”,“但是有直接的原因把当代对于理论上健全的总量经济学的探索解释为对于前凯恩斯主义理论家理论的恢复。”(26)基于这一认识,卢卡斯将微观经济基础的研究变为创立反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切入点。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高深的数学方法为分析工具和表述手段,但即使是萨金特也承认其“主要思想简单”(27)。具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将约翰·穆斯为分析微观经济问题所提出的理性预期概念拓展到宏观层面,(28)从而发展成为理性预期假说。这种假说将经济人对未来的预期假定为合理的或理性的,即假设经济人“知道决定市场未来状态的真实概率分布以及其他人现在及未来的状态”,从而“所有的个体在他们的目标及可利用信息明确的条件下最优地行动”,(29)并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一切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只能从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中得到解释。卢卡斯正是基于理性预期假说,将弗里德曼由总量分析所得出的短期货币非中性和长期货币中性的理论、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及固定的货币增长率规则置于个体行为或个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建立自己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30)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强调个体未预料到的货币量变化导致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因此货币因素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并认为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可以为理性经济人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不难看出,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不过是以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的方式复述了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政策主张。至于包括弗里德曼都难以说清的一些宏观经济问题,如货币传递机制问题,卢卡斯则利用哈耶克的不可知论,谦恭地将它们归于人类认知能力不可及的范围。
在卢卡斯看来,基于其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就能“十分圆满”地解释滞胀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政府通过增加支出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理性经济人都会像卢卡斯那样,能够有效地利用所得到的信息,知道未来的通货膨胀率会随货币增长率同比例上升,并相应调整个人的行为以达到最优化。虽然卢卡斯承认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也会出错,但他把这种错误归咎于政府政策的欺骗性,从而强调这种错误是随机的,不会造成系统性错误。结果,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而且还会导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一起上升,滞胀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严重经济问题。既然政策的无效性意味着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张固定的货币增长规则和自由放任,就成为卢卡斯理论的必然归宿。卢卡斯正是基于这一点认为,“凯恩斯理论的失败在于它给出的定量结果是错误的。它的主要前提是货币政策可以稳定利率,而且在高失业率情况下可以不必考虑通货膨胀,但这个前提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31)而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政府,“60年代并不赞同固定的货币增长法则和自由放任”。(32)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基于新货币学派的理论将固定的货币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应该说,这符合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要求,从而应实现他的理性预期:在理性经济人不会出现预期错误的情况下,经济将趋于均衡。但是,这种货币政策却导致美国经济在8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从而迫使里根政府不得不放弃新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原本就遭到西方学者的质疑,认为“预期错误看来是一种经济周期理论所依靠的一根难以置信的脆弱的芦苇”,(33)而美国经济的现实又充分证明它在经济政策层面上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背景下,以R.J.巴罗为代表的一些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不得不抛弃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抛弃新货币学派的货币非中性论,试图在新古典学派的货币中性假说下,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周期理论。
在巴罗看来,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最初似乎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但一经深入思考便会对这些成功提出疑问”。(34)这是由于该理论“把解释货币重要的短期非中性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是错误的”。(35)他认为,“包括金融媒介物在内的广义货币总量(如M[,1]或M[,2])比一个狭义货币总量(如货币基础或现金)与产出联系更为紧密”。(36)由于广义货币总量对于经济活动而言是内生的,因此,观察到的货币和产出之间正的相关关系,只是反映了经济活动对货币量的影响,而不是相反。这表明货币的内生性反应能够解释货币和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大部分相关关系。因此,即便狭义货币或基础货币与产出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也只能反映货币的内生性反应。基于这种认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大多数支持者们从强调货币冲击的分析转向了把实际冲击作为经济波动根源的分析”,从而提出了“强调引起周期波动的冲击根源是实际的而非‘货币’”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37)这种理论将实际因素限制在偏好和技术方面,并在个体理性和市场出清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假设下,认为偏好和技术的冲击,会导致消费、投资、就业量和总产出出现周期性波动,但在时间序列中可以恢复均衡。因此,“典型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导出的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它们说明,在总量经济活动中观察到的波动现象不足以构成支持政府以稳定政策的形式干预经济的理由。”(38)不过,巴罗也承认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对于理解现实的经济周期或者对于形成有用的政府政策究竟作出了多大贡献,我们还不十分清楚。”(39)但是,卢卡斯的态度却十分清楚: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完全按照真实(区别于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思考方式来构建——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是倒退到不及大卫·休谟的“古老思想的地步,这真是一种耻辱”。(40)另外,卢卡斯在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演讲中,通篇强调理性预期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成就,“70年代的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可预测的货币增长变化和不可预测的变化有非常不同的效应”,以及发现这种区别在研究经济周期中的“中心地位”。(41)他不仅只字未提该派在80年代所创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在理论上有何建树,反而认为“像1929-1933年大萧条这样的事件则完全无法归因于偏好和技术冲击”。(42)他关注的是“近期有许多人将货币特征重新引入这些模型中”,并“希望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43)
这里不难看出,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不仅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基本上否定了弗里德曼的总量分析,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以个量分析取代了总量分析。萨金特曾毫不隐讳地说:“宏观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依据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约束来解释对各个经济总量的观察结果,并预计以各种不同方式管理政府经济政策的后果。所谓的‘政府经济政策’,指的不是一个孤立的政府政策行动,而是整个政策体系”。(44)卢卡斯也坦言,以只需支付较小成本便可获得的个体行为数据,便可以“知道总体参数意味着什么”,“这恰恰是我们关注总体理论‘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原因所在”。(45)这样, 自二战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而进行的探索,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由理性预期学派蜕变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与其说卢卡斯等人的理论是对滞胀和政府经济政策失效问题的“高妙解释”,还不如说他们的理论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由微观层面扩展到宏观层面。同时,这也迎合了美国政府的意图,将美国政府发动的越南战争和在国内实施向贫穷宣战的“伟大社会”计划,而引发的滞胀问题完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从而为美国政府因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政策受挫而引发的严重经济问题找到了替罪羊。正因如此,理性预期学派远离现实的离奇断言才在美国经济学界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并使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为极具宗教色彩的一种教义。而这种教义竟成了西方经济学界判断一种理论正确与否和社会接受与否的唯一标准。托宾的这一段话足以证明这点:“‘微观基础’正是方法论上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实际上是针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复兴的口号。……最近这种反革命在经济学领域里大获全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行为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46)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基于种种个体行为来解释宏观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形成的各种流派,在西方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例如,基于经济主体在休闲与工作、消费与投资方面的个体选择行为,来分析减税政策的供给学派;利用单个企业的产权和交易费用来分析政府作用的新制度学派;将经济人的个体行为方式扩展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通过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赋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坚实的微观基础而获得新生”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自20世纪70年代初“被人们迅速接受后,在8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涵盖了宏观经济学的方方面面”。(47)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在新自由主义者中,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化五花八门,但他们都以博弈论为主要的分析工具,从而博弈论在他们的理论中“具有中心重要的地位”。正因如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将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仅仅看作类似市场中单个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甚至看作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并且认为理性经济人在与“呆傻或可恶”的政府决策者的博弈中总是赢家。这显然远离现实。尽管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策略互动,但由于政府行为往往凌驾于经济主体之上,具有强制性,因此,两者之间主要是一种监管与被监管或调控与被调控的关系。两者间的策略互动也就被限制在这种关系之下,使得相互的影响力具有不对称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于一般的策略互动关系或一般的相互博弈者间的关系,将滞胀问题归咎于经济主体的博弈行为所导致的政府政策的无效性,而不是归咎于政府的错误政策,不过是一种为西方国家的政府开脱责任的庸俗辩护论。
从凯恩斯倒退到斯密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拉斯·E.O.斯文森教授认为卢卡斯“对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和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方法”。(48)本文显然赞同斯文森教授的观点。至于这种根本上的改变,能否像斯文森教授那样认定为杰出贡献,或者能否像瑞典皇家科学院那样认为是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研究领域,则颇值得商榷。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客观上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微观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宏观环境”。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表明:没有相应“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与没有相应“宏观环境”的微观经济学一样,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这种内在联系,实际上是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微观经济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再现。因此,如何看待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的“理性预期革命”,关键在于能不能用微观经济层面的个体行为直接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即能不能用个量分析取代总量分析,而不是宏观经济学要不要“微观基础”的问题。要弄清这点,必须对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经济层面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明确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或三大社会发展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和个人全面发展的阶段。(49)在《资本论》第 1卷中,马克思为揭示商品世界的神秘性,提出并比较分析了四种经济模式,即鲁滨逊的孤岛经济模式、中世纪的家庭经济模式、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经济模式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模式。除西方经济学家经常论及的非历史的鲁滨逊孤岛经济模式外,其余三种经济模式依次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50)从宏微观经济的角度看,中世纪的家庭经济模式是单一的微观经济模式,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经济模式是宏微观经济分裂的模式,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模式则是宏微观经济合一的模式。这样,由马克思对这几种经济模式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拓展出一种假说,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分裂的假说,以探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古老的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还是现代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被投入经济领域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而不是满足资本所有者的直接消费。经营活动与直接消费的分离是一切形态的资本所共有的特征。在历史上,只有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进入到生产领域而形成产业资本后,才创造了适应“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的大规模生产,(51)并加速了生产与消费的分裂。在资本支配下,生产与消费的分裂开启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过程和货币化过程,即开启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基于生产与消费分裂而“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专业化分工,又会加速生产与消费的分裂和经济活动的货币化。只是在生产的机器大工业基础确立以后,生产与消费的分裂才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一个覆盖一切经济活动领域的庞大的专业化分工体系。
在私有制基础上,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52)专业化分工导致千百万企业相互独立,相互竞争,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私人性。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商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由此,经济活动形成了两个层面: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单个企业构成的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
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所说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了微观经济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的分裂。具体来说,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一方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可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约束。显然,约束企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属于微观经济层面,它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成本收益原则。而约束企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它是上面所说的总量比例关系的另一种表述。对企业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可知的和必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是不可知的和不必知的。而企业的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这是因为即使某类商品中的任何一个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但如果该类商品耗费的总劳动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那么所超过的部分仍为无效劳动。而体现无效劳动的那部分商品就会被“一起捉住,一起绞死”(53)。所以,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54)这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总量,尽管宏观经济层面的总量必然源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另外,企业生产的社会性质是通过它的“产品的货币性质”,(55)即它的产品转化为货币这个为社会承认的一般等价物来实现的。然而这种转化的必然性与其成功的偶然性是同时存在的,“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56)这样,只有经过“货币过滤”后的个量加总,才能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总量。或者说,只有通过“货币过滤”后的私人劳动量的加总才能等同于社会总劳动量。这点即使从严格的统计意义上来说也是成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个量与总量的关系,充分显示出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分裂。而货币是微观经济中的“异己力量”,是导致宏观经济层面与微观经济层面分裂的直接原因,同时又是连接两者的枢纽。显然,在宏微观经济分裂的情况下,用微观经济层面的个体行为直接去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既无科学价值,又远离客观现实。相反,个体行为本身更需要从宏观经济层面加以解释。因此,对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矛盾,马克思更强调的是矛盾的社会性方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最大不同之处。
基于宏微观经济分裂的假说,人们不难看出,卢卡斯用个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直接解释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现象,是根本行不通的。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领域内的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总量失衡的直接产物,而绝不可能是微观经济领域的个体理性预期行为的产物。实际上,在常态下,由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量,不仅个体或理性经济人无法正确预测到它的经济后果,就是推行这种政策的政府也无法正确预测到它的后果。只有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引发了通货膨胀之后,个体才会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或价格预期,从而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以适应所预期的物价上升,由此会加速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因此,在价格预期下,除非政府逆向调整货币政策,否则增加的货币量只会导致物价水平同比例上升,而不会刺激就业量和产量的增加。在这里,通货膨胀在先,个体的价格预期在后,货币的中性效应和政府货币政策失效,完全不是理性经济人前瞻性预期的直接结果。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持续通货膨胀所引发的滞胀问题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作为现实中的个体只能在通货膨胀出现后以适应性预期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所谓经济人的理性预期或前瞻性预期,不过是卢卡斯等人把他们运用高深的计量经济模型所得出的理论结论,强加给千百万单个的经济主体,从而使一个普通的市场参与者对未来的预期都远比专业的预测机构准确。卢卡斯已将“理性预期理论发展和应用”到类似于“皇帝的新衣”那样荒谬绝伦的地步。不过,为之喝彩的只是一群满脑子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臣民”。即使在西方社会,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面对这场经济学上的闹剧,都会抱不屑一顾的态度。
值得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者是在“回到斯密去”的旗帜下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的。显然,他们不会回到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因此,这里不妨看看新自由主义者究竟回到了斯密的何种理论。斯密认为,把资本投入产业的每一个人,都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的目的”,而“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57)当个人“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58)斯密的这段话可以归纳为两层意思: (1)个体生产的商品价值总和等于社会年收入;(2)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一致性。
从宏微观经济分裂的角度来解读斯密的上述论述,不难看出,斯密强调微观经济中的个体行为直接决定宏观经济总量,即个量总和直接构成宏观经济中的总量,个体的私人利益直接决定社会利益,这不过是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这种分析方法往往将斯密在微观经济领域所犯的理论错误,放大到了宏观经济领域。例如,斯密认为:“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59)马克思指出:“亚当·斯密就是这样把一切个别考察的商品的价格和‘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分解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之后,他还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把第四个要素,即资本的要素偷偷地塞了进来”。(60)另外,针对斯密关于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不知不觉地促进了社会利益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61)具体来说,马克思认为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媒介的货币上。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62)显然,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条件或宏观经济环境决定着个体所追求的私人利益的内容及其实现的形式和手段。斯密之所以不加限制条件地提出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论”,个量总和与宏观总量“相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货币面纱观(即认为货币只是盖在实物上的一层面纱,从而对经济活动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实际上将货币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从而把市场经济变成了实物经济。马克思对四种经济模式的分析表明,抽象掉货币,宏微观经济将合一,总量也就等于个量的加总。显然,斯密的“一致论”和“相等论”远离市场经济的现实。
自斯密后,货币面纱观或货币中性论主导了西方经济学160年,直到凯恩斯理论产生之后才被抛弃。凯恩斯理论最值得肯定的方面,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的货币面纱观或货币中性论,正视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从而能够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用总量分析取代传统的个量分析。凯恩斯在《通论》的法文版序言中,特别强调了总量分析法,并指出个量分析在微观经济层面得出的正确结论,一旦推广到宏观经济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错误。凯恩斯说:“我称我的理论为通理论,意思是说我涉及的是总体经济体系的行为——总收入、总利润、总产量、总就业、总投资、总储蓄,而不是特定行业、企业或者个人的收入、利润、产量、就业量、投资和储蓄。并且我要论证:扩大到总体经济体系所导致的重要错误在于,就孤立的局部而言就能正确地得到结论。”(63)弗里德曼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仅仅在这点上,弗里德曼不同于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然,就弗里德曼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到斯密的自由放任来说,不仅与其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毫无区别,而且影响远远大于后者)。他说:“在我们一直讨论的货币领域中,你作为一个个人可以持有你意欲持有的任何数量的现金。这一数量只受你财富水平的限制。但在任意一个时间里,一个社会的现金总额都是固定的”,而“在你个人的情况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你认识到这一点”。(64)这表明“事情出现在个人面前和出现在社会之中的差别”。(65)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观点之所以与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不同,是由于他“对货币现象潜心研究了将近半个世纪”,并认为“货币是经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66)不难看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都涉及宏微观经济的分裂问题。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宏观分析方面都以货币中性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其结果必然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而他们“回到斯密去”的目的就是要用微观经济学取代宏观经济学。对此,卢卡斯曾毫不讳言地说:“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界,新近最有趣的发展是:将诸如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总体性问题重新整合到微观经济学的一般性框架之内。如果这些进展取得成功,‘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将会完全消失,‘微观’这一修饰语也成了多余。我只需说‘经济学理论’,正如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以及瓦尔拉斯所做的那样。”(67)显然,这是从凯恩斯理论倒退到斯密的“相等论”和“一致论”,在理论上根本谈不上“杰出贡献”或“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研究领域”。这种倒退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导致了灾难性的社会经济后果。
至于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之间所发生的经济周期问题之争,显示出他们已沦为“数学囚徒”,从而丧失了对货币因素与实物因素、均衡与非均衡的辩证发展关系的理解力。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透视力要深邃得多。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在交换过程中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外在对立,一方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另一方是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体现社会劳动的货币。在为买而卖的简单商品流通中,交换的是剩余产品,目的是换取用于生产者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货币只是不同使用价值交换过程中转瞬即逝的手段,交换价值也不构成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流通中,货币成了上帝,货币资本的增殖是生产的唯一目的,而流通过程一旦发生大规模中断,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在商品中已经包含的、在流通中体现社会劳动的货币因素与在生产中形成的产品因素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全面展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这一矛盾具有对抗性,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相对过剩的社会生产力被暴力摧毁并反复出现,就是对抗性的一种表现。马克思指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68)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69)马克思研究了不同于个别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运动,揭示了实现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所必要的均衡条件;这些必要的均衡条件的满足只能经过周期性的经济震荡和破坏;而市场条件下因利润率的波动引起的固定资本突然的大规模更新,构成了经济周期性震荡的物质基础。换言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际过程是处于一种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状态。(70)理性预期学派抽象掉制度因素,并不加限制条件地将总体中某个单一的货币因素或实物因素视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即使建立起再完美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是远离现实的,无法把握极其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不仅重“犯了时代的错误”,而且还往往将他们主观上希望发生的事情,用数学模型“准确”地模拟出来,再选择性地利用数据加以验证或修改,以为这就是客观现实所注定的,经济学只是因为有了他们才变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才能对注定将要发生的事情做出前瞻性的预测。
值得一提的是,失业者在现实中的被迫、无奈与苦难,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中却成为一种“休闲活动”,一种劳动者的偏好。这样,作为对弹性工资的一种反应,劳动者可以轻松地、愉快地和自主地选择工作或失业(闲暇)。套用卢卡斯的一句话来说,在失业问题上,理性预期学派把失业等同于闲暇,是从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弗里得曼的“自然失业”,倒退到不及庇古等人的“自愿失业”地步,“这真是一种耻辱”。无独有偶,马尔萨斯曾经将失业者的死亡视为“睡眠”。(71)虽同是对失业者处境的冷漠,但表达方式却截然不同。马尔萨斯使用了诗一般的语言,而卢卡斯等人使用的却是冷冰冰的数学符号,资本家的贪婪和失业者的苦难都被转化为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科学”方程式。
结论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表明: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经济学实际上主张靠一只全能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自发力量来协调宏微观经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实际上主张靠一只万能的“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力量来协调宏微观经济;而理性预期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则实际上主张靠“先知先觉”的理性经济人来协调宏微观经济。但是,在宏微观经济分裂的情况下,这些主张都远离现实。当然,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适用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而理性预期学派的“宏观经济学”在这一时期只能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话,从而成为世界霸主国为其对外扩张而强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精神鸦片。宏微观经济的分裂,二者之间的对抗性,不仅使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个体,而且使政府都无力控制宏观环境或宏观经济层面。放任市场自发力量带来的破坏性的经济后果,是个人和社会都难以承受的。“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72)并支配着每个个体,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关系的拜物教性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实践表明,人类要摆脱这种困境,不能靠人为的方式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只能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的积极作用,以创造“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去实现宏微观经济的合一,即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经济模式。
注释:
①程恩富、王中保:《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危机》,《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另外,程恩富与曹雷系统地评介了外国学者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研究,以及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在我国的影响。详见《当代外国学者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研究》,《财经研究》2004年第2期;《外国学者对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批判——兼论中国经济改革三大流派》,《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②③④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魏埙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18-19、4、2、 360页。
⑤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3页。
⑥⑦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第325、327、328页。
⑧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魏埙译,第73页。
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第331-332页。
⑩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第332、337、360页。
(1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第313-314页。
(1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第392页。
(1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第392页。
(14)(15)(16)哈耶克:《物价与生产》,滕维藻、朱宗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17)(18)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19)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普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关于哈耶克的相关论点见F.A.Hayek,Economic Freedo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 F.A.Hayek,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The Argument Refined,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78。
(20)(21)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韩莉、韩晓雯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309-311页。关于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详细评介,见方兴起《货币学派》(武汉出版社,1996年)。
(22)(23)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朱善利、雷鸣、王异虹、温信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4、4页。
(24)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美英经济学家评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7页。
(25)卢卡斯为其投机行为作了这样的辩解:“人们全然不会对下列事实感到惊奇与不满:要使人们相信某件事,你就得以谈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方式以及用他们认为是情投意合的语言来提出问题。”(《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12页)
(26)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3页。
(27)T.J.萨金特:《动态宏观经济理论》,苏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28)J.F.Muth,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3,July 1961,pp.315-335.
(29)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183-184页。
(30)吴易风等著的《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1998年)一书,对卢卡斯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评介,且观点独到。在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方面,该书是国内少见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31)(32)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309-310页。
(33)R.J.Gordon,Macroeconomics,Scott,Foresman & Company,London,1990,p.475.
(34)(35)(36)R.J.巴罗:《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方松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页。
(37)(38)(39)R.J.巴罗:《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第4、17、5页。
(40)卢卡斯:《经济周期模型》,姚志勇、鲁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100、86页。
(41)(42)罗汉等译:《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1969-1995)》(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82-1183、1168页。
(43)罗汉等译:《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下),第1183页。
(44)T.J.萨金特:《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引言。
(45)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339-340页。
(46)J.托宾:《通向繁荣的政策》,何宝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47)R.J.巴罗:《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第14页。
(48)罗汉等译:《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下),第1148页。
(4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5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3-97页。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包括李嘉图在内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鲁滨逊故事”上“犯了时代的错误”,但是,当马克思将“鲁滨逊故事”置于历史和逻辑的分析之中时,它就成了经济分析中的一种有用的模式。
(51)尽管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产业资本,“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十五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8页)
(5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0页。
(5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6页。
(5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22页。
(5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720页。
(5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4页。
(57)(5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7页。斯密曾三次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一短语,分别见于其《天文学》、《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虽然斯密从未明确解释“看不见的手”为何物,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他将上帝或神与“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则是显而易见的。他说,上帝是人类的“直接主管和指导者”,它“指导着人类本性的全部行为”。(《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4页)无论斯密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如何,他直到临终前留下的文字都坚持这种看法。(约翰·雷:《亚当·斯密传》,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89页)
(5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第46-47页。
(6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02页。
(61)(6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2-103页。
(6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法文版序言,魏埙译,第2页。
(64)(65)(66)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51-252、249页。
(67)卢卡斯:《经济周期模型》,第107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8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81页。
(70)参阅方兴起《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年第4期。
(71)马尔萨斯说:“一人出生在早已被人占有的世界之上,如果他不能够从他享有正当要求的父母那里获得生活资料,而且假使这个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的话,那么他就没有要求获得最小一份食料的权利,……在大自然的伟大宴会上,也就没有为他而设的席位。她(大自然)……在她的餐桌坐满的时候,文雅地拒却新来的人们”。于是“死会像睡眠一样来到他们头上”。(参阅E.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徐宗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1-172页;马尔萨斯《人口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 1959年,第101页)
(7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9页。
标签:宏观经济论文; 凯恩斯主义论文; 经济周期论文; 凯恩斯论文;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微观经济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卢卡斯论文; 货币论文; 理性预期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