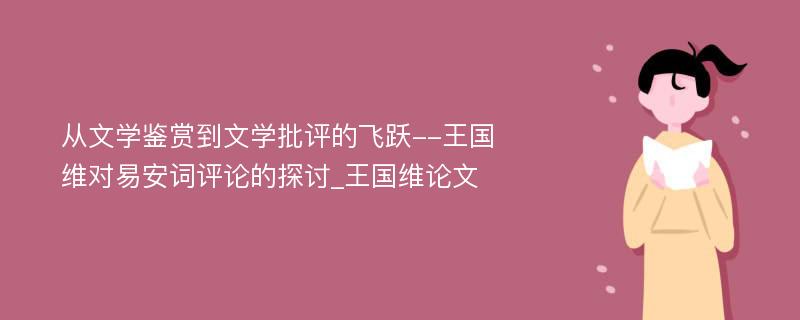
从文艺鉴赏到文学批评的跨越——王国维不涉评易安词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文艺论文,王国维论文,探微论文,不涉评易安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是近代词学批评史上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批评家,许多人走近王国维,很大程度上是从《人间词话》开始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及其散见于文集中的词论,形式上承袭的虽然是诗话词话的传统模式,但它所建立的批评体系和开拓新径的创意却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以独特的理论建构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谈锋所向、评骘面之广,几乎使词史上所有成名的词家均以独特而清晰的面目呈现在他所勾勒的批评格局之中。然而,这样一位视野开阔的批评家,却对两宋词坛上享有盛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作品未置一辞,不能不说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
李清照的词集散失较早,作品流传到清代已是篇帙无多,仅散见于一些类书、选本和其他文献著录之中。毛晋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时只收词十七首,但在时人眼中“固不能不宝而存之”并仍被推为“词家一大宗”。(注: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八,集部五一,词曲类一《漱玉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到了清代,随着词坛对李清照词的频频关注,开始有人有意识地从事李清照词的辑佚工作,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初刻《漱玉词》,即以宋本《乐府雅词》所录二十三首为主,旁搜宋人选本说部,得二十七首,合五十首为一集,又以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为附录刊行于世,收罗可谓详备。明清两代词家,尤其是清代词家对李清照词的评价一直很高。王士祯《花草蒙拾》说:“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彭孙遹《金粟词话》赞易安词云:“借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三则用“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之辞加以推许。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对李清照的词也颇为称赏,曰:“李易安词,独辟门径。”总之,清人对李清照词的发掘、辑录、评价都是很用力的。这一切都说明在王国维之前的清代词学研究格局中,李清照作为词坛大家已有的重要地位和所受的褒扬关注程度。那为什么王国维在遍评两宋词坛名家之际,唯独不见涉评在清代词家眼中得到如此嘉许的李清照?笔者以为这当与王国维的词学理论所产生的特殊背景和建构的批评格局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一
以《人间词话》为主体的词学体系是在晚清特殊文化背景和作者特殊人文经历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中西合璧、情理俱备的产物。晚清时国门洞开,来自西方的“新学”像海潮一样汹涌而至,一心向往“新学”的王国维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叔本华《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知识论》等一系列代表西方新学潮流的哲学著作深深地吸引了他。早在1901年,王国维就开始了对西方哲学的关注。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从事哲学研究的热情一度很高,这期间他写下了一系列哲学和与哲学有关的论文。与晚清许多专注于国学研究的学者相比较,王国维无论在学术观念或方法上都算是较为先进的,假如后来的他一直沿着研治哲学之路走下去,可能会是另外一番建树。问题是当他深入研究哲学时,却发现了哲学本身无法消解的矛盾和自身存在的困惑,他逐渐感觉到自己个性才情与哲学之间的不相谐合处。他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注:王国维:《自序二》、《静庵文集续编》,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以下引该书只明书名、卷册,不备注。)他痛苦地徘徊在哲学和文学之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最后,从自身才性的特点考虑,他放弃了哲学研究,选择了文学的道路,开始作词自慰,并投身到词学研究的领域之中“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王国维毕竟是把西方美学引进到中国的第一人,他舍弃哲学以后,虽然未曾回首,但他所具备的哲学思辨能力,在他转向词学后仍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往往不自觉地把西方哲学与美学的观念渗透到词学研究的方法之中,使他建构的词学理论富有系统化的倾向(注:叶嘉莹以为,王国维于《国粹学报》上刊发的六十四则词话的编排次序“确是隐然有着一种系统化之安排”,概略地说即“批评之理论与批评之实践两大部分”。见《王国维及其文学评论》第三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和近代学术色彩。“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王国维遗书》第1册,卷首。)构成了他独特的治学风格,形成了他不同于众的词学研究的门径,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
也许由于词产生的特殊文化背景,传统的词学比较偏重记录词坛的趣闻逸事或与词体作法相关的品藻议论等内容,这种传统是悠久而深远的。宋代有杨绘《本事曲》、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之属;延续到清代,词学在宋人基础上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龙沐勋先生《研究词学之商榷》曾列举清人在图谱、音律、词韵、词史、校勘等五个方面的重大成就。除此而外,批评之学在清代也有一些重要进展,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为了标举自己的词学主张,开选评之风。他们以南宋词为范本建构他们的批评格局,这种影响一直波及到后来产生过较大反响的几部重要词话诸如《介存斋论词杂著》、《蕙风词话》、《白雨斋词话》、《词概》等。在王国维之前,词坛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基本表现为侧重感受或体悟的批评范式。具体到李清照研究的个案,则呈两种态势:一是特别关注李清照作品中脍炙人口的篇章,并作摘句平章。这一类的评点,以宋代张端义《贵耳集》卷上的一段话为代表:
易安居士李氏……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且秋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文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用《文选》诸赋格。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注:引自褚武杰等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页。以下简称《李清照资料汇编》。)
罗大经《鹤林玉露》、黄升《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瞿佑《香台集》等均承此种摘句品藻的风气,并对李清照的作品有许多类似的誉扬。以后评家的摘句平章笔法亦不外乎此。清代批评家陈廷焯则从另一个层面指出:“李易安之‘绿肥红瘦’、‘宠柳娇花’等类,造语虽工,然非大雅。”(注: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表面上转换了批评的角度,但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原来的圈子中。由于李清照作品流失的多,流传的少,选家和批评家们往往把目光过度集中在某些传诵甚广、耳熟能详的名篇名句上,反复征引,一些评论言辞则津津于递相祖述,相袭相因,这类品藻几成定律,遗憾的是褒扬有加而殊无新意。
二是在李清照作品研究中,论者特别偏重于对作品本事的诠释和作者本人生活状态的关注。前者如元人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辑录的有关李清照作品创作本事的背景材料: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政易安作也。(注: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第28页。)
后者则集中在家世、婚姻等方面。关于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固然已为时人和后代所乐道,即便是李清照再嫁事宜,南宋就有王灼《碧鸡漫志》等数家笔记言及并作为谈资。到了清代一些迂执之士还藉此菲薄李清照,讥其失节,(注:徐轨:《词苑丛谈》卷三云:“惜其再适张汝舟,为世所薄。”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九云:“况桑榆一札,未免被人点检耶!”分别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第88、91页。)与此相应的是一些称赏看好李清照的词家则拍案而起,努力为之辩护。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云:“清朝庐抱孙、余理初、金伟军三先生均为李清照辨诬,王鹏运刻《漱玉词》,以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附后,显微阐幽。”卢见曾在重刊《金石录》序中以为再嫁之事乃“好事者为之”,“或造谤”遂使“易安犹蒙恶声”。(注:雅雨堂本:《金石录》序,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第94页。)一时间许多关注的目光几乎集中在再嫁问题上,并为此大打笔墨官司。再嫁公案竟成为清代李清照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从宋代到晚清,尽管有二百三十余家论及李清照其人其作,(注:据《李清照资料汇编》所辑录的资料统计。)但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不外乎上述两大方面。
王国维的特殊人文经历资助了他在词学研究领域的实质性开拓与超越,使他的词学研究具有超越同时代其他词家的识见和气魄,也使《人间词话》得以兼备近代哲学的思辨色彩,表现在词学观念和取舍尺度上则均有别于传统的范式。他以境界立论,与清人普遍看好南宋词的眼光相左,特别标举五代北宋风味。他开篇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注:见《人间词话》第一则,《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91页。以下有关《人间词话》引文均出此本。)他致力于探讨词的艺术趣味与审美规律,建构以文本审美研究为特色的批评格局。这种新意集中体现他对作品本身美感价值的开掘和对阅读二度创造所得到的审美感受的重视上。他有意识地淡化传统词话资谈考证的叙事模式,从而体现他立论的整饬性和表述上的思辨色彩;在个案批评方面也能标新立异,他擅长评点一些能充分支撑其理论观念的作家作品,他不步前人后尘,避免引述在前人批评视野中几成定律又十分眼熟的东西,力图从新的视点给人以新的感受,在立论和评点两方面均明显地表现出背离传统、刻意辟新的苦心。所以,尽管其《人间词话》仍是以传统的形式出之,却包含了一个新的审美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词话“助闲谈,资考证”的性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也许正是易安词在传统的评价体系中左右逢源颇受关注,却游离于王国维批评格局之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王国维以“境界说”建构其词学审美本体论,《人间词话》关于词学“探本之论”的阐述很引人注目。他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注:《人间词话》第九则,见第194页。)显然,王国维的词学“探本之论”和传统的词学评价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换,特别是与李清照时代的词学观念、审美尺度有了很大的区别。
李清照有一篇作于北宋末年的著名词学专文《词论》(注:此篇始见于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则“李易安评”,后人辑录时,一般题作《词论》。)。《词论》是继苏轼和李之仪等人的零散论词书简、跋语之后的一篇重要而系统的词学专论。这篇只有七百来字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词学观点。李清照十分强调词的音乐性,认为词应像唐朝开、天盛世时的“乐府、声诗”一样入乐协律。她综观有词以来的创作进程,进而以实例说明词除协律外,还须雅致。在她眼里,像晏、欧、苏等人那样写一些“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葺之诗”是不符合词的特质;像柳永《乐章集》那样“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也不符合词的雅正之道。针对北宋词坛有模棱诗、词之别,或“知之(词)者少”的状况,李清照强调词入乐和雅致的艺术标尺是符合当时创作和传播实际的,阐明了词在形成、发展时期特定文化背景下必须遵循的艺术规范;她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见解,阐明了词体的音律、风格特点,为诗、词之别立下界石,这一见解也是出于对词体特性风格的深入体悟。李清照的词学观点,从“本色”与“当行”的角度,摆脱了词论附丽于诗论的从属地位,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的本质特征和词论的理论框架,可看作是李清照《词论》的探本之说。
然而,这个当初在李清照看来至关重要的有关词本质特征的问题,随着词体的不断革新和演变,在王国维时代已经少有人固守因循了。后来的创作事实证明,李清照的词论确有其推尊词体的意义,但也有拘囿的一面。关于词体特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也有一段比较简要的阐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注:《人间词话删稿》第十二则,见第226页。)王氏主要从词体和诗体不同的表现的畛域和风味,审视了诗词之间的相异因素,以此来区分诗和词的不同特色。这与李清照《词论》中强调的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似有某些相通之处。但《人间词话》之核心问题显然不是对词体特征的刻意确认上,上述言论也不在《国粹学报》最初发表的六十四则词话之列。在王国维看来,词体问题已经不是《人间词话》中要探讨的根本问题。《人间词话》中致力标举阐发的是“境界说”。王国维在最初发表的六十四则词话中,除开篇即推出“境界说”外,用“境界”一词达十三次之多(注:参见萧艾:《王国维评传》第六章《人间词》与《人间词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可见“境界说”作为《人间词话》探本之论的特殊地位。
当初,李清照为了阐释词体特性,十分强调“入乐”的意义并重视“雅致”的风格,以声、情之“美”为标准衡量词人词作,意在推尊词体,突出词的独立审美价值和地位;而在王国维时代,词与音乐的母体关系早已剥离,作为一代文学的表征,其尊体问题已毋庸赘言,词学面临的新问题是如何建构一个有效的批评体系来总结词史的演变。王国维标榜的“境界说”,实际上是想在传统词学的模式之上推出一个新的评价体系。“境界说”实际上是围绕着一个“真”字展开的:“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注:《人间词话》第六则,第193页。)他说:“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现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唯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所能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注:引自《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王国维遗书》第11册。)他还划分了“境界”的不同层次和进境:“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要亦有深浅焉。”他从主体观察客体的倾向和主体的创作方式,将创作主体分为“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将“境界”分为“造境”和“写境”(注:《人间词话》第二则,第191页。),“境界说”描述了主体在艺术创作中对客体认识所达到的程度。他是以“真”为标准,来衡量一种文体所达到的艺术至臻境界的。当在这样的标尺之下,他不再强调诗、词这两种文体的相异因素,而是直接展开对诗、词的批评和鉴赏:“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注:《人间词话》第五十六则,第219页。)在他看来,唐中叶以后,正是在诗失去真味沦为“羔雁之具”时,词这种文体才以其“真”脱颖而出,继而成为一代文学的表征。他以论词为突破口,又不限于论词,直接把词学理论纳入到他的整个诗学审美体系之中。这是王国维关于词学持论标准的一个明显的转换,这种转换实现了从单纯的文艺鉴赏到纯粹的文学理论批评跨越的根本转换。因为王国维欲与伦比的“沧浪(严羽)所谓兴趣,阮亭(王渔洋)所谓神韵”原本均属诗学批评范畴的术语,是严、王两人对前人诗歌趣味、意旨的一种理论提炼和审美倡导。王国维拈出“境界说”标新立异,本身就包含着其诗学理论表现在诗词批评领域中的一体化倾向。
三
王国维以境界论词,对词史进行了一次盘点和检阅。他十分强调诗人所持有的一份锐感和才情,在《人间词话》中,关注作品审美价值和作者才性的成分比较突出。他非常擅长以诗人之心去直接触摸词意,表现出对作品直觉感受的深切体悟和意会;他还接受了尼采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特别致力于挖掘作品中深刻的悲剧意识,对词史上有悲剧意味的词家、词作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有个性色彩的评价。他涉评的唐宋词人多达三十余家,他欣赏的词人大多集中在五代北宋,特别推举的有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东坡、稼轩数家。
就本质而论,王国维的上述审美倾向与取舍准则并不排斥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相反,有的简直是非常融合的。李清照是一个锐感的词人,所作之词感触真切、声情宛然,兼有浓郁的感伤色彩,历来被认为是继李煜、秦观之后的纯粹的抒情词人。清人从当行本色的角度把李清照与李煜并举;从才情气韵的角度又常常把李清照与苏、辛、秦、黄等词坛巨擘相提并称。从创作上看,李清照与《人间词话》所致力褒扬的大多数词人诚属同调,具有相类近的气质与风味。
然而,李清照的持论和创作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尽相同的面目。与创作中所呈现的五代北宋词自然真淳之趣味不同,李清照在《词论》中是主张雅正、故实、技巧的,这与王国维所标举的“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语语都在目前”、“不隔”的审美趣味相去甚远。王国维反对用技巧作词,对两宋词人词作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他所欣赏的五代北宋词,乃缘于“不隔”,对南宋词,则因其“隔”而基本持否定态度。李清照是南北宋词风转变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其自身创作清新雅致、声情宛然,颇具北宋风味;其《词论》却尚雅正,主故实,重技巧,实际上已开南宋风气。对于李清照这样一个在持论和创作上有些错位且均有建树的词家,王国维不论从哪个角度评判,似乎都不能完全纳入其“境界说”的评价体系,这是否也是王国维对她不轻易涉笔的一个原因?
当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涉评易安词或许亦包含着某种传统的惯例和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中国历代文学的流传过程中,虽不乏女性作者,但真正能纳入批评视野的毕竟不在多数。更多的著录根本不把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加以推介,这种风气自古而然。王国维是在1908年完成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后,开始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人间词话》的。不论是他的《词辑》还是公开发表的六十四则词话和数十则未刊稿,都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偏好五代北宋词,二是涉评的对象均是男性词家。对于前者,可能与批评家个人的审美趣味习性相关,除《人间词话》之外,王国维另外的一些考证性的词学著述都表现出他对五代、北宋词的致力和关注;至于后者,我们也不排除王国维有因袭类似传统的惯例的可能性,或者出于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当时他撰写词话词论时,所参阅的某种选本或合集恰好不收李清照作品,比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常常提到的冯煦《宋六十名家词》就未及《漱玉词》,是以不涉评。因为一般情况下,批评家在阐发以文本批评为主的理论著述时,总以一个相对完整的作品系列为基础,从而形成系统的学说。
尽管有上述种种可能性,但笔者总觉得在王国维的整个词学研究视野中,不可能没有李清照的存在,因为后来搜集李清照作品用力最深的恰恰就是王国维之子王学初,洋洋二十八万言的《李清照集校注》裒辑之富、用力之勤,不可能没有家学的浸染和影响。所以,笔者以为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之不涉评李清照,并不是他对李清照作品的漠视和对其词学成就的排斥,相反,这正是基于建构新的词学批评体系而采取的一种刻意而高明的回避,正如李清照《词论》对同时代的著名词人周邦彦未置一辞一样,王国维对易安词的或缺,是否也包含着当年苏轼论杜甫海棠诗时所言的,有“恰似西蜀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的一份赏爱和推崇。
标签:王国维论文; 李清照论文; 人间词话论文; 王国维遗书论文; 文化论文; 白雨斋词话论文; 读书论文; 漱玉词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国粹学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