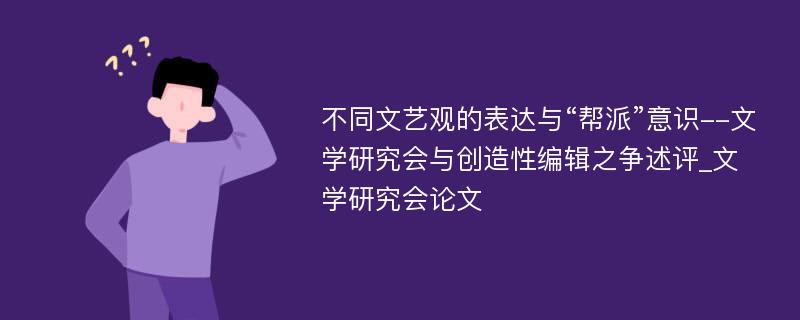
不同文艺观和“行帮意识”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争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帮论文,社论论文,研究会论文,文艺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22年3月起,文学研究会作家沈雁冰、 郑振铎与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发生了旷日持久的论争。他们的论争既有意气之争,更是有不同文艺观的论辩。
早在1921年9月29日、30日, 郁达夫就在《时事新报》刊发《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指出文学研究会作家“垄断”文坛。1922年3月15日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上, 郁达夫和郭沫若又分别发表了《艺文私见》和《海外归鸿》。郁达夫在其文中写道:“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文艺批评有真假的二种,真的文艺批评,是为常人而作的一种‘天才的赞词’。因为天才的好处,我们凡人看不出来……”,“目下中国,青黄未接,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在这混沌的苦闷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诧叱诧,那些恶鬼,怕同见不了太阳的毒雾一般,都要抱头逃命去呢!“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呢!”“真的天才和那些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冰炭不相容的,真的天才是照夜的明珠,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伏在明珠上面的木斗。木斗不除去,真的天才总不能放他的灵光,来照耀世人。除去这木斗的仙手是谁呀!就是真正的大批评家的铁笔!”郭沫若则说:“我们国内的创作界,幼稚到十二万分”,“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见不想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什么自然主义啦,什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个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我们可以各人自己表现一种主义,我们可以批评某某作家的态度是属于何种主义,但是不能以某种主义来绳人,这太蔑视作家的个性,简直是专擅君主的态度了。”显然,他们的话都是带有攻击性的,而且其矛头是指向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和郑振铎的。
沈雁冰看到郁达夫和郭沫若的文章后,自然是颇为反感的,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37、38、39期上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作为回敬。此文,先是委婉地反驳了郁达夫对他的“骂”,说:“我先得声明,我并不是‘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人,当然不生‘批评家’真假的问题,不过我现在却情愿让郁君骂是假批评家,骂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的假批评家”。然后,他便对《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作品阐述了看法。对于张资平的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他认为“为一个平常的不幸福的女子鸣不平”,是不错的,“但结构不是短篇小说的结构”,“未曾畅意的描写,颇有些急就粗制的神气”;对于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他认为“这篇东西未必能有怎样多的读者感受真的趣味”;对于郁达夫的《茫茫夜》,他指出“肯自承认而自知,我以为这就是《茫茫夜》的主人假如所以可爱的地方。除此点而外,若就命意说,这篇《茫茫夜》只是一段人生而已,只是一个人所经过的一片生活,及其当时的零碎感想而已,并没有怎样深湛的意义。似乎缺少了中心思想。但描写得很好,使人很乐意的看下去。”……因此,沈雁冰进一步指出,“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罢。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而想当然的猜想别人是‘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更可不必。真的艺术家的心胸,无有不广大的呀。我极表情于〈创造〉社诸君,所以更望他们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出在纸上,不要挂在咀上。”这些看法,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可是,郭沫若却认为沈雁冰的上述评论是“酷评”(注:郭沫若:《创造十年》, 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而且他和郁达夫认为文学研究会作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好些文章嘲骂他们,例如骂他们是颓废的“肉欲描写者”(注:CP:《丑恶描写》,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5月21日第38期。),骂郭沫若和田汉是“盲目的翻译者”。 因而,郭沫若、郁达夫等与沈雁冰、郑振铎“便结起了仇怨”(注: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并接连不断地争论不休。
1922年7月27日和8月11日,郭沫若和郁达夫又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分别发表了《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的文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前文是针对沈雁冰有关翻译问题的看法而写的。沈雁冰曾在与万良浚通信(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 )中表示:“翻译《浮士德》等书(即《神曲》、《哈孟雷德》等——笔者按),在我看来,也不是现在切要的事;因为个人研究固能唯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郑振铎也曾在《盲目的翻译家》(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年6月30日第6号。)中说:“在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Danto)的《神曲》, 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Hamlet),贵椎(Geothe)的《法鸟斯林》(Faust), 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来看看原书,开开(疑为看看——笔者按)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而郭沫若却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是专擅君主的态度”。后文是针对沈雁冰和郑振铎用化名发表所谓“骂”人文章以及他们的文艺观的。郁达夫指责他们“藏在一个匿名之下,谈几句笼统活脱有俏皮话来骂人”,未能“堂堂地布出论阵来”。对于他们主张文艺的功利性,他明确表示反对。他说:“至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问题,我也曾经思索过。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敢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这种作家惯会迎合时势,他在社会上或者容易收获一时的成功,但他人艺术(?)绝不会有永远的生命。”对于他们提倡描写下层人民的“血与泪”的文学,他也不完全赞同。他说:“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映出全人类的苦闷来,不必定要精赤裸裸地描写社会的文字,然后才能算是满纸的血泪。”郁达夫还写了小说《血与泪》,嘲笑沈雁冰和郑振铎等人提倡为人生而写作“血与泪”的文学主张,认为都是“要卖小说,非要趋附着现代的思潮不可”。
对于郭沫若和郁达夫的上述指责,沈雁冰特地撰写了《介绍外国作家目的》(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8月1日第45号。)和《文学与政治社会》,郑振铎也写了《杂谈》,作了严肃认真的答辩。郑振铎表示,他没有在《盲目的翻译家》中“骂什么人”,并坚持认为:当时翻译介绍《神曲》等类作品,“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而应翻译“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的作品。沈雁冰更是在理论高度上反驳了郭沫若的有关看法。对于翻译的动机问题,他认为除了译者的“主观的热烈爱好心”以外,更应考虑“适应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注:沈雁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92年8月1日第45期。),因而他表示“极力主张译现代的写实主义作品”。对于文艺的功利主义问题,他首先指出把“功利”看作为“金钱”或“利用”的代名词是一种可怕的误解,而“尤其可怕者”是“把凡带些政治意味社会色彩的作品统统视为下品,视为毫无足取,甚至斥为有害于艺术的独立”。接着,他援引了大量的事实说明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色彩的原因,即“环境对于作家有极大的影响”。最后,他进一步表示,“中国此后将兴的新文学果将何趋,自然是不言可喻咧。若有人以为这就是文艺的‘堕落’,我只能佩服他的大胆,佩服他的师心自用而已!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注:沈雁冰:《文学与政治社会》,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9期。)可谓异常感慨,意味深长。 对于是否应写“血与泪”文学的问题,他指出:“处中国现在这政局之下,这社会环境之内,我们有血的,但凡不曾闭了眼,聋了耳,怎能压着我们的血不沸腾?从自己热烈地憎恶现实的心境发出的呼声,要求‘血与泪’的文学,总该是正当而且合于‘自由’的事。”(注:沈雁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92年8月1日第45期。)这样一些论断,显然比郭沫若的有关看法要高明得多,深刻得多。连郭沫若后来的《创造十年》中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当时的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沈雁冰当时“有些比较进步的思想”。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郁达夫这期间不想跟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继续对立下去,并想跟他们消除意气,友好合作。他于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女神〉之生日》一文,一方面认为“中国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各人都岌岌于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只知党同伐异,不知开诚布公,到了目下终至演出甲派与乙派争辩,A团与B团谩骂的一种怪现象来”。另方面又表示“想请目下散在的研究文学的人,大家聚拢来谈一谈,好把微细的感情问题,偏于一党一派的私见,融和融和,立个将来的百年大计”。为此,他倡议于8月5日晚上举行《女神》生日纪念会,以便“我们研究文学的人大家聚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谈我们胸中所蕴积的语言,同心协力的想个以后可巩固我们中国新文学的方略”。他还拉郭沫若到闸北去找郑振铎,请他和文学研究会的其他作家参加纪念会。而郑振铎也高兴地答应参加,并表示要多邀一些文学研究会同人出席,借此机会组织作家协会。果然,纪念会依期举行,地点在一品香旅社,到会的人除创造社作家外,还有文艺研究会的沈雁冰、郑振铎、谢六逸、庐隐等。会后,还拍照留念。但组织作家协会一事,却未能实现。而且,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与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作家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与隔阂,也没有从此消除,反而愈来愈尖锐复杂,彼此更加仇视了。
果然,郭沫若于1922年8月25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2期上发表《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它》,又挑起了跟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论辩。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详细地列举了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意门湖》(唐性天译)的译文错误,以说明文学研究会不负责任。同时,他对沈雁冰发表《〈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很恼火,说沈雁冰跟“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惯于使用“藏名匿姓,不负责任”、“吞吞吐吐,射影含沙”、“人身攻击,自标盛德”,“挑剔人语,不立论衡”等手法,不敢“堂堂正正地布出论阵来”,“怀抱琵琶半遮面”,“在那里白描空吠”。而对《〈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本身却未作只言半句的评析。显然,郭沫若这样的做法,纯粹是对沈雁冰进行谩骂。
沈雁冰受到郭沫若的谩骂后,也不示弱,于同年9月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8期上发表了《“半斤”VS“八两”》一文,作为答复。在此文中,沈雁冰先是对使用化名“损”作了解释,说它是“公开的化名”,“凡认识我的,大概都知道”,并非“胆小”而不敢用真名。同时,他认为《〈创造〉给我的印象》一文是由于郭沫若“党同伐异”的一句“激将法”激出来的,但是“并非轻看《创造》,和《晨报副刊》的《估〈学衡〉》是不同的。却不料因此又开罪了”。这表明,沈雁冰并不是把创造社作家当作像学衡派来加以否定的,而是作为新文学家看待的,所作批评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并没有大错。可是,郭沫若却对它那么反感,“以‘堂堂正正的’论阵来批驳”。因此,沈雁冰责问道:“难道大半页捕风捉影的‘空吠’——原词奉璧——就算是堂堂正正的论阵么?”此外,郑振铎也发表了致郭沫若的信(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9月1日第48期。),对他批评《意门湖》表示很感谢。并说明文学研究会之所以会出版该书,是因为该书的译成还在郭沫若译出此书之前,他们没有英译本,又没有注释完备的德日对照本,因而无从知道有无错误。但是,他也指出郭沫若在批评中“夹以辱及人格的谩骂”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关于沈君的一些话”,“太谩骂一些”。由此,在这一论辩中,谁有理,谁没有理,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还是很不服气。因而,当汪馥泉于1922年11月11日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55期上发表《“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一文后,创造社的成仿吾又站出来大肆攻击沈雁冰和文学研究会。汪馥泉提议当时的各个新文学社团的作家联合,成立一个“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共同从事有关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多项研究。在他的文章中,较详细地谈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的“打架”及其原因,表示希望他们能够消除隔阂,携手合作。该文发表后,沈雁冰、郑振铎曾公开发表致汪馥泉的信,阐述了对他的提议的看法,并解释了他文中谈到的有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和原因的误解和失实之处,态度较诚恳,并无伤害创造社作家之处。可是,创造社的成仿吾却不同。他于1923年9月10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1卷第4 期上发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一文,把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打架”的责任完全归咎处文学研究会作家,对沈雁冰和文学研究会作了异常明显的攻击。诸如说:“许多人笑沈雁冰只会批评别人,自己不能创作”,“文学研究会的一部分人对于我们不怀好意,已经是隐无可隐,加之善于变化的沈雁冰,实在那里指挥一切”,沈雁冰“是政潮中一位老手”,“已经不可救药了”。而且,他还声称“我们的使命在把他们的大帝国打倒”。更有甚者,他还利用梁实秋提供的沈雁冰的一个错译写成《雅典主义》一文,大肆嘲笑沈雁冰“不懂英文”,“关于雪莱差不多什么也不懂”,“他是不量力,大胆,不负责任”。这样利用他人发现沈雁冰的一个错译,就如此嬉笑辱骂,蓄意将他搞“臭”,实在是太过份了。对于成仿吾的攻击,沈雁冰等文学研究会作家没有答辩。他们所持的态度是:“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的,同人皆不愿置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所以成仿吾屡次因辩论学理而大骂文学研究会排斥异己,广招党羽,我们都置而不辩,因为我们知道与成君辩论是极没有意味的事。”(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4年7月1日第131期。)
创造社作家这样一再从翻译问题上责难文学研究会作家,他们却未能正视自己翻译德文作品时也往往出现错误现象。最突出的是,梁俊青曾于1924年5月12日、6月10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评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致郭沫若信》,一再指出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有许多错译。此外,他还指出成仿吾、郭沫若在《创造周报》上发表的译作也译错了许多德文诗。可是,对这些批判,他们不但不接受,反而对梁俊青作了诸多攻击,而且把矛头指向文学研究会作家。成仿吾在致郑振铎的信(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4年6月9日第105期。)中说:“对于这件事, 我以为编辑《文学》的诸君倒不能不多负一点责任”。郭沫若更是说,“在上海方面有一部分最卑劣的编辑者,怀恨私仇而又不敢正正堂堂以直报怨,时常假名匿姓,暗刀伤人,于是犹未快时更怂恿少年徒党妄事攻击。”(注:《郭沫若致文学编辑信》,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4年7月1日第131期。 )对于这些指责,沈雁冰、郑振铎以“编者”的名义答辩道:“编者的责任,只在于许多稿件选择文艺的技术不太差的,评论不太没有理由的,把它们发表出来,至于文中的辞句与理由,自有在题下署名的作者负责。”(注:《〈成仿吾与郑振铎〉按语》,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4年6月9日第105期。)“郭君有‘借刀杀人’之谈, 这就是郭君所言为隐指我们的证明。……然而可惜事实上证明出来,梁君和郭君成君认识的程度,实在十倍于和我们中间任何人认识的程度。事实上证明梁君决不是我们可以利用来‘杀人’的‘刀’”(注:《郭沫若致文学编辑信》,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4年7月1日第131期。)。 梁俊青也发表《我对于郭沫若致〈文学〉编辑一封信的意见》(注:《时事新报·文学》,1924年8月4日第133期。), 指出:“我那篇评论本想寄给创造社的,不料恰好我和成仿吾讨论郭君和成君在创造周报上译错了许多德文诗的问题,那时成君夜郎自大,不肯认错,我因此感觉到成君自骄自傲之不足与言,便将该文投至《文学周刊》,……‘文学研究会’何尝借刀杀人?我梁俊青又何尝借此以出风头?”这显然是对郭沫若所言作出的有力反驳。
论辩至此,沈雁冰、郑振铎表示,“郭君及成君等如有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注:《郭沫若致文学编辑信》,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4年7月1日第131期。)此后,果然双方未再继续论辩。 他们历时三年的论辩,终告结束。
以上所述,便是文学研究会作家沈雁冰、郑振铎跟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的论辩的大体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每次论辩几乎都是郭沫若等发难的,沈雁冰等人是不得已才答辩的;而且,前者谩骂多,说理少,后者虽然也有“礼尚往来”的“回敬”,但重在说理。那么,郭沫若等人为什么一再攻击文学研究会呢?其原因在于,郭沫若等人认为文学研究会“垄断文坛”,非把它“打倒”不可。或者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时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注:郭沫若:《创造十年》,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这确是颇为直率之言。
本文1999年6月收到
标签:文学研究会论文; 郑振铎论文; 郁达夫论文; 文学论文; 创造社论文; 文艺论文; 小说论文; 郭沫若论文; 神曲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