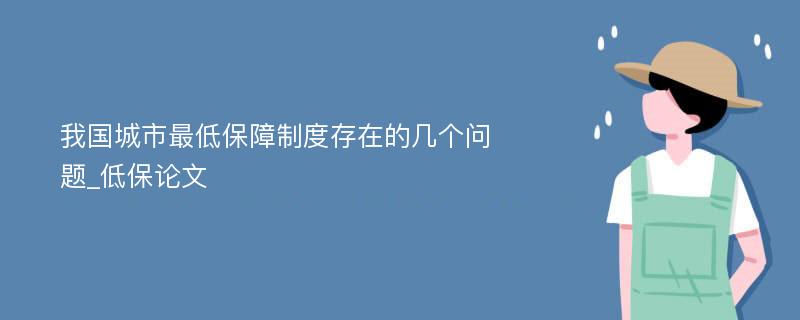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低保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低保”是圈内人士对“最低生活保障”的简称,低保制度的实施与低保工作的开展与我国城市贫困现象相伴随而产生。
贫困问题在我国一直都存在,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市中实行普遍充分的就业制度、基本均等的工资收入制度、粮油供应的价格补贴制度以较稳定的城市社会福利和救济制度,城市贫困问题相对很少。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社会政策的变化,导致城市人口的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发生了较大的分化。一方面,在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同时,收入差异的扩大导致部分低收入者的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城市中部分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滑坡,甚至出现企业破产的现象,因此导致一部分企业职工失业、半失业或收入不足。在各个城市中都出现了以失业、下岗和在职低收入为特征的新型城市贫困群体。据最新的估计数,目前我国城镇的下岗人员至少已超过1000万。(注:关信平著《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P26,湖南人民出版社。)
国外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参考了这一经验做法。当前,我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由三条保障线组成:最低工资标准线、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线。社会保障体系能否顺利建立和完善起来,对解决贫困问题以及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能否顺利到位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线”、“最后一道安全网”,对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外的经验也表明,对付因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结构转型而导致的较大规模的贫因问题,最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救助。实际上,在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赖以度过难关的正是提供失业救助、分发食品券和以工代赈等典型的社会救助手段;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其发展初期,也几乎完全是靠社会救助制度来维护社会安定的。(注:唐钧:《最后的安全网——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我国由易渐难的改革模式,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因此,必须建设好这一制度,以确保改革能够闯过“重重地雷阵”。
城市低保工作从1993年在上海起步,在试点不到两年时间里,又有厦门、青岛、大连、福州、广州、无锡等6个城市建立了这一制度; 到1998年底,全国668座城市中584座城市、1693个县中的1035个县政府所在镇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分别为87.4%和61%。全国所有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以及81%的县级市都建立了城市居民低保障度,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安徽、河南、广东、广西、吉林、辽宁、甘肃、青海等16省(区、市)已经普及了这项制度。(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讲稿》(“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管理人员第一期培训班”培训资料)。)根据民政部的要求,到1999年底,要在全国全面普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本文着重考察城市低保制度和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重要问题,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指出,能够有利于制度的完善和工作的顺利开展。
东西部“悖律”
到目前为止,全国多数城市已建立了低保制度。但是,在这些已经建立起低保制度的城市中,各自在低保标准、低保面、人员配备、资金来源、以及规范操作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具体表现为东部的低保标准较高、低保面较大、人员配备较多、资金来源较足、规范操作较齐;而西部则相反。
笔者于今年四月参加了民政部在武汉举办的“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管理人员第一期培训班”培训期间,访谈了甘肃L市、河南A市、湖北E市和黑龙江D市的民政部门官员之后,发现他们在谈到低保工作中的困难时,无一例外地提到了经费来源不足的问题。考察东西部各方面的差异,笔者觉得其中存在着这么一条“悖律”: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平均文化程度较高、人的择业意识灵活开放,因而需要通过低保接济的对象比例较小;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所以,财政状况较好,拿得出用于低保的那部分财政支出;在有较多财政经费来源而保障比例面不大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低保工作起步较早,操作也较规范,把应该保障的对象都纳入到了保障范围之中。西部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少,人的择业意识保守封闭,因而需要通过低保接济的对象比例较大;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财政状况较差,用于低保的财政支出捉襟见肘,非常紧张;在财政经费来源不足而保障比例面较大的前提下,西部地区的低保工作进展较慢,许多应该纳入低保范围的保障对象没有包括进来。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民政部99年底必须在全国各个城市建立低保制度的行政命令,许多城市采取了“下有对策”的方法。国务院97年29号文件规定,城市低保的保障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人员,第一是原来传统民政的“三无”救济对象,第二是失业人员,第三是职工,包括在职职工、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职工。据了解,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低保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保障的对象仍然局限于原来的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其余两部分对象则采用“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办法;有的地方采取出尽量压低低保线的方法(低于实测低保线),如L市98年实测应发125元,实发100元;还有的地方采取“宽进严出”的方法, 即家庭平均生活费高于低保标准的,马上将其剔除出低保对象范围,但严格控制新进来的人员;甚至有的应该纳入的保障对象,也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把他们挡在低保大门之外。在今年10月低保标准全国一次性调整之前,据22个省(区、市)的调查,已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市(县),测算的保障标准一般为90元至150元,实际执行的保障标准在70 元至120元之间,应保障的人数260万人,实际得到保障的仅有91万人;所需要的保障资金总额应为14亿元,实际只落实5亿元。 如按实际测算标准计算,这22个省(区、市)尚有169万人未进入最低生活保障网。(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讲稿》(“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管理人员第一期培训班”培训资料)。)
三条线衔接不紧凑
最低生活保障线、失业保险金、最低工资标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退休金)构成了我国城市保障制度的三道防线,这三条保障线建立的初衷是要在保障对象上分工负责、相互协调。但在实际的操作运行中,三条线之间衔接不紧密,造成一部分人员都未被三条保障线保障起来。虽然中央即将出台文件,解决这一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一问题仍将存在。三条线分属两个政府职能部门,难免会造成许多协调上的困难。
最低工资标准是针对在岗职工的,对于下岗职工发放的是基本生活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实行“三三制”原则,即由中央、社会保险、企业三家抬。中央的资金已经落实,社会保险的资金也能到位,但有一些困难,最麻烦的是企业这一部分。企业不能一概而论,涉及社会保障方面,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企业是主动地减员增效,企业原来的经济效益还可以,让部分职工下岗是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率,提高产品的利润率;另一种企业是被动地减员增效,企业本来的经济状况已经岌岌可危,让部分职工下岗,只是为了甩掉额外的包袱,企业并未扭亏为盈。前一种企业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本可以兑现,后一种企业的在岗职工都发不出工资,岂能负担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因而,“三三制”原则实行得并不彻底和不到位。
三条保障线的对象是层层向下过滤的,任何一条保障线的不到位,都会给保障工作带来麻烦,出现许多漏洞。比如说,一个并没有足额领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家庭,在按低保线标准实施“差额补助”时,是视同足额领取的。这样使一部分家庭实际的人均收入低于统计的人均收入,生活上的困难是“雪上加霜”。
中央、省属企业职工的生活保障
中央、省属企业在经济效益较好的年代,利润统统上缴中央和省里,没有给地方作出直接的经济贡献。现在这部分企业困难了,中央和省里却撤手不管,把包袱甩给了地方,这不符合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再加上新的税收制度的执行,许多中央省属企业较集中的地区的地方财政难以为继,比如兰州、武汉就存在这种情况。相应地,许多地方在中央和省里不管的前提下,也未将本地中央省属企业困难职工纳入低保范围。根据各省(区、市)对本地中央直属企业困难职工的调查摸底和测算,各地中直企业共有困难职工89万人,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困难职工家庭人数163万人,对这些人实施低保需要经费10亿多元, 而地方财政目前用于这部分人员的保障资金仅4555万元,中直企业困难职工家庭仅有7万余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绝大多数尚无着落。 (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讲稿》(“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管理人员第一期培训班”培训资料)。)
为此,许多民政工作人员建议,对中央省属在地方的企业的困难职工建立专项调剂资金,或者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协助地方一起保障这部分职工的基本生活,明确中央、省、市、区各级责任。
低保工作要有专人负责
实行低保制度以后,社会救助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三无”人员,社会救助经费也不再是一笔小数目的款项了,因而需要有专职专人管理。在这方面有的省市做得较好,但许多省市差强人意。省、市级的低保工作被归并到救灾救济处,而人员、编制、经费却没有相应地增加,许多民政工作人员只是兼做城市低保工作;在基层(街道、居委)更是没有编制、没有报酬,缺乏专人管理。这使得这项工作的水平难以达到应有的水准,须知低保制度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并且很讲究方法和技巧的工作,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有专业人员去管理。在许多国家,没有经过正规教育培训的社会保障工作专业人员是不能从事这项工作的。
保障对象应明确收入界定
保障对象的实际收入与统计收入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即前者低于后者,前者等于后者,前者高于后者。第一种情况在前面的叙述中已谈过,第二种情况是我们所希望出现的,第三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保障对象的隐性收入引起的,即应该统计而未被统计的那部分收入。这与我国个人收入透明度不高,居民收入监控体系不完善有密切关系。为此,在确定低保对象时又增加了一个限定条件“实际生活水平”,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指家庭人均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非农业户口的全体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就是针对在核查收入过程中遇到的如存款数量无法明确、隐性收入无法核定等情况而言的,特别是家庭人均收入表面虽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其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一般居民生活水平,对这部分人员各地普遍认为应不予保障。“实际生活水平”可因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而异,具体由当地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基层民政部门确定。一般规定:拥有价值超过3000元以上的非生活必需的高档消费品的,如空调、高档组合音响、移动电话、摩托车等等;金银首饰折合现金和有价证券、银行存款、现金累计人均达1200元以上者不属低保对象。但是,许多贫困人员是在最近才致贫的,因而不能根据家里的摆设去完全判断是否应纳入低保对象。
目前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把凡属就业年龄的健康人口一律视为已领取最低工资,理由是鼓励保障对象自强自立,防止发生养懒人的问题,但这一做法将那些真正就业无门的困难人员排斥在保障之外,有违最低生活保障的宗旨。
“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许多城市的低保制度实行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运作模式,这一模式是指:凡是贫困家庭中没有在职(包括离退休)人员的,救济资金由财政负担;而贫困家庭中有在职(包括离退休)人员的,救济资金由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负担;如果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确实没有能力负担,再由财政解决。例如广州市规定:月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家庭中,有在职人员的,由在职人员所在单位给予困难补助,资金由单位职工福利基金列支;无在职人员的,由民政部门给予社会救济,资金由市、区(县级市)两级财政分担,其中市财政只负担市福利事业单位收养的救济对象,其他对象的费用由区(县级市)财政负担。(注:徐驰、潘永红《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再思考》(《中国社会工作》1996年第4期)。 )这种模式内含了这样一个悖论:本来是单位效益不好造成了职工生活困难,而现在又要求单位为职工解决生活困难,实在是强人所难。(注:唐钧:《最后的安全网——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这种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 )“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意味着企业或单位之间的社会救济负担畸轻畸重。(2 )“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意味着企业或单位承担社会救济的管理和资金筹措的责任,不符合企业改革的方向,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3 )“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容易造成管理不集中、政策不统一、待遇不公平。(注:徐驰、潘永红《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再思考》(《中国社会工作》1996年第4期)。 )全国实行低保制度最早的上海实行的是这种模式,目前无单位的救助对象受助状况都已建档立案,有的区甚至已开始采用电脑管理;而有单位的救助对象因为受到条块分割的影响,居然至今尚没有一份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的完整的统计资料。(注:唐钧:《最后的安全网——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框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因而,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改变这种不良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