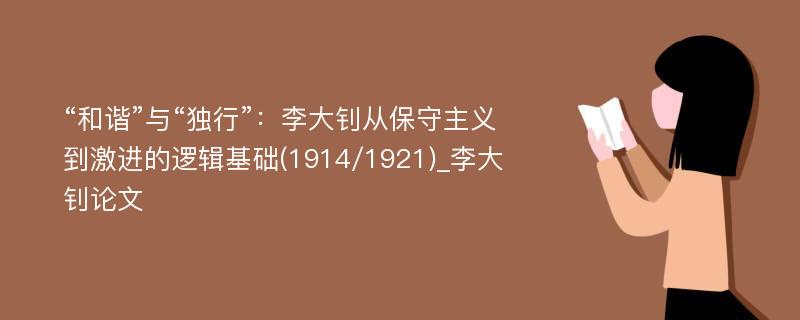
“调和”与“独行”:李大钊从保守到激进的逻辑依据(1914-192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独行论文,保守论文,逻辑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1-0059-06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给李大钊思想定性的论述文字。事实上,关于这个时期李大钊怎样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与论述并不在少数。这些文字已经散见于学术界出版的史学专著和学术论文中。这里,笔者关心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先哲究竟是在怎样一个心理状态下将两种分属不同畛阈的思想“自然”过渡或说打通的。就李大钊个人真实的内在思想底蕴而言,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时段(1914-1921)的李大钊在“前后”的哲学基点分别立足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注:关于这个观点的提出,也不是我的专利。它分别属于刘桂生、朱成甲先生以及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加鲁尚茨先生,参见《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但在“正统”研究路径中,把转变思想的理路多以“抛弃”、“否定”等词汇作为“转变”的前提。于是,“抛弃”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改良保守的态度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前提。这样,把两种思想的矛盾、对立看得很重,因此是一种去旧取新的思想路径,从而也就会把新旧之间、前后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予以冲淡,看重了变化的“条件”,而忽视了个人思想转化的内在“根据”。如果要考察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从传统中走来而对社会主义一往情深的,就不能不读李大钊,尤其是不能不寻找李大钊思想转化的逻辑依据。
“调和”:“共和”理想下的思想生成
关于民国初年调和论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不欲在此作更多的叙述。不过,这里有两点必须说明:其一,这是民国成立后不久就陷入南北府院之争的结果;其二,这是李大钊共和政治理想下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观测点。当时,李大钊随从《甲寅》,章士钊力主“调和”,他们都是从当下现实出发寻觅政治选择的诠释者。应该说,这是继民国以来袁世凯策划的“国情说”之争之后的又一次政治味极浓的思想话题。李大钊的“调和”之论当然即是这场大讨论留下的余音。自1914年至1918年,李大钊反复思索着政治文化的走向与出路,“调和”一词一度成为他笔下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无论是文化上的“调和”还是政治上的“调和”,思路都万变不离其宗:要养成“政治对抗力”。早在李大钊留日期间,他就深受梁启超、章士钊等人调和思想的影响,力主用“光荣革命”的和平形式来完成“新”与“旧”的转换。即使是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之后,他还是保持着平静的态度,主张在法律范围内实现两种力量的抗衡,从而在“对抗”、“有容”、“调和”的态势下走向“多元”、“并立”与“自由”。这完全是为了避免他在《大哀篇》里感喟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以暴易暴”理路[1](p550)。
他在1914年发表的一篇政论文章中说:“政本在有容”,“政本在有抗”,“盖衡平之宪法,成于对抗之势力。自两力相抵以维于衡平而外,决不生宪法为物,有之则一势力之宣言,强指为宪法耳。……然则对抗势力之养成,其首务矣”[1](p675-676)。李氏的这种思想积淀于心,在文化进化法则上同样显示出这一多元、自由的思想理路。他在一篇题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文章中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2](p43)李氏不“挟种族之见,以自高而卑人”的“平情论之”,带有很强的理性成分。在《调和之美》的“审美”、《辟伪调和》的“驳论”、《调和之法则》的“设计”、《调和誊言》的“主张”里,守常先生的立论都不曾离开“并立”、“竞存”的意念。如果用我们日常使用的“调和”之意来附会都是无法解读的。综合先生的“调和”思路,它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肇于两让,保于两存”;2.“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3.惟有双方,而无“第三者”;4.涵纳有容的并举精神[2](p33-36)。在李氏那里,太激进就会出现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惨剧;太保守又会因为传统势力太重而“沦于腐败”。为此,找到一种维持“竞立”格局的文化资源乃是当务之急。他反复述说“竞立对抗为并驾齐驱”之势的优长,目的只有一个——避免两种势力的复合为“一”。在李氏那里,“新”与“旧”、“古”与“今”、“缓进”与“急进”、“进步”与“保守”都不过是“名辞之争”[3](p718-719)。怎样处理“秩序”、稳定与“进步”、发展的关系是李大钊立论的中心,这也是每一位立足于现实的仁人志士所不能不关注的时代焦点。进化规则是竞争的规则,没有竞争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缺少了动力只能是社会活力的式微。还有更为清晰的思路在这里:“人类社会,繁矣颐矣。挈其纲领,亦有二种倾向,相反而实相成,以为演进之原。譬如马之两缰,部勒人群,使轨于进化之途。以年龄言,则有青年与老人;以精神言,则有进步与保守。他如思想也,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则有个人主义,有传袭主义则有实验主义,有惰性则有强力。”[2](p36-37)诸如《新的!旧的!》、《调和剩言》、《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这类带有明显自由、调和色彩的论点多是1918年中后期撰写的。这时李大钊已加盟《新青年》的编辑而成为陈独秀的“同仁”。即使如此,年龄比主编陈独秀小十载的李氏仍然“固执”个人的调和论。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发表之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早就把自己“去一取一”的价值趋向亮出来了。1915年创刊号上陈氏付梓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就完全与“调和论”背道而驰。即使是在主编的统筹下撰写并发表于《新青年》的《新的!旧的!》一文也非常不合杂志的“时宜”以及主编的“口味”。结果主编们只好在李文结尾处拖一尾巴:“守常先生要新青年创造新生活,这话固然不错。但我的意思,以为要打破矛盾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这一对“车有两轮、鸟有两翼”矛盾“合体”之“有益”的评论不是钱玄同一人的意思,而是《新青年》同仁们“整体”的倾向。应该说,李大钊1919年以前甚至在五四运动高潮之际,他那深沉的自由、多元的思想底蕴仍是其立论的哲学基础。
审视李大钊的转化前的思想,我们会在其“有容”、“调和”、“对抗”、“并立”、“竞进”等关键词中找到与自由主义观念相互“匹配”的哲学术语。就进化的“能量守恒”定律来看,李大钊的文论流布出的无非是“宽容”、“保守”、“进化”、“多元”、“制衡”、“不流血”等关于和平、调和、演变、过渡的意念。鉴于我们不是专论自由主义和李氏的关系,只是借此为下文转化的“逻辑依据”作铺垫,因此我们不妨将“自由”原则放在参考注脚里,下面着重分析一下这个思想资源在李大钊整个思想脉络里的意义(注:关于“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原则,可以参照美国学者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另外英国哲学家波普的《自由主义原则》也是重要的参考体系,见《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
应该看到,无论是“激进”取代“保守”,还是“新的”取代“旧的”,它们都是一种复制、克隆或说“轮岗”。漫长的极端权威主义的“吃掉”悲剧就在于:一方往往会在以“进步”面目出现的情况下激进得天翻地覆,可一旦打倒了另一方之后就会很快发展成为惟我独尊的“自大狂”。就此而言,新权威主义与旧权威主义确如李大钊说的那样“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因此民主自由的共和格局就是要有一个互相牵制约束对方的文化资源。为此,李大钊在力倡对“新旧”、“急缓”、“东西”一视同仁的同时,也用历史的教训告诫后人:“欧洲中世纪时代,保守主义与传袭主义之势力过重,其结果则沦于腐败。法兰西革命时代,则进步主义,趋于极端,不能制止,其结果处于爆发。是皆不能使二力有空间的交互动作之结果,以致反动相寻,不能并立于空间,则求代兴于时间。”[2](p38)这是典型的改良、进化、保守的思想路径。他将这一“调和”理论用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政治势力的相互牵制上,正乃对一元独尊的反动,也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和质地所在。
“调和”不患对立,而患“折中”。“调和”的归宿是“两存”,因此力倡涵纳“有容”的精神。在李氏那里,两者以上的调和“并立”则双美,单一则两伤。这正如“1”的一亿次方仍在元点一样,惟有以二元为起点的“多元”才会给社会带来生机与希望。
梳理李氏思想的理论源泉不难发现,他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进化论等西方思潮又时时触动着他的智慧。就传统的思想渊源而言,他与自己推崇的前驱谭嗣同、章炳麟等人有着相通的血脉。谭氏的“天地往来”、“不生不灭”等转换轮回的充满激进而又不能完全放开的观念,章氏的“苦乐共生”之“俱分进化”思想无不在“进化”的外衣下烙下了传统的印记。如果说推崇“心力”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那么传统思想里的老庄成分则成了他们的共执。“福祸相依”的转化观、“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天地论……,《易经》的辩证与“心”的力学尽在其中。李氏“调和论”中讲求的“对抗”、“并立”、“共进”无不展示出这样一个深刻的内涵。在这里,既有道德的容纳、宽厚,又有理性的辩证:“自舆氏有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服人且不可,况治国乎?而今之为治理者,辄欲滥施其力,以图苟安;受治者亦知求所以对抗,以维两力之平。”[1](674)李氏意在挖掘传统中的积极因子以“养成”良好的政治模式。也许,这正再度应验了波普所说的“自由主义原则”:“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在一块无传统的‘白板’上合理地设计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由主义原则要求,社会生活所必要的对每个人自由的种种限制应当较少到最低限度,并应尽可能做到均等(康德语)。”[5](p144-145)守常先生强调的“矛盾生活”“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但可以“转化”、“代谢”原则,无不昭示着“共和”的意义[4]。
不过,先生在“和”的同时并不为“庸”,在“调”的过程中亦不“中”。事实上,他对中西“周而复始”的进化观有自己新的理解,是一种“打通”后的生命轮回观念。如果我们根据以上关于对抗的分析以及新旧相依的研究就得出了无所谓良莠的“相对”论,那就失去意义了。我们看到,李氏强调的“车有两轮,鸟有双翼”,只不过是为了让新的事物更踏实地进步。同是那篇《新的!旧的!》一文就可以佐证。他在这篇关于新旧的文章里,“种种联想”可以说是非常具体,单就“民国”与“清室”、信仰“自由”与规定“尊孔”的权衡已经能说明问题。与谭氏、章氏的“轮回”一样,李氏的“相牵相挽”在思想倾向上显然是偏袒“新”。只是这“与时俱新”的路径不愿意流血而已。不然,这种“相牵相挽”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一“新”的含义使他在中西之间加上了“俄”这样一位“第三者”,于是他原有的“调和”格局也就不能不打破了。
“一力之独行”:新理想的诱惑
李大钊是一位坚信“新陈代谢”法则的进化论者,为此他在走向现代的道路上表现出的“道义”感十分突出。初始,他也和其他先驱一样,曾对左右中国大局的权势者抱有一定的幻想。希望借此力量在不付出太大代价的情况下将民族引向强大的国度。如上所述,反“一力之独行”、谋“各个之并立”曾是李氏的价值取向,他还是“调和论”的力倡者。可就在这些立场流露的同时,李氏又以“无可奈何”的理由“食言”。他一方面承认“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最好的办法是不用暴力手段而达到美好的目的。然而,他又清醒地告诫国人,在一种非人的暴力统治下生活,如果一味地担心代价问题,一味地忍受暴力的摧残,又何时是一个苦难的尽头呢?应该说1917年至1918年这一时期是李大钊“调和”与“独行”思想十分胶着的两年,也是他思想非常痛苦的时期。针对梁启超辈对革命者的一再非难,李氏为自己即将“出手”的“一力之独行”的拳头辩护说:“盖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虽不必尽为暴力之反响,而暴力之反响则必为革命;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必召革命。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3](p744)“和平”解决当然是上策,但若是和平不能解决问题也绝对不排除革命动武的可能性。不言而喻,李氏离“革命”的“合力”思想已经不远矣。
就在李大钊发表那篇名为《暴力与革命》的文章不到一个月,俄国爆发了影响整个世界的“十月革命”。这个对中国人民命运产生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事件很快被这位“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的嗅觉敏感人士所瞄准,李大钊像“飞毛腿”导弹一样.紧紧抱住了“赤旗”。1918年7月,抱着对自由向往的兴奋,他在《言治》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毫不掩饰地亮出了自己“革命”的底牌:“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悲观也。”[2](p58-59)李氏自以为找到了“舍此其谁”的真理,而且对俄罗斯的由乱而治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情景也应该采取这种“长痛不如短痛”的方式“快刀斩乱麻”,痛快淋漓地解决问题。在通常意义说,对一位思想先驱,这一膨胀很可能就是他辩证威力的式微。请看:“人道的钟声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p110)李氏的革命性情终于在1919年完全而彻底爆发:“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亚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2](p287)这时的李氏已经将“社会主义的道理”扛在了自己的“铁肩”上。及此,他的理论武器也由过去的对抗“进化”论转化为争斗“阶级”论。在“竞争”的链条上,李大钊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想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2](p287)
将“阶级争斗”作为取得自由的手段当然就要有暴力革命的发生,而眼前的这一切又都要求自己躬行以前自己曾经反对过的一切。诸如“一力的独行”、“好同恶异”等等“专制”的后遗症。从“民主主义战胜”到“庶民的胜利”,再到“Bolishevism”的胜利”,直至“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先驱者走了一条九九归一的道路。[2](p228-232)
对此,李大钊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将这一观点表述得相当透彻,大有非将众人拧成一股不可的味道。他的道路是要“根本解决”,而且是合情合理的“解决”,先生不紧不慢地假设道:“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2](p310)而这个“根本解决”的道路又必须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我们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2](p304-305)此时,“散沙的自由”与“各个的并立”完全不能适应“趋同”的需要,为此他提出了“世界大同”式的“人类联合”策略,目的是来个整体性的“翻身”[2](p154)。
创造性转化:过渡的逻辑依据
从李氏思想发展的线索来看,有两点最为值得注意:一是从对“人”到对“众人”的器重,这是他后来唯民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的基础;二是从“调和”进化论到“争斗”阶级论思维的打通,这是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化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重要依据。
就李大钊一贯的思想脉络来看,他的民本思想早在“五四”之前就有了深深的伏笔。在1916年的《民彝》创刊号上,李氏以《民彝与政治》为题将他理解的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与中国“民为本,君为轻”的传统紧密地拧在了一起。与其接受其他西方思想的方式一样,李氏首先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上“引经据典”。他在“四书五经”中左右逢源,《诗经》“大雅”恰恰有其需要的“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单就“彝”字的考证他还颇费心机地“说文解字”:
诠“彝”之义,古有殊训。一训器:宗彝者宗庙之常器也。古代宗法社会时代,即祭即政。盖政莫始于宗庙,器亦莫重于宗彝也。故称其重者以概其余而为百器之总名……彝亦训常,《书·洪范》云:“彝伦攸叙。”彝伦者,伦常也,又与夷通用。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夷,平也。为治理之道不尚振奇幽远之理,但求平易近人,以布帛菽粟之常,与众共由。……《书》曰:“永弼乃后于彝宪。”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3](p335)
鉴于李氏的“知识考古”万变不离其宗,因此他很容易为“民本”思想找到充足的原始依据:民彝是天意的再现,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他从“器”、“常”、“宪”三个字入手解析,将主权在民、民是政治主体的道理进行了多维的阐发。最后的结论是:“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显然,这里的“民”还带有反封建意义的“自我”、“各个”成分。不过,尽管此时李大钊“民彝”的理论生成还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但是在向“民”一边倒倾向上却为后来进至“一力之独行”的群众运动埋下了伏笔。事实上,李氏的“民彝”离“民意”已经不远了。
从“散沙之自由”到“一力之独行”,李大钊有着与鲁迅先生一样的思想痛苦经历。鲁迅的“说法”又何尝不可当作李氏的心声:“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就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6](p190)承认这么一个事实,就不能不在“大众化”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目标。读解以下文字就可见一斑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2](p183)何以故?原来都市的生活“有许多罪恶”,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农村”乃是带有浓烈“乌托邦”色彩的地方。思想的“悔改”改出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预示着意志论影响下的“唯民主义”时代的来临。
过去学术界同仁说起“世界观”的转变多以抛弃前者接受后者作为“进步”的表现(注:这种观点十分普遍并流行于众多的历史教科书中。鉴于它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表述,这里笔者不再枚举。)。其实,这即是自相矛盾的表现,因为这些人恰恰把“知人论事”这一基本分析方法忽视了。就李大钊思想的“进步”来说,笔者认为他在这方面有一个创造性的转化。
就李氏的理论背景而言,他在“进化论”与“阶级论”的思想格局里容易找到打通的润滑剂。一是两者都有手段与目的对立、统一的双重因素。在前者,“竞争”是手段,生存与进化是目的;在后者,“争斗”(“阶级竞争”、“战争”)是手段,“互助”、“大同”是目的。相形之下,除却前者目标感较弱,是一种非自觉的进化外,在手段与目的的逻辑构成上堪称殊途同归。将“斗争”与“互助”置于进化的层次来说,它们在手段和目的上都有较强的自觉意识。因此,“五四”时期的不少激进的先觉从进化论进至阶级论就不那么突兀。二是两者都强调对抗、竞斗,尤其是注重性质截然不同双方的同时存在。李大钊1916年在其论文里曾这样反复述说其“群演之道”:“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道也。”[3](p384)接着他还曾将“二体以上,互争为存”的思想扩展为:“乾坤,一战局也。阴阳,一战象也。”[3](p569)这位以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作譬喻的“互为抵抗”专家很快于1919年找到了“阶级社会自灭的途径”——“阶级斗争”。
一方面要博爱——让世界充满爱,而另一方面又要激起仇恨满腔。这个艰难的选择使他无法回避:“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以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以战争而进化。”同时又坚信“这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2](p286-287)李氏究竟是怎样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呢?这位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有意无意地为自己的转变打了个“化约”式的圆场。就是在一篇“集大成”的文章里,他还专门论述了自己所作的两方面的理解。他说:“与这‘互助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说。”注意,“仿佛”的使用很是到位,原来,李氏“一直”认为两者并不“相反”,而是“相承”。为了消泯斗争而斗争,这就是李氏逻辑的全部。[2](p286)
上面引述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发表于1919年7月6日的《每周评论》。我觉得这是研究李大钊思想转变不可不读的一篇重要文章。读解李文不难发现,李大钊的“互助”以及“大同”理想起源于人道主义,而其“阶级竞争”的归宿点也是肇始于人道主义。在该文一开始,李氏就在西方思想家那里挖掘“互助”爱心的根据,并义无返顾地认定“协和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而社会主义则是符合这一伦理法则的“主义”——“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沿着这一思路,他又根据Kropotkin的“互助论”(“Mutual Aid”)中找到了生物学的依据,得出最终的结论是“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和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他说:“总结一句话:相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2](p286-288)“斗争”或说“争斗”的目的是为了“友爱”生活的到来。“斗争”是不得不、也是不能不采取的“最后”手段。
“物心两面的改造”:世纪之交的历史评说
关于“心的改造”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李氏早期的文章里诸如“精神”、“意志”、“意念”、“悔改”等方面的论述即是他的心力意志表现。“互助的原理”也正是他以往“心力”思想顺理成章的发展。而“物的改造”则是新的历史进程中的新学说。这即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实现经济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在李氏那里,“物心两面的改造”即是客观世界的改造与自我心性的改造。不过,在提倡并驾齐驱之共同“改造”的同时,先驱还是倾向于“经济”范畴里的“争斗”优先的原则。这在哲学上也非常符合物质与意识关系之辩证法。后来,李大钊的这一“两面改造”思想被他的追随者毛泽东所接受并发展,《实践论》里所说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说法与李的思路如出一辙[7](p285)。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并认为“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2](p231)。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前辈的李氏率先遇到了毛泽东后来也遇到的问题。从他们所认可的唯物史观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足支持他的“经济变动”论点。
“物质”总是有限的,而且条件是具体可见的;而“心力”则是“无限”的,而且在理论上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在“心力”的作用下,什么权威、实际都将化作乌有。这一大事业情结之理论颇似渊于谭嗣同、章炳麟等先驱的宗教轮回信仰之说。不过,这一精神圣火的点燃虽然有佛教教义推波助澜,但主要还是中国传统里的神秘文化成分在起作用。《庄子》、《易经》以及其他大思想家“天问”式的拷打、基督教里的耐苦精神令其顿生百折不回之志:“青年锐进分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周执其易,以其无持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3](p384)这种神秘的色彩几乎可以说与佛法相近了。但其中的关键或说主题词还在于“无限的青春”之运用。无始无终、无限无极的思路已经将自我膨胀到了“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伴随着自我的这种膨胀,个性却恰恰打了个反差。从个体的有限走到全体的无限,这个过程模糊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个体—投入整体的洪流就会力大无比、气魄无限。可若是冷静的想一想,就个人的实际能量而言,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作为人的能量基本上是守恒的。也许,一个人受到启发、教育、宣传后精神会不一样,但即使如此,还是不可把个人的“心力”神化。这在李大钊和他的同仁后来思想的发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成熟的思想轨迹。
综上所述.李大钊对“中庸”、“调和”、“轮回”思想的吸收同时也说明了我们传统里并不乏自由主义的“多元”精神资源。因此,将李大钊的转变说成是“不破不立”式的“抛弃—接受”,就不仅是对历史本身、历史人物的化约,也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化约。21世纪的史学研究不但应该汲取这样的教训,也不应该在思想史的研究上的“事故多发”。就李大钊的精神个案而言,先驱者对个性发挥、人格独立的认同也是从一个具有初步自由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前提。
【收稿日期】 2002-11-06
标签:李大钊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新青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