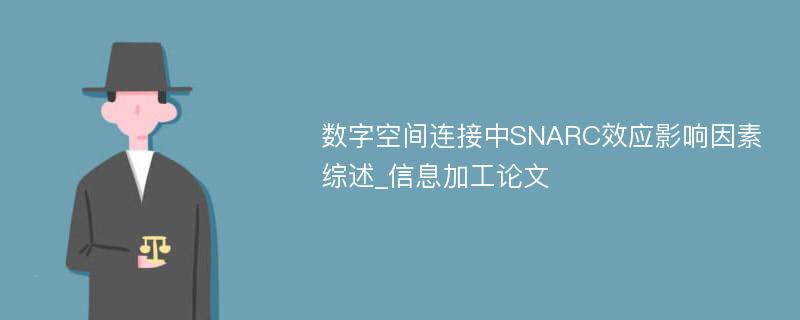
数字—空间联结SNARC效应的影响因素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效应论文,因素论文,数字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数字的出现是基于人类对生存环境认识的需要,并在空间和时间上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描述生存环境的方式。自产生以来,数字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数万年的不断进化,人类不仅具备了很强的数字加工能力,而且能够精确地把握事物的具体数量和对抽象符号所代表的数量信息进行加工与操作。但在过去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里,人们都直觉地认为数字加工是一种抽象的、脱离实物客体的非空间认知活动,除一些心理符号操作所必需的技能外,数字运算似乎不需要空间信息的参与。但大量事实表明,数字加工和空间信息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数字加工的对象是各种具体或抽象的实物客体,而这些实物客体在空间上都有其特定的分布特征,这就自然地将数字加工与空间信息联系起来。另外,研究发现,数学能力和空间技能之间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伟大的数学家们,都在不同的场合明确强调视觉空间想象在他们的数学思想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而约有15%的正常成人报告出数字的视觉空间表征。这些事实表明,数字表征与视空间的协调整合并非什么稀罕现象。早在1880年,Galton就首先注意到这一点,他用十多年不断收集上来的数据证明了空间与数字表征之间的关系。最近的十多年,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先进现代研究技术的应用,数字加工的空间表征问题越来越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已成为当前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2 数字—空间联结的证据
2.1 SNARC效应的发现
1990年,Dehaene、Dopoux和Mehler在一个被试间实验设计中采用1~99(不包括55)的数字为目标刺激,让被试判断数字是比55大还是小,其中前一半被试被要求当出现的目标数字比55小时用左手按键反应,后一半的被试则要求用右手按键反应。结果发现,前一半被试的反应明显快于后一半被试[1]。这一结果引起了Dehaene等的兴趣,之后Dehaene等改进了实验方法,采用完全被试内实验设计,以阿拉伯数字1~9为材料,以判断数字奇偶为任务。结果发现,当屏幕中央出现小数字的时候,被试左手按键的速度明显快于右手,当出现大数字时,右手按键的反应速度明显快于左手[2]。Dehaene等将这种空间和数字的关联现象命名为空间数字联合反应编码效应(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ffect,SNARC效应)。该效应的发现表明,数字的心理表征是在空间上被编码的,并且数字的这种空间认知加工是快速、自动化的。目前,SNARC效应已成为探讨数字加工与空间注意关系的重要方式。
2.2 SNARC效应的解释
对于这种现象,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1)Dehaene等认为数字奇偶判断任务中数字大小表征是自动获取的,这种表征可能与心理数字线(mental number line)有关,即数字大小沿着从左到右的心理数字线方向进行空间编码,小数字表征在心理数字线的左侧位置,大数字表征在右侧位置。当数字在数字线上的心理空间位置与反应位置的存在是一致的,那么反应是快速的;相反,如果数字在数字线上的心理空间位置与反应位置不一致,则反应会减慢[2]。(2)Proctor和Cho的两极对应理论(polarity correspondence theory)认为,分配到每一个刺激和反应上的极性取决于它们的维度相对特性,与知觉或概念相似性不同。两极分类能够产生刺激与反应间的图式,当相同极性(“+”或“-”)被确定为不同实验情景维度(如刺激和反应)时,它们之间将产生联结。当这种两极性被运用到数字加工领域时,“右”和“大”将存在正极性“+”,“左”和“小”则存在负极性“-”。数字与空间联结的产生是因为刺激和反应的极性产生了重叠,并与知觉、空间或概念性的重叠无关。这种基于不同维度正负极激活的理论,不仅被应用于SNARC效应的解释,也被应用于非数字的实验情景中[3]。(3)Gevers等的双路径模型(dual-route model)认为,数字大小能够通过不同的信息加工路径(条件和非条件路径)控制动觉反应,条件路径可通过言语指令以灵活方式控制动觉反应,非条件路径则传递刺激与反应间的前存在联结的自动激活。这两种信息加工路径是平行激活的,它将导致数字大小与反应编码联结的产生及影响反应的速度和准确率。在一致试验条件下,条件和非条件路径产生相同的刺激与反应联结,从而减少反应的潜伏期和增加反应的准确率;相反,在非一致试验条件下,两种路径将激活不同的刺激与反应联结,由于条件路径激活正确反应,非条件路径激活协调反应,因此反应潜伏期会增加,准确率会降低。激活条件路径所需的时间越长,非条件路径影响动觉反应的强度就越大。因此当足够大的非条件路径激活影响反应阈限时,错误反应将产生[4]。
3 数字—空间联结的影响因素
综合已有文献,对于影响数字—空间联结SNARC效应的因素可以归纳成以下四类变量:数字刺激、空间信息、文化和年龄特点。
3.1 数字刺激
数字刺激变量包括个位数、多位数、负数、数字格式等,这些数字信息都能够自动激活数字的空间表征。
3.1.1 个位数
早期关于SNARC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使用0~9的阿拉伯数字刺激上,如Dehaene等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对0~9的阿拉伯数字做奇偶判断,结果发现无论是奇数还是偶数,对于较小的数字左手反应总是比右手快,而较大数字则相反,右手反应比左手快[2]。其他研究者采用奇偶判断任务和数字大小判断任务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Bull等在实验中让被试对逐个呈现的探测数字(取自0~9,但不包括5)与参考数字5相比较。并要求被试,当探测数字比5小时按鼠标左键反应,比5大时按鼠标右键反应。结果发现,对于小于5的数字,按左键的反应较快,而对于大于5的数字,按右键的反应较快[5]。这些结果表明,数字大小信息能够自动激活数字的空间表征。但数字的空间表征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能够根据当前的任务需要动态地对数字在心理数字线上的空间表征进行调整。Dehaene等把数字分为0~5和4~9两种区间,要求被试对呈现的数字做奇偶判断。结果发现,当所判断的数字4和5被置放在0~5区间里时,右手反应比左手更快;而数字4和5被置放在4~9区间里时,则出现了相反的结果[2]。这表明数字的空间编码依赖于当前任务的具体要求,对于给定的数字,它的空间联系介于空间位置与数字相对大小之间。
3.1.2 多位数
数字与空间联系能否出现在多位数字上呢?Dehaene等使用0~19的阿拉伯数字对此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SNARC效应并没有明显地延伸到两位数字里。为此他们认为,心理数字线很可能只局限在一位数字的表征上[2]。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认可,因为两位数字的奇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右边数字决定的(如13的个位数字3决定了该数字的奇偶性),而且被试很可能已经使用了这种选择性注意策略。Dehaene等早期对数字大小判断的研究也发现,当探测数字(如45)比参考数字(如65)小时,左手反应比右手更快;反之,则右手反应比左手更快,这表明两位数字是能够在空间上被编码的[1]。而Brysbaert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当较小数字出现在较大数字左边时的反应要比较大数字出现在较小数字左边时更快,从而也发现了两位数字的SNARC效应[6]。这说明两位数字所表达的数字意义是能够在空间上被编码的。
但目前关于两位数字在心理数字线上是如何被表征的还存在着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两位数字是被整体加工的(holistic view),即各种数字区间能够按照任务要求被投射到一个单独的、类似连续统一体的心理数字线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位数字是被分解加工的(compositional view),即个位和多位数字是被分别进行心理表征的。尽管整体加工论最先被提出,但最近的研究证据表明,在加工两位数字时十位数和个位数是被分别表征的。如Ratinckx等通过观察掩蔽启动效应,研究了两位阿拉伯数字的命名潜伏期。结果发现,如果启动数字和目标数字在相同的位置上有着相同数字,则对目标数字的命名会更快(如启动数字是18和21,目标数字是28);相反,当启动数字和目标数字在非一致性位置上共享一个或两个数字时,数字命名的潜伏期将会减慢(如启动数字是82、86或72,目标数字是28)[7]。因此他们认为在认知加工的早期阶段,两位阿拉伯数字在数字构成上是以十位和个位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这表明个位数字和十位数字存在着不同的表征。尽管目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还不是很明确,即分开和整体效应是如何整合成一个单独加工模型的,但数字任务中对各种刺激操作所产生的效应在获取数字的认知表征上有着相当的灵活性。
3.1.3 负数
对两位数字空间表征问题的探讨,也为研究心理数字线是否能够延伸至负数上提供了参考。根据心理数字线假设,人们在对数字进行运算时倾向于把小数字与左边空间、大数字与右边空间相联系,就好像在大脑中存在一条从左向右逐渐递增的数字线,如果数字线能够向左延伸到负数上,则左手对负数的反应会比右手更快;当数字对与空间表征一致时,在负数对上左手的反应比右手更快(如-9,-7),而对于正数对右手的反应会比左手更快(如7,9)。为此,Fischer采用数字大小判断研究了加工-9~9阿拉伯数字对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他把数字对分为空间一致性和空间不一致性两种形式,并要求其中一半被试对数字对中较小的数字做判断,另一半被试对较大数字做判断。通过分析数字大小与反应手位置的相互作用,来判断负数的心理表征是否延伸至0左边的数字线上。结果发现,左手对负数的反应要快于右手,而右手对正数的反应要快于左手。这说明负数是可以被表征到心理数字线上的,但不像正数那样是以相同的方式与空间产生联系的[8]。之后,Fischer等采用奇偶判断任务的实验结果也表明,如果在数字-9~9中间增加一个固定参考数字0,这时负数就将与左边空间相联系。此外,Shaki等为了能够在负数背景下产生空间表征激活,设计了两种实验控制条件,即在一种条件下正数对和负数对是在分别的试验组里进行比较,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将正数和负数混合形成正负数对比较。结果发现,在混合试验条件下,左手对负数的反应比右手更快,右手对正数的反应比左手更快,从而获得了SNARC效应;而在负数对单独比较的条件下,也获得一个倒置的SNARC效应[9]。这说明心理数字线是能够延伸至负数上的,只不过与正数相比,负数的空间联系可能缺少自动性。
3.1.4 数字格式
数字信息能够以多种方式传递,既可以阿拉伯符号、罗马符号、手语符号、点数符号或数字单词的形式表达,也可通过视觉、听觉或触觉的方式呈现。如果SNARC效应确实需要通过数量的抽象表征,那么数字格式的变化将不会对SNARC效应产生影响。为此,Dehaene改变了实验条件,用法文数字单词取代之前的阿拉伯数字,结果发现了一个与阿拉伯数字相似的SNARC效应,而且SNARC效应的函数斜线与数字大小变化趋势相同[2]。这进一步支持了数字与空间的关系反映数量抽象表征的观点。之后,一些研究者采用不同语言符号所表示的数字(如英文数字、荷兰文数字、法文数字、中文数字等)也都发现了SNARC效应[10],这说明数字的这种空间表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它不受数字符号具体表现形式的影响。此外,启动范式的研究也为数字表征模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Reynvoet等的实验结果显示,当启动数字和目标数字相同时,被试的反应速度最快,而反应时会随着启动数字和目标数字之间的数字距离增加而延长,但这种距离效应不受启动数字和目标数字是否以相同或不同格式呈现的影响[11]。
3.2 空间信息
3.2.1 反应的空间位置
数字信息的心理表征是在空间上被组织的,因此SNARC效应需要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结构。目前关于这种参考框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数量信息是以观察者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作为参考框架编码的,即自我中心编码(egocentric coding);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数量信息是以一些非身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框架编码的,即非自我中心编码(allocentric coding)。为了探讨这种涉及SNARC效应的参考框架,Dehaene等在实验中要求被试使用交叉手对奇偶数做按键反应,即交叉手的左手按右键对偶数反应,而右手按左键对奇数反应。结果发现,在大数字上,按右键(用左手)的反应更快;而对于小数字,则按左键(用右手)的反应更快[2]。这表明数字信息的空间编码并不是使用手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反应的相对空间位置决定的。这一结论得到了使用单手按键反应实验结果的支持,Fischer的实验结果表明,当要求被试使用一只手按左边或右边的按钮来判断数字的奇偶性时,也能获得SNARC效应[12]。这说明数字信息并不是特定于身体的某一部分上被空间编码的,而是能够自动灵活地被分配到不同表征定义的参考框架中。但张丽等的研究结果却发现,只有身体位置和反应手完全一致时才出现SNARC效应,说明认知主体的身体形式对SNARC效应产生了影响[13]。
一些研究在除使用手以外的其他反应器和非二选一按键反应的其他任务上也都发现了SNARC效应。Fischer等的眼动实验结果显示,当要求被试对小数字进行判断时,眼跳至左侧方框的潜伏期短于眼跳向右侧方框;而对大数字进行判断时,眼跳至右侧方框的潜伏期短于眼跳向左侧方框。这表明,数字从中央视野移动到左右两侧视野的眼动启动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大小和眼睛移动方向之间的关系[14]。这些眼动研究结果也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表明,SNARC效应发生在早于反应器选择的加工阶段:首先,眼跳幅度并没有受到呈现数字大小的影响;其次,在手动和眼动反应的两种奇偶判断任务中,均出现了相同大小的SNARC效应。
3.2.2 数字信息的心理表征
Bachtold等认为,不仅是反应的空间协调系统,同样数字信息的内在表征在SNARC效应的产生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为此他们设计了这样的实验,首先在实验一的训练阶段给被试呈现刺激图片下方标示有11个刻度的尺子图形(表示11cm),图片中央呈现1~11(不包括6)的任意一个数字,要求被试对呈现的数字刺激做出是否比“6”cm长的判断;接着在正式实验里,让被试以想象尺子的形式取代练习时刺激图片下的尺子。实验二的程序与实验一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要求被试把呈现的数字想象成为钟面上的时间,如判断所呈现数字是否比表示时间的“6”点早或是晚。结果发现,当要求被试把刺激目标想象成为尺子上的数字时,产生了SNARC效应;而当想象成是钟面上的时间时,则出现了倒置的SNARC效应[15]。这表明数字信息的内在心理表征能够对SNARC效应产生影响。同样,这种数字心理表征也反映在一些脑损伤病人的案例上。如由于一侧顶叶受损而导致半球忽视症的病人,通常在线段分半任务中表现出向中点右边判断的偏向。Zorzi等为了验证这类病人是否也会在数字分半任务中表现出向右偏向,他们要求右顶叶受损病人说出两个数字的中间数(如3~7)。结果发现,这类病人会将数字6认为是数字3和7的中间数。Zorzi等认为,这是因为这类病人在对中间数进行判断时忽视了他们心理数字线的左边位置,因此才会将数字区间的中点指向偏右的位置[16]。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忽视只出现在与数字有关的加工上,而在其他类型的序列刺激(如月份、字母)上并没有发现。这进一步表明了数字与空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动态和表征的过程。
3.3 文化因素
3.3.1 阅读书写习惯
Dehaene等认为SNARC效应反映了后天获得的阅读书写习惯[2]。由于数字加工研究中的被试通常遵循从左向右的阅读方向,因此这种认知策略可能会从字母、单词和句子加工领域转移至数字和等式的加工中去。为了支持这种观点,Dehaene等对那些习惯从右向左阅读方向的伊朗被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些伊朗被试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SNARC效应。Dehaene等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被试习惯于把小数字与右边空间、大数字与左边空间相联系的缘故[2]。Zebian的研究也支持了这种观点,她发现当把较大数字置于较小数字的左边时,生活在贝鲁特的本地阿拉伯人更容易对这些数字进行运算。此外,Maass等对精通阿拉伯语和英语的被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这些被试身上所表现出的SNARC效应有减少的趋势[17]。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不同文化环境下人们的阅读书写习惯确实会对数字的空间表征产生影响,但并不意味着阅读书写习惯本身就是决定心理数字线方向或产生SNARC效应的主要因素,因为其他一些与数字线有关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数字的心理表征,如数字与空间位置的联系可能是早期学校教育对数字线训练的反映,或者是一种对文化特性探索策略的表达。
3.3.2 手指数数习惯
一些研究者认为,使用手指数数的习惯可能是引起数字与空间之间产生联系的原因。Butterworth的研究发现,使用手指数数是儿童解决简单数字问题的一种普遍方式,特别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大多数儿童都喜欢用他们左手手指逐一地列数物体,这就很自然地产生小数字与左边空间和大数字与右边空间的联系[18]。Conaut在报告中也指出,在206名美国学龄儿童中,几乎所有的儿童一开始都是使用他们的左手数数的,这种习惯也会对他们的空间数字认知产生影响。Fischer的研究发现,“左手开始数数”和“右手开始数数”两组被试之间在数字与空间联结效应的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手指数数习惯确实会影响个体的数字心理表征[19]。
3.4 年龄特点
3.4.1 婴幼儿的数字能力
一些发展研究表明,言语习得前的婴幼儿不仅能够辨别数字和连续数量,而且还能运算简单的加法和减法。Starkey等采用观察时间的习惯化恢复实验方法(habituation-recovery of looking time)对婴幼儿的视觉数字辨别成绩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婴幼儿天生就具有对数字的辨别能力,而且6~8个月的婴儿已具有了跨通道的数字匹配能力[20]。Wynn采用“期望违背范式”(violation-of –expectation paradigm)对婴儿的简单数学运算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婴儿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1+1=2或2-1=1的最简单数学运算期望,并能够对一定情景内的物体进行抽象编码[21]。这些研究结果也引发了研究者对这种早熟的数字能力机制源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能力反映的是对“数感”的操作;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能力在本质上并不是表示数字的,而是反映早期视空间能力的操作的。有研究进一步证明,这种涉及空间认知的数字能力是在婴幼儿发展的晚期阶段获得的。如Rourke等的研究发现,视空间学习混乱与数学技能的延迟或发展异常有关。
3.4.2 儿童的数字空间表征
对儿童处理数量信息方式的探讨,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数字和空间之间的联系是怎样产生的。尽管现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视空间能力在数字加工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明确说明数字表征是如何在空间上被编码的。因此有必要从发展性的和跨文化的研究中进一步寻找支持SNARC效应的证据。Berch等较早对此进行了探讨,他们采用数字奇偶判断任务探讨了2~8年级儿童的数字空间表征能力。结果发现,从小学三年级(9岁)起,儿童才开始表现出明显的SNARC效应,即使数量信息是无关的,也能自动地获取这些信息。它表明,该年龄阶段的儿童已能够自动激活数字大小在心理数字线上的空间表征[23]。Wood等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到了9岁,儿童才能表现出明显的SNARC效应[24]。而van Galen等对7~9岁儿童的研究却发现,当数字大小是相关时,所有儿童均表现出SNARC效应;而当数字大小是无关时,只有9岁儿童表现出该效应。为此研究者认为,7岁儿童已能够像成人一样表征数量信息,但需要理解阿拉伯数字时,直到9岁他们才能够自动地获取数量信息[25]。Imbo等近期采用空间和言语两种数字大小比较任务,考察了9岁和11岁儿童的SNARC效应。结果发现,在9岁和11岁儿童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显著SNARC效应,主要是受言语编码影响的结果[26]。此外,潘运等的研究也发现,内源性和外源性线索条件下,中小学生在数字加工任务中所表现出来的SNARC效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增大[27]。
4 展望
综合以上研究,尽管很多实验结果证明了数字大小与空间之间存在着编码上的联系,但实际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关于SNARC效应的延伸。以上所探讨的是关于数字刺激本身与空间之间的编码联系,除了数字刺激,这种空间表征是否也能够存在于那些含有顺序信息的非数字刺激之中呢?Dehaene等早期的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对字母进行判断时,在字母和空间之间并没有出现可靠的联系[2],相同的结果也出现在使用元音或辅音材料的研究中[12]。但Gevers等采用字母和月份作为刺激材料时,这些刺激材料却表现出明显的SNARC效应[28]。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问:究竟数字信息的哪些方面会被空间编码呢?数字不仅能够传递数量信息(如5辆公共汽车),也能表达顺序信息(如第5辆公共汽车),还能代表被命名的信息(如5号公共汽车线)。这些不同的数字意义可能被不同表征系统所传递。如果数量和顺序信息都能产生SNARC效应,那么可否这样假设:被空间编码的是顺序信息的属性,而不是数字的数量属性。换句话说,数量和顺序信息可能是被分别表征的,但却被相同的内在属性所辨别。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数量或顺序信息是被一种共同表征所操作的,但结果取决于任务要求,因为数量信息在等级上也包含了顺序信息。Marshuetz等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发现对非数字刺激顺序属性进行反应的脑区在数字加工任务中也能被激活[29]。目前对这方面的关注还相对较少,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从那些包含顺序属性和数量属性的不同刺激材料来进一步检验SNARC效应。
第二,关于引起SNARC效应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素引起SNARC效应产生的,目前研究者们还存在着争论。尽管现有很多研究都借助心理数字线来解释SNARC效应,但毕竟这只是研究者们为了能够解释数字空间表征效应所提出来的一种假设,现有脑神经科学研究还尚未发现数字选择神经元图形组织符号的存在,因此这种心理数字线的比喻不应该被照搬套用。将数字与空间联系起来只是作为人们使用知识和技能策略的一部分,而且这些联系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任务的要求。此外,这种数字空间联系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挑战了数字线比喻的适当性。如Schwarz等的眼动实验发现,不仅水平方向,垂直方向也存在SNARC效应。由于SNARC效应出现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相似位置上,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取代心理数字线存在的心理数字地图假设[30]。因此,今后的研究可考虑进一步扩展空间数字联系的研究领域,从众多视空间与数字大小相关联的任务出发,这样才能够积累更为全面和丰富的证据,而不仅仅局限于心理数字线的这一种解释,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数字的认知表征。
第三,关于SNARC效应的发展关键期。关于SNARC效应的发展关键期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尽管一些研究表明,学龄儿童已能够对数字进行空间表征,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儿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空间和数字技能。因为他们不可能在这些快速的判断任务中表现出反应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而且这些任务也不足以在更小的儿童身上侦测到数字与空间之间联系的存在。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更为简单的行为任务如觉察任务或分半任务,来进一步探究儿童身上有关数字空间编码发展关键期的证据。
标签:信息加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