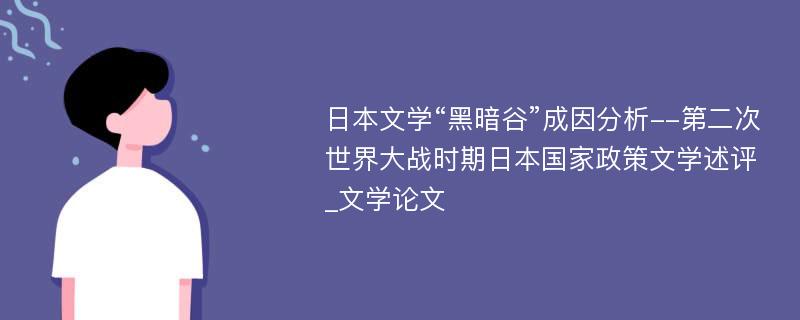
日本文学“暗谷”之成因探析——二战时期日本国策文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述评论文,探析论文,文学论文,成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文学(一般指1935-1945年左右)是日本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暗谷”时代。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非常时期,日本的文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各种角色。反对战争,以隐讳的方式进行艺术抵抗者有之;逃避现实,冷眼旁观者有之;违背良心,顺应时局者有之;为战争鼓噪,摇旗呐喊者亦有之。明治以来建立起的日本近代文学,几乎被法西斯狂潮摧残殆尽,军部策划下的国策文学代替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而成为文坛主流。以战争文学为首的御用文学大都艺术水平低下,起到了渲染法西斯侵略战争,鼓动民族情绪,鼓舞士气的作用。这种文学与政权的畸型结合,是完全背离日本文学精神和传统的。这一现象的出现绝不单单是一个文学范畴的问题,它涉及日本的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等领域。文学既反映时代思潮,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时代思潮,二者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这十年尽管是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却是承前启后,联结近现代文学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根源的研究,是日本近代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环。然而一般文学史对这十年的文学多是一笔带过,专论更属罕见。本文拟围绕这一主旨做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战时文坛的风云变幻:1936年第一个国策文学团体“文艺恳谈会”出笼,标志着法西斯当局对文艺控制的开始;1937年对文艺宣传报道进行军方控制的“内阁情报部”成立;同年9月林房雄等第一批特派记者赴中国战场采访,成为作家从军之开端;1938年1月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无产阶级作家被点名禁止写作;石川达三的反战小说被禁止发行;8月《麦子与士兵》畅销,象征着国策文学的登场;9月“笔杆子部队”结成,标志着文学家与军部协作体制的形成;1939年国策文学泛滥;1940年7月彻底清除左翼出版物,禁止30余家出版社的130多部作品发行;10月“大政翼赞会”成立,表明文坛已纳入军国主义新体制;1941年11月强征作家从军;1942年5月“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标志着文学家全面协助战争……这十年间,凡是不协助战争的文学团体、刊物一律遭到查禁、解散、封闭,进步人士被剥夺了言论自由,甚至受到迫害,文坛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侵略战争必然要使文学、艺术隶属于统治权力,日本当局一步步从思想上、组织上控制文化领域,压制言论自由,使知识分子屈服于战争政治。为了使战争顺利进行,政府不仅要把经济生产、国民生活,而且要把意识形态领域也统统纳入战争的轨道。
法西斯当局除了使用高压手段强制文艺为战争效力之外,还十分重视对国民的思想教化。1937年5月,文部省为实现“明彻国体,滋养、振作国民精神乃当务之急”的目标,编篡了150多页的《国体的主义》,下发全国的学校和教化团体。这本国民教科书开宗明义地宣称“大日本帝国永远奉行万世一系的天皇皇祖的神敕来统治,此乃我万古不易之国体”。进而阐述根据《古事记》、《日本书记》“肇国”之由来,申明“国体”在日本历史上显现之样式,敦促国民的自觉。这本教科书的实质在排斥以近代欧美思想为主干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观念,回归“国体的本义”,要国民进行举国思想改造,建设所谓“新日本”。接着,当局又颁发《臣民之道》,进一步贯彻皇国主义。
在如此的思想教化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追随当局的宣传。他们“醒悟”到,明治以来日本虽然一味地西欧化,然而西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不适合日本人以“家族爱”和“仁爱精神”为基础的国民性的。自己是日本人,应深以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为耻,应彻底“清算”这些思想,达到对于家族的国家的自觉。
文学家中的追随者首推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者”林房雄,以及自由主义作家出身的“转向者”菊池宽等。他们可谓是自发地、积极地完成这一思想改造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林房雄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三次入狱,并参与创立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1932年出狱后,提出批判政治优先的主张,否定文学对政治的从属,开始“转向”。1941年相继发表《勤王之心》、《关于转向》等文章,提倡赞美天皇的日本主义,批判无产阶级政治主义,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在行动上也是积极的战争协助者。1937年作为首批《中央公论》特派记者赴战地;1938年参与组成国策文学团体“新日本文化会”,翌年发行会志《新日本》,宣扬民族主义和日本主义,并成为右翼文学团体“日本浪漫派”的同人。他还积极参与“满洲国运动”、“汪精卫政权运动”。从“翼赞运动”到大东亚战争,林房雄与日本当局的动向积极呼应,不遗余力。他在战后仍不思改悔,1963年发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公开赞美战争,美化战争;1972年发表《悲伤的琴》作为给三岛由纪夫的镇魂歌,坚持顽固的军国主义立场。
林房雄的180度大转向,影响所及,导致了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学家出身的转向作家去从事国策文学的写作,于是,战争文学、农民文学、生产文学、大陆开拓文学、历史文学等开始泛滥。此类作品,不敢正视现实,采取妥协态度,协助了国策的推行。
火野苇平曾经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转向”。1938年以伍长的身份随军来中国参加徐州作战,以从军日记形式一气写成了战地报告文学《麦子与士兵》、《泥士与士兵》、《花与士兵》三部作品品,作品详细记述了种种战地见闻和自身的感受。出版后,迫切想了解前线情况的日本人民争相购阅,加之新闻媒介大肆宣传,使《麦子与士兵》创下了120万册的畅销记录。
小说把日本侵略中国称为“两国间的战事”,对日军野蛮杀戮中国人避而不谈,只是细腻地描写中国山河、风土人情、士兵行军的艰难,以及所到之处中国人对日军的奉迎。读后令后方的日本人为本国士兵流泪,更加蔑视中国人,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和对战争的狂热。小说是在删除了27处军方不满意的地方后才发表的,因此,其“真实性”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蛊惑性,起到了军部所所起不到的宣传效果,对民众的毒害很大。它与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大相径庭,《活着的士兵》中描写了战争的残酷与恐怖,以及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野蛮杀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战小说,因此,刚一出版即被军部禁止发行;而《麦子与士兵》则由于顺应国策,受到当局的赞赏,成为战争文学的开山之作。此后,模仿此类战争手记形式的作品大量登场,如上田广的《黄尘》、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江》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站在肯定战争的立场上来写的,并没有真正描写出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鉴于文学作品的巨大社会效应,当局开始积极筹备“笔杆子部队”,即选派作家从军,为战争进行宣传。
“转向”作家岛木健作1937年的作品《再健》由于以肯定的态度描写狱中不转向的共产党人并对农民运动进行反省而受到禁发。作者迫于这种压力,四个月后又发表了顺应国策的《生活的探求》,主人公骏介在农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成为战争体制下理想的青年形象。这部作品成为农民文学的先驱,在它的刺激下,作家们对农村和农民的关心高涨起来,失去劳动力的农村逐渐受到重视。岛木健作等30多名作家组成文学团体“农民文学恳谈会”,他们的作品基本上被限定在协助执行国策的框框内,文学价值明显下降。
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转向后写了取材于“满洲”开拓移民的《先遣队》,开创了“开拓文学”,间宫茂辅的《矿石》等作品把范围扩大到了大陆与海洋。这些作品均不同程度地受到统治权力的压迫,未能发扬真正的文学精神。
参加过无产阶级运动的藤森成吉,以《渡边华山》开历史文学之先河,此外还有高木卓的《遣唐船》,中山义秀的《碑》,本庄陆男的《石狩川》等等。对日本历史关心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作家无法描写现实而产生的逃避态度。
国策文学中虽然不乏较为优秀的作品,但是却被当局利用来加强战争宣传,推行国策。一部分作家,特别是为数不少的“转向”作家或是被迫、或是积极地充当了这一不光彩的角色,一时间国策文学泛滥,文坛凋敝,日本文学进入了日本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不毛时期。
与林房雄相“媲美”的是身为文艺家协会会长的菊池宽。他协助内阁情报部,积极推行作家从军政策,从人选到亲自带队,竭尽效劳之能事。他在把文坛与政府相联结来推行文学国策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原本是大正自由主义、合理主义文学家代表的菊池宽随着时局的进展“乐天地转向”,蜕变为活跃的战争协助者。1940年5月,菊池宽倡导大后方文艺运动讲演,亲自率队进行八城市讲演旅行。此后,几个月内陆续向台湾、中国东北、朝鲜等地输送了50余名作家,拼命为侵略政策进行宣传鼓动。同年六月,竭尽全力协助近卫内阁的“新体制运行”;1941年被选为文学家爱国大会的会长。
尽管强权政治使得一些文学家为战争效力,但从文坛整体来看,积极协力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作家则是勉强应付或以沉默表示抗议。有少数作家进行了有限的艺术抵抗,人数虽少却延续了日本文学精神,永远名载史册。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战争时期的文学杰作作为昭和文学的一个完成而值得特别评价。”(注:清水孝纯《近代日本文学史》,第254页。)宫本百合子、金子光晴、永井荷风、高见顺等作家所做的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文学抵抗令人钦佩。他们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即使在法西斯淫威下,仍然能够保持文学家的良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相比之下,一些作家的跳梁则为文坛所不耻。
二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资产阶级文艺观斗争的焦点。马克思主义艺术观一向倡导完美的艺术形式与健康进步的思想内容的高度统一,任何偏废都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林房雄等人正是从鼓吹艺术至上开始,逐步倒向日本主义,走上为反动政权效力的歧途的。
林房雄在《关于转向》中写到:“转向不是单纯的方向转换,而是人的更生。光是赤裸身体不行,用冷水清洗也不行,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才行。”“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日本人心灵的永久支柱,……也许可称为主义,却不是使人殉身的大义。”“国民的精神支柱必须从国民内部产生,必须是3000年传统的必然结晶。”他要表明的是,仅仅丢弃马克思主义,当一个普通市民还不算完成“转向”,应成为一个具有“对国体无比自觉”的臣民,为效忠天皇尽臣子之道。其所谓“大义”不外是体现封建愚忠的武士道;其“国民的精神支术”则旨在鼓吹狭隘的民族意识的“大和魂”。林房雄由批判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义的“第一次转向”到鼓吹为皇权政治效忠的“第二次转向”,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换,由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蜕变为彻头彻尾的日本主义者。林房雄、小林秀雄等人,以《文学界》为阵地,与右翼文学团体“日本浪漫派”的保田与重郎等同流合污,对左翼文学家和自由主义文人加以打击,宣扬国粹主义,民族排外主义,排斥其它进步杂志。他们作为支持战争的精神支柱,左右着战时的日本文学界。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转向风潮,转向作家成为国策文学的主要支柱。
火野苇平正是深受超国家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毒害而自觉地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典型。他在随军征战的严酷条件下,不顾一切地奋笔疾书,短短几个月就写出了洋洋数十万字的三部作品,如果不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创作冲动,是难以完成的。那么他的创作冲动是什么呢?请看他的自白:
“日本民族,日本人这个枷锁是绝对的。当祖国危急时,挺身而出有什么错呢?对祖国的爱,保卫她的热情,为她献身又有什么错呢?……今天对杀戮的肯定,即是为人类新的结合的呼唤,必须如此。”(注:火野苇平《昭和文学全集》,小学馆出版社,1989年,第13卷,第776页。)由此可见,他的创作动机是所谓的“国家爱、民族爱”,是作为日本国民为国尽忠。因此,素有“庶民作家”之称的火野苇平,便毅然加入士兵行列,努力去用笔描绘为国出征的士兵们的“雄壮”气势,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战后的一片批判声中,也有部分日本评论家提出,《麦子与士兵》中存在某种程度的人道主义,果真如此吗?请看一看下面这段描写:
几发炮弹在身边落下炸裂,又有几人牺牲了。我对这样随便地伤害宝贵的生命感到无比的愤怒。把一个人的生命培育至今所花费的精力难以描述。这些士兵都拖家带口,都是我国最重要的人。他们无不在胸中珍藏着凯旋之日的梦想。一发偶然的炮弹竟在一瞬间把一切葬送了。……我并不是惋惜为国献身,只是无论如何不能压抑这满腔的愤怒。对于如此折磨我们的同胞,威胁我生命的支那兵,我充满强烈的憎恶。我要和士兵一起出击,亲手杀死敌兵。我感到祖国这个词汇给我注入了一股暖流。……我要在我临死的时候,用敌我双方都能听到的声音高喊“大本帝国万岁”。(注:火野苇平《日本文学全集》,集英社出版社,第67集,第115页。)
由此可见,作者的所谓人道只限于本国的士兵,而对别国人的生命却视如草芥。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反对一切非主义战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格格不入。战后,火野苇平虽然对自己战时的表现有所愧疚,一再表示要写出“真正的战争小说”,可是从他战后所写的《青春与泥泞》可以看出,他始终未能冲破原有的思想局限,尽管他对战争、民族、国家等问题进行了许多思考,却始终没有真正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血腥的战争才能解决纷争,实现人类的大同。这种唯心主义史观决定了他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绝不是少数战争狂人,进步的民主势力必将战胜邪恶势力。
战后一些日本评论家还有一种奇谈怪论,把小林多喜二与火野苇平相提并论,声称他们两人虽迥然不同,但同是政治优先文学思想的牺牲品,对此本人实在难以苟同。小林多喜二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战士,他为捍卫真理,为祖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惜生命的大无畏精神受人景仰,他是日本民族的骄傲,虽死犹荣。相比之下,火野苇平为法西斯卖命,虽荣光一时,却为自己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战后他的文思渐渐枯竭,未能有所建树。
除国家主义等反动思想毒害的作用外,名利的诱惑也是导致国策文学泛滥的因素之一。在大多数老作家冷眼旁观之时,菊池宽等不甘寂寞,力图维持其文坛重镇“形象”,异常活跃,出尽风头。众所周知,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只要甘当顺民则生命可保,若积极为当局效力,即可衣食无忧,名利双收。当选派从军作家成为宣传的一大热点时,作家中出现一片骚动,对于年青作家来说,此乃提高知名度的极好机会,如果入选,不仅标志着自己文坛地位的提高,而且可得到忠于天皇的国民的“荣誉”,所以应征者为数不少。而负责人选的菊池宽更是重权在握,为选出使众人心服的人选而煞费苦心。以火野苇平为例,他虽以《粪尿谭》获芥川奖,却仍不为人所知,而一部《麦子与士兵》却使他一夜之间身价百倍,成为红极一时的“国民作家”,这对渴望成名的新人来说不啻是极大的诱惑。
以菊池宽等为领队的“笔杆子部队”被谑称为“诸侯旅行”,行前受到隆重欢送,并得到大笔费用,所到之处被奉为上宾,荣耀非常(当然,太平洋战争时强征作家入伍又另当别论)。如若阵亡,家属还会得到可观的抚恤金,可见当局对御用文人待遇之优厚。在这种局势下,一向与政治无缘的文人墨客,或为保身和生计,或贪图名利,或受反动思想迷惑,于自觉不自觉中倒向了反动政权一边,迷失了自己,迷失了方向。
战后文学家被追究负战争责任而榜上有名者达40多人。这本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反省的大好时机,遗憾的是被导向政治优先的问题上。似乎文学如果不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独立于政治之外,就可以避免国策文学的出现。殊不知文学是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根本不存在超脱现实的文学,只有真正反映和表现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对于日本文学家而言,若不彻底清算“天皇至上”、“大日本主义”等根本认识问题,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战后,三岛由纪夫由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文学家蜕变为军国主义者的现象是发人深省的。
三
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决非偶然。三岛由纪夫所竭力鼓吹的武士道精神,正是军国主义强权政治的精神基础。武士道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它已积淀在日本民族的思维模式、道德意识的深层,一遇到民族问题,就会沉渣泛起,形成产生军国主义的温床。
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导致日本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把持了国家政权,把国家一步步推向战争的深渊。军事封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着天皇的旗号推行扩张政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同时,日本的神道与国家结合,成为国家神道,更加控制了日本国民的精神阵地。法西斯分子利用国民的民族感和对天皇的崇拜心理,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叫嚣由“大日本”来统治亚洲以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这种论调激发了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也竭力鼓吹“脱亚论”、“国家主义”、“日本主义”等侵略扩张主义思想,为法西斯侵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少数文学家为战争服务,直接原因是对法西斯势力的畏惧,间接原因则是对30年代以来日益发展的文学领域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屈服。这种倾向在1942年左右达到了顶峰。珍珠港一战的胜利以及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果使国民陶醉,文学家们也融进了高呼万岁的狂热之中。1942年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即是一个几乎全体文学家都参加了的协助战争的组织。
然而,一切忘图用武力征服别国的不义之举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侵略战争不仅使被侵略国生灵涂炭,也会给本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场战争使日本付出了250万人(一说310万)生命的代价,仅投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就使十几万日本人丧命,至今日本人对核武器仍是谈虎色变。
遗憾的是,战后50年来,日本政府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一直讳忌莫深,出现了不顾历史事实,粉饰侵略,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等奇谈怪论,甚至有人硬说对“三光政策”的控拆是“白发三千丈”式的夸张。此外,在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问题上,一再让中国及被侵略各国深感失望。可见,日本国内一直潜存着一股反动逆流,这与日本民众对民族意识的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密切相关,是值得日本广大有识之士加以警惕的。
战后初期,文学领域对战争的反思是令人鼓舞的。以民主主义文学、“战后派”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文学,在战争的废墟上吸取了血与死的民族教训。作家们结合自身的感受和经历,从多角度、多层次对战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运用现代派表现手法描写这场战争给日本民族带来的苦难与心灵创伤。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强烈的时代感、反战意识和探索精神正是战时勤皇文学的反馈,是被压抑的能量的爆发。一些战争中写过御用文学的作家也开始反省自己的错误认识(如岛木健作等)。经过战争的重创,一度凋零的文学百花园又重放异彩,涌现出如野间宏的《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以及堀田善卫的《时间》等一大批揭露战争残酷的佳作。可以说,战争与战败摧毁了日本人原有的道德观、价值观,从而使日本的战后文学得以超越传统文学的框架,与世界文学接轨,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
尽管战后文学对人和社会的反映,在深度、广度以及表现手法上均大大超越了战前文学,但总体上仍偏重于个人、家庭,缺乏广阔的社会视野;对战争的性质、天皇制等问题未能进行深入的剖析;未能揭示这场战争不仅给本国人民,而且给别国人民造成的浩劫,即从加害者和被加害者双方的立场,全方位地探索战争本质的小说没有真正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日本经济的复苏,从50年代起,日本文学又逐渐把视角转向日常生活,题材日渐狭窄,具有思想性的作品为平庸的迎合民众口味的商业出版物所替代,而“武士道精神”、“大和魂”等狭隘的民族意识尚未来得及得到应有的批判与清算,战后文学就已逐渐走向衰退和解体。正是借助这一温床,战后派作家三岛由纪夫最终发展到了为法西斯招魂、殉身的可悲下场。这一事件使广大日本人民清醒地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
以大江健三郎为旗手的战后新一代文学家继承“战后派”的文学精神,努力挑起批判狭隘民族主义的重担。大江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文学主题是“实存主体”与他人的“共生”。他把视野从日本扩大到了人类整体,这确实是对日本文学传统的狭隘性的一个新突破,其积极探索的一面极为难能可贵。大江文学的开拓性及世界性视野,使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1989年,当大江健三郎去韩国作“世界是否还记得广岛”的电视演说时,韩国作家金芝河毫不客气地向大江发问:“为什么日本人在谈及广岛之前不先问一下自己下面的问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其象征性事件的南京大屠杀、强征民工、从军慰安妇问题以及对亚洲人残忍的压迫、拷问等等呢?问一下日本有没有从内部进行自我净化,清除掉所谓把亚洲从欧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论调呢?”这一尖锐的指责给大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也是值得日本广大作家加以深思的。
日本“暗谷时期”的文学失落可以使文学家从中汲取反面教训,能够从更广阔、更深层的视点出发探讨人类命运的问题。我们期待日本文学能冲破民族意识的局限,不仅限于艺术手法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内容上多产生视野广阔,既体现民族特点又具有世界性的文质兼备的优秀作品,不断继承发扬日本文学传统。这不但是文学家的使命,也有赖于日本社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只有植根于肥壤沃土,才能结出累累硕果。
标签:文学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日本文学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作家论文; 战争论文; 菊池宽论文; 日本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