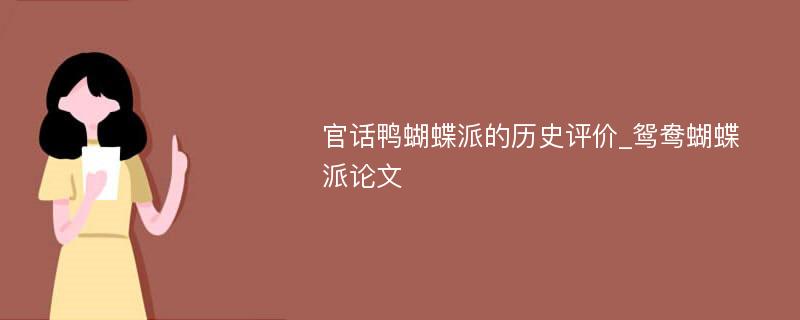
历史地评价鸳鸯蝴蝶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评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一直受批判贬斥,能对其给予公正评论的不多。本文从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历史渊源,作家的创作活动及作品的思想取向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认为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鸳鸯蝴蝶派 通俗小说 趣味性 民族特色
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派”)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遭到多次抨击、批判。到它的后期,除了对张恨水在抗战中的作品有所肯定之外,其名声一直被贬。在解放后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中,更被斥之为“文坛上的逆流”,“辛亥革命后小说的反动”,“是当时新文学发展中的狡猾的敌人。”这些充满刀光剑影的言辞,固然欠妥;深省一下过去学术界对鸳派的评价也不难看出有不少是违背历史的。鸳派是有其思想局限的,可是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鸳派在随着这一形势,经由旧文学走向新文学这一跨时代的演变过程中,其功过如何,应得到怎样的历史评价?是新文学的同路人、朋友,还是反对者、敌人?他们是顺应、追随时代潮流前进,还是螳臂挡车,阻挠新文学的向前发展?历史应该给予公正的评论。本文力图从这些方面作些探索,以求还鸳派本来的面目。
一
鸳派的出现,是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作为一个文学社团、流派的“实体”,它确是不存在的,它不象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那样,有发起人和参与者,成立组织,公开向社会发表宣言,宣布组织的宗旨和规章,提出文学主张,出版刊物和丛书。平襟亚在回忆鸳派这一名称时,谈到“在1920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某日,松江杨了公作东,请友好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叙餐。”席间,杨了公“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诵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后来大家对“鸳鸯蝴蝶”入诗又展开了评论,“刘半农认为骈文小说《玉梨魂》就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该列入‘鸳鸯蝴蝶’小说”。“这一席话隔墙有耳,随后传开,便称徐枕亚为‘鸳鸯蝴蝶派’,从而波及他人。”刘半农后来还为此顿足叫冤,说这“不过一句笑话,总不至于名登青史,遗臭千秋。”[①]可见,鸳派这个雅号是公众取的,而且是在他们小说风行了十几年以后的1920年取的。至于哪些人是鸳派作家,“历来也不曾在哪儿见到过一份完整的名单,只在人们心目中约略有个数而已。”[②]象包天笑、周瘦鹃,也只是因为“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发祥地是上海,但执笔者大多是苏州人,他们也有过一个小的组织,叫做‘星社’,主要人物有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范烟桥等”这一关系,才把他们也算鸳派人物了。原先众人取鸳派雅号,指的就是他们创作了“鸳鸯蝴蝶小说”,也正是鲁迅所说的,鸳派小说就是以“佳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鸳鸯,一对蝴蝶一样”,其“命根”就是“那婚姻问题[③],明显是指《玉梨魂》之类的言情小说,或与言情内容有关的社会小说。可是后来有些人扩大化了,把历史、侦探、武侠、公案、黑幕等小说,统统划入了鸳鸯蝴蝶派小说范围,这就失去了雅号原有的针对性,也与鲁迅所说的鸳鸯蝴蝶派意思相悖。由于这原因,就什么帐都算到鸳派身上,批判力度也不断加大,这是极为不公的。其实起于清末盛于民初的鸳派小说,和历史、武侠、黑幕等各类小说,只能统称为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五四时期为了区别于新文学,开始把它们称为旧小说或旧文学,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而传统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小说,在发展中有其独特的内涵,既已约定俗成称为鸳派,当然未尝不可,可是把其他各类小说也归之于鸳派小说,岂不风马牛不相及了。
看一个文学流派的进步或是反动,重要的一点,要看它在文艺上的追求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需要。1917年出现的文学革命,反对者只是那些维护地主阶级或封建买办阶级利益的文人,而鸳派的作家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之初,就已运用白话进行章回体小说的创作了,其代表作家包天笔,在自己创办主编《小说画报》创刊号上(1917年1月)的短引中,深有体会地指出,“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文学。”可是“今忧时之彦亦以吾国言文之不一致,为种种进化之障碍”。于是在《例言》中,又提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这与同年一二月《新青年》刊出的文学革命发难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的倡导,可说不谋而合。他们与文学革命的方向一致,指归相同,在总体上是与时代同一步伐,维护社会发展变革的,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进程中是作出了贡献的。从鸳派的作品看,它们属传统的通俗小说,源于明代的《玉娇丽》《二度梅》、清初的《玉娇梨》《花月痕》等言情小说,自然会受到传统继承关系上的思想局限。但它未必如人所说,鸳派在“散布封建伦理观念”,“代表了垂死的地主阶级和新兴起的买办势力在文艺上的要求。”鸳派的早期代表作《玉梨魂》(民初发表于《民权报》,1913年9月出版单行本),它所揭示的爱情悲剧,主要目的还在于抨击封建社会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婚姻不自由的痛苦”。年轻寡妇梨娘衷情于来家中教书的落难才子何梦霞,但迫于封建婚姻礼教的压力,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终于在病中拒服药石殉情而死。这正是梨娘对迫害她的罪恶封建社会的一种抗争,可是批判者却错误地认为作品宣扬了梨娘“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封建贞操观念。何梦霞在深受刺激后,也有所醒悟,发出了“励我青年,救兹黄种”的呼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武昌革命,最后战死沙场。小说写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而揭示的是社会问题,主要倾向是激起人们对社会的怀疑和否定,这是有进步意义的。周瘦鹃的《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的是知识青年陈宗雄在辛亥革命战争中受伤致残,而其年轻貌美的妻子待他仍一如既往,可是陈宗雄的伤残日益严重,他为自己死后爱妻的将来考虑,要她委身于昔日的同窗好友洪秋塘,毋须为他守节。这分明表现了一位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可是批判者却说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情调,它迎合着‘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买办资产阶级消遣的口味,而对青年,正是一种宣传消极绝望人生观的思想毒药。”这与事实相距多远!
《礼拜六》是鸳派产生影响最大的阵地。如果鸳派真像一些批判者所说的“代表了垂死的地主阶级和新兴起的买办势力在文艺上的要求”,那他们必然在这块阵地上要竭尽全力去维护这种“势力”的统治地位。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当年 《礼拜六》的主编周瘦鹃在《花前新记》里自称“是个十十足足、不拆不扣的《礼拜六》派”。“当年《礼拜六》的内容……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不一定都是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并且我还翻译过许多西方各家的短篇小说”,他认为《礼拜六》的作者,也包括自己在内,“有一个莫大的弱点,就是对于旧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所以在文艺领域中,就得不到较高的评价了。”[④]这是尊重事实的回忆,是对他自己当年任主编时的检查和客观评价。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对辛亥革命时期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鸳鸯蝴蝶派现象,用某一种文艺思想或某一流派的审美观点去整齐划一地衡量评价,认为“不高谈革命”“不知斗争”的作家作品,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逆流,是代表了垂死的地主阶级和新兴起的买办势力在文艺上的要求的阶级敌人。应该承认,文艺批评实际上是存在排他性的,但应该客观而不是专横,尤其在对方的审美情趣、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与自己的认识、理解有不同时,更应该客观地了解这一流派的过去和现在,认真地分析这一流派的创作是否与整个时代的方向相一致。周瘦鹃是“不折不扣”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他对自己和鸳派大本营之一的《礼拜六》的分析评价,在鸳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五四时期,在由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演变中,它们经过清末民初的一段过渡时期后,与新文学接轨虽有一定距离,但他们是和时代潮流一同向前的新文学的同路人、朋友,方向始终是一致的。特别要看到,象周瘦鹃他们的作品还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性,《真假爱情》《为国牺牲》等作品,在当时帝国主义企图瓜分吞噬中国的时候,确能起到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作用。周瘦鹃曾自叙,当年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他就写过《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等多篇爱国小说,以图唤醒同胞,奋起救国。在抗战爆发时,又创作了反抗日寇侵略的作品。这种反帝爱国思想,在鸳派中是有代表性的。正因为如此,在1936年9月向全国人民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包天笔、周瘦鹃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二十一人一同签了名,说明他们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积极参加全国文艺界的团结阵线,以表他们抗日爱国的决心。
二
鸳派小说具有趣味性的特点,而这种“趣味性”却成了批判者攻击的目标。他们认为鸳派“积极宣扬文学上的趣味主义,”“这样就把小说从改造社会的工具堕落为消遣游戏品。”这种简单化的论调,只能把文学艺术推向死胡同。当然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都非常完美统一的小说,是能震撼人们心灵,起到极好的社会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的,但把鸳派小说的趣味性看成是“堕落”,则是一种对文学艺术的规律性还缺乏全面认识的表现。鲁迅在谈到小说的起源时,曾说:“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的目的。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⑤]讲故事能消遣闲暇,这是因为故事有“有趣味”的情节。否则 就会变成干巴巴的说教,人们就达不到消遣闲暇的目的。可见趣味性正是小说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有趣味性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虽然以它前所未有的战绩,宣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开辟了一个新文学的世纪,但这场革命,由于运动领导者的形而上学思想,在批判封建旧文学中对民族文化传统采取了虚无主义态度,导致了“全盘西化”倾向,其恶果使后来新文学的发展也走了不少弯路。很明显,作为旧文学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彻底的否定之后,直至当代,确使那些“编文学的把‘鸳蝴’与桐城、公安一视同仁”了[⑥],然而历史又告诉我们,二三十年代进行了几次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但最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作家才在吸取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作了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民族形式的文艺作品。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新文学要真正获得最大多数人的喜爱赞赏,除了吸取西方文学的长处外,作家还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吸取传统文化的营养。
通俗小说历来为老百姓所喜爱,重要的是它有趣味性。趣味性最集中体现在作品情节处理上富于吸引人的艺术魅力。传统通俗小说的“志怪”、“传奇”,趣味性就在“怪”和“奇”上,后来的“话本”、“章回小说”都无不在“怪”、“奇”上下功夫,愈“怪”愈“奇”就愈有趣味性,愈能达到娱悦消遣的目的。通俗小说的长处就在于通过趣味性,使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诲,收到“劝俗”的效果。趣味性作为小说表达思想内涵的一种重要艺术手段,应当受到重视。鲁迅曾经讲过,进行文艺创作还是要讲“趣味”的。他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是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⑦]“趣味性”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实际上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审美标准。通俗文学作家进行创作时,决不是随心所欲、任意编造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就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梨娘的儿子鹏郎是作者的门生,他的母亲工于诗文,与作者曾经相识,作者的妻子婚后被恶姑虐待致死,《玉梨魂》是为悼念亡妻之作。正因为作者有生活实感,在构思这幕爱情悲剧情节时,才写得如此缠绵悱恻,逼真而曲折动人,故而轰动文坛,这决不是向壁之作所能相比的。张恨水在谈他写小说汲取材料的源泉时,曾几次说到“我南南北北地走过一些路,认识不少中下层社会的朋友,和上层也沾一点边,因为是当记者,所见所闻自然比仅仅坐衙门或教书宽广一些,这也就成为我写章回小说的题材了”。在谈到作品中反映当年官场和一般的上中层的社会相时,又说“作为新闻记者什么样的朋友都结交一些。袁世凯的第五个儿子和我比较熟,从他那里听到过一些达官贵人家的故事。孙宝琦家和许世英家我也熟悉。有时我也记下一些见闻,也就成为写小说的素材”[⑧]。作为记者,张恨水深入到了社会的各阶层之中,这种丰富多采的生活,就为他创作有“趣味性”的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但真正要创作出有“趣味性”的作品,作家还要有个基本出发点和依据,这就是进行美的“趣味性”创作的要求和准则,当然这要求和准则,不仅仅是作家主观上想要表现美的“趣味性”内容,还应该包含符合群众审美需要的客观美学价值的“趣味性”内容。只有那些与广大读者涉足现实的要求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人们普遍关注历史发展趋势的心理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作品的“趣味性”才有与读者“对话”的可能,才有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共鸣的可能,从而达到激励人们奋发精神的积极效果。这种富于艺术魅力的“趣味性”,包括通常所说的“噱头”。鸳派作家深谙这“噱头”的重要性,他们知道仅有言情故事是不够的,尽管生活中的言情故事各不相同、丰富多彩,但情节要有噱头,要能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要“给大家快快活活”[⑨],这就不容易做到了。据说张恨水应《新闻报》严独鹤之约,要写有“噱头”的连载小说,苦思了几个夜晚没睡觉,就到天桥转一转。在钟楼附近清冷的地方看到卖唱的,后来又想起几年前在街头,有一个大军阀抢姑娘的事,就与左笑鸿聊了两天,才构思完小说的轮廊,这就是《啼笑因缘》。这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反封建的言情小说,有力地暴露了当时封建军阀的丑恶和腐朽,因而“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男女学生疯狂一时”,原因就是小说“含蓄着浓厚的北方的人情味,和婉转缠绵的故事”[⑩]。又因张恨水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应该反映时代和写人民”[(11)]的思想,小说又富有吸引人的社会新闻性和趣味性,使主题深化,其“噱头”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可见鸳派小说的“趣味性”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把这种有“趣味性”的小说,通通说成是“堕落为消遣的游戏品”,这是批判者对小说的“消遣游戏”功能的一种误解。“堕落”,无非是说作者以淫秽、诲盗之作来毒害读者。但《红玫瑰》编者话中明确表示他们的编辑方针,意在“趣味”二字上下功夫,且要通俗化群众化,“切戒文字趋于恶化和腐化——轻薄和下流。”文体要“切合现在潮流,”描写“以现实的社会为背景”,[(12)]其格调是比较高的。周瘦鹃在谈到他主编的《礼拜六》时,明确指出,“总之《礼拜六》虽不曾高谈革命,但也并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13)]张恨水在总结他的创作生涯时,也严肃地说过,“我作小说,没有其它的长处,就是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14)]当然,当时或许有人写过黄色作品,但是否鸳派人物?即使是鸳派中人,也不应以偏代全,以个别代一般,而给鸳派作出“堕落”的结论。
三
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发展到现当代,鸳派小说确实起了一个过渡作用。不可否认,正当新文学在孕育着破土而出之时,鸳派也在以“正宗”的中国小说姿态亲睐着西方欧美文学,装修自己,并跟随时代的步伐,加入到新文学的阵线中,为新一代通俗小说的出现,起到了借鉴作用。
鸳派小说虽然始终没有脱下章回体这件标志旧文学的外衣,仍保留了它传统的通俗性和大众化的特色,及固有的趣味性所起到的消遣娱乐作用,但作者们对西方文学和文艺思想并不反对,他们有些人在翻译西方文学时,还深受其影响,并有意识地吸取了西洋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周瘦鹃说:“我还翻译过许多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例如法国大作家巴比斯等的作品”,“其中一部分曾经收入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191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引者注),意外地获得了鲁迅先生的赞许。”[(15)]赞许他的翻译“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高度赞扬书的出版是“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16)]译著包括了两个半世纪的西方短篇小说,不仅可看出各国文艺思潮的概况,还可看出各不相同流派的艺术风格。翻译的长篇有《福尔摩斯别传》《犹太灯》《情案》《冰天艳影》《红颜知己》《翻云复雨录》等,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他第一个把高尔基介绍给中国人民,更为世人所称道。包天笑通晓日文,在晚清时译了很多教育小说,如《埋石弃石记》《孤雏感遇记》《苦儿流浪记》《青灯回味记》《馨儿就学记》等。他的翻译文字中国化,流利生动,深为读者喜爱。此外有胡宪生、俞天游、张碧梧等分别翻译了美国布朗的《人猿泰山》(出版时改名《野人记》)。严独鹤、程小青、陈小蝶、陈霆锐等十人翻译了英国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后又有周瘦鹃、张舍我、张蕨萍翻译了《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程小青于1927年又全部加以重译,题为《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作者所写的探案,运用理化、医学知识来研究物证,采用归纳、分析的推理方法进行事实判断,这种侦探方法,富于科学价值,并非面壁虚构时的想入非非之作。鸳派翻译家所译小说,在中国窥探西方文学之初,是起过积极作用的。西方文学的进步思想和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对他们的创作,确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在小说中保留章回形式,但开卷时的“话说某省县有个某人家”,和每回结尾时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以及描写一个初次出场人物时采用“怎见得,有诗为证”,这样一些套话都废除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是有头有尾地叙说事情发生的经过,但他们在采用西方文学的手法时,则多半截取生活中某一个片段,先讲当前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采用倒叙,或插叙补叙的手法,说清事物发生的原因,最后叙写事件的结果;或有头无尾,戛然而止。塑造人物形象时,有大段的心理刻划,和所处环境的精心描绘。他们对外来的艺术技巧,也并非盲目吸收,而是重在“为我所用”。他们把中西方艺术的特质结合起来,使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充满生气。从鸳派的发展情况看,后期的张恨水小说最具这一特色,是最有代表性的。张恨水在1944年重庆的朋友祝贺他创作生涯三十周年时作的《总答谢》中,曾表示他之所以要坚持运用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章回体进行小说创作,就是考虑到章回体小说是“匹夫匹妇”都能“享受”的文体形式,而“新派小说”是除知识分子外,并非“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因此为了与旧小说争夺读者阵地,他要用章回体来创作“写现代事物的小说。”基于这一点,他在“仔细研究翻译小说,吸聚人家的长处,取人之有,补我所无”[①⑦]的情况下,写出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为群众所喜爱的作品,在通俗小说中,体现了中西方文学特质相结合的特色,可谓独树一帜。
晚清的通俗小说创作以长篇为主,但在鸳派翻译不少西方小说之后,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翻译在刊物上占了很大的份量,且内容又非常广泛,这对当时文坛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短篇小说的创作就大量地增加。包天笑主编的《小说画报》(1917年1月)全都是短篇作品。这时期的短篇小说精炼短小,不仅继承了传统的传奇、笔记小说的特点,以情节为重,叙述有头有尾,而且从西洋短篇小说中吸取营养,截取生活事件的精采片断,从一个不显眼的社会角落里,表现小人物,提出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逐渐转到精细的人物心理刻划和环境描写上来。这种短篇小说完全具备了现代小说的雏形,从现代短篇小说体裁的发展看,鸳派起到的先导和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对鸳派只要不采取某种偏见态度,能客观地看到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性和它发挥出来的历史作用,就不应该拒之于门外,而应当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里,给它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国家的小说,应该有它自己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在各个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时代都赋予了它独有的民族特色。鸳派小说独有的民族特色,在于把中国传统的艺术特质和西方文学的艺术特质融于一体,构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通俗小说。
收稿日期:1995-11-18
注释:
①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②宁远《关于鸳鸯蝴蝶派》,香港《大公报》1960年7月20日。
③ (13) (15)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文艺新闻》20~21期,1931年7~8月。
④ (14)周瘦鹃《花前新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版。
⑤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⑦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一~十二)》。
⑧ (11) (14) (17)张恨水《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1980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
⑨周瘦鹃《〈快活〉祝词》《快活》旬刊第1期,1923年出版。
⑩张明明《有关〈啼笑姻缘〉的二三事》《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9年4月版。
(12)赵苕狂《花前小语》《红玫瑰》第5卷24期,1929年9月。
(16)《教育公报》1917年11月30日。
标签:鸳鸯蝴蝶派论文; 张恨水论文; 周瘦鹃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短篇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玉梨魂论文; 啼笑因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