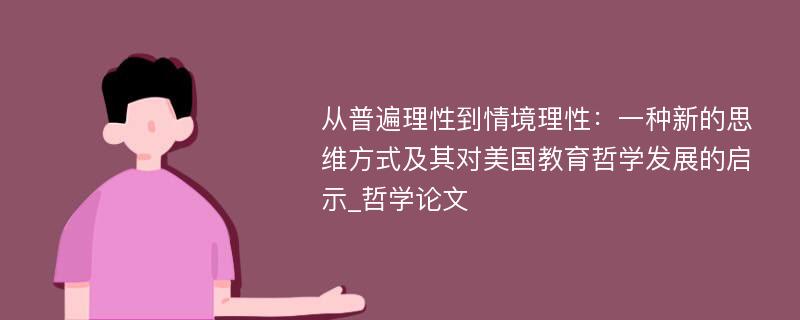
从普遍理性到情景理性——美国教育哲学发展历程的一种新思路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美国论文,新思路论文,发展历程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8)05-0079-04
1941年,美国教育哲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教育哲学在美国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至今,美国的教育哲学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生了“范式”的转换。80年代以前的教育哲学诉求于普遍理性,追寻普适的理论表征和永恒的教育真理;80年代后的教育哲学诉求于情境理性,注重对特定情境下教育问题的哲学阐释。
一、普遍理性诉求下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特征
80年代以前的教育哲学由“某某主义”教育哲学和分析教育哲学构成。尽管这两种哲学运用的研究方法不同,但是在理性诉求上却是一致的,都诉求于普遍的理性,渴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已经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教育问题。
首先,“某某主义”的教育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美国教育哲学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主要的哲学流派有唯心主义、唯实主义、永恒主义、要素主义、实用主义、进步主义、社会改造主义、存在主义等。各种“主义”的教育哲学有着同样的研究思路,即形而上学讨论现实的性质,认识论讨论知识的性质,价值论讨论价值的性质,逻辑论讨论推理的性质。[1](P93) 各种“主义”的教育哲学从自己信奉的哲学立场出发,阐述自己的主张,为自己的教育主张寻求永恒的形而上学支撑,都认为自己的教育哲学主张是面对现实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每一个派别的教育哲学都是系统的、综合的、连贯的、完善的思想体系,每一种教育哲学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了教育的永恒真理。
其次,20世纪40年代教育哲学家们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教育中的概念进行分析,从而进入了教育哲学的分析时代,60年代达到高峰,被认为是教育哲学的专业化时代。分析教育哲学对概念和命题进行语言和逻辑的分析,试图通过语言清思,消除由于教育概念的模糊所引起的争论,从而实现教育理论的清晰化,并不想创造或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哲学的思想体系。分析教育哲学并没有对经验世界中的教学、知识、学校、课程等问题提出新的主张,“只是根据经验上能够评价的词语来检查教育的理论、方案和实施”[1](P117)。尽管分析教育哲学比各个主义教育哲学教育主张降低了自己的标准,但是清思的立场依然是一种普遍理性,力图把教育的语言改造成确定的语言,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对话,使人们的表达不因为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产生歧义和误解。
在普遍理性的诉求下,教育哲学带给人的是既有“没有选择标准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又有“没有选择标准的存在主义焦虑”。“本质主义的肆虐”意味着选择标准的单一性、机械性。普遍理性意味着只要人与人之间分享着先验的理性,不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只要有足够多的叙述,就能理解并运用这种具有普遍理性的教育哲学。这样它带给人的选择标准是单一的,固定的,人们的教育行为也只能遵循某一种教育哲学提供的操作指南。“存在主义的焦虑”意味着人们无法从中判断出应该选择哪一种教育哲学作为自己的教育实践理念的支撑。每一个“主义”的教育哲学都有着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概念表征,也都提供了全面的教育理念和操作技术,面对众多的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教育哲学主张,人们只能处在困惑中。而分析教育哲学在研究技术上排斥了关于教育价值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而“概念的大扫荡”(conceptual mopping up)并没有真正的做到清思,人们不得不放弃通过逻辑的找寻纯粹的语言来建立教育的基本准则这一强硬的立场,而后期分析教育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也仅仅是修正了概念的用法,无法对概念作彻底的清思,依然是一种弱普遍主义立场。[2] 而面对教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分析教育哲学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至此,渴望普遍有效的理性诉求的教育哲学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实践问题时,越来越不合时宜,逐渐地走向了“破产”的道路。
二、情境理性诉求下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特征
80年代以后的教育哲学呈现出情境理性的诉求。哈贝马斯在1994年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提出了“情境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情境理性这个概念最讲究的是对话者之间相互采取的一种同情对方的态度。理性依赖于特定的情境,情境理性意味着同情的理解。我们的理性,其实是嵌入到场景里的理性,绝不是能够独立于这些场景、不依场景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那种抽象的柏拉图式的理性(“理念”、“共相”、“神性”)。美国教育学杂志《教育理论》(Educational Theory)的主编博布勒斯(Nicholas C Burbules)在2000年第一期的《教育理论》上撰文指出,80年代以后的教育哲学在许多方面都拒绝无关的理论表征,而是强调学问的情境性和责任性,任何一个作品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撰写的,在一定问题的语境与环境的范围内写的,还强调写作的主观性追求,反映社会和实践的影响。[3] 80年代以后的美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在理性诉求上不再找寻普适的理论表征,而是遵循情境理性,没有哪一种教育哲学能够居于统治地位。
这种理性诉求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教育哲学发挥批判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无论教育哲学与哲学是怎样一种关系,教育哲学都无可避免地袭承了哲学的批判本性。传统教育哲学的批判性在于提供一个教育正当性的标准,使实践中的人们能够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行动。而转型后的教育哲学被认为已经不能提供正当性的标准了。传统上,教育哲学所提供的正当性标准往往来源于哲学文本,从哲学的观点中演绎出教育的观点,从一个观点中推导出一系列的其他观点,形成一个等级结构式的观点体系。转型后的教育哲学认为,文本可能提供的标准都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标准已经无法保持正当性。[2] 教育哲学家把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放弃了对普遍合理性的诉求,转而强调效果的有限性,任何标准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他们强调标准的个人性,认为教育的正当性在于个人的域限(Personal Horizon)、个人的承诺和协商中的现实性。因此,教育哲学的批判性只能体现是帮助人们提高警惕,保持对文本提供的知识和进行某一选择可能带来结果的警醒。教育哲学不能提供什么永恒的真理,只能通过激发人们的思考来发挥作用。
第二,教育哲学的理论支撑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教育哲学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优越性,受认识论影响比较深刻,而转型后的教育哲学则更多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主义”教育哲学和分析教育哲学都是书斋里的教育哲学,具有典型的形而上学性,遵循的是柏拉图以来的认识论哲学传统,而以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为理论支撑和主要的理论来源的教育哲学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使得教育哲学研究能够走出书斋,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分析教育问题,在问题解决电提出主张,教育哲学也就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面貌。当前的教育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已经偏离了柏拉图式的找寻永恒的“善”这一目标,[4] 没有人再来关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休谟的认识论。[5] 所以,以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各种各样的批判理论在90年代非常的流行,他们对教育实践中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提出质疑,对教育公平、民主等理念进行重新阐释。
第三,与第二点变化直接相关,由于哲学基础发生了变化,教育哲学的面貌更加的多样化。转型后的教育哲学在研究领域上并没有明显的边界,与传统哲学联姻的教育哲学由于社会科学的闯入,“婚姻”[5] 面临着危机,教育哲学在找不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学会了“四海为家”。四海为家的教育哲学非常关注教育实践,对公众的教育问题十分关注,关心教育的人都可以讨论教育哲学。而近几年来美国社会中的热点教育问题都吸引了教育哲学研究者的主意,例如宗教问题[6]、学校改革问题[7]、黑人教育问题[8]、网络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9] 等。在众多的思想主张中,女性主义可以说呈现一种别样的风采,简·马丁和尼尔·诺丁斯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转型后的教育哲学放弃了在认识论上的永恒的理性诉求,而是遵循了情境理性,尊重了空间与位置的不同带来的教育主张的不同。在理论的表征上,研究者们不再使用确定性的语言表述,而是带着怀疑看问题,言语之间充满不确定性。
这种变化是否能被视为一种进步,美国教育哲学研究者们还在争论着,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事实上教育哲学研究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对这种变化的争论也日益的公开化和明显化。
三、情境理性诉求下美国教育哲学研究变化的原因
首先,美国教育哲学的转型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80年代之前的美国处于冷战对峙的双峰时期,加上二战后社会遗留问题的凸显,社会发展的震动幅度较大,面对现实,呈现出各种“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每一种“主义”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发展的航标。而80年代之后,冷战日益解冻,美国在政治上奉行新保守主义的策略,在经济上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策略,这种政治上的强硬与经济上的放任造成社会关系日趋紧张,而后美国又把政策调整为“第三条道路”,缓解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在这期间,尽管社会矛盾不断,但是社会依然是渐进式的变革性发展,而不是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冲突与矛盾的不断紧张与缓和中不断前进的。各种社会团体学会了在妥协中协调彼此的关系,学会了对公共事务的综合治理。因此,教育哲学也适应了在问题解决中阐述自己的主张,放弃寻找万能的教育哲学灵药,以此来适应社会发展的现状。教育哲学学会了通过对教育问题的哲学阐释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使自己的研究更有现实感。
其次,教育实践的变化也促进了教育哲学的改变。由于美国政府奉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教育事业的发展呈现出了市场化、商业化的趋势,“放权”、“校本”成为学校改革的时髦词汇。这样,基层的教育实践越来越活跃,政府、政党、学校、家长、社区、企业在学校改革这个层面上被广泛的联系起来,各种利益团体都在学校改革这个层面上出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时有冲突与紧张。在这样的关系网上,政府通过“放权”和各种能力测试的方式渴望提高学校的质量与效率,商业管理模式进入学校运作机制,各种关于教育竞争力的报告,诸如《国家在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等时刻牵动着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心。实际上,美国两党的历届政府都把教育作为自己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教育改革就不仅仅局限在学校内部的课堂教学、课程开发方面,而是扩大到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经费运作、教育公平等多个方面,这种实践的状况吸引了教育哲学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在复杂纷繁的教育实践中洞察出教育的问题所在,开始对教育目的、教育公平、教育民主等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把自己的教育哲学主张在问题解决中提出来。教育实践中各种问题的层出不穷为教育哲学的批判找到了更多的靶子,他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唤醒教育实践者,使教育实践者能够更好的反思。
再次,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讲,过分哲学化的研究道路只会把教育哲学研究带进死胡同。传统的教育哲学从哲学研究中汲取营养,发表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哲学话语多,教育话语少,很难使人明白哲学研究成果的教育学意义,过分追求宏大的理论叙事。7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教育实践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教育哲学家们开始自我反思,逐渐地,许多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开始关注教育实践,研究的问题更加地贴近实践。从方法论上讲,美国的教育哲学深受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福柯、利奥塔、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教育哲学的研究,在许多研究论文中,都以他们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支撑,而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性、统一性、整体性的批判直接影响了教育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教育哲学也批判永恒的教育理想,保持对特定情境下人们生活状态同情的理解。
四、对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因此,不可能在教育哲学发展的内容上直接借鉴。但是在教育哲学发展的思维方式上,还是有借鉴的意义。
首先,在问题解决中提出教育哲学主张。中国社会的发展处在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美国也处在“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转型期,尽管二者的转型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社会发展都是在矛盾与冲突的紧张与缓解中进行,而不是狂风暴雨般的革命,都是在社会问题的出现与解决中、各种利益团体的相互妥协中进行的。尽管转型期带给中国人生活的震动非常大,但是社会发展基本上是渐进性变革。因此,教育哲学必须不断地追问教育实践中各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不断地对各种教育主张的前提进行批判,在问题解决中阐发教育哲学主张。
其次,使教育哲学四海为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讲,在教育改革上能够直接借鉴其他国家和自己历史发展留下来的经验并不是很多,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根据当下与未来作出试探性的调整。因此,许多问题都需要在教育哲学上认识清楚。而今天的教育哲学必须关注的是存在于社会发展现实的教育问题,面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教育问题作出符合自己时代发展水平的回答。面向实践,不代表教育哲学要去解决教育实践中具体的问题,而是要以理论表征的形式为教育实践的发展“把脉”。面向实践意味着教育哲学面临着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可能会产生教育政策哲学、教育管理哲学、教育评价哲学、道德教育哲学等,在教育实践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教育哲学的反思,当教育哲学“无家可归”的时候,教育哲学就“四海为家”。
再次,美国教育哲学尽管在80年代前后发生了改变,但是有一个没有变化的就是对教育的批判精神。中国的教育哲学同样要有一种批判精神。批判有批评之义,意味着对错误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等进行系统的剖析,从而找寻出正确的答案。但是批判有着更深刻的含义,那就是对现实永远的不满足,力图发现现实的不合理之处,为着理想的实现而不断的努力。这种批判具体体现为“发现问题”和“回答问题”。尽管中国发展的大环境比较稳定,但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社会转型带来的剧痛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现实的教育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方面,它需要教育哲学研究以自己的智慧,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帮助我们的社会实现更好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8-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