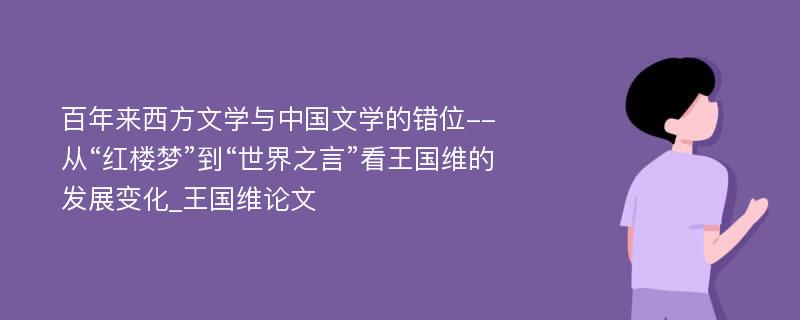
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以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的发展变化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词话论文,西学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6-0092-09
“西学东渐”这一概念,若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学术框架,至少可生出两种功能:“著述译介”和“理论参照”。著述译介属“西学东渐”之初步,不论是严复式意译,还是鲁迅式硬译,只要能忠实传递原著精义,拓展国人的知识—价值视野,皆是值得中国学术界感恩的善行。“西学东渐”之深化,则是视西学为中国学术研究之方法,这得十分审慎。
方法是什么?方法作为给定语境中的理论参照,将预设楔入对象的原则性思辨视角,并将此视角在既定论域中演绎到极致。这就应先考量“方法—对象”之间的比对关系。所谓比对,是指经交互比照而证明彼此间有对应。之所以设此程序,是因为被选作方法的某一西学原型,不管其原生语境赋予它多少正当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当初并非是为中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而特制的。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一般可能作为方法的西学原型,最初皆不免是“他者”。
在西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建构可靠的“方法—对象”关系,不无麻烦,其根源在于人世间从来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现代科学值得尊敬的理由之一,也在于它勇于声明其只追求在有限语境说有效的话。连“1+1=2”也仅仅是在十进位制内有效,还有哪种理论原型敢闯到异质论域去“自说自话”呢?
于是,选择何种西学作为研究方法才恰当,这就酷似一个亟待骨髓移植的患者,须首先确诊自身骨髓的型号。临床“配型”有效与否,当取决于“比对”。而“比对”之前提,则取决于须明白:“我是谁?我到底要什么?”毕竟以西学作中国文学研究之方法,旨在科学地回答对象“是什么?为什么?”而不是为了炫耀方法的锋利、正确乃至英明,不惜牺牲对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将对象弄得面目全非。借“他山之石”,本想“攻玉”,如果“毁玉”,那就“错位”了。
纵看20世纪百年中国文学学术,类似的“错位”,还真如赵翼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即使王国维、李泽厚、王元化那样的里程碑人物,在其学术生涯也或浅或深地留下了各自“错位”的轨迹。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李泽厚《意境杂谈》(1957),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可以说,这都是后学追思20世纪中国学术何以曲折连绵的重要史料。诚然,王国维、李泽厚、王元化所以被尊为学贯中西的“大家”,是因为他们能够走出“错位”,返回学术正道即“反正”。在此意义上,又可说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李泽厚《美的历程》(1981)、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定本(2004),是在百折不挠地昭示现代中国学术终将走向成熟。有意思的是,从王国维1904年撰《红楼梦评论》,经李泽厚,至王元化2004年刊行《文心雕龙讲疏》定本,前后恰好百年。这是否暗示:释证“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已生逢其时?
另须交代两点:(1)本文所谓“西学”,为广义之西学,不仅涵盖从域外引进的欧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述,也包括源自前苏联、由日译本中转的革命理论;(2)本文所谓“中国文学”,既包含古代作品,也包含古代及近代文学批评。本文着重分析王国维与叔本华的关系,即如何从《红楼梦评论》之“错位”,调整到《人间词话》之“反正”。
稍知王国维美学的人,皆晓其处女作《红楼梦评论》(下简称《评论》)是中国红学史上的石破天惊之作,因为作者不屑走“索隐派”的老路,而径直搬来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来解剖这部中国文学名著。重温这百年旧事,用意在于,若将王国维的处女作纳入“方法—对象”框架作专业审读,可以说它实属败笔,其后果是把中国一部最具诗哲文化的小说经典“去文化”。
当然,这并非王国维的初衷。当年他初出茅庐,颇多青春豪气。认为困扰人类的普遍精神难题自古是“婚宦”二字,“而蚩蚩者乃日用而不知”[1](P6),两千年过去,幸亏叔本华写了《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一书,在哲学上解释了这难题。同时,鉴于世界上“诗歌小说之描写此事者,通古今东西,殆不能悉数,然能解决之者鲜矣”,恰好中国有“《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能解决之者也”[1](P6)。这简直天造地设,天仙配对,王氏有意中西合璧,遂撰《评论》。
一个是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鼻祖,一个是中国古典小说至尊,相逢在王国维的笔下,堪称“门当户对”。乍看彼此也确有“共同语言”,“性爱与解脱”是国际通用语汇,与此相对应的古汉语是“色与空”。作为“方法”的叔本华理论与作为“对象”的曹雪芹小说之间也“专业对口”,王国维怎会犯错?问题是此中有陷阱,即同一词语在异质语境下的不同概念。这就是说,纵然叔本华与曹雪芹都在说“性爱(色)”或“解脱(空)”这一词语,但各自注入的内涵不尽相同。这就涉及叔本华理论与曹氏小说各自的价值取向。
就像陈寅恪先把诗人陶潜确认为中古思想家,随后再来解析其《归去来兮辞》、《归田园居》、《桃花源诗》及《形影神》也就顿显晓畅一样,后学也不妨先把曹雪芹体悟成一位有思想史襟怀的诗性小说家,由此再来读其大观园与宝黛情案,也就明白那片繁华皇苑为何终将被悲凉所淹没。
曹雪芹为何写《红楼梦》?有人认为,“整部《红楼梦》情案都是为‘情性’的确立做艰难的尝试”,甚至说“提出以‘情性’为人性之根据和世界的价值形态的根基,以取代儒、道、释的信念基础,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2](P312)。笔者大体认同这见解,并进而认为曹雪芹之所以把“情性”定位为超越宗法伦常的青春型痴情或纯情,旨在消解庄玄式“慎独”的清虚冷寂,而让逍遥人生也能分享人际情缘的灵犀欣悦。此可谓小说立意的“独特性”。
这又是一把能够打开作家的诸多匠心(即表现的“丰富性”)的金钥匙。比如,小说为何把主人公那枚与生衔来的“通灵宝玉”,说成是女娲补天时的弃石?因为“天”在中华政伦辞典中象征皇权,一个不想读“四书五经”、做济世文章的多情公子,宛如其前世便与“补天”无缘,故被冷落在大荒山青埂峰下。又如,小说为何让主人公所栖居的大观园四处播撒诗兴与鲜花?这当然是想让贾宝玉性格符号的“情性”有所附丽,有一种相应的诗意氛围,洋溢着少女情致才有的至纯至柔。因为林黛玉所隐喻的“女性的美质如果能带来平和、温静、享乐、诉诸感性愉悦、终止一切损害的力量,无疑给逍遥的出路带来一种新的决定性的力量”,“这样一来,清寂的问题便一劳永逸地解决了”[2](P325)。于是,也就有了柔情缱绻的“石木之盟”。
但这一切让王国维戴上叔本华的哲学眼镜来解读时,则“立意的独特性”、“表现的丰富性”没了,最终读出一条:“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1](P7)。故怡红院主的“通灵宝玉”也就直接通向叔氏的“性爱”之欲,不仅谐音,而且同义。于是,一连串的误判由此开始。比如,此“玉”前世为何是女娲弃石?这是为了演示“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是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1](P7)。意谓玉虽含在贾宝玉嘴中,贾宝玉不能操控玉,玉却可自由操控贾宝玉,故小说尾声会安排一和尚提醒贾宝玉:“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王国维强调,“所谓‘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者,未知其生活乃自己一念之误,而此念之所自造也。及一闻和尚之言,始知此不幸之生活,由自己之所欲,而其拒绝之也,亦不得由自己,是以有还玉之言”[1](P7)。故无须说,若玉是“性爱”,还玉便是“解脱”。
于是,王国维惊喜地发现《红楼梦》原来暗含着一个叔本华的“性爱—解脱”模式:“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蹶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读者观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之事实,其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明瞭精切何如哉。”[1](P9)且不论王国维这般欢快地勾勒作品梗概,是否将中国名著读成了叔本华哲学的跑马场,笔者只想问,主人公最后决绝出走大观园,这本是悲剧“忽剌剌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评论》却从中嚼出“最后的胜利”,这未免离小说的原汁原味太远了。
本来称《红楼梦》为“彻头彻底的悲剧”[1](P11),这也是王国维师承叔本华美学之标记。叔本华以为悲剧成因有三:一是有极恶之人;二是因命运无常;三是“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因为这“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堕于吾前”,让你防不胜防,且“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1](P11—12)。王国维认定《红楼梦》属“第三种悲剧”:“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1](P12)可惜王国维只为《红楼梦》领了“悲剧”的美学名分,此名分未免空洞,在叔本华那儿则不具哲学实质。
这就是说,若还原到意志哲学语境,莫说虚拟的小说人物,即使是堕入热恋中的血肉之躯,在叔本华看来,也不过是一群自作多情的执迷不悟者。其哲学预设很独断:种族生存或繁衍作为“物自体”,它是“不受个体化原理拘束”的宇宙意志,但又“存在于各式各样的个体中”[3](P15)。这就意味着,凡进入青春—生殖期的人,无一不是为种族意志生孩子的道具。简言之,“恋爱的结婚是为种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个人”[3](P12)。然而,偏偏性爱“是一种最激烈的情欲、是欲望中的欲望”,这就不免让当事者滋生幻觉,若能与心上人相逢于金风玉露,就有“仿佛置身于幸福的巅峰或已取得了幸福王冠的感觉”[3](P4)。这一群盲目的丘比特,永远识不破其恋爱“不管所呈现的外观是如何的神圣、灵妙,实则,它的根柢只是存在性本能之中,那是经过公认的,带有特殊使命的性本能”[4](P126)。说穿了,他们只是被种族意志哄来生殖的。或曰,种族意志只对性爱双方的精液、卵子与子宫充满憧憬,至于生殖后的婚姻是否幸福,种族意志才不管这闲事呢。
所以,普天下一切被情爱纠缠得死去活来、悱恻凄美、泣鬼神、动乾坤的“白马王子”及“灰姑娘”们,你们千万不宜“自我感觉”太好。因为在叔本华眼中,你们皆是服了蒙汗药似的,在被种族意志牵了鼻子走。你们在情恋舞台上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山盟海誓、长歌当哭,说到底,皆事先由种族意志按“目的论”设计好的。尽管你们进入角色后的动作或台词或有个人的即兴成分,但总体剧情与结局是变不了的。若这般提醒诸位不听,依旧自信你们在爱情之地“我是属于我自己的”;那么,叔本华就会请“种族的守神在他那高高的宝座上,对着被踩在自己脚底的个人权利或利益,发出轻蔑的嘲笑”[4](P153)。
那“嘲笑”嘲得很酷,因为它竟然奉劝“诸位不妨试想一下动物在交尾期的生殖行为”[3](P65)。什么叫“去文化”?人家已把“人类性爱=昆虫交尾”,那有什么“文化”可言?这般说来,《红楼梦》还是诗学意义上的悲剧么?在叔本华看来,它只是一出滑稽的“伪悲剧”。叔本华已说得很透彻,“意志是拿自己的本钱来演这一伟大悲剧和喜剧的,何况意志又是自己的观众”[5](P353)。这就意味着,种族意志只想在人类舞台编导一串永恒的“恶作剧”:它先把你的情爱撩得如火如荼,如梦如醉,让它看得过瘾了,随后又唾弃你曾为之歌泣、为之忧伤的激情(包括曹雪芹为红楼情案“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并说你的“悲剧”不在别处,只在于你浑然不知天高地厚,浑然不知你的命运只是“被命运所戏弄”,浑然不知你所心仪的价值其实一钱不值。这当然不是曹雪芹的本意,也未必是王国维倚重叔本华的初始动机。
作为“方法”的意志哲学与作为“对象”的《红楼梦》之错位悬殊如此,其症结在于,叔本华所喋喋不休的“种族本位”,与曹雪芹所诗意缠绕的“情性本位”之间,几无价值契合的可能,骨子里是对峙的。
曹雪芹“情性本位”的价值取向,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1)若置于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史,“情性本位”上承李贽“童心”说的狷介,下接龚自珍“宥情”篇的清狂,甚至鲁迅让小说喊出的“我是属于我自己的”这一“五四”启蒙之声,也未必不含“情性本位”的因子。(2)从人类价值意识进程的“两次分离”来看,或许更能掂出“情性本位”的含金量。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分离”:即人意识到自己是宇宙间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殊类属,从而在精神乃至行为上摆脱了对大自然的神秘依附,走向人的“历史本位”。其次是“个体与社会的分离”:即人还意识到每一个体又是迥异于其他个体的独特存在,故社会进步的前提应是为独立个体的自由栖居这一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即走向人的“个体本位”[6](P142—143)。故无须说,曹雪芹的“情性本位”当是这普适性“两次分离”(尤其是“第二分离”)所分娩的华夏文化的诗学婴儿。
这诗学婴儿进入红楼情案,也就发育成贾宝玉性格,以渴望情爱自由为内驱力,来征兆青春个性觉醒。此“个性觉醒”之标志,首先呈示为疏离“男尊女卑”、“贵贱不移”等宗法伦常,而痴迷于少女情致,而至于与林姑娘的“木石前盟”,更让贾宝玉即使与美貌贤淑的宝钗进了洞房,其内心也依旧“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若套用一段叔本华语录:“憧憬包含二类,一是占有某特定的女人和连接无限幸福的观念;另一是,如若不能得到某女人则联接不可言状的悲痛”[4](P150)。
显然,“某特定的女人”或“某女人”的那个“某”字,在曹雪芹心头的位置极为贵重,贵重到千金不换,世物无可替代之境。因为“某”即“特定性”,是指“情性本位”为根基的个体存在的“不可化约性”。它是最神圣的。贾宝玉对林黛玉一路恋得如痴如癫,就是为了他心中的“这一个”非她莫属的“特定性”:林不但纤丽、孤高、聪慧、娇嗔,而且绝不对他说仕进之类“混账话”,而且她也真信贾心中只有她,如此肉灵一致的潇湘妃子,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特地相许给贾的。林是贾身上最柔软的一根肋骨,最纤敏的一线神经,最急促的一串呼吸,最激越的一阵心悸。贾既然是情海最深处的波浪,那沼泽怎能满足其渴望?“沼泽”隐喻纯肉欲的肌肤之亲,这对贾来说,几近唾手可得,随手可弃。贾最渴望的是林这片世上最深、最纯洁、最具“特定性”的“情海”。可以说,《红楼梦》最富诗意、最撩人想象、最催人泪下的文笔,最终都落到“特定性”这三字上了。有此“特定性”,即有文化;抹掉这“特定性”,即“去文化”。
而叔本华“种族本位”想化约的也是这“特定性”。理由只有一条,种族意志是永恒的“自在之物”,“个体就好比只是个别的样品或标本”,故“整个自然不因个体的死亡而有所损失”[5](P377-378)。这就是说,个体相对于种族来说本无足轻重,若硬说有用,也只是“为种族的保存尽了力”[5](P379)。故叔本华反复唠叨,“恋爱的主要目的,不是爱的交流,而是占有——肉体的享乐”[4](P128);或“结婚不是心与心的结合而是身体和身体的结合”[4](P141)。女人或情侣在他的概念里,只是单一“肉体”,而非灵肉融汇的“整体”。
令笔者诧异的是,青年王国维究竟是怎么读叔本华《性爱的形上学》(以下简称《性爱》)的?《性爱》终究不如《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下简称《意志》)那般篇幅浩大,才二万四千字。王国维自1902年啃英译版《意志》啃了整整两年,且取书院派领悟方式,而不像学院派课程方式,把《意志》纳入近代西学谱系作知识学水平的整体逻辑还原,这尚可理解。然《性爱》毕竟较短,且要以此作方法论坐标,即“持此标准,以观我国”《红楼梦》这一“绝大著作”[1](P5),那么,王国维对《性爱》真的逐字逐句地读通了吗?《性爱》一文除却父权制的傲慢、单身汉的粗鲁及其词句所混杂的史前曚昧气息外,高明处实在不多。他怎么忍心用《性爱》这把刀子来解构这部哲理遥深、诗意优美、叙事精微的中国名著呢?
试举一例,若奉叔本华“种族本位”为“标准”,将如何分析《红楼梦》第九十六回痴黛玉“临终”试探病宝玉前后的心绪变异?所以出这道题,缘由有二:(1)王国维以为此情节属小说“最壮美者之一例”[1](P12),还曾在《评论》第三章尾部大段引文达六百字;(2)王国维对此妙文却语焉未详,只仓促留言“其动吾人之感情何如!”[1](P14)十个字,这又未免回到了传统评点,不像现代学术。故值得重作。
这道题原本不难解,只须抓准林最后探询贾前后为何心绪大异之内在动因即可。答案无非是在“特定性”三字:就像林是贾不容调包的“这一个”一样,贾亦属林内心须臾不甘离弃的“这一个”。贾是真爱着林的。故双亲早逝、寄人篱下、单身孤影的林也暗暗心许于贾,视之为命根。这种依恋很甜蜜,也很脆弱,因为在大观园,如此终生大事,最后并不由自己说了算,故又恐夜长梦多。也因此,当耳闻傻大姐说贾将娶薛宝钗,黛玉内心“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且又痴痴迷迷”;“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但当她摸上门去,亲聆贾说:“我为林姑娘病了。”林转眼像换了个人似的,“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这又为何?谜底仍旧在“特定性”三字:既然确证流言中的宝玉仍痴心于己,这已足矣!……黛玉也就判若两人。
由此看来,王国维能特别青睐这情节,也表明他不乏慧眼。这确实是《红楼梦》特有的叙事绝技:初看引而不发,仅仅白描,用日常细节来缀观情境,内敛得很;然细嚼会令人心生衰怜乃至悲恸,眼眶有泪珠打转,又没让滴下。这时,你不得不认同王氏心得,它的确写出了“悲剧中的悲剧”。因为当你设身处地为林姑娘想一想:此时此地她又能怎样?悲剧已经铸成,少女仍在祈望,祈望流言不实?读者像作家一样明白这不可能,于是不得不悲悯;若再遥想林姑娘可能也明白这不是空穴来风,但只要宝玉不变心,此生足矣,这又让人悲恸。
如上“悲剧效果”,顺着曹雪芹“情性本位”路子去读才得体悟。若换作叔本华的“种族本位”路子,则可分两截去读:上半截是黛玉惶恐恋情“得而复失”;下半截是黛玉憧憬真情“失而复得”。针对上半截,叔本华或许会叹息,但他旋即声明那叹息“并不是从存在一时的个体欲望所发生,而是种族灵魂的叹息。种族看到自己目的的得失情形,而发出深深的叹息”[4](P150)。这就是说,叔本华所代言的“种族意志”之叹,仅仅是着眼于惋惜林姑娘被剥夺了在大观园“生孩子”、“做母亲”的权利。针对下半截,叔本华或许也会因林姑娘的心绪逆转而有所鼓舞,但他依旧坚执“那是因为恋爱中人受种族之灵的鼓舞,了解它所担负的使命远较个体事件重大”[3](P8)。亦即暗示林姑娘“生孩子”、“做母亲”之希望或许犹存。你可以说这是叔本华的“逻辑霸权”,因为他惯于把一切不宜化约的个体意愿统统消融于“种族意志”。你也可以说这是叔本华的“思维程序”,因为在他的演绎王国,任何“特定性”皆属不合法。
关于西学方法与中国文学对象之错位成因,当有赖于具体学案具体分析,不宜一言以蔽之,也不是“知己知彼”四个字便可轻易打发。即使有涉“知己”、“知彼”,也不等于本土学者对中国文学之“知己”,必优于其对西学之“知彼”。至少就《评论》一案而言,王国维对《红楼梦》下的工夫,与对叔本华《性爱》相比,后者明显要大些。或许这很难避免。因为作为国人,若不对相关西学多做功课,他可能一筹莫展;然对母语书写的对象则似乎习焉转熟,总可应付。毛病往往就出在这儿。
这从《评论》对贾宝玉的阐释取向即可见出。也就是说,王氏很在乎宝玉形象分析所诱发的“种族本位”(西学)对“宗族本位”(国粹)的文化悖离,且“自知有罪”[1](P10),但对小说真正的艺术重心,即“情性本位”(宝玉为符号)与“宗族本位”(贾母为代表)的价值冲突,则相对隔膜。尽管“种族—宗族”之文化悖离,在中国语境(含《红楼梦》)并未构成实质性现象,而只逻辑地活跃于王氏的相关联想,但“情性—宗族”之价值冲突,倒不时跌宕于晚明以降的中国思想史,曹雪芹的功绩在于用工笔将它形象地舒展为《红楼梦》。
而“自知有罪”之言,倒真切地透露了王国维对叔本华《性爱》曾颇用心,否则,恐吃不透“种族”对“宗族”的那份“潜颠覆性”。“种族”其实只讲一条,个性要为种族繁衍服务,至于你与谁生孩子,它不管。这恰恰是“宗族”最犯忌的,什么“抗命私奔”、“贵贱无界”或“通奸”之类,“宗族”必罪之为“大逆不道”。而对此三项,“种族”偏偏又无所谓。叔本华有言,大凡因“阶级、贫富的悬殊等,反对热恋中人结合的时候,种族的守神”将“宣告那是些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东西”,种族对宗族的“种种顾忌或古板的教条,都像吃稻壳一样地吃掉”[4](P153);还说,“为了爱情,不顾父母的劝告而毅然结婚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当她的父母以自私的利己心做忠告时,她却选择了最重要的原则,并且遵循了造化的精神(应该说是种族的精神)”[3](P13);更为惊世骇俗的是,叔本华还宣布,只要是以种族的名义,他赞成“连通奸的事情也公公然然毫无忌惮地进行”,因为当事者自觉“自己的行动是为种族的利益,比起只是为个人利益的行动,具有更高的权利,因而能心平气和地干那‘不可为’的大事”[4](P152)。想必王氏当年读《性爱》不会无端地跳过如上语段,这对于至死未剪脑后长辫的中国文士来说,其身心总会有点惶悚吧。
故当王国维看到宝玉在贾府愈活愈窝囊、无趣,终于拂袖而去时,他笔下便会顺势溜出这句话:“夫宝玉者,固世俗所谓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之罪人也。”[1](P15)因为王国维很明了,这对贾母为代表的“宗族本位”意味着什么了。“忠”原指名教奉君臣之序为人际首义,然宝玉从不屑“功名仕进”,更诅咒“文死谏、武死战”皆“须眉浊物”,诚属“不忠”。贾母宠宝玉如掌上明珠,他最后竟反目不归,岂非自毁家门,有辱祖宗?此属“不孝”。但这纯然是被逼出来的双重悲剧:若贾府能尊重“木石之盟”,宝玉不至于逆叛如此;而贾母也压根儿没想到,倾心“金玉之缘”,本想为宝玉好,反倒止沸益薪。要害全在那个“特定性”:宝玉视之为第一生命即“情性本位”;贾母则恪守“宗族本位”,为“反特定性”。所以,当《评论》说宝玉实是被“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1](P12)挤出大观园的,这无异于说,红楼悲剧之第一要义,乃在“宗族本位”对“性情本位”的全面掩抑、诱迫与威逼。“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这与其说是主人公对其栖身的侯门公府的刻骨怨诉,无宁说是作家所营构的“情性”终究逃不过“宗族”一劫的典型环境。
于是问题大了,试问:宝玉出走大观园之悲剧,与叔本华“种族本位”又有何干系?因为“种族本位”本目中无人,它才不在乎宝玉当和尚终生不育呢,天下愿“为人父为人母”者滔滔皆是,故不缺宝玉这一个“特定性”。也因此,想必叔本华对宝玉悲剧也不会有半点悲戚,恐怕更多的是某种号称“解脱”的幸灾乐祸而已。叔本华曾这样描述“解脱”心理:“大多数人都必须先有本人的最大痛苦把意志压服了,然后才能出现意志的自我否定。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人们在激烈的挣扎抗拒中经过了苦难继续增长的一切阶段,而陷于绝望的边缘之后,才突然转向自己的内心,认识了自己和这世界;他这整个的人都变了样,他已超乎自己和一切痛苦之上,并且好像是由于这些痛苦而纯洁化、圣化了似的。……这是在痛苦起着纯化作用的炉火中突然出现了否定生命意志的纹银,亦即出现了解脱。”[5](P538)无怪乎王国维也说宝玉出走是“终获最后之胜利”。但“胜利”还算“悲剧”么?“种族本位”说和“悲剧之悲剧”说皆来自叔本华,但当两者都加诸于贾宝玉时,却崩出一道难以弥合的逻辑断裂。
王国维其实是用两只眼睛来读贾宝玉的:在用“种族”之眼把宝玉读作被欲望所累、混同于芸芸众生之一员的同时,又用“宗族”之眼把宝玉读作贾府赖以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一炷香火。殊不知还亟须有“第三只眼”,从宝玉这一文学符号读出曹雪芹企盼通过亲近人际情缘来温暖慎独者的内心清虚。然深谙中国历史文化的作家最后绝望了:此路不通。故宝玉“解脱”宛若丧钟,首先当为曹雪芹而悲鸣。它迴荡着无尽的酸楚、遗限和苍凉。鲁迅说红楼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7](P194),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豪对其天才先驱的惺惺相惜。偌大中国文学史能得此“后世相知”者,不是1904年时的王国维,而是1920年时的鲁迅。
简言之,王国维在“方法”(路径依赖)方面愈靠近叔本华《性爱》,则离“对象”《红楼梦》的真实意蕴愈远;他愈把宝玉性格史读作不断地挣脱种族附在自身的“恶魔”的历史,则愈走不进作家苦于“道儒兼容”之幻灭;王国维愈想赋予《红楼梦》以“人类全体之性质”[1](P19),他对小说中的中国文化精髓愈不知所云;最后,王国维愈把《红楼梦》与叔本华捆绑一体,并断言小说所以遭遇“二百余年来吾人之祖先”之冷遇(以至作者“不敢自署其名”),就是因为此书叙写了种族意志“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而此“大背于吾国人之性质”[1](P91)(宗族本位)——这就愈让笔者释怀,当初王国维把叔本华请来与《红楼梦》配对,确实是“乱点鸳鸯谱”。
在中国20世纪百年文学学术史上,王国维还不曾碰到如此严格的审读。其实,这倒是学术史的正常生态。学术史不宜作成无关痛痒的资料长编,或“为尊者讳”的思辨客套。学术史的生命是“实话实说”。若承认学术应含有科学因子,那么,科学的第一要义,当是它有责任承受经验事实或专业范式的证伪。只有经得起证伪的学说,才可能被科学共同体尊为“定律”、“公理”。科学哲学意义上的“证伪”,转换为中华学术辞典的对应词,大概是“拨乱”。“拨乱”为了“反正”,“反正”的前提是“拨乱”。这个“乱”,在晚近国史,拟含西学“方法”对中国文学“对象”的百年错位。首当其冲者,是青年王国维的《评论》。
相对于1908年脱稿的《人间词话》(以下简称《词话》),1904年《评论》实是王国维的学术习作,它是青涩和不成熟的。衡定学术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是看其能否在“方法—对象”框架告别错位,真正找到彼此契合的交接点。此交接点,用康德语式来表达,即实现“合对象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含义是指,作为“方法”所蕴蓄的理论阐释能量,与作为“对象”所潜伏的被阐释期待,无形相契。这才是“方法—对象”关系的逻辑正态。这就是说,方法是用来说明对象“是什么”与“为什么”的。方法得为对象服务,而不能为了盲从方法所属的理论原型,而牺牲对象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评论》对叔本华方法的盲从,标志有二:一是“穿凿内核”,即以欲代玉,把《性爱》的元概念“种族意志”(欲)简单地拿来,穿凿为宝玉的性格内核。结果是宝玉性格阐释也就被“种族意志”所绑架,其稀薄的生物学气息被一味放大且泛化,而小说蕴藉其中的文化诗学意味(情性本位)却被阻隔与消解。这就酷似做重症外科手术:一刀切割“体内循环”供血,让心脏全然置于“体外循环”,心脏也就不再为其机体生存而搏动。标志之二是“复制框架”,即让《评论》把《性爱》原有的“性爱—解脱”推理框架,套在红楼人物头上重演一遭,弄得不伦不类。因为叔本华把“解脱”分为两类,王国维亦步亦趋,把小说角色也一分为二:一类是惜春(含紫鹃)模式,此类人属“非常之人”,能“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一类是宝玉模式,此类人属“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痛苦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且说“前者之解脱”,“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1](P8)。这就露了破绽:因为惜春在“十二金钗”中并不显眼,年纪最幼,性情孤僻,其结局是“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真不知王国维从哪里获悉她在“知力”上“高百倍”于宝玉,而导致其解脱是“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而宝玉之解脱是“自然的也,人类的也”[1](P8—9)。这只有一个解释:当青年王国维把“方法”等同于理论原型,且让“对象”鼻子被牵着走时,其《评论》才会将《红楼梦》矮化为佐证叔本华哲学的文学注脚。
《词话》无疑是奠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地位的经典性论著。本章拟就《词话》的学理体系性,来说明何以反正,即返回到“方法—对象”的逻辑正态,从而告别错位。
若着眼于学术题材,《词话》所涉足的论域要比《评论》开阔,后者仅仅是一部清代小说,前者则从唐、宋绵延到晚清。若着眼于学术运思,则两者其实在面对同一“方法—对象”难题,即“对象”皆为中国文学,“方法”皆来自叔本华理论。这就让《词话》与《评论》有了可比性,何况作者为同一个人。
还得从“体系性”说起。《词话》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论,不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还是刘熙载《艺概》,皆不无“思想性”(创意卓见),但无“体系性”。体系不是指见解的规模性堆积或模块式排列,而是指其思辨建构要满足三个条件:(1)该理论须有一个一以贯之、拟作逻辑起点的元概念;(2)此元概念不仅能涵盖理论对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能像全息胚那般从中推导出其他相关概念;(3)此推导必具内在逻辑动力感,使学理聚合舒卷自如,其论证结构既缜密无间,又晓畅得像行云流水。
《词话》基本符合上述三条:(1)该论著有一以贯之的元概念作逻辑起点,即“境界”;(2)此“境界”拟分“内美—修能”两个层次,“内美”意指诗人对宇宙人生的价值体悟,“修能”则指其形式须清新俊爽,豁人耳目;(3)无论是从“内美”推导出“境有大小”、“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诗人之境”与“常人之境”,还是从“修能”推导出“隔与不隔”,皆具内在动力定型,无生剥硬拗之痕。但美中不足在于,元概念及相关概念之内涵与外延未见明确界定,然从相应语境来看,概念与概念间的逻辑“边界”仍隐约可辨,不至于混淆。这大概是《词话》从传统点评式文论向现代学术转型时留下的过渡轨迹。故《词话》虽称不上典型的“体系”,但已具有“体系性”则无疑,不妨称之为“准体系”或“潜体系”。
现在要问:那个让《词话》生气贯注、浑然整一的“境界”从何而来?是从叔本华哲学原型中剥出来,且是“双重剥离”:一曰从“生活之欲”中剥出“势力之欲”;二曰从“直观”中剥出“境界”。“剥”,喻指思维分离。这就是说,“做书功夫全在书外”,在王国维着手撰《词话》前,为了提炼“境界”这一元概念,他做叔本华的功课已颇具“再创性”,而不像1904年读叔氏《性爱》只具“模拟性”。
先看王国维怎样从“生活之欲”剥出“势力之欲”。“生活之欲”原指活在个体身上的种族意志。叔本华设定种族意志的“个体化原理”时有个毛病,即未明确个体“生活之欲”实含生理欲求与精神追求两项,彼此间不无异质界限。王国维1905年撰《人间嗜好之研究》时清晰地提出,除了生理之欲,人还有势力之欲,它不隶属于人的生物性生产及再生产,而只满足人的精神追求或情思熏陶;它虽“与生活无直接之关系”,但也不能“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因为“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之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而务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生活之上。此势力之欲,即谓之生活欲之苗裔,无不可也”[1](P43)。
说“势力之欲”是由“生活之欲”经“竞争”(社会实践)而生成的异质变体,王国维有此见解,委实可嘉。可嘉处有二:一是在叔本华笔下,人从生理个体转为认识主体(即人类精神素质之发生)不是靠社会实践及文化氛围,也不是从人身上历史地长出来的,倒是宇宙本原为了能顾盼自身而从外边硬塞给人的;二是王国维的“势力之欲”说,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人类学的预言,因为它在暗示学术界应到历史—文化深处去探寻人性之根。
这就是说,从生活之欲(生理性)到势力之欲(精神性),其间将经历两者之间的转化中介:一是须与外部世界(以工艺—制度为基础)发生现实关系;二是受制于给定现实关系的价值信息,将伴随主体实践活动而逐渐沉积于生理机能系统,使之转化文化心理结构,此即人性之发生。可以说,李泽厚在1980年代所贡献的、旨在探索人性的历史发生的“文化积淀”说,其源头似可上溯到王国维的“势力之欲”说。或许是李泽厚受益于其他思想资源,但“英雄所见”乃系一脉,当为史实。
所以,从人性的历史生成角度看,与人的“机体→信息→大自然”这一定式相对应的另一定式,只能是“欲念→价值→精神”,即生理性“生活之欲”只有靠价值中介,才能转化为精神性“势力之欲”。这就解释了为何叔本华明明认清了人兽的形体区别,却仍划不出两种人生之欲的异质界限。原因是他只看到了人的躯干与头部,却没有看到大脑作为人体的最精密物质,只有通过价值信息的反复刺激与浸润,它才能滋生思想与情感,即变成灵魂的居所。王国维则以其“势力之欲”说接近了这一点。
再看王国维怎样从“直观”剥出了“境界”。“直观”原是叔本华为了宇宙本原能顾盼自身,而赋予人类的一种高层次认知机能。另一种低层次认知机能即“欲念”。“欲念”只敏感于官能性对象,故叔本华嫌它所提供的世界表象不免初级、模糊、零碎即形而下;相反,宇宙意志借鉴高层次认知机能,就能逼近自身的本相。这一酷似自在之物的、高度清晰且完整的形而上的肖像,叔本华命之为“理念”。当然,“理念”不同于“概念”。叔氏认为概念须借词语来传达,而理念虽可用概念来定义,但其本性“却始终是直观的”[5](P324),即不用概念,它亦能呈示其天籁之本真。叔本华断言,宇宙本原“和我们在自己身上称为意志的东西是同一回事”[8](P83)。那么,“直观”作为人类对自身生命之体悟,也就成了洞开宇宙秘密的金钥匙(直接入口)。也因此,叔本华宣布,“我的全部哲学可以表述为一句话:世界就是对意志的自我意识”[8](P83)。
要从如上“直观”剥出“境界”来,王国维走了三步棋:其一,卸掉叔本华披在“直观”身上的那件观照宇宙本原的理念外套,而裸露其人类心理机能之本相,“直观”只是心灵对其拥有的信息的初始领悟。故王国维认定叔氏认识论“其最重要者”是“出发点在直观,而不在概念”[1](P82)。或曰直观可涵盖若干思维因子,但还未被提纯为概念。其二,被“直观”所领略的信息,既有对体外现实的耳染目濡(官能性触摸),也有对体内心灵的切己体悟(心智性内视)。然“知力愈优者,其势力之欲也就愈盛”[1](P35),愈对自我生命质量抱严肃态度者(所谓“精神贵族”),就愈不时返身自问“活得怎么样”。这个“活得怎么样”之自省,也就是个体对其所拥有的生命的终极关怀,此即“境界”。其三,“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人类对其个体生命意蕴的切己“直观”。《词话》为何说“词以境界为最上”[1](P348)?因为“境界”是指诗人对生命价值根基所能达到的高度自觉,那么,诸如“气质、神韵”之类,当不免舍“本”逐“末”[1](P372)。
而且,“境界”说一出,把王国维的“势力之欲”说也带活了。因为“境界”确分两种:“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1](P393)。王国维对此解释了两条:(1)“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1](P393)——这是就创作论而言的。(2)“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1](P393)——这是就接受论而言。然问题是:为何偏偏大诗人能说出大众很想说、却又说不出的心里话?这就又轮到“势力之欲”派大用场了。王国维说“大诗人”所以“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根子是在“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己”[1](P45)。什么叫“个性至深,人性始呈”?这就是。
更有意思的是,那段令海内外学子口传成诵的著名箴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1](P355)《词话》并非是其原始出处,其最早版本是王国维撰于1905年的《文学小言》第五条,三年后才挪为《词话》第二十六条。主要差异是在:《词话》的“三种之境界”,《文学小言》原为“三种之阶级”[1](P26)。“阶级”在此作“拾级而上之台阶”解,“境界”当意谓“精神高度”。然细读则彼此大意仍趋同,因为《文学小言》版明言:“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持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1](P26)“莫大之修养”意近大诗人才有的“境界”。
“境界”对《词话》思辨建构的全局统辖功能,不啻是“妙棋一着,全盘皆活”。然“境界”的出现,又是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作“双重剥离”后弈出的一步经典式妙棋。其妙在于,虽然就思维资源、过程而言,王国维都受惠于叔本华,然通读《词话》正文,却未见一处叔本华引文;但这并不妨碍有识者仍从《词话》的字面纸背嗅出王国维对人生的诗性遥想,其源头乃是叔本华哲学中的人本忧思,然王国维又比这位德国先哲表达得纯净且凝练。
这当然不是1904年《评论》所能比拟。四年前,王国维未及“而立之年”,其处女作在面对西学与中国文学的“方法—对象”一案时,只会模拟叔本华的理论原型,且将它膜拜为“方法”,扭曲、压扁了《红楼梦》这一“对象”。将“境界”说作为内核的《词话》,以迅猛成熟的再创力终结了这段历史。
“境界”说的诞生,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意义,恐不仅囿于文学学科。其实,它对“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学术如何智慧地善待“方法—对象”难题,已经奉献了足资后学神往并不易企及的思维范式。这就是说,王国维不仅以其《词话》告别了《评论》在“方法—对象”上的机械式错位;而且,其范式也不是那种简易可行、然终究浅显的配型式对位——王氏范式的真髓在于,它“创世纪”地验证了“方法重铸”的可操作性。宛如三部曲:先从西学原型剥离出拟对应于中国文学对象的思维资源;继而配制能整体涵盖其对象的元概念作为方法;最后生出“方法—对象”良性互动的“同步孪生”结构。
若把“境界”这一元概念(方法)置于唐、宋至清的词史系统(对象)去考察,很难说是先有对象,后有方法?抑或相反。乍看当时先有词史这一“对象”。然细想又未必,因《词话》并不旨在对词史作全方位考量,它只想从词史爬梳一条“宇宙人生关怀”的意蕴脉络,来维系或支撑其“境界”说的正当性。从这意义上说,真正作为对象的、在《词话》中舒缓展开、有序期待王氏去品鉴的那个词史,其实是作者为印证其“境界”说而精心建构的。
这就是说,若着眼于知识学,拟有两种词史:一是作为对象,即已纳入给定研究视野的词史;二是未纳入给定研究视野的词史,它还成不了对象。“对象”这概念具有伴生性,它无权独自生成。马克思说,未被人类关注的物资纯属“抽象物资”,它不是认识“对象”。这酷似天下亿万男女,唯有已在恋爱、同时又赢得芳心的那个他(她),才有资格确认自己有“对象”;否则,无“对象”可言。史实也正如此。《词话》第二十六条说过,当王国维用“境界”说,依次将“昨夜西风”、“衣带渐宽终不悔”和“众里寻他”叠出“人生三境界”,且“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1](P355)。这也就是说,当晏殊、欧阳修(当作柳永)、辛弃疾们未能像王国维独具慧眼,从北宋词读出“人本忧思”这条文脉,那么,以此文脉所贯穿的那个词史对晏、柳、辛们来说,也就形同不存在,也就无所谓“对象”了。
但也不宜倒过来说先有方法(“境界”说),后有对象(“人本忧思”为文脉的词史)。因为《文学小言》已表明,在《词话》拈出“境界”一词之前三年,王氏已在晏、柳、辛诸公中悟出“人生三阶级”(“阶级”在此与“境界”近义)。故最恰当的说法是,“方法—对象”到了《词话》语境,确已生出某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毋分先后”的“同步孪生”范式。
于是,人们很难对“境界”概念作“亲子鉴定”,判其基因到底是缘自西学,还是国学?若就其词源来说,“境界”本是中国佛学词语;若就内涵来说,它所蕴涵的个体生命本位意识却是华夏宗法谱系所稀缺的。故最聪明的办法是把“境界”视作中西汇通的诗学“混血儿”,其沉思宇宙人生的幽邃眼神确实不时闪烁西学的遗传因子,但其体格、容颜又活生生地焕发中华国学的风韵。因此,一卷《词话》在握,你将不再遭遇《评论》那样的“方法—对象”之僵硬错位。相反,“境界”说(方法)与词史(对象)之间的融洽度,只有用“孪生子”这一意象才能形容,虽然形相彼此有异,然意念节奏归一,意到笔到,毫无隔膜。
至此,不禁想起钱钟书曾称王国维赋诗,“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9](P24)。此语若移作《词话》评估,亦当警策。《词话》在“方法—对象”一案所熔铸的中西之学术“境界”,后世大概只有陈寅恪撰《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可以媲美,因为当陈寅恪将兰克的史学实证法转为极具国粹的“古典今事”说去“以诗证史”,其效果亦像《词话》一般将西学融化于中国文学研究,体匿而味存也。
标签:王国维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叔本华论文; 贾宝玉论文; 曹雪芹论文; 红楼梦评论论文; 文学论文; 人间词话论文; 红楼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