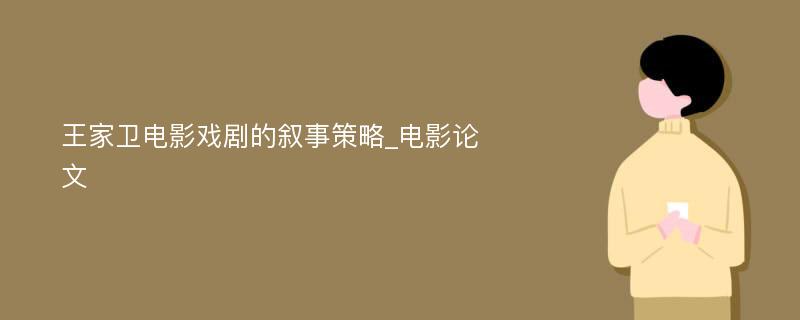
王家卫电影剧作的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王家论文,策略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的叙事结构包括时空的配置与运动、人物的设计、叙述方式的确定、节奏疏密的构思等,是个涉及方面很广,非常复杂的创作问题。结构并非单纯的技巧和形式,它包含着剧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剖析、提炼和概括,关系到作品主题意念的表达与深化,因为叙事结构进程中的任何一个细致变化都不只是形式上的需要,而是表现了主题和剧作者对主题的态度。结构与主题、创作意念密切相关,往往一部影片结构不当则主题意念都会因而达不到艺术效果。对任何剧作来说,思想意图离开了适当的叙事结构处理,就是离开了表现主题思想的基本手段。因此,剧作者若能找准剧作的表达中心,叙事过程中不离开主题意念,而有完整统一的剧作结构来贯穿主题思想,则是成功的电影剧作。
王家卫的电影剧作对时空的运用、人物设计及极具特色的画外音独白作用,都是为了反映出一种90年代香港都市人普遍的情绪体验,其叙事策略,不仅表现了后工业文明下的都市人末世失重心态,而且这种叙事结构具有独特艺术性,表现了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状态的复杂性,准确而独特地剖析了后现代人的生活面貌。
画外音独白的应用
画外音独白是王家卫电影剧作叙事中的一个主要特色。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电影叙事的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论证电影在再现的前提下,能否进行叙述(NARRATION), 而叙述一个故事意味着叙述者策略上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叙事结构和时空观念的转变,另一方面表现为叙事语式和时态的变化。
学者热内特(GENETTE)提出了文学叙事中的时态问题, 从叙事结构上讲,文学的叙事本文与电影本文在叙事结构方面有着相对的一致性。因为任何动词都涉及到时态,所以任何行为动作都关系到时态。而电影中的时间顺序,事实上也有这种情况。根据大卫·波特华(DAVID BORDWELL)的分析,经典好莱坞的叙事特点, 就是在叙事情节设计上必定有起承转合各个阶段,结尾部分一定设法结束故事的因果关系。王家卫的叙事过程中,并不重视传统观念上的叙事阶段:开端、展开、冲突、危机、高潮、结局。王家卫更侧重表达的是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故此画外音独白的应用是剧作者采取的解决方法。而且,由于剧作者所关心的是由英雄片、武侠片等包装之下各式各样都市人的心灵状态,故此,王家卫在剧作中一再应用了多视点、多角度的画外音独白进行叙事。
画外音是影片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段,创造性地构思和运用可以获取独特的艺术效果,甚至构成整部影片的独特结构及风格。例如,著名英国电影导演大卫·里恩(DAVID LEAN )在影片《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中, 就是利用了画外音独白与整体剧作结构相结合。首先,整部影片的结构由女主人公的画外音独白贯串;其次是影片的双层结构,现在和回忆的交叉,亦以画外音独白作为衔接和桥梁。这种画外音独白除了提供了反映出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外,更重要的是达到了巧妙地将回忆的心理与现实心境融合表现,并以配合场面的重复来加强这些画外音独白的艺术效果。在对比之下可见,王家卫的画外音独白应用不同于大卫·里恩之处,在于王家卫并没有刻意建构出画外音独白与剧情推进上的逻辑关系,画外音独白的内容并不构成发展和牵引剧情脉络的作用,这种人物自言自语而又无逻辑含义的独白本身,所要表达出的是都市人封闭式、不能交流的孤独个体状态。
同样是对画外音独白的应用具创新性的尝试,王家卫和玛格丽特·杜拉(MARGUERITE DURAS)画外音独白与电影剧作观念是不一样的。法国新小说派女作家、新浪潮左岸派导演玛格丽特·杜拉编剧的影片《广岛之恋》中对画外音独白极富想象力的创新运用,同时也是对电影剧作表现手段的一种新探索。影片从表现看似讲了一个日本男人和法国女演员的爱情关系,同时围绕这段男女关系情境讲述了法国女子与德国军官战时的爱情故事。画外音独白的叙述显得极其平静,而与画面上出现广岛1945年轰炸后的恐怖景象(烧焦的石头,烫伤的皮肤等)形成了强烈的声画对位。声音与画面各自叙述独立的故事,表面上似乎无所相关,然而内在联系和对比却增强了影片主题和思考内涵,对战争永远不会愈合的创伤重新进行思考。杜拉对画外音独白的探索无疑是拓展了画外音与剧作表现手法上的作用。画外音独白的应用在王家卫电影剧作中是一个主要的叙事特色。例如,《重庆森林》中警员223失恋后买了一大堆5月1日到期的凤梨罐头,独个儿躲在家里吃。画面上我们所看到的223不张嘴说话,失恋的他是相当痛苦的,但他平静的画外音独白却没有显示出他的心情。最后223吃得过多凤梨受不住而呕吐了,画外音独白亦没有丝毫显出他的悲伤情感。这种声画平行的手法,有趣地把人物及情节发展和真正动机隐藏起来。这种画外音独白的应用,非但没有如《相见恨晚》般作出了展示人物内心及推动剧情的作用;同时亦没有像《广岛之恋》一样从声画对位中突出了对战争这个主题内容的思考。王家卫电影剧作中,声音和画面的平行发展,尤其是祷文式喋喋不休的内心独白,是一般影片中所罕见的。画外音独白的应用显示出王家卫个人电影语言风格的特色;这种内心独白的处理,人物说话的速度,字句编排的长短,配合多视点独白的叙述结构,形成了一个反复吟咏的和弦感觉,制造出的情绪气氛,正好表现出一种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领域和情绪状态。
王家卫这种画外音独白应用的特色,是与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叙事方式的改变有关。当今电视媒体对于传统叙事方式是有着一定冲击的。一般的电视剧集、新闻报导或纪录片节目的叙事过程,每每会被广告所中断。广告的叙述时间也许只有数十秒,但却尝试以最吸引人的方式和映像宣传其产品。广告过后,叙述又回归有关的电视节目。另外,以遥控制快速转台,随意挑选及转换电视媒体的叙述方式,令后现代语境下的人接收到的一大堆资讯,资讯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而只是随意浮现在观看者面前,观看者根本没有时间去理解或组织所有资讯。这正是“精神分裂”式时间所展示的一种模式,而王家卫的电影中对叙事时间的处理,是后现代人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时间体验的一次真情书写。对于传统电影剧作叙事模式的连贯性,王家卫亦做出了不少突破。王家卫剧作中大量应用并非为叙事时空服务的画外音和独白,直指人物内心情感,并向传统电影剧作单向叙事时空方式作出挑战。
王家卫电影剧作中的人物,一般都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拒绝去了解别人,亦拒绝为他人所了解。这些人物有些并不知道怎样去用说话表达思想;或觉得说话并没法表达其内心;其中有些不乏害怕承担说话后的责任。他们一般都保持沉默,而这正是王家卫应用画外音独白来展示这些人物内心的主要原因,亦是王家卫所刻意侧重的地方。剧作者并不在乎画外音独白的使用是否达到传统电影剧作意义上的叙事时空及因果连贯。在其剧作中,王家卫是着眼于在后现代语境下,飘泊于表面意象世界上个体的内心独白。
与传统电影剧作,甚或其它香港电影比较,王家卫《阿飞正传》使用对白的次数少之又少。不过,影片中却应用了不少画外音独白,例如,旭仔提及的“无足鸟”传说。其它大部分的时候,旭仔都是一个没有太多说话的人。他喜欢挑逗其他女孩子,但从没有认真地跟她们对话。旭仔真正曾诉说内心感情的对象,却是一个陌生人阿超。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对陌生人吐露心迹并不用怕会带来“历史感”延续的责任。丽珍对陌生人阿超诉说内心,并让他陪伴谈了一个晚上,亦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重庆森林》中,警员223夜深致电欲与友人谈话, 但却一一失败。他退而在叨叨不休的独白中抒发出感受。一连串画外音独白:“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每个东西上都有一个日子……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不会过期”、“失恋的时候去跑步,把身体里的水分蒸发掉就不会流泪”。而另一位警员663,他一开始就选择不与人交流感受,他选择对家中的用品,如毛巾和毛公仔自言自语。他对着用过的肥皂说:“不要那么没有骨气嘛,她才走几天就瘦成这样。”这些家中用品变成警员663的发泄对象。 这些平日沉默寡言的人物,在背后却以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自我安慰。这是王家卫一种幽默的调侃,这种画外音独白的应用,在另一个程度上变成了王家卫电影剧作的一个创作特色。这些自我和偏执的人物,拒绝告诉别人自己的感受。如果要交流的话,他们会选择陌生人(如阿超),又或者“非人”(如小狗、家中物件作为倾诉对象)。在其它情况下,王家卫则安排了画外音独白的方式,让人物把情感诉诸镜头外不知名的空间或观众。在这种画外音独白之下,这些平常沉默的人物,都喋喋不休诉说感受,他们甚至不介意说了什么,因为没有对象的画外音独白,是他们唯一固守的内心世界,这种诉说方式既安全且不用承担责任。
《堕落天使》中把对画外音独白的运用达至电影时空设想的极限:哑巴志武应用画外音独白来诉说自己的感受。对于情感交流方式的单向展示,经过在《堕落天使》中的这种调侃和宿命的拼设,王家卫对画外音独白及其剧作形式的探索,无疑是到了一次巅峰的尝试。及至到《春光乍泄》,王家卫并没有摒弃画外音独白的应用,除了表达人物内心感受外,如小张出场时的阐述,亦配合了剧作中穿针引线的作用。对于语言表达情感这个主题上,王家卫在《春光乍泄》中提出一个揭示。从《堕落天使》中哑巴的画外音独白对电影语言伸缩性的假设,发展至小张在《春光乍泄》片中能听出远至数张座桌外的人说话内容,近至黎的内心感受,王家卫是首次从剧作内容的角度,展示了这些后现代语境下拒绝沟通的人物,一再应用旁人听不见的独白的矛盾和出路:小张认为用内心听是可以听出人的心声,但矛盾之处亦正在于小张这种能力也是一种虚设,画外音独白仍是《春光乍泄》中人物表现内心的途径,只是小张这个人物的设置,却仿佛在这些冰封的无法交流状态下,带来一点人性化的情调。
突破传统时空观念
时间和空间是电影构成的两个基本因素。它们在影片中互相错杂交替,相互影响。电影这门时空的艺术,叙述必须透过空间现象的流动,是以空间的表现来说明时间的流程和变化。电影的时空既可以集中、压缩,又可以延伸,还可以依据剧情的需要跳跃、停滞,甚至倒退,既可以自由地转换和转移,又可以根据创作者的想象表现现在、过去、未来三种时态,以至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
传统影片中的时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时间与事件时间的比例关系,交待出来的事件与直接表现出来的事件总要有恰当的比例。在传统剧作模式里,一个电影艺术家要善于将情节恰当地分配到事件时间和叙述时间中去。这些影片中时空的设计还包括电影里哪些部分要延伸时间;哪些部分要压缩时间,跳跃空间一笔带过;和采取什么样的结构形式来叙述情节,一如在《早春二月》的顺叙,《人证》中由高潮切入,《生活的颤音》的倒叙,还是如在《小花》中的多时空穿插的结构形式。虽然影片在结构方式上各异,在时空的运用上也有各自的特色,不过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些影片的故事构成的叙事过程,还是发生在一系列按照因果格式发生的时空结构中。叙事的因果关系是表现在井井有条的时空关系中,以达至清晰线性叙事的目的。
电影艺术在时间与空间运用的高度发展中,由于不受限制的自由能力,使现代主义时期的电影逐步深入到更为直接地反映人的心理世界。这是电影艺术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探索在欧洲不少电影中反映特
1别突出,如《广岛之恋》、《8—》、《野草莓》、《尤利西斯》等影
2片。人的思索、幻觉、回忆、理想、愿望、梦境、联想,甚至极其微妙复杂的下意识内心活动,都可以用视觉形象来表现。电影时空的内在化,心理蒙太奇的发展,使人们的心理活动,通过电影的声画具像地表达出来。现代主义时期的电影突破了传统的外部表现手法,将它的表现领域引入内心世界。
杰姆逊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下的时空观念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我用时间的空间化把这两组特征(表面与断裂)联系起来。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空间性了……在后现代的这种新空间里,我们丧失了给自己定位的能力,丧失了从认识上描绘这个空间的能力,对此我做的最后诊断是后现代新空间中的存在困惑。这种文化是一种无中心的,不能被形象化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不能给自己定位。这就是结论。”(注:钱善行主编《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 133页。)正常的空间观念是由事物构成的,或是由事物组织的。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所谈的是事物的消解,而已不能再谈组成的因素。后现代文化思潮下对于时空观念的影响,反映在电影剧作中,就是时空并不是由完整事件所组成。因为在后现代这种新时空当中,人已丧失了给自己定位的能力。就以王家卫的电影剧作中的时空应用为例,事实正是具有这种时空断裂的特色;这种结构形式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下,个体与个体分界的消失,这种文化是一种无中心的现象。人活在后现代的社会里,人的独特性消失了,身处其中的人无法从一种固有并且自满自圆的时空中给自己定位。王家卫电影中断裂的时空运用反映了一种后现代的社会下人们的精神状态,这正是杰姆逊所提及主体所体验的“精神分裂的孤独状态”。
这种“精神分裂式”状态,对叙事模式亦有一定影响。“精神分裂”文本对叙事形式的影响,并非在于现代派意义上的个人风格,也不是“精神分裂”文本中病理学意义上的非个人化风格——它的特色是无中心的,因为作为叙事过程的主体,讲述的故事并不属于主体,并不象现代派的主体那样以独特的风格去突出并控制叙事的方式本身。在后现代文化思潮下,那是总体叙事和大叙事(METANA
RRATIVE)概念的消解, 叙事的时空只有是永恒的现时之所在,“时间凝缩为一瞬间”,这种时空观念是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线连关系;反之,永远的“主观瞬间”就是后现代时空的一个叙述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家卫电影剧作中,多视点及非连贯叙事逻辑的时空运用,正是后现代时空观念的一个反映。
传统香港商业电影的时空运用方式,基本上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翻版。而王家卫电影中时空的应用,与传统香港商业电影或好莱坞电影的区别,是在于因果关系的结构方式和时空应用上。美国学者大卫·波特华( DAVID BORDWELL)在《经典好莱坞电影》( THE
CLASSICAL HOLLYWOOD CINEMA)一书中,就已对叙事和时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事实上以经典好莱坞的叙事模式来说,连续性的叙事系统,清楚的叙事线,动因和人物因果发展都被一一规范化,剧作者几乎都不假思索地在叙事中以这些模式形成井井有条的时空关系。
王家卫电影中的一些十分明显的主题(如人物情感的孤立,拒绝沟通,或交流上出现困难),在其影片中一再出现。而在展示这些主题时,王家卫把故事的时间、空间切割成零碎片段,打破了时空在传统影片中的线性叙述,从而表现出一种人物置于空间当中,但又不知身在何时何处的虚幻感。
打破时间直线顺序的方式,在各项创作形式中都已有先例。文学潮流中接连出现的意识流、后设、解构等文体,在香港文学中亦有不少例子(如近代的作家西西、黄碧云等)。而在西方文学中,如品钦《万有引力之虹》等小说的出现,亦宣告了关于时间线性关系中的过去和将来这种深度消失了。如果有对时间的解释,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人只存在于现时而没有历史的线性作用。
近年的影片如《暴雨将至》(BEFORE THE RAIN )以互为因果的圆形时间结构为本,时间次序被割裂,但线性的叙事时空仍是被再强调并重组。另一个例子,如《低俗小说》,亦可归纳为这一方面的例子。有不少评论都引述《低俗小说》为后现代电影。从时空运用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有待商榷的。《低俗小说》和《暴雨将至》两部影片都是以零散的叙事片段布置了电影的结构,然而,线性的互为因果事件,仍是两部影片的轴心,所谓的时间倒置,只可说是传统电影中“闪前”和“闪回”等把戏的深化和延续而已,基本上这两部被大部分评论家视为“后现代”的影片,与大卫·波特华在《传统好莱坞电影》一书中提及的经典好莱坞线性因果及时空构造没有多大分别。
王家卫电影剧作中对时空的处理,无疑是比上述这两部所谓“后现代”电影来得更为大胆及野心勃勃。对于时空架构的突破,文学领域上是比电影走得远,走得快。这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因为电影在集体创作和市场效益考虑上的限制,故此对时空线性叙述的颠覆,终归没做到个体创作的小说来得彻底。王家卫曾在一次流动电话广告制作特辑中提到,“如果一部电影是一本小说,一个广告是一篇散文……”从中可见王家卫对电影和文学两个媒体之间,不无一点眷恋。王家卫的剧作一直有被拿作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比较,而王家卫亦在一次访问中提及了他十分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除一般评论认为王家卫与村上春树二人之间在细节上的应用相似外(如没有名字的人物,人物拒绝情感关系、喜欢利用数字、日期等等),其实有一点被忽视了的,是二人在时空观念的突破,并且制造出现实以外的虚幻时空,专注于人物心理状态的流动。就以村上春树的《末日世界与冷酷异境》为例,当中以“末日世界”和“冷酷异境”两个时空方式,展示出一个富有未来主义色彩的东京,城市脱离了现实根源,人物如活在幻想世界当中,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王家卫的电影剧作与村上春树小说展示的时空观念及主题索求,是有相互值得参照之处。若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末日世界与冷酷异境》中以未来主义式的日本和独角兽寓言时代两个空间来达至对现在时空书写的错体感觉,那么,王家卫剧作中的时空运用无疑与村上春树有相通之处。虽则利用的时空类别有异,但如《阿飞正传》中以60年代的香港,或《东邪西毒》中以武侠世纪的虚设古代,来诉说90年代都市人的情感,事实上是异曲同工之妙。
把两个截然相异的时空拼合在一起,抵消了古代、现今、未来时空之间的界限。界定现今的相对时空,或界定古代、未来的相对性二元对立性已不复存在,这正是后现代语境下,“能指”与“所指”之间由必然关系变成随意性的多元关系。历史意识消失产生断裂感,这使后现代人告别诸如传统、历史、连续性,而浮上表层,并在非历史的当下时空体验中去感受断裂感。在后现代的时空运用上,是一种不及内层象征或寓意的拼凑。根据杰姆逊的说法,“拼凑”的出现是由于主体的消失而带来的后果,随之而来是个人艺术风格不复存在。就以王家卫电影剧作《重庆森林》为例,当中展现了时空的拼凑特色,由警匪片和爱情轻喜剧组成的两个时空拼凑在一起而不带来经典电影叙事模式上的起承转合效应。而“拼凑”和“模拟”是截然不同。同样是以警匪片作为其剧作素材,戈达尔的《精疲力尽》是模拟了警匪片的警匪追逐模式,却达至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生命荒诞。这种表面上看来荒诞无意义的表达方式,其实是一个深度模式,展示出人物生存着的一种狂乱、随意及不受控制的状态。这是存在主义关于真实性与非真实性,异化与非异化的两项对立产生的主题意义。这基本是戈达尔对警匪片一次模拟的变奏。相对于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中,对类型电影的应用亦是一种拼凑方式,就以前半部的警匪片类型为例,各当代情感书写的空间拼凑,坚决拒斥所谓可以从中找到支持或变更类型模式的说法,而展示出一种对时空认知的错体,这正是拼凑作为一种“空白模拟”:一种没有最后目的模拟特色所在。难怪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下的作者、艺术家或电影工作者都感到现今时代再没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他们都认为最独特、原创的艺术风格都已经被应用及创作过了,现今剩下的只有极少数选择及组合的可能性。王家卫曾多次提及到其剧作态度,他认为现今电影剧作就正如在超级市场内选取并组合各类型电影剧作风格。而王家卫电影剧作中对时空的多元化拼凑应用,无不受此影响。
王家卫第一部电影剧作《旺角卡门》中对时空应用的特色,已崭露头角。在空间处理上,王家卫使用了黑帮斗争的都市,与情爱世界对立的市区内小房间以及大屿山郊外空间。王家卫时空拼凑的剧作风格由此可见一斑。王家卫电影叙事结构虽然常常是应用了这种断裂拼凑的时空处理,但并不影响结构的完整性,在《阿飞正传》里,王家卫应用了60年代的香港这个时空,却轮流刻画了人物间聚散的情缘:旭仔和丽珍、旭仔和美美、丽珍与阿超、旭仔与阿超等等,一再展现出是一种缘份即情性的、一错便不再复得的现代都市情感。时空的混合亦是一种后现代“精神分裂”模式。人类都有可能只生存在现在,但只有精神分裂者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没有任何记忆亦记不起自己是谁。精神分裂就成了丧失历史感的一个强烈而集中的表现。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时空感应和身份。这不再是旧有意义上的异化。在异化里,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只不过是人没有权力拥有它。而在精神分裂中人完全失去了其身份,并已被零散化,自我已经没有过去了,展现在电影剧作中,每每是多种历史时代的特征被混合并拼凑起来。真实历史感已不复存在,曾经发生的事情,都和人的见解、记忆、经验融合在一块儿。故此,王家卫在谈及《阿飞正传》与历史感等问题时,他的想法是在电影剧作中真实历史重现的可能已不复有。这样的做法只是不断地在展现“现在”。在接受魏绍恩访问时,王家卫曾谈及(阿飞正传)的创作:“我绝对不要精确地将60年代重现,我只是想描绘一些心目中主观记忆的情景。”(注:魏绍恩《四出王家卫·洛杉矶》,香港陈米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7页。)
《重庆森林》如上所述,是以两种电影类型拼凑的两个时空,断裂的叙事时空中处处是因段落间对比而来的冲突张力,或因类比而强化的主题。及至《堕落天使》,这种都市时空的未来主义和怀旧色彩的拼凑,又因一段段人物近似即兴发挥的段落组合而成,达至对现在时空中的情感关系产生虚幻感和时空错位。《东邪西毒》中借用了武侠片的古代时空,以横向的叙事方式,叙述8名沙漠过客的故事, 从提鸡蛋少女为弟报仇的亲情,到友情(如东邪与盲侠),及至缠扰各人的爱情均层层对比,展示出一种属于后现代语境下复杂、多元的人际关系,和个体的“耗尽”的情感状态。
《春光乍泄》从剧作内容上,把两个香港人放置在阿根廷中,这本身是一个身份和空间分离的处理手法。对于香港这个地域主体,王家卫应用多个不同的时空加以索引,从黎耀辉致电给父亲,至随后想起在地球另一端倒置了的香港,由置身台北时欲回又止步的香港,至电视机内宣告悉尼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而北京落败的消息,其中不乏隐含回归将至的香港对祖国的情怀。从空间的断裂,游离于城市之间(布宜诺斯艾利斯、台北、香港),到叙事时间单向中的拼凑(黎与何、黎与小张的人物关系似续已断),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展示了剧作者尝试从别的空间来述说香港,在时间处理上首次回归到自《旺角卡门》以来,难得一见的单元叙事时间发展,表现出一种回归简朴的取向,而空间处理上,则达至一种剧作内容上的错位感(香港人流离于都市之间)。亦基于这个原因,《春光乍泄》是王卫自成名后,首次以自然流动的情感,出奇地为香港本地电影观众所接纳的作品。《春光乍泄》中配合剧作内容引发的空间断裂,实质上更真情地展示了回归前香港人的那种无根感觉。王家卫的电影剧作中一直不乏这种香港人特有的情怀,在《春光乍泄》中,剧作内容上细致著墨,配合剧作结构上时空处理,而达至浑然一体的效果。
电影是一门时空艺术,所以在创作领域中,艺术家每每进行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探索。同样,时间和空间也成为王家卫电影剧作中的重要元素。王家卫在剧作中显现了个人在碎片样零散的时间和自我封闭的空间里,无法逃避后现代文化氛围下的寂寞和情感耗尽。
人物观念的重建
传统电影剧作中,重视表现人物的特征或性质,围绕这个人物和他呈现的特征去构成的人物关系。人物关系展开和产生的情节,在传统电影剧作中,是存有着内在关联的。在这种剧作方式中,剧作者考虑到人物形象将设置成怎样的身份(地位、性格、职业等),活动范围、思想倾向、人物之间将设置成怎样的关系。人物之间的关联通过各种方式,如通过事件或者环境来展示人物关系的发展。如在影片《悲情城市》中,剧作者是通过人物的设计和人物关系的设置,实际是将台湾最基本的四种政治力量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引进了一个普通家庭,并以家庭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的变迁。
在后现代的文化思潮影响下,有关“主体”的理解,实质上对传统剧作中的人物观念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改变。关于“主体”的说法,著名德国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蒙(MANFRED FRANK)曾经论述到, 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性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它是万能的,能认识一切,主宰一切。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主体只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如果要说主体,那么,应当说存在着两种主体,即意识(虚假的主体)和无意识(真正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人的本能冲动和欲望,但随着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化,这种本能欲望日益被压抑,被驱逐出意识,从而成为“阴影”和无意识。因此,真正的主体始终处在被统治、被理性和秩序排斥的状况,它在本质上是叛逆的、反秩序的。关于意义和真理,传统的形而上学认定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客观的、自在的、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意义,这便是科学所不断寻找的真理。后现代哲学家批判这种看法,认为所谓的客观意义或真理只不过是思维创造的神话。意义或真理是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为了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虚构出来,它并非客观的、永恒的,而是一切权威的统治作为合法化的借口和工具使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形象的符号化趋向是可以被理解的;人物开始脱离了为剧情服务的原则。在后现代文艺思潮影响下,电影剧作者的人物观念产生了变化。后现代电影剧作中人物观念更重要的地方,是人物并不是单纯为了情节而存在。情节在后现代的电影剧作中没有更大的发展,因为所有为人熟悉的经典情节都在世界上各式各样影片中出现过了,情节已经是无法创新,人物设计亦是无法从崭新的生活角度切入,因为所有人物特质、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都已经被创造过,而且对于后现代的剧作者来说,现实生活是复杂并且瞬息万变,那是从生活面貌、职业身份等方面入手,并叙述的人物形象的传统叙事方式所无法完全把持的地方。故此,后现代电影剧作中一个重要特点,如展示在王家卫的电影剧作中,是人物形象的符号化,人物关系的无疾而终,那是后现代文化背景下人们迅速交往,但又缺乏建立深刻的精神面貌的一个反映。
王家卫电影剧作中的人物设计,成为香港后现代语境下大都会青年心理意识的一个揭示。在面迎全球化、国际化企业垄断下的生活模式,不论纽约、东京或香港,人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的大众传媒语言下,穿同式样牌子的衣服、鞋,喝可口可乐,听桑尼耳筒收音机。在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下,人们很难感受出与别人不同的感觉,要坚持个体的独一无二更是不可能的。这是后现代文化氛围当中,艺术创作的一种趋向,独创与大众、艺术与商业、雅与俗等之间的界限已被抵销,各个剧作者之间的艺术风格的分别已经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各类型电影模式相互融和及拼叠,这样的剧作观念亦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剧作中人物塑造的观念。一般电影中人物名称是界定人物身份的基本符码。然而,王家卫电影剧作中更多时候,人物的名称都变成了数字,或者,人物是没有名字的。在《阿飞正传》中,人物没有全名,有的也只是别名,如“美美”、“露露”是一个歌厅女子的两个别名;其他人物是“阿超”、“旭仔”、“丽珍”。人物都没有被显示出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他们的姓氏更是从不被提及的。
在《重庆森林》中,人物的名字变成了以数字来代替,两个警员的代号是223和663,人物之间也因这种数字或无名化的联系而产生新的人物关系模式。223在生日那天接到酒店金发女子的传呼, 但他从不知道那女子的名字,收到传呼机的祝贺语,223一样的欢天喜地。663与女店员之间最后虽然产生了若即若离的情感,但二人相处之间从不用名字称呼对方,结果,剧作的人物都变成了没有名字一样,人物之间从不用对方的名字作为交流的方式,就仿佛直接的交流已显得有点肉麻和不合时宜。人物关系中这种拒绝落实的态度,发展至《堕落天使》,杀手只由一个传呼机号码代替其名字。女经理人变成一个没有名字的人物,有的只是经理人这个职业身份,而这个身份亦是剧作里的一个代码,对于其工作的具体细节内容,电影剧作中并无细致描述及安排,剧作者的侧重点只是人物之间的情感刻画。王家卫从没有披露拥有更多社会或家庭内容的人物。人物飘泊于多元混杂、人情冷漠的香港大都会中,感受着无法把持、流离无根的生活状况。
《东邪西毒》中的人物都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剧中人物却与一般武侠小说读者所认识的人物历史截然不同,套用后现代文艺理论说法,正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二元关系已被打破,换来的是“能指”及“所指”间无限的可能性。而王家卫的《东邪西毒》正是利用这些著名武侠人物于原著小说中未曾涉及的“前史”部分,创作了《东邪西毒》这部影片。
其实这种“解构历史”的作法,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已屡有例子。如台湾近代诗人陈大为以《再鸿门》一诗作重读了《史记》中“鸿门宴”,尝试从一个后现代文艺观,来瓦解《史记》中被描述得惊心动魄的“鸿门宴”。在《史记》原文中,读者每每都会在阅读过程中不禁为刘邦的处境抹一额汗,又难免站在范增的位置责备项羽未能当机立断。然而,即使《史记》中司马迁的情节描写得多么细腻动人,那只是对过往历史的一次幻想和转释,真正的历史面貌是无人能得知的。这是后现代语境下对历史的理解。历史可以被描写得高潮起伏,起承转合而迂回曲折。读者依据作者的写作策略安排,历史的细节也变成一种如小说或剧作里的情节安排一般,同样有着无数的可能性。故此,对于历史人物的传释,如刘邦的胆小如鼠,或项羽的有勇无谋,也只是司马迁对历史本貌的一个可能性的描述而已。而陈大为在《再鸿门》从三个角度:读者阅读《史记》里《鸿门宴》一些阅读必然经验、司马迁写《鸿门宴》的经验及陈大为本人写《再鸿门》中后现代文化中阅读几方面,层层解构历史和写作本身的一些必然关系和理解。
王家卫的《东邪西毒》中对金庸原著《射雕英雄传》的重新阅读,亦是后现代文化氛围下的一个共性。“欧阳峰”、“黄药师”、“洪七”等人物都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著名侠客。该小说自70年代起已被屡次改编为电视剧集或电影,更令小说中人物变得家传户晓。王家卫在《东邪西毒》这部影片中,把原著中的歹角“欧阳峰”变成悲剧人物,成为电影剧作中的主角,作恶多端的他首次被披露了狠毒外表下受伤的心灵。“黄药师”这个原著中的孤僻怪侠,在王家卫的剧作中,亦因为一些情感瓜葛而飘泊于沙漠。“洪七”在原著中刚毅不屈,在《东邪西毒》的剧作处理中,他是一个敢于面对爱恨的人,愿意携着妻子闯荡江湖。而出现在金庸另一本小说中的人物“独孤求败”却被王家卫引入了《东邪西毒》的故事架构中。这个人物同时活出慕容燕、慕容嫣两个身份的角色,并在两个角色身份中变换,在爱与恨两端徘徊。人物的名称变成一个代号,名称并非代表一个既知身份的认定,相反,名称变成了混淆既定身份的界限和认识。
在王家卫6部电影中,对人物身份的选择有着一致的脉络, 这是个有趣的地方。男性角色身份,一般是“阿飞”、“杀手”和“警察”。在这三种人物身份中,如《旺角卡门》的华和《阿飞正传》中的旭仔,都是阿飞形象性格的不同侧面。《重庆森林》中的两名警察223和663,《东邪西毒》中的4位杀手和《堕落天使》中的杀手形象, 展示的是同一个身份包装之下人物性格及不同可能性的展现。在这些身份的包装下,其实他们拥有的都是边缘人物的特质。女性角色身份中,王家卫曾多次应用,如《重庆森林》中的女毒枭或《堕落天使》中的杀手经理人,这些都是商业类型片中典型社会边缘人物形象的套用。杀手、贩毒或警察的职能和人物的生活本质,只给予片面的显示,而没有深入牵涉到职业或身份本身和情节发展的关系。对于其他身份类型的处理,王家卫亦有相同的倾向。如《阿飞正传》中的女售货员、《重庆森林》中的女店员、空姐、《堕落天使》中的飞女等等,这些人物的工作身份显得像一个符号,只给予王家卫套人情感故事的途径,情感的发展依旧是单向的,固步自封的,不管情感发生在任何类型的人物身上,有趣的是女性角色的人物,一样是处于边缘。空姐往返于城市之间,售货员和女店员亦一样,每天接触不同的顾客,工作本身的流动亦相当大。发展到《春光乍泄》时,王家卫干脆摒弃了商业类型电影的人物形象,或流离工作性质的人物,单刀直入描述了3个流落异乡的人物; 《春兴乍泄》中的流浪者,大概是王家卫前5部电影一直诉求的人物本质所在。
王家卫人物的一大特征,就是无根性。故此,剧作中对人物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都欠缺具体的描述。《重庆森林》中的警察,《东邪西毒》或《堕落天使》中的杀手,行动的片段亦是被轻描淡写带过,没有具体的剧情实质。结果,是制造出一种活生生的类型电影人物形象,却在现实生活中无限飘泊的感觉。在王家卫所有人物角色中,人物与社会的关系是隔离的,从杀手、毒枭身上固然很难找到他们与社会、家庭之间的关系。另一些小人物如售货员、巡警、店员,我们知道的也只是他们的职业,对于他们的社会、家庭、人与人的实际交往和关系却一一欠奉。王家卫剧作中人物本质上的这种无根性,正体现了在人物社会关系的欠缺和角色一再飘泊于香港都市当中(或香港都市的替象里,如沙漠、布宜诺斯艾利斯、台北等等)。
王家卫曾说过:“连续5部戏下来,发现自己一直在说的, 无非就是心里面的一种拒绝:害怕被拒绝,以及被拒绝之后的反应,在选择记忆与逃避之间的反应……”(注:王志成《灯火阑珊·情感辉煌》,《影响》(台湾),1996年第2期,第46页。)于是, 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都以一种拒绝群体性,又拒绝个体孤独性的生活方式活着。每个人都渴求情感,但又害怕被拒绝而难堪。王家卫电影剧作中无论是杀手、阿飞、空姐或是警察、毒枭、舞女、店员,活着都是一样飘泊,徘徊在繁闹虚浮的都市中,疏离又封闭。追寻和拒绝两个主题被设置在每个人物身上,每个人物都在追寻:旭仔追寻生母;丽珍追寻旭仔和婚嫁;223追寻阿美、663追寻空姐和阿菲、慕容燕追杀东邪,甚至到何宝荣、 黎耀辉之间的你追我逐,每一段的追寻故事,其结局都是失败的,人物的追寻都是被拒绝了,若把追寻和拒绝的主题放在90年代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下,可以看出一种追寻香港身份本位的意义。王家卫作品中人物都是香港人,他们生活的空间有香港人熟悉的“旺角”、“重庆大厦”;甚至《东邪西毒》中的虚构人物亦是源自香港的武侠小说。王家卫的作品中的人物,不论警察、毒贩、阿飞或侠客,展示出来的都不是类型电影中的人物,也不是金钱挂帅的香港人形象。《阿飞正传》中,旭仔寻母是一个追寻过往历史的旅程,不难看出是一种久历殖民统治的香港,面临回归祖国,显示出的一次对根、对亲情、对生命的寻找。在人情冷漠的大都会中,在有限的时空和认知当中,寻找的过程是痛苦的,被拒绝的惶恐和对自我身份的无法把持,都是王家卫作品人物飘泊的原因。王家卫一再钟情社会边缘角色,亦是处于主体或母体文化边缘的香港,经济成就虽然响誉国际,电影创作的成就亦令它成为“东方好莱坞”,但香港文化一直被置于边缘,或被视为文化沙漠。不论从历史、或文化认知上,都因殖民统治而产生了无法定位的流离、无根感觉,这正是王家卫作品里人物同有的本质共性。故此,显示在王家卫的剧作里,这些人物都无法从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职业身份、或情感生活中建立其身份位置。在《东邪西毒》中,西毒说:“翻过了那座山头,仍是一样的沙漠。”在边缘的文化位置上,寻找是徒劳的,因为香港的身份从来没有存在过。加上后现代国际大都会的浮华、人情的冷漠、文化的无根、生活的无目标,生命短促变幻无所适从,这种种揭示了的是一种90年代历史转折中的香港人,在后现代语境共同文化和社会现象下独有的心理状态。自我、偏执、无根、隔绝、流离、冷漠,这都是后现代都市人共通之处,而王家卫以展示独特香港情怀的人物,却同时打动了国际电影市场上的年轻观众(如日本、韩国和法国等)。
标签:电影论文; 王家卫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情感模式论文; 阿飞正传论文; 重庆森林论文; 画外音论文; 低俗小说论文; 堕落天使论文; 广岛之恋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