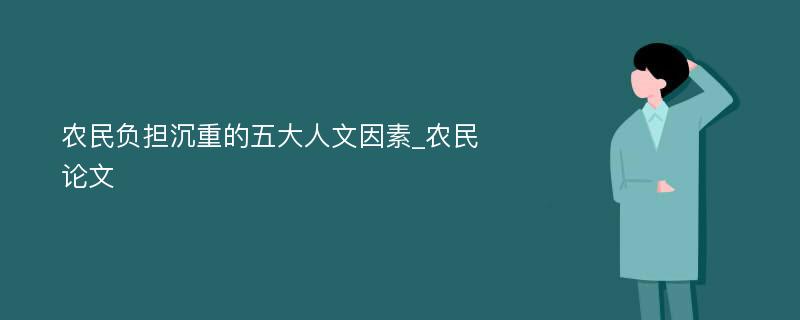
农民负担沉重的五大人为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农民负担论文,沉重论文,人为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尖锐和严重的农民负担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从更深层次的角度上来进行理性思考。虽然农民负担的产生有极其复杂的多种原因,但笔者认为,一些客观存在的原因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得了的,它需要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步消解,但一些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人为的政策制度,就必须予以清醒地认识,从而果断地予以废除和改革。从根本上说,我国新时期的农民负担主要是人为的政策制度造成的。为此,本文着重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笔者认为新时期农民负担沉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之一:“挖农补工”战略。建国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优先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资金,国家从1953年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实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隐蔽地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资金,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1985年国家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合同定购,但剪刀差并没有消除。这种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是农民的最大一项隐性负担,斯大林、毛泽东都承认国家对农民“挖得很苦”,农民对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这种“挖得很苦”、“很大贡献”,对农民来说就是人为的政策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不公平负担。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了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高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这说明本来很贫困的农民每年还要向城市和市民支付1000亿元以上的负担。这种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形成的剪刀差,给农民造成的负担时间之长、数额之大,在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大多数农民并不清楚个中缘由,也没有切身的体验,这是因为这种农民负担的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特征。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下,政府不是与单个的农民进行交易,而是通过公社、大队、生产队与之发生交易行为,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高压控制,故而未引起农民外向的强烈不满,但这种隐蔽性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却是以农业的长期落后和农民的长期贫困为代价的。
人为因素之二:城乡隔离政策。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确保这个体制的运转,国家人为地实施了一系列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市民农民分离的城乡隔离政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户籍制度上,以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把全体公民划分为标志鲜明的两个类别,农民不能进城定居生活和寻找职业。在教育制度上,城市中小学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则以摊派的方式由农民掏腰包解决,1985年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拨款,改由农民在集体提留中提取。义务教育由政府的主要责任转变为农民的主要义务。在就业制度上,国家只负担城市市民的就业和培训,农民则自谋生路,市民失业有救济,农民失业无人问。尤其突出的是,农民不仅不能到国有集体企业就业,更不能到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招干招工的首要条件就是你必须具备非农业户口。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成百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养老、医疗、救济、补助等),而农民的生老病死就只能靠自己,不仅如此,农民还要为政府分担补助救济农村五保户和军烈属。对农民来说,不存在什么童工、退休的问题,从小就得干活,一直劳累到年老死去,大多数农民有了病无钱治疗,就靠“忍过去”。除此之外,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在财政补贴上,在兵役制度上等各个方面都明显存在着城乡有别的“双重标准”。时至今日,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动摇和破除。这种人为的城乡隔离政策是建国以来中国农民的又一项最沉重的制度性负担,这种实行“双重标准”的城乡分治政策,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制度根源。
人为因素之三:现行税费缺陷。现行税费制度是一种合法但不合理的制度。农民现行的法定税费负担主要包括农业税(含地方附加、农业特产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提留统筹费、义务工和积累工、教育集资以及国家规定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定购任务等项。且不说基层政府和部门打着合法税费之名违背法律法规任意重重加码、搭车收费、提高基数、重复变相征收等种种混乱行为,单就上述合法税费本身来说,就存在严重的不合理因素。首先,从农业税来看,现行农业税制主要沿袭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1988年新开征农业特产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划分为地方税;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业税逐步由实物形式改为货币形式。传统的观点认为我国农业税率不高,但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农业税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也高于发达国家农业所实际负担的税率。不过,综观世界各国税制,基本上不单独设立面向农业和农民的税种,我国单独设立面向农业和农民的农业税的做法有损税收的统一、公平和中性原则。比照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达到纳税的起点标准。就法理来说,如果土地长期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国家没有面向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那么政府也就没有直接向农民的农业收益收取税费的理由。据统计,“九五”期间,农民年均缴纳农业税254亿元,农业特产税从1996年79.6亿元上升至1999年的88.9亿元,年均增长3.8%。其次,从“三提五统”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乡镇政府的建立,与人民公社体制相对应的“三提五统”制度却仍然保留下来,并沿袭至今。法规规定“三提五统”属于集体资金,应归集体使用,其实则为“二税”性质,成为乡镇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三提五统”实际上是对农民超经济强制,变相地平调了农民的财产,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所有权。在“三提五统”的实际征收过程中,不少乡镇政府擅自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基数,使法定的“不超过5%”的杠杠形同虚设。据统计,从1993年到1998年,全国“三提五统”费由380亿元增至729.7亿元,年均增长13.9%,人均由44.6元增至84元,年增13.8%。再次,从农民“两工”和教育集资来看,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实质上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下对农民劳动的强制性无偿的计划调配和使用,已经与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现在农村剩余劳力庞大,在组织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应引入市场机制,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使用农民劳力,农民“两工”已经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少乡镇政府借“两工”合法之名,行摊派之实。全国可统计的农民“两工”已从1994年的16.4个上升到1999年的18个,不少地方强行搞“以资代劳”,1999年全国农民承担“以资代劳”资金64亿元,人均6.9元,劳均13.6个。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可在农村农民却被迫“越俎代庖”代替政府掏钱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法》规定的教育集资就成为基层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合法借口。特别是配合教育“双基达标”而进行的教育集资活动,在很多地方不仅把它当作经常性的集资项目,而且数额特别巨大。湖南省湘潭县近几年为完成教育“双基”达标验收,共投入1.75亿元,基本上是向农民收取的,1995——1997年连续三年每年向农民集资5000万元,1998年又集资2600万元。全国各地大都差不多。
人为因素之四:基层政权膨胀。农村基层政权恶性膨胀主要体现在机构膨胀、人员膨胀、权力膨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为了克服人民公社政社不分的严重弊端,国家从1983年起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到1985年全国“撤社建乡”完成,中国建立起了史无前例的庞大的乡镇基层政权管理体制,十多年来,其机构和人员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过去人民公社时期,公社仅有八大员,成立乡镇政府后,却增至十几大员、几十大员,甚至上百大员。多轮县乡机构改革也都未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机构越精越大,人员越减越多。目前,全国共有4.8万个乡镇政府、80万个村委会和520万个村民小组,全国县及县级以下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不包括教师)高达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供养一个县及县级以下干部。另据统计,全国乡镇总供养人员为1285万人,除去已离退休的280万,在职的还有1005万人,其中党政机关人员140万人,平均每个乡镇31人,而每个乡镇实际供养人员已高达235人。
人为因素之五:政绩至上理念。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全力为民众提供公共物品,造福人民。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成为无所不管、无所不能的万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职能未能及时转变,相反,基层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纷纷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逐利主体。各级各部门的内部权力运作已蜕变成“政绩至上”的行政理念,而这种“政绩”又主要体现在一大堆上级下达的和各级加码的数字指标上,所以笔者称之为“数字型政绩至上”。这种“数字型政绩”就是把各级各部门的“政绩”简单浓缩成一大串“数字指标”,完成或超额完成“数字指标”,就表明“政绩突出”,这是各级干部升迁的主要依据,否则就是“无能”,升迁无望。在这种“数字型政绩至上主义”的行政理念驱使下,各级各部门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和表现自己的“才华”,就必然全力以赴提前或超额完成“数字指标”任务,这就使得政府行政的最大目的已经不再是提供公共物品,而是不择手段地完成“数字指标”任务。为此,虚报瞒报数字者有之,贷款交税者有之,强行收税费置民于死地者有之,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正是这种“数字型政绩至上主义”的必然结果。对基层干部来说,既然完成上级“数字指标”任务可博取“政绩”,而完成自己加码的“数字任务”又可获取私利,那么在没有外部有效约束的情况下,疯狂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横冲直撞,置民于无法招架的地步。在这种泛滥的权力面前,农民不断付出眼泪、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来“配合”完成“数字指标”任务。由于公、检、法部门在催交农民税费时常常是“一锅煮”,受到侵害的农民只能集体上访。在这样一种行政理念下,一切妨碍基层政府实现“数字政绩至上”的行为都会遭到无情地打击、摧残和限制,“官逼民死”和“农民逃亡”的现象怵目惊心。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涉农恶性案件的通报,1995年全国共查处13起恶性案件,被乡村干部逼死打死的农民12人;1996年涉农恶性案件上升到26起,乡村干部逼死打死的农民26人(其中还有一名11岁的小学生),近几年来,涉农恶性案件还在不断发生。著名经济学家盛洪称这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