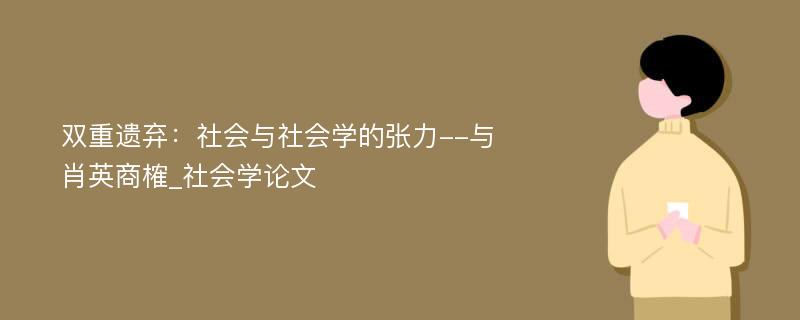
双重抛弃: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兼与肖瑛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社会论文,肖瑛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和没有社会学的社会:逻辑还是事实。社会在哪里?是谁的社会?社会给了我们什么?在漂浮社会中这些问题是漂浮的,但是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可能会引起把社会作为对象的社会学的扎根。实际上,“社会在哪里”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传统中国,就是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常常提出的(牟发松,2006)。社会在哪里是值得研究的社会无根的问题,但是,如果继续追问谁的社会在哪里就更为复杂了,当然也更为直接了:这个问题直指社会根在何处?社会学的命运完全等同于社会的虚化命运,甚至比社会的命运更差。因为社会学首先被社会抛弃了,所以无社会的社会学也就造就了无社会学的社会。
一、回归社会的社会学想象
谁的社会学,社会的社会学,还是穷人的社会学。如果是社会的社会学,那么社会是谁?无论是行动还是关系,无论是规则还是结构,无论是知识还是理性,社会最终还是要被还原为谁的问题,可能才有本体论的意义。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就是被社会抛弃的社会学,抛弃时间久了,即便有根也就腐烂了。
(一)没有社会的社会学:社会何在
没有社会的社会学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内嵌或者说社会学知识的内置(郭强,2008a)。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社会学的无根化看作纯粹是被社会抛弃的结果是冤枉了社会这个东西。没有社会的社会学的知识内嵌关键在于社会学把社会抛弃了,这是双重抛弃的一个典型特征。在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社会是一个无法指涉的概念。
肖瑛(2006)认为,“社会”虽然是一个出现较晚的概念,但又是一个最为“社会化”的概念,一个人人都在使用但很少有人能确切地说清楚其边界和具体构成的概念,一个既可以无所不包又可以空空如也的概念,用图海纳(Touraine,2003)的话说,一个“含义不明的实体”(illdefined entity)。在学科分类上,当社会学说自己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时,实际上就等于把自己当成了总体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问题是:如果我们要对社会加以解释,必然要对社会加以界定或者在知识上加以规定。
1.什么是社会的
对社会学来说,界定社会是社会学生死攸关的事情。肖瑛(同上)说:显然,“社会”仍然是一个关键概念,“倘若现在应该有一门社会学作为特殊的科学,那么,社会的概念本身,除了对那些现象的外在的概括之外,就必须对社会的、历史的事实进行一种新的抽象化和归纳整理(齐美尔,2002:60)。”涂尔干(迪尔凯姆,1995:25)指出:有一类非常特殊的性质的事实,……只能用“社会的”一词来修饰它,即可名之为社会事实。这样称呼它最为合适,因为十分清楚,它既然没有个人作为基础,那么只能以社会为基础。M·韦伯(1999:35)则刚好相反,一如他对“行动”的定义——我们要谈到的“行动”是在行动着的个体把主观意义附着在他的行为之中这一意义上来讲的——那样,只有在行动的主观意义能够说明其他人的行为并因而指向其原因的意义上,行动才是“社会的”。齐美尔的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以后所有社会学家的共识:N·卢曼(Luhmann,1999)断言,虽然“‘社会’是一个用旧了的概念,但要另找一个概念来指称(社会学的)指定对象并足以精确表达(社会学的)诸理论性目的,看起来还是会无功而返。”图海纳(Touraine,2003)则说,如果不参照诸如“社会”或“社会性”(the social)这些含义不明的实体,要界定社会学几乎就不可能。也就是说离开了社会或者社会性,那么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就失去基础。
“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着确定边界的实体,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社会性”只是作为这个物质实在的一个层面而存在(Wernick,2000)。“社会的”和“社会性”构成了社会学想象的基本内容,社会学家们赋予它们的各种想象,实质上要么是对“社会”的本体论预设的结果,要么必然对“社会”的本体论预设产生影响。因此,只有在明确界定“社会的”和“社会性”的基本内涵之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和性质才能够显现,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彰显。所以,肖瑛(2006)认为,对于社会学来说,“社会的”和“社会性”能更好、更直接地表达“社会”所内含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社会学的大师们正是在使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界定了社会学的方法论特质和视角。事实上,在近20年的学术思潮中,无论是社会学的自我批判还是社会史研究的文化学转向,焦点都集中在“社会性”和“社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波德里亚提到了“没有社会性的社会”(society without the social)(转引自Smart,1999);图海纳(Touraine,2003)竭力论证“社会性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social)和“‘社会的’概念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social’)。社会学无论是在其最初的目的上,还是在逻辑起点上——“社会的”和“社会性”,就一直关怀着整个社会的整合和团结,或者说,社会学对“社会的”和“社会性”的内涵在哲学层面上作出的不断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反思为社会学提供了终极关怀的基点,使社会学没有向完全工具主义的陷阱滑落,使社会学研究的所有出发点都是对自身所处社会甚至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
2.“社会的”之基本内涵
根据肖瑛的归纳:“社会的”的几种基本内涵包括:第一,集体性和群体性,即相对于个人而言集体和群体的优先性,或者比较中性地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社会与个人的不同(威廉斯,[1976]2005:451);第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威廉斯说,在17世纪时“社会的”就有了“关联的”(associated)、“交际的”(sociable)等指涉(同上:450)。第三,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乃是意味着利他主义,所以N·卢曼才说“社会的”太美好,威廉斯(同上:451)才说“social被用来强调正面的而非中性的意涵”。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个问题是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或者是社会学扎根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是谁的社会以及社会在哪里?尽管有市民社会的说法,似乎要把市民作为社会的主体,但是市民社会却把社会中的最穷的人群即无产阶级排除出了社会,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制造了严重的阶级对立,“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马克思、恩格斯,1995a:90),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这种异化劳动的结果是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的分离和异化,人性被扭曲,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恰恰是“通过非社会的(unsocial)、个别的利益来建立社会”,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其实质是反社会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single individual)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 of social relations)”(同上:56)。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的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马克思,[1844]2000:82)。
(二)回到社会的社会学:想象性希望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不仅是社会学家的呼唤同时也是社会本身的呼唤。在无法解决这样的根性问题的时候,肖瑛也就提出了“回到‘社会的’社会学”的主张。
1.回到社会的社会学主张
在如何回到社会的社会学方面,这个主张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其一,张扬社会学的想像力①。当然这种想像力具有特别的含义,肖瑛(2006)说,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社会”不仅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和“社会性”——被视为社会学自我认识和建构的认识论,被视为社会学认识社会的方法论,从而实现了研究对象与认识论、方法论在社会学中的统一。其原因在于“社会学的想像力”张扬的“社会性地解释社会现象”的理念就为社会学提供了依据,有效地回答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强调了构成社会的各种原则和行动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发生的。在肖瑛看来,通过这样理解社会学的想像力,就会回到有社会的社会学了。因为,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以下的弊端将得到消除:一是被当作“背景”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刚性的有机体,缺乏适当的弹性,从而否弃了“个体”在“社会”面前的能动作用,“个体”成了社会运动的消极的盲从者,一个呆子,“主体”因此而隐匿了;二是“主体”的消失必然造成社会学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的无视,社会学可能因此而重新回到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性层面上去;三是多样性的社会存在样态(societies)被遮蔽了,整个人类生活空间变成了普遍主义意义上的单一“社会”(society),并因此而清除了“相对性”、“具体性”等概念在社会学话语中的位置。为革除以上弊端,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的”和“社会性”所蕴涵的其他含义来更全面地理解“社会学的想像力”,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学视角或者说社会学的方法论体系。
其二,建立社会学抑或社会的结构二重性。在肖瑛看来,“社会的”基本内涵就是互动性。社会学的百年历程就是它在处理行动与结构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变得更为辩证的过程。而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正好说明了这个过程,同时,“结构二重性”对于我们拓展社会学的想像力,凸显社会生产机制的复杂性是不可或缺的。“结构二重性”的提出使社会学认识论成功地摒弃了传统的二元论观点,而把行动与结构、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地方性行动与超情境后果、静力学与动力学(Giddens,1993:133)等二元对立范畴统合到互动网络中,开辟了社会学认识论的“第三条道路”。
其三,回到地方性、历史性和相对性。肖瑛认为只有给社会学注入的历史性、社会性、地方性和相对性,回归到社会的社会学才是可能的。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其四,回到“日常生活”。回到世俗性和日常生活,“走向生活、走向实践”(李培林,2000)是以“社会性”为核心的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学自身历史发展的要求,回到日常生活是一个极具战斗力的口号。当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1995a:56)和“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同上:1)。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预示了社会学不是社会的,至少不是完全社会的或者不是社会性的。其原因,在肖瑛看来,它是由社会学对社会的或者社会性的看法或者规定所导致的,这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说明。笔者认为,最为关键或者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学自身,社会学自身的反身性(reflexivity)要求的知识内嵌。也就是说,社会学不是社会的社会学或者说社会学抛弃社会是社会学自身的性质所规定的,只要社会学存在一天,这种无社会的社会学就存在一天。因为社会学对社会的规定是主观的想像力。社会学抛弃社会的知识内嵌作为社会事实本身也是社会学的对象,非社会的社会学也就当然地成为社会事实的组成部分。社会学对社会的主观性既是社会学知识的一个非特有属性,同时也是社会抛弃社会学成为无社会学的社会的原因。尽管这种说明需要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解释越多,社会学离社会越远,这是社会学知识的内嵌逻辑。
2.想象还是希望抑或想象性希望
回归到社会的社会学,只能是一个对社会学知识充满期待的美好愿望。社会学是离社会最近的社会科学学科,如果能够实现这个回归社会的社会学的美好愿望也只能是离社会再近些,而不能进入社会。如果完全进入社会,那么社会学就等同社会一般。回归到含有社会的社会学或者充满社会性的社会学是有可能的,因而也是可以期待的。
如何回归到含有社会的或者含有社会性的社会学当然是具有社会学方法论的意义和社会学知识增生的价值。问题是肖瑛(2006)给出的途径是支路而非主干道。
其一,无论社会学想像力中对社会的或社会性的预设多么具有社会性,都无法把社会嵌入到社会学的知识结构中。社会学知识正是在想象中塌陷,社会离开社会学也是想像力作祟的某种意外结果。笔者没有任何否定或者去社会学想像力的任何想像力,相反,如果在含有社会的或者社会性的社会学中社会学想像力异常关键,这也正是社会学想像力在社会上得到喧嚣的原因,但同时需要提醒的是,不能因为这种喧嚣而隐藏或者掩盖了社会学想像力在社会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距离关系上的张力,以及社会离社会学越来越远的事实。如果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缩短社会学对社会的距离感,那么社会学的想像力则是建构靠近社会的社会学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准则。在知识的搀扶下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或者简洁的想象无疑美妙的畅快。但是一旦这种想像力所激发的想象成为漫无边际的臆想,则毁坏了社会学的想像力,并败坏了社会学,只能靠社会学吃饭的那些社会学家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学远离社会而去。于是社会学就彻底成为无社会的社会学,于是社会学也就彻底地拔了根,毁了基,从而半死不活地漂浮着。所以,只要社会学还是处在没有社会的社会学之尴尬的处境中时,社会学想像力只能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张力,一种离开性,一种黏合的腐败剂和拆开方。这里的意义就是社会学的想像力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性就是一种强制性,它强制所谓的社会学家不要滥用社会学想像力。
其二,结构二重性不仅无法使社会学回归到有社会的或者社会性的社会学,而且还会最终导致社会学含泪离开社会,社会含恨离开社会学。“结构二重性”,即结构既是社会行动者的行动结果,又是其中介(郭强,2007)。换言之,行动与结构之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循环的与相互建构的关系,“行动者在互动系统的再生产中利用结构化模态,并借助同样的模态反复构成着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吉登斯,1998a:93)。这种循环性是社会得以构成和变化的根本机制,是社会生活基本的、构成性的特点(Giddens,1979:69)。“结构二重性”是人的理性化能力在社会的构成和变革中得以体现的作用机制,是行动的反身性监控过程的前提(吉登斯,1998:91)。那么作为结构二重性的发明人,吉登斯本人如何看待这个理论呢?吉登斯称结构化理论“不靠谱”。吉登斯说,过了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的第一阶段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参见张璐诗,2007)。依笔者之见,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只能是社会学离社会更近一些的思路,而非一条通途。
其三,回到地方性、历史性和相对性,也是社会学知识结构的一种客观化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能否直接实现回归有社会的社会学则是值得讨论的(郭强,2000)。回到历史,向过去学习是社会学知识逻辑的来源之一,历史学是离社会学最近的学科之一,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联姻,会荡起很多新知识的涟漪(郭强,2005)。但是回到历史,只能拓展社会学的想象空间,靠近历史无法等同于靠近社会。回到地方也可能是一条林中路,因为只有在地方性的基础上社会学知识的根基才可能打牢,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学才能找到扎根的土壤,或者在时空延伸的框架下才能保持本土或地方性社会学知识的扩展性和对地方社会的浸入性。同时也要考虑另一个方面,在拟像社会中或者在景观社会中,抑或在网络社会中,地方的虚化使我们无以找到地方,这个时候又何尝能够回到地方呢?所以,肖瑛所谓的回到地方应该看作一条林中路,尽管林中美景处处,莺歌燕舞,但是搞不好就迷了路。
其四,回到日常生活也是一个好主意,回到日常生活,就是要摒弃那种“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马克思、恩格斯,1957:118-119)的宏大叙事,而是从芸芸众生的现实的、具体的、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社会构成的因素。但是回到日常生活往往只不过是一个极具战斗力的口号,因为社会学要生活,不可能只在日常生活中玩耍,社会学生活的准则是靠近精英生活的空间,因此社会学有时候就会变成精英统治的工具甚至帮凶。特别是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中,不成熟的社会学也只好冒充成熟地浸入所谓的宏观社会决策的行动框架中,畅论回到日常生活的理想以便让社会学能够生活下去。然而,因为无法回到日常生活,所以,回归到有社会的社会学也就只能存在于漫长的期待中。
3.主道还是辅路抑或为岔路
当行动者被忽视,当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普通行动者被忽视,倡导回归者的眼前只能是迷雾茫茫,也就无法看到回归有社会的社会学的主干道了。
其一,剧作者和剧中人是行动者吗?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写道: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但是,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1957:146-147)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就是要根据一个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构成这个背景的物质生产关系以及在这个关系上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人际关系、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结构性关系来考察该思想的产生、内容、表现形式以及性质”(肖瑛,2006)。一个理论的社会嵌入规定了理论内含的行动者地位,但是在宏大叙事中行动者的具体性就被淹没了。同样在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也被排除出了社会,这时的社会和这时的社会学也就把穷人抛弃了,成为所谓无人的,而实质上乃是富人的社会和社会学。“马克思认为,国家只能反映市民社会某一阶级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必然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把一个资产阶级经济与一个真正的社会国家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斯特龙伯格,2005:289)。
其二,社会是无人的社会,也就是无根的社会。前一个说法是假的,后一个说法是真的。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无论人是什么或者说人是谁;但是在社会学中有时候社会根本就是无人的,在社会学眼中只有社会结构、社会体系、社会行动以及社会关系等所谓的社会,而人却被抛弃了或者被屏蔽了。这是无根的社会学。但是无根的社会学是同无根的社会关联在一起的。当社会只有社会结构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某种类型人的结构和进化或者抛弃了一些人的结构。这时的社会肯定是无根的。无人的社会和社会学还表现为不知人是谁的,也就是说抽象的人事实上抛弃了人的社会和人的社会学。“人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也是变化的产物;在人的身上,从来就没有预先给定或确定的东西。历史既没有来由,也没有终点。人身上的所有事物,都是人类在漫长时间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如果真理是人类的真理,那么它也是人类的产物。”(肖瑛,2006)马克思则看清了这种社会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对社会的“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1995a:73)。这种动态的视角决定了马克思视野中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全面完成之前必定是一个地方性的、历史性的概念。马克思还说,“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1957:103),真正的社会建构和变革起源并内在于构成这个社会的“现实的人”(同上:50)的感性的日常活动之中,不存在超历史的历史创造者。以(英美而非法国)结构理论为例,它既无法叙述能动的主体(因为人只能是结构的生物性傀儡)也无法关照现实的历史(在结构主义理论中只能有进化,而没有历史,而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活生生的人并不能成为它用来建构知识的对象)。这里仅仅是想说明:没有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行动者乃至穷人,社会是无根的,社会学也同样是无根的,这时的社会学和社会就处在一种越来越远的状态,而不是回归到所谓的社会的社会学。社会学知识逻辑抛弃了社会学赖以生存的根基,于是,社会学不仅发挥不了其对社会应有的功用,甚至无法解释自身被社会抛弃的命运(郭强,2006)。
二、被社会抛弃的社会学
尽管吉登斯在知识上为社会学做出了许多说服力有限的辩护,但是社会学依然逐渐被社会所抛弃。1994年6月,美国社会学期刊《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专门以社会学危机问题为主题在社会学家中展开讨论。主编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写了一篇名为“社会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的文章,指出社会学令人担忧的现状,即无论从制度(institutional)方面还是从智识(intellectual)方面看,社会学都没有作出我们所期望的那种进步(Cole,1994)。前者包括社会学系和研究机构资金的缺乏,有些面临关闭的威胁;社会学家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望的下降;社会学在学术领域中被其他学科轻视或排挤;社会学研究生的教学和分配成问题,等等。后者包括社会学中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理论的缺乏;学科中认知远未达到统一或者说统一范式的缺乏;未能取得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进步;未能有效地解释或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等等(参见吴小英,1999)。十余年前所讨论的社会学危机问题到现在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峻②。这种严峻性主要表现为不仅社会学自身内在地抛弃社会,而且更为突出的表现是社会学逐渐被社会所抛弃。吉登斯说,“社会学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一门有争议的学科”。社会学被社会抛弃的原因,在社会学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学是社会麻烦制造者
布迪厄宣布社会学是一个战场,一个“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Bourdieu,1993:8)。P·柏格(Berger,1963:42)一再强调社会学思想就是尼采所说的“不信任的艺术”的一部分,社会学意识中“内在地蕴藏着一种揭穿真相的动机”,Z·鲍曼(2002)断言社会学思维是“一种抗固化的力量”。P·柏格说,社会学中的揭穿真相的动机的各种根源,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或者指涉架构(frame of reference)意义上的(Berger,1963:51)。应该说,社会学是一个复合体,不仅是麻烦制造者,而且还是抗固化的知识力量,同时还揭露社会事实的真相。
(二)高度抽象的脱离日常生活世界
布迪厄说,“我相信,只要社会学还是那么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它就无所作为。不过一旦它放下架子,深入现实生活的细枝末节,人们就可以拿它作为一种工具,就像上诊所求医问药那样来为自己服务。社会学给予我们的真正自由在于给予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去知晓我们参与其间的游戏,让我们在置身某个场域的时候尽可能地少受这个场域的各种力量的操纵,同样也少受从我们的内部发挥作用的、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布迪厄、华康德,1998:260)。归结起来,可能最为关键的并非它有没有给富人或者代表者办成事,而是它不给穷人办事。社会抛弃社会学从而使社会学成为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在社会方面主要表现为社会的危机,社会不需要社会学为其制度论证或者不需要无根的社会学为其提供知识依据,于是悬置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学理论知识的悬置(冯钢,2008),成为不成熟的社会放弃社会学的突出征兆。
(三)拯救社会学努力的失效
社会转型把社会学转掉了,或者更为直接地说,社会抛弃了社会学。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出这种被抛弃的命运和回归社会的社会学努力。M·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宣称社会学赖以发展的现代知识构型“现在将要倒塌了”(Foucault,1973:347-348)。图海纳认为“现存社会学的社会生活观”已经深陷危机之中(Touraine,1984)。吉登斯强调社会学的出路在于摆脱“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社会思想残余”(Giddens,1987)。布迪厄则提出用“反身性”(reflexivity)取代传统社会学的“客观社会”原则(布迪厄、华康德,1995)。Z·鲍曼提出了对后现代性情境进行回应的社会学构想③。波德里亚(Baudrillard,1997)关于“社会性的终结”的论说直接质疑了社会学研究的所有命题,并威胁到社会学元话语的合法性,即社会性本身的存在成为问题。被社会抛弃的命运是注定的,拯救这种命运的努力似乎又是低效的(郭强,2008a)。社会与社会学的分裂不是愈合了反而严重了。
这样的分析似乎会出现如下那种现象:没有社会的社会学依然存在,尽管危机丛生;没有社会学的社会照常运行,不管是良性还是逆行。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就表明了社会趋向解体的事实特征和社会学失根的(空)漂浮状态;如果把这种现象转为一种行动模式,那么这是典型的拔根行动。社会与社会学之间的距离远近是衡量社会是否解体和社会学是否有根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把社会与社会学之间的一种天然的关联人为地割断,以社会学为代表的知识结构的危机将成为社会危机的依据和表征。就中国社会学而言,似乎这种状态更加突出。“毕竟当今中国是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堆积如山。政府需要社会学给出解决方案,学界也不愿意持久地陷入所谓‘理论纠緾’之中。于是,大量的学者抛弃了社会理论研究,走向所谓的‘实证研究’。调查报告、经验描述、数据统计甚至直截了当地‘讲故事’,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在每年中国社会学会年会所收到的几百篇会议论文中,有关社会理论研究的论文不足百分之一。每年各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关社会理论的选题那就更是少而又少。一些学者甚至提倡‘没有任何理论预设的社会调查和经验记述’,他们认为与其要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without society)(Wolfe,1989),还不如直接面向一个‘没有社会学的社会’。事实上,社会理论在中国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社会理论的危机在中国的特殊反映。”(冯钢,2008)
三、布迪厄为何放弃社会
布迪厄无疑是当代影响最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不仅因为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概念框架和理论原则,还在于其独特而敏锐的“社会学眼光”,这种眼光有助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崭新的视角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地洞察,尤其是将隐而未现的棘手问题“连根拔起”(王建民,2006)。问题是:布迪厄是何以拔根的?这种拔根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扎根吗?用“场域”代替“社会”,从而放弃使用“社会”④概念,可能是布迪厄为拯救社会学抑或社会而挺身而出的扎根行动。
(一)空泛的社会祸害了社会学
布迪厄戳穿了社会空泛的本质,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布迪厄、华康德,1998:134)。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布迪厄不仅以场域概念置换社会的概念,而且以惯习、位置、资本、策略等概念相对应使用之,使传统社会学中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紧张对立趋向于调和。
(二)场域就是一个社会吗
“场域的观念提醒我们,只要一涉及方法,第一条必须考虑的就是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想方设法抗拒我们骨子里那种用实体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世界的基本倾向。”(布迪厄、华康德,1998:347)从场域的角度进行分析涉及三个必不可少的内在关联的环节(同上:143)。首先,必须分析与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其中,权力场域相对于其他场域如经济场域、文学场域、科学场域等更具有“元场域”的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其他场域。其次,必须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为在这个场域中,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再次,必须分析行动者的惯习,亦即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142)。社会是流动的,意味着不仅行动是流动的,结构也是流动的。如果将社会比作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行动和结构都是流动不息的河水,很难截然地分割开来,一如个人与社会也无法分割一样。
(三)场域终结社会吗
王建民说:布迪厄摒弃社会概念而代之以场域概念,实际并不是完全抛弃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而只是抛弃“空泛的社会”,或者说是以新的视角审视社会,对社会予以重新解读。在这个意义上,场域概念并非完全替代社会概念,而是通过改变社会概念中空泛的内涵,注之以历史的、整体的、流动的意蕴。场域概念终结了以碎片化、僵化、逻辑化等为表征的“大社会”,而非社会概念内涵的全部(王建民,2006)。社会依然存在,只不过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被转换了形式,社会不是实体化的、也不是意识化的,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个人的,毋宁说“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即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也在行动者之内”(布迪厄,华康德,1998:172)。场域相对于空泛的社会,在于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的“流动的社会”。社会世界的真实性在符号暴力的支配下被遮蔽起来,因此社会行动者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个未知的世界往往由统治者、知识分子、或者是教育体制、大众传媒为了追逐权力而加以扭曲。因而社会学的任务是“促使更多的人拿起反抗符号支配的武器”,还原社会世界的真相。还原社会世界的真相的前提是实践,其方式是反思。从实践出发可以克服各学科对社会生活碎片化理解的弊病,并综合建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视角,建构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而反思性的关键之处在于建构一种社会学的社会学,对学术场域以及社会学家自身进行反思,将社会学研究过程本身对象化——即参与性对象化,进而对社会现实加以“彻底地质疑”⑤。
(四)社会学的社会学
放弃社会的概念是为了更好地纳入社会的概念。这就需要对社会学进行彻底的反思。于是才有了社会学的社会学⑥ 而非社会的社会学。“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布迪厄、华康德,1998:39)。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文军,2003)。布迪厄对社会学的反思不仅是要消灭顽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社会科学的迷失自我式的混乱,以及这种思维和混乱所依托的知识形态。布迪厄深知之所以“二元对立”思维千百次地被消解而又能够死灰复燃,关键在于其社会支撑和再生产机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所以只有进行釜底抽薪式的,从根本上消除“二元对立思维”和“混乱”的再生产机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尽管布迪厄为社会学和社会学家反思自身、解放自身(获得自主性)⑦ 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进路,但是布迪厄倡导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并没有给出消除符号暴力和社会科学混乱的“明确的解决方案”。同时布迪厄的“社会学的社会学”是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和理性的政治前景的“双重忧虑”,布迪厄指出,“社会科学面临的特殊困惑在于自主性愈益增大并不同时意味着政治中立性也随之增大。社会学越是科学,它就越是与政治相关,即使它只是一种抵御性工具,亦即充当一种屏障,抵御着那些时刻阻止我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行动者的各种形式的神秘化和符号支配。”(布迪厄、华康德,1998:54)所以,拯救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应当靠反思社会学或者社会学反思也就是说靠社会学的社会学而非社会的社会学,因为后者是无法拯救社会学的。
四、社会性的终结
波德里亚对社会学丧失了信心。由于社会性的终结,波德里亚要人们放弃社会学,这是否就是社会学被社会抛弃的另类解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社会性终结尽管并非波德里亚首先提出,但是他通过对社会性终结的说明进而说明了社会学所存在的危机。
(一)社会性是一个善意的幻想
波德里亚(1990:76)从总体上否定社会性的存在,认为,所谓“社会性”不过是欧洲殖民活动的衍生品,是由欧洲生产并延伸出去的一个幻想物。“在社会学中,预设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社会及‘社会性’,由此可以进行量化研究、统计分析,也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Baudrillard,1993:81)。“事物并非社会性地发挥功能,而是象征性地、魔力般地及非理性地发挥功能”(Baudrillard,1983:3)。
(二)社会性存在的几种可能
第一,社会性作为拟像的实体而存在,也可以解释为社会性是一种拟像的实体。在波德里亚看来,“社会性”从来没有存在过,存在的只是社会性或者社会关系的“拟像”(simulacrum)。如果社会性仅仅是“拟像”的实体化,那么所有基于“社会性”的研究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游戏,不过是假借对于“社会性”的阐述来求得自身的合法性;所谓社会性的“危机”不过是将精神病人、妇女、不良少年等边缘人群视为社会学知识生产的原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拯救社会学或摆脱社会学被社会抛弃的悲惨命运呢?波德里亚提出了一个药方,即“解拟像”。通过无情的“解拟像”,即拒绝把社会性视作符号指示,拒绝这种游戏,终结任何假借社会性而存续的权力效应。因此,所有社会性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也就终结了;“社会性的危机”也因此而消逝(莫少群,2003)。
第二,社会性作为一种更精致的死亡方式的确是存在过,也可以解释为社会性是一种精致的死亡方式。社会性通过征服将它的真实性强加于各处,遍布于所有的事物之上;社会性通过制造社会性残余来摧毁社会性自身并摧毁社会本身⑧。为此,这就是社会性的一种更精致的死亡方式。社会性扩张的过程就是“摧毁性过度顺从⑨”的过程,这个成功的过程使得自身走向消亡;借助于社会性而生存的社会学也将走向终结。波德里亚指出:社会性死亡的假设也就是假设社会学本身的死亡。这就是波德里亚得出的忘掉社会学的结论⑩。
第三,社会性作为历史而存在,也是说过去存在过但是现在消失了。波德里亚指出,一旦真实与拟像不再区分,社会性就将死亡。超真实的出现和存在是社会性终结的基本方式,超真实作为拟像组成的现实,将社会性放大、取代,被到处复制、张扬、炫耀、消费,从而彻底终结了社会性。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死亡才能逃脱代码,唯有死亡才是一种真正的无视拟像和代码的象征行为。
(三)社会性的终结链接到社会与社会学的双重遗弃
“波德里亚的假设直指一个主题,曾经作为一个再现、比较、评价体系的‘社会性’成为了一组想象,曾经被物化为普遍实在和一切论据基础的‘社会性’业已被自己的拟像宣告作废。”(莫少群,2003)其一是,“失序”导致社会性和社会学的终结。“失序”是有序的结果也是秩序追求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在波德里亚看来,“失序”现象表明,现代西方社会的转型中孽生的后现代性的非社会性特性,正是这种传媒拟像所制造的“大众拟像”使社会处在既新又旧、既是又否、既实又虚、既序又乱的淆间(11),从而摧毁了一切关于“社会性”的神话,并使得社会学成为多余。其二是,波德里亚认为,正是大众和传媒的“单一化过程”或者炮制的“共同信息”导致了“社会性的终结”,随之也威胁到社会学的存在。因此,他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说明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否定一个不言而喻的或者永恒的“社会性”的存在,相反,社会性可能“仅仅短暂地存在于象征构型与我们的‘社会’之间的狭缝里”,在由传媒和大众组成的力场中,社会性解体了,相应地,社会学也随之解体(同上)。其三是,社会性是链接社会和社会学的中介。当中介断开了的时候,社会本身成为仅仅具有使用价值的工具,不再有任何象征性意义能够规范社会性的“正当使用”。例如,在医疗保障制度中,无法控制的腐化、过度消费、福利欺诈等等比比皆是,从大众到医疗专业,到官僚机构,直到整个制度都将走向瓦解(朱元鸿,1999)。当然社会学也只能随着社会的解体而瓦解或踏上穷途末路。
(四)社会学死亡般地存在着
波德里亚特别指出,社会学家是无法理解他的“社会性的终结”说的,因为社会学自身的存在就紧紧附着于对社会性的实证,“社会学只能描述社会性的扩张及其变化。它的生存仅仅依赖于积极的和确定的社会性的假设……社会性死亡的假设也就是假设社会学本身的死亡”(Baudrillard,1983:96)。尽管这个观点相当偏激,但是偏激往往说明了特定时代的特殊存在形态,其积极的功能有时就暗含在其消极的陈述之中。在某种意义上,第一,社会性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不如社会感更适合社会学的社会实际,因此就像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一样,它不仅有自毁而且还有他毁的内在逻辑,正是由于社会性本来应该有机地链接社会与社会学,但是事实上这种内在的逻辑却割断了这种脐带般的联系,于是社会与社会学都处在无根的状态(12),也就是说社会和社会学都还活的,但是问题就是像死了一般地活着,这就是笔者得出的结论。那么,到底谁抑或哪里出了问题呢?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和没有社会学的社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如果我们追问:到底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学出了问题。相互抛弃的原因恐怕主要在社会学,但是也同社会的堕落有关(13)。总之,没有了社会,社会学也就是失去了根,社会学应该是社会的社会学而社会也应该是有社会学的社会。在相互抛弃的机制下,社会没有了社会学的知识似乎也是不完善的社会,同样社会学离开了社会也就失去了根。华勒斯坦(华勒斯坦等,1997:100)指出,“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意味着更有效的知识也将通过社会而成为可能”。要找到社会,必须首先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找到普通社会行动者,只有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才是构成社会的根性要素,而只有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通行动者的行动结构中才能使社会学具有真实的和真正的社会性,这样的社会学才是具有社会的社会学;而这时的社会学也才能为社会奠基,社会才能有根,从而社会也就成为了有社会学的社会。从这段话中是否可以看出社会与社会学的希望:笔者想知道的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时代的“社会性的终结点”上,当我们已无法设定人们所处身的公众话语的某种公共场域之时,社会学将会是何种形态?社会交往崩溃而进入到通讯之中——社会性的终结——导致了网络的虚拟交流的产生。这就需要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科学用新的方式来阐述这一“日常生活”的现象,既要描述它的结构与文化,又要指向更远,通过社会的复兴而趋于日常生活的变革。在一个更完善的社会中,我们不再在日常生活与更大的、被遮蔽的社会结构之间做出判然区分,因为这些更为庞大的社会结构将不再以陌生而遥远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本身就包含着超越的可能性——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性的自由”。
本文的关键结论是:在学术上找出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机制和表现形式是为了社会学扎根在社会的沃土中,也使社会在社会学知识的浇灌下成长。但是目前社会学与社会的互相抛弃表征着社会化的无根化状态和社会的失根性特征。形成社会与社会学的互赖机制是社会和社会学扎根的基本形式(郭强,2008b)。没有社会学知识搀扶的社会是孱弱的抑或是堕落的,无根的社会学知识是漂浮的、无以至用的。
注释:
① 肖瑛(2006)认为,社会学想像力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几个关于社会的或者社会性的预设:第一,“社会”是一个其各组成部分普遍联系的整体,一个高度结构性的和集体主义的存在。古典社会学家们都“着重于‘集体主义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起源于卢梭和德国唯心主义,而后者为他们批判功利主义提供了主要的衡量标准。”(帕森斯、米尔斯等,1986:88)任何社会现象都只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其发生和变迁都受到“社会”的制约,体现了“社会”的意志。第二,“社会”虽然表现为一个物质性存在,但构成它的不仅是物质生产关系,而且指涉各种精神的和意识的关联,不过后者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被客观化,具有了“客观物质”的基本特点,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但“社会”又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有机体,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不过,即使其变化也是自主的,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借用A·孔德的话说,“社会秩序从来不会有别的什么直接的基础”(阿隆,1988:143)。第四,在个人生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方面,后者构成前者的环境,不仅发动而且制约和引导着前者,前者无以超越后者的阈限。“我们提惯习,就是认为所有个人,乃至私人,主观性,也是社会的、集体的。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人类的思维是受社会限制的,是由社会加以组织、加以构建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愿不愿意,个人总是陷入‘他头脑的局限’之中,也就是说陷入他从他所受的教化里获得的范畴体系的局限中,除非他意识到这一点。”(布迪厄、华康德,1998:170-171)基于关于“社会”及其与各组成部分的关系的上述想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坚持如下原则:第五,“社会现象的原因内在于社会本身”(Durkheim,1982:141)。
② 社会理论在中国面临的危机,突出表现为理论“悬置”。社会学在恢复之初就有意识地“悬置”这种教条化的社会理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社会学的这种“恢复”事实上意味着它与社会理论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与社会理论背后的社会哲学传统的决裂。尽管当时最早的一批从事社会学恢复工作的学者,大多是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转行”过来的,但正是由于这种“转行”带有明确的“脱离理论”的意向——如同经济学的转向本身就意味着与“劳动价值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脱钩一样——因此,社会学的“去理论化”特征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基础。问题就在于一般社会学理论传统似乎具有天然的自我“悬置”的能力,从而使它与经验现实的距离日益扩大(冯钢,2008)。
③ Z·鲍曼指出,伴随着现代性自身受到的质疑和后现代性情境的出现,社会学需要重新确立其存在的正当性。对他而言,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经由不断修正的现代性处方来解决。因此,应该创造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来应对新的社会情境。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Z·鲍曼提出了对后现代性情境进行回应的社会学构想(郑莉,2006)。
④ 实际上王建民在讨论布迪厄的社会概念时已经对社会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诠释,这是否有悖于布迪厄的原初思想,是需要读者加以甄别的。王这样解释:社会学从古典到当代的发展,始终面对“社会是什么?”这个久弥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影响人们如何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处理人际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关涉到“社会学是什么?”,即社会学何以可能或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的社会观都是一种“大社会”范式。“大社会”在本质上体现了西方社会学传统中的理性主义社会观,这里用“大社会”是与布迪厄的“社会小世界”概念相对应而使用之。具体说来,这种“大社会”范式,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么个人是被动的,受制于集体性与普遍性的逻辑。而社会至高无上(如迪尔凯姆);要么虽然承认个人主观性与能动性,但这种主观性与能动性却受类型学划分的制约,个人社会生活的历史性被静止的模式所淹没(如M·韦伯)。社会行动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动态的或者历史的,而大社会范式却简化和凝固了社会生活。这里的“大社会”并非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通常所讲的“大政府,小社会”、“小政府,大社会”意义上的含义,而是指相对于个人社会的优先性、相对于偶然事件的社会规律性、相对于自主能动性的社会强制性,以及相对个体特殊性的社会普遍性;或者是在一定理论原则制约下的社会、为研究者的一己之念所限定的社会。这两重含义与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总体性与流动性相对立。因此,它不包含政治权力或权利的分配与均衡的含义,也不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意涵(王建民,2006)。
⑤ 王建民认为,以场域替代“大社会”的做法虽然无法彻底地将后者“终结”,但场域的意义不在于将“大社会”终结这一结果,而在于启示我们尝试观察与诠释社会世界新的角度、新的方法,而不在于提供现成的、一致的答案(王建民,2006)。
⑥ 古德纳(A.Gouldner)在其《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其基本假设就是:理论是由人们的实践以总体性方式所创造的,并为他们检验的生活所塑造。因此,他所说的反思社会学是以社会学家对自身及其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的知识为基础,要求一种自觉的自我指涉,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者。并认为反思社会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深化社会学家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与给定的社会中他是谁和是什么的自我意识,以及深化他的社会角色和他的个人实践如何影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的工作的思索(文军,2003)。
⑦ “科学的德行就是旨在解放,而这一德性无疑是所有符号权力中最不具有非法意味的”,社会学家“倘若不坚信这一点,他就不可能相信社会学可以为普遍推行某种独立领域制度的自由提供可能性和必然性”(Bourdieu,1990:56)。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也能够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文化使命,他坚信光明的理性的政治前景——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布迪厄为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勾画布迪厄这一“理想图景”也正是后继者努力的方向(王庆明,2008)。
⑧ 人们长久以来总是把社会性想象为人类的客观进步,没有成为社会性的都只是有待社会化的残余。这就意味着,社会性胜利征服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制造不能被社会化的残骸的过程;社会性在真实界中“殖民”的范围越广,程度越深,它所摧毁的象征界的残骸也就越积越多(莫少群,2003);波德里亚说“社会性确实是作为对残余物的理性控制和残余物的理性生产而存在的。”
⑨ 波德里亚指出: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当中,社会性总是借着对“残余”的“合理性”控制和“合理性”生产而扩展。从16世纪成立的流浪者、精神病的收容院,到19世纪的国家救济,20世纪的社会保障等都以社会的名义将每个个体纳入更完全的“社会化”。社会性推进的每一步都曾受到不同群体的抗拒,但是这些抗拒并不能扭转社会性的胜利推进,其结果也就演变成顺从于社会性的法则:一切深陷于“恐怖主义官僚机构死的、制度化的关系、死的语言文法之中”。波德里亚将这种状况称为“摧毁性过度顺从”。
⑩ 既然社会学伴随者社会性的终结从而所引导的社会的消失而死亡,那么也就需要忘却社会学这样一个东西了。
(11) “淆间”是笔者提出的一个表达社会状况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乱世。这里的淆乱不只是事实上的而更是指涉知识上或者思想上的淆乱,比如符号取代并超越了现实,使得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消失。大众因此丧失了一切依据理性而进行的判断,处在一种不辨是非、不知真假的认识逻辑的混乱之中,最后干脆拒绝了由这些符号构成的社会规范,导致社会性的消失,及整个社会的终结。
(12) 即便是追求那种诱人的客观性也无法挽救社会性。吉登斯说:那种希望出现一位社会科学的牛顿的渴望仍然非常普遍,尽管在今天,怀疑这种可能性的人比依然抱此希望的人可能要多得多。但是,那些仍然在等待“牛顿”的人不仅是在等待一列永远不会到达的火车,而且他们根本就站错了火车站(吉登斯,2002:72)。
(13) 但就二元对立来说,“经验性”和“整体性”的承诺是社会学的“立命之本”和“安身之道”,不能放弃。社会学的理论原则使社会学刚出世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一选择也注定社会学的“命运多舛”,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后继的社会学学人为了改变此种命运,摆脱此种困境而不断努力。可以看出“客观性陷阱”是可以且可能超越的,但为什么长期以来社会学家都纷纷陷入此种陷阱呢?但为什么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对社会学影响如此至深,甚至到今天余威依存呢?布迪厄指出: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二元对立已经被千百次的消解过,但却又不断的“死而复生”,而那些使他们起死回生的人们将从中得到好处。由此可见此种二元对立表面上是科学对立,但实际上却根源于社会对立。所以要摧毁这些对立就要付出巨大代价,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布迪厄、华康德,2004:235-239)。
标签:社会学论文; 吉登斯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历史社会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历史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