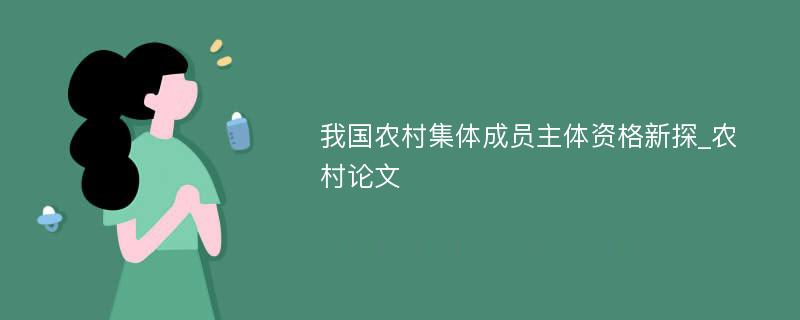
中国农村集体成员主体资格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中国论文,主体资格论文,成员论文,农村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6年5月4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6)06-0126-10 DOI:10.16494/j.cnki.1002-3933.2016.06.011 城镇化进程中,昔日“不利益”的农村集体成员身份受到追捧。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多半不愿放弃农民身份,甚至有人想方设法要变回农民。未分配到集体土地补偿费的人,时常会将农村集体组织告上法庭。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遭遇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缺乏统一标准的难题。城镇化中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急需法学关注和法理阐释。 如何认定集体成员主体资格,学说素有“户籍说”、“生活来源说”、“权利义务说”和“系统分析说”等诸多争议[1]。学界通常认为户籍说具有合理性[2]。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颁布的司法认定标准往往以户籍为主,并根据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的标准①。然而,户籍制度改革后,农民进城落户依然可保留农村集体成员身份②。农村集体成员可依法享有城市居民户籍,这样一来,户籍就丧失了区分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作用。农村集体成员主体资格认定问题似乎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集体成员资格认定困难与集体所有权法律构造及其理论基础有关。集体所有权性质上的认识混乱和集体组织法律主体地位不明,使得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设计的社会价值和应有的保护功能难以完全彰显[3]。由于集体所有权法理支撑不足,进而影响到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反过来,由于集体成员主体资格认定困难,进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集体所有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面对争议和质疑,我国物权法选择的不是废止集体所有权,而是完善集体所有权,即通过赋予“集体成员权”的方式完善集体所有权。集体成员权不仅要解决集体主体虚位问题,也要解决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初始分配问题。解决宅基地过度扩张和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必须以成员权为逻辑起点[4]。可见,集体成员权立法旨在有针对性地处理当前农村集体资产流失、承包权主体不明、宅基地过度扩张等现实问题。集体成员权能不能成为一项行之有效的物权法制度,首先取决于集体成员主体资格界定的法律逻辑,因为“立法不合逻辑”往往会成为废除立法的口实。 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至今难以达成共识,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法学思维总是将农村集体成员限定在自然人范畴内。从自然人角度解读中国农村集体成员主体资格,不是一个合适的出发点。 一、农民个人作为农村集体成员依据不足 首先,农民个人作为农村集体成员主体,不符合集体成员权立法本意。《物权法》规定集体成员权,旨在克服实践中少数村干部擅自决定集体重大财产事务、损害村民利益的弊端,以实现集体财产集体所有、集体事务集体管理、集体利益集体分享的目标[3]。集体成员权是决定集体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假如集体成员是自然人,那么每个农民都应享有这种决策权。但事实上,并非每个农民都享有这种权利。从《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集体重大事务决定的程序规定来看,参加集体重大事项决策会议的人,是村民会议的成员或者村民代表。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由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也就是说,18周岁以下的村民不是村民会议的成员,不享有集体成员权。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1条规定:“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村民代表既不是村集体自然人的代表,也不是村民的代表,而是农户的代表。这说明,村民代表参加村民会议的主体身份是农户而不是个体农民。如果集体成员权利主体是自然人,按照各地政府规章和法院解释中规定的那样,自然人出生后即成为集体成员的话,这些新生儿如何行使集体重大事项决策权?理论上只能通过代理方式进行,这样会出现多重代理现象。个体农民的权利由农户户主或代表人代理行使,农户户主或代表人的权利由农户家庭代理行使,农户家庭的权利由村民代表行使。同时,会出现村民代表投票权大小不同的情形。这显然与一个村民代表只有一票的现实不符。即使立法允许各村民代表投票权各不相同,这种多重代理也会把集体“成员制度”异化为“代表制度”。一个成员,由层层“代表人”去代表,其成员权利必然被削弱,甚至被架空。《物权法》的集体成员制度旨在把过去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代表制度”转变为反映多数人意愿的“成员制度”。把集体成员限定为自然人,无法实现集体成员权的立法目的。 其次,农民个人作为农村集体成员主体,无视农村集体成员产生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我国集体土地形成于集体化运动。通常认为,农民在集体化运动早期,即加入合作社时,入股的土地是农民“个人”的土地。其实不然。虽然土地改革按照农业人口数平均分配土地,但农民分到的土地均以户为单位颁发土地产权证,并未给每个分到土地的农民个人颁发独立的土地产权证。1950年颁发的“土地执照”,按户登记。从“1950年东北沈阳市土地执照”和“1950年东北旅顺市土地执照”两份土地执照中,可以发现,土地执照中土地产权人包含“户主姓名、全家人口、住址、共有人姓名”等内容,共有人姓名一栏记载的是农户一家人的姓名[5]。这表明,农民分到的土地是以户为单位登记的,换言之,农户家庭是土地所有权人。“1953年湖北宜昌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内容有些变化,将土地产权与房屋产权写在一张证书上,取消了“共有人姓名”一栏,但农户全家人的姓名还是全部加以记载,并明确是“本户全家(本人)”所有的土地[6]。这依然延续了以户为单位登记土地产权的做法。既然土改后的土地以户为单位登记颁发土地权证,到集体化运动时,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农户内部进行土地所有权分割,然后农民以个人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集体化运动中,入股合作社的土地是农户家庭的土地。 第三,农民个人作为农村集体成员主体,在立法逻辑上讲不通。农户家庭的新生儿可以享受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农户家庭在申请分配承包地和宅基地时,有权将新生儿算作一个农业人口,这是我国农村集体通行的做法。然而,以该新生儿是“集体成员”作为其享有集体利益的理由,站不住脚。因为自然人一出生就成为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合逻辑。自然人一出生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基于国家的主权关系,一出生就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是基于血缘关系,一出生就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没有依据。集体不可能也不会基于地域关系,认定每个在当地出生的人都是本集体的成员,也无法按照某种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规定新生儿的团体身份。农村新生儿享受农村集体利益的事实,只能寻求其他的合理解释。此外,一个农家女嫁给另一个村子的农民后,不管她有没有迁移户口,只要她在该集体生产、生活,一般即可享受该集体的利益。集体分配土地补偿费时,只要该女子在土地补偿方案确定之前嫁入的,一般能分到一份。她之所以能分配到集体利益是因为她属于“集体成员”,此种说法不能自圆其说。出嫁,只能成为某个家庭的新成员,即使她与这个家庭的成员一起生产、生活,也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她就是这个家庭所处的“集体”的成员,就像农家女嫁给城市企业的股东或职工,与他一起生产、生活,却不能当然成为该企业的股东或员工一样。如果出嫁女一旦选择成为男方的家庭成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男方所在集体或组织的成员的话,则属于“捆绑式”的身份赋予。法律不允许,集体或组织也未必会答应。看来,集体分配给嫁入女集体利益的理由,只能从“她是集体成员”这个说法之外去寻找了。还有,农家子弟在大学求学期间,一般可分到集体福利,毕业后则分不到了。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在校学生仍然依靠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依然是集体成员,而毕业生或者攻读研究生的可能有其他生活保障。这个理由同样存在解释上的困难。一个农家子弟如果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只要他不主动退出该集体、不被开除,不因法定事由消灭成员身份,原则上不可能因为到外地求学、工作、生活而发生成员身份变动。农村集体成员身份不仅仅是一份耕作身份、社保身份,更重要的是集体土地“主人”的身份。这种“主人”身份岂能因成员自身努力向上获取新的工作、新的保障而消灭呢?唯一的解释是,享有“主人”身份的集体成员主体地位,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单个的农民个人来享有的。 二、农户作为农村集体成员是立法惯例和社会习俗 农户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主体,在中国现行立法中相沿成习。《民法通则》、《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分配均以农户为权利主体。《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的“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学界通常解释为“一户一宅”。宅基地使用权主体是农户,没什么争议。倒是《民法通则》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主体是自然人。农户并非自然人以外的独立主体资格者,而是自然人的特殊法律属性的表现形式[7]。不承认农户的独立主体地位,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名为农户、实为自然人,因为农户不过是自然人的特殊法律属性而已。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承包经营户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是农户。徐国栋认为,农户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家庭合伙,是以家庭成员为合伙人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在中国固有法中,“家”是重要的法律单位,家长对家庭成员享有广泛的权利甚至权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往往是通过“家”的中介达于个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通则》把“户”作为法律主体的一种,受到了中国固有法的影响[8]。此外,“家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家庭和家庭成员无论在财产享有、意志形成和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9]笔者赞同此见解。农户是中国固有法上独立的法律主体,不能因为某些国家现行民法没有规定农户这种主体,就认定农户只是自然人的一种法律属性。农户作为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是我国立法的客观事实。 法理上,农户能不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我国,农户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既是我国农村以家庭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现实的写照,也是更好地保护缺乏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利益的需要。农户家庭作为交易主体、责任主体和信用主体是我国农村社会的习惯。我国立法把农户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没什么不妥。但有学者认为,把承包经营户作为承包经营权主体,理论上有互相矛盾之处,也不符合现实情况,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个人[10]。该主张不能成立。他所说的矛盾,主要是指《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有承包地分到个人的规定,但从这些规定中解释出“个人是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条的立法宗旨是维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妇女享有土地承包权益,不等于她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按农户家庭成员人数分配承包地”与“农户家庭作为承包经营权主体”之间并不冲突。前者是分配正义的体现,旨在保护每一个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后者是一种经济、有效、符合中国农业生产习惯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旨在确保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和稳定发展。二者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此外,以农户家庭为承包主体,可避免因农户家庭人数变动而导致的不必要的承包地调整。在承包期内,农户家庭人数有增有减,基本可以实现承包地“户均”占有数量的动态平衡。正因为农户家庭是承包地的主体,才可能在实践采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方案。倘若承包地主体是农村集体的农民个人,那么增人就要增地、减人就应减地。如此一来,承包地将因农民的出生和死亡而不断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包期内婚姻关系解除,夫妻都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司法解释,同样不能依此得出个人是承包经营权主体的结论。离婚时分割家庭财产,包含对家庭承包地的分割,但家庭承包地可以分割不等于家庭承包地“变性”为个人承包地,分割后的承包地依然是家庭承包地,哪怕该家庭只有一人。家庭承包主体是农户家庭,农户家庭人口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农户家庭只有一人不会导致家庭承包经营权变成个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承包地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以及实践中存在一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事实,不足以说明“个人是承包经营权主体”。 同时,农户家庭被视为集体成员是农村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习俗。这种习俗,从司法判例中村集体的辩词中可略见一斑。司法实践中,各方都围绕具体的自然人来判定谁是集体成员,但村集体总是下意识地用到“农户家庭成员”这个标准,并以此对抗户口标准。村集体将“农户家庭成员、农户家庭、村集体成员”三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农户家庭是集体成员,农户家庭成员自动享有集体成员利益。特别是在对待离婚妇女及其抚养的子女问题上,是否为男方家庭的成员成为村集体分配集体利益的重要依据。他们论证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因结婚成为某集体的农户家庭成员的,可享受集体利益;因离婚不再属于该集体农户家庭成员的,不能享有集体成员利益。离婚后母亲一方带走的小孩,如果依然随父姓、认父认祖的,依然被当成男方家庭成员的,也能继续享受集体利益;如果随母亲一方生活,并改变姓氏、断绝往来的,不再属于男方家庭成员的,不能分享集体利益。村集体的推论反映了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意识。“(2010)张武民一初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宝峰路居委会一组的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原告邓飞山不属于宝峰路居委会一组组织成员。1995年6月,原告邓飞山的母亲吴次浓与本组成员邓学刚解除婚姻关系,吴次浓就不属本组成员邓学刚家庭的成员。本组认为因婚姻关系成为本组任何家庭的成员,都是本组集体成员之一,本组无条件接受,除此以外未经本组在成员接受证上签字、盖章是不可能成为本组成员的。原告邓飞山随母生活,在校读书时改名为吴飞山,既不认父又不认祖父,连亲祖父邓昌进去世后都不去看一眼,断绝了祖辈关系及父子关系,不属于本组邓学刚的家庭成员。 该案中,居委会认为女方离婚后不再属于男方家庭的成员,女方带走的小孩,改姓后同时断绝了与父亲一方家庭最基本的家庭联系,也不再属于父亲一方家庭成员。这是民间一种朴素的、通常的认识。一个生活在农村的自然人能不能享有农村集体的福利,关键看他是否是某一农户家庭的成员,如果不是,将被排除在享受集体利益的主体之外。 再来看“(2011)洛民终字第2169号判决书”中村集体的辩词: 上诉人偃师市城关镇塔庄村第六村民组认为:一审仅凭户籍就认定被上诉人系塔庄村第六村民组成员,具有村民成员资格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周鲜红原籍是塔庄村第二村民组,后嫁到城关镇杏园村。几年后,周鲜红离婚,带着她女儿周姗姗(即本案另一被上诉人)又回到塔庄村第二村民组她娘家。2001年,她又和我组李某结婚,被上诉人二人户口又转到我组,2007年,周鲜红又和李某离婚,就又带着她女儿离开我组回到塔庄村第二村民组她娘家居住至今,也就是说周鲜红和其女儿周姗姗从2007年离开我组,一直就没有在我组生活、耕种。上诉人认为村民成员资格是一个特殊的法律概念,认定村民成员资格也有其特定的程序,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情况来考察才能够认定,我村村委会对此资格认定在村规民约中已有规定。一审法院仅凭户籍这一项就认定被上诉人具有村民成员资格,显然是越权行为和错误行为。 该案村委会认为户籍不是认定集体资格的唯一依据,要尊重“村规民约”,而是否在村集体耕种和生活,是村规民约认定集体成员的主要依据。村集体的村规民约得不到法院支持,或许是因为没讲清楚其中的道理:结婚后,成为男方的家庭成员,自然可享受集体成员福利;离婚后,不再是男方的家庭成员,不在本集体生产、生活,回到娘家生活,即恢复了娘家的家庭成员身份,不应再享受本集体成员利益,而应享受其娘家所在集体的利益。离婚后,户口没有迁出的,不能仅以户口作为判定其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应当根据其归属于哪个农户家庭来判断。如果离婚女子无所归,那么,应当认定其依然属于户口所在地的集体;如果该女子有所归,即有娘家能回,那么应当回归其娘家所在的集体。由于村集体在认定集体成员资格取得和消灭时,没有引入农户家庭、农户家庭成员这些重要因素,没有论证农户家庭成员、农户家庭与集体成员三者之间的联系,无法准确说明有关集体成员资格“村规民约”的正当性,只能用“不在集体生活、耕种”为由否定其集体成员资格,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虽然村集体在判断集体成员时,没有利用“农户家庭成员”这个关键概念,但从他们的相关描述中,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对于农户家庭成员、农户家庭与集体成员之间紧密联系的思想认识。法院不支持村规民约规定的集体成员认定标准,但这并不代表村规民约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它欠缺的只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已。 三、农村集体成员人格体与受益体的区分 不得不承认,中国集体成员立法存在特殊性。一方面,农民个人在各方面享受着农村集体的利益,另一方面,农户在法律地位上扮演着农村集体成员的重要角色。按照西方民法理论,似乎难以合理解释这种“权利主体与利益归属不一致”的立法现象。因而,学界一般认为,为维护法律体系的逻辑完整性,“土地承包经营户”、“农户”、甚至“农村集体”这些西方民法传统中并不存在的概念应当从中国立法中剔除出去。但这不过是削足适履的主张,笔者不敢苟同。基于中国农村集体、农户家庭和农户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基于中国农村立法事实,从中发现集体成员立法的理论依据,比简单地否定“农户”、“农村集体”等概念,似乎更有实际意义。 中国农村集体成员主体存在“人格体”与“受益体”的区分,即农户是农村集体成员的人格体,农户家庭成员是农村集体成员的受益体。 “人格体”一词借用了冯军对“Person”一词的译文,学界一般将其翻译为“人格”、“法律人格”或“人格人”[11]。德文“Person”源于拉丁文的Persona,该词原本是指用于演戏的面具,后延伸为演员在戏剧中扮演的角色。此后被引入到法律中,作为不同等级的人身份区分的法律工具。古罗马法“人格”概念的基本价值在于区分自然人不同的社会地位,是古罗马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工具[12]。《德国民法典》将罗马法上的“人格”面具从罗马市民的脸上剥离下来,转而戴在了“适合成为交易主体”的团体的脸上,使得这种团体具有“法人”身份以区别于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团体。可见,“人格”是“法律上的人”的身份标志,它不是指现实中的人或社会组织,它是为现实中的人或社会组织成为法律主体而打上的法律烙印。“人格体”一词,更有利于承载这种含义。“受益体”一词借用了法人本质学说中的“受益者主体说”,即把“受益者主体”简称为“受益体”。它的含义是指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归属于某个或某些个人时,该个人就是法律权益的“受益体”。 在西方民法理论和立法中,“人格体”与“受益体”是合二为一的。权利主体与利益归属者是同一的,可以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人就是民法上的权利主体。然而,在中国集体成员立法中,成员的“人格体”是农户,而“受益体”是农户家庭成员,即农民个人。农户是集体成员法律人格的载体,享有集体成员权的“法律人”是农户。集体成员权的行使只能以农户名义进行,集体承包地、宅基地的分配均以农户为法律人格体。集体成员的利益分配往往按照农户家庭人口来计算,农户家庭人口越多,该成员享有的承包地面积和宅基地面积就越大,其分配到的集体财产利益就越多。在这个意义上,集体成员的受益体是农户家庭成员。笔者把中国集体成员主体制度立法的理论基础概括为“人格体与受益体的区分”。 人格体与受益体的区分,与传统民法主体理论不同。西方民法理论认为,得享有民法上的规范权利或承受法律关系的资格,为主体资格。主体资格问题,是民法的核心问题,关系到民法规定的利益落实到谁的问题[7]。拉伦茨说,确定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意味着将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权利主体[7]。可见,西方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权利主体与利益归属通常是指向同一权利主体的。而在人格体与受益体区分理论中,权利主体资格与利益归属可以分别属于不同的个人或社会组织。 人格体与受益体合一理论与区分理论并无高下之别,它们只是代表了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的不同立场而已。西方近代民法理论站在自然人为唯一权利主体的个人主义立场上,认定权利主体资格与利益归属于同一权利主体。换句话说,当自然人是唯一权利主体时,主体资格、利益归属与责任承担必然指向同一主体。但在团体作为民事权利主体的情形下,这种主张未必还有充分的解释力。确定团体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后,团体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团体还是团体成员,没有法律逻辑上的必然性。立法只是在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观念之间进行选择或衡平。由于团体在它的组织领域吸收了个人的主体性,因而现代民法通常以部分利益或全部利益归属于个人的做法作为“补偿”。法人制度一般选择部分利益归属于成员,中国农户主体制度选择全部财产利益归属于农户家庭成员。由于家庭成员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契约,而是基于血缘与姻缘,成员与家庭之间的利益分配在亲情引导下容易达成某种默契和相互同意,因而农户家庭行使权利所获利益归属于家庭成员的立法可被各方接受。农户家庭享有权利主体资格,农户家庭成员享受利益的立法,不过是对源远流长的人类家庭生活习惯的认同。人格体与受益体的区分反映了团体主义的一种立法选择。 一个组织体享有名义上的主体资格,而组织体的成员享有实质上的利益,并非不可理喻的法律现象。《德国民法典》确立法人制度时,就有学者发现此现象。德国学者耶林、普兰涅尔等人认为,权利的主体是其利益的归属者,享有法人财产利益的多数个人,是实质上的权利主体。社团法人真正的权利人,是社员,而财团法人真正的权利人,是贫者病者及其他享受财团利益者[13]。法律之所以将这些实质上的主体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是基于实用的考虑,方便多个个人以一个名义上的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发生法律关系。耶林认为法人的真正主体是“受益者”,而非法人本身,这是他权利本质说的必然结论。在权利本质学说中,耶林是“利益说”的代表。他认为权利真正的实质存在于主体的利益上,在利益的实际效用和享受上。正因为权利的本质是法律保护的利益,那么享有这种利益的个人自然就是权利的真正主体。但耶林基于受益体与人格体一致观念,认为法人真正的主体是个人,法人的主体地位是名义上的,这就走向了否认法人主体地位的极端。 在法人学说中,耶林的“受益者主体说”被归入“法人否认说”,不受待见,或许与法人制度的立法目的有关。法人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发挥法人成员对法人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功能。如果否认了法人的独立主体地位,法人成员就不能只对法人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了。在这个意义上,法人独立主体地位不容“虚化”或“名义化”。但是,当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出现在现代民法中时,法人的名义主体与真正主体之间之所以能“合体”,用“受益者主体说”来解释更顺畅。由此可见,在有关团体法律制度中,客观上存在着名义主体与受益主体分离的现象。只不过,发现这一现象的“受益者主体说”,未能提炼出“人格体”与“受益体”区分的理论,而是否定了名义主体的实质上的人格体地位,而以受益体作为实质上的人格体。 集体成员人格体与受益体区分受到“受益者主体说”的启发。但不否认名义主体的实质主体地位,而是承认名义主体就是法律人格体,同时承认受益者是法律主体的“受益体”。人格体与受益体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影子。与外界发生交易关系的是人的影子,享受交易利益的是人。人的影子可能表现为家庭,也可能表现为法人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 人格体与受益体的区分可用于解释中国农村集体与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关系。由于农户家庭成员对农户家庭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无须刻意保持农户家庭与农户家庭成员之间法律地位的相互独立,因而集体利益归属于农户家庭成员的主张,就无须顾忌“成员有限责任”的功能。农户家庭是集体成员名义上的权利主体,即人格体。农户对外作为集体重大事务决定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主体。农户家庭成员是实质上的权利主体,集体重大事务如何决定在农户家庭内部由家庭成员协商。集体承包地分配面积、集体宅基地分配面积、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等财产收益依照家庭成员数量确定。由于农户家庭在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抚养、赡养缺乏劳动能力家庭成员,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并非有名无实,它不是名义上的主体,而是实质意义上的主体。笔者将农户家庭称为集体成员的人格体,农户家庭成员称为集体成员的受益体。其核心是,农户与农民分别是不同的“法律上的人”,只不过在集体成员法律制度中,农户作为集体成员的人格体,农民个人作为集体成员的受益体出现而已。 人格体与受益体区分,是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传统。该传统至少可上溯到我国古代的“计口授田制”。《魏书》卷三《太宗纪》记载北魏政府“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北魏均田令规定,“露田”的授田对象是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女,包括奴隶,甚至还有丁牛,但每户授田的丁牛数量限制在4头,每头牛授予30亩。分配土地按人口和牲口计算,说明土地的法律人格体是农户家庭,受益体是家庭成员。只不过北魏的家庭成员是广义的,还包括“丁牛”。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如《土地改革法》第11条规定:“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这是有关农村土地受益体的规定。后来土地入社,到高级社阶段,取消生产资料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社员分配集体收益一按劳动工分,二按家庭人口。农村集体利益按家庭人口分配、不按入股资产比例分配,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习惯的影响。现行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其法律主体登记为农户,而享受的面积均按人头计算。人格体与受益体区分是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一贯传统。用这种区分传统来解释现行农村集体成员的主体资格,似乎更符合中国民众对土地分配和土地占有的理解习惯。 集体成员人格体与受益体的区分深受中国传统“公私”观念的影响。“公”在中国古代有两层含义,一是《韩非子》的“背私说”,即解开个体自我的围城,与他人一起组建共同体;二是《说文解字》的“平分说”,即共同体中的财货由众人平均分配、共同分享。私为“自环”、“奸邪”之意。中国的“公私”概念将人与财产结合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结合成共同体,共同占有、共同分享共同体财富的为“公”;个人独守自我的围城,谋一己之利、求一己之欲的为“私”。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公私概念的内涵不同。 中国传统的“公”概念是包含了整个共同体成员利益的“大公”,是共同体的“大私”。个体私利、私欲必须在共同体的发展中得到实现。“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念,排斥脱离共同体的个人奋斗。游离于共同体之外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地位、个人意志等个人主义因素在中国难以发育、成长。中国特有的“寓私于公”、“公私一体”的观念与日本式的团体主义有别。在沟口雄三看来,中国的公私观念是一种足可与“commonwealth”相媲美的社会福利主义,而这种“公私合体”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社会主义不谋而合。沟口雄三用中国独特的公私观念解释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14]。 中国特有的“公私观念”必然在共同体与个人关系的法律规范中有所反映。主要表现为“守忠孝,均财货”的制度规范。一方面用“守忠孝”捍卫共同体。三纲中有两纲是家庭内部秩序的法则,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有了家庭内部的“孝”,再辅以“君为臣纲”的“忠”,小共同体不乱,大共同体不倒。唐、明、清等朝,对别籍异财、供养有缺的,或徒或杖,表明王权对家庭这种“小公”集体的极端重视。另一方面用“均财货”维护共同体成员利益。《礼记·礼运》描述了维护共同体成员利益的“大同”理想:所有老人都得以安享天年,壮年人都能贡献才力,儿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能得到丰厚的供养。虽然中国历史上还从未真正实现过这种“大同”现象,但在家庭、家族甚至宗族内,同居共财、相生相养,是客观存在的。时至今日,一些父母拿养老钱为儿女买房的事实也在诉说中国家庭“均财货”的悠久传统。以“守忠孝、均财货”维系的家庭共同体,诠释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公私观念”。这种“公私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行农村法律制度的选择。“人格体为农户,受益体为农户家庭成员”无非是中国传统“公中有私、私中有公,以私养公、以公养私”的公私观念和制度的反映。 解决各种集体成员资格纠纷,只须在“人格体与受益体区分原则”的基础上设立一项规则:集体所在地的农户家庭为集体成员人格体,农户家庭成员为集体成员受益体。集体成员资格认定规则的适用分两步,一是明确谁是该集体组织的农户,二是明确谁是该农户的家庭成员。判断一个家庭是否为该集体所在地的农户,主要依据承包地、宅基地初始分配记录。宅基地上的农房是农户家庭的住所,是农户作为集体人格体的重要标志。判断一个自然人是否为农户家庭成员,依据血缘、姻缘关系。农户家庭成员享有集体财产利益,直至其成为另一家庭成员为止。按照该规则,实践中几类突出的纠纷的处理办法是:外出上学、服兵役、服刑、打工、丧偶等各种情形,只要其未成立新的家庭,依然为集体成员受益体。离婚一方,在农村集体独立门户成为集体农户的,为集体成员人格体;未能成为农村集体所在地的农户或农户家庭成员的,不是该集体成员受益体。农民工家庭进城落户后,只要不放弃集体所在地的宅基地和农房的,即在农村集体保留了家庭住所的,视为集体成员。 ①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的意见》(津高法民一字[2007]3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的会议纪要的通知》(渝高法[2009]160号)。 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规定:“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这说明,即使农民进城落户,取得了城市居民户籍,依然可以保留集体成员身份。 (全文共15,02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