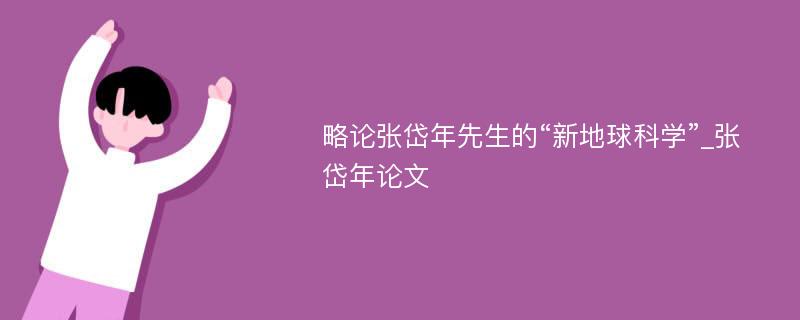
张岱年先生“新气学”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岱论文,新气学论文,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有的学者认为当称之为“新唯物论”。但正如张岱年先生自己所申明的,他“之所以特别喜欢新唯物论,即以其能含括唯物论与唯心论两方面”[1](第一卷P312),“新唯物论”只是他所特别喜欢的学说, 并不是他对自己哲学的称谓。实际上,在张岱年先生的论述里,“新唯物论”乃特指“辩证唯物论”,用它来称谓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是不妥当的。有的学者则认为当称之为“综合创新论”,但严格地讲,“综合创新论”只是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构想与论证,用来作为对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概括,也是不妥当的。那么,对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究竟怎样概括才最为恰当?我认为当根据张岱年先生自己的提法,称之为“新综合哲学”。“新综合哲学”之“新”就新在:在方法上坚持贯彻“分析与综合的统一”[1](第七卷P391); 在内容上则是用“辩证唯物论”来阐释、理解与发展中国传统的“气学”思想。作为谋求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发展的一种理路,张岱年先生对“气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显然有别于牟宗三一派之承继陆王“心学”、冯友兰等人之承继程朱“理学”,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另一发展方向。因此,为了凸显张岱年先生哲学的这一特色,以构成同牟宗三、冯友兰哲学相抗衡局面,我们主张将张岱年先生哲学称为“新气学”。本文的探讨,就是出于这一目的。之所以冠之“散论”,只不过意在申明以下探讨以表达论旨为重,不拘于行文上的形式联系。
一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惟有张岱年先生可谓一生始终信服“气学”思想。而他信服“气学”的自觉性,又决定了他一生始终坚定地宣扬和推崇“气学”。早在1937年,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他对中国哲学的后期发展做了这样的总结:“自宋至明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第一是唯理的潮流。……第二是主观唯心论的潮流。……第三是唯气的潮流亦即唯物的潮流,始于张载,张载卒后其学不传,直到明代的王廷相和清初王夫之才加以发扬,颜元、戴震的思想也是同一方向的发展”[1](第二卷P29)。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这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在后期形成了三个主要流派的最早论述,其意义在于第一次凸现了“气学”的地位,将“气学”确定为与“心学”、“理学”相抗衡的唯物主义流派。十七年后(1954年),他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专刊》上发表《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对船山的唯物论思想的历史地位与意义作出了总结:“它从唯物论的观点,给宋明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其中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哲学的发展,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哲学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恢复并推进了北宋中期的唯物论世界观”[1](第五卷P17)。船山所推进的北宋中期的唯物论,具体的讲,就是指张载的唯物论思想,所以此文发表几个月后他又在《哲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张横渠的哲学》,以与此文相呼应。《张横渠的哲学》虽然对张载哲学思想的主要方面都有所论及,但限于篇幅,难以详细阐述。于是在1956年他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出《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张载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将张载确立为宋代伟大的唯物论哲学家,并强调张载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古典唯物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地位究竟有多重要?岱年先生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张载的唯物论自然观、以其深刻的观察、丰富的内容、精辟的见解体现了巨大的创造力,其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另一方面,“气”的观点自先秦起就一直存在,但缺乏详细的说明,“到张横渠,才建立了关于气的系统的学说”[1](第五卷P23),从而为唯物论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在他以后的唯物论哲学家得以进一步展开“气本论”学说,完备了唯物论的优良传统。“宋代以后哲学关于气的学说都是以张载对于气的解释为根据的”[1](第五卷P78)。
确立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张岱年先生早年宣扬和推崇“气学”最为倾心的事。但自论张载哲学的那部书于1957年出版以后,他逐渐改变了著述倾向,更倾心于梳理“气本论”(中国唯物论)的发展历程。这样的梳理,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阐述张载的思想,但有关的阐述,被他严格作为中国唯物论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来处理。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出版于1957年的《中国唯物主义简史》和发表于1957年至1958年的《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前者是对中国唯物论思想传统的系统扼要的阐述,以揭示中国唯物论思想发展过程与规律;后者则注重阐述中国唯物论思想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
在晚年,张岱年先生基于对中国唯物论思想的系统把握,向中国哲学界提出了构建“新中国的唯物论”[1](第七卷P415) 的基本设想。按照他的设想,“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论”[1](第七卷P466); “中国特色的唯物论”亦即“新中国的唯物论”,它应该是“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古典唯物论的结合”[1](第七卷P466)。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古典唯物论则属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因而构建“新中国的唯物论”又被强调成“应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优秀传统结合”[1](第七卷P451)。 虽然主张通过中国传统“气论”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方式以构建“新中国的唯物论”是张岱年先生在晚年的特别提倡,但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这应该看作他平生致思方向的合乎逻辑的延伸:“我信持唯物论,这是我平生致思的基本方向。”[1](第七卷P405)
张岱年先生一生始终信服“气学”固然体现了一个哲学家坚定自己信念的优良品格,但他之所以能够做到一生都不动摇对“气学”的信服,就认识原因而论,又与他把“气学”思想断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直接的关系。“新综合哲学”所强调的“综合”,是“创造的综合”[1](第一卷P229), 是对所综合的东西加以进一步发展的综合。尽管张先生对“创造的综合”的论述前后期不尽相同,有略有详,有简有繁,但始终贯穿一个不变的取向,即“创造的综合”在内容与结构上必须体现“辩证唯物论”、西方逻辑分析(解析)方法与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之“融合为一”[1](第一卷P249—257)。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他就提出“将唯物、理想与解析综合于一”[1](第一卷P275),这实际上是主张两个方面的综合,“一方面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2](P43)。六十多年后,他仍然这样强调:“我属意中国所需要的新哲学,即以辩证唯物论为根本,兼有现代逻辑解析哲学方法,而又发扬中国固有哲学优良传统的新哲学”[2](P84)。他之服膺辩证唯物论,是因为他认为辩证唯物论是最伟大的哲学,在许多哲学理论问题上,辩证唯物论都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之认同逻辑解析方法, 是因为他认为“逻辑解析对于哲学可以说有根本的重要”[1](第一卷P177),哲学就其性质说,在方法上根本就少不了逻辑解析,“逻辑分析应是哲学的基本方法”[1](第一卷《自序》P3)。那么,他为什么又强调要发扬中国固有哲学优良传统?这是因为他认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创建新哲学更为重要的是综合中国固有的哲学,但这并不是说对中国古代哲学不分良莠的兼容并蓄,而是说要首先区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舍糟粕而不取,只综合其中的精华部分。“区别精华与糟粕才是批判继承的主要方法”[1](第五卷P260)。是精华还是糟粕,在他看来,不应以情感上的好恶为断,而必须以两条客观的标准来判断,“一是看思想观念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二是看思想观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是否有益于社会的发展”[2](P149)。以这个标准来取舍中国先哲的思想,他以为,中国哲学固然一直存在“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三种思想倾向,但宋以后才形成了“心学”、“理学”、“气学”三派。理学(广义)三派中,“心学”否认外界实在,“理学”(狭义)虚构绝对精神,都是唯心主义,惟有“气学”才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1](第六卷P360)。 “气学”既然被断定为唯物主义,那么“新综合哲学”在思想上继承与发展“气学”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新综合哲学”所强调的综合中国固有哲学优良传统具体就是指“气学”,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确:“气本论是唯物论的中国形式,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1](第七卷P394)
二
张岱年先生由信仰“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而走向了对中国固有唯物论之优秀传统的发掘。这一发掘,实际上就是揭示唯物论的中国表现形式,亦即所谓的“中国特色唯物论”。“中国特色”着眼的是类型。就类型上区分,西方的唯物论是以“原子”为根本范畴的理论体系,而中国的哲学家,“自荀子、王充一直到清代的王夫之、戴震,都是以气为根本范畴建立其唯物论体系的”[1](第三卷P51)。“气”既是中国唯物论的根本范畴,那么对“气”之性质的分析与界定,就成为张岱年先生为确立“新气学”所做的最基本的工作。这一工作最早开始于1936年。那年他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在该书第一篇《本根论》中,用两章的篇幅论述“气”,以说明“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根本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物质,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由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之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气之凝结。亦可谓适成一种对照”。[1](第二卷P22—73) 这是将“气”界定为“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最细微”是对“气”之空间结构的最基本的规定,而“最流动”则是对“气”之运动特性(时间性)的最基本的规定。以这两个规定来把握“气”的性质,应该说是张先生一生始终遵循的致思取向,但纵观其有关论述,不难看出他对“气”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的揭示,在不同的时期各有侧重,起先他重在阐述“气”的空间性,后来他对阐述“气”的时间性比较重视。
他对“最细微”作出具体的解释,最早见于1942年春季写成的《事理论》,在该著第二章中,他这样具体分析“气”:“指最微质之每一个而言,谓之最微质;指众多最微质或一切最微质之总和而言,即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气。即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即指无数之单体。所谓气聚为物、物散为气,即是单体结聚为兼体,兼体分解为单体。在先秦及汉宋典籍中,气与质有别。可见而无定形者为气;可见而有固定之形者为质。其实所谓可见而无定形云者,实乃未作精细观察之笼统断语。所谓气者,实乃众多或无数之最微质之集群而言。”[1](第三卷第131页)
这个分析旨在强调气乃“最微质之集群”,不是“最细微”的单体。问题是由无数“最细微”单体结构而成的“气”,其形态并不是固定的,因而不可见。不可见并不等于不存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张先生1955年在《张横渠的哲学》中,将张载所谓“气”断为物质范畴,并据此以认定张载的哲学为唯物论哲学。针对张先生的观点,有学者以张载所谓“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理由,断言张载的气是一种想象,不能视为物质范畴。针对这一反驳,张先生着重强调不能以是否看得见来判断气的性质,“张载所谓气,不一定是看不见的,也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张载强调了无形之气与有形之气的统一。有形之气是看得见的,无形之气是看不见的。他再三说明无形不是什么也没有,只是看不见而已,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1](第五卷P50)。
这一争论显然促进了张先生关于“气”之物质性的思考,使他在翌年写成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的第一章中,第一次对“气”的特性作出了三点规定:“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本来是从气体的现象抽引出来的,然而又把意义扩大了,便成为与今天所谓物质意义大致相同的观念。……中国古代中所谓气,可以说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气是不依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气可以能看得见,但不一定看得见,它的存在决不依靠人们的认识。第二,气是构成一切物体的东西,一切特殊的物体都是气所构成的。山河大地,星云雨露,草木鸟兽,以至人类的身体,都是气所构成的。第三,气是体现运动变化的东西。世界上充满了运动变化,但没有空虚的运动变化,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变化,那个在那里运动变化的东西就是气。这样,古代哲学家所谓气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物质了。”[1](第四卷P9)
较之以前的把握,这三点规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是明确地将气确定为哲学意义上的物质范畴,二是指出“气”是自己在“那里运动变化的东西”。对这两种思想的进一步阐述,见于发表于《哲学研究》1957年第2 期上的《中国古典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该文第一节就是阐述“气”的概念①,先指出“气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然后阐述这一基本概念的演变过程。通过对“气”范畴演变过程的梳理,以揭示“气”的特性:“气是客观的实体”,“指一切客观的无定形的现象”;“气有两种状态,一是不可见的状态,一是可见的状态”。在先秦,“气”主要相对于“体”、“心”、“志”、“形”、“身”② 而言,是指“构成身体的东西”,从汉代开始,“气”被逐渐地解释为“客观的实体”。这一“实体”因其是一切物体的本根,就称为“元气”,实际上“也就是今日所谓物质”;它既“有长宽深”[1](第五卷P78),又“能运动而也有静止”[1](第五卷P133)。能运动就会有变化, 所以他后来在另一文中又补充说“气是有变化的”[1](第五卷P133)。
上面已提及那几篇论文只是指明“气能运动”,“有变化”,并没有论及“气”所以能变化的原因,对这一点的揭示,最早见于《关于张载的思想与著作》。该文是为《张载集》所写的,写成于1977年,文中阐述张载的思想以强调“气”作为变化的实体,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世界的一切,从空虚无物的太虚到有形有状的万物,都是一气的变化,都统一于气。第二,气之中涵有运动变化的本性;而气之所以运动变化,就是由于气本身包含着对立的两方面,这两方面相互作用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源泉。”[1](第五卷P143) 此文的发表,标志着张岱年先生对于“气”之现代诠释已基本定型,这以后的十来年内,他对“气”之诸多诠说都可以说是对这一诠释的进一步丰富。如1982年,在《开展中国哲学固有概念范畴的研究》中,论及“气”范畴时,他先是将“气”这个词分为“常识中的所谓气”、“广泛意义的气”、“作为哲学范畴的气”,然后就“哲学范畴的气”作出具体分析,以说明“气指构成万物的东西”,“是中国哲学中物质概念”,它“与西方哲学中所谓物质虽然相当,却也有重要的区别。中国古代哲学讲气,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肯定气是有连续性的存在,肯定气与虚空的统一,这些都是与西方的物质概念不同的”[1](第四卷P223)。又如,1985年,在《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中,他仍然重复上文论及的“气”之三层涵义,而对哲学范畴的气也只是作了与上文相同的论述:“中国哲学所谓气与西方哲学中所谓物质是相当,却也有差别。西方是以固体物为模式而提出物质概念的,物质的存在形态是原子、粒子。中国古代是以气体物为模式而提出气的概念的,可以理解为波粒的统一的。中国所谓气的概念没有西方传统哲学所谓物质的机械性,却表现为一种含糊性,应该正确理解。”[1](第四卷P466) 再如,1989出版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写成于1987年),除了指出要区别常识的气概念与哲学的气概念之外,更强调对作为哲学范畴的气也要具体分析,“应区别气的本来含义与推广的含义”,不可因气的含糊性而将“气”误解为“能”、“生命力”等。因为“中国哲学强调气的运动性,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可以说气具有‘质’和‘能’统一的内容,既是物质存在,又具有功能的意义,‘质’和‘能’是相即不离的。但是,如果把‘气’理解为‘能’,也就陷入偏失了。气是生命的条件,但无生之物皆是气所构成的。因而,如果把‘气’理解为生命力,那也是不正确的。作为哲学的范畴,气指一切客观的具有运动性的存在”[1](第四卷P491)。
在严格区分了“气”的具体含义的基础上,张岱年先生对其关于“气”的理解做出详细的总结:“总起来说,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气,有几个特点:1)气凝聚而成为有形有质之物,气是构成有形有质之物的原始材料;2)气是有广度深度可言的,即是有广袤的;3)气是与心相对的,是离心而独立存在的实体;4)气是能运动的,气经常在聚散变化过程中。从这些特点看,中国哲学所谓气与西方哲学所谓物质是基本类似的。但中国哲学所谓气又有两个特点:1)气没有不可入性,而贯通于有形有质之物的内外;2)气具有内在的运动性,经常在运动变化之中。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形、质有层次之别。质是有固定形体的。(此质不是今日一般所谓性质之质)西方古代哲学所谓原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来说,应云最微之质。而中国古代哲学则认为万物的本原是非形非质的贯通于一切形质之中的气。这气没有不可入性,而具有内在的运动性。这是中国古代唯物论的一个基本的观点。[1](第四卷P490—491) ”
这个总结,可以说是他对于“气”之特点的最为集中而深刻的解释。这以后,他还多次论及“气”,其论述在内容上不能说比这一总结更丰富、更深刻,但也出现了几个新提法。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新提法是:他根据近代物理学理论,将“气”与“场”相提并论,强调“气”就是“连续性物质”。这个提法的提出最早只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年他发表《中国唯物论史导论》,明确指出:“中国唯物论的主要形式是气化论,气化论的主要观念是‘气’的观念,与西方唯物论的重要观念‘原子’有很大的不同。原子是一个一个相互分别的,具有分离性,而‘气’具有连续性,气与近代物理学所谓‘场’有近似之处。气具有流动性,含有内在的动力,因而西方学者往往将‘气’诠释为生命力。其实,气与生命属于不同的层次。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表示气与生是不同的。西方哲学所谓物质,有科学的物质概念与哲学的物质概念,二者不同;中国哲学所谓气,也可以说有常识的气概念,有哲学的气概念,二者亦不同。从常识的气概念来说,气指云气、水气以及呼吸之气等,与水火有别。从哲学的气概念来说,水火、草木以及各类动物都属于气,气指一切有广袤能运动的存在。”[1](第七卷P367) 后来,他在为《中国古代元气学说》③ 作序时,主要强调这么几点:质(有固定形体)由气构成,而气不一定有‘形’、有‘质’;气相对于‘心’或‘志’而言,是构成物体的材料;气占有空间,有广袤性;气没有不可入性,能运动,经常在运动之中,所以说“气或元气就是连续性物质”。[1](第八卷P29—31)
三
概括起来,张岱年先生关于“气”的阐释可以作如下归纳:气是物质,而且是自身内含动力的运动着的物质。作为客观的实体,气与“心”或“志”相对立,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作为世界的本原(本根),气与“形”、“质”相对言,乃构成一切物体的材料;气虽为构成物体的材料,但它自身具有不可入性;“不可入性”并不是说气静止不变化,而是说它是最细微的物质材料;气之最细微决定了它无形不可见;不可见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体,并不是由于它不具有自己的存在形式;其实,气不但有广袤,是空间形式的存在,而且能运动变化,是时间形式的存在;既然“气”之存在形式体现了时空的统一,那么,一言以蔽之,“气或元气就是连续性物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评论他的这一阐释?我认为它属于“气本论”的现代诠释,意味着传统“气学”的现代超越。何以见得?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古代哲人虽然以“气”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甚至在心中也清楚“气”之存在不是一个观念意义上的想象或预设,而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他们由于时代的局限,却无法予“气”以严格的哲学含义的解释,以至于常常根据经验,以人们常识所了解的“气”来说明他们心中所希望得到了解的那个哲学意义的“气”。对于中国唯物论哲学家来说,这不是个别现象,具有普遍性。因为从张载、王廷相到方以智④、王夫之再到戴震,可以说概不例外,都存在着这一局限性。例如,张载以“犹冰凝释于水”来说明“气之聚散于太虚”⑤。“太虚”在张载那里,是用来称谓气之本然状态,以水之结冰与融化来说明气之聚散,这很容易让人得出“气”之本然就是“水”的错误结论。又如,王廷相为了证明“气”是物质实体,就将“气”说成是可以感知的“实有之物”:“气虽无形可见,却是实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摇而得,非虚寂空冥无所索取者。”⑥ 这个说明,显然是以空气的可感知来证明哲学意义,“气”的客观实在性。再如,当方以智早年坚持唯物论立场时,他为了证明“气”的客观实在性,做了一个实验:用一个两头都有孔的罐子置于水中⑦。封其一孔,则水流进罐中;两孔皆不封,则水不能流进罐中⑧。他的说明方法虽然不同于王廷相,但他同王氏一样,也是以空气来证明“气”之哲学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基于对古代“气本论”哲学这一固有缺陷的把握,我们不难认识张先生对“气”做出现代界定的意义:他明确将“气”确定为哲学意义上的物质范畴。这一确立,不但明确了“气”作为中国古代唯物论最高范畴的意义所在,而且克服了传统“气本论”之经验论局限,使涵义复杂的“气”真正成为严格意义的哲学范畴。“气”只有被确定为严格意义的哲学范畴,传统“气本论”哲学之现代转化和现代发展才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先生关于“气”的现代界定,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传统“气本论”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对中国哲学有所了解的人还清楚,古代“气本论”哲学的另一个固有的缺陷就是为了证明“气”的永恒性而将“气”的运动解释为聚散循环。以聚散循环解释“气”之运动,对中国唯物论哲学家来说,也是普遍的现象。这与其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局限,不如说是他们将常识的“气”概念转化上升为哲学意义上的“气”范畴所必然带来的缺陷,因为物质的永恒性是以时空形式为保证的,只有取得时空形式之连续性的物质才具有永恒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不能揭示“气”的时空形式,仅仅从“气”的聚散循环来说明“气”的永恒性,那么中国“气本论”哲学将始终难以摆脱经验论的束缚,因而也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化与现代发展。就这方面而论,张先生“新气学”的贡献,最为主要的体现不在于将“气一元论”作为中国古代唯物论的重要形式”[1](第三卷P143) 来把握,也不在于对“气一元论”之精神发展历程的全面系统的梳理以及“气一元论”之概念、范畴、命题与论断的具体准确的解释,而在于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精神来发展传统“气一元论”哲学,为传统“气论”哲学的现代转化找到了现代形式,即“气”本体的时空形式以及“气化”运动之辩证方式。由于张先生“新气学”揭示了“气”时空形式以及“气化”运动之辩证方式,克服了传统“气论”哲学固有的局限性,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架构“气”之现代逻辑体系,实现“气本论”的现代转化。
再次,当我们越来越重视探讨中国哲学现代转化这一时代课题时,我们不应该也没理由不重视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古代“气本论”哲学的现代诠释与超越。之所以应高度重视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古代“气本论”哲学的现代诠释与超越,不仅是因为他的上述诠释为我们正确理解“气本论”哲学提供了新范本,更因为通过他对“气本论”哲学的现代诠释,使我们找到了谋求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新路数,即创造性的综合辩证唯物论、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特色的唯物论(气本论)于一体的“新气学”路数。这一路数对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指导意义是重大的。其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足以与现代新儒家所设计的路数形成抗衡,使中国哲学现代化运动不至于一味地走唯心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都清楚,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也就是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因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在本质上无法割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只能是为超越而继承之。在这个问题上,现代新儒家要么强调继续“心学”传统以谋求儒学(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要么强调接续“理学”传统以谋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对“气学”莫不置之于度外。在这种倾向成为支配中国现代哲学创造的主流取向的局面下,张岱年先生不赞成“新心学”、“新理学”的超越路数,一贯坚持与提倡以“新气学”路数谋求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发展,其意义之重大就是不言而喻的。值得一提的是,张岱年先生并不是盲目地提倡“新气学”,他之所以能创立和始终坚持“新气学”,与他一贯提倡的文化“综合创新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基本上不同意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曾明确指出:此法规定不能继承具体的东西而只能继承抽象的东西,是没有将传统文化区分为精华与糟粕,实际上无论是具体的东西还是抽象的东西,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正确的态度只能是继承精华的东西而抛弃糟粕的东西。任何精神价值的确立都免不了诠释学意义上的“视界融合”。由于张先生一贯认为“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1](第八卷P490),所以面对“心学”、“理学”、“气学”三大精神传统,他很自然地选出“气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精华。这一选择,决定了张先生将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气一元论”哲学作为自己哲学史家应尽的职责。张先生不但自觉地以继承和发扬“气学”为己任,而且以唯物辩证法改造“气论”哲学,把传统“气论”哲学提升到现代哲学的高度来理解,为“气论”哲学的现代转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6—05—09
注释:
① 此文未称“气”为范畴,但并不足以说明张先生论述上的矛盾,因为基本概念、或曰根本概念,照张先生的观点讲,就是指范畴.
② “气”与“体”、“心”、“志”对言,见于《孟子》;与“形”对言,见于《庄子》;与“身”对言,见于《管子》.
③ 程宜山著.
④ 方以智哲学性质是复杂的,既表现为早期的“气一元论”、中期的“心物二元论”,又表现为晚期的“太极一元论”,这里仅就其早期思想而论
⑤ 张载:《正蒙·太和》.
⑥ 王廷相:《答何柏斋造化论》.
⑦ 参见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