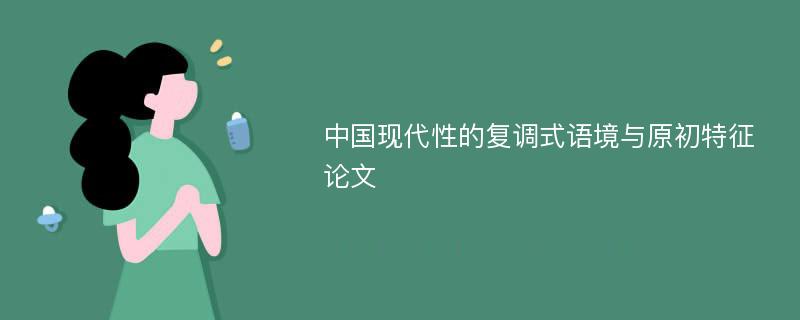
中国现代性的复调式语境与原初特征*
张 明
[摘 要] 关于现代性的求索与建构,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主题。在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侵略的现实境况下,近代中国以非自主性姿态被迫卷入现代性浪潮之中,催生了中国现代性复调式语境——“模拟”与“超越”的双重奏:一方面在救亡图存应激性反应基础上以“模拟”方式追求现代性,另一方面在落后挨打与殖民主义屈辱背景下对西式现代性表示出强烈的警惕、焦虑与批判之姿态。可以说,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力场”,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特征。这组既基于历史遭遇又基于现实考量形成的矛盾心态一直影响着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与建构。但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一矛盾结构的特殊性,也为中国现代性的重构开启了一种另类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 中国现代性 复调式语境 模拟 超越 另类现代性
当前,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讨论非常热烈,以何种资源或范式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构成了讨论争议的焦点。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问题产生的历史语境,通过对中国现代性起源与发展谱系的梳理,才能较为科学合理地回答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问题。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并非是本民族内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自我发展的自主性结晶。中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冲击之下,在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武力侵略压迫下,以主体性缺场的被动姿态卷入现代性浪潮之中的。这一历史境遇直接形塑了中国现代问题的复调式语境。一方面,在救亡图存这一应激性反应基础上形成了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心理依赖与无意识选择,以“模拟”方式追求现代性构成了中国首次遭遇现代性的必然逻辑选择;另一方面,在落后挨打与殖民主义屈辱背景下遭遇现代性的现实境况,又决定了无论是基于民族自尊抑或现实生存诉求,中国都必然会对西式现代性表示出强烈的警惕、焦虑与批判的姿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力图走出西方现代性的窠臼。这种复杂而矛盾的理论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的表述进行相关概括。①对“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应当从如下两个关键词进行界划。第一是“现代性”,也就是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实践的主题都是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所有一切的努力与探索都不外是为了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第二是“反现代性的”,这表明中国现代性的探索并非是为了整体复现西式现代性,而是基于批判、反思西方现代性进行的另类重构。如果简单地运用一组概念来粗略勾勒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生存境况的话,那么,“模拟”与“超越”的双重奏及其所构成的文化心理状态,可以较为清楚地展示这些内容。本文拟从中国现代性问题最初生发的历史语境出发,通过对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生成的复调式语境分析,以期揭示中国现代性问题从其产生之初就具备的鲜明特征——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力场”(Kraftfeld)① “力场”一词最初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者阿多诺,他用这一概念表示在一个“场域”之中存在方向不同的力的共同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力场”中的每一个力都不是可以通约的要素,它们之间相互冲突、交流形成一种“合力效应”,正是这种“合力”打破了总体性的历史逻辑,为历史发展创造了无限的潜能。这正是我们在解读中国近代现代性问题时借用阿多诺这一概念的重要原因所在,因为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困境的现代化张力与现代性张力这两个要素,并非是可以通约的,倘若只有现代化张力的视角,中国现代性与西式现代性之间就不会存在任何形式之差别;倘若缺失现代化张力之视角而仅仅存在现代性焦虑的维度,那么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建构就很容易走向反现代的前现代主义,这当然有悖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趋势。正是中国现代性这一“力场”中存在的二元要素之间相互撞击,才形塑了求索中国现代性方案的特殊性之所在。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另类现代性建构的逻辑生发点。
一、复调式语境I:“落后挨打”现实境遇基础上的“模拟”
学术界一般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展开大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尤其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中国第一次直面西方现代性的物质逻辑——坚船利炮的冲击,也第一次以最直观的形式触摸到西式现代性的一般逻辑。从此以后,近代中国以跌跌撞撞的姿态展开了关于自身现代性的艰难求索过程,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余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与建构史。
第一,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建构了中国现代性的原初语境。毫无疑问,现代性就其一般历史而言,确实是首先生发于西欧社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持了同频率的振动。西方社会现代性的产生更多的是资本逻辑内在生长的逻辑产物,是一种“内生型”现代性。相反,中国近代现代性的产生并非如此,而是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输入的结果,是一种以非自主性被动姿态卷入现代性浪潮之中的客体化过程。“中国的每一次现代性浪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西方做出的反应性行为和规划,国人对于现代性的极度向往始终是遭遇入侵、败北、屈辱和压迫后的结果。”② 谢少波:《另类立场: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赵国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这里也许会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缘何中国社会的传统力量不能继续抵御住西方现代性的输入,而必须被动地产生出中国现代性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此时以殖民主义面貌“出场”的西方现代性,在武力侵略之下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这种现代性的输入已经不仅仅是价值观念或文化理念层面的入侵,也与以往夷狄骚扰、入侵存在着质性区别。因为此时西方现代性的强势输入从根基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统治秩序,直接关涉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西方现代性更多的是资本逻辑自我价值建构与标榜的理论产物,资本逻辑在实现自身无限增殖的过程中,必然会寻求对外的扩张与侵略,亦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与市场建构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成为资本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它(资产阶级——引者注)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In the first experiment,we demonstr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under different angular distributed functions.The parameters of two ID sources areandThe numberof snapshots is set as T=500 an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SNR)is equal to 5 dB.We perform the algorithm in three cases:
第二,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现代性产生与发展的显性主题。资本逻辑是西方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西方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姻,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资本逻辑,另一面是殖民主义逻辑。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塔妮·白露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在19世纪与殖民主义之间实现了“合体”,这就是所谓的“殖民的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④ Tani Barlow(ed),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在殖民主义现代性的背景下,亦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冲击下,近代中国必然会以被动的姿态被抛入西式现代性的浪潮之中,这种现实生存境况从总体上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扩张逻辑所决定的。因此,救亡图存也就自然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核心主题,基于应激性反应而做出的学习西方现代性的选择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服务这一目的的策略性选择。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主要包括启蒙与救亡两条线索。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中国近代的中心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关于改造中国的政治斗争实践,亦即中国救亡图存的问题。梁漱溟先生将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界定为前期模仿西欧近代国家模式与后期追逐苏联共产主义国家模式这两个阶段,并且这两个阶段都是为“模仿的现代性”所主导。② 《梁漱溟全集》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7页。 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产生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存的实践主题,这种对现代性的追求一方面是面对亡国灭种之生存危机所做出的应激性反应,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性的后续求索之路更是一种基于历史发展整体性趋势而做出的判断。
第四,基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模拟”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求索的基本特征。近代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性的进程也经历了系列转折与变化,从最初器物层面的学习到后来制度层面的学习,再到文化层面的激进革命,等等。以封建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面对现代性冲击所做出的“寻求富强”为例,“富强”这一概念的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后发国家对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感性经验判断的政治心理学意蕴。因为中国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以学习西方现代性或者说追求西方现代性方案在中国的实现为目标的。尽管“落后挨打”的观念在逻辑上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与殖民主义色彩,但近代中国却是在社会全面危机与阵痛的现实经历下切实感受到了这一观念在生存意义层面上的合逻辑性,即在全球殖民主义扩张背景下,民族国家必须强大才能免受欺辱与侵略,才能维持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近代中国也正是在不断“挨打”的基础上,才体悟出了必须要学习西方现代性以求得自身的富强。这也清楚解释了缘何西方进化论思想以及后续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在中国以较快速度传播,并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进化论的历史观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被大规模接受,是因为它提供的思想框架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由西方入侵而带来屈辱与震惊的空前经历,以及有助于他们克服因不理解中国危机而产生的极度忧虑。①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同样,后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视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被接受,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延续了进化论的基本理念,为人类社会发展形塑了一条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的道路。由进化论历史观进入到唯物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二者都强调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反对历史发展循环论与退步论。当然,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取代进化论,是因为它能够通过客观存在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来更加具体实在地解释人类历史,较之于进化论的简单理论解释框架更具有说服力。② 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8-11页。
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力场”,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特征。这种既基于历史遭遇又基于现实考量形成的矛盾心态一直影响着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与建构。但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这一矛盾结构的特殊性,也为中国现代性的重构开启了一种另类可能性空间。
第三,无意识认同是后发民族国家求索现代性的一般心理过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总体性趋势。尽管每个国家、民族、地区由于各自所负载的传统、机遇等主客观因素的差异,造成了它们在历史发展坐标上的不同定位,但完成从传统社会形态之中的“脱域”并实现自身现代性的建构,这是其在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必须经历的阶段。只不过后发民族国家所建构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由外力催生的“早熟”现代性。但必须承认的是,无论现代性以何种方式在后发国家呈现(早产的或屈辱的),走向现代性都构成了任何社会都无法超脱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中国步入现代性,一方面是被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扩张“抛入”历史洪流之中的;但另一方面,从更为深层次的理论根基上来说,也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总体趋势判断基础之上的结果。也就是说,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中国必须要完成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有可能产生自身的现代性,但在近代由于殖民主义现代性的扩张,中国提前以被迫的形式去直面现代性。也正是在这种极端危机的情况下,中国仁人志士被迫认识到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要学习西方现代性。这种基于资本主义中心发展目标的建构,从社会心理层面而言,是面对强权欺侮的后发国家的无意识心理投射过程。所谓“无意识心理投射”指的是弱势在面对强势所造成的强大心理压力时,无意识产生的一种心理崇拜。因为强弱势之间存在的巨大力量差距以及弱势时刻面临的被强势吞并、消灭的生存境况,直接给弱势造成了一种心理上无比沉重的紧张感与压力感,时刻提防强势且无意识地按照强势的“镜像”去塑造自我,构成了弱势在心理上的直接反映。这种心理上将自身本质无意识投射到“他者”就是一种拜物教的过程,即一种基于自身弱势情境下的他者崇拜。从人类社会早期在面对自然强大力量时束手无策基础上形成的自然崇拜,到后来将自身的本质投射到上帝的宗教崇拜,都是因为自身力量与他者对比的巨大差异性而造成的“无意识心理投射”。随着实践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能够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也开始逐渐摆脱与自然的神圣联系和消解自然崇拜的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产阶级的崛起,从神圣化导向世俗化的“祛魅”过程也不断增强,对于上帝的宗教崇拜也逐步消却。费尔巴哈在《论基督教的本质》中就曾明确指出,神学的秘密就是人本学,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③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15页。
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在起点上为器物层面所追求的目标,其实也预设了中国现代性路径的内在逻辑转换。因为器物层面革命所带来的一个显著后果便是社会制度上的变革,尤其是在这种器物层面“模仿”遭到失败之后——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现代性的终结,急剧导致了对社会秩序及其意义世界的“重估一切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价值重估固然促进了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辩论合理性,同时也进一步压制了价值的空间,瓦解了意义世界的传统秩序。”③ 高瑞泉:《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传奇》,《学术月刊》2014年第6期。 随着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现代性的最终瓦解,从文化层面批判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构成了学习西式现代性的新路径,这就是以最彻底姿态展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学者指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悖论式”的本质,即一方面对于西方现代性、文明的积极认同与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对压迫民族不平等地位的警觉与反抗。尽管有人也曾将这种警觉与反抗的矛盾心态视为“民族主义的病灶”,但造成这种不幸的不是民族主义的情结或者是传统文化的因素,而是西方现代性及其表征的现代知识与思想。④ 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第二,一战与西方现代性破产的外部冲击促使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第一次危机的反思,构成了中国超越现代性的外在原因。现代性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对前现代社会形态、价值理念批判性超越的胜利者姿态而呈现给世人的,甚至可以说,现代性本身就是作为资本主义自我标榜的胜利宣言书而出现的。从现代性自身的视角而言,它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段不断征服、不断彰显历史一元目的论的高歌猛进的历史。但是,西方现代性在近代却遭遇了自其产生以来的第一次危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西方现代性之历史主义进步论的理性反思。所谓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即是指“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① 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册,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在此背景下,“西方的没落”开始成为西方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观念,斯宾格勒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正式提出所谓西方现代性的危机问题。这种关于西方现代性危机理性反思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欧洲,而且也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而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原先基于民族主义情结而存在的反现代性的思想特质。其中最显著的代表即梁启超。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明确提出用东方文明去拯救已经破产的西方文明,“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②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上册,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3页。 正是在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思想界接连爆发了东西文化论战与科玄论战。尽管论战双方各持不同观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受西方信仰危机的影响,在重估西方现代性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已然构成了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发展路向。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那样,中国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自主性生发的产物,而是外部输入的结果。这种外源性思想启蒙正当其轰轰烈烈展开之时,作为“母体”的西方现代性早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困境之中,这就是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面临的“生不逢时”的尴尬困境。③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二、复调式语境II:沉重现实遭遇下的“超越”逻辑
第三,殖民主义扩张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共同推动了关于现代性的另类思考。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构成了中国超越现代性的重要社会政治文化心理。西方现代性在其发展特定阶段与殖民主义合谋,在殖民主义扩张形式配合下以排他性方式实现自我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这一过程既是西式现代性无止境扩张的过程,也是广大非西方民族、国家、地区遭受侵略、凌辱的悲惨过程。中国并未因为在地理位置上的“东方性”而能够摆脱殖民主义现代性的袭扰,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世界体系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中国也以主体性缺失的状态被迫卷入现代性的浪潮之中。面对亡国灭种的社会危机,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脉络而言,一旦国族被赋予了绝对至高性地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逐步成为“规范性词汇”(the normative vocabulary)的“殖民”“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等就自然而然承载了负面意义,因为它们是直接导致中华民族陷入危机的根源。④ 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53-254页。 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决定了民族主义复活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布展过程中的意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作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代表,有着区别于第一世界民族主义的典型特征,即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并且这种抵抗包含着一般民族主义的内涵在内。正如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①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具体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运动而言,正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的初始性要求之下,正是在这种民族的觉醒基础之上,才逐渐生发出个体意识的觉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构成了连接20世纪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的重要纽带。中国近代以来政党政治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反映。正是因为直面现代民族之间竞争的残酷性以及殖民主义现代性的血腥与暴力,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保种救国,超越西方殖民主义的现代性,建构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方案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先进分子的不二选择。
那时哥们儿朝洛蒙祖坟还没有冒白烟,还没有提升为销售助理,还和我们挤在十平米大小的“烟箱子”里。媳妇来了,租不起宾馆,俩人就在“烟箱子”眉来眼去地腻歪着,害得我们哥几个晚上有“家”不能归,只在街上瞎逛。羊肉串吃得没滋味,就去火车站胡同里的小旅店看港台的武打剧或毛片。但还是出了事。哥们儿朝洛蒙和媳妇在“烟箱子”里时,被厂里管后勤的经理撞到了,当成卖淫嫖娼的把他们揪到保安室。几个保安轮流审讯,好在他媳妇还算是有心人,来时把结婚证揣在兜里。媳妇掏了结婚证,给保安看了,保安才放过他们。这事在厂里传扬开来。媳妇臊得要死,咬牙切齿跟哥们儿朝洛蒙说,再也不来这座没有人性的狗屁城市了!
近年,面对首都大环境的变化、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日趋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王致和”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找准定位,明确战略目标,创新生产与销售模式。
近代中国现代性并非是自主性产物,而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所直接做出的应激性反应,因而学习西方甚至是直接模拟西方现代性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最初生长状态。但依照历史辩证法的逻辑,这种基于本能的模拟,在另一个层面也开启了在某种程度上对西式殖民主义现代性暴力逻辑的拒斥心态。
第一,近代中国学习现代性与超越现代性的矛盾心理结构。正是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问题生成的特殊性,使中国对西方现代性的态度自然呈现为一种在关涉生存问题的关键时刻而做出应激性反应,这种反应必然表现为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带有强烈殖民色彩现代性的暴力逻辑。正如梁漱溟在阐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冲突时所指出的那样,东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并不仅仅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垒,而实实在在的是东方化的存亡问题。因为凡属东方化的国民,不是改从西方化,就是为西方所强据。“改了可以图存,不改立就覆亡。东方化的唯一根据地的中国数十年来为这种大潮所冲动,一天比一天紧迫,到现在已经撞进门来,而这为东方化浸润最深的国民,不同凡众,要他领纳西方化大是不易。逼得急了,只肯截取一二,总不肯整个的承受。”⑤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48-249页。 梁漱溟的上述话语以简明形式呈现了中国近代以来在遭遇现代性过程中的基本心态,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所表现出的一种警惕矛盾姿态与超越现代性的诉求。有学者运用“怨恨”的概念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展开的历史进程——迎合与拒斥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以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受挫与受伤的经验,促使中国民族主义者以西方的理念来反对西方,民族整体的无能感与历史自傲感(自卑与自傲)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怨恨心态的起点,并且决定了近代中国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的价值偏爱结构。⑥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25页。 我们这里所言的“超越现代性”并非是超越现代性的一般规定性,不是通过对现代性基本理念、原则的否定而实现向非现代性(既可以是前现代又可以是后现代)的转换,而是超越现代性的特殊表现形式或特殊发展阶段,即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
三、另类现代性: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问题的本质特征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提出了托卡马克的概念,并建成了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由于磁场强度技术上的限制,所能约束的高温等离子体只能是非常稀薄的.其密度比惯性约束中的小很多。因此要实现点火,就要大大增加约束时间。
第一,中国现代性建构内蕴作为一项复杂恒久性思想史议题的意义。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而言,倘若用一个主题对其进行归纳和概括,可以是救亡与图存,也可以是救亡与启蒙,上述两对范畴其实在本质上都关涉一个通约性主题,即“走向现代”。可以说,求索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自主性方案,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一项持续理论命题。无疑,中国以“落后”发展姿态在殖民主义现代性武力扩张的基础上被迫卷入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洪流之中,因而“冲击—反应”“压迫—反抗”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显著特征。中国在面临西方现代性的强烈冲击时,一方面既想维护旧有的传统、秩序与价值形态,另一方面又想借助于西方现代性理论完成对传统的置换与升级;一方面既想通过对西方现代化的借鉴、学习,努力赶超现代化的潮流,另一方面对作为“侵略者”“出场”的现代性理论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防范。同样,西方国家在向前现代中国输出现代性理论时,也面临着二元悖论,即一方面寄希望于通过现代性的冲击,涤荡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并以西方的观念重新塑造中国人民的集体心理意识;另一方面对中国接受现代性洗礼的过程又保持着高度警觉,努力打压中国真正步入西方现代性潮流并扼杀中国获得与西方平等对话、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中国追求自身现代性的过程必然充满着系列曲折性。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性也必然面临着深刻的困境,这使得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时态上一直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也使得求索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成为一直困扰中国思想界的恒久性命题。
本报告探索使用动态投资回收期法、资产收益率法、盈亏平衡分析法进行设备运行的经济效益分析,评价指标如下。
第二,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力场”是中国现代性的原初语境。正如前文所言,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产生存在着复调式语境,即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的焦虑所共同构筑的复杂关系格局。其中,“现代化的张力”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的求索之路并非如一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前现代草根浪漫主义,而是始终以追寻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为基本价值旨趣;同时,“现代性焦虑”又表征着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产生的特殊性,即并非完全复现西式现代性的一般道路与模式,而更多的是基于本民族自身历史与现实展开的特殊探索。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化的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力场”,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求索之路面临着的一组深刻而复杂的矛盾。近代中国关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从根本上而言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无意识挪用。当然,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性的特殊生存境况,也决定了对于西方现代性的焦虑必然成为中国在自身现代性求索之路中存在的社会政治心理意识。这种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从最广义层面上而言,是由现代性问题自身的逻辑所决定的。因此倘若将现代性视为对现代生活的经验体验,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现代人由于自身不同存在状态的限制,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可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倾向。波德莱尔作为现代性画家,其笔下所描绘的现代都市巴黎场景,既包含衣着鲜艳的贵族,也包含穷困潦倒的落魄之人,因而关于现代性之体验既有迎合欢呼,亦有拒斥怀疑的焦虑。同样,作为现代性体验主体的民族国家,因为各自所处历史情境之差异,对现代性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态度。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并且是在挨打基础上直面现代性,因此,一方面迎合现代性以摆脱挨打困境成为应激性反应,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挨打的基础上,加以强烈民族自尊的鼓动,对西式现代性又保持着时刻警惕与焦虑的姿态。正是这种难以抉择的矛盾心理,形塑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艰难求索之路。并且,这种既基于历史遭遇又基于现实考量形成的矛盾心态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影响着当前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第三,关于另类现代性的选择是中国现代性的初始性本质特征。在现代化张力与现代性焦虑的矛盾支配下,究竟应当如何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这是近代以来困扰中国思想界的核心问题,也是关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性问题。如果说现代性在西语环境中意味着给一种既定的现实(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与生活样态)进行理念的概括问题,那么,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却是意味着一种有待建构的现实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一方面既必须回应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期待与关切,同时也必须面对西方现代性的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西方威胁——而这种生存意义上的威胁正是中国现代性产生的原初语境。上述两种考量之间形成的紧张张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人面对现代性即羡慕又反感、既迎合又拒斥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理暴露出一种分裂的思想,一方面想靠自己打开一条现代性之路,另一方面又想沿袭西方的现代性历程,或者在两者之间调和。”① 谢少波、王逢振主编:《文化研究访谈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正是在这种矛盾焦虑心态的指导下,中国现代性问题两难困境的解决就必须要正确处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如何对待自身发展的历史境况与民族传统;二是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性的逻辑扩张。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存在全面复归传统逻辑或全盘导向西方逻辑,这两种倾向都是在中国现代性困境的两个因素之间的极端化偏向。“全盘西化”与“全盘本土化”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两种极端选择,只能成为极少数人的主观想象,可以成为理论上的“理想型”或“模式”,而绝无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因为以文化建构为例,文化认同必然是在实际生活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其间本土成分与外来成分相互作用、相辅相承,折中是无可避免的结局。②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2页。 因此,科学建构中国现代性问题必须恰如其分地把握好上述两个要素,对于这一困境的超越既不能通过走文化复古而通往前现代的反现代主义逻辑,也不能忽视民族自尊、传统与现实发展境况而导向照搬照抄西方现代性的“拿来主义”。前现代性的反现代性不可取,复现西式现代性的模拟——本质上是“一元现代性”(single modernity)话语霸权的体现——也不可取,其结果应当而且只能导向基于本民族传统与历史发展特殊实际双重考量的“多元现代性”(Mutiple Modernities)之探索。
总而言之,通过回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历史语境,可以清晰地揭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基本逻辑构架及其理论特殊性。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具体历史特征的理解之上,才能较为科学合理地定位当前建构中国现代性方案的选择及其走向问题。换言之,中国现代性问题在其产生之初就具有的复调式语境与矛盾结构,决定了未来中国现代性的重构既不能导向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能重归闭关自守的前现代性主义浪漫构想,而必须要建立在深刻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境况的基础上,科学处理与当代西方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以期建构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现代性话语与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11-0032-07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0124143901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210093)。
a汪晖:《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责任编辑:罗 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