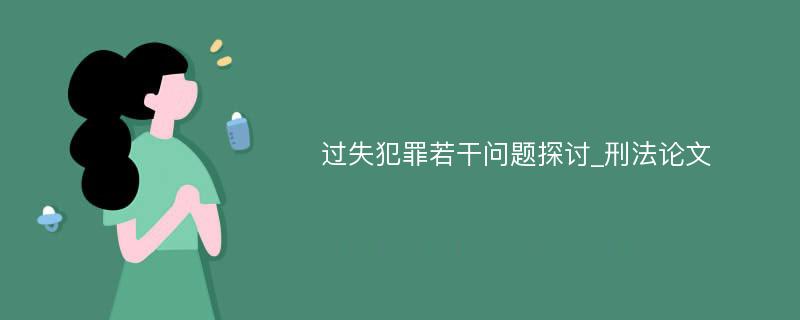
过失犯若干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失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0)03-0005-10
一、问题意识
尽管我国现行《刑法》第15条是有关“过失犯”的规定,但我国刑法理论则一直将其作为“犯罪过失”来研究。这显然有偷换概念之嫌。过失犯是一种客观行为和状态,它是指在犯罪过失心理支配下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而犯罪过失则是指导致过失犯结果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因此,仅仅研究作为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犯罪过失,能否反映出《刑法》第15条所规定的过失犯的全貌和本来面目,令人怀疑。
如就过失犯的实行行为而言,我国学者鲜有研究。有的话,也是在分则的相关罪名当中,以诸如“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违反日常生活中所应当注意的行为”之类的简单语言一笔带过,而对于其实质内容,则完全没有分析。这大约是因为,过失犯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难以一概而论,因此,以“违反各种法规的行为”或者“违反日常生活中的注意的行为”来概括比较方便易行的缘故。但是,将违反规则或者违反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的行为,直接看作为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岂不是有混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和一般过失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扩大过失犯的处罚范围之嫌吗?同时,就过失犯的主观要件而言,刑法学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应当预见”即预见义务的内容以及“能否预见”即预见的判断标准上,而对在犯罪过失的认定当中,最成问题的预见对象、预见程度,即成立过失,行为人必须对“危害社会的结果”有多大程度的预见,是只要有抽象、漠然的预见就可以,还是必须有具体的预见才行,则几乎没有提及。这样,在过失犯的处理上,往往就是追究结果责任,只要行为人有违法行为,并且引起了危害结果,就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行为在形式上引起了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实际上并不是造成该结果的原因的时候,该如何处理?这些也是过失犯的处理当中所要考虑的问题。而上述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对过失犯承担刑事责任基础的理解。即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对上述问题做出截然不同的解答。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笔者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出发,试图对过失犯的本质、实行行为、主观预见等问题进行反思,并发表白己的看法。
二、过失犯的客观方面
(一)过失犯的实行行为
关于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总论性的定义几乎看不到,在各论的论述当中,则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客观方面,通说见解认为:“是指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他人的生命安全缺乏应有的关注,违反注意义务,导致他人死亡”。就过失造成重大事故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而言,一般都概括为“实施了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换言之,就过失犯而言,其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不是采用直接定义的方法,而是以“违反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义务的行为”或者“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来加以说明的。
这种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描述为“违反规则的行为”或者“违反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义务”的行为的定义方法,过于形式,在具体应用上,明显存在难以正确认定过失犯的成立范围的问题。
首先,难以正确地限定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有扩大过失犯的成立范围的倾向。如在限速20公里的街道上,行为人以时速30公里的速度开车。路边的小巷子里突然跑出一个意图自杀的人,冲到马路中央,行为人躲闪不及,于是将该人撞死。事后发现,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即便行为人以正常速度行驶,也难以避免危险结果发生。但即便如此,行为人的行为还是会被看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因为,按照前述过失犯的实行行为的理解,此种场合下,既有危害结果发生,同时,行为人又违反了限速规定,因此,当然要构成犯罪。但是,将这种行为人难以预见和难以避免的偶然情况看作为犯罪,有悖法律的公平正义之理。同时,我国的有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在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场合,除了要考虑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外,还必须考虑行为人对发生事故所承担的责任大小。只有在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引起了一定的严重结果,并且对这种结果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同等责任的场合,才能说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①可见,将“违反规则的行为”一律看作为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显然是不妥当的。其结果,就是将已发生一定结果作为成立要件的过失犯,统统都变成了违反行政取缔法规行为的结果加重犯。[1]
其次,不符合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定义,有将过失犯和不作为犯混为一谈的倾向。如前所述,由于学者们将“违反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义务的行为”或者“违反规则的行为”作为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因此,在过失犯的构造上,自然就将违反注意义务看作为过失犯的核心内容。[2]确实,从不作为的立场出发,也能合理地说明“小心谨慎地实施了危险行为,但结果仍然发生了的场合”为什么不罚。如果强调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生活当中,到处充满危险的话,就会很自然地将“未避免危险”的不作为作为过失犯。但是,将危险的范围缩小,不把生活中的各种风险都看作为危险,而只将实质上难以忽视程度的风险作为危险,将引发该种危险的作为当作为犯罪,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在向煤油炉里加油的时候,不是采用先将火熄灭的方法,而是采用在灯捻子燃烧的状态,把炉子的盖子揭开,直接倒入煤油的方法。在采用这种方法注油的时候,由于不小心,煤油一下子漫了出来,结果引起火灾的场合,按照上述不作为犯的观点,这里应当受到谴责的对象是没有先将火熄灭,然后倒入煤油的不作为。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教授所说,刑法的任务,仅只在于禁止具有导致火灾危险的加油行为,而不是指导国民如何正确地加油。在上述案例当中,成为失火罪的实行行为的,应当是在灯捻子仍然燃烧状态下的加油行为,而不是在加油的时候,没有先将灯捻子掐灭这种“违反日常生活中的注意”的不作为。[3]换言之,过失犯的实行行为还是直接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作为,而不是单纯的没有履行义务的不作为。
最后,违背犯罪的本质。犯罪在本质上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违反法规范的行为。违反法规范,是一切违法行为(包括民事违法、行政违法等)的共同特征,但是,就刑法上的犯罪而言,其不仅仅是违反法规范,更重要的是,这种违法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或者危险,即从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结果的角度来考虑犯罪本质。但是,认为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是“违反规则的行为”的观点,实质上将行为人违反规则作为处罚过失犯的根据,而发生侵害法益的严重结果只是一个客观处罚条件而已,这样,就有可能使人误以为过失犯的本质是违反法规范,而造成严重结果只是成立犯罪的一个处罚条件而已,从而和整个犯罪概念不一致。
这样说来,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仅仅理解为“违反规则的行为”或者“违反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的事项的行为”是不妥当的。实际上,从《刑法》第15条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定义为“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行为的角度来看,应当说,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的实行行为也是从实质角度加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理解在刑法分则各个具体的过失犯的探讨当中,却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在过失犯的认定上,过于讲求形式要件,从而扩大或者缩小过失犯的成立范围。如在被告人受打工单位主管人员指派,驾驶一辆套牌拼装没有尾灯的汽车,在夜里三点多钟行驶的时候,被尾随的一辆轿车撞上了左车厢一角,造成双方车辆不同程度的损伤,尾随车辆乘车人一人重伤的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人在交通运行中,故意违反交通法规,在明知其所驾驶的大货车没有行车证、没有后灯、没有其他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仍然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致当事人驾驶的轿车尾随撞上,致使交通事故发生,致人重伤,其行为已违反了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触犯了刑法,构成了交通肇事罪。②这种判决结果显然是有问题的。首先,仅仅以被告人违反车辆必须经过检验合格,领取行驶证、路牌以及保持车况良好,各类装置齐全等的规定而认定其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路牌的汽车上路,并不必然会导致严重交通事故的发生。其次,从事故发生当时的情况来看,被告人驾车在前,是被动者,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评估后车的行驶状态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期待前车具有有效防止后车追尾碰撞的义务。因此,就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只能考虑后车即被害人所在车辆的驾驶员的责任。事实上,事后查明,后车驾驶人员在事故当时,有严重的违章行为,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但是,法院形式化理解了我国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认为行为人只要有交通违章行为,并且发生了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显然是扩大了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范围的体现。因此,正确理解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对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和“允许危险”
如果说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是具有导致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实质危险的行为的话,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具有该种危险,就值得探讨。关于这一点,主要问题是所谓允许危险的理解。
允许危险是刑法学中所公认的排除过失犯的刑事责任的事由。这种理论认为,性质上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为,若属于允许危险的话,就不是危险行为,即便引起一定结果,也可能不成立犯罪;相反地,若属于不被允许危险的话,就是危险行为,引起结果的话,可以成立过失犯。但是,何谓允许危险,理论上则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一是广义上的理解,将允许危险理解为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一般危险,如驾驶汽车的行为尽管很危险,但是,由于汽车快捷方便,而且运载量大,广泛地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各种方便,因此,虽然危险,但仍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就是因为其是被允许的危险的缘故。[4]二是狭义上的理解,将允许危险理解为实质上的危险行为,认为这种行为具有引起危害结果的实质危险,本在严格禁止范围之列,但是,由于为了救济其他利益,而不得不允许其存在。如为了抢救病人而允许救护车超速或者闯红灯行驶的场合,就是如此。[5]198
我国的学者通常在广义上理解允许危险。如有学者认为,科学实验往往带有危险性,从事科学实验的人员也总是预见到了危害后果的发生,但不能因此而禁止这种行为,只要行为人遵循了必要的规则,按照规则的要求谨慎行事,就不存在过失,就不为其行为所可能带来的危害后果负刑事责任。[6]107但是,广义地理解允许危险,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违反了允许危险的本来意义,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在现代社会中,汽车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人们已经就汽车的使用制定出了很多规则。人们按照这种规则来合理地使用汽车的话,应当说,驾驶汽车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没有什么危险,没有必要将其作为允许危险看待。相反地,如果说驾驶汽车是允许危险的话,就可能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虽然驾驶汽车本身很危险,但由于其是允许危险,所以,即便驾车撞死了人,也没有关系。这种理解显然不合乎现实的法律规定。它不仅歪曲了允许危险的本来意义,扩大了允许危险的存在范围,而且还为某些疏忽大意、不尽职责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开脱罪责的借口。
其次,广义地理解允许危险的话,会取消该原理的存在意义。从允许危险的存在意义来看,它是限制或者排除过失犯的成立范围的事由,而不是扩大过失犯的成立范围的事由。如果说驾驶汽车或者医疗行为,本身是危险行为,只是由于社会生活需要,才在一定条件下予以允许,所以,属于允许危险的话,那么,对救火车在奔赴火灾现场的途中,一路超速行驶并且连闯红灯的行为就难以理解。实际上,从法益比较衡量的角度来看,在救火的过程中,违反限速规定的行驶行为即便造成了一定危害结果,但和所要救助的利益相比,并不较大的话,也不能说该行为构成犯罪。同样,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也会面临手术失败、致患者伤残的风险,但在对和手术治愈患者所具有的利益以及当时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比较权衡之后,结果还是冒着危险给病人进行了手术的时候,这种手术行为,可以说是允许危险。即便造成了一定危害结果,也不能马上就说医生的行为构成犯罪。
最后,广义地理解允许危险的话,与过失犯的实行行为的观念也不相符合。广义上的允许危险的概念是从物理的、自然的意义上来理解行为的危险,而不是从规范的、法律的意义上来理解危险。实际上,从规范的立场来看,法律所不禁止的即允许的就是合法的。某种行为既然是允许危险行为,就意味着该行为没有引起危害结果的实质危险,不是刑法上所说的违法行为。既然不是刑法所关心的违法行为,对其探讨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从规范的立场来看,所谓允许危险,应当是指狭义上的允许危险,即实质上可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危险行为。这样理解,也和刑法通说认为刑法上的危害行为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具有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或者说是法益的实质危险的行为”的理解一致。
这样说来,过失犯中,作为限制过失犯成立范围的“允许危险”中的“危险”,应当是指刑法规范意义上的实质危险,即具有引起具体犯罪结果的危险。
在上述意义上理解“允许危险”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允许危险的适用范围相当狭窄。如果说“允许危险”就是在实质上具有引起犯罪结果的危险的行为的话,那么,其所应用的范围,就只应当限定于为了保护一个更大的利益而违反一般规则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应当遵守的注意事项,具有引起危害结果危险的行为,如救护车或者救火车为了救助病人或者灭火而违反限速规定,闯红灯行驶等。
第二,在判断是否允许危险的时候,应当进行法益的比较衡量。允许危险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本来的意思是,对于伴随有侵害法益危险的工矿业、机械交通、医疗等行业,以其对社会具有意义为根据,即便在发生了一定的侵害结果的场合,也予以允许,不作为犯罪处理。按照这种理解,允许危险的量和该行为所具有的价值成正比;发生实害结果的可能性和所预想的允许危险的大小成反比。
三、过失犯的主观方面
由于过失犯是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了该种危害结果。因此,在过失犯主观方面的认定上,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都离不开行为人的主观上的“预见”。即便是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似乎与预见能力无关,但实际上行为人并没有确切地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内在机制,以至于轻率地做出危害结果不会发生的错误判断。所以,说到底,过于自信的过失最终也还是没有充分地“预见”的问题。[7]175因此,在过失犯的认定当中,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是否具有“预见”,就成为认定过失犯的关键。
(一)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
从《刑法》第15条的规定来看,过失犯,就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没有预见,以至发生了该种后果。因此,“应当预见”是成立过失犯的前提。所谓“应当预见”,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是预见义务,二是预见能力。
就预见义务而言,我国的学说当中,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见解。认为,来自法律或者规章制度的预见责任只应限于法律或者规章制度的规定。对于超越行为人的合法或者符合规章制度要求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行为人不负有预见的义务;来自职务要求的预见义务,只限于行为人所从事的职业或所担负的职务而产生的预见义务。在职权范围内的正常活动可能产生的危害社会结果,行为人不负有预见的义务;来自公共生活准则所产生的预见义务,只限于一般人都能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反公共生活准则的场合。对于超出合乎公共生活准则的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后果,行为人不负有预见的义务。[8]354
但是,在预见能力即根据何种标准判断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是否具有预见方面,刑法理论上,则没有形成一致见解:“主观说”主张以当时具体条件下行为人本人的能力和水平为标准;①“客观说”主张以社会上一般人的能力为标准加以判断;[9]在我国,也有学者提倡这种观点;②“折中说”主张行为人的能力比一般人高的场合,就以一般人为标准;比一般人低的场合,就以行为人为标准的折中说,这是我国的通说。[8]356
上述三种观点,实际上是主观说和客观说之间的对立,而所谓折中说不过是主观说的一个变种而已。主观说是德日刑法学中旧派刑法学的主张,认为为了对行为人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只能在具体行为人的注意能力的范围之内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否则就是强人所难;相反地,德日刑法学中的新派刑法学采用以抽象的一般人的注意能力为标准的客观说,认为从防卫社会和教育刑的立场来看,每个人都必须尽到其一般的注意义务;不具有通常的注意能力的人,对社会而言,也是危险的存在,因此,从防卫社会和使不具有能力者也具有能力的角度来看,值得科处刑罚,否则,就难以实现刑法防止犯罪、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10]345由此看来,有无预见能力之争,实际上是刑法保护法益原则和责任原则在过失犯的处罚范围问题上,该如何协调的问题。
从预见能力是行为人个人的事情,其有无完全取决于各个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看,主张预见能力属于责任要素,应当以各个行为人的注意能力为标准加以判断的主观说是妥当的,它是责任原则要求的最忠实体现。但是,完全按照主观说,就有缩小过失犯的处罚范围、为过失犯开脱的嫌疑。首先,按照主观说的理解,以当时具体条件下行为人本人的能力和水平为标准,会出现行为人是否具有预见能力,完全由行为人自己说了算的局面。如在“他平常就是个稀里糊涂的人,没有预见到会发生这样的后果”的场合,法律就对其无能为力。这显然是难以实现刑法的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的;其次,会出现打击先进、鼓励落后的局面。“如甲乙二人同为工人,甲没有积极钻研,因此业务水平低,而乙则相反,勤奋钻研,自学成材,业务水平高。对于同一工作上的事故,按照甲的业务水平,没有预见能力,不以过失犯论处,而按照乙的业务水平,具有预见能力,应以过失犯论处。”[7]177这里显然包含有不合理的因素。因此,有学者说:“拒绝客观尺度,就是纵容了个人的眼光短浅、不学无术的庸碌无能”。[11]这样说来,在有无预见能力的判断标准上,不能采用主观说。
同样,完全按照客观说,也会强人所难,导致违反责任原则的结果。预见能力是主观的判断能力,其有无必须根据各个人的情况来加以认定。如果以一般人为标准加以判断的话,在行为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较低,达不到一般人的认识能力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强人所难的结果。这显然会违反近代刑法所主张的主观责任原则,出现追究行为人的客观责任或者说是结果责任的结局。
笔者认为,在有无预见能力的判断上,首先,应当以“行为人所属领域的一般人”为标准,判断行为人是否有预见能力。在其所属领域的一般人能够预见的场合,就可以说行为人具有预见能力。当然,行为人的年龄、职业以及其他认识能力、行为能力也要考虑在内。在这些事情的基础之上,以一般人为标准加以判断。这主要是因为,过失犯往往是从事业务活动的人实施的,或者是一般人违反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注意而实施的,处于该种地位的人,必须具有这种注意能力。否则,就不能从事该项工作。在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能够预见的时候,应当说,行为人就应当能够预见,否则,就会陷入主观说的窠臼;在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都难以预见的时候,就应当说,行为人没有预见,否则,难以避免客观说的弊端。这种以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为标准加以判断的学说,可以称为修正的客观说。
按照这个标准,行为人在当时条件下可能尽管没有预见,但是,从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的立场来看,这种情况,应当能够预见的话,就应当说行为人具有预见。如行为人在驾驶汽车过程中,由于眼睛近视又忘记了戴眼镜,结果看不见前方,将行人撞死的场合,尽管在危害结果发生的当时,可以说行为人没有预见能力(眼睛看不见),但是,由于行为人对于自己在驾驶汽车时必须戴眼镜一点具有注意能力,因此,可以说其对现实发生的结果具有预见,根据这一点,能够追究其过失责任。否则就会出现奖懒罚勤的结局,实现不了刑法保护法益、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相反地,一般人在当时条件下难以预见的,行为人也可以因为自身认识能力较高而能够预见。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查明行为人确实具有预见,那么,就可以行为人的实际预见情况而追究其过失责任,以体现近代刑法所坚持的责任原则的要求。因此,在有无预见能力的判断上,既不应无视行为人的实际情况,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来代替其认识能力,也不能只考虑行为人的实际情况,以他本人为标准来说明其有无预见能力,而必须以行为人本人所属的一般人为素材,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加以判断。⑤换言之,在有无预见能力的判断上,修正的客观说是妥当的。
(二)预见程度
根据《刑法》第15条的规定,成立过失犯,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必须有预见,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行为人的预见必须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说行为人对于行为的危害结果具有预见,则有不同看法。
一种见解认为,行为人只要对自己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或者是违反规则的行为具有认识,就足以说明其对危害结果具有预见。如在黄金波交通肇事案中,法院的判决根据行为人“违章占道停车,且属无证驾车”,就直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显然的过错”,而没有提到行为人对于犯罪结果有无预见。换言之,在实践当中,一般都是以只要行为人具有违反规章的意识,就认定对发生结果具有预见。
相反地,另一种见解则认为,行为人仅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还不够,其还必须对可能发生的结果具有具体预见。这是我国现在的通常见解。如一般认为,过失犯中的危害结果是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是由刑法明确规定的,所以,这里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只能是刑法分则对过失犯所规定的具体的危害结果。[12]
笔者同意我国刑法学的通常见解。在过失犯的预见程度问题上,应当坚持具体结果预见说。在判断行为人是不是具有过失,不能看行为人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偏离标准行为即违反规则或者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因为,在某一具体活动当中,行为人应当遵守的标准行为并不止一个,而是具有数个。这样说来,何谓应当实施的标准行为,其认定就很困难,弄不好就会流于任意。而且,按照这种方法认定过失,也容易得出只要实施了违反一定标准的行为,就马上可以认定其具有过失的结论。换言之,在行为人具有违反标准行为的场合,即便是偶然原因引起了结果,也能认定为过失犯,这显然扩大了过失犯的处罚范围。
在理解过失犯中的具体预见说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这种预见是指对构成要件结果的预见,而不是对结果以外内容的预见。如在过失将爆炸物遗忘在公共场所,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场合,行为人主观上的预见内容,是指对发生人员死伤、财产损失具有预见,而不要求其预见到在某年某月某日,会对某特定的被害人或者财产造成伤亡或者损失。另外,对于结果的个数也没有要求。在危险行为引起数人死伤的场合,即便行为人只对其中特定的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具有预见,也不能说,行为人只对预见的部分承担责任,而对其他损失撒手不管。
第二,对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具体因果经过不要求有预见,但对因果关系的重要部分必须具有预见。因为,要求在行为时,就对之后的因果发展方向有预见,是不现实的;同时,对已经预见到结果的人而言,仅以其对现实的因果进程没有认识而否定其主观责任,也是极不合理的。[10]36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具有发生结果的恐惧感或者没有任何根据的漠然的不安就可以说行为人对发生结果具有预见。在认定行为人是不是发生结果的预见的时候,必须考虑其对发生结果的重要部分是不是具有预见。所谓因果关系的重要部分,是指在因果经过当中,对一般人而言,能够预见到“事实”的话,就能预见构成要件结果的一般事实,至于该事实是如何引起该结果发生的即因果经过的每一个细节,则没有必要预见。如在胡同里开车的时候,由于小孩从路边窜出,结果被撞死的场合,虽说对撞死小孩的结果没有预见,但是,如果说对胡同边的巷子里“常有小孩从路边跑出来”的事实有预见的话,就可以说对发生孩子死亡的结果具有预见。
(三)预见的排除——信赖原则
对具体预见范围起限定作用的,是“信赖原则”,即“在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时候,如果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害人或者第三人采取适当的行为,即便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的不适当的行为而引起了危害结果,行为人也不承担责任”的见解。这种见解,本来源自德日,主要适用于交通事故的场合,目的是减轻驾驶人员的负担。在德日,过去,“汽车是危险的交通工具”的观念盛行,在汽车撞死人的场合,常常仅仅是因为死了人,所以,就马上要对驾车者予以处罚。这样,就迫使驾车人“在驾驶的时候,必须将被害人所可能具有的各种过失都考虑在内”,结果,不仅难以发挥汽车这种现代交通工具的特长,还会在过失的名义下,追究驾车者的无过失责任。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还过失责任的本来面目,于是法院就采用了信赖原则,以减轻驾车人的责任。[5]198我国刑法学现在也接受了这一原则。“汽车司机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时,因合理信赖他人不会横穿公路而正常驾驶,如果他人违法横穿公路被汽车撞死,该汽车司机就不负刑事责任”[6]107的论述,就是其体现。
信赖原则,在合理分配过失责任的分担,限制过失犯的成立范围方面,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但在信赖原则的适用上,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信赖原则的适用,具有一定条件。如就交通事故的场合而言,根据信赖原则,解除行为人的肇事责任的条件是,交通设施比较完善,遵守交通秩序的习惯已经形成,行为人从其经验来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他交通参与人采取不合适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具体地看,行为人也无法预见到存在使其他人采取不适当行动的特别事实。因此,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在设施完备、秩序良好的道路上驾车的时候,行为人可以说有足够的理由信赖他人采取合适的行动,但是,在路况复杂、车人混杂的公路上,或者在遇到幼儿、老人、残疾人、醉酒者的场合,不能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人会采取合适的行动。这种场合,要慎用信赖原则来解脱行为人的过失责任。
第二,行为人自己违法的时候,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适用信赖原则。这主要是指以下几种情况:违反交通法规和事故结果之间不具有条件关系的场合,如行为人无照驾驶或者驾驶没有牌照的车辆之类的场合,不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违反交通法规连续发生交通事故,但这些事故之间并没有相互联系的场合;即便遵守交通法规,也会发生事故的场合;在行为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已经成为事实,被害人也知道这一事实的情况下,不采取躲避措施,以致引起事故发生的场合;不管自己是否违反规则,都能期待对方采取适当行动的场合。⑥
四、过失犯认定中的两个特殊问题
(一)被害人自冒风险
所谓被害人自冒风险,是指法益主体即过失犯的被害人在事前就对所存在的危险具有认识,但仍然决定冒险,结果,还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使得该种危险成为现实的场合。被害人明知他人酒后驾车很危险,却仍然决意乘坐,结果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被害人死亡,或者被害人明知河豚肝脏有毒,食用河豚肝脏非常危险,但仍然要求餐馆厨师用河豚肝脏做菜,结果被害人食后中毒身亡,或者某种医疗手术技术还不成熟,存在危险,但被害人仍然执意接受该种手术治疗,结果手术失败,导致他人死亡,或者被害人明知酒后深夜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下车行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仍然要求司机放其下车,结果被撞身亡等,都是其适例。对这种被害人自冒风险而引起结果的情况,该如何处理,理论上存在争议。
对于被害人自冒风险的行为该如何处理,刑法学上的一个有力学说认为,应根据自己负责原则加以解决。所谓自己负责原则,就是被害人根据自己的积极态度在一定活动中取得了主动权的话,行为的危险和所发生的结果就应当归属于被害人自担责任领域,行为人对所发生的结果不负责任,即结果的客观归属被否定。如在暴风雨中,客人要求船夫将他留在岛上,船夫说明危险并加以劝说,但劝阻无效,客人后来被淹死的情况,就是如此。⑦在被害人自冒风险的场合,由于被害人自愿参与该危险活动,而且在其中掌握主导权,因此,对于发生在其身上的危害结果,当然也应当由其自己负责。
但是,自己负责原则适用的前提是,被害人“以自己的积极态度在一定活动中取得了主动权”,即在活动当中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场合下,如果发生了对被害人自己不利的结果,被害人当然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但是,在自冒风险的场合,被害人并没有将主导结果发生的因果关系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只是作为一个参与者而已。这时候,行为人在亲自实施危险行为,将因果关系的发展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即便说被害人自身具有保护自己法益的责任,也不能排除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不利结果在客观上所承担的责任。
笔者认为,对此应作为被害人承诺的类型之一考虑。从被害人承诺的角度来看,所谓被害人承担危险,就是其同意将行为人的行为所具有的危险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对于该危险行为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不得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对于这种理解,反对意见认为,在被害人自冒风险的场合,其承诺的是参与行为,并不是承担危险后果。但是,这是过于形式化的理解。既然是危险行为,就表明该行为蕴涵有发生结果的可能,行为人既然同意参与行为,就绝对不能说对该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表示不同意,否则,《威尼斯商人》中所要求的“只许割肉、不许流血”式的做法,就不会成为一个笑话,另外,从违法性即社会危害性评价是对包括结果在内的行为整体评价的立场出发,也能得出这种结论。因此,在被害人作为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人,能够预见到该行为的结果而执意参与其中的时候,完全可以作为“被害人承诺”的一种类型,否定该行为成立犯罪。
在以“被害人承诺”的原理来否定被害人自冒风险场合中的行为人的罪责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剥夺生命的过失行为,不能适用“被害人承诺”的原理。因为,各国刑法均认为,即便是接受他人请求,杀害他人的行为,也要作为犯罪(同意杀人罪)处罚,因此,通常见解认为,生命不在被害人可以自由处分的利益之内,换言之,被害人承诺原理,对于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不适用。由此类推,在过失导致他人死亡的场合,也不得以被害人自冒风险而免除被告人的罪责。因此,被害人在明知他人酒后驾车极为危险,但仍然乘坐该车,结果发生交通事故丧身的场合,尽管被害人具有自冒风险的行为,但仍然要追究驾车者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⑧
第二,对于造成他人重伤的过失行为,可以适用“被害人承诺”的原理。因为,在充分尊重个人自主意识的现代社会中,处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利益,是个人行使权利的体现,因此,同意伤害原则上不予处罚。但要注意的是,对于具有导致死亡危险的重大伤害,由于其直接威胁到他人生命,因此,在适用“被害人承诺”法理的时候,必须慎重。从这种立场来看,同意伤害是否违法,取决于伤势是否严重。这样说来,在被害人明知他人酒后在山路上骑车危险,但仍然执意坐在该车的后架上,结果摔落下来,造成重伤的时候,可以说被害人对可能遭受身体伤害的不利具有承诺,这时候,行为人对于该伤害结果,可以不承担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罪责。
第三,在过失犯中适用“被害人承诺”原理的时候,必须查明被害人承诺的真实内容。在判断被害人是否对所发生的结果表示承诺的时候,必须考虑被害人对发生事故的预见程度,只有在其对发生事故具有高度预见而仍然参与该行为的场合,才可以说其对被害法益具有承诺。
(二)合法行为的替代
所谓合法行为的替代,是近年来德日过失犯讨论中所热议的一个话题。通常来说,在过失犯中,结果的引起常常是因为行为人的违反规则或者违反了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的事项,但是,有时候,行为人即便慎重地实施行为,但还是难以避免结果的发生。这种场合,该如何处理?具体来说,“即便行为人谨慎行为,但仍难以避免该结果发生”这种假设性事实,是否具有免除过失犯的刑事责任的效果?有的话,其在理论上如何加以构成?这就是所谓合法行为的替代所讨论的全部内容。这种场合,由于采用了将假设的“合法行为”替代“现实的违法行为”进行讨论的方法,因此,被称为“合法行为的替代”。
最初引起这一话题的,是德国的所谓“拖拉机事件”。拖拉机驾驶员A在间隔只有75厘米宽的道路上超越前面骑自行车的人B,B由于喝得大醉,骑车时东倒西歪、摇摇晃晃,结果卷进拖拉机的后轮而被轧死。事后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便A按照法律规定,在法定间隔即150厘米宽的地方超车,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检察官以被告人犯过失致死罪对该案起诉,但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13]在日本,也存在类似的判决。如在火车司机疏忽大意,在通过视野极差的铁路道口时,没有注意到铁路道口上有一个小孩而将其轧死的案件(“京都铁路道口事件”)中,法院认为,即便驾驶员没有疏忽大意,在发现幼儿之后,迅速采取拉响汽笛、紧急刹车等措施,但从列车的时速和到人行道口之间的距离来看,也难以防止该结果的发生,因此,认定驾驶员的行为和幼儿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判处驾驶员无罪。⑨
对于法院的上述判决结论,德日的学者们都表示认可,但对得出这种判决结论的理由该如何说明,则没有定说。笔者认为,可以从“预见可能性和回避可能性说”的角度加以理解。
和故意犯的场合一样,在考虑行为人的过失犯的刑事责任的时候,也必须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过错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首先,就客观行为的危险而言,其认定必须结合行为当时的客观事实以及行为后所查明的各种情况,客观地加以判断,而不能将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考虑在内。如驾驶刹车系统坏死的汽车的行为,无论行为人是否知道该事实,都应当说,该行为是危险行为。在上述德国判例中,由于事后查明,被害人由于酩酊大醉,行为人即便按照规则在更宽的间隔(150厘米)上超车,也难以避免被害人死伤结果的发生,更何况在75厘米的间隔上超车,其危险性就更大了。因此,超车行为所具有的撞倒他人的危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能根据假设的、即便遵守交通法规也会引起同样的结果的理由而加以否定。因此,意图从客观的因果关系的角度出发,否定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说明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是相当困难的。其次,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不意味着行为人要承担过失犯的刑事责任。行为人承担过失犯的刑事责任,除了客观上引起了法益侵害结果之外,主观上还必须对该结果具有预见。在没有预见的时候,不能仅仅因为造成了侵害结果而承担客观责任,否则,就违反了责任原则。就上述拖拉机事件而言,如果从一般人的立场来看,在事故当时的间隔(75厘米)上超车,撞上被害人的可能性极小,而且行为人在当时也无法预见被害人处于醉酒的话,应当说,行为人无法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致使被害人死伤的结果,所以,没有过失;相反地,如果行为人已经意识到在事故当时的间隔上超车,极有可能使一般人摔倒,而且,从被害人的姿势等来看,其有可能处于异常状态的话,就应当说,行为人对于他人死伤具有预见,对于所发生的结果,应当承担过失责任。这样说来,对上述拖拉机事件,完全可以从行为人对结果有无预见方面来说明其应否承担责任。
同样,对于上述日本的“京都铁路道口事件”也可以同样地加以说明。在本案当中,客观地看,引起小孩死亡的原因是驾驶列车的行为,而不是其他,因此,说列车司机的行为和小孩之死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但是,从行为人的主观责任方面来看,应当说,行为人还是具有免除责任的可能。由于列车通过的是视野极差的道口;在行为人能够发现幼儿的时候,即便采取拉汽笛、紧急刹车等措施,也难以防止避免结果的发生,这种场合下,可以说,行为人没有回避结果发生的可能,因此,应当否定其过失责任。这样说来,对上述所谓“合法行为的替代”的场合,不从客观方面,而是从行为人的主观责任方面,也完全可以做出合理的说明。
五、结语
总之,我国《刑法》第15条是有关过失犯的规定,而不仅仅是犯罪过失的规定。不从过失犯的角度,而仅从犯罪过失的角度来考虑刑法第15条规定的话,就会得出行为人只要有违规行为,并出现了严重结果,就要构成过失犯的结论,这样,不仅会扩大过失犯的处罚范围,同时对作为客观事实的主观反映的犯罪过失也难以做出深刻的展开。因此,从主、客观统一的角度来研究刑法中的过失问题,已是大势所趋。
过失犯的本质是“违反预见义务”,即行为人应当认识或者预见自己行为后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由于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没有预见,以致该结果发生;在过失犯的研究当中,和故意犯一样,首先必须考虑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即具有引起犯罪结果发生的实质危险的行为,而不能仅仅考虑“违反规则”或者“违反日常生活当中应当注意的事项”的行为;在过失犯的主观方面,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预见义务、预见能力,还要考虑行为人对结果的预见程度。只有对上述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对过失犯的认定中所遇到的“自愿承担风险的行为”以及“合法行为的替代”问题做出妥当的处理。
收稿日期:2010-04-20
注释:
①参见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相关内容。另外,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有违章行为,其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负交通事故责任。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无因果关系的,不负交通事故责任。”
②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5/8/li2282464413850021216.html。
③如陈兴良教授认为,客观说因以一般人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有无预见能力,确有客观归罪和放纵犯罪之嫌。相比之下,主观说的缺陷较小,应采主观说。因为,注意能力的有无是关系到是否构成过失犯的问题,在刑事责任上,客观归罪是绝对不允许的,是和我国刑法的性质格格不入的。至于说主观说的消极性,是可以克服的。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以下。
④如有学者认为,特定一类人在该种场合下能够预见,行为人属于该种特定人员时,就可以说,应当预见。参见姜黎艳、孟庆华:《论疏忽大意过失的预见标准》。转引自高铭暄、赵秉志主编:《过失犯的基础理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⑤本案的事实是:被告人于1999年4月23日凌晨驾驶无牌照的东风牌货车行驶至梅仙线某路段时,将车调头逆向停放于公路的路侧,与酒后无证驾乘无牌二轮摩托车行驶到该处的被害人潘某、黄某相撞,造成二被害人死亡。被告人事后驾车逃逸。以上内容,参见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刑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⑥转引自[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Ⅰ》,东京,成文堂1999年版,第362页。
⑦关于自己负责原理的介绍,参见[日]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以下。
⑧在国外,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在我国,是以交通肇事罪论处的。由于我国的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对于公共安全利益,个人无法放弃,因此,这种场合下,无论如何都是要处理的。
⑨[日]大审院1929年4月11日的判决,载《法律新闻》,3006号,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