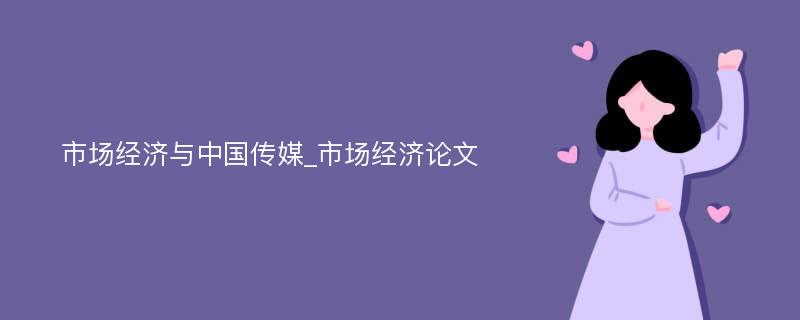
市场经济与中国传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中国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至今为止,我们人类已经走过了三种经济形态: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一直扮演主角。
在自然经济中,自然是占主体地位的。换句话说,经济是依附于自然的。我个人认为,在那时,人们对自然——首先是自然界——是深怀恐惧和敬畏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宗教,尤其是拜神教,都产生于那个时代。
我认为,在自然经济时代,人们由于还无力破坏大自然,因此形成与自然界无奈的和谐关系。
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已具备了改造和破坏自然的某些能力,由此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人为经济的时期。
过去我们有一种偏见,认为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实际上,资本主义也用计划经济手段,如罗斯福新政。
中男改革开放20年,最大限度证明了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
现在看来,我们过去把社会主义观念过多地定位在经济形态或成分上,忽略了科技进步以及经济行为的演变。其结果是自己束缚了自己,把社会主义搞僵化了。
对比三种经济形态而言,自然经济大都以家庭或氏族为经营单位;而计划经济则以集体或国家为主体;而计划经济则打破了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界限,甚至跨越了国家,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跨国公司增多的原因之一。
自然经济的目的是自给自足,养活自己。计划经济的目的则在于照顾集体或不同利益群体的均衡。而市场经济则是以谋取最大利润为前提的。
相对而言,计划经济中的人为色彩要更浓一些,而市场经济则更像是“超自然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是靠“看不见的手”来操作市场经济的。抽象说,市场经济是人的有意识不去控制的经济行为。
比如,在自然经济中,人们没有能力控制经济。到了计划经济,人们开始控制经济。而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又开始放弃控制。
如果说自然经济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朴素的道德经济,那也多半指它与自然的相容性。而计划经济从目的性而言,它对于集体或相关利益群体而言是道德的,但是它忽略了个人。市场经济则是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作为一种社会游戏,它的规则就是法律,法大于人,在这里张扬个性,主张个体独立意识,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平等,强调个人的质量,而不是集体的数量。从这些角度看,它更接近于道德经济。
(二)
大众传播媒介从产生的开始就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大众传媒的产生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
比如,最早的世界通讯社路透社,就是基于伦敦市场交易所的讯息需要应运而生的。大众传媒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登上舞台相关。
从历史看,原始社会几乎不需要信息。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信息工具是为某个小团体和个人服务的。如中国的邸报,完全是为唐宋王朝统治阶级服务的。
进入资本主义后,财富成了社会衡量个人的标准。官位和血统被弃置一边。在这时,信息交流发生了质变。第一是信息交流从自上而下变成了双向或多向;第二是市场经济对信息有更强依赖性。这些都使传媒大众化。
虽然,人类几千年一直把教育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但是大众传播方式与教育有巨大不同。最明显的就是,大众传媒力求培养的是社会消费者。他们消费文化、政治和商品。
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消费,那么生产就变得毫无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又是“消费经济”。消费是出发点,又是归宿。这一点与计划经济不同。计划经济力图控制人们的消费,或者说生产扩大是第一位的。从这一角度,也许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一种“生产经济”。
从字面上看,消费这个词意味着花掉多余的。对吃不饱的人,几乎谈不上消费。所以,不难理解大众传媒的发达为什么与人类社会度过温饱期迈入“小康”有关。一句话,市场经济需要大众传媒来维持和扩大消费。
从宏观上看,战争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并不大。在早期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夺权时,大众传媒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今天,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平等、自由和公正的标志。
(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发展迅速。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营的传媒现在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最大的变化是,国家不再给媒介补贴了。失去了国家财政支持,媒介不得不自负盈亏。除极少数传媒,像人民日报等,还在享受一点国家补助外,中国大多数传媒已走向市场。
有趣的是,10年前,新闻界还在探讨传媒应不应该面向市场,而今天,他们已不得不在“海”里游泳了。
媒介走向市场后,出现了一个最大矛盾是,如何解决报纸和电子传媒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一方面传媒似属国有,他们的政治性质未变;但是一方面,传媒在经济上获取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他们必须要十分注视发行量和收视率,因为失去受众,他们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10年前,传媒人士像商店售货员一样,对微笑服务和“读者是上帝”的说法大不适应。而且,比起第三产业的服务员,搞宣传的人更难调整这种心态。因为毕竟,新闻宣传在几十年中曾经属上层建筑,传媒人士也一直有“上层人士”的优越感。
但是,市场经济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这种观念。市场重心从生产者移向了消费者,过去生产者是大爷,生产什么你就消费什么,生产没商量,所以板着面孔也无所谓,产品好坏就这些,别的没有,没有竞争。现在不同了,竞争成了最响亮的口号,消费者忽然一下子成了不自信的“上帝”。
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不得不把命运与订户联系起来。过去是公费订阅,国家财政支出,现在是个人掏腰包。尤其是这几年机构改革,行政减员,公费订报进一步下降,这都使报纸不得不多考虑读者爱好。
目前发行上最艰难的是那些挂靠机关的省级或地方机关报,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报道和发行联系起来,哪个省或地区订报多一些,报道上就照顾一点。虽然,这种方式目前颇有争议,但许多报社也是无奈。
好在社会经济转轨时,新旧体制并存,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传媒既面对挑战,又有机遇。机遇是可以利用市场经济,巩固自己的经济实力,使报道转型,平稳过渡,毕竟中国的改革还不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比如说,过去困扰中国传媒的会议和领导人报道,现在通过扩版等变通方式得到缓解。有意思的是,现在传媒有时会发现如果没有会议和领导人支撑头条新闻,他们还真不习惯在别的新闻中搜寻头题。
广播电视在市场经济中也有竞争。广播在老大哥报纸和小弟弟电视的围攻下,生存困难。虽然是国家垄断,但听众日降,即使办许多分台和系列频道也难以长远。
相对说,电视日子好过。在击败广播和报纸后,电视开始击败自己。卫星电视等高科技使电视的遥控器成了电视人的天敌。几秒钟换一台成为流行文化。中国人均城市电视频道均用量可以说已步入发达国家。但这只说明,我们的电视是超前发展了。
目前,中国已出现了十多家报社收入超亿元。其中大部分是晚报。电视台更是广告收入很高。这与当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形成鲜明对比,可见媒介业在中国是很赚钱。
近几年实行的双休日制度,也为中国的周末报和版提供了大好机会。可以想像,中国这个被西方人视为大市场的人口大国在迈入市场经济后将为媒介业和娱乐业提供一个多么广阔的天地。可以说,中国已真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消费时代,而第一代独生子女是消费一代。
(四)
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出现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成为第一家。今年中国宣传主管部门更是把组建报业集团作为一种大事来抓。
曾记何时,在大学新闻系的教科书里,报业集团还被当作资本主义社会大财阀垄断报业的象征。
中国近年推行报业集团,可以视作积极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一大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组建报业集团得到政府的首肯和大力支持。
中国目前的报业集团大都以报业为主,或者说以主报为中心,再向相关行业辐射。
经过一些年的报业经营尝试期,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如果在经营上走得太远,或者说离报业过远,他们就会失去新闻业经商的许多优势。
在相当长的未来里,中国报业还比较难以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集团。虽然新华社办了许多报刊,虽然有的报纸想办电台和电视台,但在目前看,是不允许的。其实不仅中国,国外对媒介过于集中也有一些限制。
报业集团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首先是中国报业在市场经济面前,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调整结构迎接挑战。
10年前,当报业逐渐进入市场时,无论是主管领导还是报人自身,都对报业的市场前景不大乐观。报业的自负盈亏可说是出于无奈,因为政府已“断奶”,吃“皇粮”已不饱。
而今天不同了,政府和报人两方面都有积极组建报团的意向。
对中国来说,组建报团无疑有利于国家从宏观上对报业、乃至舆论进行调控。中国目前有3000多家报纸,加上大量的刊物,管理起来并非易事。用报团这个龙头来调整管理结构,不失为一条良策。
问题是报团搞大后,它的经营部分必然加大,那么它的经营和宣传两者是一种什么关系和比重?
现在,许多报纸都在呼吁引进经营人才,足见对经营的重视。换言之,报社不缺报人,缺的是有头脑的商人。
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们的报业充斥着一流的报人,但他们大多是对经商不在行,可谓重文轻商。现在一些报社往往是报务和经营一肩挑,一套人马,两块牌子,造成有偿新闻,降低记者威信。另一方面,新闻把关人又为经营所困扰,总编辑一肩挑忙得团团转,报务和经营仍难以两全。
过去一些报社只有编委会,经理人员只能偶尔列席重要会议。今后可以预见报社经营管理层的声音将越来越大。报务和经营的分工将日益明确。
报团现象虽然很热闹,但其实广播电视集团的组建也只是时间问题。电视台财大气粗,早已有集团规模。过去总是要电视支援广播,好比当年广播支援电视初建所需之人才,现在电视反过来帮助老大哥,而这种帮助又很有可能以广电集团形式出现。
组建媒介集团对中国传媒市场竞争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十分明确,但这个问题无疑值得研究。
(五)
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率和公平的,从这一点上讲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但在我看来,经济和道德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正像效率和公平之间也有一定分歧一样。
经济形式和道德表现形式就有不同。经济因其目的性而采用利益式利润最大量化的行为。它可以利用人性恶的一面。而道德则着眼于开发人性善的一面,主张利益均衡化。
所以,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和道德有冲突,这也影响到传媒。当传媒完全摇摆在商人和报人的角色错位之间时,必然影响整个行业的道德状况。
现代社会人们正是在这种多重角色的冲突中失去一部分自我和独立。这也是我们的时代病,当我们大喊独立意识,我们却也正在大量失去独立。这与现代人类的自我清醒意识有关,也与我们人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有关。一方面,我们要使每个人的角色分工不能再细再具体了,另一方面这又与人全面发展相背。
我们追求的东西也在多样化。我们用市场经济来最大限度使效率量化,但公正无法量化。表面看,效率和公正不矛盾。每个人有提高效率的机会。这是天赋“效率权”的一个佐证。
但是从深层想,在追求高效时,只有追求方式可以说是公正或公平的。而追求效率毕竟不是一句空话,它有排它的目的性。有时它甚至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而公平在此时成为了制约效率的工具。
新闻媒介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商业化了。但它的确不是普通的企业,生产普遍的产品。它是一种舆论,既可以传达社会信息,又可以对社会的一些方面实施监督。
虽然,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增加了许多,像电脑网的出现。但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取代一些传统媒介,比如报纸。同样,虽然今天的信息爆炸已使人们开始逃避信息,正如逃避责任,但是有选择的信息或相关个人的信息却比以前更明显影响我们的生活。从一定角度看,这是我们的“信息病”。
市场经济把传媒领到一个新十字路口;一方面,它必须像企业那样去生存;另一方面,它又要考虑不失去自己固有的特色和传统的性质,在法律的基础上给社会提供一种监督方式。
人们可以想像到报摊上购买信息,但是无法想像到何处去购买舆论监督。正好比如果一个社会不可以随便买卖法律,舆论也是不能购买的。
因为信息可能只与个人有关,而舆论却与大众相关。我们说信息不一定是新闻,我们还可以说新闻不一定是舆论。因为舆论可以像道德和公平一样潜伏着,随时监督着社会。
当社会靠法律和道德来监督时,道德监督则较多依靠着舆论来完成。
当20世纪末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国这个文化和道德古国时,中国媒体已经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转换,但在这背后,我们还缺乏规范化的有序的动作机制,这意味着在下个世纪我们还将面临更多的变革,这种变革将决定我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社会角色定位。
当我们在“文革”后选择把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时,就注定了我们要选择市场经济。
就前三种现有经济形态而言,无疑市场经济是最有活力的,最有利于谋取最大利益值的。
如果我们完全把经济当成一种手段而言,那么,市场经济中所表现出的对人这个社会主体的忽略以及它那冷酷的机械色彩,是可以忽略小记的。
巧合的是,市场经济大行其市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带动第二次浪潮,而英国的经济学家也为这种冷静的市场经济哲学注入了相适应的规则和理论。
虽然,有人管日本人叫“经济动物”,但实际上人是社会动物,有时,在短时期里,经济会成为我们的目的,但是,从比较长远来看,精神文化显然更容易成为我们人类追求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个社会或民族只有物质文明史,而没有精神文明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