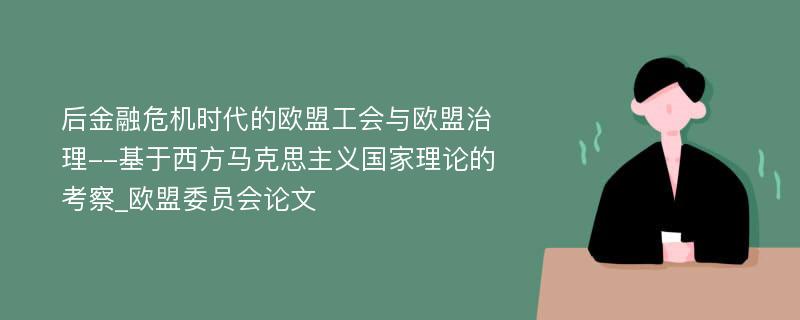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角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工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单一欧洲法令”到《里斯本条约》,欧洲一体化进程通过让步与妥协广泛吸纳了各类社会力量的参与。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至2011年已造成2000多万人的失业。①为应对危机,欧盟机构于2012年3月开始实施结构调整和紧缩政策,对欧元区实行严格的货币稳定政策。然而,各类救助方案的出台并没有征得欧盟工会和其他社会伙伴的同意,欧盟工会在争取欧盟社会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地位尴尬。危机之初,欧盟工会被视为与国家政府和商业界同等重要的危机管理者,而福利削减和紧缩政策却把工会视为需要处理的问题之一。工会权利在后危机时代的重建中更是不断遭到削减。 经济危机为考察欧盟跨国工会在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良好的视角,既暴露出欧盟跨国工会组织存在的问题,也显示出跨国劳工代表在地区治理中的潜力。本文拟借助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通过考察当前在欧盟层面上作用最为显著的跨国工会组织“欧洲工会联合会”(ETUC)的实践活动来理解跨国工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前景。本文认为,在与欧盟机构长期的互动中,ETUC在思想和行动上深受新自由主义欧洲一体化方案的影响,难以超越欧盟制度结构的限制。金融危机为欧盟工会带来了机遇,使其能够在欧盟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依然不足以扭转欧洲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路径。 本文首先分析回顾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葛兰西的国家理论对劳工和国家关系的论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欧盟工会在欧盟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最后讨论欧盟工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对新自由主义欧洲一体化政策议程的抵制与修正,认为欧盟工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伙伴,是一体化前进方向的重要修正者。 一、社会力量、国家形态与欧盟治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 社会力量与国家形态的关系在政治学研究中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而多元主义理论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主流理论。多元主义一般认为,国家是中立的,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争夺的场所;利益集团是政治过程的主角,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分析的基本单位。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各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应该如何认识这种差异的性质?新多元主义承认,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拥有不同的权力资源。例如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E.Lindblom)就指出,实业家们不是简单地作为某个特殊利益的代表而出现的,它具有“特权地位……公共事物掌握在政府和实业界两个领导集团的手中”。②林德布洛姆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特权地位及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劳工所无法具备的。但新多元主义学者往往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地位差异视为其自身资源差异的结果,而对更大背景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关系视而不见,因而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劳工组织在资本主义政治治理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则在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从“霸权/领导权”的角度看待劳工、资本及其与政治形态的关系,这对于理解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的关系十分关键。该理论继承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思路,认为观念和思想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霸权即是一种文化支配形式,是一种得到赞同的秩序。③“霸权是一种关于秩序性质的价值结构与理解结构,它充斥、弥漫于整个国家体系与非国家实体之中。在霸权秩序下这些价值与理解相对稳定而又无可置疑。它对大多数行为主体来说是自然秩序。这种结构以权力的结构为基础,一个国家的支配地位不足以建立霸权,霸权来自于主导国家的主导社会阶层,以至于他们的所想所做获得了其他国家和其他阶层的默许”。④也就是说在某种霸权形态下,占主导地位的阶级集团主要是通过取得从属性阶级集团的默许来实施统治的,而且这种统治充分地体现在生产方式、国家形态和国际秩序三个层面上。 从生产方式上看,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的社会权力表现为指挥监督劳动过程的权力,“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起的作用也就越大。”⑤资本主义还通过强制性的市场依附以及商品拜物教把人置于其社会统治下,屈从于一个以“商品”为代表的客体世界,劳动者被解除了权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社会权力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充斥着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关系,与其政治生活的再生产密不可分,因而具有政治性。劳资双方的对抗性关系源于各自在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地位的不平等。 从国家形态上看,资本的社会权力的政治性必然反映在政治形态上。正如艾伦·伍德(Ellen Wood)所说:“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秘密……有一个必然结果:工人个人和资本家个人间的权力分配构成了社会整体的政治结构的条件,即阶级力量和国家权力的平衡,国家权力允许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维护资本家的绝对的私有财产权以及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⑥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也认为:“生产的结构即使不是由国家创立的,至少也是在国家的鼓励和维护下存在的。生产产生行使权力的能力,但权力决定了生产得以产生的方式。”⑦这些观点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与政治制度安排存在着客观的内在的一致性。 除了上述物质方面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尤其重视资本权力的思想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包括有形产品的生产,也包括实现这种生产所必需的知识、制度和组织的生产,并形成了超越特定的经济/公司利益的“霸权方案”。它集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级及阶层的不同追求和普遍利益,以经济领域为基础并囊括了特定的积累策略和增长模式,⑧进而超越经济领域涵盖政治和社会领域,诸如社会改革或思想领域的道德重建等,最后建立起一种稳定的霸权性的政治制度。反映在国际秩序层面上,“当主导国家和主导社会阶级通过捍卫为众多从属国及从属阶级接受或默许的普遍原则来维护自身地位时,全球霸权就存在了”。⑨“全球霸权通过核心国家和正在工业化的社会中精英阶级的同盟合作,以及全球政治经济制度所提供的控制机制来发挥作用”。⑩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新自由主义霸权方案就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安排,它在生产场所、国家形态和欧盟治理三个层面上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一体化要求,并在上述层面上透露出劳资双方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的霸权结构塑造了各类社会力量,但却不是决定后者的唯一因素。通过与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其所形成的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的“必要的相互作用”,社会力量的能动作用也能得到表达,“这种交互作用无非是真实的辩证过程”。(11)也就是说,劳工组织也可以有所作为。由于社会力量的利益和策略是具体的、历史的,资本对劳工的结构性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劳工建构、表达和对抗资本领导权的活动也必然会展现出来,表现为话语权的争夺和各类积累策略的冲突。结果,阶级成了生产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因素,并可以在地区层面或全球层面上表现出来,成为世界经济和国家间政治体之间的中介,社会团体也建立了彼此间的跨国联系。(12) 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看来,政治形态是嵌在社会力量的具体的历史的结构之中的,既非超历史的范畴,又非韦伯眼中的自主的制度行为体,而是政治力量平衡的产物,是一种能够反映社会力量平衡变化的社会关系,(13)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基本集团和从属集团的利益之间的不稳固平衡”。(14)国家政治形态的变化塑造着具体的社会力量,同时也被后者所塑造。用鲍勃·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方法的国家理论”表述就是,国家既不是中立的工具也不是理性的计算主体,作为多种组织机构的集合体,国家是不同的政治力量相互争夺权力的策略场所,具有不同身份的特殊力量会在国家系统的结构限制下追求不同的特殊策略以实现它们的特殊利益,并将各自的策略传递给多个部门,以影响这些部门单个的或集体的活动,促使国家制度结构向有利于实现其利益的方向变革。(15)当然,杰索普还认为:“国家不是同样对所有社会力量开放并同样适用于所有目的的中立的工具,它有一个内在的、确定的偏向,这使它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开放,更容易为资本主义政策调动起来”。(16)联系到本文的研究,杰索普认为欧盟也是一种国家形态,它“是许多权力中心的集合体,它为欧盟内外不同力量为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活动提供了不平等的机会”。(17) 总之,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上述思路,欧盟机构是一个有着自身战略选择性的超国家多层治理机构,既依赖各类社会团体(如劳工和资本)的策略发挥作用,其本身又具备一定的倾向性。工会对抗资本霸权的斗争“尽管属于伦理政治的范畴,但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18)这种历史结构框定了欧盟工会所能取得的成就及其限度,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仅凭各类劳工社会团体及其联盟是难以构造出某种“霸权方案”的,其斗争目标往往表现为阻止某些新自由主义法案的提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工人没有什么理想要实现,他们要做的只是把资产阶级社会所孕育的新社会元素解放出来而已”。(19) 二、新自由主义重组下的欧盟工会与欧盟治理 组织多层次的劳资对话与合作曾是战后欧洲大陆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制度,但总体性的欧洲层面的社会对话出现较晚。工会真正参与欧盟治理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实现的。此后,工会被纳入了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欧盟治理机制当中。由于欧盟体制的制约,工会形成了在欧盟体制框架内发挥影响的行动策略,实际上成了新自由重组方案的合作小伙伴,(20)无法对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政治氛围构成根本性挑战。 (一)欧洲治理的新自由主义转向 在许多从事欧洲研究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重组为工会参与欧盟治理,也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启带来了动力。(21)他们认为,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政治形态和思想观念等多个层面发生的变化使欧盟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新自由主义形态。(22) 20世纪80年代,面对以美国资本和技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的发展,欧洲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美国和日本的巨大竞争压力。为了捍卫全球竞争力,欧洲国家希望通过一体化进程消除国家政府对贸易和竞争的限制,实现生产的跨国化,使欧洲经济空间更具跨国性。这一过程在社会关系层面导致跨国集团的出现,他们努力为建立跨国资本的霸权创造条件,其核心代表就是“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ERT)。ERT成立于1983年,由沃尔沃CEO皮哈尔·吉林哈默(Pehr Gyllenhammar)和欧盟委员会委员艾德涅·达维农(Etienne Davignon)倡议建立。他们通过在成员国和欧共体层面开展密集的游说活动,积极参与欧盟高官的官方会议,发布一体化的战略报告,对一体化发展“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3) 在新的形势下,以本国为基础的出口资本加入了跨国资本的同盟,而以国内为市场且受到进口竞争的资本却日渐衰落。劳工也被迫处于守势,接受了压制工资、改革福利国家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包括经理人、银行家、保险公司掮客、地产商、金融服务业、欧盟委员会成员、具有市场倾向的政治家、新自由主义思想库和许多媒体人在内的社会政治力量联盟,并建立了大量的跨国交往渠道。(24) 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新型跨国集团的出现使欧洲一体化将增强国际竞争力作为首要的目标,经济指导思想也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哈耶克认为,新自由主义既是一个经济方案又是一个政治方案。作为经济方案其目标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释放市场的力量。而作为政治方案,它明确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福利国家。(25)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上述变革过程概括为“欧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在综合分析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这一“转向”大致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1)欧洲货币体系(EMS)标志着新自由主义重组的开始,它迫使成员国实施预算规范和限制性的货币政策,以技术官僚的方式避免了公众的关注。(26)(2)单一欧洲市场(SEM)标志着欧洲一体化的重启,欧盟委员会和跨国资本是其推动力量。(27)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将单一市场与货币、技术和社会领域的一体化远景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众多社会力量的心声,既包括处于守势地位的以内部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团体,也包括积极呼吁建设“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的工会组织。(3)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建立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完成。人们一般认为,EMU的核心功能是加强欧盟全球货币竞争力、降低交易成本、加强文化稳定性,是先前一体化进程的逻辑延伸。而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发现,马约的聚合标准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使核心政策领域出现去政治化特征,没有为提高工资和制定更多的社会政策留下空间,也没有缓解高失业和慢增长的紧迫问题。EMU比SEM具有更多的戒律新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特征,即新自由主义准则和政策被转变成法律或准法律并成为制度,从而不再受到民主辩论和民主决策程序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确保私人财产权,使国家公共政策符合国际流动资本的利益。戒律新自由主义将财政、货币、贸易和投资政策都变成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东西,市场效率、纪律、商业信心、政策可信性和国际竞争力等要素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且不受其他价值如公平、福利等的挑战。新自由主义原则一旦变成法律,任何修改都极其困难,需要极为特殊的条件和繁琐的程序,如特定多数或全体一致等。EMU对欧洲央行独立性的强调、欧洲法院以市场自由优先于工人罢工权所做出的裁定等都是戒律新自由主义的表现,是力图摆脱民主政治约束的明证。(28)结果欧洲一体化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抵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法国甚至引发了抗议浪潮。 尽管政治抗议日益增多,但欧洲一体化仍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整个90年代,欧盟统治阶级身段灵活,广泛动员了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他们承认欧洲劳工的社会民主诉求,但“这些诉求最终必须服从新自由主义竞争力这一高高在上的目标”。(29) (二)新自由主义重组下的欧盟工会 在新自由主义重组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葛兰西曾经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是通过“领导权”来实现的,既有赞同的一面,又有强制的一面。对资本主义而言,“有必要剥夺工人阶级作为其他受压迫阶级领导者的历史作用……但资本家出于产业的目的不希望摧毁所有的组织形式。在工厂里,只有当部分工人中存在着最低限度的赞同时,才可能有纪律和生产流畅运行。”(30)这样,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工会就在与资本的谈判中具有了“受压迫阶级领导者”和“异议管理者”的两种身份,在赞同与强制之间维持平衡。 在欧洲,从煤钢联营时期开始,共同体就努力把社会对话制度引入到一体化进程中来,但进展缓慢。1973年,为了促进在共同体层面上代表工人的劳资谈判制度的建设,欧盟委员会支持了欧洲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ETUC”)的组建。从1972年到1978年,欧共体举行了6次由劳资双方代表、共同体机构与成员国政府代表参加的“三方会谈”,讨论了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工资限制与财政政策等问题,但总的看来收获不大。1978年,ETUC要求达成共同体层面的集体协议,否则就退出会谈,结果谈判不欢而散。(31) 到了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重组迫切希望将工会领导人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以达到以下目的:(1)加强市场导向的结构重组和新自由主义信条的合法性;(2)希望工会支持低于生产率增长的温和的工资增长政策,这对刺激投资和维护货币稳定十分重要,既降低通胀风险又维持较高的政府预算;(3)支持建立对资方友好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调整社会保障体系;(4)帮助成员国解决国内经济不均衡增长带来的问题。(32) 为了笼络工会,德洛尔在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希望通过社会对话机制,增强成员国工会领导人的欧洲意识,并培植欧洲层面的工会行为体,使之以劳资社会伙伴的身份参与欧盟治理。为此,他劝说代表欧洲资本家利益的欧洲雇主协会联盟接受与工会的谈判机制,构筑劳资伙伴关系框架,因为若无工会的支持,资方所偏爱的内部市场计划就无法实现。在1989年制定的《社会宪章行动计划》中,欧盟委员会允诺在递交社会政策立法动议前须向社会对话中的劳资伙伴咨询。然而,由于欧盟治理权力分布依然不均衡,“民主赤字”问题使社会对话的范围依然非常有限。直到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附的《社会政策议定书》才引入了劳资伙伴咨询与谈判程序,使关于社会对话的规定成为制度,欧洲劳资伙伴而非欧盟机构成了欧洲社会政策领域的“共同立法者”。虽然《社会政策议定书》及以后的条约修订扩大了特定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大幅拓展了欧盟的行动能力,但是欧盟迫于“民主赤字”的压力,更加倚重社会对话等治理模式。20世纪80-90年代,ETUC就将“社会对话”作为工作重点,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解除管制政策,并认为此举不可避免。(33)至此,工会组织被正式纳入到欧盟治理机构之中。 然而,在社会伙伴关系中,劳资双方的结构地位并不平等。这也表现在劳资双方对待一体化的态度上。有学者指出,为了抵制欧洲层面的社会规制目标,在欧洲层面资方可以根本不作为或者只在民族国家层面作为,而劳方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即欧洲层面的社会规制,各成员国工会组织必须克服国家利益的束缚,在超国家层面形成共同的战略和行动。(34)这就是说,在欧盟架构中,劳方比资方更迫切地希望在欧盟层面形成政治压力。在考克斯看来,这是因为“一个霸权性的世界秩序产生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它凭借普遍化的积累和管理方式在各国社会力量间建立秩序。新自由主义霸权代表着资本主义组织精英的国际一致性”。(35)也就是说,当新自由主义成为霸权时,资方完全可以不借助政治来实现统治。因此,另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欧佛比克明确指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是一种阶级的统治形式,而非国家的统治形式”。(36)这就揭示了欧盟社会伙伴中的资方与欧盟委员会等治理机构在新自由主义霸权方面的内在一致性和欧洲层面的工会作为“小伙伴”的实质。这一本质也可以部分地解释劳资双方在社会伙伴谈判结果是否有约束力上的分歧。例如工会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就谋求建立有约束力的谈判磋商机制,而资方始终拒绝有约束力的承诺。而当马斯特里赫特政府间会议在社会政策领域适用多数表决制时,资方又希望通过引入和工会谈判达成的协议来拖延、稀释或替代欧盟委员会的严厉立法提案。(37)其目的是排斥政治干预,去政治化,使资本的戒律高于政治的干预。 除了社会伙伴以外,欧洲层面的工会还以游说组织的身份对欧盟的立法工作施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战略合作对象是欧洲议会中的社会党团体和欧盟委员会,其中与社会党团体的合作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对ETUC来说,欧洲议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38)但泰勒(Taylor)等人的研究指出,由于在欧洲层面上并不存在战后民族国家内部所形成的那种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间的密切关系,而且随着国家层面上“主导性政党与工会间联系”的渐渐消失,工会要在过于碎片化的欧洲议会中建立稳定的联盟就更加困难了。(39)因此将欧洲议会作为抵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平台依然困难重重。 此外,欧盟委员会因在立法方面举足轻重而成为ETUC的另一个工作对象。欧盟委员会下属各部门的权力和职能各不相同,其中负责教育、竞争和贸易等问题的部门与工人直接相关,就业和社会事务总司和企业总司掌管工人权利方面的政策。然而与内部市场总司相比,前者的权力和地位就显得很弱小。ETUC常常指望就业和社会事务总司,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欧洲工作理事会指令》(European Works Council Directive)和《欧洲公司地位指令》(Directive to the European Company Statue)是欧洲工会在社会对话下取得的重要成果,但与《单一欧洲法令》的力度相比对劳工的让步也就仅仅具有象征性罢了。 近年来,欧洲法院在关于工人权利和工会地位方面变得愈发重要。有学者指出,欧洲法院的一系列裁定表明,在欧盟政治和法律框架下,资本主义的自由流动原则与既有的工人基本权利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40)欧洲工会不得不在越来越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敌意的体制架构下谋求开展工作。(41) 综上所述,欧盟治理机构为工会提供的制度空间非常有限,工会在欧盟层面也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代表,“社会对话”模式过于软弱。面对欧盟机构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劳工只能在维护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就业增长之间做出妥协。ETUC具有深厚的社会民主工会背景,社团传统根深蒂固,对欧盟的现有体制结构、总体治理目标、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赞同,它似乎并不希望从根本上反对欧盟机构的治理策略。 三、金融危机与欧盟工会 近年来,全球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又的确给欧洲各国工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进入21世纪后,生产的跨国化、碎片化和欧洲经济的金融化迫使工会不断后退,失业增加、工会成员流失、集体谈判中的不断退让使工会的谈判地位日益萎缩。但是,工会结构性权力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工会只能是现状的被动接受者。某些特殊时刻如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常常会成为工会加强国际团结的重要契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后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这样的时刻。 葛兰西指出,当“第一种前途(强制)越直接越基本”时,第二种“前途(赞同)”就会越“遥远”。(4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治理的强制方面愈发突出,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更是不加限制,这表现为资本的结构性权力和各从属社会团体的结构性权力之间愈发激烈的对抗。面对欧盟日益从紧的危机治理政策,工会渐渐进入了社会斗争主体的角色。 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如贝弗利·西尔弗(Beverley Silver)就系统地研究了工会的权力结构问题。他认为一般而言工会具有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结构性权力来自工人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可以使用罢工为武器并动员其会员进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联系性权力则是工人能够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或政党,并扩大与其他社会运动的合作,动员其成员开展斗争。(43)在更广大的制度和思想背景下,工会的策略也能够形成各种不同的国家\劳工关系。如在战后统合主义的政治安排下,资本对劳工的结构权力就受到了民主政治的限制,对有组织劳工的政治包容使其结构性权力得到提升。因此,西尔弗说道:“如果联系性权力越来越重要,那么劳工运动的未来轨迹将会受到更大的政治背景的强烈影响,而他们也就变成了这一背景的一部分”。(44)这应验了葛兰西的说法,“工会运动就是一种政治运动”。(45) 虽然工会在欧洲层面上享有的结构性权力非常有限,但在欧洲社会领域中的联系性权力却在不断增长。实际上早在危机之前的2004-2006年,在针对“服务指令”的斗争中工会和社会运动就展示了大规模动员群众的能力,(46)“欧洲社会论坛”的召开也表明在欧洲层面上工会和社会运动间的合作正在加强。2007年,ETUC在塞维利亚大会上采取了更加自信的姿态,宣布自己要发起“进攻”。ETUC秘书长约翰·蒙克斯(John Monks)甚至直称,“现在出现了工会反击的条件”。(47) 2008年,反击的条件如期而至。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盟阶级关系的紧张,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到2013年5月,欧洲失业总人数已达到1922万,失业率为12.1%。(48)2008年危机爆发之初,公民社会团体和工会组织联合举行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反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危机管理政策,但在2009年之前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罢工浪潮。然而自2010年欧盟机构大范围推行紧缩措施以后,工人尤其是公共部门职员的罢工活动开始大量涌现。在希腊、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荷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英国等国都爆发了总罢工。2010年9月,在布鲁塞尔爆发了10万群众参加的示威游行,2011年9月在弗罗茨瓦夫(Wroclaw)的游行群众达到5万人。虽然此刻尚未出现欧洲总罢工的统一协调组织,但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推动下,工会在动员和倡议方面的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以ETUC为代表的欧盟层面的工会组织感到有必要挺身而出,代表工人和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并调整自身的政策定位。 从近年来ETUC的官方文件和行动实践来看,其斗争策略发生了许多变化,改变了以往对欧盟委员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味迁就的态度,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维护工人的经济权利,反对一味地压制工资,反对财政部门和欧盟委员会的紧缩政策,将斗争矛头直指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金融化的“赌场”资本主义。 2011年5月,ETUC在雅典召开代表大会,强烈反对紧缩政策,呼吁实施“社会和绿色新政”,在欧元区危机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支持由欧洲央行(ECB)发行欧元债券,支持低利率政策,努力探索协调集体谈判的可能性。(49)工资问题是另一个大问题。著名工运学者佩德里纳(Vasco Pedrina)指出,“欧元区附加协定”(Euro Plus Pact)中的“工资紧身衣”和扩大救市计划对作为欧盟社会模式支柱之一的“社会伙伴自主权”提出了挑战。(50)ETUC强烈批评欧洲议会2011年9月提出的经济治理“六部立法”(Six-Pact),认为这些立法可能会引发全欧洲范围内工资的向下竞争,导致财政紧缩政策失衡,抑制经济活动。 第二,不满于欧盟制度机构对工会行动的限制,将斗争矛头直指欧盟治理机构及其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创议。 厄恩(Roland Erne)相信,欧盟工会完全有能力将欧盟的技术治理重新引上政治的轨道。(51)随着危机的加深,ETUC指责欧盟委员会在促进社会对话方面不积极。霍夫曼(Hoffman)批评道,该委员会“在相当程度上无视立法措施和志愿原则”;在修改“欧洲工作理事会指令”时,还打破了社会对话的既定程序。(52)为了对欧盟委员会施加压力,ETUC决定拒绝以138条款规定的社会伙伴身份与之开启正式的官方谈判,但由于修改“欧洲工作理事会指令”的最后文件必须经由欧盟层面的工会和雇主谈判才能最终加以确定,ETUC从大局着眼做出了让步,但提出了“欧洲公民倡议”,以此作为对欧盟委员会施压的新途径,动员底层工会会员反对欧盟委员会的工资抑制政策。 ETUC总干事西格尔(Bernadette Ségol)还批评了欧盟委员会对通缩风险的低估,认为“欧洲需要采取新的路径。投资计划和量化宽松会有帮助,但投资水平需要提高,改革需要关注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和改善技能”,“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必须成为首要目标。失业远非主要是‘结构性的’,紧缩和工资改革使失业更加严峻”。(53)西格尔认为,希腊的局势也是整个欧洲的机会,有助于重新评估危机以来欧盟经济社会政策的缺陷并找到新的路径。他说,“紧缩和结构性改革并没有解决希腊等国面临的问题。相反,它们已经增加了新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旧的。公民已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税收征管和腐败并没有得到改善。……只有以ETUC提出的投资建议。10年以上2%的GDP,才能创造希腊和整个欧洲迫切需要的增长和就业机会”。他说,“必须给予希腊新政府充足的时间实施新政策,这对欧洲民主至关重要,希腊人民明确表达了结束紧缩政策的愿望”。(54)ETUC对欧盟治理机构的抵制在更大层面上涉及欧洲政治形态和有组织劳工关系的战略选择,并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欧盟的社会领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工会提供机会结构。 尽管策略更加强硬,手段更为激进,但ETUC的行动与纲领并没有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合作框架,更没有对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ETUC依然重视利用旧有框架下的社会伙伴关系发挥影响,力争团结商业机构和欧盟机构,将其视为合作伙伴,并希望以二战以后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处理方式防止金融危机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 2009年5月,ETUC在《巴黎宣言》中对欧盟危机管理政策做出了回应,要求通过增加投资、加强福利体系、增加社会包容、更有力的集体谈判体系和工人权利、对金融业实行有数管理来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55)除了对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表达工会的诉求之外,该宣言还号召商界人士参与社会对话,协助解决危机。工会希望在欧盟层面上制定有利于工人的法案,至少能与工人合作。但这种立场无力彻底解决欧洲工人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无法促使欧盟治理机构真正改变立场和政策。 2010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决定成立以范龙佩为首的“经济治理工作组”,就规范财政纪律及强化经济治理等提出一揽子方案,如签订了“欧元附加协定”(Euro Plus Pact),建立了“欧洲学期”机制,签署了“财政契约”,并开始实施“欧洲2020战略”(Europe 2020 Strategy)。起初工会和大多数左派观察家都认为加强欧盟层面的宏观经济协调很有必要,但“欧洲2020战略”和“财政契约”的出台随即被解读为对工人的攻击,目的是以工资压制政策代替货币贬值。欧洲工会协会(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ETUI)总干事菲利普·普歇(Philippe Pochet)指出,《里斯本条约》以来的欧盟治理思想是希望由欧洲理事会来维护欧洲公众的利益,但“欧洲2020战略”的潜台词却是将财长们置于中心位置,不论在国内还是欧洲层面都是如此。“财长们才是该战略的真正协调者”。(56)这些后续政策没有提供足够的措施缓解工人因结构调整而增加的负担,有悖于欧盟委员会所谓的聪慧、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 上述经济治理方案严重挫伤了工会的期望,引发了普遍的抗议,也使ETUC对欧盟的政策前景感到失望,并担心工会的要求得不到考虑,甚至连过去的工作成果,那些较为常见的对话、磋商和妥协也会被取消。2014年12月,欧元区通胀率再度跌至负值,这在2009年危机以来还是第一次。面对严重的通缩,ETUC执行委员会于2014年12月3日发布了《欧洲经济治理评估》。《评估》认为,当今欧洲经济治理机构把财政稳定(削减公共赤字和公共部门债务)和成本竞争力(相互竞争削减工资)作为关键问题,而对“经济复苏、可持续增长、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社会凝聚力等目标”却漠然视之。《评估》认为,这会将“调整的全部重担落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最终会严重削弱工人对欧洲联盟的支持”。为此,ETUC呼吁采取以下措施:“外贸盈余国家必须部分地承担起单一货币的再平衡负担”;限制稳定与增长公约对私营部门承担公共债务融资的负面影响;“将欧元区作为整体看待”,为避免通缩要求“通胀率低于但接近2%”;将“促进就业,改善和协调生活和工作条件,并促进社会公正和保护”等社会内容置于欧洲经济治理的核心;在国家和欧盟层面的机制中使社会伙伴发挥更大作用。(57) 从工会的各类政策主张来看,一方面,核心竞争力、工资构成等问题越来越受到那些工会无法施加影响的领域的限制,工会的政策运作空间受到了挤压;另一方面,欧洲层面的工会与公民社会组织和学术界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合作,系统全面地获得了金融市场和银行监管的专业知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工会已经能够在认知领域与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方案展开论战,认知领域成了ETUC的斗争新舞台。 四、欧盟工会参与欧盟治理的前景 关于欧盟工会参与欧盟治理的地位和前途,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看法。乐观主义者期待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能够促成跨国劳工团结的出现,而悲观主义者则对劳工能否发展成为一种跨国社会行为体表示怀疑。(58) 从乐观方面看,的确存在着许多积极的迹象。首先,如前文所述,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层面的工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斗争策略,反对欧盟委员会的各种极端政策,并积极扩大与其他公民社会团体的合作,大大提高了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组织动员能力;其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各种应对措施,加大了成员国之间和不同成员国国家工会之间的政策分歧。以ETUC为代表的欧盟工会介于成员国国家工会和欧盟机构之间,在协调不同地区的利益乃至提出共同诉求方面愈发重要;第三,欧洲议会选举出现了有利于工会的新契机。布鲁塞尔工会运动政策顾问科瓦尔斯基(Wolfgang Kowalsky)认为,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具有更强的“欧洲”色彩,欧盟治理机构已经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权力格局,欧洲议会成为大赢家,工会支持欧盟理事会向欧洲议会转交权力。(59)在这种情况下,ETUC既不可能退出欧盟层面的政治活动,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过分依赖欧盟委员会。 从悲观方面看,问题也相当严重。包括ETUC在内的欧洲跨国工会依然存在着许多组织缺陷和思想利益分歧。首先,参与欧盟治理的跨国工会行为体来源多样、组织松散。仅ETUC就由37个国家的88个工会组成,代表6千多万欧洲工人。此外在行业和公司层面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跨国劳工组织,如行业层面的“欧洲产业联合会”(European Industry Federations,EIF)、“欧洲金属工人联合会”(European Metalworker Federation,EMF)、“欧洲公共服务工会联合会”(European Federation of Public Service Unions,EPSU),公司层面的欧洲工人委员会(European works councils,EWCs)等。其次,由于来源国的生产结构基础差异极大,各国工会的思想和政治取向各不相同。例如北方国家的工会强烈要求扩大就业保障等社会福利方面的内容,而南欧和东欧新成员国的工会则更偏爱经济民族主义策略,不太热衷欧盟层面上劳工标准的协调。在出口导向和跨国行业中的劳工更有可能参与跨国活动,因而支持某些欧洲层面的政策倡议。而受到进口竞争的企业劳工则更有可能抵制新自由主义和欧洲一体化。此外,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国家身份也导致众多分歧,很难形成共同的利益联盟。(60)第三,在欧盟工会的代表制结构中还形成了不同于各成员国底层工人的“欧盟工会精英”,即国际工会官僚中的“工人贵族”。欧盟层面的工会和国家层面的工会之间也往往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例如前者支持欧洲一体化,后者反对经济和福利重组。第四,跨国团结问题越来越重要了。“欧盟2020战略”的竞争条款目前虽然关注的是“聪慧、包容和可持续性的”增长,但却潜在地加剧了欧盟内部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工人内部的竞争。欧盟工会将不得不小心避免地区竞争议程将欧盟工会运动碎片化,并对移民工人和跨国团结造成负面影响。当前,欧盟机构实施的紧缩计划极易造成各国国内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斗争也极易引发阶级冲突。如许多国家的工会批评ETUC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斗争中不够积极。 尽管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悲观或乐观的理由,但对于欧盟工会的发展前景却不能过于乐观或悲观。通过探讨欧盟层面的有组织劳工在欧盟治理中的地位变化,本文认为虽然欧盟治理机构为工会提供的制度空间非常有限,但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的治理理念和策略的形成提供了重要途径,使工会得以利用其联系性权力提高对欧盟机构的影响力。 金融危机使欧洲资本放弃了很多阶级妥协方面的内容,而这曾经是支撑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然而,就目前而言,欧盟工会尚不具备超越欧盟制度界限的力量,而且很可能依然会留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社会力量大联盟之内。不能期望工会提出替代欧盟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新方案,而应该在社会斗争的具体情况下理解其施动力量。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影响下,ETUC和欧盟机构很可能仍将彼此视为重要伙伴。 就斗争策略而言,以ETUC为代表的欧盟工会正在从以往被动地适应欧洲机构转向有选择性地加以反对,并调整了自身的定位,逐渐摆脱欧盟机构内游说组织的身份,与NGO等其他社会力量建立联盟,共同提出对欧盟治理的诉求。近年来的事态发展表明,ETUC的动员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危机爆发后,ETUC在“欧洲行动日”活动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能力。在21世纪初,ETUC的动员口号还是“更欧洲化”,而到了2011年,ETUC雅典大会的主题就发展成“为社会的欧洲而动员”,其话语减少了新自由主义妥协的色彩并增加了对整个社会领域的关注。这表明,虽然目前ETUC还不大可能演变成一个完全成熟的社会运动组织,但其政治要求和行动策略已经不限于工作场所,而是转而关注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联盟,不仅在生产方面,也在更大范围的环境和社会领域讨论有关剥削的根本问题。工会与公民社会组织的频繁互动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欧盟层面开展更广泛的动员非常必要,这无疑有助于克服欧洲劳工运动内部存在的种种狭隘的利益分歧,将欧洲工人汇入更广阔的欧洲公民社会之中。 注释: ①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hort-term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Outlook and Key Challenges in G20 Countries,May 2012,Geneva and Paris,p.1. ②[美]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王逸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53页。 ③Andrew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Oxford:Basil Blackwell Press,1987,p.167. ④C.Murphy and R.Tooze,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Lynne Rienner,1991,p.70.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432页。 ⑥E.M.Wood,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0-21. ⑦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Chichest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1. ⑧Bob 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99. ⑨Stephen Gill,Gramsci,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64. ⑩Robert Cox,"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Millennium,Vol.12,1983,pp.162-175. (1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12)[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13)Bob 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 (14)[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44页。 (15)Bob 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p.268. (16)Ibid.,pp.147-148. (17)Bob Jessop,State Power:A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p.37. (1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2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20)G.Taylor and A.Mathers,"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A European Labour Movement in the Making?",Capital and Class,Vol.78,2002,pp.39-69. (21)H.J.Bielin and T.Schulten,"Competitive Reatructuring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in Alan W.Cafruny and Magnus Ryner eds.,A Ruined Fortress? Neoliberal Hegemony and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Rowman & Littlefiald Publishers,INC.,2003,p.232. (22)Dorothee Bohle,"Neoliberal Hegemony,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the Terms of the EU's Eastward Expansion",Capital and Class,Spring 2006,p,64. (23)张海洋:《欧盟利益集团与欧盟决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6页。 (24)Belen Balanya et al.,Europe Inc.:Regional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Power,London:Pluto Press,2000. (25)[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98页。 (26)H.J.Bieling,"Europe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in A.Bieler and A.D.Morton eds.,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The Restructuring of European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algrave Press,2001,pp.93-114. (27)W.Sandholtz and J.Zysman,"1992:Recasting the European Bargain",World Politics,Vol.17,No.1,1989,pp.114-118. (28)S.Gill,"New Constitutionalism,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acifica Review,Vol.10,No.1,1998,pp.23-38. (29)Bastiaan van Apeldoorn,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the Struggle over European Integration,Routledge,2002. (30)A.Gramsci,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1921-1926),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8,p.167. (31)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32)H.J.Bieling and T.Schulten,"Competitive Restructuring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Corporatist Involvement and Beyond",in A.W.Cafruny and M.Ryner eds.,A Ruined Fortress? Neoliberal Hegemony and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p.237. (33)H.J.Bieling and T.Schulten,"Competitive Restructuring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Corporatist Involvement and Beyond". (34)郑春荣:“欧洲社会对话的新制度主义解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第75页。 (35)Robert W.Cox,"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2,No.2,1983,p.171. (36)Henk Overbeek,"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Ronen P alan ed.,Global Political Economy:Contemporary Theories,London:Routledge,2000,p.176. (37)郑春荣:“欧洲社会对话的新制度主义解析”,第78页。 (38)M.Kovacs,"How do Trade Unions Interact with the European Parliament?",ETUI Working Paper 02/2008,2008. (39)G.Taylor,A.Mathers and M.Upchurch,"Beyond the Chains that Bind:The Political Crisis of Unions in Western Europe",Labor History,Vol.52,No.3,2011,pp.287-305. (40)B.Bercusson,"The Trade Union Movement and the European Union:Judgment Day",European Law Journal,Vol.13,No.3,2007,pp.279-308. (41)I.Bruff and L.Horn,"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Crisis",Competition and Change,Vol.16,No.3,2012,p.165. (4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33页。 (43)B.J.Silver,Forces of Labor: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3-16. (44)Ibid.,p.173. (45)A.Gramsci,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1921-1926),p.77. (46)A.Bieler,"Co-option or Resistance? Trade Unions and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in Europe",Capital and Class,Vol.93,2007,pp.111-124. (47)J.Monks,"Locusts Versus Labour:Handling the New Capitalism",Keynote Speech Harvard University,16 April 2008. (48)“欧洲失业率再创新高,失业总人数已达1922万”,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7/02/content_29298247.htm,2015年8月14日访问。 (49)V.Glassner and P.Pochet,"Why Trade Unions Seek to Coordinate Wage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Eurozone: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ETUI Working Paper,No.3,2011. (50)V.Pedrina,"The Euro Crisis and 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Movement",Global Labour Column,No.71,September,2011, http://www.global-labour-university.org/fileadmin/GLU_Column/papers/no_71_Pedrina.pdf,last acceased on 14 August 2015. (51)R.Erne,European Unions-Labour's Quest for a Transnational Democracy,Cornell: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 (52)J.Hoffmann,R.Hoffmann and K.Llanwarne,"Prospects for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rade Unions in the Midst of Modernisation,Europeanisation and Globalization",Transfer,Vol.15,No.3-4,2009,p.404. (53)Bernadette Ségol,"EC Economic Forecast Optimistic:Underestimates Deflation Risk",05.02.2015,http://www.etuc.org/press/ec-economic-forecast-optimistic-underestimates-deflation-risk#.VPq8NyxCQOU,last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5. (54)Bernadette Ségol,"Greece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all Europe",05.02.2015,http://www.etuc.org/press/greece-represents-opportunity-alt-europe#.VPrB8SxCQOV,last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5. (55)ETUC,"Fight the Crisis:Put People First",May 2009,https://www.etuc.org/fight-crisis-put-people-first,last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5. (56)P.Pochct,What's wrong with EU2020? ETUI Policy Brief:Social Policy,02/2010,http://www.etui.org/Publications2/Policy-Briefs/European-Social-Policy/What-s-wrong-with-EU2020,last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5. (57)ETUC,"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Governance(ETUC Position)",http://www.etuc.org/node/12535#.VRNUJywxjB8,last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5. (58)M.Burawoy,"From Polanyi to Pollyanna: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r Studies",Global Labour Journal,Vol.1,No.2,2010,p.311. (59)Wolfgang Kowalsky,"Is Europe Back On Track?",Social Europe,16 July 2014,http://www.socialeurope.eu/2014/07/europe-back-track/,last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5. (60)K.Gajewska,"The Emergence of a European Labour Protest Movement?",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Vol.14,No.1,2008,pp.108-109.标签:欧盟委员会论文; 欧洲一体化论文; 英国退出欧盟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企业工会论文; 欧盟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