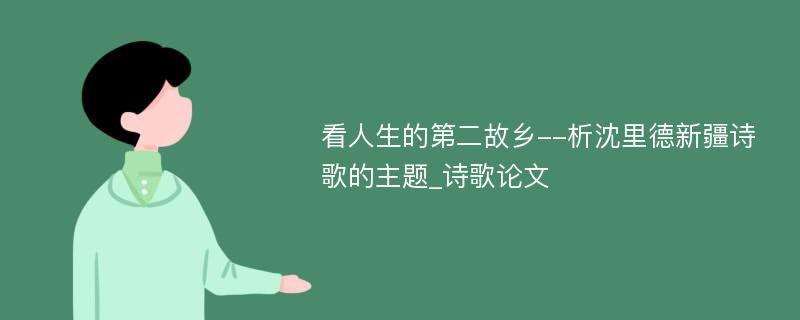
守望生命中的第二故乡——探析沈苇诗歌的新疆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新疆论文,诗歌论文,第二故乡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苇从事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日益商业化、市场化,诗歌作为一种纯文学形式,其创作已逐渐被边缘化。而诗人沈苇却一直用他的耐心、恒心、爱心、诚心,坚守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用纯美的诗歌表达着对新疆的专注和挚爱。这份无畏而专注的书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诗人是“地域的孩子”,也是“地域的作品”。当诗人置身于一个色彩浓郁的地域,尤其在新疆这片风情独特的地方时,稍不留神就会误入“地域性”这一迷人的陷阱。或者他们并没有对“地域性资源”进行贩卖,也会被人误解成“地域性”的二道贩子。对沈苇这个“异乡人”来说,要摆脱这种尴尬和无奈更是难上加难。十多年来,行走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沈苇,一直都把“新疆主题”当作其诗歌创作的源头活水和内在的精神原动力,但他的诗歌没有落入贩卖“地域性资源”的俗套,而是成为展示魅力新疆过往与现在的标志性作品。1995年,他的首部诗集《在瞬间的逗留》一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于1998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在新时期西部诗歌的画廊中,沈苇的《在瞬间的逗留》为我们展开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沈苇生长在江南水乡,工作在大西北,二者地域风貌与人文景观的巨大反差,给他以西部生活的新视角。雄浑的境界与灵动的诗魂、粗粝的意象与细腻的情愫、富有弹性的语言与深邃的思考,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沈苇诗歌的独特景观。诗人对语言有特殊的敏感,熟练地把握了现代汉语的意象手法,其话语方式既有深厚的民族底蕴,又有新鲜的时代感。诗人无意对西部景物做具象而铺陈的描述,而是着眼于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解剖,充分展示了抒情主人公面对阔大雄奇的西部自然景色而引发的对宇宙奥秘和人生真谛的思考。”[1]鲁迅文学奖评委会给予的这一评语,肯定和总结了沈苇的诗,特别是他的关于新疆主题的诗歌创作。然而,沈苇诗歌中的新疆究竟具有什么特质,新疆主题又是如何在他的诗歌中逐渐成长和表现的,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对“新边塞诗”的突破与超越
“新边塞诗”是由“边塞诗”延伸而来的一个概念,它相对于古典的边塞诗而言,反映了80年代新的边塞生活和新的边塞风物,并由此表现出边塞人的新情感和新的思想意识;在艺术思想和艺术追求上也呈现出新的审美倾向。上世纪50年代,“新边塞诗”曾一度繁荣,而“新边塞诗”作为一个概念,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提出来。作为一种清新的诗歌样式,“新边塞诗”深受人们的欢迎,它给人们带去了强烈的阅读快感和视觉享受,甚至震撼了西北乃至中国文坛。“新边塞诗”既具有独特而深沉的地域性,又极富当代性色彩。它的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源自其所具有的不同于别类诗歌的特质。在内容上,它摆脱了表层性描写的束缚,以一种隐含的、意向化的传达手段,表现对西部风情和生命意识的抒写,对现代文明的礼赞与呼唤,对大自然的感应和契合;在艺术上,它做到了意与象的交融,心绪与画面的叠合,使诗的深层思想寓意活跃在写实与象征之间,从而实现了对边塞时空和题材自身的超越。
正是由于“新边塞诗”这股强劲的冲击力和豪放激越、粗犷强悍的震撼力,使得“新边塞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坛独树一帜,一时间,周涛、杨牧、昌耀等“新边塞诗”创作的代表人物,频频出现在文学报刊上。遗憾的是“新边塞诗”一时的风光,如同昙花一现,最终归于平淡和沉寂。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份沉寂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上世纪80年代末或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西部诗人,如杨梓、金玮等,秉承传统,创新形式,以自己独特的感知方式和表现手法呈现出别样的新疆乃至西部,重新获得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诗人沈苇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位佼佼者,但他的诗歌创作又区别于杨梓、金玮等人,其对异域风情的书写和展现,因个性而极具魅力。
(一)独特的个人化写作
“新边塞诗”,离不开“新边塞诗群”。“新边塞诗”来自“新边塞诗群”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虽然诗人们在创作的道路上,竭尽去展现各自的特色,但作为一个群体,很多时候又不可避免地落入到了群体意识的窠臼,共同的创作风格与美学追求成为他们从事创作的囚笼,因而,对多样性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文体价值。诗人沈苇在意识到这种局限之后,极力地倡导个人化诗歌写作。他一直强调“诗坛虚假的集体主义是迷信和惰性造成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写作值得用毕生的精力去追求”(沈苇《高处的深渊》)[2]。在他有关新疆主题的诗歌作品中,他以特有的视角去审视新疆,极力避免触及到人们耳熟能详的字眼,诸如天山、塔克拉玛干、准噶尔、塔里木等,而是更多地关注新疆这一地域里日常的风俗和民间风情。沈苇在对这些风俗和风情的书写中,努力突破单纯风景或地域性特色描写的局限,尝试着用或刚劲或柔软的文字去宣泄诗人特有的个体感受和生命体验。诗人在《眺望》中曾写道:“我扶着闪电的栏杆/苍生啊,在我躯体的辽远国土上/众多嘴巴发出咆哮和呻吟/出来吧,卡在喉咙里的雷声/迅速滚向一个深渊……”,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新疆的地貌和呼啸声,更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在宣泄强烈的个人化情感。当然,关于这种“个人化”写作的诗歌还有很多,又如:
“送走金银花之夏……要有一种疯狂点燃远方,或者必须爱上寒风的刀和鞭……”[3]
——《运往冬天》
“峡谷中的村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村庄一年年缩小,墓地一天天变大……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忙碌/当他们抬头时,就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
——《吐峪沟》
沈苇的这些诗歌,没有过多的修饰,却在朴素明净中彰显一种芬芳,一种希望,一种荡气回肠的个人化、个性化的人生感悟。
(二)直视人类基本的主题
在审美追求上,从事“新边塞诗”创作的诗人们,大都关注新疆乃至西部这片神奇土地上极易找到且又特殊的标志性意象,如大漠、戈壁、冰山、雪峰、黄沙、风暴、长河、落日、草原、骆驼、古战场等等,而诗人沈苇却善于捕捉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事与物,更多的去写那些诸如“红辣子和裂口的黄泥小屋”(红辣子、裂口的黄泥小屋是诗人诗歌中两个较为特殊且有代表性的意象)给自己带来的人生感悟,如《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滋泥泉子》、《东方守墓人》等等。
同时,沈苇特别关注新疆这一大背景下,人性的真、善、美,人类的爱与信仰、悲恨与死亡、生命与存在,人类家园乃至整个世界的奥秘与意义。“我想写出这样的诗:它应该包含了宇宙之密与尘世之火、天空的上升与大地的沉沦、个体的感动与普遍的颤栗、灵的高翔与肉的低吟……它有一个梦想:包括全部的地狱和天堂!”,“这样的诗直接面对阿莱克桑德所说的人类基本主题:爱,悲痛,恨和死亡,面对人性中一切原始的本质的事物说话,并且正如罗丹所言:要点是感动,是爱,是希望、颤栗、生活……它细小的核来自光辉的源头,成长、铺展、扩大,用无边无际的安慰将我们和未来笼罩。它是精神的庆典,语言的顶峰,经验与激情的女儿。”(沈苇《高处的深渊》)[4]又如:
“这是开都河畔我与蚂蚁共度的一个下午/太阳向每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
——《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
“人很小,太阳很大/当我向着塔克拉玛干沙漠靠近……那么,我会真实感受到灵魂的升腾/像所有挽留中的生命那样/死亡并不是真实的”
——《旅途》
“我支付着青春,爱,信仰,忧伤/为了生命中昂贵的娱乐”
——《娱乐》
“孩子,这个冬天的大雪无法覆盖大地的悲恸/这个冬天的寒风吹向众人骨头里的震颤/失血的天空布满冒烟的亡魂/和因恐惧而瞪大的眼睛/多少撕心裂肺的母亲在痛哭……当活着的人一如既往活着/怀念、哀悼、落泪,被遗忘笼罩/请问,死者是否宽恕了生者?”
——《哀歌:悼念“12.8”克拉玛依特大火灾中死难的学生》
沈苇总是带着一种冷静的眼光,以旁观者的姿态去审视“新边塞诗”。他不去妄言历史感和责任感,只是利用朴素而平凡的文字去揭开在外人看来蒙在“新疆”脸上的那层神秘面纱,从而向世人展示真实的新疆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热情而朴实的人们。因此,沈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人类的基本主题,从而使得笔下的新疆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可爱。而他有关新疆主题的诗歌,也有了一种因包容而广阔,因透明而纯粹的思想和气质,正如邹汉明在《攀登悬崖的灵魂》中所说:“沈苇的贡献在于为当代中国诗歌引入了一股亲切的异域气味,这种气味帮助他确立了诗歌的个性,并幸福地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声音。”[5]沈苇的诗歌,不再是一个被诗人随意填充的躯壳,它已经成为了诗人心灵的舞蹈,他被一种生命的本能驱使,将精神和肉体同时置于新疆,去经历痛苦,去遭受折磨,从而达到内省的深度与广度,实现自我人格的重塑与精神旨向的建构。
二、诗人之路与第二故乡
诗人沈苇笔下的新疆真实而魅力无穷,这和他个人对新疆那份炙热的爱,密不可分。沈苇自己也曾说:“自从10年前自我放逐来到新疆,新疆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浙江,也热爱新疆,我现在已是半个南方人和半个西北人的混血儿。我喜欢自己身上体现一种杂色和混血,它是一种拓展,一种包容。我想把南方的细腻、敏感、美与西部的辽阔、粗粝、力量结合起来,成为一名既不同于南方诗人又与西部诗人有所区别的诗人。”[6]这也正如历代诗人几乎都有个梦想,那就是希望寻找到与自己的内心相匹配的第二故乡,只不过这一“故乡”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家乡,而是诗人之魂的栖息地。被迫离家,漂泊异乡,近乎自虐式的偏执,也似乎是诗人一种无法超越的宿命。要想真实而深刻地认知自己和曾经的那片故土,也只有远离故土,独步第二故乡,才能真正检验个人生命的强度、韧性和承载力。诗人沈苇从吴越之地来到大漠深处,经受了二十多年新疆生活的磨练,终于在现实与诗歌的纠结中找到了心灵的故乡。过程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正是诗人的这份苦苦追寻和孜孜不倦,才使得他笔下的魅力新疆多了一份另类的特质。
(一)他乡的诗人之路
不可否认,面对“异乡人”,人们起初的情感是趋于保守和充满戒心。沈苇初来新疆,就深切体会到了这种孤立和陌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让他举步维艰,与生俱来的江南灵气和现实中新疆粗犷豪迈间的杂糅与冲突,始终撕扯着他的灵与肉,使他饱受精神苦闷与肉体痛苦的双重折磨。两个声音的争吵充斥于他的诗歌空间,这是冰与火、死与生、潮湿与干旱、狭窄与辽阔、葱郁与荒芜、时空与历史的纠缠,也是诗人沈苇在融入异域之前所经历的内心和现实的双重考验,在《旅途》和《故土》中诗人沈苇就将他身在异域最初的迷茫与随后的迎头融入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岁月的增进,独步异乡的沈苇少了几分儒雅的秀气,多了几分浑厚豪迈的大气,执着在融入“第二故乡”的征途中,沈苇的诗人之路有了别样的景致:
“当我向着塔克拉玛干沙漠靠近/感到自己正成为沙砾的一分子/而太阳是天空惟一的皇帝/这使我丧失骄傲和自信/仿佛我是来清点各地渺茫的灵魂”
——《旅途》
“这是我离开故土的第二个冬天/月色照旧,风景照旧/我的马车在寒霜里哆嗦着前进/………但我知道:沦落之处便是再生之地……一个声音说:死了/另一个声音紧接着压倒了这个声音:获救了!”
——《故土》
如今,回过头来看沈苇这个时期的诗歌,它们的与众不同,它们的不可替代,正是得益于诗人所经历的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纠葛与交融,得益于诗人那番艰难的融入与追寻。身在异域的沈苇,用真诚和耐心倾听着来自异域文化的声声呼唤,在诗人之路上他选择了坚守。由此,沈苇把对新疆的那份深沉而真切的体验上升为一种知识上、灵魂上的领悟和修辞上、意象上多元的诗意表达。在《混血的城》中诗人写道:“让我写写这座混血的城/整整八年,它培养我的忍耐、我的边疆气质/整整八年,夏天用火,冬天用冰/以两种方式重塑我的心灵……它远离大海,远离浪涛拍岸/另一种浪涛拍打我——/热的血、浓的血、清洁的血、泥泞的血/在大十字和小十字相遇,融会成/同一种赤诚的血……整整八年,我,一个异乡人,爱着/这混血的城/我的双脚长出了一点根,而且光/时常高过鹰的翅膀/高过博格达峰耀眼的雪冠……”异域给诗人所带来的空前包容和巨大震撼,把诗人从内心的挣扎、纠结引向自我救赎,从而提升了“异乡人”的境界和层次。
关于这首诗,作者曾说是写给乌鲁木齐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已经从一个外来者逐渐融入到了这座混血域,“异乡人”也终于进入了他乡。当然,在这里,诗人沈苇并不是过客式的走马观花,为此他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八年来他不仅是以“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更是以“心”来学习地方性知识,感受地方性体验,从精神上生成与之密切关联的“脐带”。
(二)混血、杂色、综合的诗歌之旅
沈苇曾这样表达过自己的诗歌抱负:“抒情诗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而应该有更大包容的考虑。混血的诗正是一种杂色、综合、立体的抒情诗,它是我的诗学之梦。”[7]也正是在这个诗学之梦的感召下,融入新疆的沈苇,在他关于新疆主题的诗歌中出现了多重混血:“第一重混血——地理的混血:在江南与西域之间;第二重混血——文化和文明混血:江南风情、西部文明及中亚诸文明的汇通;第三重混血——诗歌混血:在西方现代诗歌中与中亚诗歌文化的双重影响下”[8]。然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建立在对多元文明和多元诗学深刻认识上的“混血的诗”不仅仅是文明的地图和文化的展示,在丰富的文明和文化中也揭示了一些基本的东西,即基本的人性和基本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这些诗歌又集江南丰富、滋润、细腻的血肉与新疆开阔、明朗、包容的骨架于一身,读起来给人一种既朴实清俊又沉稳坚实的感觉,而且在清新中又不乏沉雄的大气和沁人肺腑的启示与哲思。
“你眺望西湖,我谈论塔克拉玛干/仿佛被地理和气候拆散的一对/执手相见,却依稀难认/我愿意掉进地域在我身上做成的巨大裂缝……一种放肆的美便溢出波光涟漪的西湖”
——《杭州,一个故园》
“波斯王宫,烤肉与美酒,艳舞与蛇/东方的污秽笼罩一层淡淡辉光……一千年过去,打开蒙尘的残卷一看/他的情人是一枚青色的无花果/一碗羊奶中飘浮的月亮”
——《嘴唇以上的歌》
在这两首诗歌中,沈苇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与生俱来的江南灵气和现实中新疆的博大,巧妙地杂糅到一起,新疆文化、中亚文化和西方文化又与无形中相互汇通,充分调动了诗人的思维,展示了诗歌世界中杂色、混血、综合之后的丰腴之美。
(三)诗歌在“第二故乡”成长
沈苇来到新疆为的是寻找到能检阅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的第二故乡,而且这种理想中的第二故乡不仅仅是他安居乐业的世界,更是他心灵的故乡。二十几年来,沈苇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走过新疆的100多个市县,在了解新疆这个亚洲腹地的神奇、美丽、丰盛、华美与绚烂的同时,也懂得了新疆的特殊魅力在于它能不动声色地吸纳一切生活元素,并将多种生命味道幻化成自己的味道,把大地的气质转变成人群的气质,把艺术方向确定为生活方向。因此,二十几年的新疆生活和十几年的诗歌创作,让诗人沈苇洗尽了身上的铅华,留下了虔诚与谦卑。这种生命体验,这种寻找和成长的过程在他的诗歌中表现为:种族、宗教、风俗、历史、文化乃至时空的界限被模糊,一种在时间上深久发酵,并且经过岁月洗礼过的心灵开始喷发。此时诗人沈苇的内心也被这片神奇的土地照亮,他和故乡与新疆在诗歌中相互守望。守望过往,守望生命中的两个故乡。
“荒原显现他的肉身,如同显现一株牧草……杂色的羊群,婴儿的眼睛,瞳仁中渐渐放大一位综合的上帝……”
——《大融合》
“……人的生活,到处都是可以筑居的地方/正如浪子以离开的方式爱着故乡/从我身上放逐出去的无数个我/正以遥远的方式亲近隐秘的我”
——《有时我觉得》
二十几年的新疆生活,沈苇对生存有着复杂的体验,在诗歌的世界中,他捕捉到了这片神奇之地、神圣之地上由多种信仰和丰富的生命追求糅合在一起的新疆文化,也让自己的灵魂在苏醒后得到提升。
三、在第二故乡检验灵魂的强度和载力
沈苇曾在《自然之女》中说:“我,一名游子,一个自我放逐者/出门迎娶,热泪盈眶,已把异乡当作故乡”。[9]的确,在很多外来者的眼中,对这个地方再有感情也只能是异乡,但沈苇固执地守望着这片土地,因为他已经把新疆当成了生命中的第二故乡,而且也一直凭借着自己心音的驱使,用诗歌抒写生命的博大,努力在第二故乡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
(一)寻访新疆地区已消失的文明
作为古丝绸之路重地,新疆在历史上曾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间站,被称为宗教、民族、风俗、语言、文化的博物馆。然而在时间的冲刷下,新疆的有些传统和文明已经丧失,对已经逝去的东西,很多作家都会选择避而不谈,沈苇却把关注和描写这个地区所丧失的经验和传统以及复活这个地区已消失与碎片化的东西,当成是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韧力的最好方式,他的《新柔巴依》就是其中的体现:
“沙漠围向冰山上孤傲的雪莲花/飞禽与走兽守护深山中的珍宝,以及/无人见识得美。假如秘密的圭臬仍然存在/”芝麻开门“的钥匙是否依然有用”(《新柔巴依》)
“古道湮没,楼兰的蜃景灿烂一现/香喷喷的妃子何时告别了喀什噶尔/天鹅成群结队回到美丽的巴音郭楞,它们去过的世界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见”(《新柔巴依》,)
“从宇宙阳台往下看,死者与生者平起平坐/一次,在炎热的吐鲁番,我去参观博物馆/我对木乃伊少女说:醒醒!一旦她醒来/整个消失的过去都将高大地站在眼前”(《新柔巴依》)
对于诗人沈苇来说,他用他的想象复活新疆逝去的文明,把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过去和经验移入自身,从而取得“第二故乡”的认同,唤起了一种广阔而辽远的灵魂的升华,这样他就会更加努力地执着于米兰、楼兰等这些沙埋文明,终其一生去靠近和探寻这其中的悬疑之谜。正是因为如此,沈苇的诗歌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而也获得了在第二故乡品悟人生,获得真情和真知的机会。此后,沈苇又将这份经历注入诗歌之中,让自己的灵魂与情思在第二故乡升华
(二)灵魂在第二故乡被照亮和提升
诗人沈苇既然执着于复活这个地区已消失的文明,在这个过程当然少不了他与往昔情景的对话。然而对一个外来者来说,这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与过去对话,尤其是与神圣而又一无所知的文明在诗歌中对话,诗人沈苇的“渺小”和“无知”就会被无休止的放大。因此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他的态度都是敬畏甚至是谦卑的,在面对新疆的丰盛和灿烂时,他也总会俯下身,以一颗赤子之心,静静的欣赏、体验、感悟和书写。此时诗人沈苇那种超越自己的感觉也被彻底唤醒,每一个俯身都在无形中闪烁着诗意的火花:
“沙漠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心灵/人的心灵还配不上它的荒凉”
——《大融合》
“在山顶,谦卑将你放入一个深渊/在山顶,如在一个阿拉伯式的穹顶/在经历了一千零一夜之后,上帝离你并不遥远”
——《正午的忧伤》
虽然沈苇只是一个“外来者”,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比许多自称是新疆的人都更加虔诚地热爱着这片土地,他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着,用自己的心灵聆听着,虽然过程是艰辛的,但他也无时无刻体会着创作的快乐。因此,繁华落尽,一切归于平淡后,新疆已成为沈苇真正的精神的故乡,也是在第二故乡,他的灵魂更能得以被照亮和提升。
沈苇关于新疆主题的诗歌,从个人的感悟入手,进入到大范围的文化混血中,怀着敬畏之情描摹和书写新疆的宏伟、博大、丰美以及绚烂的历史、文化。他将人类的基本主题和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与新疆这个大背景相结合,在诗歌中穿越时空的隧道,捡拾文明的碎片。这在展示新疆多元文化历经不衰和繁华中的朴素的同时,也使诗人沈苇得以在第二故乡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