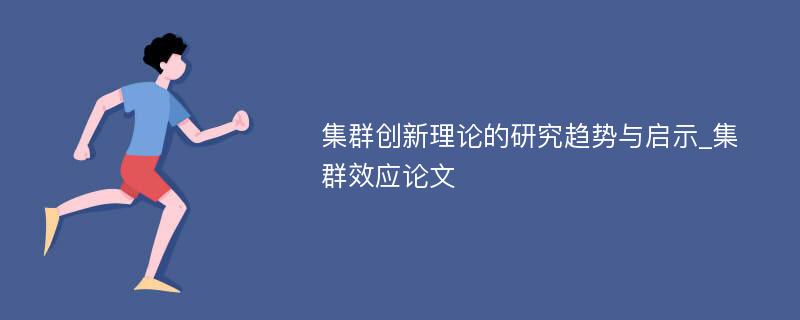
集群创新理论研究动态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集群论文,启示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6)05—0006—06
1 引言
随着经济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加速,创新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集群发展趋势。以美国的高技术园区发展为例,自1951年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高技术园区——斯坦福研究园(硅谷的前身)以来,50年代共建立了4 个高技术园区,60年代建立了7个高技术园区,70年代建立了12个高技术园区,80年代则建立了289个高技术园区[1]。在美国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和地区也纷纷建立了大量的高技术园区,如日本的筑波、印度的班加罗尔、芬兰的赫尔辛基、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台湾的新竹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Porter[2]、Asheim[3]、Todtling & Kaufmann[4] 等学者以大量的事实证明,现代企业的创新,在空间上表现为明显的集群分布特征;在方式上则由过去单个分散企业的独立行为甚至只是企业家的偏好,越来越倾向于众多企业聚集而采取集群行为,从而获得集群创新优势。我们把这种通过集群(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通过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或靠近)进行创新,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促进知识在集群内部创造、储存、转移和应用的各种活动而产生的创新聚集效应,获得集群创新优势的创新行为称作集群创新[5~8]。研究企业的集群创新是产业集群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课题。然而,关于集群创新的多数研究大都集中于集群创新环境[9,10]、集群创新政策[11~13]、集群创新地理空间[14,15]、集群创新网络[16~18] 等四个方面。本文将着重对集群创新动力机制、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集群创新绩效进行梳理、分析和比较、总结和评述,以期对集群创新理论的发展动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2 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关于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早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对集群创新的生成动力的认识和描述上。如Marshall从“外部经济”角度进行探讨,并认为专门人才、原材料供给、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是集聚创新的动力,但受研究目的与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Marshall没有将他的协同创新环境这一思路充分展开,挖掘聚集产生的非物质原因;Alfred Weber最早提出聚集经济的概念,他从区位因素角度进行分析,首次使用聚集因素,并认为大量集聚因素是集聚的动力。后来,Allen Young从“规模报酬理论”角度,Hoover从“集聚体”的规模效益角度,Krugman[19] 从规模递增收益角度等,探讨了不同的集群创新生成动力。Brown[20] 把这些生成动力归结为自发作用的市场力量,具有不稳定性和孤立性,而且有些动力因素随着集群创新的生长而具有不断消退的作用趋势,各种动力之间没有稳定的作用关系。
在集群创新动力研究方面,突出的转变是从对生成动力的辨识、对属性和作用的分析发展到对动力生长、动力之间关系和作用机制的分析[10]。集群创新发展动力与生成动力相比具有更高层次的属性和更稳定的作用形式,集群创新正是在比较稳定的技术创新、非正规学习、合作竞争、知识共享和溢出、网络协作、区域品牌意识等驱动力的作用下得以发展并显示出强劲的竞争优势[21,22]。发展动力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它们一般具有相对固定的协调关系,有明显的作用规则。
一些学者认为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是地方化的知识创造以及企业和个人学习新技术、学习如何相互信任并共享信息。Saxenian[23] 在研究硅谷的发展时认为当地良好的社会交往氛围加快了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Enright[24] 认为知识外溢和熟练劳动力市场推动了集群创新的发展;Walz[25] 通过增长极理论和创新理论进行分析, 认为地方化的知识创造所推动的创新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Best[26] 认为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有四种:集中专业化、知识外溢、技术多样化和水平整合及再整合,它们依次对集群创新的发展产生作用,并形成循环状的稳定结构;魏守华[27] 对几种集群创新动力进行了整合: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图形的方式构造出集群创新的动力机制,并以浙江嵊州领带集群为例,对动力机制的作用进行了实证;Swann[28] 采用实例分析方法分别研究和比较了多个集群创新的发展情况,将集群创新的动力机制描绘成包括产业优势、新企业进入、企业孵化增长,以及气候、基础设施、文化资本等共同作用的正反馈系统。还有许多学者强调知识传播对集群创新的推动作用。Morgan & Nauwelaer[29] 认为除了传统的外部经济,知识网络、学习机制和社会资本也是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Pinch & Henry[30] 认为Krugman 所强调的历史偶然性和外部经济只是集群创新演进的外部原因,基于非贸易联系的知识传播才是根本原因;Baptasta[31]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 由紧密的个人联系和完备的企业网络、充分的企业间相互作用所促进的知识传播是集群创新发展的内在原因。从总体上看,上述的研究观点都是基于新古典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延伸。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透视集群创新动力机制是集群创新理论的新发展。Tichy[32] 借鉴佛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时间维度考察了集群创新的演进,并将集群创新生命周期划分成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 衰退阶段; Ahokangas & Herd[33] 认为集群创新的发展动力是企业群体在外界环境作用下的自发行为和集体选择过程,所以它也具备优胜劣汰、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具有自组织、自适应和协同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而不是无组织的混合体和堆积物;陈雪梅等[34] 借助生物学中描述不同种群共生现象的逻辑斯蒂模型来描述集群创新现象的动态演化过程,将处于集群动态演化过程中企业所经历的内生和外生变化典型地简化为企业的产出信号, 通过对企业产出变化的刻画来解释集群创新的发展机制。 另外,Brenner & Greif[35] 应用复杂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来研究集群创新动力机制,发现经济学在解释集群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不足,而复杂科学理论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他们应用复杂科学理论探讨了集群创新内的两个主要机制:促进集群创新超越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和集群的当地共生互动作用(symbiotic interactions);Chiles[36] 认为,集群创新不只具备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区位效应、创新能力、竞争优势等静态特征,它更是在独特的企业家精神作用下的复杂动态过程,集群规模的扩大、集群效应的发挥、 企业能力的提高等都可用涌现(emergence)来解释;马刚[37] 分别从涌现性的发生条件、机制、 规律以及判断依据等四方面来分析集群创新的动力机制,解释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非线性、动态性等复杂性质,并分析其功能演化规律。以上生物学和复杂科学的理论观点丰富了集群创新理论体系,并弥补了经济学在刻画集群创新动力机制动态作用过程方面的不足,为研究和把握集群创新动力机制及其作用规律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为培育集群创新动力机制并控制其演化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3 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的研究
早在1920年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就谈及了集群中的知识溢出与扩散创新机制及其对产业区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但是,基于知识在集群中流动的观点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还是近10年来的事。根据对“知识”概念的不同理解,至少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研究集群创新的扩散和溢出问题。
基于溢出与集体学习的视角。 以意大利的 Becattini、Deiottanti、Bellandi[38] 等学者为主要代表新马歇尔主义学派认为,通过溢出与劳动力转移,知识被认为在空气中自由扩散,并通过这种方式在集群内产生扩散创新能力。与新马歇尔主义主要关注集聚经济不同的是,经济地理学家更多的是关注地理与区位维度。不过,他们仍然倾向于将知识与技术的主要变化理解为通过非正式交流、客户/生产商关系、技能劳动力的转移、示范效应和企业衍生等途径引致的知识扩散机制的结果。正如Capello[17] 所描述的那样,“集体学习”是集群内代理商之间通过基于共同的规则和组织管理程序的交互作用机制而产生的知识积累与转移的动态过程。集群内经济代理商可以自由地、无成本地获取,而集群外代理商却难以获取。Lawson[39] 认为:合作、诚信、集体学习和不确定性的降低对于企业的创新和整个经济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Asheim[6] 和Maskell[40] 则强调地方集体学习对于避免集群锁定在某一特定技术轨迹,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马歇尔主义学派和经济地理学派把分析单位局限于地区层面,把企业的学习过程视为一种“黑箱”。另外,他们的观点高度依赖于地方知识溢出,但却不能清楚地提供知识溢出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联机制。在这个方面,“新创新经济”学派作了一些弥补。新创新经济学派作了大量的经验性分析以支持地方化溢出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41,42],运用“知识生产函数”作为分析工具,对知识溢出与创新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经验性研究[43]。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具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基础设施”(如私人和公共实验室)大学等地区,由于地区内知识溢出而产生较多的创新成果;地理邻近性对于集群创新的重要性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不同,创新与生产活动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阶段性的空间集聚。与此同时,Feldman[42] 研究表明,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地理范围的限制,但并不是说,在所有条件下地方化对于集群创新都重要。以上研究都未强调知识溢出机制以及知识溢出的地理层面的实现机制,因此,没有解释整个知识的扩散与溢出过程。
基于新熊彼特主义Ⅰ的视角。该视角最大的贡献是,认识到了隐性知识与编码化知识之间的区别,视企业为技术能力积累的主体,并且认为新知识的生成过程是互补性知识组合的结果,是地方化隐性知识和外部编码化知识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并不像标准的新古典理论认为的那样,所有知识都易于传递,知识流动不是无成本的,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代理商都能获取,因此不能视为一种公共产品[44]。特别是隐性知识具有高度异质性资产的特征,是很难模仿的,它不能在空气中自由地获取[45]。但Belussi & Gottardi[46] 研究表明,本地企业的地方化隐性知识的扩散、溢出与利用绝不是确保集群创新动态演变的充分条件,还必须有不同主体互补性知识的组合才能成功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强调地方知识系统与全球知识系统之间的关联性,是该视角的一大贡献。与外部知识源的联系不仅仅是克服技术锁定的有效方式,而且有利于维持集群创新的内生增长[47]。
基于新熊彼特主义Ⅱ的视角。该视角是一种隐性知识领域的深入视野。主要来源于Cowun、David & Foray[48] 等学者近年来的学术贡献。他们认为,每个企业需要使用地方化隐性知识来吸收外部编码化知识,然而,这两种知识之间的界限将随产业的不同以及编码化的激励水平的不同而变化。他们对于在有价值的知识传播中知识扩散的典型机制(如非正式交流、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地理邻近性)的效应产生了某些疑问。如,“经常被引用的面对面的交流只是使有关‘谁知道什么以及在哪里就业’的信息获取变得容易,而这些信息只是一种地方性公共产品”[49]。经验性研究表明,“现有企业的工程师团体与许多‘弱式关系’有联系,这些关系倾向于扩散有关新技术被采纳或模仿的信息和传说”。但是,那些关系看上去并没有承载许多对于有效创新所必需的技术信息。同样地,劳动力的流动可能不一定代表一种有价值的知识扩散和溢出模式,除非在企业之间移动的员工是高技能的劳动力,而且在离开企业之前获取了充足的技术能力,否则,一般劳动力的移动不会引致有价值的知识在集群内的扩散和溢出。
新熊彼特主义Ⅰ视角并没有放弃熊彼特主义Ⅱ的研究方法,但是,它对于运用正式交流和劳动力的移动作为集群内知识扩散的机制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某些质疑,在某种程度上讲,它在尝试着打开地区分析层次的知识扩散、溢出与集群创新的黑箱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
4 集群创新绩效研究
关于集群创新绩效问题,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综述文献,主要有以下观点:(1)集群创新绩效来自于集群成员之间的知识外溢作用。Baptasta[31] 通过英国1975~1982年248家企业的数据对集群是否更具创新性进行了研究,证明了集群通过专业化知识的普遍传播和溢出构成的外部性和专业化实现创新,从而对区域整体创新绩效有明显的促进。(2)集群创新绩效与集群的集体学习关系密切。Capello[17] 通过对特定集群企业的实证分析,得出集群学习与企业突破性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集群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3)集群创新绩效与拥有大量创新企业和集群内相关知识的积累联系紧密。Baptasta[31] 运用英国New castle大学的城市与地区发展研究中心(CURDS)1981年的调查资料,将科学技术的接纳时间作为随机变量,分析了集群对科技创新扩散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公司,在新科技的采纳时间上,呈现出显著差异。(4)集群创新绩效受集群环境的影响。包括受集群的创新文化、企业的创新能力、集群的创新组织、集群的创新模式、集群外部供应商和客户、集群企业竞争者、集群外部知识等环境因素。Lichtenstein[50] 通过运用企业孵化器模拟企业生态因素。目的在于通过试验获取,未来企业生存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和市场关系。(5)集群不是企业创新的充分条件,集群创新绩效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企业创新活动的持续性、更大范围的创新网络、NIS运作成效、企业竞争行为、企业环境压力、企业盈利能力、国家经济结构和制度等。(6)集群创新绩效是由于社会网络增进了信任和联系,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有利于隐含知识和敏感信息的传播,带来了技术创新的优势。Love & Roper[51] 以英国、德国与爱尔兰3个国家的制造业厂商为研究对象,发现网络关联效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显著超过区位效果,即产业集群中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直接,新技术的创造与扩散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仍需考虑到其他相关因素所构成的复杂网络,例如新技术获得的实际速度、特性、对经济体系的影响以及配套政策的拟定,皆与新技术的创造与扩散息息相关。综上所述,学者从集群学习、集群环境等方面对集群创新绩效进行了研究,对集群创新绩效问题研究做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贡献。我们认为,集群学习、集群环境、知识流动、知识外溢、企业间相互作用、企业行为等因素诚然是集群具有较好创新绩效的主要原因,但这些因素不是集群所独有的因素,其他企业组织也存在这些因素,因此集群强大的创新机制和优秀的创新绩效还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集群创新绩效来自于集群的社会网络。因此,集群不仅存在社会网络,还存在市场关系网络,社会网络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市场关系网络是集群产生强大创新机制和优秀创新绩效的更重要的原因。
5 对我国集群创新发展的启示
研究国外集群创新理论,不只是为了认识和探讨国外集群创新的发展情况,更重要的是借鉴国外经验教训,发展我国的集群创新理论,但由于制度、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国外的理论和研究对分析、理解中国集群创新理论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总有隔靴搔痒之感,难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现实。因此,在发展集群的过程中,急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集群创新理论。
5.1 构建良好的知识创新空间
事物之间在一个具体的场所发生作用,知识创造也不例外。野中郁次郎定义了一个“巴”的概念。“巴”是知识分享、创造和使用的背景环境。巴既指物理的场所,如办公室、饭桌以及其他商务场所,也指虚拟的空间如电话、电子邮件等,还包括精神空间如共享的经验、观念和理想等。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相互作用。个人的知识一旦置身于巴中,就能够被共享、更新和增强。野中郁次郎指出:与其说巴是一个容纳知识和容纳有知识的人的物理空间,不如说巴本身就是知识,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创造巴的过程。国外一些企业和研究机构特别注意鼓励这种员工之间的互动作用,除了聚餐、轮岗等制度外,甚至在建筑物的布局上,刻意留下一块公共的空间,便于不同部门员工相互沟通交流。硅谷的酒吧、公交车辆上、各种名目的聚会、日本公司员工下班之后的聚餐、同学聚会都是这种巴的表现。
大量的知识创新依赖于非正式组织的活动,这与生产线的运转依赖于体系内部严密的分工协作大不相同。企业及政府部门应该对非正式活动持积极鼓励的态度,而繁琐的登记程序、严格的审查制度必然削弱甚至扼制人们知识创新的内在动力。
5.2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行为无法新建一个集群,无法成为集群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集群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对市场机会的即时识别和高效利用。但是,我国的科技园区大都是以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以及劳动力价格优势来吸引企业进区而形成空间集聚的,由于这种聚集不是以企业间内在的产业关联为基础,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地区政策的差距逐渐缩小,这种地理上的聚集显得极为脆弱。在吸取国外集群创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集群创新起步阶段,政府部门的适当介入是必要的。除了举办培训研讨活动、出台一些政策措施加以引导以外,在起步阶段充当协调人角色非常必要,但政府介入的实际效果与社会接受能力有关。社会接受能力是企业研发能力、企业家精神和集体学习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是集群创新的物质基础;企业家精神是对承担创新风险的偏好,是集群创新的人文基础;集体学习能力是企业间互动学习与交流,是集群创新的社会基础。如果仅是集体学习能力缺乏,经过培训研讨和政策引导以及政府部门适当的协调,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一般就会合作交流。而当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不足时,政府的介入就非常必要。
5.3 加强地方公共机构的建设
集群不仅仅是同行业的企业的集聚,还包括相关联的服务机构的集聚。公共机构可以加强集群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市场的联系,促进企业间互助协作以及同业对话,如共同营销、共同设计、合作培训等,提高企业间合作的效率,还可以在提高信息、提供基础设施等方面提高政策质量,改善政府行为。我国在集群创新发展方面,应吸取国外集群创新发展经验,各地应积极建立地方和部门公共机构,如与行业紧密关联的教育培训机构、产品检验及技术认证机构、市场调查机构、人才交流机构、金融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鼓励公共机构在集群内发行专业性报纸和学术杂志,对产业进行深入研究,推动地方的信息传播与交流。
5.4 加大集群与外界的联系程度
如果集群能够保持较大的开放性和弹性,使各种资源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则有助于保持集群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反之则会表现出僵化封闭,知识技术趋同,互补性消失等不良后果,最终使集群丧失活力和竞争力。因此,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形式的区域封锁和地方保护,及时从集群外部引入新的信息和技术,促进人才、技术、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加强集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推进集群持续学习和调整。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572047);博士创新工程基金资助项目(2005—7—13)
标签:集群效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