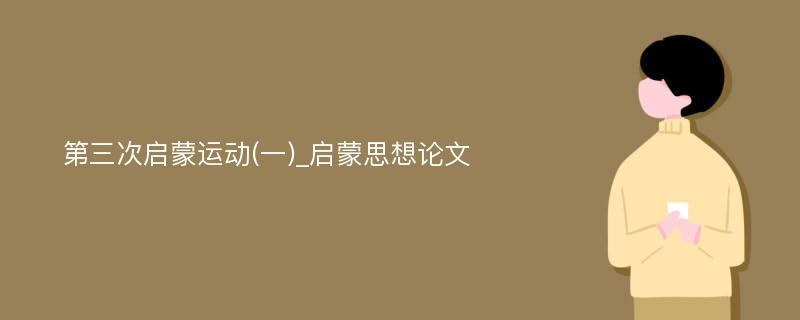
第三次启蒙(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场新的启蒙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程,面对扑面而来的后工业社会浪潮,托夫勒说:“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出现。它到处遭到了一批视而不见的人的压制。这个新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形式,改变了我们工作、爱情和生活的方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冲突,尤其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意识。这个新文明今天已局部存在。许多人尝试着使自己的生活去适应明天的节奏。另外有些人对未来则心存疑惧,陷入绝境之中。他们迷恋过去,妄想重振自己熟悉的那个垂死的旧世界。”“这个新文明的诞生,是我们生活中唯一最为爆炸性的事件。”“它的深刻意义,就像一万年前发明农业的第一次浪潮对人类解放的变革,或者如同工业革命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所带来的震撼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1]3
然而,面对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那些在民主、法治意识熏染中长大的人,“以为自己熟悉的世界是永世长存的。他们很难设想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更不用说是一个全新的文明了。他们当然也认识到事情在变化中。但是他们以为今天的变革,将以某种方式轻轻地从他们身旁掠过,而不会对他们所熟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有所动摇。他们期待着未来将一如既往。”[1]5 事实上,“人们正在进入的世界,是如此远离我们过去的经验,以致所有的心理预测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然而,绝对清楚的一点是,强大的力量正在汇合起来,去改变社会性格——发扬某些特性,抑制另外一些特性,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得到改造。”[1]434
如果如托夫勒所说一万年前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的话,那么人类是在无知无觉中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及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人类才开始了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从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人类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然而,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了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也就是说,人类曾经有过两次启蒙运动:一次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另一次发生在18世纪。这也就是托夫勒所说的:“人类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这两次浪潮都淹没了早先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以前人所不能想像的生活方式,替代了原来的生活方式。第一次浪潮的变化,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变革,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是三百年。今天的历史发展甚至更快,第三次浪潮的变革可能只要几十年就会完成。我们正好生长在这急剧转变的时刻,因而在生活中感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全面冲击。”[1]4
在今天,我们经常谈到的启蒙,往往是指18世纪这场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重大历史阶段的开启,都需要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去帮助人们树立新的观念,设计新的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型塑出人类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工业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走到了自己的顶峰,后工业社会的进程开始启动。也就是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古希腊的哲学运动,都属于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标志着农业社会开始走向成熟;18世纪则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启蒙,也是工业社会进入发展期的起点;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同样需要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这就是人类历史行进中的第三次启蒙。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如果我们不想经历农业社会启蒙前的蒙昧的话,如果我们不想经历工业社会启蒙前的“血”与“火”的战争和灾难的话,就需要尽早地启动后工业社会启蒙议程。如果没有一次及时的彻底的启蒙,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过程中的流血冲突和社会震荡也就会再次重演,而且会表现得更加惨烈,甚至会把人类导向灭绝的境地。
对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托夫勒满怀信心地说:“即使今后几十年里充满了动荡和骚乱,甚至是暴力遍地横行,但不会把人类全部摧毁。对于令人震惊的变革,现在我们取得了经验,并没有乱成一团和张皇失措,而在事实上,它形成了一个轮廓鲜明,清晰可辨的图景,特别是这些变革的累积,在我们生活、工作、娱乐和思想的方式上,汇集成巨大的变革,而一个健全的合乎需要的未来是可能实现的。”[1]6—7 有了这样的信心和乐观态度, 我们也就乐意于投身到一场面向未来的启蒙运动中去,而且在投身于其中的同时,发现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责任,随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深入,我们的历史责任感也就愈益增强。因为,我们将深深地感受到,正如那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启蒙中作出贡献的先贤们一样,在今天,“为人类生存而行动,再度变成可能和理直气壮了。总之,革命性的前提,启迪了我们的智慧,焕发了我们的信心。”[1]7 或者说,我们从此走上一条义无反顾的道路,不畏侧面来风,也不畏前进中可能出现的恶言秽语,仅仅让前进路上的光明去把那些卑污的面目照得更加清晰。
在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中,相信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与只看历史发展中负面影响的悲观主义并存,它所表明的是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以躁动的历史运动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从根本上说,那是人类控制历史进程的能力不足的表现,是因为工业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是人无法驾驭的。在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中,这种情况就不再会出现了,因为,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已经为人类积蓄了足够驾驭历史和控制社会的能力,而且,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在道德制度的安排中能够找到融洽的接合点。这时,所缺少的只是观念的转变,只要呼唤出合作的理念,一切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在我们准备投身于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中去的时候,最不能容忍的是那样一类人,他们觉得,“深刻的政治变革的前景及其危险是如此的可怕,因此不管现状多么使人不能适应和令人难以忍受,骤然看来,好像还是大千世界中最好的了。”[1]488 因为,反对变革和顽固维护工业文明的人可以在认识提高之后而发生转变,即使不愿转变,也可以成为展开辩论的对手,而面对抱残守缺一族,你却会感到无话可说。
二、第三次启蒙的根据
托夫勒对工业社会作出了准确的描述:“工业革命一方面以它自己富有特色的技术,各种社会组织机构,以及它自己的情报信息手段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一个惊人的一体化的社会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把一个社会整体无形地撕裂,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形成充满了经济紧张,社会冲突和心理不适应的状况。”其实,工业社会仅仅拥有了形式上的一体性,而在实质性的方面,处处都是分裂的,而且,形式的方面与实质的方面也是分裂开来的。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工业社会在一切方面都丧失了总体性,它在形式上的一体性也只是一种有形无质的整体性,是失去了总体性的整体性。所以,托夫勒批评说,在工业社会中,处处都有“无形的楔子”“把人类生活劈成两半”。[1]35
专业化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社会的层面上,它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具体的问题上,就很难在进步的意义上作出必然如此的判断。以医生为例,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专业化的执业医师,有负责治疗耳朵和眼睛的专科医生,有儿科医生和妇科医生,有精神病科医生和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等,这无疑是工业社会专业分工的结果,在社会的层面上可以看作是医疗事业的进步。但是,面对一些综合性的疑难杂症,中医可能会提出更为实质性的和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由此看来,在农业社会,在专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将会逼使中医的行医者去选择对人体整体把握的路径。所以说,中医属于农业社会的医疗技术,而专业化的医术则属于工业社会的医疗技术,就这两种技术的比较而言,轩轾难判,只是在社会的层面上,才会更多地肯定和推荐专业化的医术。专业化不是技术进步的惟一特征,或者说,技术进步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专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专业化恰恰需要得到关于对象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所提供的支持。瞻望后工业社会,我们相信,技术发展中的专业化历程会继续前行,同时,综合化也是并行的趋势,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关于对象世界的总体性把握的要求也就会越强烈。其实,即使从纯粹形式的方面,也会看到,越来越细密的专业分工不仅没有促使人们分离的倾向,反而会把人们联系得越来越紧密,高度的专业化使人们只有在对他人的依赖中才能生存于社会之中。这种形式上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需要拥有彼此互动的“质性”,毫无疑问,人们之间的那种根源于内在动力的合作,就是这种“质性”,是一种不同于现今外在协作和协调的“质性”。
工业社会使人类失去了生活的世界,它以社会的名义冲击、压抑和排挤了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畸形化、片面化。也许人们会对我们关于失去了生活世界的判断表示不同意见,即认为工业社会有着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生活内容。对此,我们会沉默。因为,当你把那种有形无质的形式也称作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沉默来表示无奈。想一想近代以来的社会,解放的主线自始至终被人们牵在手中,一切都是解放的手段,服务于解放,理性是要解放蒙昧的人,科学技术是要解放生产力,当一切都解放完了之后,还要寻找可以解放的对象,那就变成了“性解放”。在人沉迷于解放的时候,生活如何能够成为主题?或者,如果把解放也看作为生活,那么生活在一切都被解放了之后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应与解放一道终结呢?因而,我们今天心灵上的痛苦、人际关系上的冲突、生活境遇上的矛盾等等,都是工业社会的结果,同样,也只能在历史转型中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托夫勒所说:“我们是旧工业文明的最后一代,又是未来新文明中的一员。因此,我们许多个人的烦恼、痛苦和转向,都能从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之间的巨大冲突、在我们个人和政治制度中所引起的矛盾里找到根源。”[1]7
工业社会制造了地球难以承担的“环境问题”,如果环境保护主义者到卢梭那里寻求理论依托的时候,绝不可能发现积极的解决现实问题的良策,只会走向悲观主义的方向或提出反对人类进步的消极对策。社会是发展的,人类在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需要有新的认识视角,都需要去主动地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因而,也就不应从旧的理论中去寻找依托。面对工业社会在当代社会中的消极效应,我们仅仅赞叹工业社会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有先见之明是无意义的,毕竟卢梭是以工业社会启蒙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世人认同的。工业社会在当代的消极表现,只有通过另一场启蒙,即后工业社会的启蒙,才能从根本上加以消除。
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然而,正当人类游弋的湖面因工业社会的污染而变得恶臭难闻时,却峰回路转,走向了后工业社会宽阔的洋面。对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怀着乐观或悲观的态度,都是不足取的,而是应当理性地审察和谨慎地应对。正如工业社会经历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找到了走向成熟的道路一样,面对通往后工业社会的进程,惟有通过一场启蒙运动,去思考、探索和发现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正确道路,去理性地设计出科学的适应于后工业社会的制度、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把人的思想抛在背后,当现代化的许多问题还未搞清楚的时候,后现代已经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课题;当工业社会还有待健全的时候,后工业社会却急切地撞进我们的生活。虽然工业化与现代化是平行的两条历史线索,但是,后工业化与人们所理解的或当代较为时髦的后现代并不必然相伴而生,“后现代”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是在工业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如果说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有一次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后现代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所做出的是准备工作,是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清理障碍。它与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文艺复兴与18世纪之间的关系。
把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人们的观念或生产的需要等任何一种因素都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是历史发展必然性决定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托夫勒在分析工业化的过程时,就批判了各种各样决定论的和“创世论”的观点。托夫勒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其他的‘独立的可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1]123—124 就后工业化而言,其可变因素更加复杂,试图从中厘清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因素,肯定是枉然无功的。其实,对于一切历史性变革过程,都只能持有总体性的观念,在表面上不尽相同的各种因素的背后,去发现总体性的质;在形式上复合交织的动因背后,去把握总体性进程,而不是去将某一或某些因素确定为最基本、最主要的动因。传统认识论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架构,仅仅适用于对微观的、简单的、孤立的发生过程的理解,对于人类历史宏观性的根本变革,是没有意义的。
托夫勒认为,工业社会的文化“强调孤立地研究事物”,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则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1]333 “反对那种认为完整的事物可以通过孤立地研究其中一部分而得到理解的观点。”[1]335 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它所代表的人类进步绝不是某一或某些标准能够衡量出来的。正如托夫勒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世界上正在飞快地发展着另外一种看法: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一句话,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进步再也不会是自动化的成就,也不会单以物质标准来衡量了。”[1]326 在后工业社会,“以分散而不是集中的人口,来改变我们的空间居住分布情况。”[1]330 所以,才会表现出这样一种状况:“面对技术、社会、政治的新现实,工业时代的思想结构,越来越使人感到格格不入。”[1]343
托夫勒猜测说,后工业社会的文明,“具有自己特征的世界观,有它对待时间、空间、逻辑和因果关系的独特的方法。”[1]5 工业化冲破了一切部落边界,后工业化则使部落重新复活。然而,复活的部落已经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全方位开放的,是完全包容了社会总体性的部落。人们从这些部落中走出走进,都是为了更准确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根据托夫勒的推断,在后工业社会,将在历史上出现“超越市场”的文明。“这个超越市场,并不是指没有任何交换网的文明,……所谓的超越市场是指依赖市场,而又不再由于需要建设、扩张、规划和完善这个市场结构而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资财与时间。这个文明,恰恰是由于市场已经适得其所,而能向新的任务迈进。”“以前倾注于建设世界市场体系的巨大精力,现在可以用来为人类其他的目标服务。仅从这一事实出发,就能产生无限的文明变革:……特别是将出现崭新的社会和政治机构。”[1]317
托夫勒认为后工业社会生来就有许多特点,比如:“分散式生产、适当的规模、可再生的能源、非都市化、居家工作、高度的自己生产自己消费……”[1]374 当然,人们也“需要生活中的平衡——工作与娱乐之间的平衡、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之间的平衡、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平衡、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平衡。同时比起任何以前的人们来,他们将看到自己将置身于远为复杂的条件下,来安排他们自己。”[1]435 虽然,这些根据古典美学原则所作出的社会构想依然是乌托邦性质的,因为,关键不在于是否所有这些平衡会出现,而在于我们应当拥有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及其制度来保证社会生活是和谐的。但是,毕竟人类正在建构一种新的文明。
托夫勒指出:“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文明,必须在各国立即设计一个新的更适宜的政治结构。这是一项痛苦然而是必要的工程。它的规模将动人心魄,并无疑将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465 最为根本的是:当我们开始这项工作之前,我们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将该批判的对象一一找出,将应建立的项目一一确定,将纷繁芜杂的现象一一剔除,从中发现我们的基本目标。“有几代人生来是创造一种文明的,还有几代人生来是保持一种文明。”[1]488 我们这一代人,属于创造后工业文明的一代,“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1]492 当我们准备投身于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时,实际上所担负的是对连同我们自身在内的工业文明的超越,割掉我们思想观念中那条已经开始退化了的工业文明的“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