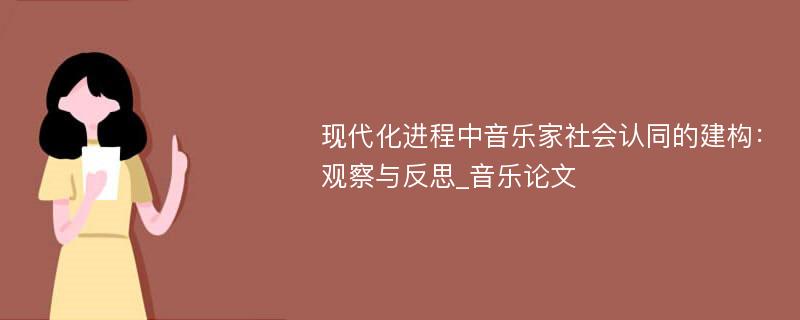
现代性进程中的音乐家社会身份建构:观察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音乐家论文,进程论文,身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2)01-0026-10
一、论题的前提及由来
在音乐的文化性研究中,关注作为“人”的音乐家应是题中要义。在著名辞书《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1980年版)中,“音乐学”(musicology)条目的作者达克勒斯(Vincent Duckles)指出,常规的音乐学定义有二,其一是最为常见的说法——音乐学是“音乐的学术性研究”;其二是美国音乐学协会于1955年提出的观点,认为音乐学是“一个研究对象为音乐艺术的知识领域,其中音乐被作为物理的、心理的、审美的和文化的现象来看待”。①但作者随后强调指出,近年来出现了第三种定义,引起了音乐学家的高度关注——“对音乐的深入研究其中心不应是音乐本身,而应是‘人’,即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行动的音乐家。这种从音乐到人、从产品(它暗示具有固定性的‘作品’)到生产者和参与者的重心转移,带来了研究方法的转换。”②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余年之后的该辞书新版(2001年版)中,“音乐学”词条的整体内容虽有较大程度的修订甚至改写,但上述针对音乐学的定义及强调以“人”为研究中心的论点却没有发生变化。③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世界范围的音乐学研究更加重视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社会视角的整体动向。近二十余年来在西方音乐学中方兴未艾的所谓“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也正是以摆脱“纯音乐”的封闭自律性,纳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为其主导旨趣。④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音乐学家郭乃安先生在一篇名为“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的文章中,也做出了关注“人”的强烈呼吁:“音乐具有它自身独立的品格,但它又不能脱离它所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环境。关于音乐与其外部诸条件之联系的研究,对于音乐本质的理解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所有外部条件对于音乐的影响力,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在音乐本身与其外部诸条件的交互关系中有一个中心的接触点,那就是人……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⑤郭先生的论述以音乐声学、律学、乐器学、旋法-调式研究、结构分析、音乐地理学、仪式学等领域的具体课题为例证,说明在所有上述研究中,如果没有联系在具体环境和具体生态中的“人”的因素,就不可能达成有效的结论。通读整篇文章,我们并没有看到郭乃安先生引录或借鉴西方音乐学界近来以“人”为研究重点的思路转向,他是通过自身丰富的音乐经验和深入的研究实践达到了与西方学界同行基本一致的学术立场。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本文的研究尝试即是以上述学理前提为出发点,呼应音乐人类学及整个音乐学研究中以“人”为中心的学术趋势,从“现代性”的学理视角重新审视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建构和转型这一具体命题,并将这一命题放入到具体的历史文化经验中予以考察,从中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思考和看法,以求教于大家并希望引发更为深入的讨论。
笔者对音乐家社会身份建构的关注首先是通过所指导的一篇博士论文来体现的。⑥我在一篇短文中做了如下评述:“近日,笔者指导的博士生夏滟洲完成了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这篇题为《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研究——从中世纪到贝多芬》的博士论文,在选题上试图有所突破,从社会学角度切入西方音乐史,以‘作曲家’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生成和变化作为中心论题。笔者从中也获益良多……从中世纪的‘匿名型’作曲家,到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的‘依附型’作曲家,再到19世纪前后的‘自由型’作曲家,作曲家的身份和地位在西方文化的演进中逐渐生成,至贝多芬时代基本确立。从这条大致清晰的历史轨迹中,不仅可以看到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从‘功能性’走向‘自律性’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作曲家的自我意识从萌芽、生长至成熟的进程。”⑦
可以看出,该博士论文已大致梳理出了西方社会中音乐家-作曲家从“匿名”至“依附”再到“自由”的身份确立曲折历程。作者以贝多芬作为这一历程的重要关节点,不仅是出于论文篇幅和容量的考虑,也是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建构这一历史进程本身所具有的形貌表露。正是在贝多芬身上,我们第一次在历史中见证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并能够依靠自己的艺术劳动和成就得到社会承认和普遍尊重的现代意义上的音乐艺术家。如夏滟洲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中所言:
……西方作曲家社会身份的确立经历着一个漫长的社会过程。在中世纪古代至文艺复兴早期,从事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被列入等级制,音乐理论家地位高于实践的作为实践音乐家的音乐表演家。居于这一身份的“作曲家”,在教会仪式中基本完全是附属性的神职人员,没有自我身份。而世俗音乐中的音乐家,则以其活动为谋求自身地位迈出较早的一步,通过谋求保护来改变生活,从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之后到18世纪中叶,社会结构处在封建的以及发育不健全的商业资本社会中,从教会到宫廷,一度形成了稳定的赞助制度时期,音乐和作曲作为一种职业,得到认可并在西方社会得到公认。由于身份制社会使每个人能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宫廷的雇佣,所以,从事音乐作曲职业的人仍然处在一种顺从性的地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兴起,音乐的市场机制开始浮现,刺激了作曲家追求创作自由的想法。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基本是“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贵族的赞助体制开始衰落,但还没有完全退出。与之并存的市场发育,形成了音乐的社会建制,确定了音乐作品概念的主导地位。处于这一历史关头的贝多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作曲家身份成型的标志。在他毕生的经历中,音乐会建制的成熟,音乐出版与教学等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作曲家人格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⑧
在笔者看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以贝多芬为标志性人物的“自由音乐家”的身份确立是最值得关注的文化社会学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直至贝多芬的时代,世界上各种文化和社会中的音乐家社会身份无一不是依附性和“功能性”的——他们或是在宗教性的神圣礼仪中充当执行者,或是在世俗性的活动与典礼场合中担当不可或缺的配角,或是直接参与各类日常的民俗生活(而在此时,他们就与普通人混同而不再具有自己独立的“音乐家”身份)。应该指出,因为人类的灵性生活、政治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一直存在并需要音乐的伴随,上述“功能性”的音乐家社会身份在贝多芬之后的时代也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
但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在贝多芬所处的时代前后,我们现代人已经习以为常的音乐的“非功能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在19世纪至20世纪成为常规——音乐的存在目的不是为了服务于音乐之外的任何目的,而就是为了聆听,为了音乐自身。正如我们作为听者在当下典型的音乐行为模式是所谓的“音乐会聆听”——我们出席音乐会,正当的目的和意图不是为了宗教崇拜,不是为了政治聚会,甚至也不是为了道德教化,就是“为听而听”。当然,聆听音乐最终还是为了获得心灵滋养和听觉愉悦。也正是出于音乐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去功能化”的“自律性”,音乐家-作曲家才最终获得了“独立”的“自由身”——以贝多芬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音乐家”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二、“现代性”视野下的音乐家社会身份建构
为了进一步理解“自由艺术家”和音乐自律性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我们有必要在此引入“现代性”的学理概念。显然,音乐因摆脱外在功能而获得“自律性”并引发音乐家获得独立品格的“自由身”,这绝不是出于偶然,而应被看作是人类整体社会从古代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一个延伸性的文化结果。我以为,只有通过“现代性”的视角,才能对音乐家社会身份的建构和转型这一具体课题带来更加具有穿透力的检视。“现代性”作为一个覆盖面很广的话题,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也在国内人文社科界引起多方面的商讨和争论,其中心议题是研究人类社会进入所谓“现代”之后,其社会结构、价值理念以及文化生态等方面与“前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和承继性,这种“现代性”对当下和未来可能具有的影响与前景,以及围绕“现代性”是否终结而引发的“后现代”问题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音乐学者也已经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趋势,并开始尝试在研究中纳入“现代性”的研究思路与理念。⑨
对于音乐的“现代性”而论,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时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⑩因而,音乐家的社会身份转型在这一时期达至不同于“前现代”的自由身状态,看来确乎是事出有因。可以说,我们当前所习以为常的“艺术音乐”的几乎所有的建制、机制、观念和价值,似乎都是在这一时段建构成型,并传至20世纪及当下,而音乐在现代及当下所暴露的诸多问题和疑难也都恰恰隐伏在那个二百余年前的启蒙时代。李晓冬在《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西方音乐进程》一文中,论证了西方音乐自启蒙运动以来,通过形式主义美学思潮、绝对音乐观念和自觉的器乐音乐的运作全面体现出音乐中的“现代性”诉求,并进一步指出这些现代性诉求在当下所遭遇的困境和问题。(11)而在笔者看来,除了李晓冬文中所指出的音乐思想层面和价值层面上的现代性诉求,音乐的现代性作为一个覆盖性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在音乐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体现。而这些现代性现象与我们所关注的音乐家社会身份建构和转型问题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如学界一般公认,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和观念在西方是通过启蒙运动构建成型的,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以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独立等为终极诉求,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也形成了摆脱外在功利和附属功能、追求艺术自身尊严和个人风格的价值取向。我们看到,正是在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的18世纪中叶,音乐与诗歌、绘画、雕塑和舞蹈一起被归入“美艺术”的范畴,从而最终形成了一直传承至今的“现代”的艺术体系。(12)而“美学”(aesthetics)作为一种研究人的感性知识和“审美”感觉的专门学科,在1750年通过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首次得到命名,恰是应和了这时期的思想进展需要,而绝不是偶然或碰巧的个人奇想。康德在18世纪末通过《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这“三大批判”的划时代贡献,分别为人类的认识、道德和审美这三个不同的精神领域进行了根本性的规范界定。就我们当下的课题兴趣而论,康德的突出意义在于,他从学理上对“审美”不同于认识和道德的根本性质进行了明晰、全面而深刻的定义——即著名的关于审美判断的四大要点(美是不涉及利害和概念的快感;美只针对客体对象的形式;审美的快感虽是个别的但却具有普遍性;美具有无目的和目的性(13)),从而使“美”和“审美”获得了与人类其他实践生活和精神活动具有同等尊严的合法地位,并使“审美”成为与理性认识和伦理意志平起平坐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人类精神活动范畴之一。
艺术作为“美”的直接承载体而获得自律、自治和自主(autonomy)的大门由此敞开。所谓“自律”(或称自治、自主),指的正是摆脱任何外在束缚的“去功能化”而独立自足的状态。(14)而现代性在艺术中的重要表征,恰恰就是艺术的自律性的生成与表达。正如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现代性理论的重要学者哈贝马斯所指出的:
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艺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文化现代性的特征就在于,原先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理性,被分离成三个自律的领域。它们是科学、道德和艺术。18世纪以来,古老世界观所遗留下来的那些问题被加以整理,以便被置于正当性的诸特定层面上,它们是真理、规范性的正义、本真性和美……科学话语、道德力量和法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渐次被体制化了……由启蒙哲学家们在18世纪精心阐述的现代性规划,是一种遵循其内在逻辑坚持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与自主的艺术的努力。(15)
显然,“发展……自主的艺术的努力”,是18世纪以来“现代性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现代性规划,其基本特征即是理性化的体制建构“……艺术的生成和批评渐次被体制化了”。以这种视野观察音乐文化与音乐生活,我们会发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音乐发展的诸多现象完全符合上述的论断。例如,作为现代音乐生活最重要的载体——“音乐会”建制,其发育在17世纪末,而成型和成熟恰是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通过音乐会,音乐的具体生产过程逐渐摆脱了对贵族和宫廷的依赖,从而具有了面向广大公众的“商品”属性,并以此极大地推动了音乐的现代性转型。(16)又如,我们当今身处其中的“音乐学院”体制,其创立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795年——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学院作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正规音乐学院,尽管其创建是应时之需,但它在学制、科目、考试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体制化”的设计和安排,由此开创了“职业性”音乐家培养的科学建构,并也成为日后世界上所有其他音乐学院的模板。(17)再如,音乐批评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性”品格的公众音乐文化现象,它的发展也与18世纪以来报纸、杂志等“公共空间”载体的形塑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清晰可见的文化现象,音乐批评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其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其时间不早不晚,也正是在18世纪末左右。(18)貌似碰巧的是,美国音乐哲学家莉迪娅·戈尔在《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一书中,将“音乐作品”这一具有主导地位的“现代性”音乐观念的兴起定位在1800年左右,认为自此时起,音乐作品的概念开始渗入到所有的音乐创作和表演实践中,并对日后的音乐生活发生着支配性的影响。
所有上述具有现代性表征的音乐例证和文化现象均发生或兴起于18世纪中后叶,这当然不是碰巧,更不是偶然。它们恰好证明,音乐的“现代性进程”或“现代性转型”是一个整体性的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嬗变过程,所有具体的音乐意识和思想变化、音乐行为方式改变以及音乐生活的性质转换都隶属于这个更大的整体过程。以此推衍,音乐家的社会身份转型当然没有例外也隶属于这一整体的现代性进程,而且其关键性的转变也发生在18世纪中后叶这一大致相同的时间段中。绝非偶然的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这三个古典乐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们的生平经历就恰好体现了此时音乐家社会身份转型的不同模式和阶段。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
有趣的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大师,恰好典型地体现出当时音乐艺术家社会身份转变的不同阶段,反映了艺术生产体系和艺术家社会生活从旧式的“前现代”结构向新型的“现代性”体制转换的复杂过程。
长者海顿(1732-1809年),一生大部分时间受雇于贵族,同当时大多数职业音乐家一样,委身于传统的“赞助体系”(patronage system)的保护伞之下,职位明确,责任清晰,虽然创作上不免受到雇主趣味和爱好的牵制,但也解除了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晚年又直接得益于音乐艺术早期市场体系的勃兴,可谓横跨新旧两种体制并顺利平滑过渡。
比海顿晚一代的莫扎特(1756-1791年),在其艺术生命成熟后不久便脱离传统的“赞助体系”,但不幸在尚不稳定的市场格局中无法求得生存,最终陷入债务缠身、贫病交加的境地,从某种角度看是这一转换过程中的牺牲品。
后辈贝多芬(1770-1827年),显然已经处于这一转换过程即将完成的终端,他成长于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后”氛围,身怀强烈的艺术家个人自尊意识,充分利用了当时新旧体制并行的“双轨制”优势,虽仍然依赖贵族朋友的慷慨赞助,但并不就此构成对贵族的人身依附,而是在创作中遵循自己内心的艺术召唤,并不断通过自己作品的委约、出版和演出,在市场上取得盈利,从而获得了富足和具有尊严的个人生活。(19)
在上一节最后,笔者已提及贝多芬在确立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音乐家”社会身份这一过程中的枢纽地位。而上面的论述将这一过程放置到文化和音乐的现代性视野中去,相信由此我们对音乐家社会身份建构与转型这一问题会获得更为透彻的理解与认识。
三、现代性的后果:音乐家社会地位的快速提升
贝多芬之后,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建构仍在继续发展和变化。有关这一有趣的课题,尚需有更多实证性的历史考查和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就此进行详尽论述,但出于笔者的理论兴趣,我仍想对这一进程中的一些关键现象和重要方面做提纲挈领式的考察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毋庸置疑,音乐现代性在19世纪中继续推进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音乐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以及与此互为因果的音乐家社会地位的飞速提高。从某种角度说,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以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19世纪西方所达到的社会认同度和普遍尊重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在之后的20世纪也此景不再。众所周知,德国著名19世纪哲学家叔本华曾提出,音乐是一门高于其他任何其他艺术门类的独特品种,因其本身就是世界的本质——意志的直接写照,而其他艺术则需要通过理念才能间接地反映意志,因而在普遍性和直接性上都低于音乐。(20)应该指出,叔本华的这一著名论断虽然与其独特的哲学认识紧密相关,但也明显反映出19世纪初以来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文人对音乐的无限性和神秘感予以正面肯定和褒扬的思想传统的影响。(21)也正是在这一思想传统的惯性支持下,才出现了19世纪后半叶英国批评家沃尔特·佩特的那句被后人多次引用的名言:“一切艺术总是渴望达至音乐的状态”(All art constantly aspires towards the condition of music)。(22)
这种前所未有的“音乐至上论”催生了音乐家社会地位的普遍改善和空前提高。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和内在性质由此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和转型。当然,音乐家的“自由身”建构与获得当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曲折甚至风险。可以想见,脱离了传统的“赞助体制”保护,直接面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市场,音乐家在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他的基本生计却也可能遭到威胁——如莫扎特的生平遭遇已有所预示,而莫扎特之后另一个更加不幸的作曲家舒伯特(1797-1828年),终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职位,在世人尚未看清自己艺术创作的真正价值之前便因病英年早逝,令人唏嘘。莫扎特、舒伯特的命运并非个别例子,他们可被看作是现代性进程中音乐家社会身份转型的不幸失败者,这其中有他们自身性格和运气不佳的缘由,也有社会运行体制发育不成熟的原因。
尽管有上述莫扎特、舒伯特这样的刺目例证,音乐家社会身份不断独立并获得尊严的转型大趋势毫无疑问是有利于音乐家的。自19世纪以后,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音乐家不仅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成为社会“上层”的一分子,而且甚至获取了以前音乐家所难以想见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例如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年),他在非常年轻时就因自己的突出歌剧写作才能爆得大名,其名声不仅传遍意大利,而且享誉全欧洲。1824年,著名意大利作家司汤达在其撰写的《罗西尼传》中将这位作曲家比作一个征服了全世界的新的拿破仑,而此时的罗西尼年仅32周岁!由于他的巨大成功,罗西尼在他37岁之前已积累了足够的经济财富,以至于在他生平的最后40年间居然彻底辍笔而过起了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逍遥隐居生活。而罗西尼对自己通过艺术创作而得来的尊贵身份也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他曾对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称自己是欧洲最伟大的两个人物之一(另一位是当时的英国名将、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23)
罗西尼的特殊人生轨迹代表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商业体制中作曲家通过歌剧创作版权而获取丰厚收入和社会声望的个案。而现代性社会为作曲家和音乐家建构社会身份还提供了其他的有效途径。帕格尼尼(1782-1840年)的小提琴演奏和李斯特(1811-1886年)的钢琴演奏给音乐世界带来了全新的元素:以辉煌的炫技天才展现艺术家的超人魔力。在他们身上,音乐家绝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仆人和随从,而是具有无限魅力和感召力的特殊天才,他们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并以自己夺目的音乐才华反衬出凡俗世界的普通和平庸。帕格尼尼的小提琴绝技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传闻说他是魔鬼附体,或者他就是人间的撒旦。李斯特在炫技展览和蛊惑观众的道路上紧跟帕格尼尼,并进一步使之发扬光大。有关他在1840年代至1850年代旅行演出所到之处掀起的迷惑、喝彩、狂热乃至歇斯底里,这都已是音乐史中的常识,无需在此赘述。在诸如帕格尼尼和李斯特这样的音乐家身上,所有对教会、贵族、国家和政府的经济依赖和实体依靠均被打破,音乐家已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音乐艺术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在某些时候站到社会的塔尖顶层。
即便是此时仍存在一些贵族或富豪对音乐家的赞助,但这种赞助的性质已经和18世纪之前的“前现代”音乐状态下的情况有了明显差别。例如,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1840-1893年)在其艺术风格发展成熟之时幸遇冯·梅克夫人(1831-1894年)的慷慨私人赞助(1870-1890年),这使作曲家可以离开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职而专事作曲。但需提请注意,柴科夫斯基并没有就此构成对梅克夫人的个人依附(众所周知,他与她二人甚至从未谋面),梅克夫人也完全没有对作曲家的创作提出任何要求或干涉。柴科夫斯基完全保持着自己的“自由艺术家”身份,而梅克夫人所提供的经济资助只是让他的这种自由更有保障、更加可靠。令人感兴趣的是,也就在这一时期,国家的政治体制也在为成功的音乐家提供保障和支持,以替代原来教会和贵族的“赞助”。我们看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8年为柴科夫斯基提供了一份年俸,作为对这位作曲家艺术成就的承认和嘉奖。(24)而柴科夫斯基绝非孤例,如挪威政府于1874年为著名作曲家格里格(1843-1907年)提供了足以让他解除生计之虞的年俸,(25)而芬兰政府在19世纪末出于公众的舆论请求也给西贝柳斯(1865-1957年)这位给芬兰音乐带来世界声誉的作曲家提供了年俸,以使他可以摆脱在音乐学院的教学负担而专心从事创作。(26)
这种通过国家财政来为音乐家个人的艺术创作提供支持的情况,在德国音乐家瓦格纳(1813-1883年)的事例中成为一个极端特别的个案:在这里,不再是艺术家为王宫提供服务——这种关系被彻底倒转过来,而是王宫通过国家机器为艺术家的梦想和创造提供全力服务。话说路德维希二世(1845-1886年)性格偏执而富于幻想,痴迷艺术,早就深为瓦格纳的天才倾倒,他于1864年登基巴伐利亚公国国王,一上台便决意为瓦格纳实现艺术理想提供一切帮助。除第一次与瓦格纳见面就奖赏4千古尔盾并答应为他偿还一切债务之外,国王还每年为瓦格纳提供8千古尔盾的高额年俸(相当于内阁高官的收入),以便让瓦格纳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中恣意驰骋。自此,瓦格纳在事业发展最紧要的关口,总是路德维希二世慷慨解囊,为瓦格纳渡过难关,尽管两人之间关系时好时坏,而且国王用国库财政为瓦格纳个人艺术发展大开方便之门的举措也遭到众大臣和其他人士的强烈反对。据估算,自路德维希二世与瓦格纳相识至瓦格纳去世的19年间,国王为瓦格纳所支付的资助(包括赞助金、年俸、房租以及礼品等)总计达56万马克之巨,相当于当时整个巴伐利亚公国全年国民支出预算的七分之一。(27)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路德维希国王,就没有瓦格纳日后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反过来说,也正是瓦格纳视音乐和艺术为德国民族最高目的的雄图大略使路德维希国王的人生获得了超越性的意义。尽管这一近乎童话般的传奇具有某种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但深究起来,它的发生却只有在音乐的现代性条件下——音乐本身获得了社会公认的“自律性”,而作曲家则被普遍看作是社会和民族的精神代言者才有可能。自启蒙运动以来的音乐家社会地位的普遍提升,至瓦格纳终于到达顶点。就一个音乐家在世及身后所能达到的社会影响和声誉高度而言,瓦格纳可谓空前绝后。在他的身上,社会对音乐家的尊重甚至尊崇以一种极端和夸张的方式被体现出来。但也正是瓦格纳事例的“不可思议”性,才反衬出现当代社会中的惯常普遍现象——我们现今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具有才能并取得成功的音乐家应该赢得社会尊重。
四、现代性之于当代音乐家:反思和追问
现代性的推进,对于音乐家社会身份的提升显然具有突出的正面意义。而音乐家在现当代社会中赢得荣誉和声望,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进入20世纪以来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由于音乐表演在当代音乐生活中的显赫地位,音乐表演家(尤其是指挥家)甚至超越作曲家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知名度。举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例证:仅在英国,因杰出艺术成就获封爵士而具有“贵族”身份的音乐家有一个很长的名单,其中包括我们都较为熟悉的如埃尔加(作曲家,1904年封爵)、沃尔顿(作曲家,1951年封爵)、蒂皮特(作曲家,1966年封爵)、布里顿(1976年赐封贵族)、巴比罗利(指挥家,1949年封爵)、诺林顿(指挥家,1977年封爵)、科林·戴维斯(指挥家,1980年封爵)、西蒙·拉特尔(指挥家,1994年封爵)等等。(28)
但是,现代性诉求对于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建构,其效应也并不是全然正面的。正如当前诸多学者在现代性的研究和反思中所指出的,现代性的进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在带来“进步”和“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催生着“异化”和“疑难”。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重要先驱马克斯·韦伯早就意识到,现代性社会所特有的对传统价值的“祛魅”和“理性化”趋向,必将导致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瓦解,从而引发深刻的“意义危机”。韦伯一方面认识到现代性的理性化进程的不可逆转和巨大效能,但另一方面又对这一进程所具有的不祥前景持深刻的悲观和怀疑态度。(29)就我们所关心的现代人社会身份构建问题,韦伯也曾有极为尖锐的悲观性评述:“‘职业人’一词,在韦伯的著作中,几乎可以等同于他所理解的‘现代人’。然而,资本主义在制度层面上不断理性化的结果,使得‘职业人’今天成为社会分工‘事理上之必然’……我们因此也不难了解韦伯在阐述‘现代性’的特质时,并未局限于表彰人类理性的成就,反而以刻意以悲观的语气,反讽一批‘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感情的享乐者’也许会成为代表‘现代’的‘最后的人物’……他们表面上看来都拥有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机会,实际上却愈来愈像资本主义这部大机器中的小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体制里循规蹈矩地运转,这是‘理性’中的‘非理性’成分。”(30)
通过上述引述,可以看到,韦伯非常深刻地指出了现代人社会身份中理性化建构中的非理性面向。这正是现代社会中诸多事物走向自我反面的“异化”现象的表征。那么,我们不禁会询问,音乐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人”其社会身份建构的现代性经验中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异化”现象?更进一步,这种音乐家社会身份的“异化”现象是否导源于音乐现代性进程中本身也存在的“异化”?
不幸果然如此。进入20世纪以来,以摆脱具体社会功能的自律性为其根本特征的“严肃音乐”在语言、技法、表现和形式方面有诸多推进,但总体而言,其艺术影响和社会关注度与19世纪相比,毋庸讳言是呈下降趋势。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现当代音乐生活中,创作于现当代的音乐作品恰恰只占很少的份额,活跃于舞台上的音乐“主流曲(剧)目”是诞生于18、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代。其他门类的姊妹艺术如文学、美术特别是电影,其受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主要是产生于当前的新创作,与之相比,音乐艺术中这种沉湎于过去的“时代倒错”文化现象确实显得反常。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自然极为复杂,不仅包括音乐内部语言形式方面的因由,也涉及音乐之外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缘故,本文不拟在此深究。(31)但与之紧密相关的后果是,现当代音乐家(尤其是作曲家)的社会身份建构因为音乐生活的反常而陷入了某种不健康的窘境中。英国作曲家、音乐学家赫德在权威性的《新牛津音乐指南》这部中型辞书中撰写了一个饶有兴趣的条目“作曲家”,(32)其中他客观分析了当代作曲家的生存机制——版权制度、委约制度、“驻团(校)作曲家”制度,以及辅助性的教学、表演、批评等工作岗位为作曲家所提供的机会。但在条目最后他以略带悲叹的口吻写道:
虽然对新音乐的需求并不在少(首演总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但随后经常性的重复上演通常并不多。新作品进入常规保留曲目的数量极为有限……因而,职业作曲家的境遇总显得有些奇怪,甚至有些不自然。他赢得了自己的法律权利,不再有遭人严重盗版侵权的危险(像莫扎特那样)……他被社会所认可,而且如果接受赞助,也完全可以将赞助置于自己的条件框架中。但令人怀疑的是,是否有人真正需要他。最激进的先锋音乐只吸引极少数人。对于其余的人而言,过去的音乐提供了足够的满足。当然,仍有一些作曲家的作品极为流行,因而获得了比以往最成功的作曲家也不敢梦想的收入。但仅仅是在20世纪才在“通俗”作曲家和“严肃”作曲家之间划出了明晰的界限。舒伯特可以用同等的信服力和同样的基本语汇写作伟大的交响曲和通俗的舞曲。这种自然的境况一去不复返了……(33)
我们不必完全认同上述观点的悲观论调,但其中所阐述的现当代作曲家不自然的“异化”身份却发人深省。这种“异化”,主要体现为作曲家作为艺术家与他(她)身处其中的周围社会之间丧失了自然的联系和功能性的纽带,从而使作曲家的艺术生产和社会对其产品的接受之间出现断裂性的沟壑。现代音乐作品缺乏听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一个自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困扰音乐界的难题。关于这一难题,以往通常所见或是责怪作曲家一味追求音响形式的创新而置听众于不顾,或是责备听众的审美欣赏习惯过于保守而无法跟上音乐的发展速度。但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一危机的产生正是音乐现代性的表征——音乐自律性本身所带来的“异化”后果之一。正如笔者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所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西方世界中所谓的‘自律性’(autonomy)的音乐观念不断成型和发展,最终成为音乐艺术界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这种‘自律性’的音乐意识,导致音乐生产和音乐生活走向自身的‘异化’——音乐成为一个独立于人的‘对象’,从而服从于不断强化的‘规训’,扭曲为‘工具性’的存在……既然音乐作为‘自律性’的存在,废除了功能性的‘应景意识’,那么它的‘公共意义’何在?……音乐从一种‘公共话语’转变为‘私密表述’,并在‘个人原创性’这一典型‘现代性’诉求的驱动下,在不断征服新领地的同时,越来越成为‘晦涩难懂’的‘私人密码’。体裁的共享期待开始衰落,形式语言的‘共同实践’成为过去。于是乎……听众和音乐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可避免……”(34)
至此,我们看到一个巨大怪圈的形成。音乐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原来一直具有明确的实际功能——无论是民间的婚丧嫁娶的陪衬,还是崇高的祭祀礼仪的伴从,或是私人聚会时娱乐调剂手段。音乐家在这种“前现代”的“功能性”音乐活动中,也相应只具有配角和随从的社会身份定位。但随着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音乐进程步伐,音乐经历了“去功能化”的过程而形成了自律性的“艺术音乐”或“音乐会音乐”。音乐家也由此转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音乐家”,并进而成为备受尊崇的社会名流与上层人士。然而,音乐现代性的推进却很快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音乐的“无功能性”致使音乐与社会的关联感下降,听众对音乐的关注度随之下滑,这直接导致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出现定位困难。
总之,音乐的现代性诉求和自律性状态,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面,在积极推动音乐艺术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诸多无法回避并难以解决的问题。文中以上所述当然主要是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进程和西方音乐家的社会身份构建状况,但由于中国音乐自20世纪初以来已同中国社会一道全面卷入现代性进程,因而文中所述的所有情况实际上都与我们自己、与中国的当下息息相关。君不见,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家的社会身份建构也遭遇着同样的曲折历程,而且由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有其特殊的背景和路径,中国音乐家的身份建构的现代性诉求也有其特殊的性格和面貌。笔者在此约请更多的学者来共同关注音乐家的社会身份问题并从现代性角度积极开展该问题的中西比较研究,因为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是为了一时的个人兴趣,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为了中国音乐的当下实际和未来走向。
2012年2月于沪上“书乐斋”
①Vincent Duckles,"Musicology",in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London,1980,Vol.12,p.836.(除特别注明,本文中出现的西文中译均为笔者所译。)
③参见Vincent Duckles and Jan Pasler,"I.The Nature of Musicology",from "Musicology",in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London,2001.(2001版的第二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辞典》以下简写为The New GroveⅡ。)
④参见David Beard and Kenneth Gloag,"New Musicology",in Musicology:The Key Concepts,London and New York,2005.
⑤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第16页。
⑥参见夏滟洲:《西方作曲家的社会身份研究——从中世纪到贝多芬》,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08年1月通过答辩。
⑦杨燕迪:《作曲家的自我意识》,载《文汇报》2008年7月2日第11版。
⑧同注⑥,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打印稿,2008,第160-161页。
⑨可参见杨燕迪:《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前期中西音乐中的体现及其反思》,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杨燕迪:《诊断音乐:病理与处方》;[英]休伊特著,孙红杰译:《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与后现代状况》中译本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此文也发表在《黄钟》2007年第1期;李晓冬:《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西方音乐进程》,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夏滟洲的上述博士论文中也引入了“现代性”视角,请见该文第三章,“身份的获致:现代性形成初期条件下作曲家的追求”。
⑩应该指出,本文作者对音乐现代性的认识已和几年前有所不同。我在《音乐的“现代性”转型》(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一文中主要论述了现代性在20世纪上半叶中西音乐发展中的不同体现。而目前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音乐现代性的发生更为关键的时间段是启蒙运动时期。可以说,音乐现代性的诸多症候在20世纪或许体现得更为明显,但其根源和成型是在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时期,并在整个19世纪持续推进。
(11)参见李晓冬:《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西方音乐进程》,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2)参见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1994,尤其是第32-38页的论述。
(13)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尤其是第358-373页对康德审美判断学说的梳理和总结。
(14)德国著名音乐学家达尔豪斯指出,“自律性原则意味着:第一,它强调聆听音乐时注重其自足的意义,因而形式而非功能占据主导地位;第二,它以现代精神看待艺术,即,作品是作为自由艺术而存在,赞助人和购买人对作品的内容和外在形式都不发生任何影响。”见达尔豪斯著:《音乐史学原理》,杨燕迪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第165-166页。
(15)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周宪译,载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42-143页。
(16)参见美国音乐学家保罗·亨利·朗在《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一书中对音乐会建制发展的概述,特别是此书第十四章中的“18世纪音乐的社会学概观”一节,第十九章中的“19世纪的音乐实践”一节。
(17)参见William Weber和Denis Arnold等人撰写的长条,“Conservatories”,in The New GroveⅡ,London.2001.
(18)参见杨燕迪:《音乐批评的现代制度发育过程及相关反思》,载《音乐研究》,2011年第2期。
(19)杨燕迪:《作曲家海顿二百年祭》,载《文汇报》2009年10月24日第6版。
(20)相关论述请参见石冲之译、杨一之校的中译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特别是其中第52节,商务印书馆,1982。另可参见韦启昌的中译本《叔本华美学随笔》,特别是其中的“论音乐”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1)参见保罗·亨利·朗上引书,特别是此书第十五章中“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一节的论述。
(22)[英]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张岩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152页。原书第一版于1873年出版。
(23)参见Tim Blanning,The Triumph of Music,London,2008,pp.45-46.
(24)参见Roland John Wiley,"Pyotr Ⅱ'yich Tchaikovsky","5.Return to Life",in New Grove Ⅱ,London,2001.
(25)参见John Horton and Nils Grinde,"Edvard Grieg","2.Nationalism and Fame,1864–79",in New Grove Ⅱ,London,2001.
(26)参见[芬兰]尼尔斯-艾里克·林波姆:《西贝柳斯》,陈洪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第41-42页。
(27)Barry Millington,"Relationship with King Ludwig Ⅱ",in Barry Millington,ed.,The Wagner Compendium,London,1992,pp.121-122.
(28)参见Tim Blanning,The Triumph of Music,London,2008,p.64.
(29)参见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尤其是其中第二章“现代性的社会学分析”。
(30)同上,第80-81页。
(31)关于世界范围内严肃音乐在现当代社会中的危机和问题,一个较新的权威性论述是美国指挥家、音乐学家列昂·勃兹坦(Leon Botstein)的专论“Music of a Century:Museum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Subsidy”(一个世纪的音乐:博物馆文化与补贴的政治),载Nicholas Cook and Anthony Pople,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Music,Cambridge,2004.
(32)Michael Hurd,"Composer",in Denis Arnold,ed.,The New Oxford Companion to Music,London,1984,pp.439-441.
(33)同上,第441页。
(34)杨燕迪:《诊断音乐:病理与处方》,[英]伊凡·休伊特:《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孙红杰译,中译本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3-5页。
标签:音乐论文; 现代性论文; 音乐学论文; 瓦格纳论文; 贝多芬论文; 作曲家论文; 艺术音乐论文; 艺术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古典音乐论文; 钢琴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