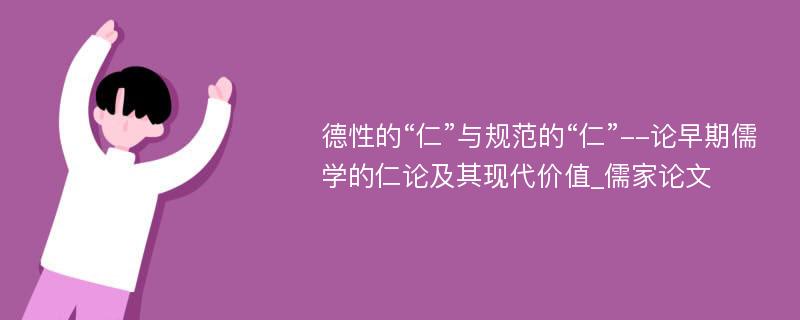
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简论早期儒家的“仁”说及其现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德性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0)05-0062-0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因其关注社会人伦,“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为评断儒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价值,或视其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主干,或肯定其为“人学”。前一种视角认定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儒学被定位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长期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方向。后一种视角认为儒学以“三纲领”、“八条目”即所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本内容,重视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成己成人,确立了中国人基本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这样的儒学乃人生宝典,成德教义。人们对儒学的评断,视角不同,趣向有别,结论各有其据,且各以不同的侧面接触到了儒学的特质与价值。但是人们对儒学已有的评断,并没有终结人们对其特质与价值的现代性思考。在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其理论价值究竟表现在哪里,儒家学说究竟为当代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什么样的人生经验与人生智慧,或者说在儒家学说中,哪些具体理论对于人们今天的生活仍然具有实际的借鉴意义,能够在现代人类文化中彰显其普适价值,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拟通过对早期儒家的“仁”范畴的论析,对儒学的思想特质与现代价值作出自己的解释与评断。
一
儒学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理论内容的思想系统,也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化发展的思想系统。解析儒家学说的现代性意义,不论是学术视角还是文本选择都可有不同。就文本而言,人们可专探“六经”之类的传统典籍,也可专注于先秦儒家以及两汉、两宋时期的儒家著述。对于儒学典籍既可作专题的解析,也可作系统的研探。朱熹当年论及阅读儒家典籍“四书”,曾主张人们先读《大学》,认为先读《大学》,可以帮助人们“定其规模”,从总体上把握儒家理论的基本架构与思想内容。其后应阅读《论语》。阅读《论语》可帮助人们“立其根本”,了解儒学的早期形态,熟悉儒学的原创性思想。再后读《孟子》,“以观其发越”,了解儒学的演绎与发展。最后阅读“中庸”。阅读《中庸》可“求古人微妙处”,即了解形上层面的儒学理论,理解儒学的“高明”与价值。朱熹这种主张,立意虽在论释自己所理解的阅读“四书”的方法,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实际上认定在儒学的演绎发展中,《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旨趣和价值并不完全相同。朱熹主张的阅读“四书”的方法,是以他对“四书”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价值的理解为基础的。其中,他以为阅读《论语》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儒学成型时期的理论内容及其思想价值的观念,对于我们选择儒家典籍,思考儒学价值极具启发意义。今天,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论析儒学理论的现代性价值,同样应当将目光首先投向《论语》这部在理论方面最具原创性的早期儒学经典。以《论语》为解释对象,探讨儒学的思想特质与理论价值,学术视角与学科参照又可有不同,在同一学科范围之内,不同层面的理论指向也可构成不同的解释视角。如果我们专从伦理学的角度解读《论语》,伦理德性与伦理规范应当是我们必须留意的两个解释向度。
伦理德性是人所具有的道德品质,是人的美德。从伦理德性的角度来解读《论语》,可以说早期儒家关于人的德性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仁”范畴的论释建构起来的。对于德性的理解,东西方哲学家有所不同。在西方哲学史上,德性曾被划分为道德的德性与非道德的德性。道德的德性是所谓伦理德性,非道德的德性是所谓理智德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伦理德性即“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在中国哲学史上,哲人们认定“道德”即是“得道”,所谓德性的意蕴直指人优秀的道德品质或人的美德。《论语》论释的德性之“仁”,即是对人的德性或美德的概括与表述。在《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较多,譬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等。在这些论述中,“仁”多表示德性。这样的德性,乃人的美德,早期儒家十分推重。与“仁”这种德性相关,《论语》中还论释过“义”、“礼”、“智”、“信”等表述德性的范畴。“义”、“礼”、“智”、“信”作为人的德性或说美德,实为“仁”这种德性的具体体现,或说都源于德性之“仁”。西方哲学家曾有以中道为伦理德性者,并认为这样的德性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论语》中也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的论断,并以“无过无不及”释中。但从《论语》中对德性之“仁”的论释来看,早期儒家虽也主张“为仁由己”,肯定德性之“仁”与道德主体自身的选择相关,但早期儒家更多的是将“仁”这种德性理解为源自人的“爱人”之心,强调所谓“人有是心,则有是德”。故《论语·颜渊》中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的记述。这种记述,曾影响后人以“爱人”论释德性之“仁”。实际上这样的论释并不十分确切。“仁”作为德性,是人的一种品性,“爱人”则只是人这种品性的具体体现。
与德性之“仁”的观念相联系,《论语》中也将“仁”视为人的最高道德境界。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即是表示自己未能达到“圣”与“仁”的境界。孔子还曾说过:“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所谓“求仁得仁”之“仁”,似也可以理解为人在生活中所达到的道德境界,故有无“怨”之说。《论语》中释“仁”的实例还有很多。杨伯峻先生作《论语译注》,曾指出“仁”范畴在《论语》中出现达105次之多,且“仁”的意蕴多与人的德性关联。早期儒家以“仁”为最高德性,认定“仁”为诸德之源和最高道德境界,使德性之“仁”成了儒家有关德性理论的核心范畴。今天,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以德性之“仁”为善为美,将德性之“仁”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与理想追求,仍有利于维系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德性之“仁”说应当是早期儒家伦理思想中最具现实价值的内容之一。
依早期儒家的观念,道德即是“得道”,“得道”一方面需“外得于人”,另一方面需“内得于己”。内凝性应是德性的重要特征,这使得《论语》中对德性之“仁”的论释,多为对于“仁”德的现象性描述,少有理论性的论释与界定。但早期儒家对于德性之“仁”的论述仍为后世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有所发展。孔子之后,孟轲强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以“仁”为“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更加注重从德性的角度释“仁”。两宋时期的儒家学者,一方面肯定“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伊川易传·复传》),同时也明确地肯定“仁”乃“四德”之源:“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伊川易传·乾传》)。后来朱熹曾具体解析程伊川这种“仁”包“义”、“礼”、“智”、“信”“四德”的思想。在朱熹看来:“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文集》卷五十八)。从程伊川和朱晦庵对“仁”包“四德”的解析来看,“仁”德已居“四德”之首。程伊川还曾将人心比喻为谷种,将谷种的“生之性”比喻为“仁”:“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二程遗书》卷十八)。这种譬喻也是要肯定“仁”乃诸德之源。宋儒从心性的角度释“仁”,的确加深了人们对德性之“仁”的理解。因为德性作为道德品质,是与道德主体的心理、情感联系在一起的。以现代伦理学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德性实际上应是道德主体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培植并表现出来的心理自我,是一种内在于道德主体的品质。离开道德主体的心性品质,很难具体论释人的德性。但从孟轲到宋代儒家对德性之“仁”的论述来看,理论层面又并未超越《论语》解析德性之“仁”的内容,仍多停留于对德性之“仁”的外在表现的描述。这种现象给我们一种启示,这就是单从德性的角度对“仁”做出界定,在学理上是较为困难的。因为在《论语》中,“仁”既是一个表示伦理德性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表示伦理规范的范畴。在“仁”这个范畴中,德性的含义与规范的含义既相互区别又有机统一。我们要更深入地了解早期儒家主张的德性之“仁”,尚需要在关注德性之“仁”的基础上,深入地解析早期儒家所理解的规范之“仁”。
二
伦理规范是人们在道德生活中的行为原则、标准。如果说内凝性是伦理德性的特征之一,那么,外在性则应是伦理规范的特征之一。同时,相对于伦理德性而言,伦理规范的内容需具备约束道德主体行为的具体标准、原则,故伦理规范需有明确的界定,现象性描述无法为道德主体提供具体的行为标准、原则。因此,我们考察早期儒家关于伦理规范的理论,可以看到早期儒家论释规范之“仁”比论释德性之“仁”更具理性的色彩。
早期儒家对规范之“仁”的论释见于《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是《论语》中对“仁”这一儒家学说的核心范畴最具理论价值的界定。这种界定,不仅最富创意,最具理论价值,同时也是唯一准确表达“仁”范畴基本内容的理论性描述。因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既能够使人了解儒家所主张的作为规范的“仁”的具体内容,为人们提供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行为准则,同时也能够深化人们对德性之“仁”的具体内容的了解,使人们对德性之“仁”的了解不再停留于德性之“仁”多样的具体表现这种层面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规范之“仁”的基本内容,为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原则。这种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提倡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也要让别人行得通。用现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的话说:“‘立’是有所成而足以无倚,‘达’是有所通而能显于众。”[1]要而言之,这种由规范之“仁”表达的伦理原则,实即主张己之所欲,亦施与人。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存在所谓己之所欲的问题,也存在“己所不欲”的问题。早期儒家关于伦理规范的理论,如果停留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伦理原则,尚不足以应对人们生活中存在的“己所不欲”的问题。故《论语》中既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早期儒家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范,是通过“恕”范畴来具体阐释的。曾参曾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这样的论断来总括孔子的思想学说。这种概括与后人将孔子的学说在总体上视为“仁”学实具相同层面的含义。《论语》中论释“忠”这一范畴的实例很多,譬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忠”或“忠信”,都可以从规范的角度去解读。但《论语》对作为规范的“忠”的论释也多为现象性描述。
“恕”则有所不同。在《论语》中,“恕”作为一个表述规范的范畴,其含义十分明确:“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里,孔子不仅将“恕”看做一个人需要终身实践的行为原则,而且非常明确地将“恕”的内容表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当说《论语》中的这种论述,是对“恕”范畴的一种非常确切的界定。通过这种界定,我们对作为规范的“恕”的内容可以获得十分具体的了解。当《论语》中将“仁”界定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恕”界定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完整且具有普适性的道德行为准则。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如果能够自觉地坚持这样的准则,不仅可以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彰显其良好的人格品质,同时也可以保证其行为成为有益于他人乃至于社会的道德的行为。
关于“恕”与“仁”的关系,有学者主张“恕”为行“仁”之方,也有学者强调“忠恕即仁”。张岱年即肯定“合忠与恕,便是仁”[1](250)。依照张先生的理解,“忠恕”在儒家学说中,是除“仁”之外最具体地表述规范的范畴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仁”与“忠恕”在表述儒家主张的行为规范时实际上属于同一层面的范畴。因为《论语》中对“仁”的界定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恕”的界定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界定刚好从两个方面规定了儒家主张的“推己及人”,全面地表达了儒家所认定的人的行为规范的内容,为维系和保持人们社会生活的秩序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但也最适用的行为原则。应当肯定,张先生对《论语》中的“仁”与“忠恕”范畴的解析是合理的。儒家伦理中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即其主张的人的道德行为规范或原则,而这种规范或原则,确实是通过“仁”与“恕”两个范畴来全面表达的。但从实质上来看,这种伦理原则仍为规范之“仁”,“恕”只是“仁”的一种体现。
早期儒家以规范之“仁”确立的伦理原则,是一个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直接联系的行为原则。这样的伦理原则,实际上是主张以道德主体的“欲”或“不欲”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点和标准。这种行为原则可表现为外在的标准,也可存在于道德主体的内心。人们依据这样的标准,既能够深切地体会他人之所“欲”,也能够具体地理解他人之所“不欲”;基于这样的原则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则能使自己的行为控制在应当或者适宜的范围之内,或者说,使自己的行为成为道德的行为。同时,这一基本的伦理原则,不仅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的规范作用,也便于人们的道德践履。《论语》中“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的说法,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断定“推己及人”乃为“仁之方”,实际上兼顾到了道德个体的为“仁之方”。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道德主体实际上由不同的道德个体构成。在道德活动中,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为“仁之方”,也各具个性。因此,早期儒家以规范之“仁”表述的伦理原则,仅要求人们在生活中依据这种原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对道德活动中个体的“立人”、“达人”和“勿施于人”的结果提出具体的要求。如何“立人”、“达人”和“勿施于人”,这得从道德个体的实际出发。换言之,儒家所谓“仁者”,标准是在生活中实行以规范之“仁”所表达的伦理原则,这样的原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实行的。如果将“立人”、“达人”之说,与具体的行为后果要求联系起来理解儒家主张的伦理原则,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儒家学者看来,有能力“兼济天下”者可践履规范之“仁”,仅能“独善其身”者同样可以践履规范之“仁”。
早期儒家理解的规范之“仁”,不仅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出了最基本的行为原则,也为儒家关于伦理规范的理论奠定了基石。如前所述,从德性的角度来看,“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推重的人的美德,在这五种德性之中,“仁”乃其他四德之源。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仁”、“义”、“礼”、“智”、“信”则是儒家倡导的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汉儒董仲舒将“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五常”即五种原则或规范。在“五常”中,“仁”是最基本的原则或规范,“礼”则是一个需要辨析的原则或规范。在儒学的演化中,荀子曾主张“隆礼”,强调:“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荀子·大略》)。荀况所论之“礼”,层面有所不同。早期儒家也区隔制度层面之“礼”与伦理道德层面之“礼”。《论语·为政》中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说法。相对于“德”而言的“礼”,内容即多在广义的制度的范围。早期儒家也十分重视伦理道德范围的“礼”。但在早期儒家看来,作为伦理规范的“礼”,从属于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之“仁”。《孟子·离娄上》中曾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的说法。在孟子看来,在伦理道德范围之内,“礼”只是对“仁”、“义”的调节与修饰。换言之,作为规范的“礼”,本质上是对规范之“仁”的补充。但在儒家伦理的思想系统中,“礼”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礼”不仅是德性,同时也是规范。荀子所谓“人无礼不生”的观念,即是对于早期儒家在伦理道德的范围重“礼”思想的发挥与拓展。但是在伦理规范的范围内,不论是“礼”,还是“义”与“智”、“信”,其成立的基础或根据都在于规范之“仁”,是规范之“仁”撑起了儒家伦理规范理论的大厦,并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制定了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今天,人们审视儒家学说的现代价值,肯定早期儒家即已提出了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普适价值的“伦理金律”。论及其具体内容时,则有主张“仁”说者,也有主张“恕”道者。但所论皆不太符合早期儒家的思想实际。当我们考察《论语》中所论规范之“仁”以后,也可以肯定儒家的贡献在于其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或说道德律则。但这种律则或规范的具体内容只能是规范之“仁”,或者说这一律则或规范的内容应当既包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两者间否定任一方面的内容,都无法全面实践儒家主张的道德律则或规范,也不可能全面地揭示儒家规范之“仁”本有的实践功能与理论价值。
三
伦理规范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行为原则、标准,这样的原则、标准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要求与道德意识统一的结果。因此,德性与规范虽有别,但两者并非决然分隔。我们从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两个向度考察早期儒家的“仁”说,应关注二者的差别,也应留意两者的联系。因为在早期儒家典籍《论语》中,“仁”本来就是一个既表述德性的基本范畴,又是一个表述规范的基本范畴。这样的“仁”范畴,不仅使早期儒家从理论的层面论释了人的最高的德性与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广阔的解释发展空间。
后世儒学的发展,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这种过程,使儒学中出现了众多的学术派别与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要而言之,后世儒学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系统:其一是以子思、孟轲以及后来的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学,其二则是以《大学》、《荀子》以及后来的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学。儒学中出现这种学术旨趣大相径庭的思想系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文化背景。但就考察早期儒家的“仁”说对于儒学发展的影响而言,我们也可以将这两系儒学的产生看做是二者在诠释早期儒家的“仁”说时,对“仁”所蕴含的德性意与规范意认同选择有别的结果。思孟一系的儒学,认定“恻隐之心,仁也”,其思想特征是主张人性本善,将人的伦理德性自然化、本体化,专从心性的层面论释人的道德活动基础,实际上从理论上拓展了早期儒家德性之“仁”的观念。荀况的儒学虽肯定“仁义德行”为“常安之术”,但认定人性本恶,强调“隆礼”、“化性”。程、朱所代表的儒学在“所以然”与“所当然”的意义上释理,认为理所表明的“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这样的理,既指事物的自然理则,也包括人的行为规范,理论旨趣在于将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原则本体化,把人的伦理规范、原则等同于“天理”,以“天理”作为人的道德活动的根基。所以这派学者虽也强调“仁”是四德之源,但似乎更重“仁”为德行之据,实际上在理论上拓展了早期儒家主张的规范之“仁”的观念。
思孟一系的儒学与荀况、程、朱一系的儒学在学理方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限于篇幅,对两系儒学学理上的优劣短长,本文难作专门评述。但就后世儒学对早期儒家“仁”范畴的具体诠释而言,若绝对地将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分隔开来理解《论语》中阐释的“仁”范畴,其思想局限则显而易见。这样的思想局限,可在后世儒家对“仁”、“义”和“忠恕”范畴的诠释中得到实证。在后世儒家对“仁”、“义”范畴的诠释中,孟轲以“仁”为人心,以“义”为人路,主张“居仁”“由义”。所谓“居仁”,实即强调德性之“仁”。在孟子的儒学中,“仁”被作为规范的论述较少。而如此释“仁”,是不太符合《论语》中“仁”范畴的本意的,孟轲对“仁”、“义”关系的理解与《论语》也有所不同。汉儒董仲舒对“仁”、“义”的论释似与孟轲的论释相反:“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董仲舒这种“仁主人,义主我”的观念,实际上将“仁”范畴限定在规范的范围,但在《论语》中,“仁”实际上也是一个表述最高德性的范畴。而“义”在《论语》中则不仅是一个表示德性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表述规范的范畴。故董仲舒对“仁”、“义”的理解也不尽符合《论语》中“仁”、“义”的本意。
对“忠恕”的诠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论语》中的“忠恕”观念补充和完善了早期儒家所主张的基本的伦理规范,后世儒家也十分重视对“忠恕”的解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论及“忠恕”范畴时认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则实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对“忠恕”的这种理解,后来受到冯友兰等一批学者的高度重视。冯氏在其《新世训》中专论“行忠恕”。主张“忠恕”既可以作为实行道德的方法,也可以作为普遍的“待人接物”的方法。但是冯友兰把“忠”视为“积极”的“推己及人”,把“恕”则看做“消极”的“推己及人”:“我们可以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忠恕都是推己及人,不过忠是就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就推己及人的消极面说。”[2]冯友兰对“忠”、“恕”的这种理解,似也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主张“仁”与“恕”有别,“仁”是“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后施之者”,“恕”是“以己之欲,譬之于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后施之者”(《四书章句集注》)。二者存在“从容勉强”和“深浅”的差别。冯友兰论释“忠恕”时所持之“积极”说与“消极”说,大概与朱熹的这种观念相关,因为冯友兰也强调“恕”为实行道德的方法。但朱熹与冯友兰对“仁”、“恕”范畴的解析,是否符合《论语》的文本原意,却值得探讨。因为,“忠”、“恕”均可既表示德性又表示规范。对“忠”、“恕”的践履,都可以体现人良好的道德品质,导致人的道德行为。那么,“忠”、“恕”何来“积极”与“消极”的差别呢?冯友兰以“积极”与“消极”的“推己及人”来诠释“忠”、“恕”之别,在学术界影响很大,青年学者中,依冯氏所持“忠”为“积极”的“推己及人”与“恕”为“消极”的“推己及人”这种说法来诠释“忠”、“恕”者尤多。
但是如果从文本的实际出发,认定“忠”是“积极”的“推己及人”,“恕”是“消极”的“推己及.人”。似都存在对《论语》误读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这种观念忽略了《论语》中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的统一,否定了人之道德行为的自律性特征与自觉性特征。儒家非常看重人的主体性,强调德行的自觉。孔子曾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主张行“仁”的前提在于“我欲仁”。孟子也曾说过:“舜明于庶务,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即是强调人的道德行为是自觉地依据于“仁义”德性的行为,而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勉强地去实行“仁义”这样的规范。人具备“仁义”这样的德性,并自觉地在生活中保持这样的德性,才能够自觉地践履“仁义”这样的规范。“恕”是早期儒家所主张的人应当“终身行之”的伦理规范,实行“恕”道,当然也应以人们对于实行“恕”道的自觉与自愿为前提;人们在生活中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时候,其行为也当是主动的自觉的行为。对这样的行为当然不宜以“消极”言其特征。实际上,凡道德的行为,似乎都不应是“消极”的行为,而所谓“消极”的行为,则不应是道德的行为。
后世儒家诠释“仁”、“义”、“忠恕”之类的观念,之所以出现背离早期儒家思想的情形,最重要的原因,似都在于重视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的区别,忽略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的统一,离开《论语》释“仁”的本意来诠释与界定早期儒家的“仁”范畴。这使得后世学者对“仁”范畴的界定始终未能真正地超越《论语》中对“仁”的规定。儒学在经历过长时期的理论拓展之后,历史上有些儒家代表人物终于发现《论语》中对“仁”的界定是无法超越的,意识到《论语》中对“仁”的界定,后人无法改变,也不宜改变。在学术史上,较早具备这种自觉的学者当数北宋时期的程明道、程伊川兄弟。二程兄弟都曾与其弟子们专门探讨儒家的“仁”范畴。程伊川的弟子问“仁”,程伊川的回答是:“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言:‘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爱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谓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二程遗书》卷十八)。程伊川实际上批评了孟轲、韩愈一类学者对儒家“仁”范畴理解的片面与局限,否定了孟、韩等人对“仁”的论释。但是,他并没有对“仁”作出自己的界定。
在如何释“仁”的问题上,程明道的贡献大于程伊川。程伊川只是意识到了孟轲、韩愈一类儒家学者释“仁”的理论局限,程明道则指出了克服孟、韩一类学者的理论局限的正确途径,这就是使对于“仁”的解读与理解,回归到早期儒家经典《论语》中对“仁”的界定。在程明道看来,在儒学中,“仁”范畴是一个最不易把握也最不易表述的范畴,唯有《论语》中对“仁”的界定才是最好的界定:“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二程遗书》卷二上)。“仁至难言”四字表明程颢对儒学的“仁”范畴曾有过长时间的思考探索,了解对“仁”范畴作出界定的理论难度;“故止曰”三字则表明程颢意识到了《论语》中对“仁”的界定,后人无法企及与超越,唯有坚持和依据《论语》中对“仁”的界定去理解“仁”,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儒学中“仁”这一范畴的本质内容。从“仁”范畴对于建构儒家思想系统的作用来看,应当说程明道对《论语》中关于“仁”范畴界定的肯定是颇具理论眼光的。
在现当代学者中,明确肯定《论语》中对“仁”范畴的界定者当推张岱年先生。张先生曾详释孔子的“仁之解说”,认为“仁之本旨,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的“仁”“切近简易,而又宏伟广大;统涵诸德,而不失自为一德”[1](257)。因此,依据《论语》中对“仁”的界说去考察《论语》中对“仁”的其他论述,“则无有不通”。张先生也曾批评后人研究儒学而不识孔子有过关于“仁”的界说的局限与缺失:“后人惟不知孔子自有仁之界说,而谓孔子一生未尝说出仁之确旨,乃自己为仁字另定界说。结果或失之玄虚,或失之儱侗,或失之肤泛,或失之琐碎;且皆于《论语》言仁各条或合或不合,牵强比附,终不可通。”[1](257)张先生对儒学的“仁”之论说,深思熟虑,可谓深解“仁之确旨”。值得我们在解读早期儒家的以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为基本内容的“仁”说时借鉴、咀嚼与思考。
总之,“仁”是早期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范畴。这一范畴既表明了儒家所理解并推崇的最高德性,又界定了儒家所主张的人们生活中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在儒家学者看来,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能够自觉地坚持“由仁义行”,其结果则可为“行仁义”。换言之,一个人若能够具备由“仁”这一范畴所表达的美好德性,实践由“仁”这一范畴所界定的伦理规范,其行为即会是道德的行为,亦即能获取自己圆满的人生价值。在儒家学说中,这种以“仁”范畴表达和论释的人的美德与行为规范及二者统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与思考。因为人的德性与人的德行是统一的。德性是德行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德性,可以导引行为的道德;坚持德行,则可以完善和彰显人的美德,这些观念是早期儒家伦理中最富创意的思想,最具现代价值的理论内容,也是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倡导与追求的伦理意识。因此,我们今天解析评断儒家学说,应当重视早期儒家的“仁”说,并在解析评断中,真实地再现早期儒家所论释的德性之“仁”与规范之“仁”的区别与统一,从而全面地理解儒学的价值,继承和弘扬儒家的“仁”说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论语论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文; 论语·述而论文; 读书论文; 朱熹论文; 大学论文; 道德论文; 孔子论文;
